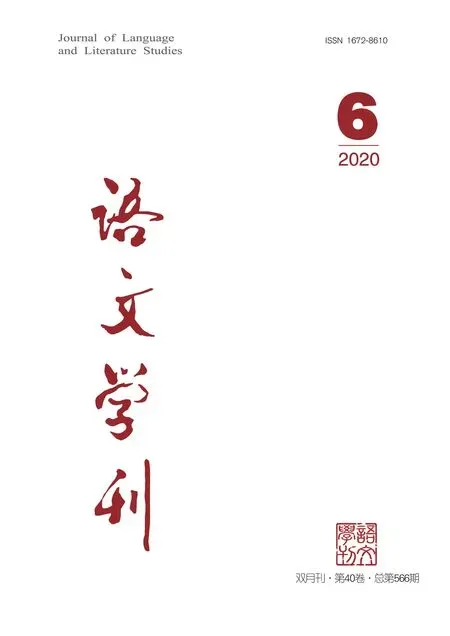《文心雕龙·体性》之“轻靡”辨析
○ 刘慧青 万奇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文心雕龙·体性》篇曰:“若总其归塗,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1]505龙学家们对“八体”解释较为统一,认为此“八体”指八种风格[2],但论及刘勰对“八体”的褒贬态度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五种:(一)赞成“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贬抑“新奇”“轻靡”。如范文澜认为“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义”[1]507,周振甫也说“刘勰对其中新奇和轻靡两体有贬词”[3]255,持此观点的学者还有王运熙、陆侃如、牟世金、林杉等。(二)赞成“典雅”“远奥”“精约”“显附”“壮丽”,贬抑“繁缛”“新奇”“轻靡”。如张可礼认为:“总观刘勰对八体的态度,还是有所轩轾的。他对典雅、远奥、精约、显附和壮丽五体是肯定的,对繁缛、新奇和轻靡三体是否定的。”[4](三)赞成“典雅”“精约”“显附”“壮丽”“新奇”,贬抑“远奥”“繁缛”“轻靡”。如余元桂认为“在肯定典雅、清丽、精约和显附的前提下,刘勰并不反对新奇的风格”[5]。(四)赞成“典雅”“精约”“显附”“壮丽”,贬抑“远奥”“繁缛”“新奇”“轻靡”。如詹锳认为刘勰“言外之意,似乎赞成‘典雅’‘精约’‘显附’‘壮丽’的一派,而不大附和‘远奥’‘繁缛’‘新奇’‘轻靡’的一派”[6]37。(五)对八体持全部肯定的态度。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指出:“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7]95杨明也认为“‘新奇’‘轻靡’两个名目本身并非贬词”[8]114。
综上论之,尽管研究者们对“八体”的看法有较大的异议,但大都将“轻靡”归入贬抑的范畴。那么,在刘勰看来,“轻靡”是否具有绝对的贬义色彩呢?“轻靡”作为《文心雕龙》中重要的理论概念,应该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但很多龙学家们并未对“轻靡”本身做出解释,便直接将其定性为贬义,这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以期能更接近刘勰的原意。要理解“轻靡”在此处之义,应该追溯“轻”“靡”各自的内涵。
一、“轻”的审美内涵
(一)“轻”的语义演变
“轻”qīng,古文:輕。《说文解字》释“轻”曰“轻车也”。段玉裁注曰:“轻本车名。故字从车。引申为凡轻重之轻。”[9]721由“轻”的原义“轻车”,出现了两大引申义。一是装备灵巧、便捷。如春秋时期《国语》中提到“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10]442。由装备灵巧引申为动作的轻盈、轻快,如庾信《和咏舞》中的“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11]。接着又引申到文学范畴,如“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12]151。二是与“重”相对,分量小、数量少。如《国语》中提到“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10]83。从此义又间接引申出多种意义:程度轻,如“重病得愈者,使种杏五株;轻病愈,为栽一株”[13];人的思想轻、不重视,如《韩非子》“听楚之虚言而轻强秦之实祸,则危国之本也”[14];人的行为轻,不慎重,如《左传》“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15]等等。由此可见,“轻”的义项由原来的中性义,延伸出了具有感情色彩的含义。

在刘勰之前,因“轻”用于文学范畴的情况较少,故不宜简单地对“轻”的“文学范畴”引申义下褒贬定论。而就上述所引陆机《文赋》之例而言,张凤翼认为“言拙喻巧,是以拙而用其巧也。理朴辞轻,是以朴而运其逸也”,许文雨说“或拙词孕以巧义,或真情缘以轻辞”[12]152-153,可以看出,此处的“轻”与“巧”互文,或释为“逸”,或包孕“情”,大体上呈褒义。
“轻”在《文心雕龙》之前的语义和褒贬情感态度的变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上图,此后“轻”的释义几乎都可以从上述的语义中找到源头。通过上述爬梳,应有利于我们理解《体性》篇中“轻”的审美内涵。
(二)“轻靡”之“轻”的审美内涵
“《文心雕龙》是有严密体系的书”[3]1,各篇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为了理解《体性》篇中“轻靡”之“轻”的内涵和情感态度,就要立足全书。“轻”在《文心雕龙》共出现24次,内容并不一致,除“轻”的本义未涉及,其他语义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感情色彩意义出处篇目中性分量小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指瑕》动作轻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程度轻《丧服》举轻以包重《征圣》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镕裁》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丽辞》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序志》文学范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明诗》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哀吊》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奏启》数穷八体……八曰轻靡……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壮与轻乖《体性》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时序》褒义人的个性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 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体性》仲宣轻脆以躁竞《程器》贬义人的行为人的思想周礼曰师氏诏王为轻命。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诏策》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议对》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指瑕》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知音》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
上表将《文心雕龙》中的“轻”按情感色彩分为两大类。其中,“轻靡”之“轻”属于文学范畴,与“轻绮”“轻清”“轻澹”密切相关。
《明诗》篇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1]67此处之“轻”表现为“力柔”,即风格柔弱。“柔”是指西晋诗歌不如建安诗歌一样慷慨有力,西晋群才不像建安诗人那样磊落使才。此处的“轻”,刘勰并未明确表示自己的褒贬态度。另外,刘勰在《体性》篇中提出“壮与轻乖”,周振甫根据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解释,“壮和轻,是指气象的刚柔说的。”[3]255“刚柔”在文中共出现5次,“然才有庸隽,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1]505-543,刘勰对“刚柔”的态度并没有偏颇,一直强调“随性适分”。所以,“轻”在风格上体现为与“壮”相对的“柔”,应无贬义。
“轻清”之“清”是刘勰钟爱的审美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共出现47次。《说文解字》中释曰:“清,朖(朗)也,澂水之皃。”段玉裁注:“朖者,明也。澂而后明,故云澂水之皃。”[9]550因此,“清”可以理解为清明、朗丽。“轻”与“清”连用,应指文辞轻便、朗丽,给读者以流畅的阅读感受。《哀吊》篇“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范文澜解释“轻清”为“下笔绣辞,扬手文飞”[1]251,王运熙释为“笔调清新”[16]106;《奏启》篇“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周振甫解释“轻清”为“文辞轻快”[3]217,王运熙也将其释为“轻快清朗”[16]214。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提到“轻唇利吻”,就指出轻便明快的语言更有利于情感的表达。所以,“轻”的表达方式体现为“明快”“轻快”,应无贬义。
“清澹”之“澹”在《文心雕龙》中常常与“淡”字混用,如《时序》篇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与《镕裁》篇中“ 权衡损益,斟酌浓淡”含义相同,即与“浓”相对的“淡”。又《时序》篇中“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之“澹”,龙学家们翻译为“清淡”“恬淡”“虚淡”,释义略有差别,都将此处的“澹”与“淡”等同起来。所谓“正始馀风,篇体轻澹”,即诗歌风格在“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建安诗风后,渐趋于平淡;“轻澹”是刘勰形容正始诗风的。在《明诗》篇中,“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可见贵黄老,尚虚谈的玄言思想已被引入文学创作;那么,“轻澹”的“轻”还表现为“轻虚”,指向一种自然悠远的境界。因此,“轻”在内容上表现为“平淡”“轻虚”,应无贬义。
综上所述,“轻靡”之“轻”的审美内涵就可以概括为风格上的“力柔”“轻快”,内容上的“轻虚”“平淡”。因此,在《文心雕龙》中,当“轻”属于文学范畴时,应无贬义的情况。
二、“靡”的审美内涵
(一)“靡”的含义界定
“靡”为多音字,当读mǐ时,《说文解字》释曰“柀靡也”,段玉裁注“柀靡,分散下垂之皃”[9]583。因此,“靡”的本义应为“分散”“倒下”,如《左传》中“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17],“靡”就指本义“倒下”。另段玉裁又指出“凡物分散则微细”[9]583,由本义“分散”引申出“细腻”“细密”,如《方言》“‘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郭璞注‘靡,细好也’”[18]。由“靡”之“细密”义还可引申为“靡丽”之意[9]583,如《汉书》“‘众庶莫不辍作怠情,靡衣媮食,倾耳以待命者’,颜师古注曰‘靡,轻丽也’”[19],这样,“靡”就有了“华丽”“美丽”之义。段玉裁还指出“靡”可以与“亡”或“无”字组成双声字,因此“靡”又可释为“无”[9]583,如《诗经》“‘有怀于卫,靡日不思’,‘靡’注释为‘无’”[20]。这是“靡”由原义所引申出的几个主要语义,可以看出,“靡”读作三声时的感情色彩似乎是没有贬义的。
“靡”读“mí”时,意义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力古汉语字典》对“靡”字的解释,除上述段注中提到的,又引申出以下两个主要语义:一是损害。如《国语·越语下》云:“王若行之,将妨于国,靡王躬身。”韦昭注:“‘靡’,损也”;二是浪费,奢侈。如汉贾谊《论积贮疏》:“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21]等。“靡”读作二声时,与我们今人理解的“靡”更为接近,贬义较多。

综上,“靡”字在不同的字音状态下,有不同的含义和感情色彩;《文心雕龙》中“靡”字的含义,大都包含于上述义项之中。
(二)“轻靡”之“靡”的审美内涵
“靡”在六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审美概念。与“轻”相同,要想对“轻靡”之“靡”做出较客观、全面、正确的解读,也应该立足于全书,对“靡”进行分类,找出与“轻靡”之“靡”相关的内容,来理解其审美内涵。《文心雕龙》中一共出现33处“靡”,使用情况如下表:

感情色彩意义出处篇目中性不、无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原道》祝币史辞,靡神不至《祝盟》夏商以前,其词靡闻《诔碑》金石靡矣,声其销乎《诸子》阴阳莫忒,鬼神靡遁《论说》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夸饰》言必鹏运,气靡鸿渐《夸饰》令章靡疚,亦善之亚《指瑕》倒下→影响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正纬》习亦凝真,功沿渐靡《体性》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时序》顺适字靡易流,文阻难运《练字》(縻)被系的犯人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谐讔》细密、细致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铨赋》张衡《七辨》,结采绵靡《杂文》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封禅》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体性》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才略》音调(柔、悦、和)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明诗》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乐府》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声律》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章句》褒义文学审美概念丽《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辨骚》《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乐府》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诔碑》负文馀力,飞靡弄巧《杂文》《封禅》[丽]靡而不典《封禅》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章表》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句》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时序》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才略》文学审美概念数穷八体……八曰轻靡……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壮与轻乖《体性》
对“靡”的含义及感情色彩进行分类后,发现全书中的“靡”如杨明所说的“《文心雕龙》诸篇中靡字,均非贬词”[8]115。表中前四者语义与“轻靡”之“靡”相差较大,暂且不论。
首先,《文心雕龙》中“靡”释作“密”,甚至与“密”同时出现的情况共有5处。《铨赋》篇“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中“靡密”一般都解释为王粲作赋“文辞细密”;《丽辞》篇中刘勰提及“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后,以王粲作为反对的典型,可以看出其“用事细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高度赞扬王粲赋文辞与用事之“密”,如《铨赋》篇称王粲的赋为“魏晋之赋首”,《才略》篇又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等等。除王粲外,刘勰评价庾亮表奏“靡密以闲畅”,是“笔端之良工”,充分肯定他文辞的“靡密”。“靡”不仅是文辞、用事细密,而且还表现为“结构细密”。如刘勰在《封禅》篇论及扬雄的《剧秦》是模仿司马相如而做的,用怪异躲闪的话,兼写神怪的事,但是也有其优点,“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也就是称赞扬雄《剧秦》细密的结构。可见,“靡”当“密”解,主要指文辞、用事、结构等形式的“细密”,从中能够明确看出刘勰对“靡密”形式的肯定态度。另外,张衡与班固之例在后文做解释。
其次,《文心雕龙》中与音调有关的“靡”出现了4次。《乐府》中“音靡节平”的“靡”与“平”的意义应该相当,大多数学者将“平”译为“平和”“平淡”,那么“靡”不应为贬义,此句释作“音调柔靡,节奏平和”[16]较符合原义。所以,此处之“靡”应与之前“轻”有相同的意义,即力量上的“柔”。《声律》篇“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中的“累累如贯珠”出自于《礼记·乐记》的“累累乎端如贯珠。”郑注:“言歌声之著,动人心之审,如有此事”[22],此处“靡”的解释应如王运熙的“声音美妙柔美”和王元化、戚良德的“声音动听”等,这就使“靡”有了偏褒义的理解。《章句》篇“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对于“靡曼”,龙学家们的解释大同小异,即“柔美舒缓”“柔弱细长”。“靡”为“柔美”或“柔弱”,虽感情色彩略有差异,却无明显的贬义色彩。《明诗》篇“流靡以自妍”则是强调了音韵的和谐之美。综上,《文心雕龙》中与音韵有关的“靡”,包含“力量柔弱”“声音动听”“音韵和谐”等义,感情色彩或偏褒义,或为中性,没有贬义的情况。
再次,“靡”释为“丽”,全文一共出现9处,可见两者关系密切。文学从起源时歌唱劳动,到进入礼仪时代歌颂心怀天下之志,由“质朴”趋向“雅丽”,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刘勰处在尚“丽”的时代背景下,对“丽”也应持肯定态度。《文心雕龙》全篇以骈文写作,其特点是“俪”,对偶句式,形式优美,符合六朝时期文人审美的总体倾向;刘勰专设《丽辞》篇,指出“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1]589,强调文采和骈俪的重要性。但是,“丽”是“丽则”,有度之“丽”,而不是“丽淫”,这才是刘勰所提倡之“丽”。
“绮靡”乃汉魏以来的常用语,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注“绮靡,精妙之言”,张凤翼注“绮靡,华丽也”[12]152-153。《文赋》之后,“绮靡”一般是指“华丽”,它在诗中表现为“丽”辞,是“缘情”的必备条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用了“绮靡”。《辨骚》篇中指出“《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范文澜和戚良德指出此处“绮靡”在唐写本中作“靡妙”,释作“美妙”;王运熙和周振甫等人的通行本中作“绮靡”,译作“绮丽细腻”。因此,“靡妙”或“绮靡”都是指为情服务的“美”辞、“好”辞。《时序》篇“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中的“清英”谓“清美”,“绮靡”谓“柔美”,“结藻”指辞藻,“流韵”指作品的声韵;这样,“绮靡”就超出“文辞”范畴,表现为音韵之美,这就与之前论述的音调之“靡”有关了。又因《时序》中的“绮靡”与“清英”相对应,所以该“绮靡”不仅表现为“柔”,更突出“美”,应为偏于褒义的感情色彩。
“靡而非(不)典”全书中共出现两次,一处出自《乐府》篇“《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部分学者认为“丽”“靡”与“经”“典”意义相反,所以是贬义。“宗经”自然是刘勰十分推崇的,但“辨骚”同样位于“文之枢纽”部分,“辨的目的是为了求‘变’,为了探求文‘变’之道,所以说‘变乎骚’”[23],说明刘勰很重视文学的发展变化。“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词”“故能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这些溢美之词,充分体现了刘勰肯定从经书的“典雅”到楚辞的“靡丽”之变。《乐府》中“靡而非典”是从经典诗文到郊庙歌的一种新变,刘勰只是在客观叙述文体的演变过程,并无贬斥之意。第二处是《封禅》篇中的“封禅[丽]靡而不典”,范文澜、王元化、戚良德将此句写为“丽而不典”,王运熙、周振甫、林杉则将其写为“靡而不典”,这应该可以证实这句中“靡”“丽”同意;同时,刘勰评价司马相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赞美了他的文采;还指出司马相如的《封禅》是后代班固、扬雄学习的典范。那么刘勰说“封禅[丽]靡而不典”不应为否定的态度,“靡”自然也非贬义的。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靡”与“典”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刘勰对“靡”也非持贬义态度。
《诔碑》篇的“辞靡律调”,是刘勰对傅毅诔文特点的赞扬,“辞靡律调”可释作“文辞精美、音律和谐”;《章句》“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中,“明靡”和“清英”的作用是使“句无玷”“字不妄”,自然无贬义色彩;《才略》篇“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清靡”与“辨切”是曹摅长篇和季鹰短韵各自的优点。《杂文》篇“负文馀力,飞靡弄巧”,王元化将“靡”释作“美好的文辞”、林杉作“华丽的文辞”、王运熙释作“丽”。《章表》篇“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指魏国初年的表章一般只陈述事实,无法达到文采华丽的程度。接着,刘勰在《章表》篇肯定了孔融《荐袮衡表》“气扬采飞”,诸葛亮《出师表》“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虽然二表有华丽和质朴之不同,但都是杰出的表文。因此,表文要“美”,那么文辞“靡丽”是必不可少的。由以上可以看出,“靡”释为“丽”“美”,并不是贬义的,刘勰对它是持肯定态度的。
由上所述,“轻靡”之“靡”的审美内涵应为文章形式的“密”“丽”,风格上与“轻”都有“柔”的特点。因此,在《文心雕龙》中,当“靡”释作“密”“丽”或与音调有关时,应该是具有褒义色彩的。
三、轻靡:褒乎?贬乎?
(一)从特点描述析“轻靡”褒贬
刘勰在《体性》篇中提出“八体”之后,对“八体”各自的特点进行了阐释:论及“轻靡”是“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黄札曰:“辞须蒨秀,意取柔靡,皆入此类。江淹恨赋,孔稚圭北山移文之流是也”[7]96。那么,“轻靡”的特点是文辞表现秀美,情志表达力柔,这就对应了前文分析的“轻”和“靡”二范畴。
另有一些学者将“浮文”“弱植”“缥缈”“附俗”分别释为“文辞浮华”“情志柔弱”“内容虚浮”“迎合世俗”,认为刘勰对“轻靡”持否定态度,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先论“缥缈”。与《文心雕龙》成书时间相近的《文选》中说“群仙缥眇,餐玉清涯”,李善注“缥眇,远视之貌”[24],“缥缈”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意境悠远美;唐代司空图的《注愍征赋述》云:“其雅调之清越也,有若缥缈鸾虹,譻譻嫋空”[25],此处的“缥缈”形容声音清越悠扬。那么,刘勰笔下的“缥缈”应与二人相差不远,既可以指意境的高远,又能指音韵的悠扬。次论“浮文”。在《文心雕龙》中,“文”多指文辞、文采,通过上文“靡”的部分用例分析以及《声律》篇,可以发现刘勰较为重视“文”与“音”的关系,“音”是检验“文”是否“美”的一个标准。因此,“浮文”在形式上可以表现为“浮音”,即“音韵飘逸”,应与“缥缈”一致。再论“弱植”。《楚辞·招魂》云:“弱颜固植。”王逸注:“植,志也。”[26]很多学者据此将“植”释作“志”。因“壮与轻乖”中的“壮”和“轻”,表示作品的“刚健”与“柔婉”。那么,“弱植”可以理解为“情志柔婉”。刘勰认为文势有强弱、刚柔、轻壮之分,但轻壮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别。刘勰在书中既有对“壮”的肯定,如《檄移》篇“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也提到了“轻”运用成功的实例,如《明诗》篇论及《古诗十九首》中的《孤竹》篇“婉转附物,怊怅切情”。作品或表现出“刚健”的风格,或表现出“柔婉”风格,都是诗人的一种选择,只要运用得好,这两种风格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末论“附俗”。文学不能总是“音韵飘逸”“意境高远”,还应“附俗”,即文学必须植根于世俗,要为现实服务,形式上可以“缥缈”,但内容上不能虚无。因此,“浮文弱植,缥缈附俗”应是刘勰对于“轻靡”的特点和要求的客观表述。
(二)从“风格”与“个性”关系论“轻靡”褒贬
《体性》篇论述的是“风格”与“个性”的关系。刘勰列举了十二家来证明“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其中“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之“轻”,是形容潘岳的个性的,此处之“轻”对于“轻靡”之“轻”的理解具有重要作用。戚良德释此句为“潘岳聪明随意,所以作品机锋突出而声韵畅达”[27],将“轻敏”单释为“轻快敏捷”,这是符合刘勰本意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表达对潘岳创作才能的赞赏,“潘岳敏给,辞自和畅”(《才略》),“及潘岳既作,实锺其美”(《哀吊》),钟嵘在《诗品》中同样给予潘岳高度的评价“其源出于仲宣。《翰林》叹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28]174。曹旭释“翩翩奕奕”为“轻捷优美貌。此谓李充《翰林论》曾赞叹潘岳诗文词如飞鸟一般轻捷美好”[28]179。因此,潘岳个性“轻敏”之“轻”表现出的文学风格应为“轻快”,这与前文释“轻”的风格表现是一致的。除潘岳外,刘勰在《体性》篇中还提到“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此处虽未有“轻”,但《程器》篇曰:“仲宣轻锐以躁竞”。那么,锐即为轻锐,将“轻”与“锐”相组合,很明显“轻”即为王粲“轻快”的个性,进而表现出“颖出才果”“轻快锐利”的文学风格。
刘勰论述“靡”时,列举的作家首先是班固,“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注:“《后汉书·班固传》曰:‘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此雅懿之徵’”[7]97。“雅懿”可理解为“雅正温和”。班固“雅正温和”的个性影响了文章“裁密而思靡”风格的形成。“裁密而思靡”根据《后汉书·班固传论》“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29]之句进行理解,即班固的文章风格为:文辞周密,叙事详尽。因此,研究者们对于此处的“靡”,一般都将其释作“细致”。那么,刘勰用“靡”形容班固的文学风格,与其“雅正温和”的个性相对应。其次,具有“靡”文学风格的代表作家还有张衡。刘勰在《杂文》篇评价张衡《七辨》“结采绵密”;在《体性》篇又曰:“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刘勰经常以“淹通”“通赡”“博雅”等溢美之词来评价张衡,因其个性之“博通”,表现出文辞“绵密”的风格特点。
在《体性》篇中,除两次提及“轻靡”之外,又在列举作家“个性”与“风格”关系时分别提及“轻”“靡”。虽然“轻”论述个性,“靡”论述风格,但个性与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以上所举的四个实例可以看出,作家优质的个性品质正向影响着他们文学风格的形成。因此,刘勰对“轻靡”的态度应是肯定的。
(三)从八体总述看“轻靡”褒贬
如果刘勰对“轻靡”的态度是贬义的,那么就无法理解他之后所说的“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1]506。“殊”和“合”即“相反”与“相成”,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经常提及的辩证法命题,如《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30]。刘勰用形象化语言来描述“八体”,指出这八种风格虽然不同,只要彼此融会贯通合于一定规律,那么这八种风格就可以像车辅凑合一样,相反相成。可知刘勰对“八体”的态度并无差别,都是他所肯定的。刘勰还指出“八体屡迁”。“人之为文,难拘一体,非谓工为典雅者,遂不能为新奇,能为精约者,遂不能为繁缛。”[7]96诗人作文章,很难只有一种风格,好的诗人对于看上去完全相反的两种的风格也能运用自如。《定势》篇同样印证了此观点:“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1]530这符合刘勰贯穿于全书的“折中”思想;《通变》篇也说“櫽括乎雅俗之际”,学习者在学习雅正的基础上,对俗的一面也需掌握并加以运用。轻靡者“缥缈附俗”就有“俗”的因子。
当然,“八体”并不是指所有的作品只有这八种风格,它们是刘勰从众多风格中概括出来的。这八种风格类型可以组成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风格[6]9。即使一部文学作品,往往也不局限于一种风格,如“隐秀”的“隐”可能接近远奥的风格,“秀”可能接近新奇的风格,但不能认为“隐”就是远奥,“秀”就是新奇;或者一些作品风格可能是中间型,介于典雅与新奇之间,介乎壮丽与轻靡之间……。文章不仅因个性、时代、文体等会造成风格上的差异,而且还会因作者个人运用情况的不同而成败各异。轻靡运用得好,可以产生流美的效果;典雅运用得不当,也可能表现得刻板陈旧。
总之,刘勰对“八体”总的倾向应是:八体并陈,全部肯定。那么,“轻靡”是“八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刘勰经过客观总结后提出并赞成的一体。刘勰是将“轻靡”做褒义词来使用的,并无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