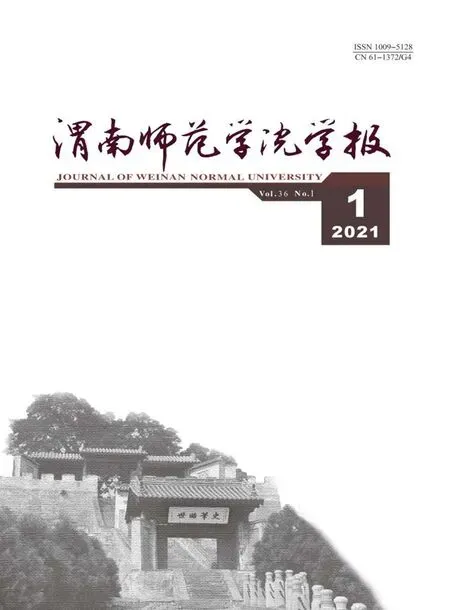汉武帝年号与封禅关系探析
郭 培 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年号纪元是汉武帝朝重大的纪元事件。《史记》在《孝武本纪》《封禅书》两部分均做了记载,内容大略一致:“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1]460-461这段就是诸家试图解开纪元起始问题时常提到的引文。
年号纪元问题,不仅关系纪年方式的变革,更是当时去秦兴汉新制度建立中的重要一环。封禅祭祀动摇了袭秦旧制的传统,为年号纪元的施行做出准备,而天瑞命元和历法推算两种历法方式的修定,则共同完成了汉代全新的正朔、服色制度的确立,真正实现了汉武帝所追求的天命归一的政治统治目的。因此,将改元年号问题投置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追寻纪年变革原因、目的,既可以使得诸家关于“年号”纷争的疑点得到澄清,在一定程度上对“太初”始定年号的论断作补充,又能通过封禅与年号、历法改革等事件进行关联的立体性考察,揭示汉统治者从五德终始到天命归一观念的变革,从而实现真正地改朝换代,建立大汉一统的王朝政治。
一、年号纪元纷争的几种代表性看法
汉武帝即位54年,其间以多个年号纪元。《汉书·律历志》曰:“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乙酉,距初元七十六岁。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汉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故《汉志》曰岁名困敦,正月岁星出婺女。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各四年,后二年,著《纪》即位五十四年。”[2]1023而对于初始年号的创制,大致有建元说、追命说和班改说(班固修改说的简称)三种看法。
第一,建元说。建元是武帝的第一个年号,自此以后所有的年号,从建元开始。持此观点者有唐代张守节、颜师古,今人陈直等。《史记正义》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数年,至其终。武帝即位,初有年号,改元以建元为始。”[1]461张守节以景帝、武帝两朝比较而强调汉武帝朝开始有年号,而年号自武帝即位便设置了。《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2]156认同此说。今人陈直则从出土文物力证汉武帝年号始于建元,《汉书新证》曰:“《日知录》及《廿二史札记》,皆以武帝建元、元光两年号为追记者,其实不然。《筠清馆金石记》卷五、三十九页,有‘高阳右军,建元二年’戈。杭州邹氏藏建元元年砖。西安南郊曾出土有‘建元四年长安高’陶尊(现藏西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又《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一、一百四页,有元光二年尺,其非追记可知。”[3]25而这一看似铁证的论断,却遭到裘锡圭先生的驳斥:“《汉金文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书所著录汉器中记元朔、元狩、元鼎年号诸器,皆为伪作,字体卑弱,与武帝时真器迥然有别。”[4]55事实上,《史记》中没有明确年号标记时间的书史特点,直接证明了年号不当始于建元。
第二,追命论。追命论,即指年号是追命前事后加而来的。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武帝初年未有年号,依然是按着前朝数字纪年的方法,如高祖元年、二年乃至十二年,并没有年号纪元。明人顾炎武指出:“是建元、元光之号,皆自后追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号也。”[5]653既然武帝朝即位初,是数字纪年,没有专属的年号。但武帝朝年号起于何时?从何年追命?梳理下来,大致有元鼎、元封、元狩、太初4种说法,现将代表人物观点胪列于下:
其一,元鼎说。此派认为,年号始于元鼎四年(前113),之前年号皆从元鼎四年开始追加。北宋刘攽曰:“《封禅书》云:‘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所谓‘其后三年’者,盖尽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宝鼎,又无缘先三年而称之,以此而言,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实年号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则始有诏书矣。”[6]1011南宋吴仁杰亦说:“年号起于元鼎四年,刘说是也。”[6]1011可知,刘、吴皆认为元鼎以前的年号是追加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曰:“时虽从有司之议,改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三元为元朔,四元为元狩,至五元则未有以名,帝意将有所待也。明年宝鼎出,遂改元为元鼎,而以是年为元鼎四年(前113)。然则谓年号起于元鼎固然,谓元鼎为后来追改者,亦不误也。”[5]1619泷川进一步指出年号起于元鼎,而元鼎四年(前113)之前的年号追加而成,故提出年号起于或追改于元鼎的两说之法。
其二,元封说。清人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曰:“《史记·封禅书》云,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此武帝第五改元之三年也。次年得鼎,始改元元鼎也。《兒宽传》:“宽从东封泰山,还上寿曰:‘将建大元本瑞,登吿岱宗,发祉闿门,以候景至。’苏林注曰:‘太元,太初历也。本瑞,谓白麟、宝鼎之属也。’是元封以前,建元等号,皆从后补书无疑。又第三为元朔,史记不载,而以元狩为三元,恐误脱也。”[7]460周寿昌引《兒宽传》和“元朔”年号脱误,提出年号始于元封,于此开始追加以前年号。
其三,元狩说。持此说者,有清人史学海、赵翼及今人顾颉刚先生。史学海《汉书校证》释“三元”曰:“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学海按,《封禅书》作‘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本书《武纪》‘三元’为‘元朔’,而《志》与《史》皆不数者,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元朔非天瑞也。窃疑初时追命,前元本无元朔,盖建元六年,元光是十二年,故三元即为元狩,至元狩十年得宝鼎,追前四年,改为元鼎,并将元光七年改为元朔,故太初以前皆六年而改元。刘攽谓年号之起在元鼎,非也,年号起于元狩耳。”[6]318史学海认为元狩符合天瑞纪年,而始以之纪元,并以之追加前元。元狩十年(前113)获得宝鼎后,又以元鼎纪年,元狩七年至十年亦以元鼎追加。赵翼《廿二史札记》曰:“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据《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畤。以后则但云其后,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后年耶?”[8]38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论述“汉武帝的郊祀于求仙”时,亦指出:“中国的皇帝有年号……这事的创始,由于武帝的获麟。”[9]17
其四,太初说。按《汉书·律历志》的记载,以上提及的年号,在汉武帝朝的顺序为元狩、元鼎、元封,元封最后。《律历志》曰:“汉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2]1023可知,“前十一月”是太初元年以前的年号称呼,若元封时已有年号,何不以年号称?元封最后尚无年号,况前时年号?辛德勇先生指出:“‘元封’这一年号,应当一如元鼎以及更早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诸年号,只是用于追记往事。”[10]57“‘太初’年号也应当是在这一年五月间与《太初历》一并启用。”[10]69“太初”元年始有年号,并以此追加前事的提法当允。
第三,班改说。武帝三元的年号应该是“元朔”,诸家论说却是“元狩”。班改说主要针对“元朔”年号而论。钱大昕曰:“元光之后,尚有元朔,则元狩乃四元,非三元,班史改以为‘今’,无‘三元’字,盖得之矣。言建元、元光而不言元朔者,‘建’以斗建为名,‘光’以长星为名,皆取天象,若元朔纪年,应劭解朔为苏,取‘品物苏息’之义,不主天瑞,故不及之耳。”[5]1619日本学者亦发现《汉书·郊祀志》对此处所作的改动,泷川资言曰:“《汉志》改‘三元’作‘今’。”[5]1619钱氏以“朔”为“苏”,泷川以“今”作“三”,事实上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建元说和追命说的诸多提法本身存在抵牾处,年号当从太初年始创制。辛德勇先生已就这一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将“年号”事件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追寻其发生的原因,以及期待的最终目的,会使这一问题立体起来。既能解决诸家纷扰的“元朔”之疑,又能对“太初”年号的制定从制度改革的角度进行一些补论。
二、汉世年号改元的制度背景
诸家在论及“改元元号”问题时,都围绕“有司言”这句话的时间、语句及其可能出现的历史背景作了一番研读,并得出一家之言。但鲜有注家对“年号纪元”的原因进行探讨。武帝朝为什么要改元,其改元的年号方法尽如有司所言的“天瑞”命名吗?事实上,改元年号不仅仅是纪年事件,更是关系重大的政治事件。
武帝朝之前,汉文帝、景帝朝都有改元事件。文帝朝改元之事,发生在文帝十四年,《史记·孝文本纪》曰:“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1]429可知文帝时,通晓五德终始说的张苍和公孙臣就文帝朝是土德还是水德,进行了一次交锋。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五德之下的符应不同,正朔、服色、制度亦不同。《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1]1366“五德”不同,符应有异。秦获符瑞为黑龙,遂以水德命之,而正朔以冬十月为年首,服色上(尚)黑,制度以六为名。而这些正朔、服色、制度是受命帝王合德于天的表现。《史记·历书》有言:“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1]1256受命帝王兴国,则改正朔、服色、制度,以合五德。孝文朝的这次论证,暂由张苍获胜,但“十五年,黄龙见成纪”[1]430。黄龙乃土德之瑞,于是文帝召回公孙臣,欲以土德施行,使“(公孙臣)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1]1381。文帝朝见土德之瑞,先有改元之事,即十七年“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1]430,但服色、制度尚未完成,就遇到方士新桓平因假玉杯遭诛杀之事[1]430,“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1]1383。新桓平的事情,让文帝朝的改元有始却无终。景帝朝有两次改元,分别以中元、后元别之,但并未言及原因。而武帝即位初,天下安宁,“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但“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而遭到窦太后的反对以终,事见《史记·孝武本纪》,可知在景帝朝亦未完成正朔服色制度之改。
武帝朝廷议改元之事,《汉书·律历志》曰:“上乃诏宽(兒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2]975武帝与兒宽的对话,说明武帝朝改正朔、易服色,与孝文、孝景帝朝一样,为昭示“受命于天”。而此时已是汉兴百二岁矣,武帝朝依然在正朔、服色、制度上沿袭前代。所以司马迁、壶遂、公孙卿等人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司马迁等人受命造汉历,为的是改变历纪坏废的现状。
由此可见,从孝文帝、景帝,至武帝,都在践行同一个使命,即改正朔服色制度,以明受命于天,实现真正的改朝换代。《汉书·律历志》曰:“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2]974高祖时百废待兴,袭用秦制,而文帝、景帝朝虽有改元之事,但并未完成,直到武帝时的汉历改革,《史记·孝武本纪》曰:“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1]483此时的汉历已经完全区别于秦制了,前文已言,秦以十月为岁首,色上黑。修改后的汉历,则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以五字行事,并更定此年的年号为“太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汉历修定时间为“夏”,秦制自“正月”十月至汉历“夏”这一时段,严格来说“也是出自稍后追记”[10]69。按着正月为岁首的汉历规制,正月以前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月并不能按汉历计算,应该算“一段过渡时期”。[10]70可以说,自太初元年(前104)开始,汉朝开始实行全新的正朔服色制度。这次汉历的改革真正实现了有汉以来独立制度体系的确立,体现了王权真正受命于天的使命。
三、封禅破旧制基础上的汉历改革
旧制废除,汉历新建,“太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纪元的年号。那么,此前的纪元是如何追命的?
武帝朝改历事件,因意义重大而载入史册,《史记·历书》和《汉书·律历志》均有记载。相较而言,《汉书》详于《史记》,但二书都记录了这次改元的年号为“太初”,且都有“其(《史记·历书》有‘更’)以七年为元年(‘太初’见于《史记·历书》)”的记载。“七年改元年”这也是汉袭秦制的表现。《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依水德建制之事。除定岁首、易服色之外,还提到“度以六为名”,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张晏语对此做解释:“张晏曰:‘水,北方,黑。水终数六,故以方六寸为符,六尺为步。’”[1]238指出数“六”是水德之符。泷川资言《考证》则引《始皇本纪》为证:“《始皇本纪》‘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5]1588从两位注释可知,秦时纪年以六而数,每六年为一纪,汉袭秦制,可知在武帝改历之前,也遵从以六为纪的纪年规律。故“七年改元年”,当指太初元年实乃前元之七年。前六年共同使用一个年号。
关于“太初”年号,《汉书·律历志》曰:
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2]975
这一段叙述了“太初”年号的来历。清人王元启从推步之术指出班氏于此间之误,其言:“历家推步之术,代有不同,甲曰焉逢,寅曰摄提格,从古更无异说。况《太初历》史公手定,不应年岁甲子尚有错记。《汉志》云‘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元封七年,复得焉逢摄提格之岁’,则是岁之为甲寅,班氏亦既明知,而其下复有‘太岁在子’之云,前后自为乖异,必误文也。”[5]1450王引之亦指出班氏此处的自相矛盾,其曰:“《汉志》‘太岁在子’当作‘太岁在寅’,后人改之也。太岁在寅曰摄提格,上言摄提格之岁,则下当言太岁在寅。”[5]1450班氏于此处的记载必当有误,此事已无疑。但从两位注家的解释可知,班氏在用历法推算时出了错,抑或班氏推术无误,但记录有误,而出现了这样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正是这个错误,可以更加确定此“太初”年号是推算出的合于“星度”的新正。可知,历法推算是武帝朝改元的一种重要方式。
《史记》中还记载了另一种改元的方式,就是上文提到的那段热议语段,即“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关于天瑞命年的记载,《史记·封禅书》曰:“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有司言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1]1398-1399这两段话中都是“有司言”的形式出现,似乎都是一种陈情建言,前言以天瑞命年,未见武帝之诏“可”;而后天降宝鼎,亦是祥瑞,故有司依然建议天瑞命名,故有“鼎出为元鼎”之言,而“今年”行封禅大典,更是盛世一桩,当以元封名之。若无武帝诏“可”,此处恐与前言“天瑞”纪年者一样,成为争议热点。但清人梁玉绳对这段文字的考证,得出了新的证据,其曰:“‘有司言’以下十七字当在前‘群臣更上寿’句下,错简也。”[5]1637梁认为,“有司言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句,当放置在“群臣更上寿”句下,这样连缀成篇,其上下文当是: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有司言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如有望,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此段引文据中华书局1982年版《史记》与梁玉绳言合成的文字。)
这里除了讲述封禅的经过,还提到了大赦天下、赐民酒食布匹、无税之福。梁玉绳所说错简之语,至班固时已经补齐。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下诏改元为元封。语在《武纪》。[2]1236

《汉书》的文字与《史记》略有差异,内容相当。值得注意的是改元为元封元年之语,很容易使人有年号始于“元封”的判断。但细读后,会发现,“十月为元封元年”依然承袭的是秦以十月为岁首的旧制,并未真正实现正朔制度的改革。诏书颁布在夏四月,而诏定以去年十月为岁首,事实上也属于追记性质。辛德勇先生持此观点:“由年初之冬季到夏季四月,时间已经过整整半年,其属于事后逆推追记的性质。”[10]257而这次有司建言的年号命名方式,事实上也是一贯提倡的“天瑞”命名。缙绅士大夫进言武帝封禅时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1]1355封禅前所显现的符瑞,即为宝鼎,《汉书·郊祀志》曰:“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体,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2]1233符瑞现,而祭祀于郊,这里是封泰山,禅肃然山,是以合明应,而示帝王受命于天的重要行动。因此,在上天下降符瑞之兆后所行封禅,并以之为年号,也是天瑞纪年的方式,各年号依照天瑞而定,按照有司所建言,即一元曰建元,钱大昕所谓“‘建’以斗建为名”也;二元曰元光,以长星为名;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这里的“三”元,周寿昌以为脱“三元元朔”而误将四年元狩写成三元元狩;钱大昕对比《汉书》,发现“三元”替换为“今”,而认为是有司言错,班固有意改之。事实上,司马迁是封禅典礼的参与者。《史记·封禅书》曰:“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1]1404司马迁随从武帝参与了巡祭诸神名川,亦入寿宫侍祠。但不同于有司专记礼节,司马迁更多地记录自己参与封禅过程中的言行。而且,既然清人钱大昕推测班氏改“今”,说明班固见到的也是“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这句话,自然,周寿昌“误脱”说不成立了。既然班固看到《史记》原本是“三元”,那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司马迁就是这样记录的。因为所获得一角兽被视为祥瑞,有司遂建言以之命年号。
天瑞纪元自然是与祥瑞的出现相关,但天降祥瑞非人为把控,对于“祥瑞之兆”,古人是十分谨慎的。文帝时以望气著称的新垣平曾因以玉杯为诈,而被文帝诛杀。武帝朝获得宝鼎后,武帝先派使者验问巫锦,并无奸诈才以礼祠之,即使群臣建议尊宝鼎,藏于帝廷时,武帝亦保持清醒的头脑再次审视所获之鼎:“天子曰:‘闲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年丰庑未有报,鼎曷为出哉?’”[1]465可见,帝王对于天降祥瑞的认定是谨小慎微的,只有真正的天降祥瑞才能被认可。故有司所言,郊得一角兽是所获祥瑞的第三次,是例举言之。元狩之前的“元朔”年号,亦是拟就未行,但并非以“天瑞”命名,而应该如“太初”一样,是推算星度命名。当无天瑞再现时,依历算得正朔之名。改元年号,或以天瑞命,或以历法推,共同构成了武帝朝改元纪年的方式。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1]1256武帝的封禅开始动摇影响了汉高祖乃至武帝朝多年的袭秦旧制,在《太初历》彻底完成正朔、服色、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年号纪元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是武帝朝建立新面貌的一次重要举措。
四、结语
武帝年号纪元,是中国历法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尝试,正如清人赵翼所言:“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候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8]38这“万世不易之良法”,与汉武帝朝《太初历》的制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历法的修定,不仅仅开启了全新的纪年方式,而且实现了有汉肇建以来真正的改朝换代。在实现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太初历》的制定与封禅祭祀俱是武帝朝昭示受命于天,动摇袭秦旧制的重大举措,彰显了汉帝王为建立有汉一代新的统治秩序所作的制度、文化层面的革新。封禅大典废除秦旧制,为太初制度改革做出准备;继而汉武帝依历法推算和天瑞纪年的方式,施行新的正朔、服色制度,从而真正实现了有汉一代改朝换代,天命所归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