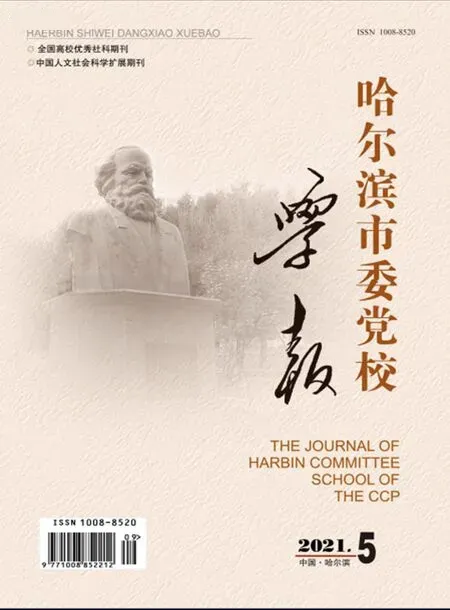仁与天、气
——康有为、谭嗣同哲学比较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相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也在作为当事人的康有为、谭嗣同和作为关系人的梁启超那里得到了印证。问题的关键是:承认康有为、谭嗣同思想最为接近是否就意味着二者思想只有同而没有异?进一步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康有为、谭嗣同对于诸多问题的回答成为两个人之间的默契,而与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其他近代哲学家拉开了距离。如果说诸多问题的高度契合使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相近的话,那么,两个人对相同问题的回答却往往蕴含着不同的意趣和诉求。对于这一点,康有为、谭嗣同的仁学便是明证。本人拟从仁与天、气为切入点,通过对康有为、谭嗣同哲学的比较,直观感受二者思想的异同关系。
一、推崇仁为世界万物本原的仁学派
对于哲学来说,宇宙本原是灵魂;对于哲学家来说,对宇宙本原的回答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谭嗣同都尊奉仁为世界万物的本原,一起在本体哲学领域建构了仁学派。两个人组成的仁学派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独树一帜,既成为中国近代心学的组成部分,又展示了近代心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康有为、谭嗣同构成的仁学派对仁顶礼膜拜,与梁启超以情感为本原的情感派、严复以不可知论为归宿的实证派和章炳麟以阿赖耶识为旨归的唯识派泾渭分明,成为中国近代心学的四大形态和样式之一。不仅如此,康有为、谭嗣同将作为世界本原的仁与以太、电和力等源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概念相提并论,对这些自然科学概念和所属学科、领域的青睐同样与其他近代哲学家形成鲜明的学术分野,而成为只存在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在这个前提下尚须进一步澄清的是:康有为、谭嗣同所理解的仁大不相同,对与仁密不可分的电、力和以太的看法同样相去甚远。
首先,康有为、谭嗣同都推崇仁,都将仁奉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尽管如此,在对仁的具体理解上,康有为所讲的仁与不忍人之心相互印证,并且把仁称为“不忍之心”。谭嗣同借助以太凸显仁的微生灭即不生不灭,并且将仁诠释为一、通。康有为、谭嗣同对电的不同理解既受制于两个人的仁学观,又反过来加大了仁学观的差异。
一方面,康有为、谭嗣同都尊奉仁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对仁的界定、诠释都显示出与古代哲学的学术分野。这主要表现为都将仁与以太、电、力等源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概念相提并论,用这些概念来阐释仁的做法更是惊人相似。康有为声称:“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1]谭嗣同断言:“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所以通之具。”[2]291在选择和吸纳西学的过程中,康有为、谭嗣同出于论证仁的需要以及对仁与以太、电、力关系的理解,侧重以太、电、力为首的物理学。显而易见,两个人的这个做法与梁启超、严复青睐以达尔文进化论为首的生物学迥异其趣,与后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更是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康有为、谭嗣同对以太、电、力的阐发并不相同,并通过对三者的排序直观地展示出来。如果说康有为的排序是力、电、以太的话,那么,谭嗣同的排序则是以太、力、电。这样一来,两个人所讲的与以太、电、力息息相通的仁以及推崇仁的仁学便呈现出明显差异。这是因为,康有为、谭嗣同的哲学建构主要是借助西方的自然科学完成的,对自然科学的不同侧重和取舍在影响两个人对仁的界定和理解的同时,不仅决定了仁学的理论来源和内容构成,而且反映出两个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哲学意趣和价值诉求。
其次,康有为、谭嗣同都将仁与电相提并论,对电的界定、理解却迥然相异。在对电的理解上,康有为电神互释,谭嗣同电脑混用。无论康有为还是谭嗣同都不止一次地以电释仁,致使电成为仁学的组成部分。由此不难想象,两个人对电的不同界定和理解既出于仁学建构的需要,又加剧了仁学的差异。
仁是中国哲学源远流长的概念,具有生生、感通之义,因而与麻木不仁、隔绝不通相反。近代物理学中的电学传入中国之后,电的神奇让近代哲学家浮想联翩。康有为、谭嗣同将电与仁直接联系起来,使电成为仁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和哲学概念。
康有为认为,电与神相通,试图用凡物皆有电来证明万物都有知。沿着这个思路,他习惯于用电来解释仁,以此证明人与人之间的不忍人之心即仁的相互感通。
在谭嗣同那里,电与脑相连,甚至可以将二者视为同一种存在。于是,他写道:“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人知脑气筋(英文写作nerve,现译为神经——引者注)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夫固言脑即电矣,则脑气筋之周布即电线之四达,大脑小脑之盘结即电线之总汇。一有所切,电线即传信于脑,而知为触、为痒、为痛。其机极灵,其行极速。惟病麻木萎痹,则不知之,如电线已摧坏,不复能传信至脑,虽一身如异域然,如医家谓麻木萎痹为不仁……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2]295-296在谭嗣同的视界中,人的大脑神经布满周身,犹如电线四达;电流传动则犹如仁的相互感通。
至此可见,康有为、谭嗣同对电的界定沿着不同思路展开——一言以蔽之,康有为电神互释,谭嗣同则电脑混用。如果说康有为的电神互释沿着以不忍人之心释仁的思路、为源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辩护的话,那么,谭嗣同的电脑混用则为通过庄子的名实论而破对待,进而将仁界定为通而致一提供了前提。
再次,康有为、谭嗣同一面以力释仁,一面对力予以不同的界定和理解。总的说来,康有为热衷于“爱力”,谭嗣同倾心于心力。这意味着康有为侧重从“爱”的角度诠释仁,建构了“博爱派哲学”;谭嗣同侧重从“力”的角度诠释仁,建构了挽救劫难的救赎仁学。
康有为所讲的力与爱相伴随,在将仁与力相提并论的过程中为仁注入爱的内涵。可以看到,他热衷于从爱的角度定义力,于是出现了“热力”“爱力”“吸摄之力”“爱质”等诸多概念和名词,并且在仁与力相提并论的过程中使它们成为仁的别称。作为康有为以爱释仁的结果,除了将仁的基本内涵界定为博爱以外,还使爱与力连成“爱力”。梁启超指出,对于康有为的哲学来说,“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3]。梁启超对康有为哲学的概括,直观地表明了“爱力”在康有为哲学中的地位。
谭嗣同仁学中的力与心如影随形,心力也由此成为他后期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依据谭嗣同本人的界定,所谓心力,就是“人之所赖以办事者”。他进一步解释说,心力具有十八种之多,“略举之,约十有八”[2]363。谭嗣同用心力来凸显心之力量即人之精神的威力无穷,《仁学》的宗旨是为了“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进而言之,心之所以能够堪此重责大任,秘密在于心力的伟大神奇和无所不能。对此,他不止一次地宣称: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2]357
惟一心是实。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4]
康有为、谭嗣同对力的界定不仅预示着仁学的差异,而且通过仁的别称最直观地体现出来。如果说作为康有为之仁代名词的是不忍人之心的话,那么,作为谭嗣同之仁代名词的则是慈悲之心。
最后,康有为、谭嗣同都将仁与以太直接联系起来,致使以太成为仁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对以太的理解上,两个人的观点呈现出明显的分歧。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康有为、谭嗣同无论对以太的内涵还是地位,都有不同的界定和理解。这既取决于两个人的仁学观,又加剧了仁学的不同。
就对以太内涵的界定而论,康有为将以太与不忍人之心相提并论,谭嗣同则将以太理解为微生灭。康有为将以太与电、力并提,旨在证明仁就是源于孟子所讲的不忍人之心,他称之为“不忍之心”。与对“不忍之心”的推崇一脉相承,康有为将以太理解为“不忍之心”,致使博爱成为仁最基本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等是近代的价值理念,康有为、谭嗣同的仁学建构都容纳了这些价值理念,以此推动包括仁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内容转换和现代化。尽管如此,两个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侧重和态度相差悬殊,并且通过对仁之内涵的界定、解读体现出来。康有为极力凸显仁的博爱内容,连篇累牍地断言人道以博爱为主,因而将博爱说成是仁最基本的内涵。谭嗣同将仁与五花八门的概念、名词相提并论,其中包括物理学上的“爱力”和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却始终没有提到博爱,取代博爱的是佛学所讲的慈悲。在谭嗣同的视界中,无论不忍人之心还是博爱都是以太所不曾拥有的内涵,既然并非仁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也就没有出现在仁学中。谭嗣同所讲的以太即微生灭,而微生灭即不生不灭则是他将佛学源于“八不中道”的流转无常、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与以太相互阐发的结果。不难想象,谭嗣同对以太的这些界定是康有为所讲的以太、仁以及他的全部哲学思想中所没有的内容。
康有为、谭嗣同对以太的界定不同,以太对于两个人仁学的意义和在仁学中的地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通过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相关概念的使用最直观地反映出来:康有为之仁的第一概念是“不忍人之心”,故而宣称“不忍人之心,仁也”;谭嗣同之仁的第一概念则是以太,故而强调“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2]295。康有为以不忍人之心释仁,以太在他的仁学以及哲学思想中并不是最核心的概念;谭嗣同以以太释仁,以太在他那里尤其是在后期哲学中成为仅次于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在康有为哲学中与仁最密切的概念是不忍人之心的话,那么,在谭嗣同那里,代替不忍人之心地位的则是以太。对于仁与以太的关系,谭嗣同一而再、再而三地界定说:
一、……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所以通之具。
二、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2]291
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2]293
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精而言之,夫亦曰“仁”而已矣。[5]
谭嗣同的这些议论旨在申明,对于仁与以太的关系,可以从两个不同维度去把握:从细节上看,二者具有体用、精粗之别;从实质上看,仁与以太异名而同实,因而可以相互替代——在这个意义上,仁就是以太,以太就是仁。鉴于以太对于仁的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谭嗣同除了在阐发仁的《仁学》中界定以太内涵、提升以太地位以外,还专门作《以太说》,将以太说成是宇宙间的第一存在和主宰力量。有鉴于此,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谭嗣同哲学的宇宙本原是以太,并且由此断言谭嗣同的哲学在性质上属于唯物论。用唯物论来评价谭嗣同的后期哲学是否合适不是这里探讨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评价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太对于谭嗣同后期哲学的重要性以及以太与谭嗣同仁学的密不可分。
除此之外,康有为、谭嗣同都将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还原为孔学一家,进而将孔学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代表。对仁的不同界定表明,两个人对作为中国本土文化象征的孔学拥有不同理解。在共同赋予仁自由、平等、民主等近代价值理念的前提下,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界定沿着一个注重博爱、平等的思路展开,最终演绎出对孔学的不同认定。在康有为那里,孔学的功能是立——性善说和不忍之心;在谭嗣同那里,孔学的特点是破——破除对待,走向致一、通而平等。
仁学既是康有为、谭嗣同哲学的基本形态,也是两个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仁是康有为、谭嗣同哲学的基本范畴,对仁的不同界定和诠释反过来决定了两个人对宇宙本原的不同看法,进而影响着康有为、谭嗣同建构的哲学样式。在这方面,康有为的天、气、仁并用与谭嗣同的由气转仁呈现出明显差异。
二、康有为:天、气与仁并用
在康有为的哲学中,天、气与仁同时使用。他在承认不忍人之心、仁是世界万物本原的同时,将天、气(康有为又称为元气)奉为世界本原。这使仁与天、气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学术界甚至出现了康有为的哲学究竟以仁还是以天或气为本原的争论。
康有为将元或称元气说成是宇宙本原,并把人与天一起说成是元(或元气)的派生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厌其烦地写道:
天与人皆在元气之中,不相远也。[6]569
岂知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犹波涛与沤同起于海,人与天实同起也。然天地自元而分别为有形象之物矣。人之性命虽变化于天道,实不知几经百千万变化而来,其神气之本,由于元。溯其未分,则在天地之前矣。人之所以最贵而先天者,在参天地为十端,在此也。精奥之论,盖孔子口说,至董生发之深博,与华严性海同。幸出自董生,若出自后儒,则以为剿佛氏之说矣。(尝窃愤儒生只能割地,佛言魂,耶言天,皆孔子所固有,不必因其同而自绝也。理本大同,哲人同具,否则人有宫室、饮食,而吾亦将绝食露处矣。)[7]
太一者,太极也,即元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易》所谓“乾元统天”者也。天地、阴阳、四时、鬼神,皆元之分转变化,万物资始也。其元气之降于人,为性灵明德者曰命,天命之谓性也。此天之分与人者,世分官职于天,当尊其德性,以修其道教也。人之本乃在天元,故礼之本亦出于太一。其本原之深远微妙,非孔子孰能知而制之?夫人非人能为,天所生也。天为生之本,故万物皆出于天,皆直隶于天,与人同气一体。报本反始,故大礼必祀天,制作必法天,生杀必称天,仪体必象天,盖不忘本也。[6]565
稍加思考即可发现,康有为在论述元气是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彰显元的地位。他的具体做法是把元置于天和人的存在之前,使元成为天、人和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并在这个前提下将元与太一、太极相提并论。在提升元之地位的同时,康有为突出天的本原地位。在这方面,他除了发出“万物皆出于天”的论断以外,还强调天地是生物之本,人与万物皆由天地派生而来。于是,康有为反复强调:
天地者,生之本,众生原出于天,皆为同气,故万物一体,本无贵贱。[8]
夫天地者生之本,万物分天地之气而生。人处万物之中,得天地之一分焉,故天地万物皆同气也。[9]
议论至此,康有为的哲学中便出现了元、气、天和仁等多个本原,于是便出现了学术界关于元、气、天与仁在康有为哲学中何者为本原的讨论乃至争论。其实,对于他来说,元与天何者为本原并不矛盾,上述不同说法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尽管具体表述有所出入,思想主旨并无区别。具体地说,正如康有为宣称元为本原时不忘强调“人与天同本于元”,借此突出人与天的密切相关一样,他肯定天为本原只是为了突出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因此,康有为的初衷是借助对天、元、气的推崇,从不同角度共同证明天、人与万物密不可分,是同原而生的一体关系。出于同样的初衷和逻辑,他指出,元作为本原显于人性是人人同具的仁即不忍人之心;天是本原则表明人的不忍人之心是天赋的,上天在生人之时即赋予人此种善性,故而人之性善与生俱来,人人无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天并无区别——甚至可以说,只要能突出人的性善,将元具体叫作什么并不重要。于是,康有为解释说,元就是婆罗门教所讲的“大梵天王”,老子所讲的“道”。同样的道理,元既可以与气相提并论,称为“元气”,也可以与天并论,称为“天元”。与此相一致,康有为对元、天、气的推崇与对仁的推崇并行不悖,在时间上可以同时,并不存在像谭嗣同那样早期推崇元气论,后期转向心学,推崇仁便不再以气为本原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诸天讲》是康有为生平最后一部著作。讲天的《诸天讲》前后耗时四十二年之久方才面世,这既可以视为康有为对此书的酝酿、修改,也可以看成他对天的热情四十余年而不辍,始终如一日。
进而言之,康有为之所以对天津津乐道,热情不衰,是因为天在他的哲学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既与人之性善的与生俱来以及由此对人生而具有自主之权的论证密不可分,又与让人摆脱家国的羁绊而“直隶于天”的意图息息相通。《诸天讲》的主体内容是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天体演化论相杂糅,在揭示宇宙由来和天体演化的基础上,探究二百四十二重天。翻阅、研究《诸天讲》,最大的感受是:书中的内容庞杂得超乎想象,与天相关的各种自然科学如进化论、天体演化论、地心说、日心说、相对论和牛顿力学等一应俱全,其中还夹杂着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为首的五花八门的宗教。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从明末一直到康有为所处的近代,西方传教士正是利用各种自然科学展开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据康有为本人在《诸天讲》自序中所言,他讲诸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宣讲天文学或自然科学而是别有企图。对于他意欲何为,康有为坦言:“吾之谈天也,欲为吾同胞天人发聋振聩,俾人人自知为天上人,知诸天之无量。人可乘为以太而天游,则天人之电道,与天上之极乐,自有在矣。夫谈天岂有尽乎?故久而未布。丙寅讲学于天游学院,诸门人咸请刻布此书以便学者,虽惭简陋,亦足为见大心泰之助,以除人间之苦,则所获多矣。”[10]13康有为的这段表白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他讲天的初衷和心态,那就是“人在地球,心想天界”,而这一点恰恰与他在自序中署名“天游化人康有为”相印证。
《诸天讲》是康有为讲天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推崇天的两个心迹:第一,一贯的宗教情结。诚然,《诸天讲》的主流既不是康有为早期奔走呼号的孔教,也不是《大同书》中占据首位的佛教,而是道教。尽管如此,使人放弃做家人、做国人的世俗生活而做遨游诸天的天人还是使《诸天讲》带有布道的成分,更何况书中充斥着各种宗教学说,道教更是在书中占据重要一席。第二,请天为人代言。早期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之时,康有为就声称孔子讲性与天道,孔子的所有主张都源于天。在《大同书》中,他更是以人“直隶于天”的名义提倡取消家庭和国家。《诸天讲》延续了“直隶于天”的主题,着重让人知道自己是“天上人”而做“天人”,以此摆脱家庭、国家带来的种种羁绊。更为重要的是:《大同书》中的人尽管摆脱了家庭和国家,却依然隶属于社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概括为“社会主义派哲学”。《诸天讲》则将人的“独立”推向了极致,使人成为独来独往的“天上之人”。这一点正是康有为在《诸天讲》的自序中不厌其烦讲述的内容[10]11-12。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做天人的快乐与做地人的忧苦形成强烈对比。依据他的分析,做地人之所以与忧俱来,是由于人无论囿于一家、一乡、一邑还是囿于一国,都会引起纷争而备受煎熬和拖累。康有为特意强调,各种宗教的宗旨无非是引导人摆脱苦难,最终臻于快乐之境。结果却总是效果不佳,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症结在于“未知吾地为天上之星,吾人为天上之人”。由于诊断失误,“所发之药,未必对症”。这样一来,结局可想而知——一切都于事无补。在此分析之后,康有为宣布,唯有自己找到了通往快乐的康庄大道。于是,他接着写道:“然则,欲至人道之极乐,其为天人乎?庄子曰:‘人之生也,与忧俱来。’况其寿至短,其知有涯,以至短之寿,有限之知,穷愁苦悲,日夕之劳困不释。或苦寒饥,家累国争,憧憧尔思,雷风水火,震撼骇疑;或日月遇食,彗星流飞,火山喷火,地裂海啸,洪水泛滥,神鬼精魅,幻诡离奇,不辨其物质,不得其是非,哀恐畏慑,忧患伤之,痛心莫解,惊魂若痴,此亦人间世之最可悯悲者也。且爱恶相攻而吉凶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惟天生人,有欲不能无求,求之不给不能无争,争则不能无乱,一战之惨,死人百万,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二十八岁时,居吾粤西樵山北银河之澹如楼,因读《历象考成》,而昔昔观天文焉。因得远镜见火星之火山冰海,而悟他星之有人物焉。因推诸天之无量,即亦有无量之人物、政教、风俗、礼乐、文章焉,乃作《诸天书》,于今四十二年矣……日为天游……吾心游诸天之无量,陶陶然浩浩然。”[10]12
由此可见,康有为找到的快乐秘方是:人生在地球上,活在地球上,却不要自认是地球上的人。这是因为,了解了诸天的情况则会发现,地球只是天上的一颗星星而已。既然地球作为天上的一颗星星而从属于天,那么,地球之人便都成为天上之人即“天人”。他反复强调,人只有彻底弄懂了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不是“地人”而是“天人”,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家庭以及乡邑、国家等种种羁绊,进而摆脱由家庭、乡邑和国家带来的诸多忧苦而与乐俱生。
鉴于天对于人的至关重要,天成为康有为受用终身的哲学范畴。因为天与人的天赋人权密切相关,只有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论证、伸张人的自主、平等之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彰显这种权利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权威性。因此,号召人“直隶于天”成为康有为一贯的追求,阐发这一道理的《诸天讲》反复修改四十余年便是明证。同样的道理,在酝酿、打磨了近二十年的《大同书》中,天赋之权仍然是主要内容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天为思想主题和逻辑主线,可以窥探、梳理出康有为思想一以贯之的相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的哲学没有截然的阶段划分,天、气、仁贯穿始终。仁在康有为那里具有实体性,之所以成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因为仁具有生生不息的特性。援引、借用康有为的比喻说,仁就像果仁(万物的种子)那样产生万物。正因为仁具有实体性,故而成为“爱力”“爱质”等实体性的存在。
三、谭嗣同:由气转仁
与康有为哲学中的情形类似,天、气与仁都是谭嗣同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并且都与世界本原密不可分。两个人哲学的这一特点与严复、梁启超的哲学相去甚远。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剖析可以发现,谭嗣同所讲的天、气与康有为呈现出巨大差异:第一,在理论来源上,康有为所讲的天、气以孔子、孟子和董仲舒的思想为主要来源,谭嗣同则以王充、张载和王夫之的思想为主要来源;第二,在仁与天、气的关系上,康有为的仁学与对天、气的推崇带有共时性,气与仁在谭嗣同的哲学中并无共时性。这是因为谭嗣同所讲的仁没有实体性,甚至成为虚、空的代名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宣布“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为识”[2]292之日,也就是与元气论诀别之时。
谭嗣同早年与康有为一样将气视为宇宙本原,并且突出天与气、元气的密切关系。此时的谭嗣同反复强调:
元气絪缊,以运为化生者也。而地球又运于元气之中。[11]127
天以其浑沌磅礴之气,充塞固结而成质,质立而人物生焉。[11]128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元气论与天密切相关。奥秘在于,对于元气论者来说,对元气的推崇也蕴含着天的至高地位。在这方面,从东汉王充到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再到宋代张载,都是典型的代表。谭嗣同对气与天的理解带有中国古代哲学的痕迹,呈现出与康有为的相似性,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两个人的哲学与古代哲学的一脉相承。与此同时,谭嗣同对天、气的理解与康有为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择其要者,大端有二:第一,谭嗣同没有强调元气或天与人的一致性,没有像康有为那样让人“直隶于天”。这意味着谭嗣同没有借助天的权威宣扬天赋人权论,对平等、民权的张扬主要是借助仁学进行的。第二,谭嗣同早期所讲的元气或天无论理论来源还是内容构成都比较纯粹,没有像康有为那样将元气与老子之道、大梵天王以及基督教的耶和华混为一谈,因而与各种宗教、精神意识或神无涉。这意味着谭嗣同早期的哲学属于唯物论,与后期的心学泾渭分明。他在《仁学》中呼吁像西方那样“称天而治”,显然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此时之天并不具有世界本原之义。
在谭嗣同三十岁时,对元气论的推崇戛然而止。对于自己思想的变化之大,他本人给予“前后判若两人”的评价。对此,谭嗣同解释说:“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天谋鬼谋,偶而不奇。”[12]正是在经历甲午战争的重创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从前“所愿皆虚”,并且反省到以前的愿望之所以落空,是因为“所学皆虚”。当然,为谭嗣同所视为虚的,也包括元气论在内。谭嗣同对自己“所愿皆虚”的概括与康有为断言大同社会“愿求皆获”形成鲜明对照,也表明此时的谭嗣同心灰意冷,情绪跌到了谷底。在苦闷彷徨中,他于1896年春开始“北游访学”,期望借助此举为救亡图存寻求新的出路。
在“北游访学”的过程中,谭嗣同确立了“以心挽劫”的救亡纲领和哲学宗旨,最终形成了《仁学》一书。在作为后期哲学代表作的《仁学》中,他用仁取代了气、天在哲学中的位置,明确断言“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为识”。与康有为相比,谭嗣同的元气论更具有唯物论精神,并且与后期的仁学截然不同。正因为如此,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以“北游访学”为界,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时期。这就是说,在谭嗣同那里,仁学是作为从前哲学的反动出现的,与元气论并非一脉相承,而是取而代之。在《仁学》中,谭嗣同皈依佛学,并将佛学与庄子的思想相和合而构建了仁学。对于“北游访学”时的思想状态,他本人有过一段集中回忆和描述。现摘录如下:“远羁金陵,孤寂无俚,每摒挡繁剧,辄取梵夹而泛观之,虽有悟于华严唯识,假以探天人之奥,而尤服膺大鉴。盖其宗旨岂亶,无异孟子性善之说,亦与庄子于道之宏大而辟、深闳而肆者相合。至于陆子静、王阳明,其有所发,尤章章也。嗣同以为苟于此探其赜,则其所以去尔蔽,祛尔惑,睿尔智,成尔功者,诚匪夷所思矣。”[13]显而易见,谭嗣同的这个说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佛学和庄子思想对于《仁学》的至关重要。
对于谭嗣同来说,从早期哲学到后期哲学的心路历程就是由元气论转向仁学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由物学转向心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经过哲学嬗变的谭嗣同将佛学和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联系起来,声称宇宙本原——仁不生不灭,而不生不灭也就是微生灭。在他看来,宇宙本原——仁粗而言之就是以太,以太“精而言之,夫亦曰‘仁’而已矣”[5]。不生不灭出于以太之“动机”,从根本上说则与佛学密切相关。不生不灭表明,作为世界本原的仁并非恒常不变的,而是瞬息万变的。对此,谭嗣同称为微生灭。无论从仁的微生灭还是从万物的变幻无常、流变不息来说,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谭嗣同宣称:
天地万物之始,一泡焉耳。泡分万泡,如镕金汁,因风旋转,卒成圆体。日又再分,遂得此土。遇冷而缩,由缩而干;缩不齐度,凸凹其状,枣暴果暵,或乃有纹,纹亦有理,如山如河。缩疾干迟,溢为洚水;干更加缩,水始归墟。沮洳郁蒸,草蕃虫蜎,璧他利亚,微植微生,螺蛤蛇龟,渐具禽形。禽至猩猿,得人七八。人之聪秀,后亦胜前。恩怨纷结,方生方灭,息息生灭,实未尝生灭,见生灭者,适成唯识。即彼藏识,亦无生灭,佛与众生,同其不断。忽被七识所执,转为我相。执生意识,所见成相。眼耳鼻舌身,又各有见,一一成相。相实无枉受薰习,此生所造,还人藏识,为来生因。因又成果,颠倒循环,无始沦滔。沦滔不已,乃灼然谓天地万物矣。天地乎,万物乎,夫孰知其在内而不在外乎?虽然,亦可反言之曰:心在外而不在内。是何故乎?曰:心之生也,必有缘,必有所缘。缘与所缘,相续不断。强不令缘,亦必缘空。但有彼此迭代,竟无脱然两释。或缘真,或缘妄,或缘过去,或缘未来;非皆依于真天地万物乎,妄天地万物乎,过去之天地万物乎,未来之天地万物乎?世则既名为外矣,故心亦在外,非在内也。将以眼识为在内乎?眼识幻而色,故好色之心,非在内也。心栖泊于外,流转不停,寖至无所栖泊,执为大苦。偶于色而一驻焉,方以得所栖泊为乐。其令栖泊偶久者,诧以为美,亦愈以为乐。然而既名之栖泊矣,无能终久也。栖泊既厌,又转而之他。凡好色若子女玉帛,若书画,若山水,及一切有形,皆未有好其一而念念不息者,以皆非本心也,代之心也。何以知为代?以心所本无也。推之耳鼻舌身,亦复如是。吾大脑之所在,藏识之所在也。其前有圆洼焉,吾意以为镜,天地万物毕现影于中焉。继又以天地万物为镜,吾现影于中焉。两镜相涵,互为容纳,光影重重,非内非外。[2]330-331
这段话出自《仁学》,是谭嗣同秉持仁学的思路对哲学的集中表达。透过谭嗣同奉仁为世界本原而描述的宇宙状态,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仁不是固定的实体或者说没有确定性。正因为如此,他断言不生不灭是“仁之体”。谭嗣同所讲的不生不灭即微生灭是一种“旋生旋灭,即灭即生”的状态,而微生灭与以太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微生灭脱胎于佛学,是对八不中道即“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中观》)的翻版和发挥。有鉴于此,谭嗣同将之说成是“仁之体”表明,他所讲的仁以佛学为母版,仁学的主体内容则是佛学与庄子思想的和合。第二,无论将不生不灭说成是“仁之体”还是对佛学与庄子思想的和合都表明,谭嗣同推崇的仁与天尤其是气没有直接关系。天尤其是气在仁学中的退场在某种意义上割断了谭嗣同哲学的连续性,难怪他自己称经过转变的哲学与之前“前后判若两人”。
上述内容显示,康有为、谭嗣同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彼此的思想异同互见。因此,既要肯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又要充分关注二者思想的不同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比较具有了不容忽视乃至不容低估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二者思想的比较,不仅可以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加强对谭嗣同思想的原创性、独特性的深刻体悟,而且可以透过二者思想的异同关系领悟戊戌启蒙思想家之间多维、多向的关系,进而全面把握、评价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之间以及近代哲学家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