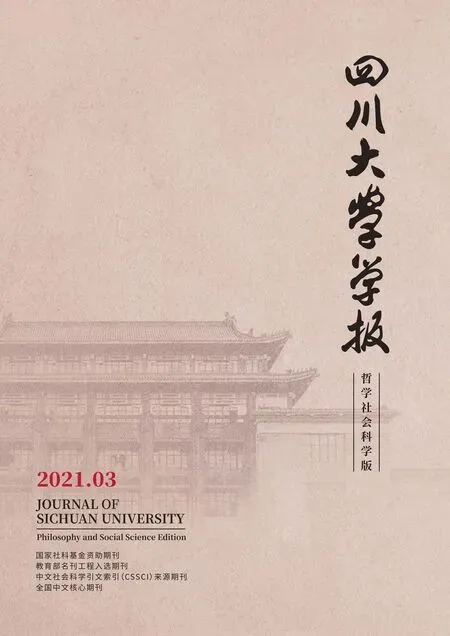艺术的消逝?
——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误解
余 玥
“艺术的终结”至今仍是美学和艺术理论界最为炙手可热的论题,它被认为是来自黑格尔的主张。在海德格尔之后,所谓黑格尔“终结论”的实质,就被定位为要让艺术思考变成哲学体系并终结于概念的表达,此定位后被伽达默尔所继承。尽管20世纪后期贝尔廷和丹托对“终结论”另有来自分析哲学传统的表述,但其核心仍是艺术的观念化,丹托甚至主张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除了创作不再负责观念诠释和思维体系构建的工作。(1)丹托因此说道:“艺术终于可以卸下肩头的重担,交棒给哲学家。”丹托:《在艺术终结之后》,林雅琪等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第43页。在其影响下,“艺术终结论”也成为我国近十年的热点话题并带动黑格尔美学研究的回潮,但迄今为止,相关后者的论文仍在强调艺术在辩证逻辑体系中将被超越。(2)朱立元:《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西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46-156页。虽然朱立元看到了黑格尔极少用“终结”一词,以及有研究反对黑格尔那里存在“艺术终结论”,但他仍主要采用了一种内在逻辑发展的方式来看待黑格尔美学。
事实上,黑格尔根本没有说过“艺术的终结”,而只提过“艺术的消逝”,且目的仅是为“美的艺术”辩护,并努力使之成为真正的精神科学。显然,将艺术葬入往昔并令其从属于概念哲学,这种当代“终结论”主张与黑格尔为艺术和美的自由显现做积极慎重辩护的态度是矛盾的。遗憾的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和意义至今鲜被重视。由于海德格尔对黑格尔“艺术的消逝” 的讨论过于简短,(3)与此直接相关者仅3页。参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后记,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第63-65页。而丹托所谓“艺术的终结”则带有太多自主想法,(4)彭锋甚至认为,丹托在“艺术终结论”上对黑格尔的依托是添加上去的,实则二者根本不同。参见彭锋:《艺术的终结与禅》,《文艺研究》2019年第3期,第5-8页。要弄清后世“消逝-终结”说与黑格尔想法的矛盾及其意义,伽达默尔是十分合适的参照。他一生不断尝试对“艺术的消逝特性”进行阐释,且在《伽达默尔全集》第八卷中保存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材料,尤其《美的现时性》一文更可被理解为与黑格尔美学的直接对话。但从黑格尔研究的最新进展来看,伽达默尔的这些解读更多地强化了海德格尔以来对“艺术消逝-终结”的看法,并未真正进入黑格尔美学。事实上,在黑格尔那里,“艺术的消逝”不仅并非“艺术的终结”,反而从属于一种批判性地为“美的艺术”奠基的工作,这一工作的要旨在于将艺术从糟糕的时代处境和狭隘自闭的分析中解放出来,把它置于与其他重要精神性原则的广泛互动统一中去,并重视由此产生的客观现实的社会-政治效应及其永恒意义。因此,它根本不是一种要让艺术在概念思考中过时的形而上学表达。而这种表达却被伽达默尔及其他“艺术终结论”者认为是理解“艺术消逝性”的关键。为说明伽达默尔解读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将从艺术、美、美学三个中心词出发,呈现伽达默尔对黑格尔“艺术消逝特性”的理解及反对;第二部分转回黑格尔,根据美学讲座的编撰历史和最新研究,指出“艺术的消逝”的真正含义;第三部分集中分析伽达默尔理解之不足,并为一种积极的“艺术消逝”阐释及“美的艺术”之客观性辩护。
一、 反对黑格尔:伽达默尔论艺术的消逝与美的艺术
在伽达默尔众多的美学论述中,1974年出版的《美的现时性:艺术作为游戏、象征和节日》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在占据全文一半篇幅的导言中,伽达默尔对“美的艺术”这一黑格尔美学讲座的主题词做了多方面的考察(这种考察甚至在《真理与方法》中都未明确进行过),考察围绕着三个中心展开:艺术,美和美学,目标是为艺术的现时性做辩护,而实现目标的最大障碍就是黑格尔所提出的“艺术已然消逝”的说法。然而事实上,虽然古代艺术曾衰落过,但在基督教艺术受到重视和近代人文主义盛行之后,艺术已经复兴且至今不衰。(5)H.-G. 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Symbol und Fest,”in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Band 8), sthetik und Poetik I, Kunst als Aussag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3, S.94-142.在此情境下,为什么要认可“黑格尔”的说法(6)请读者注意:本部分所论黑格尔仅限于伽达默尔理解范围内,而黑格尔的真正形象在本文第二、三部分才会被集中分析。并为艺术的现时性辩护呢?
为弄清个中缘由,我们先来看伽达默尔为什么赞成黑格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曾问及:“在一部艺术作品最初所设定的世界关系和它在此后变化了的生活环境中的继续存在之间似乎要有区分,但是最初的世界和后来的世界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呢?”比如一尊古代神像,当它还在庙堂之中被古人朝奉时,对它的意义诠释显然不会和其在今日的博物馆中一样,然而这些理解和诠释之间的分界线何在?黑格尔的回答是:在已经扬弃了古代认知的我们今日的自我认知之中,差异才真正出现。只有当自我意识在当下对艺术作品的意义做出回应的时候,分界线才由时代的共同意识借助现代的艺术概念理解所划定。这样一来,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的关键,似乎就只是扬弃过往的当下概念把握的诠释效果而已。如果这样来解释艺术的消逝,那么黑格尔绝不是指再无艺术,而只是说理解过往艺术的一切可能都在正在发生的当下被规定好了。因此,在另一篇讨论黑格尔的文章中,伽达默尔指出:“我现在通过艺术的消逝看到了黑格尔如何在其美学中来主张这种消逝。……除了正在发生的未来,它没有表达任何未来。……艺术的消逝性特征,在黑格尔如此理解之时,……只是包含了:艺术由此内在于一种更高的真理诉求来展现它的功能。”(7)H.-G. Gadamer, “Die Stellung der Poesie im System der Hegelschen sthetik und die Frage des Vergangenheitscharakters der Kunst,” in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Band 8), sthetik und Poetik I, Kunst als Aussag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3, S.228-229.
这样一来,“美的现时性”似乎就在黑格尔“艺术的消逝”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而非被其所阻碍。德文Aktualität一词除了现时之外,还有能动的含义。从黑格尔的视角看,这种能动性当然就体现在当下自我意识所做出的诠释和理解之中。这看上去似乎也是伽达默尔的意思:艺术就在“一种伟大的与世界的关联辩护整体中围绕着自身而存在,一种不言自明的融汇进程在共同体、社会、教会和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自我理解之间完全地进行着”,(8)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Symbol und Fest,” S.97.这种融汇进程同时也是对艺术作品认识的教化进程。对此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就连对自然美的欣赏也是教化的产物——在启蒙思潮兴起之前的阿尔卑斯山,从未被当做自然美的典范。正是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明了这种人为创制的、意识性的艺术美对于自然美的优势,还说明了此种作为时代共同理性之表达的艺术美在让人们形成普遍精神方面的教化之功。但二者不同的关键,就是伽达默尔阐述了上述艺术教化共同体在黑格尔时代的破裂。他要求人们重新诠释艺术的“分界线”。事实上,伽达默尔反复强调现代艺术产生的共同体分离和破坏性语境。(9)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Symbol und Fest,” S.98; H.-G. Gadamer, “Ende der Kunst? Von Hegels Lehre vom Vergangenheitscharakter der Kunst bis zur Anti-Kunst von heute,” in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Band 8), sthetik und Poetik I, Kunst als Aussag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3, S.209.无论是波德莱尔的漫游式写作、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还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戏剧等都体现了现代艺术的去中心特征,说明今日艺术家创作与共同体不言自明的世界理解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统一的艺术哲学-形而上学想法的失效。既然如此,时代艺术意识及其对过往艺术的当下评判当然不再有效。于是,谁及怎样划定这条明显的艺术分界线,在黑格尔后就重新成为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状况,伽达默尔才再次提出“艺术今日是什么”的问题。第一个关键词因此便是今日“艺术”,它“不仅是一个关于我们美学的自身可理解性的问题,……而是一种在现代艺术家要求之中的新的社会行动,它是一种反对公民的教化宗教的类型,……在艺术家的要求中存在着的是……一种新的团结进程”。(10)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Symbol und Fest,”S.101.换言之:需要形成一种新的共同艺术意识,这种意识是从黑格尔式的共同体已经破裂、形而上学统一许诺已经失效的情况下,作为无确定答案的真理寻求和诠释活动显现自身的。它因此也反对黑格尔式的艺术教化主张,因为教化不可避免地指向大众的艺术趣味养成,但大众趣味在现实中却又注定分散。“教化的真正过程……似乎是自我崩溃的”。(1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只有真正面对艺术共同体的分裂和艺术公民教化的崩溃处境,才能重新通过视域融合形成新的共同艺术意识。
那么,此可能的融合视域何在呢?在古希腊,艺术作品是指相对自然而言的人工创制品。“美的艺术”因此并指一种非自然地、创制性地(在古希腊文中与“诗学地”同源)充实人类精神形态空间的活动,是精神存在者的原初显现。(12)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Symbol und Fest,” S.104f.伽达默尔所论的第二个关键词“美”,德文Schön,源于动词“直观”(schauen),因此审美活动原本就是对显现者的精神性观看,(13)H.-G. Gadamer, “Anschauung und Anschaulichkeit,” in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Band 8), sthetik und Poetik I, Kunst als Aussag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3, S.190.而这正是柏拉图《斐多》以来理性(nous)哲学传统的关键,即灵魂对世界显现的智性观看:“这就是哲学的道路。柏拉图将美称为最甚之‘显现而出者’及‘吸引向内者’,即所谓理想的可见性。”(14)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Symbol und Fest,” S.106.而美就是意识对原初显现者的创造性回忆,艺术作品之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认为与模仿相关,正是源于此——对原初显现的追忆活动:模仿(mimesis),原意就是返回、回忆与再现。自海德格尔开启存在论转向之后,便开启了重要的精神返回步伐。在古希腊“美好”风俗共同体中展现出来的共同“艺术”意识(它关系着城邦的属人所创造的精神特质),是基于对灵魂所见的世界整体显现的模仿。而这才是艺术作品被共同体当下时代意识所接受和承认的真正存在论根源。当海德格尔指责黑格尔将美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等同起来的时候,他想说的是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对美之发生的漠视,(15)海德格尔:《黑格尔与希腊人》,《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09页。而伽达默尔继承了这一批判,让对“美的艺术”的源头诠释成为新艺术共识产生的第一步:迈向从未消逝的传统。伽达默尔的“美”并非是出现在社会和国家共同体之后的更高哲学真理的概念,相反它先于任何共同体,从其古老之源出发并与我们在当下遭遇。这就意味着对黑格尔的颠倒:不是正在发生的未来规定着美和艺术作品,而是正在遭遇的过去生成着它们;而“美的艺术”也根本不是普遍时代精神认可的结果,相反却是时代精神的发源地;诸多源泉的“现时性”就体现在从作品的多元显现走向交互诠释的诸进路之中,而非要将各种必将消逝的作品诠释扬弃在唯一的哲学真理之内。至于这种交互诠释共同体能够成形的根据,也非由艺术作品诠释之具体内容的精神统一性提供,而由其追忆真理(去蔽)的方法同一性保证。
于是引出了第三个中心词:美学。仅仅说灵魂对于原初显现者创制性的回忆,并不足以解释我们在此究竟是和什么样的东西打交道,它又是如何构成交互诠释和视域融合的约束性条件之类问题。伽达默尔因此回到了美学定义上来对其研究美的方法进行思考。美学创始人鲍姆佳通曾将美学定义为“思考美的艺术”(ars pulchre cogitandi),它类比修辞学的定义,即“良好言谈的艺术”(ars bene dicendi)。伽达默尔认为这暗示了美的艺术与言谈的艺术具有内在关联。按照康德的理论,这种相关性体现为:当我在诠释美的艺术作品或作出美学判断时,这种诠释或判断应该同时是可普遍传达的,我必定希望我所做的美学判断能够通过传达得到每个人的情感赞同。在此处隐藏着一个难题:如果普遍赞同构成了美的判断和诠释的基础,那就等于说,只有精神共同体的承认才能确定什么是美的艺术,但成问题的恰恰是这一共同体是怎么形成的;如果将普遍赞同视为对艺术作品本身可言说性的认可,那么我们赞同的就只是“艺术作品要就其自身被说成艺术作品”,但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为解决这一难题,既不能单纯突出作品自身的表达,也不能片面强调接受者的承认,而必须小心守候在二者的遭遇时刻。在这一时刻,艺术“就之成形”(Anbild)。Anbild这一生造词与图像(Bild)一词共享词根,它指向柏拉图意义上世界显现的“原像”。但“就之成形”表达的是在接受者承认中才成形的艺术作品的自行道说,或在共同回忆中才显现的原像。换言之,它强调一种遭遇双方的现时成形。伽达默尔因此将之(在康德意义上)理解为一种“击打而出”的言谈:(16)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Symbol und Fest,”S.108, 109, 112.一切诠释都围绕着双方遭遇之时彼此击打所产生的震惊效应展开,而只有这一时机才造就了艺术阐释的可能性。这种彼此击打的时机性及其来去往返就是康德所说的“游戏”状态,因为它既不包含对共同体承认的优先性认可,也不包含对艺术作品自身可道说性的优先性认可,所以诚如康德所言它是“无倾向性”的。游戏因此被视为阐释学美学方法无约束条件的约束条件,它只有在对话双方参与的语境下才能发挥其创制性作用,而在开放语境中当下就成形者即是艺术作品。
二、艺术的消逝:黑格尔美学讲座的语境分析
伽达默尔对“美的艺术”之现时性的辩护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个论题:1.艺术作品及其诠释,就是在新老视域分界线上的、对诸多独特处境的多元诠释。这些诠释要求新的统一或视域融合。2.新统一达成的可能性条件在于对源初传统的创造性再现。它在美的直观中获得其哲学表达。3.美学的创造性回忆方法是一种游戏性的言谈和对话的方法。它在艺术作品的自身言说与受众的共同认知之遭遇中往复发生。
这三个论题都与伽达默尔关于黑格尔“艺术已经消逝”的主张有交相辩难的旨趣:
1.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主张艺术作品的重要性已经转移到对艺术概念的哲学反思中,转移到现时统一的时代精神的教化和养成之中,但黑格尔没有看到这种教化其实是自行崩溃的。
2.对于美的艺术而言,黑格尔认为重要的是共同体形成之后的、正在发生的未来维度,而非伽达默尔强调的正在遭遇的传统维度。
3.体系性地超出美学方法,进展到唯一内在往复上升的哲学-形而上学概念真理寻求中去,是黑格尔美学的真正目的。(17)参见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上卷第219-221页对黑格尔哲学和艺术关系的讨论。但黑格尔没有真正理解解释学的往复遭遇和击打性发生的非体系性的可能途径。
如前所述,这些理解其实从海德格尔乃至更早黑格尔《美学》讲座的编者霍托以来就一直存在,它们在当代也以“艺术终结论”的形态继续发展。所有这些理解都将“艺术已然消逝”简单地放进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又将整个体系简单概括为概念的进展,却全然不顾以下事实,即《美学》讲座的编排并非是黑格尔所为,它直到今日无论从传承还是编撰上都仍处于令人很不满意的状况,且它与体系的具体关系更是不完全清楚的。这尤其体现在它缺乏一个说明其与体系关系的导论这一事实上:(18)W. Jaeschke, Hegel Handbuch, Leben-Werk-Schule(3.Auflage), Stuttgart: J. B. Metzler Verlag, 2016, S.384f.出现“艺术已然消逝”这一说法的霍托本导论其实是编撰的。虽然这并不是说因此美学就不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之中,但我们显然应该非常小心。得益于谢菲尔德近二十多年对黑格尔美学讲座原始材料的汇编工作,以及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我们今日已可不再仅从被霍托以“体系的完满性”为目标所编织的、窄化了的黑格尔形象出发,去分析“艺术的消逝”的语义。2018年,珊特考伦著名的“经典阐释”书系主编对黑格尔美学讲座进行了最新的权威阐释,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9)B. Sandkaulen, “Einleitung: Über das Projekt einer Philosophie der Kunst,” in G. W. F.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sthetik(Kalssiker Auslegen Bd.40), Hrsg. v. B. Sandkaule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18, S.11-15.
1.“艺术的消逝(Vergangene)”不是“艺术的终结(Ende)”。 “艺术的终结”这一说法,无论在霍托本还是新近汇编本中都找不到。
2.“消逝”的说法在黑格尔各版本美学讲座中的确一直存在,但黑格尔对之的阐释并没有后来者理解的那么偏激,它的语境是:艺术既非根据其内容,也非根据其形式才成为将精神的真正兴趣呈现在意识之中的最高的和绝对的方式。只有在一种比单纯的形式内容分析更为广大的范围内,真理才能够在艺术作品中展现出来。这并非是说,艺术的感性表达会在真理的概念体系前失去效力。恰恰相反,正因为黑格尔要让艺术在绝对精神的层次展现其感性的效力,所以仅仅从艺术形式和内容出发是不够的,艺术必须被纳入与其他文化性自我理解媒介的比较之中。
3.在纳入其他文化自我理解媒介之后,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艺术和古希腊艺术表现出的真正精神兴趣的不同。在1828—1829年的讲座材料中,这意味着一种艺术(古典艺术)的消逝和另一种艺术(浪漫艺术)的产生。分界线被划了出来,不可逆转的文化转折已经发生,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艺术都将消逝。
4.黑格尔谈到艺术消逝时还有一个明确的文化语境,即反对一种“理性教化”或“反思性教化”。它们都指向现代的唯理化进程,这尤其体现为对一般形式法则和义务法律的强调。而艺术因为仅被视为单纯的感性体现,所以才应该消逝或只起工具作用。但特别是1826年的讲座材料显示出,黑格尔严厉批评这种见解是单纯反思性和抽象性的,而艺术恰有针对之的疗救之功。假如把黑格尔艺术科学的想法错误地看成现代唯理化倾向的组成部分,就无法理解黑格尔的中心任务是捍卫艺术哲学的绝对地位。只有将“艺术消逝”理解为批评而非肯定性断言,这一表面的矛盾才能得以解释。
5.“艺术消逝”是事实描述,更是一种批评,它导向以思想的方式来观察艺术。这不仅要求我们反对贬低艺术的唯理论的态度,同时也要求我们反对另一种将艺术绝对化的观点,此观点因为拒斥现代唯理论倾向而神话艺术,这就是谢林和浪漫主义者的“艺术新神话”和“复魅”的主张。但对于黑格尔来说更有吸引力的,是介乎二者间的席勒的观点:不是通过创造神话,展示空洞浪漫的、对神秘的“美的艺术”的虔思姿态,而是通过进入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现实,通过让艺术成为其中各方意见的反思平衡基底,从而在艺术进程中反思艺术,让美的艺术真正肩负起现时精神共同体构建的作用,且所有这些作用都必定要经受住精神科学具体且现实的确定性考察。就此而言,“艺术新神话”的主张也开始消逝了。在谢菲尔德整理的美学讲座材料中,这种“消逝”特别体现在黑格尔提到但没有详细展开的、从“浪漫型艺术”向“自律型艺术”的转化之中。
珊特考伦关于“艺术的消逝”分析的最后两点恰恰是伽达默尔没有重视的。它们的关键都在于:通过对艺术与其他精神媒介的交互比较、分析和融汇,阐明美的艺术在现时精神活动诸领域中的客观性和现实性。“艺术的消逝”首先属于黑格尔的一个批判计划,它一方面针对现代唯理论工具化和抽象化艺术的主张,另一方面也针对艺术神话神秘化和空洞化艺术的主张。在此之后,黑格尔的核心任务,就是为真正现实的艺术科学及其感性显现奠基。然而在伽达默尔的理解中,“艺术的消逝”却指向现在正发挥作用但终归要被超越的那些时代艺术教化,指向要被形而上学的概念思维所倾覆的艺术理解,以及艺术在哲学体系中的过渡性地位。正因如此,伽达默尔才不厌其烦地强调,“艺术的消逝”在黑格尔那里代表着启蒙时代的救赎历史的“最后铸造形态”,这种形态的真理只是最早呈现在艺术中,但很快就会被基督教人本主义教化传统的自明性及其概念规定所彻底吞没。只有在海德格尔对存在-神-逻辑学(黑格尔是最突出代表)的批判之后,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艺术作品自行设立为艺术作品的问题才重新变得急迫起来,它同时意味着对旧日那种教化的反抗。(20)Gadamer, “Ende der Kunst? Von Hegels Lehre vom Vergangenheitscharakter der Kunst bis zur Anti-Kunst von heute,” in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Band 8), sthetik und Poetik I, Kunst als Aussag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3, S.208ff.不难看出,本文之前列出伽达默尔的三个反“黑格尔”的论题,都紧密围绕着此展开,但也都完全忽略了黑格尔美学从一开始在上述两种艺术立场之中寻求中介融合的真正目标。
三、“美的艺术”的客观性:被伽达默尔误解的黑格尔
不恰当的“反黑格尔”论题说明:伽达默尔在进入黑格尔美学之前,就已经想要告别它。而对黑格尔美学的深入考察将揭示其理解的谬误所在。作为科学的美学,其对象就是美的艺术,这一在《美学》中开宗明义的说法,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理解,而是面临着诸多的反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批评美的对象不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美只是感觉、游戏,是欺骗性的假象,而非严肃的思考,也不关乎真理。黑格尔对此的答复是:美学的对象不仅不是假的,而且正是存在和真理自身的一种特别显现(schein)。(21)黑格尔认为不存在无真理意义的Schein,且Schein甚至最初就必须存在。参见余玥:《本质与幻相:哲学史视野下黑格尔逻辑学本质论开端处的给予性问题》,《现代哲学》2018年第6期,第71-80页。但与伽达默尔引入柏拉图来说明对此真理传统的显现和回忆根本不同,黑格尔对此自由显现的阐述始于一种康德式的现代处境,即精神在其自身进程中产生出来的诸如认识与欲望、自然与自由、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等分裂,只有通过美的显现才能得以中介调和,并深入更高的统一。换言之,美的艺术的显现并非向着源初存在的返回步伐,而是针对分裂现状的和解性精神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分裂现状一方面表现出黑格尔对当时艺术整体状况的极度不满——而非如伽达默尔所暗示的,黑格尔认为艺术理解在其时代已经完满或接近完满了;另一方面也指向黑格尔对美的艺术在现代能够发挥的克服分裂的现实作用的重视(此种分裂当然也表现在唯理论倾向和艺术新神话主张的张力之中)——而非如同伽达默尔接续海德格尔所主张的那样,美的显现是存在之道说来自远古的召唤。
正是出于对美的显现这种中介及和解作用的重视,当回顾美学进程时,黑格尔不是从鲍姆佳通而是从康德开始的。正是康德开始将美作为沟通割裂的认识与实践、自然与自由的中介。但黑格尔并不满意康德完全将美放在主体中的做法,因为它使得美的客观效应无法被讨论。由此,他才转向席勒的《人的美学教育书简》,认为“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的主体性与抽象性,敢于尝试超出它们,去以思想的方式将统一与和解把握为真,并以艺术的方式将之现实化”。(22)G. W. F. Hegel, Vorlesung über die sthetik I (G. W. F. Hegel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13),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70, S.89.的确,席勒美学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美的艺术的中介和解作用,以现实可行的方式,为未来的良善政治造就有教养之人的根基。他因此将康德那种审美与道德、政治只有若即若离关系的主张,重新铸造为一种美与善相结合、主体理想与现实情境相平衡的理论。相较于主体性的美,这种具有现实作用的客观美更吸引黑格尔。
相比之下,伽达默尔对席勒兴趣不大。在《真理与方法》的相关段落中,伽达默尔只是说通过席勒的审美教育,“在真正的道德和政治自由——这种自由本应是由艺术提供的——的位置上,出现了某个‘审美国度’的教化,即某个爱好艺术的文化社会的教化”。但他恰恰放过了其中最关键的“美”的客观和解作用,反过来批评这种共同体中“美和艺术所提升的情感自由只是在某个审美王国中的自由,而不是实在中的自由”。(23)以上引文均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 第106页。这一难以为席勒研究者接受的说法引导伽达默尔得出席勒主张的教化普遍性终将崩溃的结论。他没有考虑到,席勒(与黑格尔一样)恰恰是因为非常严肃地看到了当时艺术的分裂多元状况,才在更广博的精神中去考虑艺术与其他精神性媒介(如政治和历史)的互动统一关系的。
必须指出,审美教育对于席勒是一种有待实施的疗救方案,而非一种既成事实。艺术教化在席勒和黑格尔时代的实际状况,也并不等于二者对艺术教化的现实疗救功能的分析与寄望。我们更不能因此认为艺术教化的现状与其疗救理想间只有一种不可克服的二元论,所以基于后者的美的普遍共同体在现实中必定瓦解。相反正是由于实际状况的糟糕,才急需疗救方案的客观实施。对黑格尔来说,这就需要建立关于美的艺术的精神科学,不仅从主体层面,且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政治现实效果的客观层面,为自由美的调解作用做辩护。而伽达默尔似乎混淆了这二者的区别,才将当时艺术教化的实际状况当成了席勒和黑格尔艺术教化方案实施产生的效果,且这种糟糕的效果反过来又证明了此教化方案的不可行,因此伽达默尔才主张跳出现代,向古老的传统寻求答案。这种对现代方案的误解同时也导致伽达默尔一个更成问题的偏见,就是不恰当地强调那种在当时实际状况中“正在发生的未来”,强调时代精神对过往的扬弃,并将之与“艺术的消逝”和哲学超出艺术的体系进展联系起来,却没有顾及黑格尔已经对此种作为“正在发生的未来”的时代精神做过严厉批判。
关于此批判,黑格尔在肯定席勒通过审美教育将分裂的精神与自然统一在当下现实生活中这一贡献后就进一步指出,这种想法发展到谢林就形成了一种理念,一种“绝对观点:即使艺术早已开始主张其与人的最高趣味相关的那种独树一帜的本性和尊严,但也只有到了现在,艺术的概念和科学地位才被发现,并且它——即使这在某方面看来是过头和偏颇的(此处未及详论)——才在其高迈真实的使命中被接纳”。早已被主张的艺术尊严只有在现在才被作为概念和科学发现,并被作为艺术高迈真实的使命,这对应着对时代精神的现时艺术理解的重视态度,而被伽达默尔认为是黑格尔的主张。但此处却明白显示,它其实是被黑格尔自己批评为“过头和偏颇”的主张!其理由虽然“此处未及详论”,但在讲座关于“艺术美或理想”的部分却已经给出。(24)Hegel, Vorlesung über die sthetik I, S.91f., 316-361.在那里,黑格尔再次强调,理想与实在的协调一致是需要人的艺术活动来创造的,而这种创造是在精神世界的关系总和及其客观现实表现中以广博的方式进行的。然后他分别批评了此种创制活动在涉及与过往关系时的两种偏颇主张:1.主张艺术是时代性的,艺术家要扬弃过去的时代,专注于自己的时代文化,而受众也是在此中来理解作品的;2.主张艺术家要客观按照题材的内容和时代来处理作品,对过去时代谨守忠实。显而易见,第一种主张正是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持有的主张,而黑格尔事实上却是它的批判者!
黑格尔批评第一种主张“偏颇”的理由在于,侧重时代文化的艺术完全可能是出于对过去的无知、文化修养的缺乏,对自己时代文化偏执的骄傲或者单纯迎合观众日常偶然的主观意见才被创造出来的,因而都难以摆脱主观性,也经不起精神科学的检验。这再次表明黑格尔对其时代艺术糟糕处境的明确认识。而黑格尔自己真正的主张,即对时代与过往关系处理的“真正客观和适配方式”,(25)Hegel, Vorlesung über die sthetik I, S.353.正是一种古今和世界各民族精神的对话的方式。之所以是“民族”,因为艺术不是小圈子品味可以限制和规定的,而是在时代之中发挥着效用,并由之呈现自身且被受众直接认可。这一在广阔精神领域之中的创作和接受的交互作用共同体,就被称为“民族”;而之所以要求对话和适配,则是因为各民族在各时代所作出的艺术作品都是其自身广博精神的直接呈现,并能为其他民族以共通的感受亲切生动地觉察,进而唤起更深沉、系统的交互理解可能,而不会让自己沉沦于其身处共同体的那些庸常见解中。只有通过这种特别的对话和适配,才有了人类共同体的内心生活的客观内容和实现。而只有在此自由显现出来的美的艺术,才是人道的和有力量的,也才是真正客观的。
这一主张听上去类似于伽达默尔阐释学美学的核心见解,但其相似性有限。这是因为当伽达默尔谈论对话时,他无法说明:诸种美的艺术既然都是对传统的创造性回忆和诠释,那么这些诠释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以至于它们能逃脱无所不包的源初性传统,并发生真正的差异性对话?难道仅仅是因为引发对话的“遭遇”和“击打”不一样吗?事实上,一切真正完满的对话都试图“将一个陌生视域带进自己视域的不足,以实现在其他性中理解他者”,而非在传统的笼罩性下空洞地表露震惊感受,但它们全都只不过是传统的变形而已。(26)参见佘诗琴:《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核心悖论——弗兰克的一种视角》,《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第33页。此文中关于黑格尔与伽达默尔关系的见解同样并未真正顾及黑格尔本身的思想。相反,为黑格尔所看重的艺术呈现及其客观效应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绝不是通过对源初性传统的创制性回忆就可统一的,更不是由对此传统的不同诠释活动所造成的。多元艺术的对话因此也根本不是伽达默尔的美学阐释学所能肩负的工作,后者与法学阐释、宗教阐释等不同,独树一帜地指向对源初传统的那些创制-模拟活动。对于黑格尔来说,美的艺术绝非那么独树一帜,而是既关系实际民族-社会-政治状况,也关系不同的认知模式、情感表现、作品分类和思考图式,它是一切精神活动的一个真正值得重视的综合点。举例来说,当黑格尔分析浪漫型艺术的时候,就区分了天国的、尘世的和独立个体三种形态,它们分别关系到基督教、中世纪政治文化生活和近代个体兴起,涉及从罗马民族到近代欧洲各民族之精神表现,以及其彼此间的相互对话、影响和统一。在每一小类型内部,又有更多精神原则被引入,如在天国型艺术中涉及新约文化影响史、宗教之爱及其影响下的团契生活和社会表现;在尘世型艺术中讨论罗马政治的荣誉原则,家庭之爱及二者的现实冲突和混合;在独立个体型艺术中研究日耳曼民族戏剧(莎士比亚)及民间诗歌与近代下层阶级的关系,他们的投机冒险对世俗生活的影响。这一简短的概述已经能让人体会黑格尔“客观”美学的综合性和现实性究竟何在。
当然,正确理解美学的综合性和现实性,同样要避免将之看作仅是服务于民族、政治与社会效用的工具甚或将它们混为一谈。美的艺术之所以是绝对精神和自由的显现,恰恰因为它不是现代唯理论希望利用的手段:所有美的艺术作品都是因为其是民族精神自由创作和对话的显现,而非因为它们曾服务过当时的现实需求,才成为艺术史中永恒的伟大作品的。作品的永恒性与它们携带着现时信息并具有现实作用虽不矛盾,但艺术作品的意义不仅不会耗散在诸种各有所求的实践活动的现实作用之中,相反,它让这些作用的根本一致性以可传达和交流的方式在表象中呈现出来并永恒化。正因如此,美学才不是诸实践科学中的一种,而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并且更为重要的,诸种具有精神一致性的艺术呈现及其历史进程,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有着具体的承担者的,它就是那些主体性的民族共同体:即使古希腊及其艺术的当时效用早已消亡,但它至今仍展现着该民族绝无仅有且无比广博的精神。相形之下,尽管伽达默尔也反对艺术工具化,但在他那里却很难找到自由艺术显现和对话进程的不同具体承担者。因为既然同为对源初传统的创制性回忆,柏拉图相比于莎士比亚的希腊人身份,真的有何特殊吗?而当一切主体性的特殊承担者都被抽空之后,对话究竟是由谁在进行,又如何不至于空洞呢?
“艺术的消逝”不等于艺术的概念化,更不等于艺术的当下阐释化,统一的传统也不能抵御它。对于黑格尔,它更是一种在走向精神的客观综合前,为清理战场所开展的批判活动的信号弹。在今日诸美学家中,一定程度理解此信号意义的人是郎西埃,尤其是他在《美感论》中将黑格尔刻画为“自由民众艺术”的捍卫者的时候。(27)郎西埃:《美感论:艺术审美机制的世纪场景》,赵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6页。这些民众所理解的艺术,就是他们在其感性生活中所结成的共同体的表达,而这种感性生活又总是处于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乃至哲学的开放性关系之中,它们的界限和分隔远没有它们的联合和互动重要。
结 论
黑格尔三版《哲学百科全书纲要》由客观精神向绝对精神过渡部分都说明,从各特定民族的实践通向众民族的普遍精神的交互实现,就是艺术概念产生的最重要关键。(28)参见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纲要》,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817年,第208-209页;1827年,第349-353页;1830年,第381-386页。客观精神之客观性的最稳固表现,即民族国家制度和法规范,在各民族国家战争与和平交织的世界史中,只是动荡的和未完成的,正因如此,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才有“明日之国”的可能,它被黑格尔以预言的方式指向美国。(29)参见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298-303页。但这并非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于:如果在动荡的世界历史中,每个民族实践创造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那么真正能作为普遍精神现实地保留下来的究竟是什么?——唯有后者,也就是能够经历作为世界法庭的世界历史的审判并显现出永恒性的东西,才是对于绝对精神而言客观的东西:譬如希腊人的城邦和法制已经消逝,但希腊人的艺术永存。这艺术绝非一段残梦,而是在当时德国文化和政治中最鲜活有力的精神现实力量源泉,并且这一力量也绝不会仅限于在“当时”“德国”发生作用。每一个民族,如果它是伟大的,就都和希腊一样具有这种不被实际政治制度实践所限的力量。借用黑格尔早年关于绝对精神的说法,这些不同的力量就像许多被打断了时间进程的、差异化的直线,然后又被合并成一束,“它们同时对称地自行连接起来,于是每条线在其自身内各自形成起来的那些相同的差别,就汇合在一起了”。(3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4页。在对永恒差异进行永恒综合的现实力量进行概念分析之前,仅仅以直观的方式,人们已能觉察到为什么黑格尔所言“真正客观和适配方式”是一种古今和世界各民族精神对话的方式。
因此,放弃从永恒艺术与客观世界史的以上交合点去理解黑格尔,仅仅强调艺术在某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体系中的初阶地位——这些目前流行的、关于黑格尔“艺术的消逝”的论调——太过偏颇,把黑格尔变成某种单薄时代精神的卫道士的做法更为荒谬。伽达默尔对此的思考当然远为深入。但即使如此,他也仍不能回避以下反问:将黑格尔美学定位在“正在发生的未来”上充分吗?将“艺术的消逝”与启蒙时代的救赎历史绑定在一起合适吗?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将艺术优先置入永恒差异化进程中去的现实综合活动,优先突出所有艺术的共有源泉(即发生意义上的传统)的做法不会掏空艺术作为特殊者的特殊性吗?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回答仅是:不会,因为总有不同的击打和阐释,那就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该问题所关心的焦点正是这些不同之处从何而来。即使补上阐释“偏见-前见”之在先性说明也用处不大,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偏见是如何成为这样而非那样的“偏见”的?它的现实形成机制是什么?黑格尔的美学和整个绝对精神就是要深入对此问题的探究,这些探究在今日关于“艺术的消逝”的讨论中并没有被公正严肃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