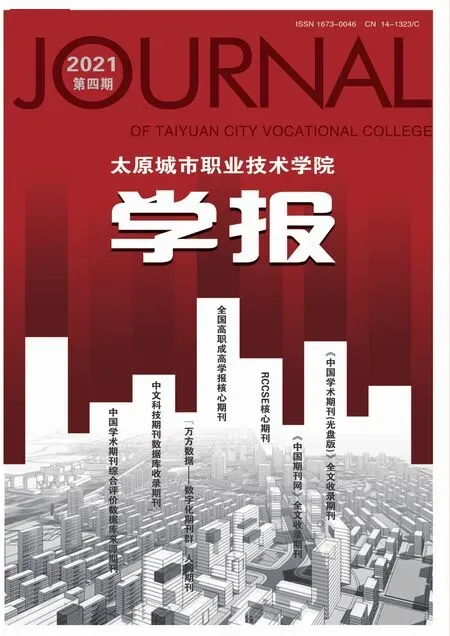钟嵘“直寻”说与王夫之“现量”说之比较
■王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一、理论来源
(一)“直寻”说的理论来源
《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讨论诗歌的美学专著,其作者是南朝的诗论家钟嵘。它是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钟嵘在《诗品》一书中提出了诸如“吟咏性情”说、“滋味”说、“诗有三义”说等著名的文学理论。相对而言,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的“直寻说”并未如前三者一样妇孺皆知,但在崇尚雕琢矫饰的齐梁文坛,却吹来了一阵新风,其跟随《文心雕龙》的脚步,举起了反对形式主义的大旗,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钟嵘的“直寻”说对后世严羽的“妙悟”说、王夫之的“现量”说等诗学理论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追根溯源,“直寻”首次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直”在这里是伸直的意思。“寻”是古代的量词,大约八尺。这个成语比喻在小处忍受一些委屈,来换取之后较大的好处。再有宋·朱熹《答吕子约》:“幸甚,幸甚,枉尺直寻,素未尝以此奉疑也”。此后,“直寻”作为一个固定词语使用。而在《诗品序》中,钟嵘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意味着观照古往今来的著名的诗句,大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直接抒写,在这里则明确提出了“直寻”说,“直寻”作为一个诗学理论术语,第一次被正式提出,至此独立出来,完成了从一个普通词汇到诗歌术语的飞越。
“直寻”亦是对《诗经》感兴传统的继承。钟嵘有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句话的意思是气引起了物的变迁,物的变化又引发了人的感受,人们感受到了这一点,故作诗歌来对此吟咏。“直寻”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直抒胸臆,或者仅仅是反映事物。这涉及到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的构建:人作为世间的“三才”,起着中介的作用,通过感受外物,达到内心的呼应,即景而作,好的词句自然会脱口而出。“直寻”强调直觉、情感、形象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诗经》中的“感”是有感于外物之感,“兴”亦是即景即情之兴。这与《诗经》中的感兴传统不谋而合。
(二)“现量”说的理论来源
王夫之,又名王船山,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论家,著有《唐诗评选》《名诗评选》等理论专著,对古典美学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其中,“现量”说也是王夫之最重要的一个诗学理论。“现量”一词在王夫之论诗的文字中一共出现过七次,“即《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两次,《古诗评选》一次,《唐诗评选》两次,《明诗评选》一次,《姜斋诗集》(《题卢雁绝句序》)一次”。
“现量”最早是作为一个佛家用语而出现,其最终是作为一种教义来阐释“心”与“境”之间的基本关系。王夫之把“现量”这个概念引进美学领域,首先,用来说明审美意象的基本性质,即审美意象必须从直接审美观照中产生;其次,是对钟嵘“直寻”说和严羽“妙悟”说的继承和完善。
二、意蕴分析
(一)“直寻”说的基本内涵
1.“直寻”说的基本条件
在近年来对钟嵘“直寻”说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直寻”的理解不外乎两种:一是直抒胸臆,二是直接反映事物。笔者认为“直寻”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直抒胸臆,或者直接反映事物。前者忽视了物作为引发情感的中介物的存在,后者机械地被动反映事物,则在很大程度上会陷入丧失作家主体性的怪圈。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直寻”这一诗歌美学理论,因此想要正确理解这一思想还需要深入《诗品序》的文本进行细读。
“直寻”首先是在物的基础上进行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句话的意思是气引起了物的变迁,物的变化又引发了人的感受,人们感受到了这一点,故作诗歌来对此吟咏。然而钟嵘所说的物并不只限于自然之物,春鸟秋风、秋蝉夏云、暑雨冬月会给人带来感触,社会的变迁也会给人带来触动。钟嵘将物的范围延伸到社会层面,走出了狭隘的定位,将诗人与时代的兴衰紧密相连。楚国的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姬妾离开宫廷,北方的荒野上尸骨乱生,魂魄和飞蓬相互追逐,将士们举着武器在边地戍守,保卫家国……诗人见证了时代的动荡,触景生情,写出诗句感叹民生疾苦,时代动荡,百姓流亡。情的抒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由此可以看出,钟嵘所说的“直寻”并非一味地无病呻吟,为文造情,而是在物的基础上进行深发,达到内心的呼应,才有感情的抒发。所以,物的存在是“直寻”说提出的基本前提。
由物产生了情的深发,自然要将情落实到实在,这需要借助一定的修辞技巧。《诗品序》中说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已经写完了,而有余音绕梁之意叫做兴;表面写物,实则在抒发自己的志向,称作比;直接铺陈叙事叫做赋。能在创作中妥善运用这三种方法,那么就能达到诗歌的极致。因而赋比兴这三种修辞手法在情向诗的转换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而“味”则是“直寻”所要追求的诗歌最终的表达效果。“滋味”说是钟嵘又一著名的诗学理论。一首诗歌想要做到有“滋味”,就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人触物生情,有感而发,心中已经有了所写诗歌的框架和内容,通过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让心中所想进一步物化,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满统一。
2.“直寻”说的基本原则
《诗品序》第六段开头将筹划国事的文书与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与诗歌分开。前者可以广泛地用典,引用古事,但是论及诗歌,钟嵘则发出了至于吟咏性情,抒发言论,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的思考。紧接着,钟嵘引援了四个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思君如流水”所写即是所见,并非来回揣摩之语言;“高台多悲风”也是眼之所见,身之所历;“清晨登陇首”亦是诗人登陇所感,并非出自典故;“明月照积雪”并非出自经书典籍。钟嵘在这里强调了意象的重要性。紧接着,钟嵘批驳刘宋大明、泰始中,诗文胡乱用典近乎抄书的风气,并指出任、王融等人为追求文章的奇特,局部多处用典而损害了文章整体。从这里可以窥见,“直寻”除了要满足形象性和非用典两个原则,还需要满足直接性的原则,即不要逻辑推理,它所追求的是一种直观、直接等非理性感受。最后,“直寻”还要遵守契合性原则。这又回到了开篇谈及“直寻”说的理论来源时所提到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的构建:人作为世间的“三才”,起着中介的作用,通过感受外物,达到内心的呼应,即景而作,好的词句自然会脱口而出。
综上所述,“直寻”要满足形象性、直接性、契合性、非用典四个基本原则。
(二)“现量”说的基本内涵
1.“现量”说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相宗络索》:“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王夫之在《相宗络索》中对“现量”下的定义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思:现在、现成和显现真实。现在,是指诗歌传作要立足当下,要立足此情此景,而不是对过去进行回忆;现成,是指凭借直觉,排除理性因素,一旦有所感发,就立刻下笔,不经过多余的思考;显现真实,是指对事物的描绘要力求真实,全面展现事物的本质,不能掺杂虚假。
2.具体文本分析
王夫之引用了“长河落日圆”“隔水问樵夫”两个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诗人使至塞上,目光所及之处,均是边陲大漠中的壮阔奇景,意境开阔,气象雄浑。诗人站在一座高山之上,看着巨大圆润的落日倒映在宽广的大河中,触发了诗人内心的情感,当即写下“长河落日圆”这一千古佳句。这句诗中仅仅是景物的出现,但得到了诗人内心情感的观照,赋予了景物审美的意义。不多说一字,就将对大漠奇景的赞叹、对祖国幅员辽阔的自豪、对戍守边疆的豪迈,即刻跃然纸上。另一句说的是诗人上终南山游玩,流连忘返,最终决定在终南山上借宿一夜。无奈山上人迹罕至,诗人顺着砍柴声前来寻找,发现了山涧那边的樵夫,询问他哪里能够住宿。诗人立足当下,不假思索地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感,不加其他的雕饰。诗人将砍柴的嘣嘣声、溪水的叮咚声和诗人与樵夫之间一问一答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了一丝生气,看似平常之语,却是全文画龙点睛之处。由此可见,即情即景而作的诗句自然比反复推敲的诗句更有灵魂和韵味。
三、“直寻”说与“现量”说两者之比较
(一)“直寻”说与“现量”说之同质性比较
1.对直接性、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把握
直接,即在一种直观感悟中心与物直接对话,无需逻辑推理作为中介。“直接性”是钟嵘“直寻”说的基本原则之一,王夫之“现量”说的特征之一就是“现成”,二者均指凭借直觉,排除理性因素,一旦有所感发,就立刻下笔,不经过多余的思考。王夫之认为,立足当下直接把握,自然是最妙。再有,两者均强调情感的作用,两者均认为要在外物上赋予情感才能作出好诗。
2.强调物与人的统一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诗人的创作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物的基础上一触而发。王夫之认为事物本身就具有美的属性,钟嵘也说在外物感发的基础上作诗。物的存在是诗歌创作的客观条件,主观则要依靠人作为中介主体进行作用。“直寻”说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契合性原则,即为物、人、情三者的统一。这又回到了开篇谈及“直寻”说的理论来源时所提到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的构建:人作为世间的“三才”,起着中介的作用,通过感受外物,达到内心的呼应,即景而作,因景生情,好的词句自然会脱口而出。可以说,没有人对物进行观照,物就仅仅是自然之物,没有作者感情的投射就无法成为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对象。王夫之的《诗广传》中也说道:“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浮照兴类”。在这里,王夫之也强调“人心”要与“天化”相值而取。外物本身就具有美的属性,经过诗人的审美关照,才能达到汇通的境界。
(二)“直寻”说与“现量”说之异质性比较
1.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的创作理论
王夫之“现量”说的第三个特征,即显现真实。显现真实,是指对事物的描绘要力求真实,全面展现事物的本质,不能参杂虚假。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而这一点在钟嵘的“直寻"”说中却几乎没有涉及。对事物的描绘力求真实,王夫之强调要多角度、全面地反映该事物,不能过于笼统。对事物的描绘力求真实,也并非一味排斥虚构。诗人在尊重客观事物与规律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加以虚构,体现了王夫之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创作理论。
2.对时空维度的把握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提到“身之所历,目之所限,是铁门限。”在这里,王夫之强调作诗一定要写自己真实经历过,眼睛看见过的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限。王夫之在下文中提到了王维写自己登终南山的例子:中间的主峰耸起,把终南山东西山脉相隔开来,不同的山脉阴晴的状态都有所不同。这是诗人登上终南山后极目远眺,方能写下的所感所得。诗人能写出这样变化多端的奇异景象,必定是亲身看到奇景后的真实记录,如果仅凭一己的想象,必定很难做到这一点。接下来,王夫之还以杜甫的《登岳阳楼》为例,杜甫在登上岳阳楼后看见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写出了“乾坤日夜浮”这样的佳句。如果不是杜甫亲眼所见洞庭湖容纳天地、包罗万象的奇景,必然写不出这样气势磅礴的诗句。相较而言,钟嵘更强调的是直观性、直接性,而王夫之在这里则更为强调“身之所历”,即时空性、在场性,强调对时空维度的把握。
综上所述,王夫之在对直接性、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把握,强调人作为中介主体的作用等方面对钟嵘的“直寻”说中的观点有所继承;其在钟嵘“直寻”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创作理论以及对时空维度的把握,丰富了其自身提出的“现量”说,也是对钟嵘“直寻”说的超越。
四、思想意义
钟嵘的“直寻”说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王夫之的“现量”说也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现量”说既与“直寻”说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两者均丰富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内涵,指导了诗歌创作实践,为后世诗歌品评提供了自身的一套标准。它们所产生的巨大的思想意义表现如下:首先,对形式主义诗风的拨乱反正。在崇尚声律和骈偶的南朝,刘勰与钟嵘相继举起了反对形式主义的大旗,提倡即景而作,即心而作,无疑对过于精雕细琢、缺乏内涵的南朝诗歌具有警示作用。其次,作家反对形式主义诗风的勇气和作为文人对现世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是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钟嵘和王夫之不仅关注自然景物,还将眼光投射到社会现实上,表达对人生和现实的关注,这种积极的入世思想值得肯定。最后,丰富了我国古代早期诗歌的创作理论。钟嵘提出的“直寻”说和王夫之提出的“现量”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