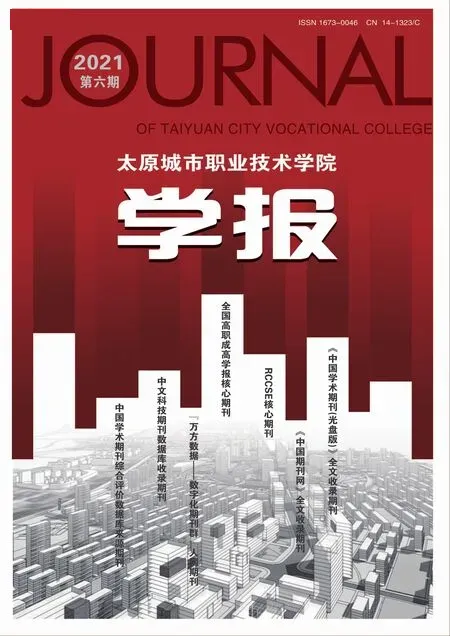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
——从契约文书谈起
■陈古目草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敦煌,自古就是丝绸之路重镇,曾一度辉煌。安史之乱后,吐蕃迅速控制陇右及河西走廊乃至西域大部,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开始,将敦煌作为其统治河陇西域的据点,统摄管理各部落军政民生事务长达六十多年[1],在此期间吐蕃统治者分封部落,编辑户口,将13个乡的原著汉人,孙波、吐谷浑等族人及僧人、道士等前后划分为12个部落[2]。这些部落民只是身份的变化,其实际的生产生活与唐王朝统治时期基本一致,也需要服徭役,缴纳赋税,战时则要应征入伍,去前线作战[3]。吐蕃统治后期,民族关系缓和,汉族和其他民族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相关契约文书就直接反映了这种现象。契约是经济法律类应用文书,记录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文书中的经济交易往往发生在各民族之间,他们贸易平等,各族人民互助交流,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民族交融的缩影。
一、统治机构的契约管理
吐蕃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以建立部落组织为基础,分部落之后,依然在其内部施行唐时制定的户籍制度,计口授田,维护其原有的经济能力。为了管理高效,吐蕃在敦煌建立了层级严密的军政管理系统,兼理经济民生[4],吐蕃按其自身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杨铭、刘忠等认为敦煌在吐蕃统治期间设置的部落之内,又将其本部的将、十户制与唐代的乡、里制相结合,实行了十将、五岗制来编制民户[5]。吐蕃依靠这一套社会制度管理军民,逐步稳定社会经济,使当地由占领初期的对抗、混乱逐步走向了井然有序。吐蕃吸收唐制建立的这套制度,其实际内涵与唐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稍作顺应调整,依然组织严密,运行高效。看ITJ844、ITJ914、ITJ1379《发放堪布图登三次口粮契约》第一,ITJ844号:
……
6.2月11日,将小麦蕃斗半四升交于旧管粮官卢彼赞。
7.彼费所开收据之证人为:范悉诺历,左国仓。
8.张鲁历等盖印作证。
9.(倒写)(缴粮)指令完成,契约盖印。(陈践译文)
这份文书记录的是堪布领取口粮的契约。文书末有范悉诺历、左国仓、张鲁历等盖印作证,并主管官员签署盖印。由文书内容可知,诸寺户纳粮,有专门官员负责契约文书管理,一一记录备案,(还粮)指令完成,即有官员在契约上盖印,记载详尽。不仅如此,S.5820、S.5826《未年(803)尼明相卖牛契》、S.1475v《寅年(822?)令狐宠宠卖牛契》等文书,也是初订的私契,后需经专门的官府机构专管官员核查取得正式的契约文书才算交易完成。陆离先生详细分析了其交易的过程[6],他也认为这一时期吐蕃经济管理制度继承学习唐朝,如果有买卖交易则先立私契,后上报官府(节度使衙),经官员核实后进行批复并订立正式官方性质的市券。大量的私契、市券文书即可说明这一经济活动清晰的管理层级审批制度。随着吐蕃统治的深入,社会制度也在渐渐完善。吐蕃在学习唐朝先进制度的同时,其本土民间习惯法也融入其中,体现着吐蕃统治下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独特风格。
二、寺院与民间的契约关系
吐蕃历任赞普采取了各种措施大力兴佛,蕃占时期,佛教在敦煌盛极一时。除去寺院属民制和养僧制度外,吐蕃沙州官府也不时向寺院布施钱粮[7]。因此,僧人拥有财富,寺庙将这些上供的多余粮食以及钱财物品借贷给民众,就产生了僧俗之间的契约文书。这类契约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未违约情况下没有利息,百姓极欢迎,因而在敦煌契约文书中数量较多,且个别保存完好。
(一)寺院僧人产生的契约
依据寺院和僧人财力的多寡,一般在大寺院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僧人能够进行牛驴等大宗商品的买卖,而规模较小的寺院就不具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其僧人只能进行私人小件物品的租赁,或许连供养的寺户也没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卖东西为济。如S.5820、S.5826《未年(803)尼明相卖牛契》即可为证,其契文如下:
1.黑牛一头三岁,并无印记。
2.未年润十月廿五日,尼明相为无粮食及
3.有债负,今将前件牛出卖与张抱玉。准
……
7.有人先悔者,罚麦三石,入不悔人。恐人无信,
8.古(故)立此契为记。
9.麦主
10.牛主尼僧明相年五十三
11.保人尼僧净情年十八
12.保人僧寅照
13.保人王忠敬年廿六
14.见人尼明香。
VP1435《某部落尼帕都购牛契》(杨铭译文)也有相似情况记录:
僧人(ban vde)帕央(Dpal byang)向……部落的尼帕都(Gnyi apal vdus)买一头双角黑色母牛,价值一两半银钱(Srang)[1-2]。
……
对此签定的契约,证人苟录赞(Mgos klu rtsan)、张德通(Gzham de rton)等[签章][6-7]。
(倒书)…… [玉]通[8]。
以上第一件文书中的尼明相,为寺院僧人,因为没有粮食而且有债务,不得已卖牛,买主张抱玉是个汉人,为他们的这次买卖作保的僧人有净情、寅照、明香等。违约惩罚条款显示:如果牛有问题,或者有人毁约要赔给对方相应财务。与之不同的是“尼帕央”,VP1435《某部落尼帕都购牛契》是一件买牛契约,买主是个部落尼,“帕央”“帕都”二词为藏语音译,说明他们是少数民族,帕央向尼帕都买了一头牛,价值一两半银,价值不菲,他有这个经济实力,说明身份非凡。为这次买卖作保的人有苟录赞、张德通,还有一个人名“玉通”,或许是当地的官员,签名签发。这两位僧人的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但他们见证了在吐蕃统治下的社会底层生活,同时他们也起到了民族沟通的桥梁作用。
(二)百姓向寺院的借贷契约
百姓为生活所迫,经常向寺庙、官府等举债,这一时期有大量百姓向寺院借贷的契约,最根本的原因是寺院财力雄厚,有众多的寺户,特别像永寿寺、图灵寺等大寺,更是百姓借贷的首选。吐蕃推行的“七户养僧制”在敦煌产生了影响,所以寺院有了多余财富,可借给百姓,这其中最多的就是借粮契约。看P.4686《子年(832?)悉董萨部落百姓孙清便粟契(附便豆二笔)》:
1.子年二月廿三日,悉董萨部落百姓孙清为无粮用,今于永寿寺便佛物
2.粟汉斗参硕。其粟请限至秋八月末送纳。如违,倍,仍任掣夺家资,用
3.充粟直。如身有东西不在,及依限不办填还,一仰保人等依时限还
4.足。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为凭。便粟人孙清(朱印)(朱印)
5.保人兄孙昌奴(朱印)
6.见人
7.见人僧宝积(署名)
……
以及P.3730v《未年(839)纥骨萨部落百姓吴琼岳便粟契(附龙华子便谷凭)》:
1.未年四月三日,纥骨萨部落百姓吴琼岳为无粮用,今于永寿寺僧手下便?(一)
……
4.便粟人吴琼岳(朱印)保人男恩子保人僧灵俊(署名)
5.保人男悉弘洛 悉弘洛易五月十一日吴琼岳便豆两硕捌斗 琼岳洛易
6.保人男钟爱保人僧
7.未年四月四日,纥骨萨百姓龙华子便捌斗贰胜 华子洛易
以上两件文书比较有代表性,都是百姓向寺院进行借贷的契约,文书中均未提及利息利率,由此可见,在不违约的情况下,默认没有利息。这样的方式有利于双方,寺院收取了人心,百姓也可解燃眉之急。文书中的“悉董萨”和“纥骨萨”部落是吐蕃统治后期新设立的两个军事性质的部落,其部民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民族,他们是由早期设置的“擘三部落”以及“丝绵部落”“行人部落”等重新组织起来的。此时,吐蕃为了长期统治的打算,在会盟前后,调整了各项施政措施,汉人的地位相应有所提高[8]。
这类文书中的保人大多是寺院僧人,P.4686(藏文卷1297)《子年(832?)悉董萨部落百姓孙清便粟契》中的见人“僧宝积”,P.3730v《未年(839)纥骨萨部落百姓吴琼岳便粟契(附龙华子便谷凭)》中保人“僧灵俊”等,他们任僧职,或者与契主相识,参与了租赁事宜。其中最值得探讨的是一个名为“悉弘洛易”的保人,他当是少数民族无疑,在契约上三处签署,第五行开头有“悉弘洛易”,末尾有“琼岳洛易”,第七行末尾有“华子洛易”,都写在借粮记录的后面,极有可能是署名,“琼岳”当为“吴琼岳”,“华子”应是“龙华子”,那么这个“洛易”就有可能是“悉弘洛易”,只写名,形式一致。而第五行的“悉弘洛易”,中间墨点无法识别,有可能是在姓名上盖章,重复出现,作用与前一致。由此可见其关键性作用。这两件文书的契主都是汉人,纥骨萨部落的吴琼岳与这位“悉弘洛易”关系密切,说明当时各民族在大的部落划分下小杂居,相互之间以及与寺院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三、百姓之间的契约关系
百姓生活直接与土地相关,所以粮食种子、农具借贷占了敦煌契约文书的相当一部分。这类契约双方中有汉人、吐蕃人,而且文末的保人见人中还出现了其他民族的人。在吐蕃统治敦煌的中后期,百姓之间逐渐减弱了民族歧视区分;生产生活中表现出不自觉的民族交流和融合。观照百姓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可见有微妙的体现,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如VP1282(VoL 70.fol.13)《鼠年买妻契》(陈践译文):
1.鼠年冬,王乔乔买央绛长当悉诺和苏典之妹名诺当为妻,
2.此买卖婚姻,任何时候勿争议,勿反悔。若出现另外户主,或此女逃逸,
3.付与买方7两纯银,增加一倍偿还,或找一个身份相同者顶替,立
4.即付与(王乔乔)之外,按以往规矩,(卖方向买方)偿还该女之生活用费,契约当事人摁手印签字,
5.证人僧人益西、卢幡冠、僧人马和宋等人盖印6.(倒写)央绛长当悉诺签名。央绛苏典签名。
还有S.1475v《未年(827?)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卖地契》:……
2.未年十月三日,上部落百姓安环清为
3.突田债负,不办输纳,今将前件地
4.出买(卖)与同部落人武国子。其地亩别……
5.地主安环清年廿一
6.师叔正灯(押)
7.姊夫安恒子
8.母安年五十二
9.见人张良友
以及藏文写卷P.T.1297(3)《购马契约》契文如下:羊年春,尚腊桑与尚......在将军衙署.....比丘和尚张本嘉从蔡多部落甲杂腊赞处购马一匹,毛色、纹理为:儿马,白额,马身有叶状与骰点斑纹。……说合证人:论腊桑腊顿、论腊桑多子、吴高戎、周达来、哈华华、蒙达错、蒙尚结诸人,立契约盖印,马主和应诺人按指印,旧契由和尚本嘉掌握。牙登苏赞盖印以上三件文书中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买卖双方均属不同民族,第一件VP1282(Vol.70.fol.13)《鼠年买妻契》是一份婚姻买卖契约,从人名分析,买方为唐人王乔乔,卖方为胡人(非吐著人)央绛长当悉诺和央绛苏典,交易物为他们的妹妹诺当,买卖双方都不是吐蕃人,但却用藏文立契,看出藏文在使用上的价值。第二件S.1475v《未年 (827?)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卖地契约》中的安环清应是粟特安氏后裔[9],买方武国子是个汉人,为他作保的人有粟特本族人,也有汉人张良友,还有寺院僧人正灯,多个民族、不同身份的人参与了这一件文书的制定。P.T.1297(3)《购马契约》由吐蕃文翻译而来,很明显,买方比丘和尚“张本嘉”还带着他的汉姓“张”,而卖方蔡多部落甲杂腊赞是个吐蕃人,他们之间交易了一匹马。证人中论腊桑腊顿、论腊桑多子是具有官职的吐蕃人,他们极有可能作为专管官员见证了这次买卖。吴高戎、周达来等人应该是汉人。这三份契约中都至少有两个民族的人作为交易双方出现:(1)汉人——其他(非吐蕃)族人;(2)粟特人——汉人;(3)汉人——吐蕃人。吐蕃统治初期,这样的交易发生的几率不大,只有到了后期,社会发展,民族关系出现缓和,他们之间才能频繁地进行贸易。吐蕃的统治在这一时期相对宽松,其他民族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当地逐渐走向了社会秩序修复后的相对稳定阶段。
四、结论
在吐蕃统治敦煌的几十年间,汉蕃各族人民在这里生存交融。吐蕃王朝最初以战争取得敦煌地区的统治权,进入敦煌之后却没有野蛮地全面施行他们的奴隶制社会制度,而是逐步学习唐朝先进的社会管理政策,治理敦煌。从当时的契约文书看,保人、知见人和契约双方关系密切,政权统治逐步巩固,法令颁布,任命官员管理社会经济事务,为契约的制定提供官方的正式文书。寺院以不违约情况下的无息借贷为百姓提供粮食,寺户在为寺院纳粮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无息借贷的实惠。民间的借贷买卖形式多样,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牛马奴仆的交易,小到衣物碗碟的租借,不一而足,各个民族都参与其中,虽有法律规定的违约处罚,但保人见人仍愿意为契约双方作保,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逐渐展开。人民之间交流增多,民族关系也逐步改善,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是河西走廊上民族融合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