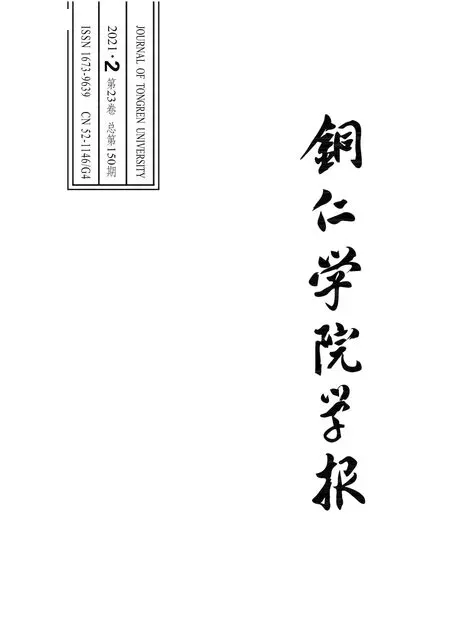充实而有光辉——读范子烨《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
张德恒
充实而有光辉——读范子烨《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
张德恒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范子烨《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积二十余年之功,对《世说新语》的原名、体例、成书情形、各种古注、日藏残卷进行深细考论,揭示《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内涵,析论《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描写手法,阐述《世说新语》与魏晋清谈之关系。该书由文本到文献、由文献到文化,对《世说新语》做出全面深入的探索,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考论详切、文辞丽雅,充实而有光辉,彰显出作者坚定的治学信念。
范子烨; 《世说新语》; 考论; 诗性品格; 治学信念
《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1](后文简称范著)是范子烨先生积二十余年研究心得撰成的一部“《世说》学”研究力作。作者在该书《绪论》中云:“自1991年9月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师从霍松林教授,即以《世说》为博士学位论文之课题进行相关研究,每恭承先生之音旨,未敢少怠,而学业遂有所长进。在1998年博士论文出版后,又发表多篇论文,不断修订增补,改正错误,新旧两合,乃成本书,前后历时将近二十年。二十年的笔耕,终于了结了一段难了的《世说》缘,在我的心灵世界中也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回声。”[1]6而据杨勇先生为该书所作《代序》以及范子烨《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2]之《后记》中相关记述,可知作者至迟在1985至1988年间既已“憧憬魏晋风流,狂读《世说新语》和嵇、阮诗文”[2]403并且多有心得、创见。正是因为此书乃作者厚积薄发、精义纷披之作,故在其“前身”《<世说新语>研究》完稿、初版之时即得到著名文学史家卞孝萱的反复赞誉。卞先生不仅将其收入《六朝文学丛书》中,并在该丛书《总序》中称道:“著者采用考论结合、由考立论的方式,对《世说新语》的体例、成书时间、编纂原因,敬胤《世说注》及刘孝标《世说注》,传世古抄本《世说新书》残卷,宋人对《世说新语》正文及刘《注》的删节,以及《世说新语》文本的疑难诸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著者对书中的故事原型、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亦多新的阐发。”[3]4而且在为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4]所撰序言的开首便说:“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先生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位质量很高的文学博士。1994年我赴该校主持答辩,很欣赏范子烨君的学位论文《<世说新语>研究》,后收入我主编的《六朝文学丛书》中,已经出版。”[4]1由此不难觇窥《<世说新语>研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世说新语>研究》相比,《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堂庑更为阔大、考论更趋详尽、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当然也更能体现作者攻研《世说新语》的卓越成就。
一、文本探原
范著共计十章,其中前两章对《世说新语》的原名、体例,以及成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深细考论。
考定《世说新语》原名《世说》。《世说新语》名称非一,或作《世说》或作《世说新书》或作《世说新语》或作“刘义庆《记》”,等等。孰为后先,孰正孰变?在鲁迅、杨勇,以及日本学者松岗荣志研究的基础上,范著进一步增广例证,考定《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在杨勇援引刘孝标《世说注》五例以证《世说新语》原名《世说》之基础上,范著复举《世说·雅量》第40条刘《注》之“《世说》虚也”[5]448、《世说·赏誉》第143条刘《注》之“则《世说》谬设斯语也”[5]583、《世说·捷悟》第6条刘《注》之“《世说》为谬”[5]688、《世说·贤媛》第13条刘《注》之“而《世说》云自不肯还”[5]803、《世说·惑溺》第5条刘《注》之“唯见《世说》”[5]1078,并结合刘孝标(462—521)之生活时代,尤其是《梁书》卷五十《刘峻传》“峻年八岁,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实悯峻,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6]701之记载,推论刘峻生年上距《世说》成书仅有二十二年,刘峻八岁时为宋明帝泰始六年(470),上距《世说》成书的元嘉十七年(440)仅有三十年,而彼时孝标已能识字读书,从而加强了刘孝标《世说注》中反复出现的《世说》即《世说新语》原名的可信性。不仅如此,范著复谓“宋末齐初之学者史敬胤,其为《世说》作注,距《世说》成书四十三至五十四年,比孝标作《世说注》早十六至二十七年”[1]9,而《世说·尤悔》第4条敬胤注有“《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也”[7]626之语,从而更进一步证明《世说新语》原名《世说》。不仅如此,范著更举唐李善《文选注》中多处引据《世说》的注文,并参以《南史》卷十三《刘义庆传》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从而定案《世说新语》原名《世说》,以“新书”“新语”附加《世说》之后,皆为后起之名。
《世说》虽为“纂辑旧文”“杂采群书”之作,但其内容之组合与编次实有统一之体例。范著指出《世说》总的编辑体例是“分门隶事”,而在各门之中,诸条目的组织亦具章法。首先是各门内容大致皆以时代先后为序,偶尔也会在此基础上关照内容主题,尽量做到“以类相从”。这就使《世说》的同一门中内容“颇有关联性,并由这种密切的关联性而使全书具有整体性,从而使全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1]20。其次是在以时间为序排列内容的基础上,集中记述某一人物或同一家族人物,如此便使记述对象相对集中、风神全备。至于《世说》纂辑旧文的具体方法,范著则概括出通常采用的五种:简择法,即简化旧文,择取其某一片段;增益法,即摄取旧文而增加新内容;拆分法,即将旧文之某一条拆分为多条;兼存法,情况有二,一是同条兼存,即某一条在论述某一故事或某种言语之时,标示其他流行的不同说法,二是异条兼存,即将同属一门而在言语、情节上大同小异之内容兼容并蓄;附注法,即于行文之末附加少许具有说明性质的文字,以方便读者理解,这些说明性文字,或揭示人物间关系、或彰显人物语言的背景与含义、或故作宕笔勾连今古、或评骘人物表明态度。作者进而指出五种方法中又以兼存、附注两法于“南北朝小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1]31,并说明“《世说》编者纂辑旧文,往往综合运用这五种方法”[1]33,如此便避免了读者胶柱鼓瑟望文求“法”。综上可知,作者实际从内容的外部编排与内部处理两个层面揭明《世说》纂辑旧文的方法。
关于《世说》的体例。作者既揭示出《世说》依门系事的体例乃渊源于刘向(前77—前6)《说苑》、应劭(153—196)《风俗通义》、干宝(?—336)《搜神记》,以及晋末宋初荀氏的《灵鬼志》,更深入考察了《世说》体例与“九品模式”之关系,而后者的考证则将看似松散的《世说》诸门类密结一处,显示出严谨的逻辑层次。作者由我国中世纪贯彻始终的选官大法“九品中正制”切入,指出其直接肇源于班固(36—96)《汉书·古今人表》,而“九品官人法作为横亘中世纪的政治选官制度,对我国当时的文学艺术发生了极其特殊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有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乃至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建构,都是基于九品这一文化观念而建构起来的,它们也因此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43《世说》之体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那由褒到贬,褒在前、贬居后,愈往前愈褒、越往后越贬的编纂次序正与“九品官人法”之“九品模式”相对应。作者并将《世说》各门名称与常璩(291?—361)《华阳国志》的人物品题语词加以比较,从而深刻揭示“九品模式”中的文化意蕴。在此基础上,作者上溯三代,厘清九品文化观念的历史渊源,下及唐宋元明清,列出受到《世说》“九品模式”影响的系列著作,从而将中国的“九品”文化,尤其是中古以降的深刻作用于文学作品的“九品模式”之发展脉络清晰呈现出来。作者并据此而最终定案《世说》原本当为三十六门(九的倍数),而“三十八”“三十九”门之说皆误,考论详实。
范著第二章“《世说新语》成书考”对《世说》作者及成书情况进行细致考索。自《隋书·经籍志》以降,下及《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乃至日本藤原佐世(828—898)《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在著录《世说》一书时,皆以刘义庆为该书作者。而萧梁时代的刘孝标在注《世说·假谲》第10条时所谓“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5]1008之“康王”必指刘义庆无疑,这就高度确认了刘的《世说》著作权。但自明代何良俊(1506—1573)以降,质疑《世说》作者为刘义庆者亦不乏其人,如何氏即谓“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世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1]56清代毛际可(1633—1708)踵承其说,谓“予谓临川宗藩贵重,赞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1]56鲁迅更进而推断,“《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1]56,且谓“《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抄撮故书之作,正和《幽冥录》一样。”[1]57著者复从语言风格之不统一、条目分类安排不当、记录同一言行而存异说等三方面各举例证,证实《世说》一书系成于众手。
那么,《世说》具体是由哪些人共同修撰完成的呢?作者依据“《世说》全书六万余言,编纂这样一部著作,编纂者本身的创作和言行不能不受其影响。同时,编纂者也必然具备与《世说》相近的文章水平和遣词用语习惯”[1]60的判断,通过将刘义庆及其幕下士袁淑、鲍照、何长瑜等人的作品与《世说》内容进行比勘,得出刘义庆文学水平迥在《世说》之下,而袁、鲍、何等三人皆为《世说》的撰写、编辑者。作者并从氏族谱系与文士交往的角度勾稽刘义庆及其幕僚与南朝名门大族相关人物的关系,进而将相关人物与《世说》之关系进行揭示,从而更加生动立体地还原了刘义庆及其门下士编纂《世说》一书的过程。关于《世说》一书编纂的时间和原因,作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考察《世说》所载由晋入宋人物之生卒年,并结合刘义庆出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判定《世说》撰辑成书是在元嘉十六年(439)四月至元嘉十七年十月间,而成书地点即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只有在此期间,刘义庆才有可能导率幕下文士编撰《世说》。至于刘义庆组织、编撰此书的原因,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周密论证:政治环境方面,作者揭示出宋文帝多猜忌,刘义庆著书有颇示己志显示其无意争竞的潜在含义。而刘义庆生母即惨遭宋文帝杀害的大将檀道济之姐,此更使刘义庆必然倍加小心,其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而“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良有以也。社会时代方面,作者列举多个例证,阐明“刘宋去魏晋未远,讲说前朝的人物和故事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1]107,而刘义庆之所以编纂《世说》实受此种风气之影响。家族文化方面,作者溯源析流,阐述了彭城刘氏多代多人推重文章学术的事实,并举证史志中所载大量刘氏成员著作名称、卷数引证彭城刘氏的家族传统,揭示刘义庆之编纂《世说》,实亦家风使然。
二、文献考论
范著第三至六章从文献学的角度、由远及近地对《世说新语》的各种古注、版本进行翔实考述。
第三章分别对敬胤和刘孝标的《世说注》进行考论,并比较二者优劣。
关于敬胤《世说注》。首先,作者对刘兆云以《世说·企羡》第2条敬胤注:“史畴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内史,民其后也”[7]651之“民”为敬胤自称的观点表示认同,亦即认为敬胤全名当为“史敬胤”。①其次,作者根据敬胤注中的“今”字所涉人事“确证史敬胤的《世说注》最后完成于永明年代”[1]115,即公元483—493年之间。再次,作者由敬胤注中“前篇”“别说”等语词判定敬胤注“是一部覆盖《世说》全书,规模庞大、自成体例的学术巨著”[1]115,从而否定了宋人汪藻“疑敬胤专录此传疑纠谬,后人妄取,以补其书”[1]115的说法。又次,作者在对敬胤注详加审视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其注释的三种体例。一是疏证。或彰明人物的名字、籍贯、履历、家世和谱系[1]116,或揭示舆地之变迁[1]116-117,或疏解旧典[1]117。二是补叙。即援引史籍,补叙事实。敬胤于此不惮繁琐,引证史料颇多。三是驳议。即对《世说》原书之虚谬加以反驳,或对其所载之人、事加以评论,由此使原著文字更加显豁。最后,作者指出敬胤《世说注》具有特殊的文献与史料价值,尤其是其中内容多“可补唐修《晋书》之阙,足资治晋史者参考。”[1]121但是从文学角度来看,则敬胤注在注释的准确性与简洁性方面远不及刘孝标《世说注》,这可能就是刘注出而敬注废之原因。
关于刘孝标《世说注》。首先,作者指出刘义庆《世说》原本为八卷,刘孝标注本为十卷,此新增的两卷,或为孝标注释之结果,或与陶弘景(456—536)所著《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有关。其次,作者根据刘孝标生平及其撰著《类苑》的时间,大致推定其《世说注》可能撰成于梁天监十五年(516)至普通二年(521)之间。再次,作者对刘注中的谬误进行分类举证,其中包括妄断真伪、失于臆测者,张冠李戴、误指人物者,误引误记、下笔疏漏者,疏于稽考、引证无力者。但作者同时也申明“刘孝标乃一代学术巨子,其浩荡如万里长江,纵然千里一曲,又何伤大雅!同时,我们必须把后人删削、篡改的因素考虑在内,或许上举各例,并非刘孝标本人造成的,亦未可知”[1]135,持论审慎,运思缜密。
第四章,作者对日本的《世说新书》残卷进行考论,通过对残卷避讳情况的详审考察,考定残卷“抄写时间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至大同六年(540)之间”[1]143,从而打破以此日藏残卷为唐抄本之旧说。在将残卷与宋本进行仔细比较后,作者指出:“残卷虽系与原本最近之古本,但其讹误、脱漏亦多,故宋本之价值是它所取代不了的。”[1]154
第五章,作者对宋人删改《世说》及刘孝标《世说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自北宋晏殊(991—1055)以降,历南宋董弅、刘辰翁、刘应登诸人,《世说》原本及孝标注迭遭删改,大失原貌,而在古本不存、宋本堪贵的情形下,如何根据现有文献来考察、还原《世说》及刘注之原貌,从而最大限度地使人们察识这部中古名著及其名注,就显得特别必要。范著“本章据宋本、古抄本‘残卷’及明袁氏嘉趣堂本,结合唐宋诸类书之转载文字,全面考察宋人增改、删削《世说》的情况”[1]157,最大程度使人得窥《世说》及刘注真貌。
关于宋人对《世说》原文的删改。作者撮举例证释明宋人删改《世说》原文的几种情况,即:删削在人物语言、故事情节方面具有一定相似、相近性的“重复”条目[1]157;删削叙事过繁的条目,基本保证“一条叙一事”的模式;删削有关人物名、字的字句;删削事涉神鬼的条目。另有不知原因而遭删改之字句,以及尽删相关条目内容之情况。作者认为宋人对《世说》原文的删改“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世说》这部魏晋文化之百科全书原有的丰富性”[1]182。
三、文化阐释
范著第七至十章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世说新语》文本进行分门别类的考释,对《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进行探赜发微的阐述,对《世说新语》语言艺术之诗性特质以及人物形象之描写手法进行细致探论,对《世说新语》与魏晋清谈之关系作出还原性揭示。
第七章,作者认为“研究《世说》,若持轻忽之态度是万万不可的,而必须具备细大不捐、探赜求实的精神,否则只能是入宝山而空回,临华筵而虚腹。”[1]242本着这种求实的精神、态度,作者由宏观到微观,对《世说新语》文本进行探河穷源的考论。宏观上,作者指出“《世说》的‘世’,谓世间、世界”[1]243,而《汉书·艺文志》中所载以“说”为名之书甚多,诸子书中以“说”名篇者亦不少,其中的“说”有三义,一为解说、论说,二为说法、学说,三为“小说”,即无关宏旨的琐屑之谈。“就刘义庆《世说》而言,其‘说’的意蕴兼具上述三方面因素,而尤其偏向于传统的‘小说’观念。”[1]243如此,作者便圆满地完成对《世说》书名之释义。关于《世说》各门之名称,作者结合马瑞志对《世说》的英译,广征经史子集,中西汇通,条条圆融。微观上,作者对《世说》中许多涉及语典的关键性疑难词汇进行精准阐释。如以《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8]168以解释《世说·德行》中的“四时之气”[5]42,从而揭示出褚裒深沉的性格、浑厚的内蕴、开阔的胸襟、豁达的性情。再如以疾笃、病危、病重释“绵惙”[5]42,从而破除了以“绵惙”为“绵缀”的错误认识。又如以《墨子》卷十三《公输第五十》阐发《世说·文学》“善云梯仰攻”[5]256隐含之微义,并附带阐述《世说》“言语”“文学”等篇中以军事、战争相关之典故,令人有豁然开朗、拓地千里之感。另如以佛祖说法接引、普度众生释“津梁”,则《世说·言语》中的“疲于津梁”[5]121语意显明;从现实人生的角度观察“羊叔子”“铜雀妓”[5]169从而使王献之对二者的评价之词含义明晰;通过博引众籍以阐析“白旃檀”虽然芳香馥郁却“不逆风熏”之特性,从而明确《世说·文学》之“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5]258乃“似褒而实贬,似扬而实抑”[1]268的真实语意。等等。作者还对《世说》中关涉彼时习俗的语汇进行了疏解。如点明“五碗盘”“其形制甚小,成年人即使吃‘五碗’,亦难果其腹”[1]297的特质,揭示王导“弹指”动作与“兰阇”语言的一致性,通过考察中药“远志”的名称、特征明确《世说·排掉》中“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5]944之语意,通过考察中药“王不留行”的药性明确《世说·俭啬》中“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5]1026的真正内涵并揭示出“晋代的药物学知识普及得很好,这也是与士人的养生意识分不开”[5]69之时代特征。而尤其是,作者在解释《世说·言语》“二儿故琢钉戏”[1]297时,既引清人周亮工之记述,又结合自身童年经历以生动细致描述“琢钉戏”,令人有水银注地之感:“今日我国东北乡村之儿童犹为此戏,名曰‘摔(guai)钉子’,而多在潮湿的地面上进行。其戏法先由一儿画一小方界,然后另一儿于界内琢一钉,即周氏所谓‘签’。接着再由他儿琢钉,然后拔起,若将‘签’拔倒,则胜;若不能拔倒,则输;反复拔摔,直到一方被拔倒为止。笔者在童年时代擅长此种游戏,可为《世说》此条作定说。可知这种儿童游戏历史悠久,且不独盛行于江南也。”[1]298凡此,既体现出作者渊博深厚的学养,亦体现出作者积学为宝转识成慧的学术境界。
第八章,作者对《世说新语》中若干“故事”的阐述尤其能体现出其敏锐的思致与深厚的学识。作者择取《世说》中的六则故事,对其进行深刻周密的历史文化解读,掘微发隐,从而藉之彰显出魏晋时代独特的文化精神。第一,作者在陈寅恪对“竹林七贤”质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首先,“竹林七贤”名目的创造者可能是谢安。《世说·文学》第94条: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刘孝标注:宏以……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5]322职是,可知所谓“竹林名士”不过是谢安一时兴之所至的戏谑之言,却被袁宏录入书中。其次,“竹林七贤”之名目被东晋士林普遍接受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七贤”既是东晋时代士林人物品藻的重要对象,亦与当时名僧和名士交游之现象相关。而之所以冠“竹林”于“七贤”之上,固然如陈寅恪所论“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9]202,实亦与晋人对竹子的耽爱相关,譬如《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10]2075,《世说·任诞》第46条“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5]893邓德明《南康记》:“(翟矫)好种竹,辟命屡至,叹曰:‘吾焉能易吾种竹之心,而从事于笼鸟盆鱼之间哉?’竟不就。”[1]315等等。其例甚多,兹不备具。总而言之,可以说作者的论述粉碎了“竹林七贤”的历史旧梦,却从更深刻的文化层面重构了“竹林七贤”,而这种重构不仅没有减损七贤之辉光,反而使其更加充实而富有魅力,令人弥增神往之情。第二,作者对嵇康锻铁的“奇异”史事作出深刻的文化解读。嵇康锻铁事见诸《世说·简傲》第3条: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5]901嵇康锻铁事亦见于《文士传》、《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等。作者先对嵇康锻铁的时地作出考证,指出“嵇康锻铁之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当时魏国之都城洛邑”“另一处是怀州修武县西北的百家岩”[1]319,尤其重点考述了怀州修武的嵇康遗迹,从而勾勒出嵇康一生的主要行迹,“修武在山阳(今河南焦作市附近)之东北,两地距离很近,魏晋时期同属河内郡。该郡之西为河东郡,地处黄河之北,而洛邑居黄河之南。嵇康一生主要活动在这三个地区。”[1]323并参考钟会撰成《四本论》之时间,定嵇康锻铁洛阳在嘉平五年(253),也就是说,《世说·简傲》第3条所载钟会往见嵇康事,当发生在嘉平五年。至于嵇康锻铁之原因,作者则从“社会背景”与“嵇康自身”两方面进行阐述。前者从嵇康的生平经历、思想观念切入,指出锻铁乃嵇康的“龙蟠凤逸之举”[1]328,而最为奇崛与奇绝的是,作者复从服散养生的角度,结合嵇康诗文及大量医学文献,证明“嵇康锻铁也是出于养生取药之需。铁本身即是具有滋补效用的中药。”[1]344如此,便使嵇康锻铁之事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文化、社会风尚紧密联系起来,便将嵇中散傲视千古的卓荦形象深刻、生动展现出来。掩卷沉思,我们似可闻见嵇中散挥动炉锤叮叮当当地奏出的遥远绝响!第三,作者从音乐文化的角度入手对阮籍长啸作出深刻阐发。作者敏锐地注意到阮籍之啸的传播距离“阮步兵啸,闻数百步”[5]762,而阮籍尝拜访的苏门真人,其啸则“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5]762,二人之啸显然与人们通常认为的“啸为口哨”之论不合。作者由是将古代文献中对啸的记述与游牧民族的“浩林·潮尔”(俗称“呼麦”)联系起来,揭明二者在音乐形态上的种种吻合,从而为阮籍之啸乃至中国文学史之啸找到现实遗存,丰富、深化、生动了人们对啸的认识。第四,作者由《世说·任诞》第54条的“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5]898出发,探究王廞(伯舆)生平行实,尤其揭明其对女性的尊重,最终指出“王廞是一个至情至性和任情任性的文化人,他的‘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的名言,正是其内心世界与性格本真的流露。评价这样一位深情缅邈的诗人和艺术家,我们是不能拘泥于古人所谓‘乱臣贼子’之说的。”[1]378在此,作者由文及人,深具“理解之同情”,亦富“深情缅邈”之韵致。第五,作者对《世说·贤媛》第26条中谢道韫所谓“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5]820之“阿大”作出详审考定,认为此“阿大”当指谢道韫之父谢奕,从而理顺人物关系,还原语境现场。第六,作者对东吴亡国之君孙皓的《尔汝歌》作出考释,探其源流,审其名实,并最终点出晋元帝之所以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5]108的感叹,实与三十年前平吴时之“欢呼雀跃”相关,如此便深刻揭示了历史人物的心理。
第九章,作者对《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和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揭明《世说新语》的语言具有世俗化特征,也就是说《世说新语》是将当时人的语言运用于书中,从而使其灵动自然、充满口语化、生活化。作者更从“言文离合”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揭示,他认为“先秦时代的语录体散文是用当时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此即所谓‘言文合一’,而至秦汉时代则‘言’‘文’殊途。经过汉末、三国的离析动荡,至晋宋时代,我国的语文在《世说》中再一次实现了‘言文合一’(现代社会的白话文运动,正与此遥遥嗣响)。”[1]427如此,作者便在更广阔的视域下为《世说》语言的世俗化、独特性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思路对于我们观照中国文学史是大有裨益的。然而,颇具辩证色彩的是,作者不仅揭示了《世说》语言具有世俗化特征,更论证了《世说》的用典艺术与诗性特征,指出《世说》用典表现在“旁征博引,化古通今”“自然浑成,融化无迹”“传情达意,形完神足”“自出机杼,富于新意”“意蕴深厚,发人深思”等多个方面,而其直接摄取典故的方式则有“明取”“暗取”,等等。作者指出:“《世说》不是诗,而富有诗的韵味。这并不仅仅由于我们作为读者能够在这部叙事作品中见出诗意来,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本身即具有诗歌艺术的特质。用典既是这种特质的具体显现,也是这种特质赖以形成的一种艺术手段。”[1]455至于《世说》语言之风格,作者认为《世说》一书而兼众美,既有“烂若披锦”的华丽美,亦有“纡余委曲”的含蓄美,既有“排沙简金”的简洁美,亦有“韶音令辞”的音乐美,而究其原因,则由彼时“士人特殊的审美观念以及作品自身的文化特质”[1]436所致。本章亦对《世说》中的男孩群像、女性形象进行赏鉴析论,从而揭示出《世说》独特的人文价值、人性关怀,丰富人们对彼时思想观念、社会氛围的认识。
第十章,探讨《世说新语》与魏晋清谈之关系。作者对清谈的研究,并非以其思想内容为第一着眼点,而是侧重解决形式方面的问题,依托《世说》,旁参其他史料,通过对清谈形式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之探讨,对清谈的某些本质特征进行深度考察。作者认为“清谈”之事实既发生于后汉,则此语之起源亦当在彼时,关于清谈思想之起源,作者折中群说,认为清谈“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与分合演化的结果”[1]483,作者并由《世说》的编纂得到启发,从而得出“东汉名士开启了魏晋清谈的先声,清谈思想与习俗的萌芽是首先发生在他们身上”以及“清谈发始于东汉安、顺二帝时代(107—144年)”[1]484的结论。作者考察“清谈”之语义,认为有“雅谈”“美谈”“正论”诸义,而“在中古时代,‘清谈’一词的最常见意义,是指士族知识分子以探讨《周易》《老子》《庄子》及其他方面的学术问题为基本内容,以讲究修辞和技巧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谈讲和论辩。”[1]490在此意义上,清谈又与“清言”、“咏”(包括言咏、谈咏、理咏、咏谑、咏语、咏言)、“言”(包括言理、言玄理、言谈、微言)诸词同义,由是可知,“古人使用‘清谈’一词,情况十分复杂。对有关‘清谈’的每一种语境,都应该作具体的辨析,这样才可作为立论的依据,否则就可能方枘圆凿,远离本意。”[1]495至于清谈的方式,作者则根据实例归纳出(一)口谈与笔谈;(二)公座之谈、私座之谈与自然之谈。并对“口谈的基本模式”、“口谈与佛家‘讲经之制’”的关系、“口谈的音调”、“口谈之‘番数’”、“口谈中的‘通’”、“口谈中的配角”、“口谈的美境”诸问题进行证释,且指出“晋人在清谈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实际上是为了充分体味清谈的美好境界,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因为增加了生命的密度,也就等于延续了生命的长度。”[1]515作者例举魏晋清谈家的相关言论以申述彼时人物的“论辩艺术”,而特别批判了徒逞唇舌无益学术的诡辩,作者认为“一切有良知的学者,一切爱好真理的人们,都应对其进行自觉的挞伐和抵制,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我煌煌华夏民族斯文之不坠,悠悠五千载文化之赓续,完全依赖于对学术的追求与真理的捍卫。”[1]523这种论述贯通古今,借助对“诡辩”的批判,实际体现出作者对学术研究高尚、纯正境界的追求。
作者亦对“魏晋清谈中的言语游戏”进行梳理考论,作者根据嘲戏(一种幽默滑稽的言语游戏)的内容不同,将其分为八类:一是嘲族,即就所属家族相嘲,如《世说·排调》第12条:“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5]929这种“嘲族”现象,实际上是中古士人重谱牒重家族门风的一种别样表现。二是嘲地望,如《世说·排掉》第41条:“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5]950习凿齿,襄阳人;孙兴公,太原人,他们彼此以地望相嘲。以地望相嘲实际是由各区域文化、经济等发展不平衡所致,处于优势区的人物希冀藉此羞辱落后区域之人物。三是嘲容貌,如《世说·排调》第21条:“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5]939康是胡人,故被嘲戏。较之嘲族、嘲地望,以容貌相嘲,原因更直接,嘲戏性质亦更恶劣。四是以他人之尴尬相嘲,如《世说·排调》第55条:“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5]959此类嘲戏实际反映了嘲戏者敏捷的应变和表达能力。五是以学问相嘲,如《世说·排调》第48条:“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5]955此类嘲戏实有解除、缓解尴尬之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嘲戏者的聪敏捷悟。六是就宗教信仰相嘲,如《世说·排调》第51页:“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5]956此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从而达到促其反省之目的。七是就性格、行为相嘲,如《世说·排调》第28条:“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5]942此类嘲戏实际是借表象事物、行为来彰显深藏的心理、性情,从而促使被嘲者有以思之。八是嘲人名字,如《世说·排调》第63条:“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座。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5]966-967《老子》一书主要讲道,王思道名中有“道”,故桓玄巧用“顾名思义”一语以调戏之。以上各类嘲戏,无不体现出嘲戏者敏锐的机变能力。在分疏嘲戏种类的基础上,作者复总结嘲戏的形式特点,或为自我嘲戏、或为嘲戏他人、或为双方嘲戏、或为多人嘲戏,并分别举例以实己说。而笔者亦关注到,作者的例证几乎全部出自《世说·排调》,这种现象实际说明在《世说·排调》的滑稽调笑声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古文化信息,魏晋之排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玩笑,而是人们宗族观念、学问修养、才思机变等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体现。
作者也对清谈家的风流雅器麈尾和如意进行了考察。作者通过查考古今文献,认定“麈尾用麋鹿之尾制成”,而“麋鹿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鹿科动物。”[1]542“在中古时期,麋鹿主要分布于吴(今浙江)、楚(今湘鄂)一带”[1]543“在蜀中地区也有分布”[1]543-544,作者考察麈尾源流,认为麈尾是“东汉贵族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讲授儒家经典的学者所常用”[1]545,“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思想。”[1]545而“汉代麈尾的主要产地可能是著名的皇家园林上林苑。”[1]545中古时期,麈尾为清谈之雅器,助成魏晋风流。隋唐时期,“麈尾仍在文士间流行”,而在宋代,麈尾已不多见。作者特别举出《红楼梦》中描述麈尾的情节,认为“这是麈尾——永恒的句号。”[1]551此部分的考述实不啻一篇“麈尾小史”。至于麈尾在清谈过程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中古之清谈,通常采取主客问答的方式。主是主讲人,客是问难者。麈尾是主讲人身份的标志,在通常情况下,客是不拿麈尾的。”[1]558作者亦对麈尾与中古名僧之关系,尤其是与古天竺的大德居士维摩诘之关系作出分析,认为“《维摩诘经》盛行于中古士林,当时的士林名流及一般僧侣无不以为枕中秘宝”[1]568,而“随着《维摩经》的流传,维摩的精神特质自然影响于中古名士”。[1]569而其影响之要点,乃在“辩才与智慧”“‘不二法门’——‘无’”“‘火中莲花’式的人生境界”三端。最后,作者感叹道:“麈尾的优美意蕴毕竟注入了华夏文化的浩渺烟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当我们偶尔瞥见它那一缕清波时,又是多么欣慰!”[1]577作者考察清谈雅器如意,要点如下:“如意,俗称‘老头乐’,为搔痒之用具,因其便于使用,如人之意,故名为如意”[1]578;“如意取材于木、玉、铁等等”[1]578;“如意本系僧侣之法器”[1]579;“如意的使用,可能与士人服用五石散的风气有关。因为服药之后,周身发热、发痒,自然需要用东西搔痒,如意便适应了这种需求。同时,清谈家们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般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所以身体往往会有不太舒适的感觉,这样如意也就派上了用场。”[1]578因“中古时代名士与名僧颇多交游,同时由于生理上的需要,所以如意自然和麈尾一同进入清谈场中,并流行起来。”[1]581
四、烛隐显微与他山之石
范著另有附录四篇,首篇《临川王刘义庆年谱》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刘氏生平事迹作出更为详实的考察,后出转精。其中最为卓绝的部分,笔者认为是对刘义庆与宋文帝刘义隆(424—453年在位)“微妙”关系的梳理呈现。譬如“元嘉八年(431)”“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1]590;“义庆固求解仆射”“秋八月甲辰,临川王刘义庆解尚书仆射”[1]591;“元嘉九年”,何长瑜为嘲谑之语,“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1]591,以上充分显示出刘义庆的谦退与持身谨重。再如,“元嘉十二年”[1]593“元嘉十四年”[1]594谱文反复提及“祥瑞事件”,“元嘉十七年”谱文则述及刘义庆创作《乌夜啼》之背景[1]595,同年谱文复提及两则“祥瑞事件”[1]596,这些“祥瑞事件”均由刘义庆奏上“以闻”,结合《乌夜啼》创作背景来看,它们其实反映了刘义庆虽以宗室而出镇,其真实心态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果我们再稍微留意一下范谱“元嘉十八年”[1]596的两则谱文,“五月甲申,甘露降丹阳秣陵卫将军临川王义庆园,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1]596“六月,甘露降广陵孟玉秀家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1]596,就很容易产生如下认识:元嘉十八年六月的降甘露事件,当是义庆为避祸而故意紧接上月的“甘露降”而为之。总之,以上列举的相关内容,如散而观之,则不易察觉其中隐微,而经过作者的系统梳理,则刘义庆之隐微心态,以及其与宋文帝之间微妙的君臣关系,全部表呈而出,《宋书·刘义庆传》所谓“(刘义庆)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11]1477,范谱不仅通过详征文献、精心编排为“世路艰难”下的刘义庆画影图形、辨骨写心,而且也间接地道出刘义庆编纂《世说》的现实原因。
次篇《<世说新语>的世界》是作者翻译的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Mather)论述《世说》的一篇文章,此文是马氏英译《世说》之导论,而实不啻为一篇综合深入论述《世说》之恢弘引言。马氏此文首先讨论《世说》的真实性问题,马氏通过列举实例,肯定《世说》的真实性,但是,由于《世说》并未列入史部,而是长期被置于子部和小说部,故马氏进而指出“描述历史似乎还不是《世说》作者意图之所在”,并重点论述《世说》的娱乐因素。[1]601在马氏看来,《世说》“故事构成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异常狭窄的世界:皇帝、太子、大臣、官僚、将军、文质彬彬的隐士和温文尔雅的僧侣。尽管他们生活在极其优雅而敏感的象牙之塔中,其中大部分人还是经常涉足充斥着流血漂杵的战争和尔虞我诈的派系斗争的尘世。这是一个黑云漠漠的世界,与才智和睿识的光辉构成了鲜明的对照”[1]602。马氏此论,周全而深刻,理性而诗意,其末句尤见研探之功:他没有因耽爱《世说》语言文词而孤赏其中人物之风华,而是更着意指出这群“才智”“睿识”之士所处的时代环境,从而使人得以更深切地体察《世说》中的人物风神及其内蕴。踵承此意,马氏复对《世说》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史背景、《世说》人物与历史事件以及思想史之关系进行分析,宏观的“史”的述论与微观的文本印证,彼此水乳交融,显示出马氏对《世说》全面而深细的把握。而作者的译文则不仅准确达意,而且雅涵神韵,譬如上举“黑云漠漠”一段,于阐述析论中蕴含诗意,足见作者之英文造诣及对马氏“导论”体悟之深透莹澈。
第三篇《<世说新语>法译本审查报告》是作者翻译的马瑞志的另一篇关于《世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马瑞志对比利时高级汉学研究所学术带头人贝莱佩尔创写的法文本《世说新语》的批评。对贝译的批评与指正体现出马氏研寻《世说》的深厚功力。作者翻译此文,一方面借马氏之口间接介绍了《世说》第一个外文全译本之概况、水准;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了马氏的《世说》研究。
第四篇《马瑞志的英文译注本<世说新语>》是作者对马氏《世说》译注本的评介。
五、辞章与信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著通体洋溢着奔放的情感,而表述则雅洁神秀,充满诗性之美,与《世说新语》原著和谐汇融,珠联璧合。试读以下段落:
“九品之文化观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我们面对华夏的历史长空游目骋怀之际,无论是乱云飞渡,雨骤风狂,还是艳阳高照,重霄湛碧,我们都可以发现九品观念那苍茫浑厚的姿影。”[1]48
“避世高蹈本非其初衷,锻铁幽谷亦出于无奈。他表面上寄情烟月,傲戏林莽,实则窥测风云;他貌若洁身自好,飘然远翥,实则与世俗根本不妥协。在熊熊炉光的映照之下,嵇康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在叮当作响的打铁声中,嵇康等待着施展抱负的良机。他的桀骜不驯、金刚怒目般的性格,他的璀璨华丽、多姿多彩的思想,他的崇力尚志的生活信条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隐然映现于此。”[1]327
“如果说《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以诗的艺术形式激扬其心灵世界的天风海涛的话,那么阮公之啸,则是以音乐的艺术形式传达其对现实与人生的体悟与忧怀,淋漓尽致地展现自我的个性。阮籍之啸,是知与意的融合,是情与理的凝铸。他的血肉之躯在历史的秋风中早已凋谢了,他的啸声却仍然在华夏历史的长空里袅袅迂回。在阮籍辞世后大约两个世纪,刘宋著名诗人颜延之在《五君咏·阮步兵》一诗中吟道:‘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枷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阮公以其卓尔不群的啸声,冲决了世俗的长堤,震颤了权柄的桎梏。阮公之啸,其美何限!”[1]366-367
综上可知,范著由文本到文献,由文献到文化,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地对《世说新语》作出坚确深刻的考释。范著的谋篇布局为《世说》学的建构支撑起谨致的框架,范著的阐微发覆于《世说》学的拓进厥功甚著,范著的学术表述与《世说》原著水乳交融、流光生辉,具有诗性品格。而范著对文献史料海涵地覆般勾稽引征,以及弥纶群言、独断己意的著述风格,则使其具有《世说》研究的集大成性。
最后当说,与作者初版的《<世说新语>研究》[3]相较,《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1]无论在论证的邃密上,抑或在容量的增益上,皆有重大的突破、提高,充分显示了作者二十余年勠力《世说新语》研究的坚实成绩。而笔者更注意到,在相隔二十余年出版的两部著作的后记中,作者表达了同样的理念、叙述了同一个典故:“无论如何,我都坚信自己近十年来所发表的学术成果的生命总要比我个人的生命长一些,因为这些论著的完成,并非如卢梭所谓‘为生计而运思’或‘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的结果。平心而论,我对所谓‘成功’并无兴趣。唯其如此,我的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书而多活几天。”[1]684(《<世说新语>研究》“后记”表述略异,意旨相同,见该书第336页)“记得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他的著名小说《格利佛游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些中世纪经院哲学家(Philosophers in Scholasticism)的亡灵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及柏拉图诸大师的魂魄邂逅,竟然不敢直面相对,所以格利佛船长连这些‘家’们的脸都看不清楚。做学问做到如此地步,就成了不幸。这种不幸的滋味,我是领略不到的;换句话说,倘若百年之后我遇到那些我倾情研究的古典作家,我绝不会‘没脸见鬼’,因为我对他们创造的杰作是虔诚的。”[1]684笔者每读至此,都不能不为作者坚钢一般的治学信念所感动,也不能不顿生一种勤勉向上勠力学术之决心!在这个学术研究与学者精神普遍分离、著作普遍缺乏生命力的时代,作者将二十余年的“虔诚”寄注于《世说新语》研究,不仅重现了这部古老经典的光辉真面,而且其自身亦充溢着饱满劲健的生命力。职是之故,笔者坚信,范子烨《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不仅会予人以学术的启发,更将在为人为学上感人至深、励人奋进,显示出坚韧持久的影响力!
① 作者近来又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证,认为“敬胤当为宋末齐初之人,主要活动在永明时代,敬胤《世说注》也完成于此时。其真实姓名可能是王敬胤,而不是史敬胤。”(《学术交流》2020年第3期)作者这种执着的求真求是治学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而笔者亦怀疑,上引敬胤注的句读或当作“史畴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内史民其后也。”也就是说,“位至豫章太守”是史畴终官豫章太守,而御史中丞、武昌内史均为史畴后裔史民的官衔。这样理解与注文前面对江渊一系的缕述方式相一致。
[1] 范子烨.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2] 范子烨.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3] 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
[7] 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12.
[10]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
Plentifulness and Splendor: Some Thoughts of Reading Fan Ziye’s Study on The Precise Description of Wei-Jin Demeanor:
ZHANG Deheng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200, Shandong, China )
In the book named, Fan Ziye have endeavored in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name, style, writing situation, various ancient annotations, and Japanese and Tibetan fragments of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more than 20 years. He revealed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stories, analyzed the language arts and description techniques and elucid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and the idle talks in Wei-Jin Dynasties. The book of Fan deeply and widely explored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from texts to literature even to culture. Fan's works are rich in content, rigorous in structure, detailed in textual research, and elegant in rhetoric. They are substantial and brilliant, demonstrating the author's firm academic conviction.
Fan Ziye,poetic character, academic conviction
I206.2
A
1673-9639 (2021) 02-0025-11
2021-01-07
山东理工大学青年教师项目“唐宋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研究”(4033/720002)。
张德恒(1985-),男,河北唐山人,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东亚经学,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文学,古琴史。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