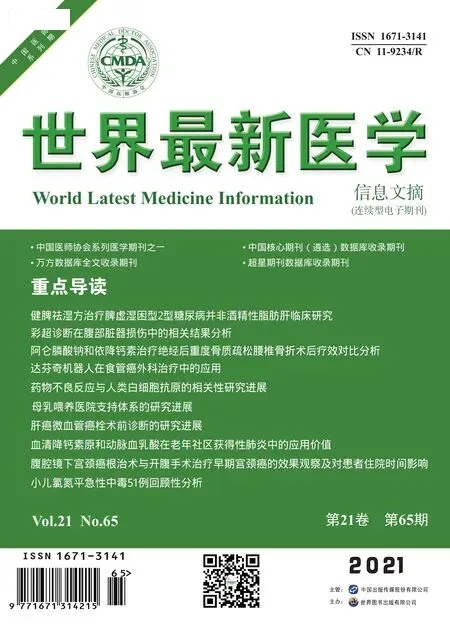《伤寒论》中心悸辨证论治规律浅析
郭迪,杜雨锡
(1 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 长春;2 吉林市中心医院,吉林 吉林)
0 引言
心悸是指患者出现心中悸动不安,甚则不能自主的病证,一般多呈阵发性,病情较重亦可呈持续性[1]。心悸时,心率可快、可慢,也可有心律失常,心率和心律正常者亦可有心悸[2]。在临床上常见于由于器质性与非器质性病变引起的心律失常如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房纤颤、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性期前收缩、房室传导阻滞等[3]。
1 病机概述
《中医内科学》[1]中描述心悸的病机关键为“阴阳失调,气血失和,心神失养”。钱旻[4]认为心悸有虚有实,以虚者居多,并将其病因概括为虚证、饮证、气郁证三类。蒋健[5]将心悸分为郁证性心悸和非郁证性两类。李小慧[6]认为心悸主要病位在心,与肝胆、脾、肾等脏腑功能的失调密切相关,故其从心、脾、肾、肝胆分论病机。贾涛[7]认为心室肥大所致心悸多与水饮停心相关,而高热、甲亢等心搏出量增加所致的心悸与火热扰心证相关,无器质性病变的心律不齐、心脏神经症等则与心阴心阳亏虚、心脾两虚等密切相关。笔者根据不同病机将《伤寒论》中描述的心悸的汤证归纳为八种:心之阳气不足的桂枝甘草汤证;气血亏虚的小建中汤证;心之阴阳两虚的炙甘草汤证;心阳虚,下焦阴寒上逆的桂枝加桂汤证;脾虚水停的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证;肾阳虚水泛的真武汤证;胃阳虚,中焦停饮的茯苓甘草汤证;少阴枢机不利,阳气郁遏之四逆散证[8]。
2 辨证分型
2.1 心阳不足,心失所养
《伤寒论》中描述的典型心悸是由于脏腑本虚或者失治误治致使的脏腑虚弱所引起,如吴谦分析《伤寒论》原文第64 条,由于“发汗过多”,外亡其液,内虚其气,气液两虚,中空无倚,故“心下悸”,“叉手冒心”,欲得自按,以护庇而求定也。尤怡认为“叉手自冒心者”是里虚欲为外护;“悸”是心动;“欲得按者”是心中筑筑然不宁,欲得按而止之,宜补助心阳为主。钱潢认为“阳本受气于胸中,故膻中为气之海,上通于肺而为呼吸,位处心胸之间。发汗过多,则阳气散亡,气海空虚,所以叉手自冒复其心胸,而心下觉惕惕然悸动也”。由此可见此条所论述心悸的病因在发汗过多,如徐大椿言“发汗不误,误在过多,汗为心之液,多则心气虚”;陈修园[9]言“此一节言发汗而伤其心气也”。
2.2 中焦虚寒,气血亏虚,复被邪扰
成无己[10]分析原文第102 条,认为“伤寒二三日”是邪气在表,未当传里之时,“心中悸而烦”是非邪气搏所致。心悸者,气虚也;烦者,血虚也。以气血内虚“与小建中汤先建其里”。这样看来本条所述心悸确是气血亏虚所致。对于诊治卢之颐进一步提出“助土辅火之要法”。周扬俊将此条心悸选用小建中汤的缘由详细阐述“二三日为病不久,心中悸烦,则其悸为阳气素虚”,用药上注重的是“倍芍药以益营,入胶饴以养胃,仍不去姜桂以散邪,使中气建立”。说明了“保卫气,存津液”是《伤寒论》最重要的治疗原则,也是治疗里虚伤寒的法则。
2.3 心之阴阳两虚
张璐分析《伤寒论》原文第177 条“炙甘草汤一证”,但言“脉结代,心动悸”,并不言从前所见何证,曾服何药所致,细绎其方,不出乎滋养真阴,回枯润燥,兼和营散邪之剂。以方测证,他认为这是由于患者胃气素虚,所以汗下不解,胃气转伤,真阴槁竭,遂致“心悸脉代”。汪琥分析此条病机必系“发汗过剂,汗多亡阳,阳亡则气馁,又汗为血液,汗多则血虚,血虚气馁”。尤怡从营卫学说讨论“脉结代者”,邪气阻滞而营卫涩少也;“心动悸者”,神气不振而都城震惊也。周扬俊认为“今脉结代心动悸,非无阳以宣其气,更无阴以养其心”。程知认为病始外感而渐内累于心,所以“阴虚而真气不相续也,故峻补其阴以生血,更助其阳以散寒”。可见多数医家认为此时外邪已罢,诊治重点在里虚。
2.4 心阳亏虚,下焦阴寒,乘虚上逆
《伤寒论》原文第117 条:“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成无己[10]分析“烧针发汗”则损阴血,而惊动心气。“针处被寒”,气聚而成核。心气因惊而虚,肾气乘寒气而动,发为奔豚。王丙认为,烧针入穴,既开难闭,汗出后寒易袭之,凝于穴道,肉为之僵故“核起”,血为之郁故“色赤”。可见本条所述之证是内外共同为患,外为寒闭阳郁,内为心阳虚下焦水寒上冲。黄元御认为此证为“汗后阳虚脾陷”引起,即以桂枝加桂汤“以疏风木而降奔豚”。由此可见发生奔豚的过程是在于强则发汗,损伤心阳,阳虚阴乘,下焦水寒之气上犯心胸所致,治疗上外宜温灸散寒,内宜温通心阳。
2.5 脾虚水停,水气冲逆
《伤寒论》原文第67 条:“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本条虽未直言“心悸”,但确实是在形容心悸的表现。吴谦对其与前面所述气虚证病因病机辨析:伤寒若过发汗,则有“心下悸,叉手冒心,脐下悸,欲作奔豚”等证;今误吐下,则胸虚邪陷,故“心下逆满,气上冲胸也”。本证为中阳不足,水饮内停,治当温化水饮,健运中土。
2.6 肾阳虚弱,水邪泛溢
成无己[10]分析《伤寒论》原文第82 条“发汗不解仍发热”邪气未解也;“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汗出亡阳也。里虚为悸,上虚为眩,经虚为身瞤振振摇,与真武汤主之温经复阳。方有执[11]认为其病因在于发汗不当,应该小发其汗,却大汗流漓。汪琥认为“此条病,乃太阳真寒证”,真阳素虚之人卒中风寒,先应补里固表后用温解之法,如若强发汗则真气内虚,导致“心阳不安则悸”。郑重光认为此条病机是“汗多亡阳,卫气解散”。以上医家均认为发汗伤阳,太阳表邪不去,伤及少阴,肾阳被伤。
2.7 胃阳不足,水停中焦
《伤寒论》原文第356 条:“伤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水停心下,甚者则悸,钱潢释其原因“盖以伤寒见厥,则阴寒在里,里寒则胃气不行,水液不布,必停蓄于心下,阻绝气道,所以筑筑然而悸动”。悸为水甚,而厥则寒甚,方有执认为“寒无象而水有质,水去则寒消。入胃者,水能渗土也”所以才应以治水为先。柯琴认为“心下悸是有水气,今乘其未及渍胃时先治之,不致厥利相连,此治法有次第也”。对于本条后半段的假设,以变为常,以厥为寒,会出现误治,以防误治章楠提出正法“今邪在厥阴,不能兼治,故先用茯苓甘草汤化三焦之气以行水,后治其厥也”。魏荔彤详析:“使水涤而阳气有升无降,此正从标水以治本阳也。”本条所言心下悸是水饮内停的主症之一,水饮得去,阳气恢复畅行,则悸厥自然可愈[12]。
2.8 少阴阳气内郁,不达四末
《伤寒论》原文第318 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本证诸多或然症,在病机上舒诏分析“虚寒协饮,上逆而咳,凌心而悸”。在辨证论治上吴人驹提出“悸属阳虚,而表寒为甚,加桂枝同柴胡以治表”;吴谦认为“或悸者,饮停侮心,加桂枝通阳以益心也”。总之心悸作为本条兼证,应该详析病机在原方加味化裁,随证治之。
2.9 邪犯少阳,胆火内郁,枢机不利
《伤寒论》原文第96 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本条也是在或然症里出现“心下悸”;张志聪和陈念祖都认为病机是“涉于少阴之肾气”;唐宗海则进一步认为:“或三焦中火弱水盛,水气逆于心下膈膜之间,则心下悸。”三焦本来就属于少阳,假如三焦通调水道功能受到影响,水气为病,水气上冲必会出现心下悸。在治疗上卢之颐提出“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之岑高,加茯苓之潜踵,镇定中黄,转输癃闭”。本条的特点就是根据或然症灵活加减。
3 小结
张仲景于《伤寒论》中论述心悸的汤证共有以上八种,其病机各有不同却不外两方面,即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中所言“心悸之由,不越二种,一者气虚也,二者停饮也。”将《伤寒论》中涉及到心悸的条文按照汤证分类列举,整理探讨历代医家对有关心悸条文的认识,有助于在临床上把握病机主次,随证施治,从而达到提升临床疗效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