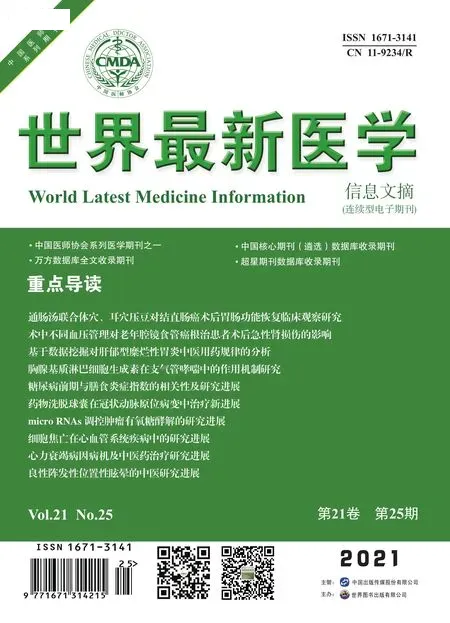慢性肾脏病合并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诊治进展
鄢佳妮,杜晓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重庆 400042)
0 引言
慢性肾脏病因其不断攀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990年至2016年间,CK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增加了89%、87%,导致了全球共1,186,561人次死亡和35,032,384伤残调整寿命年[1]。ACS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的发病趋势也从2007年的15.9%增加到2012年的19.7%[2]。2015年美国国家心血管中心登记数据[3]显示:共计832272名ACS患者中,分别有27.1%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及37.8%的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同时合并了慢性肾脏病,占比远远高于既往的报道。而且,随着CKD分期的进展,肾功能损害越重,心脏缺血事件发生率越高,不良预后明显增多。据报道,CKD5期合并ACS的患者死亡风险大约高出非CKD患者5~7倍[3],表明CKD合并ACS其短期生存及远期预后均较差。本文主要就慢性肾脏病合并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诊治进展进行综述。
1 CKD继发ACS的临床特征不典型
ACS典型的临床表现为胸痛或者不适(压迫感,沉闷感,紧缩压榨感),疼痛可放射至上臂、颈部、下颌或上腹部。但研究[4]显示,8.7%的ACS患者在入院时并无典型临床表现。对于ESRD患者而言,发生ACS后更易出现不典型症状,如单纯性呼吸困难、出汗、恶心、呕吐、心悸、晕厥甚至是心搏骤停。已进入血液透析的AMI患者较非CKD患者则更少出现胸痛症状(41.2% vs 61.6%),且CKD合并ACS患者入院心电图发生ST段抬高不到一般人群的1/2,其后期较非CKD患者更易出现左束支传导阻滞(8.2% vs 6.5%),另约45%的透析患者发生ACS时心电图无特异性改变,这可能与左心室肥大的非特异性复极异常有关[5],故连续监测心电图尤为重要。
2 CKD继发ACS的危险因素
CKD合并ACS这类患者的危险因素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危险因素包括了高龄、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脂代谢异常、体力活动缺乏等[6]。非传统因素主要是CKD患者特有的危险因素,包括eGFR降低、蛋白尿,合并代谢综合征包括胰岛素抵抗、糖脂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炎症状态、营养不良。此外,透析患者血液透析时血流动力学的改变、贫血、血浆容量增多、动脉粥样硬化、动静脉瘘、肾素-血管紧张素(RAS)系统激活以及尿毒症毒素潴留,尤其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异常的钙磷代谢、血管钙化等均是CKD发生ACS的非传统危险因素。CKD患者发生ACS的诱发因素包括血液透析时血液动力学不稳定、透析低血压、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透析后血液浓缩、间断容量超负荷、水电解质紊乱、微量白蛋白尿、凝血系统激活和血栓形成发生率增高、左心室肥厚、扩张、收缩功能下降等。
3 CKD继发ACS的治疗策略
3.1 药物治疗
CKD合并ACS这类患者在不同病情阶段的溶栓药物选择暂无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推荐。
3.1.1 抗血小板治疗
对于CKD患者而言,所有无禁忌证的患者均应尽早服用阿司匹林,但ACS患者往往因出血等不良反应而治疗依从性较差。阿司匹林出血风险呈剂量依赖性,所以长期小剂量应用可能更安全。AASER研究[7]表明,长期接受小剂量阿司匹林治疗虽然不能减少CKD患者主要的复合终点如非致命性心肌梗死、非致命性外周动脉疾病,心血管死亡,但其冠心病事件、出血等次要终点有所减少,并能延缓肾脏病进展。目前认为,EP2Y12-ADP受体拮抗剂第一代药物噻氯匹定和第二代药物氯吡格雷起效慢、缺乏稳定疗效,新型拮抗剂普拉格雷、替格瑞洛在患有CKD的NSTE-ACS患者中具有更强的血小板抑制作用,且缺血相关并发症更少,更具优势[8]。荟萃分析[9]发现,与氯吡格雷相比,新型拮抗剂能有效减少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而不会增加CKD患者的出血风险,有利于降低进一步行侵入性治疗的死亡率。但普拉格雷、替格瑞洛可能在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特性和临床效果上存在差异,仍需要循证医学证据,因此2015年欧洲心脏协会NSTE-ACS合并CKD患者管理指南尚未推荐终末期肾病患者使用,而氯吡格雷仅用于需要如预防支架内血栓的选择性指征的患者[10]。
3.1.2 抗凝治疗
出血是抗血栓治疗的主要并发症,ESRD尤其是血液透析患者,出血风险增加,因此在合并ACS时抗凝治疗带来的出血风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而现在很多重大随机试验中这部分患者常常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因此关于这类患者的抗凝治疗策略尚缺乏强有力的循证证据和指南推荐[10]。
抗凝血酶药物:(1)肝素:尽管不需要对肾功能不全患者使用普通肝素(UFH)进行剂量调整,但由于药物在体内清除延迟,其出血风险仍很高。(2)UFH是目前最常用的抗凝药物,但靶向抗凝血酶药物如比伐卢定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安全效益。比如,研究发现[11],在接受PCI的ESRD患者中,UFH组更容易出现急性冠脉综合征(37.8% VS 27.4%)或心源性休克(3.74% VS 1.98%)等高危并发症,而与UFH组相比,接受比伐卢定的患者的院内出血概率(7.0% VS 9.5%)和死亡率(2.6% VS 4.2%)均较低。
利伐沙班是一种Xa因子抑制剂、非维生素K拮抗剂的口服抗凝剂,在COMPASS研究[12],对于慢性冠脉综合征或者外周动脉疾病患者(包括中度CKD患者),与单用阿司匹林相比,利伐沙班2.5mg bid联合阿司匹林100mg qd显著降低了冠状动脉疾病和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卒中、心血管死亡和心肌梗死的复合风险达24%,且没有额外的出血风险。
3.1.3 糖蛋白Ⅱb/Ⅲa抑制剂
2015年美国心脏协会对ACS合并CKD患者的抗栓药物推荐[13]基本与欧洲指南一致,认为GP IIb/IIIa受体抑制剂对这类患者结局的影响好坏参半,倾向于早期使用,但不推荐作为三联抗血小板方案(推荐级别为IIA)。在CKD患者中药物剂量需根据肾小球滤过率作适当调整,比如阿昔单抗可作为血液透析的ACS患者的辅助用药而无需调整剂量;依替巴胎则在CrCl <50mL/min时需调整剂量,且禁用于血透患者;而替罗非班在CrCl <60mL/min时需调整剂量,在PCI术中不建议其作为阿昔单抗的替代方案,而在血透患者的安全性和使用尚未明确。
3.1.4 β受体阻滞剂
合并CKD的ACS患者应常规并且长期使用β受体阻滞剂,除非存在相关禁忌症。酒石酸美托洛尔、艾司洛尔、卡维地洛主要经肝脏代谢,故CKD患者无需调整剂量。
3.1.5 他汀类药物
若无明显用药禁忌,ESC2015欧洲指南推荐应尽早长期使用高强度他汀类药物治疗[10],证据级别为IA,但对于合并CKD特别是血液透析患者,尚存争议。既往SHARP等研究[14][15]已证实他汀类药物联合依折麦布的双降脂疗法(DLLT)成功降低了MACE风险,并且提出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目标水平“越低越好”这一概念,但目前仅少数高强度他汀能达到≥50%的降幅,例如瑞舒伐他汀。PRECISE-IVUS亚组分析[16]发现,阿托伐他汀联合依折麦布强化降脂治疗组比单用阿托伐他汀组具有更明显的冠状动脉斑块消退作用。该研究首次为CKD合并冠心病需要更强的降脂治疗提供了依据,但因排除了CKD5期的患者,对于血液透析患者缺乏有力证据。
3.1.6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
ACEI和ARB的益处已经在普通人群中得到证实,特别是在冠脉病变患者中。然而,源于对高钾的担忧限制了RAAS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国际透析结果和实践模式研究(DOPPS)[17]显示,与单用ACEI组相比,单用ARB组的CKD合并ACS患者死亡率降低了约10%。
3.2 血运重建治疗
3.2.1 冠状动脉造影
国内外均有文献报道,患者在行冠状动脉造影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应用对比剂后,易于出现肾功能恶化,甚至发生造影剂后急性肾损伤(CI-AKI)及胆固醇结晶栓塞性肾病[18][19],所以,对CKD基础上合并ACS这类患者,在造影剂的选择和支架的洗脱药物上要更加小心,但如何选择尚需要更多的研究。
3.2.2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冠状动脉钙化在CKD患者中非常普遍且往往进展十分迅速。CDCS研究[20]显示,中国有77.4%的透析患者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血管钙化,其脆弱的血管条件也给进一步PCI治疗增加了难度。可通过先行冠状动脉旋磨术预处理高度钙化的病变血管,再安置支架置入,以提高介入治疗的安全性和成功率。此外新一代药物洗脱支架与可吸收生物聚合物涂层可以有效减少血栓事件[21]和再狭窄率,其优越性和安全性已在近些年的随机试验中得到证实[22][23]。
需要注意的是,CI-AKI仍是PCI患者最常见的医源性肾功能衰竭,重在于防,应做好围手术期充分水化、使用低渗性造影剂、减少术中所用的造影剂体积[24]。Mehran等研究[25]进一步支持最小化造影剂量,基于eGFR的造影剂剂量公式(建议限制在其eGFR的3倍以下,最好是2倍左右)有助于降低CI-AKI和进展到需要血液透析的风险。
3.2.3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目前诊断CKD患者CABG的随机试验的证据很少。轻度CKD和 ESRD患者,选择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比PCI可能具有更好的生存率。然而,对于ESRD患者,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的最佳选择尚无定论。Abduzhappar等[26]观察971名开始透析前5年接受了首次CABG或PCI治疗的ESRD患者,研究了CABG和PCI手术史与全因生存率的关系,结果在接受多支血管治疗的亚组中,CABG组生存率更好。一旦患者开始进入透析阶段,CABG组死亡率降低了34%。
EXCEL试验[27]招募了1869名左主CAD患者和低、中SYNTAX评分患者(其中CKD 361名),随机分至PCI或CABG组,CKD合并CAD患者30天内发生急性肾损伤与3年死亡、中风或心肌梗死风险明显增加(50.7% vs 14.4%),其中CABG术后需要肾脏替代治疗也更多;采用PCI或CABG进行左主冠状动脉疾病血管重建的相对长期预后可能会受eGFR水平影响。
目前临床上需全面评估患者心功能和肾功能风险,推荐轻、中度肾功能不全患者在病情允许时应积极选择PCI治疗,但在重度肾功能不全合并ACS 时,由于疾病本身病死率很高,并发出血、超容量负荷、急性肾损伤、感染等更多,临床往往更倾向于药物治疗。
3.3 CKD继发ACS患者的血液透析方案调整
首先需防治ACS患者血液透析时发生心源性猝死,建议:(1)改良透析液成分:避免使用低钾 (钾浓度<2mEq/L)和低钙 (钙浓度<2.5mEq/L) 透析液,因为钙、钾离子浓度的降低及碳酸氢根离子浓度较高均可延长QT间期,导致心脏不稳定、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心源性猝死。Pun等[28]认为,与浓度≥2.0 mEq/L的透析液相比,低钾透析液发生心源性猝死风险高出两倍。但DOPPS研究[29]发现,透析液钾浓度与心律失常或猝死无关;但该研究队列仅限于指定透析液钾浓度为2.0 mEq/L与3.0 mEq/L的患者。(2)优化透析模式:建议采用每日透析、CRRT治疗等方式,降低透析效率,防治治疗过程中发生交感兴奋或RAS过度激活。(3)遵循个体化治疗原则,积极推进“一人一方案”。
4 小结与展望
CKD合并ACS因其发病率高,死亡率高,预后更差,是肾内科医师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CKD患者发生ACS临床症状可能不典型,易于漏诊,最好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治疗上需遵循抗凝治疗同时应警惕出血风险原则,根据CKD和ACS的严重程度,综合考虑是否行介入治疗方案。对于ACS患者的血液净化治疗,防治心源性猝死是关键。目前关于ACS的大型临床研究都几乎未纳入血液透析患者,未来几年,尚需要进行更多的前瞻性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来获取循证医学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