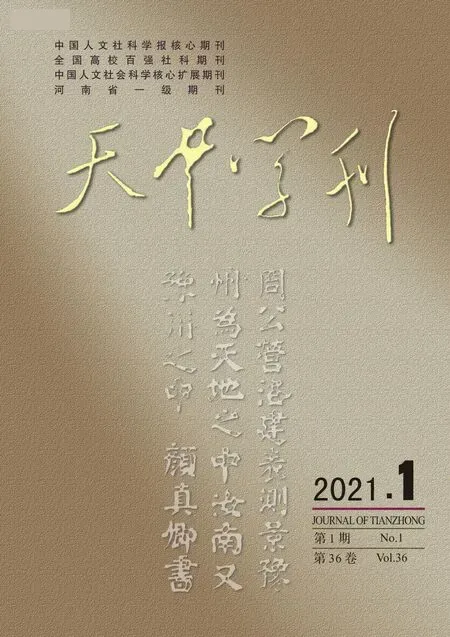稼轩词《青玉案》主旨献疑
齐凯
稼轩词《青玉案》主旨献疑
齐凯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百年以来的传播与接受史中,人们多认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词别有寄托,但在更早的晚明以前,此词并不受关注,即使在明末和清代受到关注后,一些人也认为它不过意在表现男女情事。从“艳情论”到“寄托论”,此词“真意”看似被逐渐挖掘出来,但以“寄托”解释此词造成了诸多问题,如割裂文本、强制编年、循环论证等。调整解读策略,回归文本整体性,并将其置于当时文化语境和宋词书写传统考察,视其为一首单纯的节日应景之作较为合理。
辛弃疾;《青玉案》;艳情论;寄托论;选本
从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开始,古代众多文学批评家逐渐认识到,作者之意与读者所理解的文本“原意”并不经常保持一致,并试图提炼出某种解读方法和策略,最大限度地消除读者对文学文本的认识偏差。对于词文体而言,它在早期的发展阶段中并不存在太多主旨方面的歧义,但随着诗学传统浸润其中以及文体地位的提升,对其做准确、清晰的解读,有时会变得困难很多。
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词就展示了这种复杂的状况。百年以来的传播与接受史中,人们多认为此词“别有寄托”,将其视为辛弃疾的代表作之一,并置诸词籍选本、评本和研究文章之中。而在更早的时期,人们对此词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与百年以来的情况大不相同:这首词在晚明以前极少受关注,即使在明末和清代受到关注后,部分学者认为此词不过意在表现男女情事,并无寄托在内。从“艳情论”到“寄托论”的转变过程中,此词的文学价值看似被发现,实际上很可能是其主旨被一步步过度阐释,从而导致此词更广泛的传播与接受。本文首先将回顾此词的接受史,探讨这首词是在何种接受观念的影响下,由不受关注变为公认的经典名篇;其次重点辨析“寄托论”,分析其问题;最后调整解词策略,重新审视此词文本。
一、接受史:从“艳情”到“寄托”
人们对《青玉案·元夕》主旨认识的变化,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恋情”期
宋元明时期,除了晚明卓人月编选的《古今词统》从稼轩的这首《青玉案》中看到了“寄托”,其余选家并未看到此词有何寄托处,只是视其为“艳情”或“恋情”之作。
晚明以前,收录有此词的词籍选本,只有南宋后期赵闻礼所编的《阳春白雪》和明代钱允治编选的《类选笺释续选草堂诗余》。此二者所录,在题目和个别文字上稍有出入,对此词也没有评点,但种种迹象表明,编选者是将这首《青玉案》视为传统节序词的,并不认为词中情感除了男女之情外,还有什么深意在内:《阳春白雪》选词主要是从应歌的角度①,偏重于清雅婉丽之作;《类选笺释续选草堂诗余》将此词作者标为“无名氏”,而佚名的作品往往意味着某种语境的丢失,对于阅读者而言,很难从中读出隐晦的含义。
其他收录稼轩词作的词籍选本,如宋人所编《群英草堂诗余》《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绝妙好词》,明人所编《词林万选》《类编草堂诗余》等,都没有选录这首《青玉案》。究其原因,最大可能是这些编选者们都不觉得此词具有代表性和特色。历来人们对稼轩其人其词的印象固化,认为稼轩是英雄之人,其词是英雄之词。辛弃疾自己也有“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之语,这很容易使人觉得其词即如其人。在这种认识下,还有什么比意在言外、深有寄托的词作更能代表他的特色呢?反言之,一首浅显易懂属意恋情的词,是不太可能成为他的代表作的。这种推测绝非妄言,在晚明卓人月编选《古今词统》之后,此词被不同的词选家和评论家所关注,种种证据表明,这一“接受史”的转变,除了因为看重其艺术风格外,主要源于词中“深意”被发现。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本阶段的四百年里,众词选家们对《青玉案》不屑一顾,其原因正与后来人多以“寄托”解此词相左。
(二)演变期
从晚明卓人月编选《古今词统》至王国维著《人间词话》,此词逐渐受到关注和讨论,关于其主旨的看法亦分为“恋情(艳情)”和“寄托”两说。
卓人月编选《古今词统》,将这首《青玉案》收录其中,这是此词被关注的发端,同时,书中徐士俊的评语亦开启了以“寄托”解此词的思路。徐士俊与卓人月相交甚笃,且参与了《古今词统》的选编工作,他在书中所做的评语很大程度也代表着卓人月的词学态度。书中眉批曰:“(‘蓦然’三句)星中织女,亦复吹落人世。”[1]381将所寻之“那人”比喻成“星中织女”,这种比喻背后暗藏深意:“星中织女”乃高洁、神秘、不食凡俗烟火之人,而词中“那人”不在热闹、明亮的地方与众人一起玩乐,反倒在“灯火阑珊处”,如此二者就有了一种属类的相似性,“那人”也就成了高洁、不群的象征。此解一出,原本看似平常的词作立刻就被赋予了全新而又高远的含义。
自此,清代以来那些具有鲜明标准的一众选本纷纷选录此词。我们并不知道清代人对此词的关注是否受到《古今词统》的影响和启发,但可以肯定,清人在词选中屡屡选录此词,主要也是因为发现了词中“那人”的特殊,发现了此词“寄托”的“深意”。
清代朱彝尊、汪森编《词综》,周济编《词辨》和《宋四家词选》,于辛弃疾名下所录第一首词即此词。朱彝尊选词,甚重白石,以雅为宗:“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填词最雅无过石帚……”[2]周济更是提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词学主张[3]序论。自然,在此二者眼中,《青玉案·元夕》就不太可能是与雅正和“寄托”相乖的艳情词。梁启超发出“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之论[4]88,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朱彝尊和周济选本的启发,或者说是朱、周二人对于此词含而未申的观点,在梁启超这里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梁令娴在《艺蘅馆词选》中选录此词,并引录其父梁启超所论,其以“寄托”解此词的态度亦不言自明。
与卓人月、徐士俊不同,由明入清的彭孙遹是将此词当作恋情词看待的。夏承焘说:“彭孙遹《金粟词话》以‘秦周之佳境’评‘蓦然回首’三句,那还只是艺术手法的欣赏,并不曾接触到它的思想感情。”[5]120实际上,彭孙遹《金粟词话》中“辛稼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秦、周之佳境也”还有前后文:“柳耆卿‘却旁金笼教鹦鹉,念粉郎言语’,花间之丽句也;辛稼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亦近似柳七语矣”;“山谷‘女边着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如齐梁乐府‘雾露隐芙蓉’、‘明灯照空局’,何等蕴藉乃沿为如此语乎。”[6]722②彭孙遹将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与柳永的《甘草子》(秋暮)、秦观的《迎春乐》(菖蒲叶叶知多少)、黄庭坚的《两同心》二首(一笑千金、秋水遥岑)以及《子夜歌》(我念欢的的、今日已欢别)并提而论,而这些作品无一不写男女情事。在这种并列的叙述模式下,彭孙遹将此词当作恋情词是显见无疑的。
此后陈廷焯在《词则》中更为明确地指出《青玉案》是恋情词:“艳语亦以气行之,是稼轩本色。”[7]911所谓“艳语”,就是专门写男欢女爱、男女之情之语。值得注意的是,在选录了此词的各个选本中,陈廷焯的《词则》是一个特例。其特殊性不仅在于认定这首词是恋情词,而且认定这首本不该入选的恋情词是因为“以气行之”,在风格上表现了“稼轩本色”,所以才被采纳。这给我们间接透露出一个信息:此前众多选本都不选这首词,一是因为选家们认为它就是恋情之作,二是他们并没有像陈廷焯一样觉得这首词在风格上有独到之处,或者在他们看来,无论风格如何独特,“艳语”的存在使他们不会青睐此词。
在此一阶段中,王国维对此词的品评应引起注意。首刊于1908年的《人间词话》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不许也。”[8]6一方面,从所引的三首词来看,晏殊和欧阳修的《蝶恋花》二词都写男女恋情,《青玉案》字面上也是写男女情事,可以猜想王国维很可能将此词与晏、欧的这两首恋情词一样看待;另一方面,他脱离整个文本,截取这三首词中的几句加以阐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文本解读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纯粹感悟式的赏读,类似于西方的“读者中心论”。尽管王国维明确表示“境界”并非这些作品的原意,可是这种感悟式的解词方法却为后来人开了法门。不难想见,《人间词话》的巨大影响力促使读者不得不留意这首词。与王国维同时期的谭献在《复堂词话》中更明确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的词学主张。这使后来人在解读此词的时候,就更难以避免求其“深意”了。
(三)“寄托”期
从王国维以后至今,这首词被当作稼轩词的经典之作。尽管仍有一些人认为此词属于艳情词,如梁启勋在《词学》中论此词:“的是踏灯情事,而意境之高超,可谓独绝。”[9]47与陈廷焯一样,认为这首词在主旨和内容上并无可取之处,其高妙处在艺术风格。彭玉平说:“但详观全词所写,于元夕灯会实用情描摹,并未见笔致幽约吞吐之处。如果一定要套到寄托的框架中去,当然未必不行,但终显立论未稳,倒不如让它坐实艳词的面目,还读者一个轻松。”[10]398常国武亦指出:“通观全篇,这实在是一首地地道道的艳词。”[11]190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这首词是别有寄托的。顾随说:“夫那人而在灯火阑珊处,是固不入宝马雕车之队,不逐盈盈笑语之群,为复是闹中取静?为复是别有怀抱?为复是孤芳自赏?要之,不同乎流俗,高出乎侪辈,可断言。”[12]24夏承焘说:“说这首词主要是写一个孤高、淡泊、自甘寂寞的女性形象,那还是表面的看法。作者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有许多作品,大抵都寄托了他自己的身世之感。这首词里的‘那人’形象,何尝不是作者自己人格的写照?”[5]120刘扬忠说:“我认为梁启超所谓‘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算是推测到了它别有寄托,然而‘自怜’之说,却有违稼轩本意。这里所表现的,恰恰不是‘自怜幽独’,感叹被冷落,而是一种耐得清冷、耐得幽独,自守清高的政治情怀。”[13]130张忠纲曰:“稼轩恋情词中亦有少量确为有意识寄托自身情怀的词作,明写恋情而实寓身世之感,寄慨遥深,意在言外。为后人称许的《青玉案·元夕》即属此类。”[14]88喻朝刚亦说:“作者笔下的‘那人’,不慕繁华,自甘寂寞,与世人情趣大异,是一个富于象征性的形象。词人对‘她’的追求,寄托了深刻的寓意,表达了不愿随波逐流的美好品格。”[15]859
二、“寄托论”:被过度阐释的主旨
以“寄托”论此词者,主要依据有如下三点,且这三点逐层推进:第一,此词末三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别有深意,所寻的“那人”不同流俗,自甘寂寞,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写照;第二,词人的个性、怀抱与词中的“那人”形象相契合;第三,辛弃疾在政治上不得意,故其词多有寄托,这首也不例外。仔细分析之下,“寄托说”的这三点依据,亦正是其症结所在。
(一)对词末三句的辨析
就第一点而言,论者多将焦点放到词的末三句上,并据此阐发,从而割裂了文本的整体联系。解读此词的关键不在于最后三句,而在于下阕前三句:“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这里的“他”毫无疑问就是后面所说的“那人”,但是“他”并非突然出现的一个形象,而是与前二句有承接关系:正是因为那位笑语盈盈又身带幽香的美丽女子远去了,词中主人公才要去“寻他”。也即是说,“那人”和“他”就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的女子,并不是什么幽独不群的女性。只有这样理解,“他”的出现才不至于突兀。谢永芳在这首词的“题解”中说:“词写元夕观灯,灯火阑珊,心底涌起的另一番情味反而愈加缱绻,挥之难去。前一部分打通上下分片通则,极写元夕的辉煌灯火以及观灯的热闹场面。‘众里寻他’以下,写灯火冷落处所苦苦寻觅的心仪对象。在前后极其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中,表现出‘自怜幽独’之意。”[16]214且不论所谓的“打通上下分片通则”的说法是否正确,即使“蛾儿雪柳”二句和上片的“宝马雕车”都是泛写游玩的群像,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突然出现的“他(她)”以及“众里寻他”这一件事呢?“寄托说”认为词人整晚在苦苦寻觅一位不群的女子,可是我们在词里看到的除了寻人一事外,词中男主人公还饶有兴致地写了各种热闹的景象,笔调是那么轻快,语言是那么明朗,这反倒表明他出行不是带着寻人的目的,而是就像大家一样游玩闲逛而已。这种情况下,词旨的严肃性被极大地冲淡了,如果还坚持“灯火阑珊处”的女子是一种人格、品质的象征,我们也无法对这个问题自圆其说:男主人公在游玩的路途中,突然心血来潮要去找一位女子,“众里寻他千百度”表明这位女子不应该是约定好的熟人或朋友,这样一位陌生的女性,仅仅是因为“在阑珊处”就表明她高洁不群吗?
将“灯火阑珊处”视为暗喻女子高洁不群的证据,这既不严肃,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果更审慎地考察一下辛弃疾其他的词,我们会发现,那些能确定有一己寄托的词作,或在词中描写南北局势和景色,或提到军事物象,或采用历史上那些精忠报国的人事典故,或选用具有家国之思色彩的传统意象等。总之,词人总会留下可以破解的证据和线索,使读者知道他要表达的是文字之外的意思。可是,在这首词中我们看不出这样的证据,相比之下,“灯火阑珊”根本就没有太多的言外之意,更别说有什么固有的喻指性。假使一个词语没有形成某种稳定的言外之意和互文传统,我们对其求之过深或者别为旁解,就走上了一条自说自话、根本无法求证真假的歧路。陈邦炎反对将这首词当成词人自况,但是他仍将词中“那人”与上片孤立来看,认为:“这(指‘蓦然’三句)是一个与前八句所描摹、烘染的元夕场景迥异其趣的意境,也是一个极美、极高的意境。这里,没有人对‘那人’作外貌或内心的描述,只推出了一个以‘灯火阑珊’作背景的画面,而读者自会想见其亭亭玉立的倩影及其孤芳高洁的情操。”[17]134这也成为一种刻意求深之举,或者说只是一种感悟、发挥之言。
从创作心理考察,词人写“灯火阑珊处”而非其他地方,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加强对比——既然前边写了热闹,后边就必须写岑寂或者清冷,这是写法上的需要,进而突出辛苦找寻之后发现“那人”的惊喜之情,而非为了“寄托”。这种“惊喜”,与之前游玩时轻松欢快的气氛相照应,又在其基础上有所升华:从被动的“看”,到主动的“寻”,在这场节日狂欢中,主人公不再是无目的游冶的旁观者,而是由惊到喜的主动参与者。
(二)自传体解词及其影响
第二点依据基于第一点而来,并且进一步将这首词看作自传体。由于研究者据此词末三句认定了这位女子是一位特别的女性,那么接下来的逻辑似乎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一个不群的、甘于寂寞的女子,由于没有确指,具有一定的朦胧性,人们的解读习惯往往会将其当成一种虚笔和象征,而词中男主人公对这种象征形象的追求,正反映出对某种人格、品质、气质的企慕或认同。
按照解诗的经验,词中的“我”被看成词人自己,再结合词人的主要经历和个性特点,这首词就成了词人剖白自我的心声。正如诸葛忆兵所论:“词人真正爱慕、追求的是一位自甘寂寞、远离尘嚣、沉思娴静的女子。这位理想女性,不就是词人不慕荣华富贵、超众脱俗、清高孤独人格的写照吗?词人并不是真的要在人群中寻找这么一位女子,否则,根据辛弃疾在此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好,他应该到冷僻幽静处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才合理,为什么要到喧闹的元宵灯节来呢?词人不过是借用特定情景,表达自己的心胸怀抱。”[18]第一句话就显示了论者是在两个前提条件下来解读这首词的:其一,偷偷地将词中主人公置换为词人,默认此词为自传体;其二,认定这位女子绝非寻常女性,而是“一位自甘寂寞、远离尘嚣、沉思娴静的女子”。
默认此词为自传体这一行为要比笃定词中女子高洁、不群更加危险。美国学者艾朗诺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说明这种解读方式对解读易安词以及那些伪作有多么大的影响,同时也非常警惕地指出:“词体文学的自传体阅读习惯并不仅仅适用于李清照或其他女词人,读者也如此欣赏男词人的作品,个别词家尤其突出……欧阳修常写情爱之词,而读者又无法明确分辨词作者与词中角色的界限,致使他的政敌借机利用,冒欧公之名伪造了若干首词来描写老夫对少女的爱情,以此坐实他的‘盗甥’罪名。”[19]85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词与诗的不同:诗是要“言志”的,尽管辛弃疾的诸多词作在功用上已经与诗的这一传统合流,可是词毕竟不是诗,其娱情的功能始终没有被词人完全抛弃。对于《青玉案·元夕》而言,它为什么就不可能是词人游玩时候的一时兴起之作?即使不是出于自己寻芳幽会的真实经历,是不是可以依据他人情事敷衍成文呢?我们将会在下文看到,在当时环境里男女欢会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词人完全可能将这一普遍性事件当作素材写入词中。自传体预设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将这种可能性抹杀掉了,尽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编年系事与循环论证
自传体的预设,加上对“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悟式解读,又敷衍出了第三点证据。既然词中男主人公被当成辛弃疾自己,那么这首词的产生动因就与辛弃疾的境遇紧密联系起来了。即便无法确知何年何地因何事促使辛弃疾写了这首词,研究者们仍然试图把它系年到词人最为苦闷的时期之一,并且相信:一定是由于政治抱负不得施展,词人才写了这首词以表心迹,抒发幽怀。夏承焘说:“这词编在四卷本《稼轩词》的甲集里,甲集编于淳熙十五年(1188),可知这词必作于淳熙十五年之前。淳熙十五年,作者四十九岁,他被迫退休于江西上饶,已经六七年了;这词里所谓‘灯火阑珊处’,可能也就是作者那时在政治上被排斥的境地的写照。梁启超说这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很可信的评语。”[5]120推知此词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以辛弃疾被迫退居上饶六七年为此词的写作背景和动因则明显不妥。因为我们无法将这首词明确系于这“六七年”之内或之前。还有学者如邓广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将之系于更早的乾道七年(1171年),那时我们的词人正在司农寺主簿任上。虽然夏先生说这首词“可能”是词人被排挤的写照,但是他对梁启超的评语加以肯定,表明他实际上认为这首词写于词人退居上饶时期或稍后。现在看来,这种系年是缺乏说服力的。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自传体的预设之下,研究者倾向于朝着有利于“寄托说”的方向去编年系地、考订事迹,反过来,“明确”的创作背景又为“寄托说”提供了支持,造成循环论证。王步高在《稼轩词〈青玉案〉写作年代》一文中,列举关于《青玉案·元夕》系年的五种说法之后说道:“一般认为,这是作者自况,是在投降派当权时,自己仍顽强坚持抗战,不肯屈服的节操风度的真实写照。对于内容的这一理解,各家基本一致。我们且以此为基础,联系作者生平,对上述说法作一分析。”[20]首先认定写作背景就是词人受投降派的政治打压,然后联系作者生平去分析各家系年之说,其结果只会是越发坐实这首词的“寄托”之意。
三、《青玉案》文本的再认识
接受史表明,《青玉案·元夕》之所以越来越受人关注,是因为人们在这首词里看出了言外的深意。这不但提高了此词品格,使它看起来文如其人,而且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的巨大反差,也使其更加符合传统的审美标准和期待。可是,回归文本之后,一旦我们发现此词所谓的“深意”很可能是被过度阐释的,又该如何去解读和看待它呢?
(一)回归文本整体性
在重新审视这首词之前,有必要反思相关的文本解读策略。在我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思维的影响下,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一切因素,都被当作解读一首诗的“钥匙”,但这把“钥匙”究竟能打开多少把“意义”的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葛兆光将这把钥匙称之为“背景批评”,指出精细准确的背景,确实有利于阐释诗歌的意义,但是“背景批评”并非万能,且存在很多问题:史料的匮乏使得背景模糊不清,而编年系诗者往往强作解人;即使背景清晰,诗人也很可能并非为此背景而触动诗怀;过分精细的背景,消解了诗中美好的情感,只剩下历史和事实的残酷[21]6–21。
以“寄托”解此词,所有的出发点都基于我们确知:作者是以收复失地、精忠报国为己任,却又屡受朝廷投降派打压的英雄式人物辛弃疾。这样的认识本身没有错,用来解读作品时则容易出现问题:不但忽视了词体并不等同于自传的可能,更没有考虑身为一个鲜活人物的情感和行为的复杂性。詹福瑞认为:要先从“常情”的角度看待词,而不是只将其当作历史的记录,有的词是有寄托的,“但也不是所有的迷离其言的词都有寄托,或者把柔情绮思、描摹物类,都视为迷离其言的寄托。词人是人,也有常情,喜欢花花草草,喜欢虫鸟动物,喜欢漂亮的女人,甚至还要调调情。顺手填词写诗,无非一时遣兴之作,有何深意?但学者专家偏不信,偏要钻到里边去,从小中找大……不相信平常心、庸常情,实则是被诗的比兴理论异化了”[22]154。
尤其是当这种“知人论世”的解读行为使得文本无法自成一个完整的语境,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重新审视解读策略存在的问题?上文已经指出,在“寄托论”的统摄下,这首词上下片的逻辑关系迥异他词,下片各句的语意也无法衔接连贯,可惜持“寄托论”者没有注意到。
既然这首词无法给我们提供较为明确的编年系地信息,首先考虑的解读策略应该是从文本分析入手,尝试如何解读才能将文本的各个部分沟通成一个意脉贯通的整体:“进入文本分析的层次,就是要把全部复杂的、分散的乃至矛盾的部分统合起来,使之在逻辑上有序化,这就是最起码的一元化。”[23]146“这里所谓的元,通俗地说,就是系统性。”[23]147以文本的系统性为着眼点,我们试着分析这首词到底写了什么。
作为节日词,上片从色、香、声三方面极写各种热闹场景:“花千树”“星如雨”,写灯火辉煌;“宝马雕车香满路”写游人之众和香味;“凤箫声动”写音乐响起,“玉壶光转”写光影变幻,“一夜鱼龙舞”写表演之盛。在这举城狂欢的场景里,观者的所有感官被充分调动起来,各种感觉被不断打断又重新被激发,不仅目不暇接,而且鼻、耳、心亦不暇接,暗示了这场狂欢的盛大异常:首先眼睛被远处高悬的灯火所吸引,正满心惊叹时闻到一阵阵的香味,不得不把投向远处的眼光拉近,发现人们骑着宝马、坐着豪车从眼前经过,香味正是从车上散发出来的。很快,观者又被响起的笛箫声吸引,在月光、灯火的辉映下,看到了鱼龙戏舞。上片不是依照常规的远、近、高、低、大、小、深、浅的先后空间模式布局,而是随着心理感官的随机变化行文。可以说,上片的所有感觉和印象,都很碎片化,观者犹如一台没有完全确定焦点的摄像机,被迫在各个拍摄对象之间游移不定。
下片则明显不一样。不但观者的视野达到了聚焦,其心理情感也达到了聚合,落在“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的女子身上。“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二句明显与上片的写法不同,所写不再是模糊的印象,而是具体的形象,观者的感官再没有被其他事物打搅,而是全部停留在近处的女子身上,她美丽的衣饰、动人的笑语和身上的幽香,都深深地吸引着观者。为何此时不去表达爱意呢?怕是观者已经目摇心醉、一时痴了吧。等回过神来,这位动人的女子已经消失在人海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正见痴态,而于“蓦然回首”之际,却发现这位女子正在身后。“灯火阑珊处”这种安排,一是与前片热闹形成对比,借以反衬发现“那人”的喜悦之情,二是给读者提供一个“久寻未得”的解释:观者只顾着在热闹明亮的地方去寻找,却忽略了灯光昏暗的地方。我们应注意到,词中“寻他”这一情节颇具戏剧性,与古代才子佳人恋爱的某些情节很相似:才子对佳人一见钟情以至于苦苦“寻芳”,历尽波折,最终得到一个较为欢喜和满意的结局。这一情节安排很可能是词人故意为之,造成喜剧的效果,用以契合整个节日的欢乐气氛。
(二)文本的外部考察
从文本本身出发,此词重点应该就是表现元夕时节的男女情事,至于是否词人自道,我们无法确证。而从宋代元夕文化和相关词作来看,在元夕词中书写男女情事,乃是渊源有自。
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元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民间节日,由于官方对这一节日相当重视,促成了元夕时节举国狂欢的盛况。首先,皇宫禁内会张灯结彩,表演歌舞。其次,官府会主导和安排社会上的庆祝活动,如搭建作为庆祝之用的“山棚”,在“山棚”前建起三座彩门,彩门上用金泥书写牌匾“宣和与民同乐”,设立“棘盆”,棘盆内设置乐棚,差遣府衙中的乐人奏乐和表演杂戏等。再次,官方还会参与社会上的庆祝活动,如天子会于正月十六登上宣德楼,卷帘宣谕万姓,而京师的地方长官则会在放灯第五夜,乘坐小轿子,由舞队簇拥着出行,可以前后连绵十余里,遇到一些小商小贩,随行的官吏还会给他们发钱。官方的大力主导和参与,使得当时元宵节“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阡陌纵横,城阍不禁”。这样一个完全放松而喜庆的日子,为游玩的男男女女创造了欢会的机会,正如柳永《玉楼春》词中所说“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隐晦地指出正是元夕这“不禁夜”的狂欢环境,促成了大量的幽会欢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说道:“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24]173
基于这样一种元夕文化环境,在描写元夕的宋词当中,寻芳欢会、男女情事就成了很常见的内容。除了以上所举柳永的《玉楼春》,据传为崇宁间太学生江致和所作的《五福降中天》一词,毫不掩饰地描写他在元宵时节偶遇一绝色女子,乃念念不忘,渴思幽欢之情。词曰:
喜元宵三五,纵马御柳沟东。斜日映朱帘,瞥见芳容。秋水娇横俊眼,腻雪轻铺素胸。爱把菱花,笑匀粉面露春葱。 徘徊步懒,奈一点灵犀未通。怅望七香车去,慢辗春风。云情雨态,愿暂入阳台梦中。路隔烟霞甚时遇,许到蓬宫。[6]35
南宋杨湜的《古今词话》和宋代传奇小说集《绿窗新话》皆录其本事,虽难辨真假,然当时元夕之风俗好尚,于此可见一斑。
早于辛弃疾的李邴,其《女冠子·上元》描绘他在元夕日置身于北宋汴京的所见所感,亦提到男女幽会的情形:
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天街游处。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毕豪富。纱笼才过处。喝道转身,一壁小来且住。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 东来西往谁家女。买玉梅争戴,缓步香风度。北观南顾。见画烛影里,神仙无数。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归去。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26]950–951
除了与辛弃疾一样写了灿烂的花灯、豪富的游人外,他还写到一对对欢会的情侣,此外还有来来往往的妙龄女子和花枝招展的青楼女子,看得他目摇心醉又尴尬不已。这暗示了男女欢会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范成大《菩萨蛮·元夕立春》写道:
雪林一夜收寒了。东风恰向灯前到。今夕是何年。新春新月圆。 绮丛香雾隔。犹记疏狂客。留取缕金幡。夜蛾相并看。[26]1618
所谓“缕金幡”,就是镂金的春幡,于立春日簪之于首,乃古之旧俗,“留取”二字则暗示此“缕金幡”为一女子所赠,联系前文“绮丛香雾隔。犹记疏狂客”二语,可知此处乃是追忆一段情事。略晚于辛弃疾的孙维信在词中明确提到自己游冶花丛的经历,其《望远行·元夕》曰:
又远到元宵台榭。记轻衫短帽,酒朋诗社。烂漫向、罗绮丛中,驰骋风流俊雅。转头是、三十年话。 量减才悭,自觉是、欢情衰谢。但一点难忘,酒痕香帕。如今雪鬓霜髭,嬉游不忺深夜。怕相逢、风前月下。[26]2485
作者置身于“元宵台榭”的场景中,仍念念不忘当年的情事,对30年前“烂漫向、罗绮丛中,驰骋风流俊雅”的经历记忆尤深。再如高观国的《声声慢·元夕》:
壶天不夜,宝炷生香,光风荡摇金碧。月滟冰痕,花外峭寒无力。歌传翠帘尽卷,误惊回、瑶台仙迹。禁漏促,拼千金一刻,未酬佳夕。 卷地香尘不断,最得意、输他五陵狂客。楚柳吴梅,无限眼边春色。鲛绡暗中寄与,待重寻、行云消息。乍醉醒,怕南楼、吹断晓笛。[26]2358
“鲛绡暗中寄与,待重寻、行云消息”,暗示与陌生女子的一见钟情,与《青玉案·元夕》的情节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此处是寻而不得。
总之,在元夕节令词中书写男女情事是有一定传统的,《青玉案·元夕》也遵循着这一传统。就主题和内容而言,此词与宋代那些描写元夕热闹情景和男女情事的词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在下片,词人以一贯的幽默,构建了一个小小的富有戏剧性的独幕剧,为词中元夕热闹的场景添了一笔欢乐的气氛,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艺术创新力。以上反思,并非为此词主旨强做定论,而是区分不同说法和相关证据的可信度,试图在此基础上找出更合理的解读策略。本文并没有发现考据学所谓的“死证”,同样,持“寄托论”者也无法提供准确的编年系事的证据,既然这样,毋宁直面文本本身,并将其置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宋词书写传统来考察。同时,我想指出:尽管“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文学作品允许出现不同的理解和感悟,但是这只是针对读者而言;对于作品以及作者本身来说,作品的主旨是一定的,是不可发挥的,本文的立足点即在于此。
① 以古歌曲“阳春白雪”为词籍名,除了编选者可能有自矜之意,还暗示了音乐歌唱方面的考量:古曲《阳春》《白雪》之难和,不在于歌词,而在于乐调太高,所以宋玉说“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此外,沈松勤教授勘比了《阳春白雪》每卷所收之慢词和令、引的数量,指出是集“有意识地以调谱类别而编,体现了分类选歌的功能特征”。见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② 唐圭璋在《词话丛编》中将“柳耆卿‘却旁金笼教鹦鹉,念粉郎言语’,花间之丽句也;辛稼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亦近似柳七语矣;山谷‘女边着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如齐梁乐府‘雾露隐芙蓉’、‘明灯照空局’,何等蕴藉,乃沿为如此语乎?”析为两段:自“柳耆卿”至“柳七语矣”为一段,余下为一段。查《词话丛编》所用别下斋本《金粟词话》,“柳七语矣”之“矣”字刚好为一列最末一字,并无空格,所以从形式上无法判断是否该分为两段还是一段。但是从所讨论的作品看,即使不论《青玉案》一词,其余诸作都是在描写恋情,且句式类似,所以我更倾向于合为一段。
[1] 卓人月.古今词统[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 朱彝尊,汪森.词综:发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
[3] 周济.宋四家词选[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4]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1936.
[5]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6]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陈廷焯.词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梁启勋.词学:下编[M].北京:中国书店,1985.
[10] 彭玉平.唐宋名家词导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1] 常国武.辛稼轩词集导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12] 顾随.顾随讲词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13] 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M].济南:齐鲁书社,1990.
[14] 张忠纲,董丽伟.论辛弃疾的恋情词[J].文史哲,1992(4):88.
[15] 唐圭璋,钟振振.唐宋词鉴赏辞典[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16] 谢永芳.辛弃疾诗词全集[M].武汉:崇文书局,2016.
[17] 陈邦炎.说词百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 诸葛忆兵.论辛弃疾艳情词[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6.
[19] 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M].夏丽丽,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20] 王步高.稼轩词《青玉案》写作年代质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6):56–59.
[21] 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2] 詹福瑞.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3] 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4] 周密.武林旧事[M].李小龙,赵锐,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25] 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6]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I207.22
A
1006–5261(2021)01–0102–09
2020-05-04
齐凯(1989―),男,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