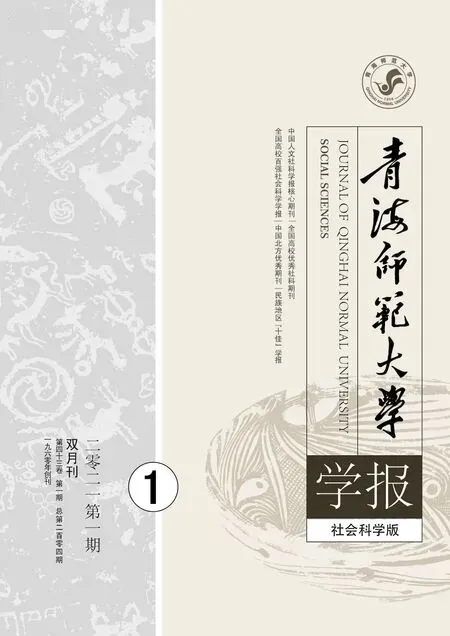征知与伦理
——荀子的“心”及其价值意义
耿静波
(天津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天津 300191))
作为先秦哲学的总结者和集大成者,荀子哲学在自然观、认识论、心性论等方面皆作出重要推进,尤其是其关于“心”的讨论,更具独到见解。而其关于“心”的探讨,确立于“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基础上。在自然观问题上,荀子在吸收老子和宋、尹学派自然天道观相关思想,剔除其中消极因素,在吸收孔子、墨子思想中重视人事经验的成分,批判他们关于“天命”“天道”等观点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自然观思想。《天论》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1]荀子指出,天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世间的治乱吉凶,与其运行没有必然联系,只取决于人是否合乎自然规律。以此为基点,荀子综合百家之长,对先秦认识论、心性论等进行了系统总结(1)关于荀子以“心有征知”等为代表的认识论,学界多有讨论,如惠吉兴认为荀子的认识论在本质上属于社会道德认识论,不是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见《解蔽与成圣:荀子认识论新探》,《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于宁等认为荀子的心、知学说在先秦儒学体系中最为系统,他的心、知学说并不是一种认识论或知识论的系统,而是一种依止于人格教养的智慧论,见《归本于人格学的智慧论──荀子心、知学说的一个特色》,《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闵永顺认为荀子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与唯物认识论结合起来,表明他的认识论思想已达到先秦时期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荀子的“天官意物”与“心有征知”思想探析》,《管子学刊》1996年第3期;严火其等则指出荀子的“天官”对个别性的认识是经验论、反映论的,“天君”对“道”的把握依赖于直觉和体悟。两种对事物的认识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而且应该相互补充,详见《必要的张力:在天官和天君之间——荀子认识思想新论》,《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
一
荀子认为,认识对象是与认识主体相对的现实存在。荀子肯定自然万物是客观存在的,有自己运动变化的规律,且自然规律不因人的主观好恶而改变;同时,其从“明于天人相分”出发,认为自然万物的生成消散是天地内在的功能,故其《天论》云:“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2]荀子的意思是,列星的转移与日月的更替,四时变更和阴阳变化,所有这些自然而然发生的现象,即是“天”。荀子在强调“天”“天道”客观自然性的同时,也指出其可知性。荀子语:“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3]
依照荀子的看法,人天生具有认识的能力,客观事物存在与变化又有可以被认识的规律。人认识事物的智慧和能力与生俱来;而认识则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的材质与认识对象的结合中产生的,是接触认识对象的过程。这同时体现了荀子认识论方面的世界可知论观点。
荀子在《正名》中语:“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行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4]这里的“天官”,如上所述,即人天生所具有的感觉器官,包括眼、耳、鼻、口(舌)、身等,它们各有其功能及不同的接受对象,每一种感觉器官各司其职,此即谓“当簿其类”。而“心”,也就是荀子所谓的“天君”,对“天官”所接受的具体感觉进行辨别和分析,即“征知”。在认识的过程中,“天官”的“簿类”功能不可或缺,但是鉴于“天官”所提供“答案”的主观性及臆断性,有时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以致正确“认识”的获得有赖于“天官”与“天君”的密切配合。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荀子看来,“征知”并不是认识过程的最终环节。荀子把学习视作认识的重要来源途径,强调认识的材质以及“心”的认知作用,然而,荀子认为,“行”才是认识和学习的最终目的及归宿。《劝学》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5]即只有把获得的认识和习得的知识,牢牢记在心里,融会贯通,切实落实到日用常行之中,才能获得“真知”。《儒效》亦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6]由此看出,荀子不单是指出“行”作为“知”的延伸与深化,甚至提出“行”高于“知”的观点。因为在其看来,认识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指导我们的具体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知道,行,体道者也。”[7]在实践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知”的价值,同时也能更深刻体会其中的意蕴。“体道”是“知道”的特殊形式,真正的体道者,必善于在实际行动中明察力行所获得的认识,做到“知有所合”。荀子甚至从圣人“行之”、德性伦理角度论证了“行可兼知”以及“行可证知”等道理。
二
对于解决认识上的主观性、臆断性问题方面,我们来看荀子相关论述,《解蔽》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8]在荀子看来,若心弛散而不能安定下来,则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以致连粗浅的道理也认识不清楚。其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9]结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在此强调,要做到“虚壹而静”,不因现有的知识影响接受新的知识,不因对别的事物的认识而阻碍专心地关注现有事物。如此,便能知“道”,进而达到清晰明了、圆融无碍的认识境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虚”“静”是道家的常用概念,借以说明本体以及本原状况。所不同的是,道家使用此类概念的时候,一方面,是在讨论本体状况;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同时寓有超越性的价值追求。而荀子则是借“虚壹而静”,予以说明使“认识”客观理性呈现的方法。也就是说,荀子对“心”的认识、理解与道家强调对“心”精神性价值追求的阐释是有所区别的。
在荀子的认识论系统里,由知性层面来看,无疑,认识“天道”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自然。他说:“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观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10]在荀子看来,人在做到“虚壹而静”之后,可以抵达圆融无碍的认识境界,即可以理解和把握宇宙的一切有形。进而,人们就可以坐知天下,通达古今,明观万物而看清真相,考察社会治乱而通晓法度,治理天下,掌握规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对“认识”地位及作用的极度重视,对宰制自然世界的莫大期许与自信。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以及“虚壹而静”的思想,是从理论层面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认识的一次重大突破,把人同自然界区分开来,将人看作是“自觉的人”,重视其理性分析及推演能力,人是自然之主,应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反观荀子之前涉及天人关系的几种观点。殷人崇敬具有祖先神性质的“帝”之后,周代更多的是祭祀“天”,认为“天”为至上神,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是“天”按照主观意愿所作的安排。而就思孟学派的思想体系来看,“天人合一”价值理想的完成,也只是在过于重视价值视域,通过“尽性”来实现的。至于墨家方面,较之其时流行的“天命论”及“时命论”,墨家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更为系统与严密,却对经验主义过分依赖,重塑宗教信仰,以致最终确认“天意”、鬼神的存在。因此可以说,荀子的上述认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进步,由荀子对人作为知识主体的强调,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认识论是对先秦诸子认识论的重要发展与推进,对于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
荀子是以“知”来阐释人的本性的。荀子《解蔽》:“人生而有知。……心生而有知。”[11]同时,《非相》又提到:“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12]荀子这里是以“知”“辨”指出人之为人的本原。荀子认为,人天然禀得的“性”,仅是一种能够辨别的能力。结合孟子对“心”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对“心”的诠释与荀子对“心”的阐释截然不同。由孟子依“不忍人之心”确立性善论,我们很容易理解,孟子把心看为道德本心;荀子则承认人天生有认识的能力,物本来有可以被认识的理则,认识结果的获得有赖于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相接触的过程。这表明了其对感官认知作用的认可。有鉴于此,荀子尤重视“心”的思维功能。荀子将人的目、耳、口、鼻、形体等感觉器官称为“天官”,把“心”等人的思维器官称为“天君”。荀子认为,心作为思维器官,与“天官”相比,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和能力。他说: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13]
意思是说,心是身体的支配者,精神的主宰者。它是“天君”,是命令者,它发出命令驱使“天官”。它是主动、能动的,而不是受动、被动的。心的限制或使用、行动或停止,都是自己作主,心也不能被强迫而改变意志,其对身体、精神的主宰具有绝对性。但作为“天官”的口却能被外力所强制而说话或沉默,形体也可被外力所控制而运动或静止,其他的感官也是如此。
当然,荀子在强调“心有征知”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由人的情感等心理升华而形成的道德意识,即“心”的道德理性范畴。自春秋时起,人们对“心”的认识有所发展,在将其与耳、目等感官并提,肯定其生理现实性的同时,把“心”抽离出来,赋予其道德评判的功能。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曰:“心不则德之经为顽。”这显然在生理属性之外,使“心”承载起道德属性。这一倾向,在孟子、荀子思想中均有体现。在以“情”为“性”的基础上,荀子认为由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正名》云:“性者,天之就也。”[14]《性恶》亦提到,“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15]“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而“善”则来自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秩序建构的需要,其“凃之人可以为禹”亦是源于“心”控制情欲并使之合于道德的能力。如《正名》曰:“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17]依荀子看来,人具有饥食渴饮以及好利恶害、好逸恶劳等自然本性,而“善”出于人为。鉴于此,只有以心控制情欲,方能确立道德意识。这样看来,在道德教化方面,与孟子由“本心”“性善”出发而重视“存心养性”,重视内在“善性”相比,荀子则是更注重“向善”性,强调道德内省,主张人们通过努力修习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综上,荀子对“心”的独特论述,及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人性相关思想,对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对董仲舒及扬雄的心性论产生深刻影响;及至宋明,尽管孟子的性善论占据宋明理学支配地位,荀子的性恶论更多地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荀子的人性论亦成为宋儒构建人性理论的重要参考依据及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司马光语:“孟子以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诱之也。荀子以为人性恶,其善者,圣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遗其大体也。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而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18]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更是对孟、荀人性论进行了系统整合。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荀子基于“心有征知”、情性等而确立的独特心性思想对中国古代心性哲学、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关于荀子心性相关思想的探讨思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以及新时代文化建设等,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