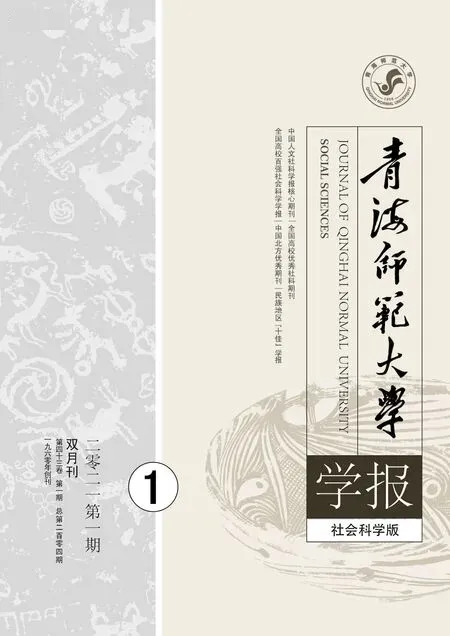《左传》所见族灭现象与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
牛杰群,李健胜
(1.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2.青海师范大学 黄河文化研究院,青海 西宁 810008)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社会动乱期,随着王权的衰落和各诸侯国实力的增强,以周礼为制度文化基础的周代贵族政治体制逐渐崩解。这使得各贵族集团围绕着国家权力与自身利益展开了一场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因此产生族灭现象。春秋时期的族灭现象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贵族政治崩坏的历史事实,也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观念的变化。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与族灭关系较为紧密的预言、“忠”、宗族观念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族灭与春秋社会的预言观
细读《左传》可以发现,在一个家族灭亡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预言[1]来对这个家族的命运做出预测,且很多都得以应验。虽然这些预言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并使我们对《左传》作为编年体史料的可靠性与权威性产生怀疑,但即使如此,从这些预言性质的史料中,依然可以发现以《左传》为载体反映的春秋时期复杂多元的思维观念。
当代学者大都按照自己所设定的标准对《左传》中的预言进行了分类(1)参见贾红莲:《〈左传〉预言发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潘万木、黄永林:《〈左传〉之预言叙述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曲文:《论〈左传〉中的人事预言》,《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邵志叶:《〈左传〉预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黄明磊:《〈左传〉历史观与春秋史的建构——以预言性质史料为角度的考察》,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大体来说,可分为神异预言、人事预言、自然预言(2)本文对《左传》中的预言分类,主要采用黄明磊的研究成果。参见黄明磊:《〈左传〉历史观与春秋史的建构——以预言性质史料为角度的考察》,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42页。。族灭现象主要涉及神异预言和人事预言,以下笔者详述之。
神异预言为书中一些历史人物利用相术、卜筮、梦境、谶谣、鬼神、氛气等神秘超自然的手段对同时期某个家族的命运前途作出的预测和判断[2]。这一预言主要表现在族灭家族的宗子身上,如若敖氏的宗子斗越椒出生时,子文前往探视,见其状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3]《左传·宣公四年》在其临死前,聚其族人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4]《左传·宣公四年》《左传》的记载也影响到了后世史家的看法,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认为“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灭若敖氏是也”[5]卷七《性相近也》,清代的高士奇也言:“越椒狼子野心,必灭若敖氏之宗”[6]卷四十六《楚诸令尹代政》,可见《左传》这种神异预言影响之深刻。无独有偶,类似预言在其他家族灭亡的过程中亦有体现,如羊舌食我出生之时,叔向的母亲前往探视,刚到大堂,听闻食我的哭声,就急忙返回,并言:“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7]《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国语》中也有相同的记载[8]卷十四《晋语八》,而后世史书在记载帝王出生时,运用的手法与此异曲同工。
《左传》中根据人的相貌和声音所作预言,并将家族兴衰归因于此,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后世一些学者也对其提出质疑,针对上述斗越椒的预言,清末的韩席筹认为:“……夫初生之子,闻其声而观其状,即断为狼子野心,而必欲杀之,已无此情理……此盖子文偶有疾恶越椒之言,椒亡,楚人追思子文之贤知,或过甚其词,传因叙录以寄慨耳。”[9]针对《左传》对羊舌食我的记叙,东汉思想家王充认为“食我之乱,见始生之声。孩子始生,未与物接,谁令悖者?……人生目辄眊瞭,眊瞭禀之于天,不同气也,非幼小之时瞭,长大与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恶有质……”[10]《论衡·本性》。可见,在古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由相术而成的预言,但这些神异预言也反映了在礼乐崩坏环境下相术观念的广泛流行,以及家族兴衰系于宗主个人禀赋的观念。
除此之外,《左传》中的族灭现象大量表现在人事预言当中。人事预言,为某个历史人物通过对其他人物的言谈举止或某些行为观察后,对该人物或家族未来命运的推测和判断。[11]如鲁文公九年(公元前618),斗越椒前往鲁国朝聘时,因其行为傲慢,叔仲惠伯预言其“是必灭若敖氏之宗”[12]。而晋国三郤在灭亡前,《左传》中同样有其族灭的预言。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郤锜去鲁国乞师,行为不恭敬,孟献子预言:“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13]仅仅一年之后,郤犨在卫国宴会上,因其行为傲慢,宁惠子言:“苦成叔家其亡乎!……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14]《左传·成公十四年》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晋厉公派郤至到周王室敬献楚国俘虏,郤至夸耀自己的功劳,单襄公也预言:“温季其亡乎!”[15]
类似的笔法在栾氏家族的族灭过程中仍然可见。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秦景公问士鞅,晋大夫哪个先灭亡,士鞅对曰:“其栾氏乎……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16]士鞅预言栾黡身上累计的无德行为会在栾盈身上得以体现,但从《左传》其他方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栾盈是个乐善好施之人,于是,神异预言与人事预言交叉的情况显现出来。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栾盈借齐国之力,回其封地曲沃准备叛乱,并把相关计划对胥午和盘托出。胥午曰:“不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子必不免。吾非爱死也,知不集也。”[17]而最终的结局也正如胥午所预言的那样。
相对于郤氏与栾氏这样因无德非礼而遭族灭之祸,从而使得家族骤亡,赵氏与楚若敖氏却在族灭之后幸运地得以复立,究其原因,与这些家族先前人物对“德”的重视与践行有极大的关系。[18]如赵衰并未因追随重耳回国而居功自傲,面对晋文公的赏赐,赵衰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臣弗如也”[19]卷十《晋语四》,表现出极大的谦让之德。晋文公赞赏其“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矣”[20]卷十《晋语四》。
《左传》中神异与人事等预言性质的史料,一方面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相信灵异,相信相术会使得家族兴起或衰亡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人们尊德崇礼的社会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视礼德观念引导下的政治行为。而这些预言与行为也表现了春秋社会更加多元丰富的观念意识。
二、族灭与春秋社会的“忠”观念
《说文解字》云:“忠,敬也,尽心曰忠。”[21]可见,“忠”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社会美德。“忠”字在《左传》中出现70次[22],主要讲的是臣下对君上的效忠。
受商周贵族政治及服役制度影响而形成的双重君臣关系,在西周时期主要体现于天子与诸侯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及诸侯国内部诸侯与卿大夫事实上的君臣关系。春秋早期,随着天子与诸侯血缘关系的疏远及诸侯国的崛起,使得前者的君臣关系逐渐失衡,后者却更加稳固,表现出来的则是家族灭亡后部分贵族对国君的效忠。如若敖氏遭遇族灭之祸后,子文之孙箴尹克黄访齐归来,别人劝其不可回去,箴尹克黄却言:“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23]《左传·宣公四年》最终获得楚庄王的宽宥而复立其氏。
春秋中后期,随着各国政治权力下移,这种事实上的君臣关系在卿大夫及其家臣间也有出现。家臣一旦“策名委质”后,即与家主产生隶属关系,只知尽忠家主,而不知有国君,并作为正统的主臣关系准则为社会舆论所强调。[24]如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栾盈被范宣子逐出晋国,且严禁其家臣跟从,否则“为大戮施”,尽管这样,其家臣辛俞还是跟从栾盈。后被官吏所擒拿,晋君问其故,辛俞曰:“……臣闻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25]卷十四《晋语八》栾盈借齐国的帮助回到曲沃准备叛乱时,其党胥午问众人:“今也得栾孺子何如?”对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得主,何贰之有!”[26]《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讲此话者,应是栾氏的家臣)商周以来的双重君主观虽在春秋时期有所保留,并进一步深入贵族集团的各阶层。但这种忠于国君、忠于家主的君臣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表现出来的则是族灭过程中基于某种利益的“忠”。如卫国北宫喜灭亡齐氏后,与卫灵公盟于彭水,由叛乱之臣一跃成为卫国的忠臣,并获谥“贞子”,得齐氏之墓。墓地是家族中除宗庙外的第二个圣地,北宫氏灭齐氏而得其墓,可见其中的象征意义。
在臣忠于国君的前提下,国君也应该有一定的德行,如晏婴主张“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098页。银雀山汉墓竹简与《左传》所载类似,参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主编》(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8—99页。。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商周以来特定礼仪程式的君臣关系。正所谓:“君令、臣共,……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礼之善物也。”[27]《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族灭现象表现出的则是对这种礼仪型君臣关系及其观念的破坏。族灭之前,一方面家族“族大逼君”,架空公室,如楚之若敖氏,晋国的栾书与齐国的崔杼甚至还有弑君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君不讲“忠”观念,冤杀大臣并灭其家族。如楚之郤宛家族,因费无极的陷害而被令尹子常诛灭,这也正是春秋时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28]《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真实写照。
三、族灭现象与春秋时期的宗族观念——以血食为中心
西周春秋时期,国家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扩展而成。故对于贵族中的个体而言,家族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并且古代贵族认为鬼神和活人一样需要饮食,正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29]《左传·僖公十年》,所以在贵族团体中形成了强烈的保宗守族观念,保住宗族,就意味着延续祖先祭祀,就意味着其家族的血脉不会断绝。在族灭过程中,这种观念具有生动地体现。在家族灭亡前的预言中,会预言家族灭亡后,祭祀的断绝。而家族族灭后,公室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会恢复一些家族的氏族封号。无论是族灭之前的预言恐惧,或是族灭之后的家族复立,这些言语与举动的背后都表现出春秋时期以血食为中心重视家族延续的宗族观念。
(一)血食的一般含义
血液信仰是文明早期世界众多民族、部族的共同原始信仰。而这种信仰来源于人类在血液流完后人就会死亡的经验之中,意识到血液是人类灵魂的居所及其对于人体生命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从而产生了对血液的敬畏与崇拜。[30]血食一词在《辞源》中谓“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31]。《汉语大词典》解释其为“受享祭品。古代杀牲取血以祭,故称”[32]。但血食最初用的并非都是牲畜之血,也包含一定的人血[33],是以活人作牺牲,用之以祭祀祖先神灵。王克林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血祭[34],《周礼》中也有“以血祭祭社稷”[35]《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的语言表述。而“食”则有供奉或祭祀祖先神灵之意。因此,血食是通过用牲畜或人血来供奉祖先神灵,使其获得食物来源的一种祭祀方式。
“血食”一词,在《左传》与《国语》中均有出现。如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楚文王讨伐申国,路过邓国的时候,邓国三臣(骓甥、聃甥、养甥)主张杀掉楚文王,认为最后灭亡邓国的定是此人。但邓侯认为楚邓表亲,杀之不详。三臣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36]此句中的血食则含有祭祀祖先、社稷,使得国家、宗族得以延续之意。《国语》中对血食一词也有类似的表达,如“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37]卷六《齐语》“吴国为不道,求残我社稷宗庙,以为平原,弗使血食。”[38]卷十九《吴语》因此,只有家族得以延续,并且受到家族男性后代的祭祀,祖先才不会出现无祀可食的情况。而一旦家族遭遇族灭之祸使其灭亡,尤其是家族宗子等男性后裔的消失,其祖先则会面临无人祭祀的局面,也意味着家族血脉的断绝。故以血食为中心的保宗、保族、保祀的宗族观念,在春秋时期十分受到家族重视。如果宗族灭亡,宗庙也就绝祀,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孝,所谓“灭宗废祀,非孝也”[39]《左传·定公四年》。
(二)族灭与春秋时期的宗族观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些小的家族从大家族分离出来,并逐渐发展,与原来的家族逐渐疏远或基于各自利益而处于对立的阵营。没有发展起来的家族,由于谋求自身生存并适应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而继续依赖原先的家族。一些势单力薄的家族为政治避难,也不得不投身于强宗大族以获得庇护。上述说明,在春秋时期愈发激烈的政治斗争下,个人的荣辱是完全寄托于整个家族的盛衰之上的,而小家族的安危,同样仰赖于大家族的存亡。正如《仪礼》所言:“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40]《仪礼·丧服》在这种情况下,尊祖敬宗,保宗保族,注重家族血脉延续的宗族观念越来越被时人所重视。故《礼记》言:“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41]《礼记·大传》
若敖氏家族族灭的预言当中,子文为避免若敖氏遭遇族灭之祸,主张杀掉斗越椒,并哭泣着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42]《左传·宣公四年》意思为鬼如果也需要求食,那么若敖氏的鬼神不是要挨饿吗?子文之言,意为斗越椒会导致若敖氏灭亡,从而使其祖先无法食用血食而挨饿。果不其然,因若敖氏族大逼君导致其最终被庄王所灭,氏族封号被取消。正出使齐国的子文之孙箴尹克黄力排众议,回国向楚庄王认罪,楚庄王因为令尹子文当年曾“毁家纾难”的高尚政治道德,“使复其所,改命曰生”[43]《左传·宣公四年》,以改名的方式恢复其氏族封号。《国语》谓:“庄王之世灭若敖氏,唯子文之后在,至于今处郧,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后己之富乎?”[44]卷十八《楚语下》
正如若敖氏家族那样,因族灭导致其家族男性后代消失从而使其祖先断绝血食来源的情况,国君往往因其先祖有功于国或其家族曾经的有德之举等政治行为,出于保留其家族祭祀的考虑,会恢复其家族封号或立其后人以保证家族血脉的延续。春秋中后期,这种宗族延续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鲁叔孙豹与晋范宣子讨论何为不朽,范宣子认为“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45]为不朽。而叔孙豹则认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46]。叔孙豹把祭祀文化中的“不朽”观念转变为一个完全人本主义的“不朽”观念,是文化发展中创造性转化的实例。[47]可见春秋中后期,上述以血食为中心的保宗、保族、保祀的宗族观念更含有一层德性观念的色彩,同时也表现出家族成员的德行对于家族延续的重要意义。
综上,以血食为中心的保宗、保族、保祀的宗族观念,在春秋时期甚受重视,虽然一些家族因族灭而灭宗废祀,但因其先祖的德行或功勋,公室出于延续宗族,不使其祖先血食断绝的角度考虑,会采取改姓复氏或立其家族后人的方式,使其家族得以复立。而这些行为和举动也表明了春秋时期的保宗、保族、保祀的宗族观是商周以来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教、文化观念的上升与凝固,在此基础上德性意识的加入更加充实了这一观念的思想内涵,使其在春秋中后期得到一定的升华,并兼具一些人本主义的特征。
四、结 语
本文笔者就与族灭关系较为紧密的预言、“忠”、血食三个方面论述了族灭现象所表现的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在《左传》预言性质的史料中,表现出春秋时期人们一方面相信灵异,一方面又相信德、礼的社会观念,而这也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观念的复杂多元。在族灭与“忠”观念方面,虽然族灭现象与商周以来的双重君主观有一定关联,但族灭现象表现出的则是对这种礼仪型君臣关系的破坏。一方面贵族势力膨胀而架空公室,甚至于弑君窃国;一方面,君上不讲道义冤杀甚至族灭一些家族,即使如北宫氏在族灭齐氏后拥护公室统治,表现出来的也是基于某种政治利益的“忠”观念。与此同时,一些家族族灭之后,国君出于不使其家族祭祀断绝而复立其氏。正是以血食为中心的保宗、保族、保祀,重视家族血脉延续的宗族观念的体现。
总之,上述史实展现了春秋时期纷繁复杂的观念意识,或不断地更新与扬弃,或延续旧有传统,进而表现出春秋时期新旧交织[48]的社会特征。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社会观念及其演变发展的具体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