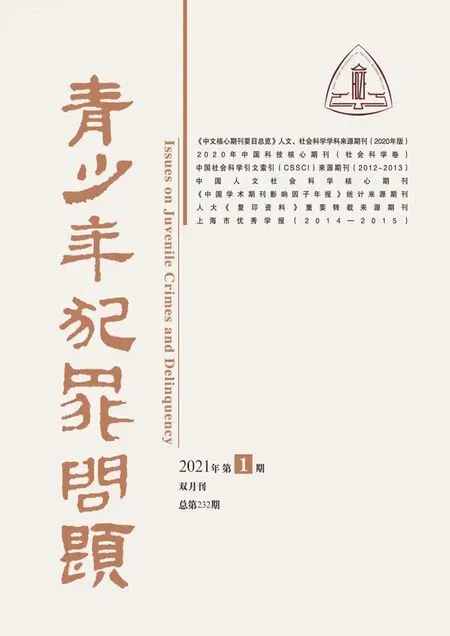对“犯罪着手”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陆诗忠
“犯罪着手”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其具有区别预备犯和未遂犯的基本功能,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因而,其也就成为犯罪停止形态理论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然而,在笔者看来,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着手”的研究还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亟须进一步的研究。
一、“犯罪着手”的判断标准研究
在“犯罪着手”判断标准这一问题上,德日刑法理论中历来意见纷呈,有“主观说”“形式客观说”“实质客观说”“折中说”之争。(1)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年版,第50页以下。众所周知,我国刑法理论历来强调“主客观相统一”是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理论在犯罪着手的问题上自会贯彻这一原则,是不可能将主观方面或者客观方面予以绝对化的,而是会充分考虑到犯罪的各个方面,不会存在“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弊端。因而,我国刑法学在“犯罪着手”问题上,并不存在主观说和形式客观说的理论土壤,由此也就不会存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上述争议。
从笔者所搜集的文献材料来看,我国刑法理论就“犯罪着手”的争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犯罪着手的判断中,是客观要素(行为的构成要件定型性、法益危险性)占主导地位,还是主观要素(犯罪的意图、犯罪的计划)占主导地位?在此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主观要素仅仅是用来确定行为所威胁法益的性质进而确定该行为是属于哪个罪名着手的主观材料。有学者则认为主观要素具有独立的价值,绝不只是判断客观危险的材料。按照后一种意见,如果一个行为不能直接体现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图,就不能成立犯罪的着手。(2)孙国祥:《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页。其二,行为对法益的危险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够认定为犯罪的着手,是抽象的危险即可,还是危险必须达到现实、紧迫的程度?(3)具体争论请参见后文部分。其三,“形式客观说”“实质客观说”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国传统观点被认为是“形式客观说”。传统观点认为,犯罪着手是指行为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行为。但该观点遭到了“实质客观说”的激烈批判。认为其存在不少问题:难以将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区别开来;会扩大或者缩小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忽视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等。(4)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据此,“实质客观说”认为在发生侵害法益的具体危险的事后,才是实行的着手。(5)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该观点已经成为学界有力的观点。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涉及的是对“犯罪着手”的判断,要不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要素的问题。对此,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判断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不能摆脱行为的主观内容而仅凭客观情况予以判断。对此笔者是赞同的。这是因为,犯罪人的主观意图、计划支配着客观行为的发展方向,进而决定行为的基本性质。完全离开行为的主观意图、计划,而试图能够确定实行行为的性质,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犯罪着手的认定上,当然也应当考虑成立犯罪所必要的主观要素。如,“为了盗窃枪支而伸手接近枪支的行为”。该行为相对于盗窃枪支罪而言,是具有导致枪支被盗的现实危险的行为,但是相对于意图取得枪支后在进行抢劫的犯罪而言,该行为就不具有引起财物被抢的现实危险性。所以,在判断犯罪着手时,应当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要素。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犯罪着手”判断中,主观要素的作用是,通过主观要素和客观行为的结合,来判断实行行为的基本性质,而不是如“主观说”所认为的那样,将犯罪的“着手”理解为将客观行为作为辅助材料来判断主观犯罪意图存在与否的依据。一言以蔽之,同样的客观行为在不同的主观意图支配下实施可能具有不同的实行性质。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犯罪着手的判断这一问题上,首先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当然,对超出主观意图之外的因素,诸如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犯罪计划等,则不必也不应当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相对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而言,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成为“犯罪着手”理论争议中最为集中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形式客观说”与“实质客观说”之争。在“形式客观说”内部又有“构成要件定型说”与“密接相关行为说”之分;在“实质客观说”内部又有“具体危险说”与“抽象危险说”之别。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我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具体的危险说。该说认为,构成犯罪着手应当是行为开始对刑法的保护法益造成“紧迫、具体、现实、直接”的危险或威胁。如有的学者指出,“实行行为只能是具有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的行为;行为人开始事实这种行为时,就是实行行为的着手”。(6)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既然刑法规范的任务是保护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利益,故对法益只有抽象危险性的行为没有必要处罚,当法益受到具体的危险之威胁是直接而又紧迫时,才应认定实行的着手”。(7)郑泽善:《刑法总论争议问题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页。
二是抽象的危险说。该说认为,认定为犯罪着手行为不必达到紧迫、具体危险的程度,只要对保护法益形成抽象的危险即可。如有的学者指出:“实行行为作为犯罪进入未遂阶段的重要标志,它所具有的不是所谓的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性,而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抽象的危险性。”(8)陈家林:《不能犯初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在笔者看来,将“犯罪着手”理解为具有急迫现实危险的行为并不可取。依据如此的理解,并不是行为具有法益的危险性就是着手,而是当危险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才是着手。从逻辑上看,“具体危险说”对犯罪着手的把握肯定会稍晚于“抽象危险说”。然而,如此理解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承认犯罪着手是犯罪实行的起点,另一方面,又认为“危险达到一定程度”,即当实行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时才是犯罪的着手。其理论前后显然是矛盾的。另外,其主张“只有危险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行为才是犯罪的着手,方具有刑事可罚性。这就意味着未达到一定程度的“实行行为”将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然而,这是不够合理的,对法益威胁具有间接性的预备行为尚具有刑事可罚性,较之预备行为对法益更具有威胁性的实行行为岂有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之理?再者,将“犯罪着手”理解为具有急迫现实危险的行为有违于犯罪着手理论的初衷。犯罪着手理论旨在解决预备犯与未遂犯如何区分的问题,而不在于解决“可罚的未遂犯” “不可罚的未遂犯”“不能犯”之间如何区分的问题。后者的区分应依据其他理论(不能犯理论、实质的构成要件理论、可罚的违法性等理论)去解决。换言之,将“犯罪着手”理解为具有急迫现实危险的行为,这是在赋予犯罪着手理论不必要的研究课题。在此意义上,确定犯罪着手,其意义就在于给未遂犯的成立寻找标准。一旦离开了“未遂犯成立界限”的实质内容,犯罪着手就不再具有任何实际的实践意义。最后,将犯罪着手理解为具有急迫现实危险的行为,容易将构成要件的行为(实行行为)一分为二,将前半段的实行行为划入预备行为。这是因为,在其看来尽管某行为在性质上是属于构成要件行为但只要它还没有产生急迫现实危险性就应当属于预备犯的范畴。这不禁会让人怀疑:将“犯罪着手”理解为具有急迫现实危险性的行为,这到底是在寻找未遂犯的着手时间还是在寻找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
在刑法理论上,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被认为是实行行为的定型,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法定的抽象危险性。因而,在犯罪着手的认定上,笔者赞同抽象危险说。只是该说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某行为在什么情况下会具有“抽象危险”。这就成为该说的诟病之所在。在笔者看来,当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即可认为具有“抽象危险”。换言之,当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包含着危害结果发生的根据和内容,具有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内在属性,能够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其行为就属于犯罪着手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果将“犯罪着手”理解为具有急迫现实危险的行为,那么在解释“隔离犯”“间接正犯”的着手时将存在一些问题。所谓“隔离犯”,是指行为与结果的发生之间在时间、场所上存在间隔的犯罪。例如,行为人以毒杀的意图,将下了毒药的白酒,邮寄到被害人住宅,被害人因饮酒而死亡的情形。在上述情形中,行为与结果的发生之间有着时间上、场所上的间隔,在理论上就被称为“隔离犯”。在“隔离犯”着手的认定上,理论上历来就有“寄送主义”“达到主义”之争。前者认为其着手时间是被邮寄的毒药发送时,后者则认为只有当毒酒被对方或者对方可能饮用的状态时,才是犯罪着手。“达到主义”无疑是将“犯罪着手”理解为具有急迫现实危险的行为。可是,如此理解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即“隔离犯”是否着手将取决于第三人的行为,不再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比如,在毒药寄送的过程中,邮局人员不小心将其毁坏,则其行为将不具有急迫现实的危险性,不成立犯罪着手;相反则成立犯罪着手。如此结论,难以为人们所接受。
“间接正犯”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所谓“间接正犯”,就是利用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例如,甲让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乙窃取了他人的财物。如果坚持将“犯罪着手”理解为具有急迫现实危险的行为,那么“间接正犯”的着手就应当是被利用者的行为具有引起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或者紧迫的危险。利用者开始实施被利用者的行为,以及被利用者开始实施犯罪行为时,都不能认为“间接正犯”的着手。可是,上述理解带来的问题是,使得“间接正犯”着手完全依附于被利用实施的行为是否已经“着手”。这样会使得“间接正犯”着手的判断完全失去了独立性。
需要强调的是,将犯罪着手仅仅理解为“犯罪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并不可取。有学者认为,犯罪着手是实行的起点,但不是预备的终点:“犯罪着手不是介于犯罪预备阶段和实行阶段之间的一个独立的阶段或点,而是实行行为本身的起点。”(9)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该论者还进一步明确了以下两点:第一,犯罪着手是实行行为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实行行为紧密连接几乎不可分割的行为;第二,犯罪着手不是属于预备阶段的预备行为的终了行为,而是实行阶段实行行为的开始。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之下,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固然是相互衔接的,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中间地带。但也有例外,即存在预备行为完成后,并未马上进入实行的情况,例如对被害人进行的“尾随行为”“守候行为”。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将犯罪着手理解为不限于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是将其扩展至与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紧密相接的行为,这是否会存在“形式客观说”的弊端?在“形式客观说”内部,有学者主张不仅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犯罪着手,而且实施与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有密接关系的行为”也认为是犯罪着手。(10)[日]植松正:《刑法概论I总论》(再订版),劲草书屋1974年版,第315页。但对此认识,学界不乏批判的声音:“扩张着手的范围到实施与实行行为密接的行为时,很容易使得概念不适当地变得暧昧,恐怕要招来预备、阴谋与未遂区别的困难吧!”(11)[日]日本刑法学会编:《刑法讲座》(4),有斐阁1973年版,第5页。但在笔者看来,上述疑虑显然是因为在理论上没有能够揭示出“有密接关系的行为”的真正内涵。但这不足以否定其合理性。这是因为,犯罪的预备行为都具有刑事可罚性,以犯罪论处。而较之更进一步,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行为却不能以犯罪论处。这显然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再者,将犯罪着手限定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将会出现对刑法法益的保护不够周延的问题。例如,甲以故意杀人的意图,用手枪已经瞄准被害人的行为,将直接立即破坏相关的刑法法益,该行为很显然是一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再比如,在抢劫罪中,如果乙已经手持凶器跟踪到受害人身后,假定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比如警察的及时赶到)就能立即实施犯罪行为,该行为很显然也是一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犯罪着手行为应当包括两部分内容:介于实行行为与预备行为之间的“犯罪着手”和作为犯罪实行行为组成部分的“犯罪着手”。换言之,开始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固然是“犯罪着手”行为,与构成要件行为紧密相接的行为,同样也应当被理解为犯罪着手。
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何种性质的行为是“与构成要件行为紧密相接的行为”或者说该种性质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对此笔者认为,该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与构成要件行为之间存在时间上、地点上的接近性;在成功实施该行为的场合,对于实行行为的实施,便不存在其他可成为障碍的情形,或者说,该行为的实施可以使得行为人排除各种干扰去进一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为了进一步明确该观点,下文结合五个具体案例予以阐释。
案例1:某甲因不满邻居乙将车子停在其门前,双手持菜刀一把及铁管一支到乙的住家门前想要和乙理论。乙不予理睬,甲即持铁管击破玻璃门上之玻璃,并扬言要杀害乙。乙于是跑上二楼打电话报警,并跑出家中。甲于是在后追赶约三、四百米时,即为警察查获。
在本案中,甲对乙进行追赶的行为本身并不属于构成要件行为(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也不属于故意杀人罪的预备行为。但是该行为与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关系紧密。其相对于故意杀人罪的预备行为而言则更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也就更具有刑事可罚性。在此意义上,该性质的行为应该理解为犯罪着手。
案例2:甲与乙是邻居关系,但相处的并不和谐。某日,二人因为琐事发生了争执。甲遂产生与乙全家同归于尽的念头,便用汽油泼在自己的身上及乙的房屋墙壁上,并试图用打火机点燃汽油。但是因为打火机受潮未能点着,又从身上取出另外一个打火机试图对汽油进行引燃。这时其父亲赶来将甲拖到马路上。当地警察也闻讯赶来,并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予以处理。
在本案中,甲所实施的行为并没有达到让目的物引燃的程度。故而,其行为并不属于构成要件行为(放火罪的实行行为),也明显不属于放火罪的预备行为。但是,一旦打着打火机,将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因而,甲第一次试图打出火的行为与放火罪的实行行为便具有时空关系上的紧密性。其相对于放火罪的预备行为而言则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更具有刑事可罚性,具有很强的刑事惩罚性。在此意义上,该性质的行为应当被理解为犯罪着手。
案例3:甲决意对一家银行进行抢劫。某天,甲持枪走进银行内,发现柜台仍有些顾客,甲等了几分钟后便在取款单上写上马上交钱的恐吓语,计划稍后递给柜台内的银行职员。只是写完后,其发现又有些顾客陆续走进来。甲于是放弃了该次抢劫行为。
在本案例中,甲的行为是否已经达到“犯罪着手”的程度?在笔者看来,当甲在取款单上写完恐吓语后,可以确定其已经具有抢劫的犯罪意图。虽然,该恐吓语需要等待适当时机才能交给职员,但是此时甲已经进入被害人领域空间内,只要一有适当时机,甲即交出写有恐吓内容的取款单威胁职员。因此,甲的行为应当理解为犯罪着手。
案例4:甲强行将某妇女乙拖到车上,意图到某一偏僻之处对该妇女实施性侵害行为。但在路上,该妇女侥幸逃脱。
本案中甲的行为是否属于强奸罪的预备行为,还是属于强奸罪的着手?在笔者看来,基于行为人拟到特定地点,才对被害人实施性侵害。所以,在其尚未到达犯罪地点之前的行为与性侵害行为之间欠缺空间与时间上的紧密关联性,且行为人对实现性侵害行为仍需要介入重要的行为。也就是说,虽然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际控制,但这种控制是为了稍后的性侵害行为而为的控制,因而不应将甲的行为理解为犯罪着手,而应当理解为犯罪的预备行为。如果行为人在性侵害之间所实施的强制方法足以令被害人丧失意识而无法抗拒,例如下迷药,那么即使行为人尚未找到特定地点进行性侵害,其行为应当被理解为犯罪着手。因为该强制行为通常可以持续到实质的性侵害之实行,无须行为人再实施其他重要的行为。
案例5:甲发现他人停放在屋外的小客车内有某些珍贵物品,遂产生窃取的意图。其便用万能钥匙插入该车右前门的锁内,试图打开车门。恰在此时,被小区的保安人员发现便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
甲的行为是属于盗窃罪的预备行为,还是属于盗窃罪的着手行为?在笔者看来,甲的行为应该属于盗窃罪的着手行为。其原因在于,在本案中行为人只要将车门一打开,车内的财物即可以被任意拿走。换而言之,该行为与“窃取财物”的行为具有紧密关联性,无需行为人实施其他重要的行为即可“水到渠成”地去实施“窃取财物”的行为。
根据笔者对“与构成要件行为紧密相接”的上述理解,下列行为均可理解为犯罪着手。1.“部分开始使用犯罪工具的行为”。开始使用犯罪工具的行为,一般来说是实行行为,不宜理解为“与构成要件行为紧密相接的行为”,比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使用犯罪工具的行为,就应当属于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但是对此也不能绝对化,犯罪工具的使用在不同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例如,行为人驾驶盗窃而来的车辆去某地抢劫或者杀人,途中被截捕。这里对汽车这个犯罪工具的驾驶,就应当理解为“与构成要件行为紧密相接的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是准备用车辆撞死被害人而驾车向被害人冲去,这里对犯罪工具的使用则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所以,“部分开始使用犯罪工具的行为”应当被理解为“与构成要件行为紧密相接”的行为。2.接近犯罪对象的行为。此类行为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对犯罪对象进行“尾随”的行为。该行为是指在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犯罪案件中,行为人对被害人紧跟其后,准备伺机进行加害的行为。另一类是对犯罪对象进行“守候”的行为。该行为是指行为人埋伏或等候在预定地点准备实施故意杀人、抢劫等犯罪的行为。3.寻找犯罪对象的行为。该行为人是指在故意杀人、抢劫或者盗窃犯罪案件中,行为人公开或者秘密查找被害人或者财物的行为。
在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实质客观说”忽视了“形式客观说”的积极方面,这是不可取的。“形式客观说”在犯罪着手的认定上坚持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形式客观说”虽然抽象空洞,但它是唯一符合犯罪构成理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再者,该说对“形式客观说”所作的批判也是存在不少可疑之处。其一,“形式客观说”将着手理解为开始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已经指明了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的界限: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才是犯罪未遂行为,否则是犯罪预备行为。这并非如某些批判者所言的那样,它“什么也没说”。至于说,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构成要件的行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由于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各不相同,当然不可能对其一一加以描述,而只能提出一个总的标准。具体的认定理应借助于其他刑法理论去解释。我们不能因为实践中仍需具体认定某种行为是不是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否认“形式客观说”的合理性。其二,批判者以“形式客观说”会扩大或者缩小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来否定其合理性,也是值得商榷的。很明显,批判者在这里是先入为主地将自己所确立的“处罚范围”理解为是恰当的。可其“恰当”性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不得而知的。其三,“形式客观说”不可能忽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形式客观说”是我国刑法学的传统观点。而“犯罪是主、客观的统一”是传统刑法学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自然会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对犯罪着手的认定上。
笔者虽然赞同“形式客观说”的基本立场,但并不意味着笔者就排斥“实质的客观说”。事实上,二者的关系应该表述为,“实质的客观说”是对“形式客观说”的补充,是对“形式客观说”的修正与发展。换而言之,我们一方面应当肯定“形式客观说”的基础地位,承认“犯罪着手是以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为标志”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在如何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行为的开始”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借鉴“实质客观说”中的合理内容。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要借助于“实质客观说”才能对某行为是否对法益具有侵害性作出具体的判断,才能最终确定该行为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行为”。
二、复行为犯着手的认定
复行为犯的着手问题,国内刑法学界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在复行为犯中,应当以行为人开始实施第一个要素行为为犯罪着手:“这类犯罪的实行行为,是由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两部分构成的。而两种行为都具有实行行为的性质,因此,只要开始实行手段行为,就应当视为该种犯罪的着手。”(12)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页。该认识居于通说地位。但也有学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复行为犯内部有着不同的类型,即“紧密型复行为犯”“松散型复行为犯”,这两种复行为犯的着手有着不同的着手标准。第一种类型的复行为犯,其着手的标准是行为人开始实施第二个要素行为;第二种类型的复行为犯,其着手的标准则是行为人开始实施第二个要素行为。为此,论者有以下论述:“紧密型复行为犯的特点是复数行为之间结合得比较紧密。只有行为人开始实施第二个行为后,才能够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害性,才能根据犯罪行为的种类、行为的具体表现从实质和形式相结合的角度认定着手的成立。所以,对于紧密型复行为犯来说,只有开始实施两种行为时,才能认为是整个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13)王明辉:《复行为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松散型复行为犯的复数行为之间结合程度较弱。所以在修正形态的犯罪考察中,对于复数行为不一定进行整体性考虑。只要行为人开始实施第一个行为就已经成立实行着手。”(14)王明辉:《复行为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论者将复行为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犯罪着手问题上赋予其不同的认定标准,则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论者一方面认为构成复行为犯中的要素行为都是实行行为,而另一方面又否认在“紧密型复行为犯”中实行行为开始并非犯罪着手,这显然是矛盾的,有违于犯罪着手理论的基本认知。在刑法理论上,犯罪着手被认为是实行行为的开始。况且,如果犯罪着手不是实行行为的开始,那么理论上还必须说明如何判断实行行为的起点,这无疑徒增了理论的负担。
笔者也注意到,在学界有否认“紧密型复行为犯”的见解,否认其第一个要素行为的实施确实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紧迫危险性,进而维护通说的见解:“对于诸如诬告陷害罪、损害商业信誉等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并列规定在同一罪状中的犯罪,经常被人误作复行为犯。其实,这些犯罪中的捏造行为只是一种预备性质的行为,根本不能与告发或者散布虚假事实等直接侵害法益的实行行为相提并论,自然应以开始实施告发或者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为着手,因此,应特别注意区分规定在同一罪状中的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15)周铭川:《论实行的着手》,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4期。笔者也赞同在“紧密型复行为犯”中,其第一个要素行为的实施确实不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紧迫危险性,但这不足以否认该要素行为是实施为犯罪着手的标准。这是因为,将实行行为限定为对法益侵害具有现实、紧迫危险的行为也是值得商榷的,对此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赘。另一方面,论者将“紧密型复行为犯”予以排除也难以为笔者所赞同。这是因为,“预备行为实行化”是具有法理依据的。承认该立法现象,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在笔者看来,无论何种类型的复行为犯,其犯罪着手的标准都是应当以行为人开始实施第一个要素行为。不过,在此我们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如果行为人实施的第一个要素行为就停顿下来,与第二个行为的实施在时间、地点上不具有密接性,就不宜认定为犯罪着手。这是因为,只有数个“要素行为”之间具有密接性,前后衔接,才能结合成一个法律意义上、整体意义上的行为,才能成立复行为犯。这是复行为犯的应有之义。这还因为,复行为犯是“构成要件的行为单数”。复行为犯的构成要件虽然是由数个要素行为融合而成的,但其实质是一个有机构成要件。该构成要件具有独立完整的结构,但是这种融合绝不是随意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则的。事实上,凡是属于“构成要件的行为单数”(接续犯、结合犯)的犯罪形态无不要求行为之间具有时间、地点上的密接性。比如,成立接续犯,要求行为人必须在同一个机会以性质相同的数个举动接连不断地完成一个犯罪行为一样;成立结合犯,不仅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基础犯罪和相结合之罪在犯罪场所上应当具有同一性,还要求二者能相继在同一时间实施。也就是说,只有当第一个要素行为能够与第二个要素行为具有时间、地点上的密接性时,其第一个要素行为的实施才是犯罪的“着手”。这一点既适用于“紧密型复行为犯”,也适用于“松散型复行为犯”。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紧密型复行为犯”,还是“松散型复行为犯”,其第一个“要素行为”在自然意义上都具有预备性质,但在规范意义上是具有实行性质的。在此意义上,第一个“要素行为”就不宜被理解为规范意义上的预备行为。因而,当行为人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要素行为,且该行为与第二个要素行为的实施在时间、地点上具有密接性时,就可以理解为犯罪着手。
三、原因自由行为(犯)的着手
所谓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如何认定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着手,在刑法理论上历来有三种观点。其一,“原因设定行为说”。该说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着手是行为人开始实施使其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定责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设定行为之时。(16)[日]木村龟二:《刑法总论》(增补版),有斐阁1984年版,第348页。其二,“结果行为说”。该说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着手开始于行为人开始实施结果行为之时。(17)[日]西原春夫:《刑法总论》(改订准备版)(下卷),成文堂1995年版,第463页。其三,“个别化说”。该说认为,在原因自由行为着手的认定上,应当分别不同情况予以考察:在不作为犯及过失犯场合。因为原因行为本身具有结果发生之现实危险性,故而应当以原因行为的开始为着手;在故意的作为场合则将结果行为的开始视为犯罪的着手。(18)[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第4版),成文堂1994年版,第378页。需要指出的是,第三种观点并无多少独立的价值,其在实质上仍然是“结果行为说”。这是因为,其之所以认为,在不作为犯及过失犯场合,原因自由行为的着手开始于原因行为,无非是原因行为本身就具有“结果行为”的属性。
在上述三种学说中,对我国刑法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当属“结果行为说”。比如,张明楷教授就认为,“在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应当以行为人实施结果行为、造成了危险结果时为着手,而不是开始实施原因行为(如醉酒)时为着手”。(19)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林亚刚教授就认为如果将结果行为的实施认定为犯罪着手,被非难的罪过就是经结果行为事后追认到原因行为之上而被非难的,如此理解并不符合“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的要求以及罪过认定的基本原理,因而“在原因自由行为发生法益侵害时,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为原因自由行为着手比较合理”。(20)林亚刚:《刑法学教义》(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页。
上述观点孰是孰非?在笔者看来,没有必要将着手问题与责任能力问题捆绑在一起,不能说行为人只有存在责任能力时,才能承认其行为存在犯罪着手的可能。“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只是认定犯罪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并不要求结果行为与责任能力同在。这正是创制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意义之所在。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确立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是为了防止客观归罪,从而坚持责任主义的立场。但原则必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并不违背设立原则的初衷,就是合理的,就应当承认这种例外。(2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1页。也就是说,应当将“犯罪着手”问题与“责任能力”问题分开而论,二者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前者解决的何为实行行为开始的问题,后者则解决的是主观罪过的前提问题。此为其一。其二,犯罪着手本身就是实行行为的着手。无论如何,“原因设定行为”并不属于实行行为的范畴,也不符合实行行为本质的要求。而原因自由行为的原因设定行为(如醉酒行为)不具有产生危害结果的基本属性。既如此,又怎能将“原因设定行为”的开始实施理解为犯罪着手呢?事实上,原因自由行为中的“结果行为”,与通常意义的实行行为并无什么不同。原因自由行为中的杀人行为、盗窃行为与故意杀人罪中的杀人行为、盗窃罪中的盗窃行为在犯罪着手的基本属性上应当是同一的,其着手不可能是其之前的饮酒行为之类的原因行为。
进一步分析,如果将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着手理解为“行为人开始实施使其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定责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设定行为”,难以合乎情理:按照“原因设定行为说”的理解,当行为人仅仅实施了原因设定行为而没有实施结果行为的,其所实施的原因设定行为也应当被认定为着手。然而,这难以为人们所接受。例如,某甲具有故意杀害他人的意念,遂大量饮酒以便“借酒壮胆”。但是醉酒后,甲自动放弃杀害他人的意图,没有进一步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根据“原因设定行为说”的理解,某甲的行为已经属于犯罪着手。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任何一位法官会认定某甲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否定“原因设定行为说”对犯罪着手的认定,也不会放纵对“原因设定行为”的惩治。我们并不否认“原因设定行为”的可罚性。这是因为,“原因设定行为”对“结果行为”的实施的是具有支配力的,具有“预备行为”的性质。据此对仅仅实施“原因设定行为”的,可以按照预备犯的规定处罚。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将“原因设定行为”予以犯罪化。
四、不作为犯罪的着手
“不作为犯罪”是指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能够作为而不作为的犯罪,即“应能为而不为”。不作为犯在理论上通常分为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因而,刑法理论对“不作为犯”着手的理论探讨是分别进行的。
刑法理论通常认为,基于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并不以法律规定的特定结果的发生为条件。因而其在能够履行而故意不履行该义务时,不作为行为即属于完成,法益侵害已经发生。换言之,在纯正不作为犯中,其着手开始于作为义务形成之时。
对于上述认识,笔者并不予以认同。其一,“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不以法律规定的特定结果的发生为条件”,这一命题本身是存在疑问的。比如,“逃税罪”在刑法理论上被认为是纯正不作为犯,但不能说该罪的成立就不要求出现“国家税款流失”的特定结果。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是逃税罪成立的要素之一。我们怎能说,“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不以法律规定的特定结果的发生为条件”呢?其二,即便“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不以法律规定的特定结果的发生为条件”这一命题是成立的,也不意味着其着手就开始于作为义务形成之时。这是因为行为人“作为义务形成之时”并非其真正不履行或者说已到该履行的时候而表示不履行之时。
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问题上,德国刑法理论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着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应在于不作为得以实现构成要件之最初时刻,即因不作为而使得第一个救助可能性丧失时为着手。(22)林亚刚:《刑法学教义》(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0页。有学者则主张,在已经实现构成要件的最后时刻,即使得最后一个救助可能性丧失时为着手。(23)林亚刚:《刑法学教义》(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0页。还有学者主张,在不作为破坏保证人义务之时为着手。(24)林亚刚:《刑法学教义》(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0页。而在日本较多的学者主张,应当从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性上去考虑着手:“不作为犯并不具有像作为犯那样自然的、物理的实行行为,但是可以说,开始实施包含了实现构成要件现实危险的、作为行为人人格的主体现实化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身体态度的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时,就是实行的着手。”(25)[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1986年版,第157页。
我国刑法理论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问题关注较少。张明楷教授认为,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导致法益发生了紧迫危险(危险结果)时,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26)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林亚刚教授赞同该观点,并作了进一步分析:“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履行作为义务时,并不意味着特定的危害结果必然同时发生,如果不作为行为对于法益不具有现实的危险性,这种情形下,仅仅从不履行义务的形式上考察,很难说其不作为行为就属于必须由刑法予以评价的犯罪行为。例如,即便母亲企图将婴儿饿死,但首次不给婴儿喂奶,不宜认为是杀人的着手。不应仅考察不履行特定作为义务的形式,更应当从实质上考察其不履行特定义务是否对法益构成现实的危险。”(27)林亚刚:《刑法学教义》(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页。
在笔者看来,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着手的考察还应当遵循认定犯罪着手的一般原理,即根据当时的情形,行为人如果不实施某种积极的行为,就会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时,就可认定为犯罪的着手,无须强调犯罪着手行为必须是“对法益构成现实的危险”的行为。其道理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需要强调的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不作为,其实是防止特定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这与作为犯中的作为是制造危害结果,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认定不作为的着手时,必须结合具体案件,具体考察案件中是否存在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事实。只有当不履行义务将会导致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受到威胁时,方可认定为犯罪着手,换言之,只有当上述意义的“事实”存在时,不作为才是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才是作为义务的形成之时。根据这样理解,企图将婴儿饿死的母亲,即便首次不给婴儿喂奶,也有可能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的着手。能否认定为杀人的着手,取决于婴儿当时的饥饿程度、身体状况。如果婴儿当时处于极端饥饿状态、身体状况“岌岌可危”,首次不给婴儿喂奶的行为即可成立犯罪的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