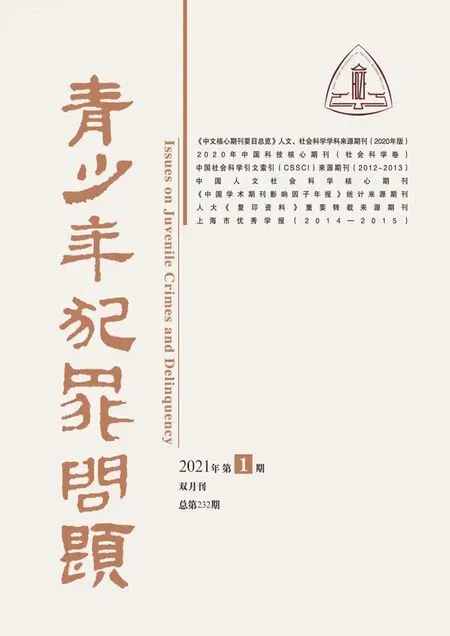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彭文华 傅 亮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及其修改、完善,具体历经了从1979年《刑法》(以下简称“79刑法”)、1997年修订的《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演变过程。“79刑法”第14条首次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划分。第一,不满14周岁的人对任何犯罪均不负刑事责任;第二,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承担刑事责任;第三,因不足16周岁而不处罚的情况下,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时,政府可对其采取收容教养;第四,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97刑法”第17条在“79刑法”的基础上,对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的人追责进行了具体化,即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这八种罪名承担刑事责任。相比“79刑法”的规定,“97刑法” 的规定更加明确、具体,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近年来,类似大连13岁男孩杀人案、湖南12岁男孩弑母案等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案件不时爆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引发社会关注。不少人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显得有些过时,有必要重新审视“97刑法”关于14周岁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合理性。当然,反对者也大有人在,认为不满14周岁的人犯罪早就有之,不应轻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为了回应社会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关注,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修改,总体上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其中,二审稿在“97刑法”的基础上对不满14周岁绝对免责的条款进行了个别下调,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在二审稿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对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质疑应当说是较为强烈的。基于对这种质疑的回应,最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二审稿的基础上,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进行了补充,即只有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鉴于此次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备受关注,本文拟对该问题加以针对性研究,以深化人们对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解和认识。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草案二审稿突然加入了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引发学界广泛争议。总体而言,学界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降低论,即认为可以降低现有刑事责任年龄,从而对犯罪低龄化的现实做出回应;二是维持论,即维持“97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未成年人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三是弹性论,即适应具体情形需要,设定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区间,有区分地对实施特定犯罪的未成年人施加刑罚。
降低论的理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犯罪低龄化现状愈演愈烈,需要给予回应。持降低观点的学者认为,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1995年至2004年)显示,每年15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占全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比例均为40%以上,必须尽快动用刑法对此类未成年人行为进行规制。(1)杨统旭:《现行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困境及出路》,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6期。其次,与1979年相比,中国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无论是经济上,抑或是教育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青少年相比四十余年前同龄人而言,其生理发育、认知能力和辨认能力都大有提升,现如今有些12岁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辨认能力,甚至比过去14岁未成年人还强,将刑事责任年龄定为14岁不合时宜,有必要降低。(2)张建军:《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之检视》,载《政法学刊》2007年第4期。最后,报应主义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基础之一,在给予行为人惩罚作为报应,也要考虑被害人的感受,一味地保护未成年人而忽视被害人的感受是不合适的。刑法需要兼顾行为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利益,侧重保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利益是不公平的,所以必须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保护被害一方的利益。(3)张寒玉、王英:《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1期。
维持论的理由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基于家庭、社会责任之立场。维持论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急速变革的社会转型期,本就处于心理躁动期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心理和行为的不适应,出现了社会结构稳定时期的青少年很少产生的心理问题,如青少年犯罪、问题行为以及心理疾病加剧等。这一类型的犯罪是不能完全归因于刑法的不力的,更重要的是陪伴未成年成长的父母以及社会的责任。于家庭和社会而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推卸责任之嫌。(4)林清红:《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不宜降低》,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1期。第二,基于伦理学的立场。维持论者认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有违中国“恤幼”的历史传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刑法的宽容性、人道性,也不符合对未成年人保护、教育的目的,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如果对青年人都不妥善保护,天下秩序是要乱的,所以必须对青少年予以充分保护。(5)曾粤兴、倪传洲:《伦理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刍议》,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三,基于刑法谦抑性的需要。维持论者认为,刑法应该恪守其谦抑性,对未成年人应重在落实与完善相应的惩戒教育措施,而不是动辄施加刑罚处罚。就目前的社会状况来看,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元化的,单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针对根本原因进行针对性回应,无法达到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而且,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犯罪低龄化并未越来越严重。相反,自2008年以后,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从2008年的88891名降至2017年的32778名,呈明显下降趋势。第四,标签论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从标签理论来看,对未成年人动用刑罚意味着给其提前贴上了不良标签,且未成年人在监狱中容易产生交叉感染,不容易进行教育改造,等等。这都无助于未成年人的矫正和回归社会。
弹性论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年龄的界限不能成为属于意识范畴的认识辨别能力的绝对界限,人的认识辨别能力属于意识的范畴,它不可能像黑白两种颜色那样有绝对界限可以分得一清二楚,以14周岁为界限,满14周岁有认识辨别能力,不满14周岁则无认识辨别能力,这显然是不成立的。(6)陈艳:《刑事责任年龄弹性规定之我见》,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第2期。第二,刚性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先天的制度缺陷。有学者指出:“一旦立法者没有及时地、准确地把握事实年龄,那么这种偏差就很可能会产生制度上的风险:或者因为拟制年龄较之事实年龄过高而导致放纵未成年人犯罪,或者由于拟制年龄较之事实年龄过低而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7)参见张拓:《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弹性化之提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2期。第三,现行刑事责任年龄的硬性规定不利于预防犯罪的目的实现。“我国对少年违法犯罪一向坚持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在司法实践中,政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少年,可判可不判的尽量不判,可以判轻刑的尽量判轻刑,能缓刑的尽量缓刑,能在监外执行的尽量监外执行。这诚然充分贯彻了党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未免‘心太软’。”(8)参见谭志君:《悬崖勒马缰何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1999年第4期。刚性的刑事责任年龄使刑法的震慑作用被大幅削弱,如大连13岁男孩等将犯罪视为小事就是例证,而弹性刑事责任年龄能有效弥补其缺陷。
不难看出,降低论立足于青少年的发育提前的现实情况和保护被害人的立场,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势在必行。而维持论则更加倡导对待未成年人应该以教育为主,无需过早动用刑罚,认为应该维持现状。此两种观点都属于刚性立法模式,要么绝对的下降,要么绝对的维持,而忽略了个体在意志上的差别。比较而言,弹性论属于折中的观点,其所认为的对刑事责任年龄秉持弹性的理念,试图力避降低论与维持论之不足,从中寻求相对适中的解决方案。那么,究竟何种观点相对科学、合理呢?这有必要从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和划分根据上寻求理论依据。
三、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及其划分依据
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从其主观恶性,还是从其客观社会危害性来看,有时并不亚于成年人犯罪。那么,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前,为何刑法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绝对免责?为何可以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相对免责?又为何可以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减轻责任?这关系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及其划分依据问题。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
早期的人类社会并无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人与动物都需要接受法律的审判与惩罚,而后期伴随着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才衍生出了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规定,并对其进行了划分,其本质是启蒙思想家反对罪刑擅断、提倡罪刑法定的结果,因为罪刑法定要求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确定化、具体化,而不能根据所谓的刑事责任能力加以模糊推断。
1.早期刑法惩罚的目的:消除罪恶,维护正义与教化。纵观人类的惩罚史,早期的制裁对象并不限于人类,其他生物甚至无生命的物体也会受到严厉处置。“在远古时代,无生命的物体可以受到法律的惩罚……”(9)Harry Hibschman, “When Animals Were Criminals”, Legal Chatter, vol. 2, no. 4,November 1938,p.39.例如,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会在公共会堂会举行一些独特的谋杀审判,如果凶手不为人所知或找不到,也要接受审判。同时,“因攻击人而致其死亡的无生命的东西,如石头、梁、铁片,等等,也要在普里坦库尼受审。最后是动物,它们同样是死亡的诉讼事由。”(10)Walter Woodburn Hyde,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of Animals and Lifeless Thing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64 U. Pa. L. Rev. 696, 730 (1915-1916),p.696.后来,人类意识到惩罚岩石、洪水等无生命物体无任何意义,有时也不现实,因而很快将责任和罪刑归咎于生物。由于动物与人类之密切关系,危害人类之举时有发生,往往成为刑罚制裁的对象。例如,在法国,“1314年,一头公牛袭击并杀死了穆瓦西附近的一名男子。这头野兽被判绞死在公共绞刑架上,该判决得到了巴黎议会的批准。1389年在第戎一匹马因犯杀人罪被判处死刑,1694年一匹母马以犯罪被烧死。”(11)Harry Hibschman, “When Animals Were Criminals”, Legal Chatter, vol. 2, no. 4,November 1938,p.39.
如果说惩罚无生命物体与蒙昧时期人类的认知水平直接相关的话,那么惩罚动物则与人类的认知水平似乎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因为,人类惩罚动物的历史源远流长,一度非常盛行。“在正规的法院出现之前,它们被交付给受伤的人或他的亲属进行惩罚。后来它们被带到法庭——家养动物被带到世俗法庭,野生动物被带到教会法庭。在那里,它们被正式传讯,由律师代表出庭、审判、无罪释放或定罪——如果罪名成立,它们将受到惩罚。这些并不是独特的诉讼。这种现象在整个欧洲甚至美国都很常见。”(12)Harry Hibschman,“When Animals Were Criminals”,Legal Chatter, vol. 2, no. 4,November 1938,p.39.时至今日惩罚动物“罪犯”尽管极为鲜见,但并没有绝迹。“虽然今天对动物罪犯的审判和处决很少像过去那样是正式场合,但是起诉和惩罚动物犯罪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1世纪。”(13)Jen Girgen,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of Animals,9 Animal L.97,134 (2003), p.131.
人类惩罚动物有其深刻的宗教渊源和基础。“古代法学的刑法性质,坚持惩罚的机械性、严厉性,几乎没有明确指向和无意识的性质,坚持惩罚有自己的宗教基础……责任、复仇,事实上所有的法律反应都是建立在群体的心理而不是个人心理的基础之上。”(14)[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人类在早期对于什么是犯罪、如何处罚犯罪,具有鲜明的情绪与情感色彩,往往伴有偶然性与随机性。“对犯罪据以惩罚的原则非常含混,执行刑罚的方式也是不确定的,更多的是为偶然性和个人情绪而非明确性的制度机制所掌控。”(15)[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而宗教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是建立在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之虔诚信奉的基础上的,排除异己、魔幻化未受洗礼的人和物是宗教之本能反应。因此,除人之外,动物特别是那些对人类及其利益具有攻击性的动物,也会毫无例外地受到宗教法的严厉惩罚。这是因为,在宗教信徒看来,“所有的动物都是魔鬼的化身,所有的异教徒和未受洗的人都是魔鬼的化身”。(16)Evans, E. P. (Edward Payson),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 of Animals,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06, p.vi.
惩罚动物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消除罪恶,以实现纯粹的形式正义。例如,1494年,在意大利一头猪因在教堂所属的土地上谋杀而被定罪,裁判理由是,“因为嫌恶和恐惧犯罪,最终以儆效尤及维护正义,我们裁定、判决、宣告并行使财产处置权,现被作为囚犯拘留在赛义德修道院当事猪,应当成为绞刑架的主人被绞死或勒死。”(17)Harry Hibschman,“When Animals Were Criminals”,Legal Chatter, vol.2, no.4,November 1938,p.40.当然,惩罚动物类似于动物训练,也是具有一定的实定效果的。“在某些方面,实验室模型类似于动物训练——因为动物通常被用于实验对象——以及类似于儿童教养——这两种情况都使用了常见的惩罚刺激类型。”(18)Barry F.Singer,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unishment, 1 Crime L.&Just.Ann.142,183 (1972),p.149.
2.刑事责任年龄是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确立的当然结果。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崛起,探究犯罪与刑罚背后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使命。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动物犯罪及其惩罚的合理性及其意义。尽管惩罚动物能消除恶患并实现纯粹形式正义,但除此之外难遂他愿,因为动物行为乃纯粹本能反应。“如果我不小心踩到我的狗,即使它平时很友好,它可能会咬我。我认为,这是一种本能行为,几乎是性格的反射。”(19)A. Warren Stearns,Evolution of Punishment, 27 Am.Inst.Crim. L.&Criminology 219,230 (1936), p.219.行为之本能决定了动物缺乏自由意志。“马没有自由意志,它们的自然法不过是自身本质性倾向的集合体和宇宙法则的一部分。”(20)[法]雅克·马里旦:《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鞠成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因此,靠本能驱动的动物感知与认知不可能有着严密论证和推理,只能是中性而非理性的。“动物的这种推断不可能建立在任何论证或推理的过程上,它不能根据那样的论证或推理过程得出结论说,相似的事件必定跟随相似的对象,自然的过程在运行时将永远是规则的。”这使得在以往的多个世纪里,那些对动物使用司法程序的人,常被指责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即他们接受对动物和人类拥有恶魔般所有权的教条、相信并执行对蛮兽的报应惩罚以及赋予动物以意识和道德责任。(21)See Harry Hibschman,“When Animals Were Criminals”,Legal Chatter, vol. 2,no. 4,November 1938,p.43.
不难看出,缺乏自由意志与行为之本能与非理性,是决定动物不被认为具有犯罪主体资格的根本原因。尽管动物亦有其行动准则,但局限于生存、繁衍等本能反应之内。对于缺乏自由意志且非理性的动物本能行为,通过囚禁、杀死动物等制裁措施惩罚动物“罪犯”,除了在形式上能防止其继续实施危害行为外,对犯罪动物本身以及其他动物并不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因而其作用和意义极为有限。在惩罚效果上,惩罚动物“罪犯”与惩罚无生命物体更为相似。因此,赋予动物以犯罪主体资格不具有实质意义。
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人具有自由意志与理性。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认识并遵守道德伦理规范,是人构成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并遵守道德伦理规范,是由人的理性决定的。“就吾人全体状态以考虑可欲求者为何(即关于考虑何者为善为有益)之等等考虑,则根据理性。”(2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66页。理性驱使人类不会像动物那样基于本能而为,而是必须权衡利弊得失。(23)[英]休谟:《论道德原理;论人类理智》,周晓亮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232页。以理性为基础,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人类的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符合人的本性与目的要求。“由于人性的特殊性,存在着一种人类理性可以发现的秩序或安排;人的意志必须按照这些要求行动,以使自己与人的本质性或必然性目的相符合。”(24)[法]雅克·马里旦:《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鞠成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犯罪属于非理性表现,如果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实施犯罪,就为处罚提供了根据。
自由意志与理性,是人类获得犯罪主体资格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能构成犯罪并接受刑罚制裁的根本保证。动物由于不具有自由意志,其行为具有本能与非理性特征,因而不具备获得犯罪主体资格的基本条件。动物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意味着只有人类才能构成犯罪,刑法人类中心主义遂得以确立。由此可见,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是先验而非经验的,是唯心而非唯物的。由于人的认知能力与年龄直接攸关,故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奠定了刑事责任年龄在刑法中的地位,是刑法人类中心主义赋予刑事责任年龄在犯罪认定中的支配地位。从这一点来看,刑事责任年龄也应该是先验而非经验的,是唯心而非唯物的。
(二)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理论依据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理论上只是概括区分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限制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减轻刑事责任年龄等,至于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划分,其理论依据是什么,通常并未诠释。我们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依据主要有二:一是自由意志论;二是法律拟制论。
1.自由意志论。根据刑法古典学派的自由意志论,任何人都有为善避恶的自由意志,犯罪是恶,有自由意志的人能避之而实施之,就应承担刑事责任,即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的存在不需要原因,人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依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做出行为,古典主义学派的道义责任论便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根据该学说,人只要达到一定年龄后,除精神不健全者外,都具有根据自己的意思行动的自由。(25)彭文华:《自由意志、道德代理与智能代理——兼论人工智能犯罪主体资格之生成》,载《法学》2019年第10期。因此,未成年人不需要承担或者减轻其刑事责任的原因,在于其还未产生成熟的自由意志。虽然一些决定论学者试图通过科学实验从自然科学角度彻底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但至今他们仍无法做到这一点。决定论至少无法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具有危险性格的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即使具有相当大危险的动物,且已经将其危险性格征表出来了,为何仍然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二是为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以后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在我国,将自由意志作为刑事责任制度的基础,一直以来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般说来,一个正常人生理上的成熟达到一定时期时,自己的大脑对自己的行为和外界事物就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支配自已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自己的行为代表了自己的意志,并且是受自己的意志所支配的。”(26)史言:《刑事责任年龄》,载《法学》1957年第1期。根据学界一般观点,关于年龄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其自身清晰的脉络。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第一原因是年龄,只有达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不同的年龄能够征表其自由意志的不同程度,最终产生足以承担刑事责任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人达到一定年龄后,会产生成熟的自由意志以支配其行为,从而为其承担刑事责任奠定基础。动物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在于其无自由意志,而只有一般的动物本能。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之所以不承担刑事责任,原因在于其未达年龄前,不足以产生成熟的自由意志支配其行为。
既然承担刑事责任与自由意志密切相关,那么自由意志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刑事责任划分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不同年龄会孕育不同的自由意志,进而产生不同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一定的年龄阶段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自由意志,并征表出与该年龄阶段相适应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从而成为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因此,自由意志就成为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理论依据。
2.法律拟制论。法律拟制是指立法者基于某种价值目的考虑,不论事实上的真实性,有意用现有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去解释和适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将不同事物等同对待并赋予其相同法律效果,从而达到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能体现法律基本价值之目的的立法技术或立法活动。(27)刘宪权、李振林:《论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英国学者亨利·萨姆奈·梅因指出,法律拟制的年代早已过去,我们现在已经不必要再去用法律拟制这种粗糙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公认的有益的目的了。(28)参见[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沈景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不过,这只是针对封建罪刑擅断时代随意的法律拟制而言的,事实上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学部门,不会彻底摈弃也不可能完全摈弃法律拟制。这是因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律,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做到结构化、类型化,乃至于任何概念都泾渭分明。同时,法律评价离不开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主要体现为主体的认识和评价,这是难以做到界限历然、泾渭分明的。
刑法属于实践性很强的法律部门。为了适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充分体现刑法的公平、公正,刑法更需要将某些不同事物等同对待并赋予其相同的法律效果,以迎合社会需要,实现立法目的。因此,刑法从来不乏法律拟制的例子。例如,行为人为了实施抢劫而携带了凶器,但到了现场后,发现根本用不上凶器甚至不需使用暴力,所以只实施了抢夺的行为。曾经,人们对此类行为如何定罪存在颇多争议,之后刑法通过立法将携带却没有使用凶器的抢夺行为一律拟制为抢劫罪。另外,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也设置了诸多法律拟制条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该规定将本该由故意犯罪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形,拟制为共同犯罪也可以由交通肇事罪这类过失犯罪构成。
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亦离不开法律拟制。如前所述,虽然自由意志为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奠定基础,但并未解决如何划分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由于刑事责任年龄关系到不同年龄的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如何承担刑事责任问题,因而需要一个相对具体的标准来明确不同年龄承担不同刑事责任的界限,这显然离不开法律拟制。具体地说,为什么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只对八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就不是完全由自由意志的差别决定的,实质上是刑法拟制的结果。其目的在于明确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具体犯罪类型,在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也为司法提供具体、明确的可操作性标准和依据,有利于司法的协调、一致与刑法适用的公平、公正。
四、刑事责任年龄弹性论之提倡
(一)刚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之弊端
1.不利于保护被害人权利。根据被害人保护理论,刑事责任与被害人权利保护之间联系的核心,在于对被害人参与责任的衡量,即被害人的参与达到何种程度才值得刑法降低或者失去值得保护性和需要保护性。(29)[德]托马斯·希伦坎普:《被害人教义学今何在?——对于作为立法、解释、归责和量刑原则之“被害人学准则”的一个小结》,陈璇译,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我国司法解释对被害人参与准则就曾有过规定。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才有可能构成犯罪。这表明被害人若自陷风险或者事先违法,行为人可能因此得到刑事免责或者量刑减免。而在近些年来曝光的未成年人案件中,尤其在最近媒体颇为关注的大连13岁男孩杀人案中,10岁小女孩作为被害人,其在犯罪过程中的参与责任几乎为0,但刑法却因为男孩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免予其刑事处罚,只裁定了3年的收容教养。最为可怕之处在于,男孩被警察找上门的时候,清晰地认识到其为小孩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客观地说,13岁的未成年人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难道10岁小孩作为被害人就不需要刑法的保护吗?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便表明了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立场,(30)参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零容忍——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就四名强奸、杀害未成年人的罪犯被执行死刑一事答记者问》,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 2018/11/id/3589463.shtml,2020年12月11日访问。该文提到了对未成年犯罪零容忍。这当然不限于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需要反思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某些规定,其中自然包括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2.难以因地制宜适应现实需要。自“79刑法”制定以来,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直规定为14周岁。简而言之,立法机关基于年龄和刑事责任呈现的比例关系,根据某一年龄段能够体现大多数人是否具有一定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而硬性规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在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法律拟制为14周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忽略个体不一情况的,这也是维护刑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一致性的代价,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刚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只注重具体运用而设置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却没有为拟制年龄与事实年龄之间的偏差留有充分的余地。在情势变迁之后,如果立法不能及时跟进现实需要,将导致忽略个体不宜情况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如未满14周岁的人明知故犯等),那么这种偏差就很可能会产生制度上的风险。要么因为法律拟制年龄过低而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害者的合法利益,要么因为法律拟制年龄过高,而纵容未成年人的犯罪。在法律拟制年龄过高而纵容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一种现象时,刚性的刑事责任年龄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负担。
3.不能客观反映个体差异。传统刚性的刑事责任年龄理念是建立在“人是抽象的、理性的、自由的”古典主义立场上的。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只要是生活于世间的正常人,都有理性灵光照耀下自由选择、自由行动的能力,此犯罪人与彼犯罪人、犯罪人与社会一般人之间均具有相同的理性觉悟和主观意识。”(31)韩康、蔡栩:《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弹性立法模式之提倡——以法律推定准确性为标准展开的论证》,载《犯罪研究》2020年第5期。古典主义把犯罪人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人格忽略,其所主张的道义责任立场,目的在于反对封建刑法的不平等性、残酷性以及恣意性,从而粉碎封建贵族的司法特权。但其抽象化的拟制并未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样貌,忽略个体不一的情况,会造成司法不公。尽管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基础是自由意志,但决定论的一些观点也有借鉴意义。人的自由意志的成熟程度,其实与人所处的家庭环境、营养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息息相关。刚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忽略决定论的某些合理因素,难以客观反应个体的现实差异。
(二)刑事责任年龄弹性论之类型
关于承担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14周岁是否为必然?答案是否定的。各国都会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来拟制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大多为13、14周岁,但也有例外。例如,瑞士、新加坡为7岁,墨西哥、菲律宾为9岁,土耳其、荷兰为12岁,以色列、法国为13岁,日本、意大利、俄罗斯为14岁,丹麦、芬兰为15岁,西班牙、葡萄牙为16岁,波兰为17岁,卢森堡为18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建议各国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12岁以上,而未绝对明确具体到哪一岁。可见,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并非必然,主要是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而定。各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并非具有一致性,为弹性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奠定了基础。所谓刑事责任年龄弹性论,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责任年龄中设置最低年龄区间,在最低区间内采取无责推定的方式。
弹性论分为激进的弹性论和保守的弹性论。激进的弹性理论主要针对传统的英美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而言的。英国曾是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先行者,但英国议会在1998年已经废止了10-14岁的儿童可推翻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推定,表明英国目前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0岁,即1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同成年人一样承担刑事责任。在刑事责任年龄上,美国在20世纪之前一直采用普通法体系规则。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人们逐渐就国家应该承担起对青少年的保护责任而非一味地依靠刑法惩罚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少年司法改革在整个美国风靡起来,并引发了刑事责任年龄上的改革。截至目前,美国只有19个州设置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大多数州不再继续保留恶意补足年龄制度。(32)这里的美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州的统计数据源于Juvenile Justice Geography官网,http://www.jjgps. org/jurisdictional-boundaries, 2020年12月15日访问。其中只有7个州保留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分别是俄克拉荷马州(7-14岁)、华盛顿州(8-12岁)、内华达州(8-14岁) 、南达科他州(10-14岁)、加利福尼亚州(14岁以下)、阿肯色州(13以下,只适用于两类谋杀罪)以及马里兰州(无具体规定,但有判例规定)。此外,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马来西亚等,也都保留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33)俞元恺:《英美法系“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与借鉴可能——关于当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争议的回应》,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0年第1期。
保守的弹性理论是指在弹性区间内一般推定未成年人为无责任能力人,采取定性+定量的模式对部分行为进行规制。定性指的是部分社会危害极大且无需较高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暴力犯罪;定量指的是在满足定性的前提下,在量刑上足以对其定较高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34)张拓:《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弹性化之提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2期。我国学者金泽刚教授就曾指出应让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受那八大罪名的刑事规制。(35)金泽刚、张涛:《调整绝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新思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年第3期。保守的弹性理论亦为笔者所提倡。
(三)刑事责任年龄弹性论之优势
目前,降低论的支持者除了部分学者,还包括众多网民。他们从朴素的正义价值观出发,提出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他们看来,面对频频曝光的未成年人案件,刑法必须出击,不能让刑法成为未成年人渣的保护法。维持论者的主张者主要为学者,学者们主要从教育矫正的角度来阐述其观点。比较而言,弹性论秉持了折中的立场:一方面,认为刑法需要面对犯罪低龄化现实做出回应,对个别社会危害极大,认识能力无需过强的罪名和行为进行合理规制,以回应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基于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大多数行为不进行刻意的刑法规制。
1.有利于坚守刑罚之公平与正义。刑罚之正当依据为何?其价值理念又为何?对此,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旧派与新派在刑罚论领域中的绝对主义(报应刑论)与相对主义(目的刑论)之争,并不是关于刑罚目的本身的争论,而是关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争论。”(36)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04页。关于刑罚正当化依据,主要有报应刑论、目的刑论以及并合主义。其中,并合主义乃多数说。所谓并合主义,其实是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的折中说,其以相对报应刑为内容,认为刑罚的正当化依据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正义要求,同时为了实现防止犯罪,应当在报应刑的范围内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并合主义的经典表述为,“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根据并合主义,如果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动用刑罚来加以规制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如前所述,刑法关于14周岁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硬性规定,忽略了被害人的利益,以及未成年人本身行为之危害性的对向报应需要,可谓有利有弊。若采取保守的刑事责任年龄弹性论,一方面可以对部分实施了社会危害性极大且无需过高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未成年人加以刑罚规制,从而坚守刑罚之正义;另一方面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亦是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安抚和补偿,从而坚守刑罚之公平。
2.有利于贯彻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教育、感化、挽救”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我国从“79刑法”实施以来即确立的针对未成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和立法原则。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正式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笔者以为可以对该条规定的“教育”和“惩罚”做规范性理解,即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虽然说要强调教育刑,但在教育刑观念下并不必然导向无罪或者说不惩罚,应当对犯罪进行分类,遵循“轻轻重重”的原则,能够通过教育或者感化解决的,尽量不动用刑罚,但对某些极重的犯罪,刑罚则有动用的必要性。(37)陈伟:《教育刑与刑罚的教育功能》,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维持论对于刑事责任年龄一成不变的主张,过于强调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忽略了惩罚为辅的方针。降低论主张绝对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涉嫌过失犯罪和轻微犯罪进行惩罚时,极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弹性论则强调既维持又降低,可谓扬两者之所长而抑两者之所短。维持指大多数情况下继续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不惩罚社会危害性极大且需要较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犯罪;降低则指的是对部分社会危害性极大,且不需要较强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的犯罪进行辅助的惩罚。弹性论符合目前我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可以说有其现实基础和合理性。
3.有利于实现犯罪预防。刑罚之根本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现行刑法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对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为绝对的刑事豁免,虽有收容教养制度之规定,似乎不利于实现犯罪预防。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一般情况下只是责令其监护人多加管教,只有在必要之时,才会动用收容教养,且收容教养往往容易流于形式,即使不流于形式,收容教养最长不过4年,难以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不过,若认为设置最低年龄区间,拟定在最低年龄区间内的未成年人对刑法所有的罪名及危害性都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拥有和成年人一样的自由意志,从而理性支配其行为,亦是不现实的,如上文所述,年龄是决定自由意志的关键,虽不能证明在最低区间内的青少年对所有罪名能有清楚认知能力,但对于最基本的“杀人放火”等类似行为,至少12、13周岁的未成年人还是能对此做出一个最基本的是非判断的。因此,保守弹性论所提倡的在最低区间内对部分罪名承担刑事责任是合理的。通过立法手段,在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中设置弹性年龄区间,可以使刑法对未成年人产生威慑性,让其不敢知法犯法,这无疑有利于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
五、《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及其适用
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颁布,其第1条规定除了对草案二审稿的相关规定进行适当修改外,还将原来的收容教养改成了专门矫治教育,从而与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由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设置严格的限制条件,如何适用需要进一步研讨。
(一)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特点
从《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来看,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1.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具有附属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下调至12周岁,并非具有绝对性,而是具有相对性与附属性。换句话说,未成年人若在12周岁到14周岁之间,一般情况下仍然推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才能对其进行刑事责任追究。这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论所提倡的彻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显然不是同一立场。
2.仅限于特定类犯罪之特殊情节。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才可能追究刑事责任。此规定是在二审稿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规定。这意味着,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虽未致人死亡,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也可能追究刑事责任。
3.严格的程序性限制。尽管此次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修改扩大了对未成年人的处罚范围,但也增加了严格的程序性限制条件。即只有满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一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追究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结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亦有可能认为其不满足情节恶劣这一条件,而不予批准追诉。此条款亦是把最后的裁量权交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表明了立法机关极为谨慎的态度,秉持对未成年人以教育和保护为主,不轻易动用刑罚的立场。
4.强调矫正教育的作用。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款规定,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所犯非法定的罪刑而不予刑罚处罚的,由过去的收容教养改为了专门矫治教育。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称,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此次修改必须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38)参见《未成年人犯罪不能一放了之》,https://www.sohu.com/a/424481699_119861,2020年12月26日访问。该文一文提到了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众所周知,以往收容教养制度在性质、期限、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决定程序、执行机关等方面,缺乏相对明确、具体的规定,影响了相关工作正常开展。尤为欠妥的是,收容教养制度更突出“收容”职能,即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在实践中,往往成为刑罚“够不着”时的替代手段。某种程度上,其严厉性并不逊色于管制、拘役等刑罚,与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精神不无违背。(39)佟丽华:《共同推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完善》,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8月27日。《刑法修正案(十一)》强调“专门矫治教育”,侧重的是“矫治教育”而非收容,其进步之处不言而喻。
(二)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评价
立法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尽管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如何降低,则是个技巧性很强的问题。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来看,应当说最大程度地遏制了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之弊,未来应当会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1.刑事责任年龄个别降低是博弈的结果。对于刑法立法,如有学者指出,立法过程不再只是单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利益分配形式,而是多种利益、多元主体的言说空间,此为政策博弈向立法博弈的转型。(40)许章润:《从政策博弈到立法博弈——关于当代中国立法民主化进程的省察》,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此次有关刑事责任年龄个别降低的规定,是立法机关、学界和第三方力量(主要为普通民众和非法学人士)博弈的结果。“79刑法”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14岁,有其现实需要,也是历史必然。但是,面对近年来频发的、类似大连13岁少年杀人案、湖南12岁少年杀母案等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特别是犯罪人事后明知故犯的态度,激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对那些施暴者要有相应的制裁,有必要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少年施暴者进行刑法惩处,成为不少人的共识。(41)党小学:《遏制校园暴力,刑事责任年龄该不该降》,载《检察日报》2016年3月10日。甚至有人将不分青红皂白地保护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称为人渣保护法,这虽然有言过其实之嫌,却也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诉求。而在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不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在自媒体异常发达的今天,即便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恶性犯罪属于少数,但由其轻易传播引发的巨大影响,无疑将该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影响变相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立法适当回应民意,果断遏止自媒体时代的少年恶性犯罪,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当然,刑事责任年龄也不能按照某些人的想法那样,彻底、绝对性地降低,采取折中做法个别性降低,并通过核准追诉这一程序限制,将决定权掌握在最高司法机关手中,不失为妥协之策。
2.彰显了刑法的谦抑性,象征意义更大。刑法的制裁措施最为严厉,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地位,其他法律有赖于刑法保障,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制违法行为时,才有必要适用刑法,这就决定了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42)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有关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一方面在罪名上进行了限制,即限于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另一方面,追诉的前提条件是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准。这表明,立法者认为虽未满14周岁,但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至少应当允许存在的,只不过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的程序性限制也表明,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进行个别刑事追究,是一个必须保持谦抑、慎之又慎的问题。另外,抛开互联网的曝光案件,理性看待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事实上是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未成年犯罪案件从2008年的88891人降到了2017年的32778人。人们之所以认为未成年犯罪越发严重,只是因为互联网扮演了一个放大器的作用,真正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来并不会很多。总之,此次刑法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修订,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3.与其他未成人年法规相衔接,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一)》有在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出规定时,充分考虑了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的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加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比如细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和进一步筑牢互联网安全“防火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仅强调教育,还强调了提前干预,要求对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及时进行分级预防和矫治。《刑法修正案(十一)》辅助性地制裁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罪,凸显的是以教育为主而对大多数未成年人不动用刑法规制的宗旨。只有在必要时才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行专门矫治教育,体现的是与过去的收容教养“一关了之”的做法决裂的态度。以惩罚为辅,意味着也不再像以往一样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一放了之”,而是对特殊案件保持惩罚的可能性,旨在警示那些有犯罪动机的未满14周岁的人,不得越雷池一步。
(三)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一是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二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三是情节恶劣;四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四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认定。本次规定中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行为人所触犯的具体罪名还是具体行为?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不同的认定结论。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绑架过程中杀害被害人的,应当构成绑架罪而非故意杀人罪。那么,如果12周岁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害人,是按照其行为来定罪还是按照绑架罪不处罚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02年作出的《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规定:“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作出的《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相对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基于此,我们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也应当扩大解释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行为,而不是指具体的罪名。这意味着,凡是在犯罪过程中包含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尽管根据刑法规定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之外的其他罪名,也可以由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构成。常见的有:放火、爆炸、决水、投放投毒物质等过程中有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的;强奸过程中有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的;抢劫过程中有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的,等等。
2.“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认定。关于“特别残忍手段”,刑法在其他规定中有体现。从审判实践来看,主要根据使用的凶器、打击的部位、使用的方法等来判断手段是否残忍。常见的特别残忍手段包括:将被害人伤害后又故意砍下被害人手脚或者伤害脚筋的;挖人眼睛致人眼睛失明的;割人耳鼻或刻骸骨的;撕扯人的头皮的;挖割人的内脏的;以火烤、冷冻等极其残忍方法实施伤害或杀害行为的,等等。在理解“特别残忍手段”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不能以出现的后果是否特别严重来反判断手段是否残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后果严重,并不意味着伤害手段特别残忍。例如,死亡是最严重的后果,但致死的手段并非就是特别残忍的,适用安眠药杀人就不应认定为特别残忍。如果根据后果判断手段是否特别残忍,会导致“手段特别残忍”被架空,有违立法本意。二是不能将常规的手段认定为“特别残忍手段”。在司法实践中,持刀杀人、持枪杀人、将人打死等,均属于常规的犯罪手段,而非特别残忍的手段。否则,容易导致以后果判断替代手段判断,有所不妥。总之,判断犯罪手段是否特别残忍,侧重的不是对法益侵害程度和后果的判断,而是着眼于对一种善良风尚和伦理道德的违反。手段残忍不必然造成更大的危害后果,但是却足以反映出与一般的杀人手段相比,该手段本身的反伦理、反道德性更加严重。(4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 2004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以下。何谓严重残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严重残疾”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被害人身体器官大部缺损、器官明显畸形、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造成严重并发症等。一般来说,残疾分为三类:一是一般残疾(十至七级);二是严重残疾(六至三级);三是特别严重残疾(二至一级)。由此可见,残疾鉴定六级以上的,可视为“严重残疾”。需要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所规定的“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是与“致人死亡”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的另一种危害后果。这意味着,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即使没有致人死亡,但只要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就存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同样,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存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3.“情节恶劣”的认定。《刑法修正案(十一)》所规定的“情节恶劣”,到底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同位语?还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行为,并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就属于“情节恶劣”?我们认为,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场,适用条件理应更加严格才是合理的。据此,“情节恶劣”应当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之外的限制性条件。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二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且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关于“情节恶劣”的具体表现形式,应该遵守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既要考虑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又要考虑行为手段、行为对象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需要加以综合考虑。在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并不难判断。例如,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致使两人以上死亡的,多次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且存在致人死亡情形的,等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且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一般是指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两人以上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具有两种以上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多次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且存在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等等。
4.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问题。即使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也要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特别的程序性限制,与其他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明显不同,体现了立法机关对追究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的刑事责任的慎重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核准追诉时,无疑要审查是否符合追究刑事责任的实质要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是否是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是否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否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是否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形。至于审查的形式也绝不能仅仅限于书面审查,必要时应讯问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及其监护人的辩解意见,充分考量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最终决定是否核准。追究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的刑事责任之核准追诉,与超过20年的追诉时效的核准追诉有所不同。《刑法》第87条所规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情形,是针对已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其本质在于已过追诉时效本应导致刑事责任消灭,但因为存在特殊情形需要继续追诉。其追诉条件是“认为必须追诉”,相对来说较为笼统、概括。而对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是针对特殊情形下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而言的,与追诉时效无关。其追诉条件是刑法明确规定的,相对来说较为客观、具体实际。
结 语
此次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出台争议颇多,反对者大有人在。客观地说,此次修改之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纵观刑法之限定性规定,诸如酌定减轻处罚、超过20年追诉时效而需要核准追诉的,等等。尽管也有严格的限制适用条件,但像对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这样设置如此多的限制条件,还是绝无仅有的。由于限制条件多,且具体要求十分苛刻,可以预见全国每年惩治的该类犯罪案件数量并不很多,甚至可以说是个别的。仅此而言,立法机关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立法机关需要回应社会以及民意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关切,另一方面又要体现不得擅自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则意识与法治态度,因而不得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慎之又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不再“一放了之”的态度,又彰显了国家坚持对待未成年人应该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而非“一关了之”。本文所主张的刑事责任年龄弹性论,既提倡在大多数情况对未成年人应以教育和保护为主,让其有自我修正的机会,又提倡在某些特殊情况,对未成年人进行必要惩戒,威慑其他有犯罪动机的未成年人,以便更好地衡平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刑罚效果的最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