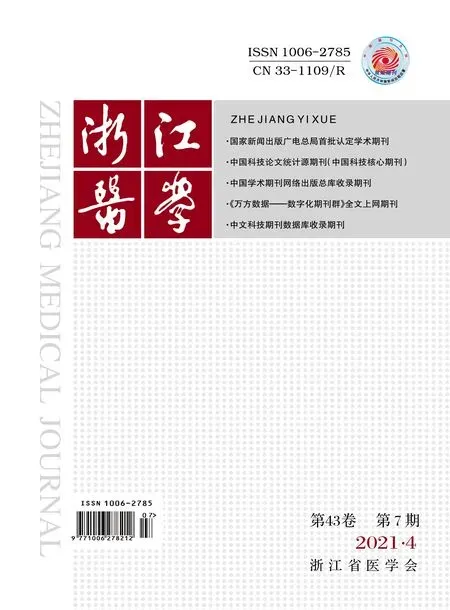冠心病非传统危险因素治疗干预措施的研究进展
朱立军 黄进宇
自他汀类药物问世以来,冠心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通过强化血脂管理可使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风险降低25%~35%[1]。然而,采用现行标准防治措施使LDL-C达标,血糖和血压得到控制,心血管病的发病和事件风险依然存在。一些用于预测心血管残余风险的非传统危险因素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已知的冠心病非传统危险因素多达上百种,然而被证实有明确机制并通过临床干预可获益的却不多,针对这些非传统危险因素的治疗措施进展也较缓慢。本文就冠心病非传统危险因素干预治疗措施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yperhomocysteinemia,HHcy)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水平与冠心病的严重程度正相关,冠心病患者病变血管支数和血管狭窄程度随Hcy水平升高而增加[2]。HHcy增加患者MACE和全因死亡风险[3],在后他汀时代即使将LDL-C控制在低于1.8 mmol/L的理想水平,Hcy仍具有预测心脏死亡的能力[4]。Hcy降低一氧化氮(NO)生物利用度,引起内皮功能障碍;诱导平滑肌细胞原癌基因和信使RNA表达,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提高血小板凝血活性并抑制纤溶系统,增加血栓形成风险。独立于传统的危险因素,血清中Hcy水平每升高5 mmol/L,将使MACE风险增加20%左右[5]。
叶酸和B族维生素是治疗HHcy的常用药物,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叶酸和B族维生素治疗能降低冠心病风险[6]。Willems等[7]对计划行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的HHcy患者予以补充维生素B12和叶酸,6个月后冠状动脉内多普勒超声血流速度测定显示治疗组在输注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溶液后冠状动脉血流量(coronary blood flow,CBF)较基线水平增加96%,而接受安慰剂治疗的对照组CBF降低了16%。生理状态下ACh诱导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发挥扩血管作用,病理状态下则直接激动毒蕈碱受体收缩血管平滑肌。Hcy水平升高会损伤内皮功能,血管在Ach作用下表现为收缩,补充叶酸和B族维生素后内皮功能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增加。曹松臻等[8]报道心绞痛患者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维生素B6、B12和叶酸片后血浆Hcy水平明显降低,治疗组心绞痛发作频率、持续时间以及MACE发生率明显低于未接受维生素治疗的对照组。
Lee等[9]认为补充叶酸和B族维生素可能增加慢性肾功能不全人群的MACE发生率,但Towfighi等[10]对上述研究中无肾功能异常者进行亚组分析,发现大剂量B族维生素依然能降低老年人的卒中、心肌梗死和死亡风险。年龄、Hcy基线水平、肾功能等因素会改变降Hcy治疗对个体心血管风险的影响,肾功能不全是导致叶酸、B族维生素治疗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随着人口老龄化进展,肾功能不全的发生率日益增高;由于肾脏排泄功能减退,大约85%的肾功能不全患者会发生HHcy[11]。因此如何治疗冠心病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的HHcy,以降低心血管风险,是临床医生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2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
尿酸(uric acid,UA)与冠心病相关性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是目前普遍认可的非传统危险因素之一。荟萃分析显示HUA增加一般人群的冠心病发病和死亡风险,血清UA每升高59.5 umol/L,冠心病发生率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增加20%和9%[12]。Magnoni等[13]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患者进行冠状动脉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发现高UA组靶血管病变严重,斑块破裂更常见。UA水平可独立预测患者2年内心血管死亡的风险(HR=1.41,95%CI:1.26~1.57,P<0.001),超过国际参考值上限(357 μmol/L)者与更高的院内死亡率相关[13-14]。
循环中适宜浓度的UA可保护血管内皮免受氧化应激,并作为NO的载体发挥舒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当UA水平过高而渗入内皮细胞,细胞内UA会激活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诱导剧烈的氧化应激反应,阻碍L-精氨酸的吸收、增强其降解导致NO生物利用度降低、内皮功能障碍。细胞内UA还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核转录因子NF-κB及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p38,诱导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内皮素-1、IL-1及IL-6等炎症因子的释放,加重血管炎症反应,促进血管收缩[15]。
别嘌呤醇是治疗HUA的传统药物,近年来其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价值也备受关注。别嘌呤醇抑制黄嘌呤氧化酶介导的氧化应激,增加NO生成和利用,并能抑制嘌呤分解,增加三磷酸腺苷和氧的局部组织利用率,减少急性缺血事件及缺血再灌注损伤[16]。黄英等[17]对ACS患者常规抗缺血治疗基础上加用别嘌呤醇,2年随访期间别嘌呤醇组炎症因子水平和MACE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大剂量别嘌呤醇可改善缺血性心脏病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提高大动脉顺应性,降低左心室收缩末容积,逆转左心室肥厚,减少MACE和死亡率[18]。然而,大剂量别嘌呤醇的使用可能引起剥脱性皮炎等严重皮肤不良反应,尤其在亚洲人、黑种人和太平洋岛民等种族中,致死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更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别嘌呤醇的应用[19]。
苯溴马隆是治疗HUA的另一种常用药物,不同于别嘌呤醇抑制UA生成,它通过促进UA排泄发挥作用。给予痛风患者约定日剂量的苯溴马隆治疗能降低冠心病风险,且疗效并不明显劣于别嘌呤醇(苯溴马隆HR=0.79,95%CI:0.63~0.97,P<0.05;别嘌呤醇 HR=0.74,95%CI:0.58~0.94,P<0.05)[20]。苯溴马隆的药物不良反应较轻,患者用药依从性好,在降低冠心病残余风险方面或许有较好前景,但是目前关于苯溴马隆及其他降UA药物心血管获益的文献仍然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维生素D缺乏
维生素D是一种脂溶性的环戊烷多氢菲类化合物,除了参与调控钙磷代谢和骨骼生长发育,对心血管系统也有保护作用。研究发现维生素D水平随冠心病病情加剧而降低,一到三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血清维生素D明显低于无显著病变者,ACS患者维生素D亦低于稳定型心绞痛患者[21]。维生素D缺乏导致p65蛋白表达增加、SIRT1蛋白表达下降,增强NF-κB途径诱导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促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22]。维生素D还能作用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血管紧张素(1-7)/Mas受体轴,抑制血管紧张素Ⅱ生成,缺乏维生素D将导致血压升高,心肌负荷加重[23]。按欧洲高血压指南标准对成年高血压患者规范治疗后,维生素D缺乏的人群平均血压较正常人群要高2.4/3.5 mmHg[24]。
补充维生素D成本低、安全性高,甚至通过增强户外活动和光照即可实现,口服补充维生素D在临床中被广泛用于预防和治疗老年骨质疏松。如果补充维生素D能作为冠心病一级和二级预防的手段,将极具推广性和普适性。早期研究发现对维生素D缺乏的患者补充维生素D3能减少粥样斑块的形成面积和破裂风险,对预防和改善心肌缺血有利[25]。然而Legarth等[26]报道分析了14项关于补充维生素D与心血管获益的研究,发现虽然补充维生素D可有效提高血清25羟维生素D水平,但是对降低冠心病风险的证据却显然不足。其中10项研究中患者MACE和死亡风险没有降低,内皮功能及血脂水平也无明显改善,剩余4项规模较小的随机对照研究提示补充维生素D对冠心病有益。尽管总体上补充维生素D防治冠心病的结果不甚理想,但是横向比较各研究结果发现糖尿病亚组补充维生素D一定程度上能改善血管炎症反应。糖尿病人群普遍存在维生素D缺乏,动物实验显示补充维生素D可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胰岛功能障碍,抑制RAS系统过度激活,但临床中对2型糖尿病患者补充维生素D是否有益尚无一致意见,需要后续研究的验证。Wu等[27]使用活性较强的1,25-二羟维生素D3对患者进行干预,6个月后冠状动脉造影SYNTAX评分降低,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与肾素-血管紧张素活性也明显下降,摄入高活性的维生素D3而非普通维生素D可能是决定有无心血管获益的关键,有待进一步明确。
4 慢性炎症反应
上世纪末Ross教授提出冠心病是一种炎症性疾病,为冠心病发病机制的探索提供了全新方向。现代研究越来越证实慢性感染、自身免疫紊乱与冠心病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4.1 慢性感染 人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HCMV)感染与冠心病相关,这一联系在流行病学、血清学、分子生物学上均已得到证实。研究发现HCMV-IgM抗体滴度与hs-CRP水平正相关;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后可长期潜伏,在宿主免疫力低下时反复激活引起亚临床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不断加重动脉壁损伤。CMV感染后转录合成的某些蛋白干扰宿主正常的脂质代谢,引起TC和TG水平增高,并增强清道夫受体启动基因活性,促进平滑肌细胞对胆固醇酯的摄取和堆积。尽管目前尚无临床研究说明抗病毒治疗对人类冠心病的影响,但已有动物实验表明预防性使用阿昔洛韦可减少CMV感染所致的心脏移植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对已感染CMV的大鼠使用更昔洛韦治疗,可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血管炎症反应和粥样硬化病变进展[28]。
4.1.1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or pylori,Hp) Hp感染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成年人的患病率超过80%,发达国家中感染者比例也高达20%~50%。慢性Hp感染影响维生素B12和叶酸吸收,引起HHcy,并诱导促炎状态,刺激炎症因子、可溶性黏附分子和凝血因子释放[29-30]。既往对Hp感染是否与冠心病相关存在争议,Fang等[31]对44项符合条件的研究进行荟萃分析,明确了Hp染增加 ACS 风险(OR=2.03,95%CI:1.66~2.47,P<0.001)。王建伟等[32]发现早期根除Hp治疗可降低65岁以下消化性溃疡患者的冠心病发病率(2.58%比3.35%)和死亡率(2.86%比4.43%)。
4.1.2 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 HCV感染是冠心病的潜在危险因素,随机效应模型中冠心病患者感染HCV的RR值为1.25,固定效应模型中冠心病合并HCV感染的总体OR值为1.94[33]。使用直接抗病毒药物清除HCV可减少MACE,风险下降程度与 HCV清除率独立相关(OR=4.716,95%CI:1.832~12.138,P<0.01)[34]。
4.1.3 其他病原体 肺炎支原体、衣原体、牙龈卟啉单胞菌、单纯疱疹病毒等引起的慢性感染也与冠心病有关,这些病原体筛查简便,并有相应防治措施,然而由于病程长、症状不明显,极易被忽视。加强对慢性感染危害的认知,提高预防和治疗的积极性,有利于降低冠心病的潜在风险。
4.2 自身免疫性疾病 冠心病在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atic lupus erythematosis,SLE)等风湿性疾病人群中患病率高,发病年龄小,是引起死亡的重要原因。异常的免疫反应导致外周循环自身抗体滴度增高、局部免疫复合物沉积,持续激活全身炎症反应,加剧冠状动脉病变。瑞典学者Holmqvist等[35]在全国范围内对新发的RA患者进行长达17年的跟踪随访,发现RA患者的ACS发生率是普通人的1.41倍。而SLE对动脉粥样硬化影响更大,患者罹患冠心病的风险要比普通人高2倍以上(RR=3.39,95%CI:2.15~5.35,P<0.05)[36]。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冠心病患者预后差,MACE和再次血运重建率明显较普通冠心病患者高[37]。
对于合并冠心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在抗风湿治疗方案中需尽量减少皮质类固醇的使用以降低冠心病风险,而慢作用抗风湿药如甲氨蝶呤、氯喹等则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最近问世的几种生物制剂TNF抑制剂、IL-1受体拮抗剂、IL-1β单克隆抗体、CD20单克隆抗体等,除了具有明确的抗风湿效果,在降低这类人群的心血管风险方面也表现出非凡潜力[38]。近期的一项大规模前瞻性临床研究CANTOS研究发现对心肌梗死后hs-CRP较高的患者使用小剂量的IL-1β单克隆抗体卡那单抗(Canakinumab)可使炎症指标降低、MACE减少的同时不良反应较少,总体相对安全[39]。这个研究结果甚至提示不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群使用免疫抑制剂进行二级预防也能带来心血管获益,这为冠心病的抗炎治疗和消除残余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
5 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
血浆高Fib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存在和严重程度独立相关,是预测患者不良临床结局的重要指标[40]。作为一种急性期反应物,Fib在炎症状态时迅速增高。高水平的Fib及其代谢产物不仅参与局部血栓形成,还会增加血液黏稠度,损伤内皮细胞结构和功能,刺激平滑肌细胞增殖迁移、胶原合成和脂质堆积[41]。戒烟、控制体重等生活方式干预和贝特类药物可有效降低Fib水平,活血化瘀类中药在这方面也有一定潜力;蛇毒类制剂、降纤酶等药物虽然降纤效果明显,却因存在出血风险限制了其作为冠心病预防手段的应用。目前关于Fib究竟是冠心病的病因还是单纯的生物标志物仍然充满争议,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降纤治疗能否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42]。
6 脂蛋白a[lipoprotein a,Lp(a)]
Lp(a)是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残余风险生物标志物之一。Lp(a)浓度稳定,改善生活方式、他汀及依折麦布等药物对降低其浓度无明显效果。通过胞吞进入内皮的Lp(a)刺激平滑肌细胞增殖和泡沫细胞形成,诱导炎症细胞趋化,竞争性抑制纤溶酶介导血栓形成。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型(PCSK9)抑制剂在降低LDL-C的同时可使LP(a)下降约30%。脂蛋白血液分离术是一种特殊的有创性降脂治疗技术,常作为终极手段应用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和其他药物无效的严重冠心病患者。针对载脂蛋白B和载脂蛋白A的两种反义寡核苷酸 Mipomersen 和 AKCEA-APO(a)-L 是降低 Lp(a)的新方法,将投入3期临床研究评估其对心血管结局的影响[43-44]。
7 小结
冠心病患者MACE发生率高,即使接受规范的治疗并积极改善生活方式使冠心病传统危险因素得到控制,心血管残余风险依旧不能消除。非传统危险因素如HHcy、HUA、维生素D缺乏、慢性炎症反应以及血浆Fib、Lp(a)等与冠心病关系密切,是预测其发生、发展及患者长期预后的潜在性指标。探究改善此类指标异常的治疗措施,或许可以成为消除冠心病残余风险的新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