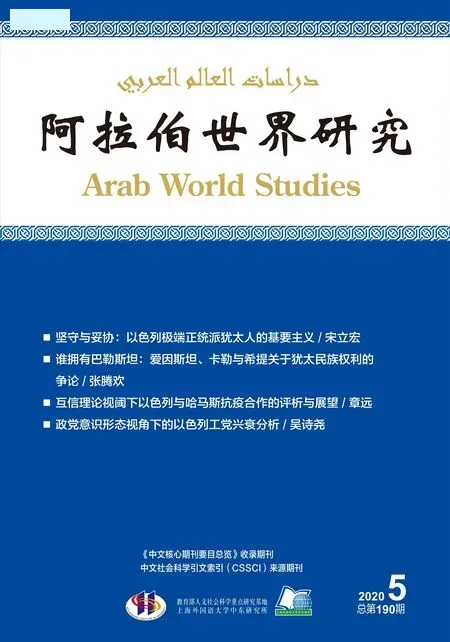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国家治理困境
邢文海
2011年初,埃及爆发了“一·二五革命”,执政近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下台。2020年2月,穆巴拉克去世,再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学界围绕2011年埃及剧变的政治、经济动因的研究成果不少(1)这类成果较多,国外代表作如Maha Abdelrahman, Egypt’s Long Revolution: Protest Movements and Uprising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Alaa Al-Din Arafat, Egypt in Crisis: The Fall of Islamism and Pro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国内代表作如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陈天社等:《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但鲜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所面临的难题与危机。本文尝试以此为分析框架,从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探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家治理的成效及其困境。
一、 路径依赖阻碍政府治理革新
穆巴拉克时期的治理模式延续了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的制度框架,在其任内的改革并没有解决埃及面临的长期性、根本性的治理问题。穆巴拉克当局主要采取干预型规制的治理手段,其政治治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和局限性,原因在于统治阶层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所推行的若干政治经济改革未能跳出威权政治运作的路径依赖,牺牲了大多数民众的福祉,弱化了政权的自我调节功能和治理革新效果,侵蚀了执政的民意基础。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国家对于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成为阻碍政府治理革新的重要因素。
第一,政治多元化改革有名无实。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在总统制、多党政治的基础上实现了议会选举和总统直选。一方面,政党政治的实践提升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与追求民主政治的偏好。这一时期,埃及举行了七次议会选举,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与其他反对派政党间的竞争在形式上日趋激烈。2005年埃及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制总统竞选,有多达10位候选人参选。另一方面,埃及政府推行政治多元化改革的背后是西方长期插手埃及国内事务的结果,外部干涉对于埃及治理能力的提升无疑是“揠苗助长”之举,使得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与民主化政治诉求陷入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2)陈天社等:《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第36页。由于穆巴拉克政府对于反对派政党的强力控制,埃及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长期流于形式,反对派政党的精英主义倾向也导致其缺乏监督执政党的民意基础,但却刺激了宗教政治势力的崛起,进一步激化了街头运动。2005年以后,埃及街头反政府抗议活动与日俱增。2006年,《今日埃及报》(Al-MasryAl-Youm)共报道了222起罢工、静坐和示威活动,这一数字在2007年增至580起。2004年至2008年,有170万人次以上的埃及劳工参与了超过1,900场抗议示威活动。至2010年,埃及平均每天发生5场抗议活动。(3)Alaa Al-Din Arafat, Egypt in Crisis: The Fall of Islamism and Prospects of Democrati ̄za ̄tion, p. 14.尽管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治多元化改革“先放后收”,因循威权主义政治路径,旨在通过改革来填补纳赛尔、萨达特时代所遗留的“政权合法性真空”。(4)范鸿达:《埃及“1·25革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比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6期,第62页。但事实证明,此举非但没有缓和国内矛盾,反而对于埃及政局稳定造成了冲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穆巴拉克的个人权威以及民族民主党执政的民意基础。
第二,法治化改革浅尝辄止。埃及1971年永久宪法在前几部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的原则。但当时埃及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由总统兼任。穆巴拉克在上台之初积极推行司法系统的独立化。1984年,埃及颁布第35号法,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由最高法院院长出任。这项改革重新划定了埃及的行政部门与司法机构的职权,实现了司法权的相对独立。但穆巴拉克政府的法治化建设并未深入,而是以不危及自身统治地位为前提,借此来形塑其宪政民主的合法性。(5)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在穆巴拉克时期,包括紧急状态法在内的特别法被周期性地启动,常态化地运用这一系列特别法律不仅强化了穆巴拉克政权的统治,而且该法也成为其打压反对派的重要工具,甚至有评论称其“使埃及从亚历山大到阿斯旺都变成监狱”。(6)王泰:《2011,埃及的政治继承与民主之变——从宪政改革到政治革命》,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5页。尽管司法体系一再呼吁废除《紧急状态法》,但这项法律一直到2012年6月才暂时告一段落。缺乏法治化的环境,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无法解决治理主体一元性、摆脱威权主义模式依赖和推行循序渐进式治理变革的重要原因。法治化改革的浅尝辄止,也为穆巴拉克政权迅速倒台埋下了伏笔。
第三,私有化改革造就了政权内部“金字塔”式的腐败。腐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在埃及,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反映了少数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一种特殊裙带关系,即一些大型企业得到政治精英的支持,从而获得特权和相关政策的保护,形成垄断利益。这种政商层层勾结牟利的现象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7)Ishac Diwan, Philip Keefer and Marc Schiffbauer, “Pyramid Capitalism: Cronyism, Regul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in Egypt,”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5, No. 1, 2020, pp. 215-216.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共进行了两轮私有化改革。1991年,埃及政府开始推动第一轮私有化改革,此轮改革力度相对较小,所出售的国有企业不涉及敏感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经济领域相互关联的公司数量明显增加,导致裙带关系活动随着私有化改革扩展到了新的经济领域。在贾迈勒的影响下,埃及加快了私有化、金融及贸易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步伐。1996年,埃及进行了第二轮私有化改革,相较于第一轮改革,这轮改革涉及诸多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相关行业,如房地产建筑业、沿海地区的旅游业、石油和天然气、中高端制造业、银行和通信行业等。自1991年至1998年,埃及政府通过私有化改革获得了20.49亿美元的收入。(8)Clement M. Henry and Robert Springborg,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3.至2002年,埃及政府共出售了186家国有企业的股份。(9)埃及信息部国家新闻总署:《埃及二十一年成就(1981-2002)》,北京: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2002年版,第5页。然而,尽管政府在某些领域实现了经济自由化改革,但在一些关键性行业却人为设置了准入门槛。1996年至2006年间,埃及358个行业中涉及私有化改革的相关行业成为政商裙带关系泛滥的“重灾区”,这些行业的总体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裙带关系影响较小的行业。裙带关系的泛滥使埃及就业机会朝着规模较小、生产效率较低的公司倾斜,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不均等,进而造成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与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企业享有多项税收以及监管特权,包括贸易保护政策、能源补贴、土地使用权和免于部分监管执法的特权,这削弱了其他企业的竞争力和投资效率,恶化了整体营商环境。
此外,埃及政府的亲商政策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天平向特定利益团体倾斜。2001年,埃及工商业所得税收入仅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4%。2004年纳齐夫总理上台后废除累进税率,将公司所得税从42%降至20%的统一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以及房产税的税率。至2009/2010年度,年收入高于5,000埃磅的工薪阶层纳税总额达130亿埃磅,而营业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大企业纳税金额却只有225亿埃磅。(10)Maha Abdelrahman, Egypt’s Long Revolution: Protest Movements and Uprisings, p. 15.2004年埃及政府启动的改革对金融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到2008年,埃及的银行数量从62家下降到39家,外资股权占比增加并实际控制了15家银行,约四分之一的国有银行被私有化。至2008年,私人银行控制了埃及50%以上的存款,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65%,银行对私人部门的贷款占GDP的35%,这导致在2003年至2010年间埃及银行贷款大部分都流向了这些有政治关系的公司。(11)Ishac Diwan and Marc Schiffbauer, “Private Banking and Crony Capitalism in Egypt,”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 20, No. 3, 2018, pp. 9-10.
民意的压力通常可以通过选举调整和政策变化加以转换,但如果制度相对僵化和保守,民怨更有可能引发革命或叛乱。(12)Jack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36.穆巴拉克政权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是造成法治不彰、腐败盛行,从而导致民怨沸腾的重要原因,当局的腐败丑闻也是引发“一·二五革命”的关键诱因。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46%的埃及受访者将腐败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才是缺乏民主和糟糕的经济环境。(13)Hamouda Chekir and Ishac Diwan, “Crony Capitalism in Egypt,”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5, No. 2, 2014, pp. 5-6.
二、 经济结构性问题恶化
经济治理倡导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而践行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有助于提升治理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应注重经济增长的果实是否惠及全民,是否能够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发展与制度公平相互协调,进而实现参与和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不容否认的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1年至2001年期间,埃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4.7%。(14)埃及信息部国家新闻总署:《埃及二十一年成就(1981-2002)》,第5页。自2002年至2010年,埃及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4%~6%左右。至2010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88.9亿美元。(15)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Egypt, Arab Rep.”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egypt-arab-rep,登录时间:2019年11月2日。1981年,埃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2美元,(16)世界知识年鉴编委会编:《世界知识年鉴(198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至2010年增至2,644.82美元。(17)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Egypt, Arab Rep.”.由此可见,埃及的经济发展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经济治理成效和问题比较突出。治理效率低下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不断恶化,是埃及“一·二五”革命最为根本的原因,加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绝大多数埃及民众沦为弱势群体。埃及经济问题恶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货膨胀率长期偏高,贫困率以及贫困人口数居高不下。穆巴拉克上台初期,埃及就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贸易赤字较大,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这些因素导致埃及国内物价飙升,陷入了恶性的通货膨胀。1985/1986年度,埃及通货膨胀率达13%,1986/1987年度则飙升到31%,此后连续数年埃及通货膨胀率都在10%以上。至20世纪90年代,埃及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降低了债务负担和贸易赤字,通货膨胀率也得到了一定遏制。由于埃及对于侨汇、油气、苏伊士运河、旅游业等地租性收入的依赖性较强,外部经济环境的周期性波动对埃及物价水平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通货膨胀率逐步攀升,这与埃及长期依赖大宗商品进口密切相关。2004年至2009年间,埃及物价水平波动较大,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底层民众家庭支出中食品开支比重随之上升,经济负担日益沉重。2004年,埃及年通货膨胀率达12.9%,此后虽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总体物价水平仍相对偏高。2007年至2009年,埃及通货膨胀率连续三年高达10%以上。2008年8月,埃及当月物价指数高达25%,国内食品价格上涨了35%。(18)Rachel Trego,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gyptian Food-subsidy System during Food-price Shock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21, No. 4-5, June 2011, pp. 668-670.至2009年,埃及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6.2%。(19)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AFDB),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1, p. 156.粮价上涨引发了埃及国内多轮反政府抗议示威,加之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致使埃及民众生活质量不断下滑。穆巴拉克政府的补贴政策虽然起到了缓解民众对物价上涨不满的作用,但制度设计存在的严重缺陷导致浪费严重。从2002年至2009年,各项补贴和转移支付占政府开支的比例从24%上升至45%。(20)余建华等:《中东变局研究(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粮食和燃料补贴预算占埃及GDP的16%。然而,只有20%的补贴被发放给贫困阶层,剩下的80%则惠及了非贫困人口。(21)Nemat Shafik, “Making Sure Middle East Growth Is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y 10, 2012, https://blogs.imf.org/2012/05/10/making-sure-middle-east-growth-is-in ̄clu ̄sive/,登录时间:2019年10月24日。价格补贴还变相鼓励了社会上的浪费行为,走私、黑市交易和腐败寻租行为泛滥,这导致了该时期严重的食品短缺问题。
在穆巴拉克时期,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与民众的贫困问题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时期埃及的贫困人口占比相对较高,且呈现出区域贫困集中化的趋势。1994年至1995年,埃及极端贫困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4%,包括相对贫困人口在内的贫困率高达51.3%。2004年至2005年,极端贫困率从此前(1999年至2000年)的16.7%增至19.6%,埃及极端贫困人口数量达到1,397.4万人。(22)Ruslan Yemtsov, Upper Egypt: Pathways to Shared, Document of the World Bank, Report No. 49086-EG, 2009, p. 11.该时期,埃及贫困问题凸显出城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1990年,埃及极端贫困率为25%,其中城市极端贫困率为20.3%,乡村极端贫困率为28.6%。2000年,埃及极端贫困率为16.9%,其中城市极端贫困率达9.3%,农村极端贫困率达22.1%。2009年,埃及全国极端贫困率为21.6%,其中城市极端贫困率为11.0%,而农村极端贫困率达28.9%。(23)Maha Abdelrahman, Egypt’s Long Revolution: Protest Movements and Uprisings, pp. 14-15.从减贫扶困的力度上看,1990年至2009年间,埃及城市极端贫困率从20.3%降至11.0%,而农村地区极端贫困率未降反升,从28.6%升至28.9%。(24)Ruslan Yemtsov, Upper Egypt: Pathways to Shared, p. 11.这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埃及农村地区发展的相对迟缓,还反映出穆巴拉克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农村所产生的冲击。至2011年,埃及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较高,按每天生活水平低于2美元标准计算,15岁以下人口的贫困率达23%,15~19岁人口的贫困率为28%。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年龄在15岁以下和15~19岁的农村青少年贫困率分别为30%和12.16%。(25)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Arab Republic of Egypt, Strategic Plan for Pre-university Education 2014-2030, Cairo: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pp. 9-10.
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埃及贫困问题也存在区域集中化的现象,这在上埃及农村地区尤为明显。上埃及地区的贫困问题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加突出,极端贫困率从1994/1995年度至2004/2005年度呈上升趋势,从29.3%增至39.1%。2005年至2008年间,上埃及农村地区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仅为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1999/2000年度至2004/2005年度,上埃及地区城市极端贫困及相对贫困人口占比从48.9%降至38.0%,而乡村地区则从63.5%增至64.6%。下埃及地区城市极端贫困及相对贫困人口占比则从33.5%降至27.7%,乡村地区从57.1%降至42.0%。(26)Ruslan Yemtsov, Upper Egypt: Pathways to Shared, p. 11.开罗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贫困率相对较低且下降较快,而上埃及、下埃及地区的总体贫困率仍相对较高。
本文对有源相控阵天线接收链路等效噪声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详细推导出等效噪声计算公式,该计算方法中每个T/R通道的增益、噪声系数等技术指标都分别作用于最终结果,适用于任意变化的有源相控阵天线。该方法推导出的等效噪声计算公式已经在仿真及雷达系统中获得了实际应用,该公式有助于精确计算有源相控阵天线接收系统的性能。
第二,失业问题严重,青年失业问题尤为尖锐,成为埃及社会稳定的长期隐忧。纳赛尔时期,埃及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1960年初,埃及失业率为2.2%。1964年,埃及开始实行毕业生就业保障制度。这项计划将各教育阶段的毕业生分配到政府及公共部门工作,此举虽然缓解了失业问题,但造成了政府及公共服务部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萨达特时期,埃及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失业率逐渐攀升。1976年失业率达7.7%左右。(27)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316页。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人口增长较快,失业问题长期化,并且在“一·二五革命”前夕进一步加剧。1985年,穆巴拉克废除毕业生就业保障计划,造成此后十年间埃及中学毕业生失业率的大幅攀升。为解决就业问题,埃及政府部门长期超额雇佣应届毕业生以缓解青年失业问题对社会的冲击。1999年,政府部门以及教育行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33%,这一比例在2003年和2007年分别为37.9%和31.7%。(28)Anne Alexander and Mostafa Bassiouny, Bread, Freedom, Social Justice: Worker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p. 87.从产业结构上来看,1982年至2011年间,埃及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变化幅度不大,工业占比有所增加,农业产值有所下降。长期以来,农业经济是埃及重要的经济支柱,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工业产值占比有所增加,但基础较为薄弱,吸纳了部分技术教育毕业生就业;第三产业则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向。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穆巴拉克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私有化政策,造成国内失业问题进一步加剧,历届政府未能为失业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然而,埃及政治宣传的话语体系与社会现实困境之间的差距愈加显现。随着国内外公司引进最新的生产技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失业状况。2003年,埃及失业率为11%,较1990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埃及全国失业人数也从129.1万人增至224万人。(29)李超民:《埃及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至2010年,埃及全国失业人口已达235.1万人,失业率为9.0%。(30)“4-2 Annual Estimate of Labor Force Status, By Sex (2009-2018),” in Central Agency for Public Mobilization and Statistics (Egypt),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Cairo: CAPMS, September 2019, p. 80.
21世纪初至2011年埃及剧变前后,失业问题呈现出长期化、年轻化、高学历化的特点,青年失业率较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虽然埃及当局承诺让青年人获得更多权利,但政府部门明确提出的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的目标,无法有效地将埃及快速增长的青年人口转化为劳动力市场的合格劳动力,也未能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公共政策以提升应届生的就业竞争力,教育资金的投入也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就业机会。这导致了埃及失业问题长期化、年轻化、高学历化。青年失业率较高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2010年,埃及18岁至29岁人口的失业率为20.4%。其中,拥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失业率为26.8%,高中学历和技术教育学历的男性失业率则分别为19.3%和11.2%。拥有技术教育文凭的女性、大学学历的女性和高中学历的女性失业比例更是分别高达56.1%、55.1%和45.5%。2009年一项关于埃及青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高学历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甚至更高。其中,18岁至29岁的人口中近58.5%处于失业状态,女性和男性的失业率分别达83%和27%。(31)Heba Handoussa, ed., Egypt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Youth in Egypt: Building our Future, Cairo: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Institute of National Planning, 2010, pp. 147-162.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失业率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这种现象在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人群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系列问题激化了年轻人对当局的不满与反抗情绪。
第三,阶层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不满情绪蔓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益于石油等收入的增长,埃及国民经济较为稳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埃及中产阶层规模萎缩的趋势较为明显。1991年,埃及中产阶层约占社会总人口的45%,但到2006年,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一度降至12.4%,社会底层人口所占比重达到了69.1%。(32)埃及国家统计局:《2006年埃及全国人口统计普查》,转引自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132页。2010年,埃及中产阶层所占人口比例缓慢回升至22%。(33)Alaa Al-Din Arafat, Egypt in Crisis: The Fall of Islamism and Prospects of Democratiza ̄tion, p. 13.自1996年至2000年,埃及的基尼系数从0.3013升至0.3276,2005年降至0.3214。(34)Ahmed Ezz Eldin Mohamed, “The Welfare State in Egypt, 1995-2005: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l Muntaqa, Vol. 1, No. 1, 2018, p. 72.社会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比从1996年的26.04%升至2000年的28.34%,到2005年仍为27.64%。相比之下,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收入占比从1996年的9.51%降至2000年的8.95%。(35)World Bank and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ab Republic of Egypt: A Poverty Assessment Updat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p. 61.2005年,埃及有将近四分之三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55%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上埃及的农村地区。大部分贫困人口从事农业和建筑业的工作,这两个行业吸纳了大量非正规劳动力,相对贫困人口分别占该行业从业人数的26.3%和26%。(36)Ahmed Ezz Eldin Mohamed, “The Welfare State in Egypt, 1995-2005: A Comparative Approach,” p. 72.
穆巴拉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客观上扩大了贫富差距,侵蚀了中产阶层的切身利益,引发了社会中下阶层的愤怒,为2011年埃及剧变蓄积了社会不满情绪。根据第四和第五次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研究数据,2000年,埃及中产阶层较为广泛地支持穆巴拉克的威权主义统治,有75%的中产阶层受访者支持“维持秩序”。在2008年,则有55%受访者选择支持“保护言论自由”和“争取更多的发言权”。而贫困阶层中对于民主偏好度的比例从2000年的22%上升至2008年的47%,富裕阶层对民主偏好度的比例从2000年的44%下降至2008年的31%。就年龄而言,20岁至29岁年轻受访者比30岁以上的受访者更偏好民主。2000年,34%的年轻人具有民主偏好,而相比之下,只有18%的30岁至59岁的青壮年和20%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更倾向于民主。至2008年,民主偏好度的年龄层差异已经基本消失。(37)Ishac Diwan,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Changing Public Opinion in Egypt: A Story of Revolution,” in Edward A. Sayre and Tarik M. Yousef, eds., Young Generation Awakening: Economics, Society, and Policy on the Eve of the Arab Spr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38.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民意变化的趋势基本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埃及中产阶层对于穆巴拉克政权由普遍支持到多数反对的态度转变。与2000年的调查数据相比,2008年埃及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度上升,特别是贫困阶层和中产阶层对民主的支持明显上升,而富裕阶层对民主的支持在下降。这反映了各个阶层的埃及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显著增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中产阶层人群的不满情绪越强烈。埃及的中产阶层最终成为埃及“一·二五革命”的主要支持者。
总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穆巴拉克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治理效率提升的主要成果,而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与失业问题长期化、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埃及市场失灵、治理效率低下的必然恶果。最终,这一恶果正是由经济能力极为脆弱的埃及中下层民众承担。在穆巴拉克时期,一方面,埃及经济实现了长期较快的发展,度过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政府对于西方经济理论采取盲目崇信的态度,在国内产业基础羸弱等背景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最终造成经济结构性失衡、对外依附性过高、政府财政效率不彰、社会财富再分配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一·二五革命”背后的经济社会动因凸显了埃及经济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穆巴拉克执政后期,一些长期性的经济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刺激了埃及民众的民主偏好和不满情绪,这凸显了穆巴拉克政权长期忽视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所带来的恶果。在青年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长期失业、区域贫困化、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条件恶化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对于埃及社会稳定产生了直接冲击和影响。缺乏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以牺牲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展权益为代价,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的加剧与抗议运动的陡然升级。
三、 社会治理变革的迟滞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既是治理的主体,同时也是治理客体。埃及社会治理问题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国家力量过于强势、社会力量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从而导致社会管理相对低效、治理变革较为迟滞,这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长期累积的产物。在穆巴拉克时期,“强政府与弱社会”的传统管理模式显著,社会治理水平滞后于信息化所带来的时代变革,主要表现为民生治理体系不完善,民生问题成为制约埃及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政府长期控制并主导公共服务供给,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采取促进与抑制并存的双重管理手段,使得非政府组织无法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互联网普及迅速,但治理严重滞后,反对派在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下得以迅速集结,打破了政府对于信息传播的垄断。
第一,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民生治理体系不完善。埃及的民生问题治理难度极大。以教育问题为例,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的教育系统无法有效地将青年人口转化为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力,教育资源的投入无法有效转化为就业机会,造成了失业问题长期化、年轻化和高学历化,这与埃及教育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存在直接关系。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学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公立教育长期无法满足民众的教育需求。埃及公立教育系统长期僵化臃肿、质量不佳,客观上催生了私立教育市场的日渐兴起,但私立教育在制度上一直受到相当大的政策制约,在教育治理体系中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这一时期,外国投资者陆续在埃及设立了一些私立大学以及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由于政府掌控私立学校的土地供应问题,从而有效限制了私立教育的发展规模。在大学前教育阶段,就读于普通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要远多于私立学校。2009/2010年度,埃及小学在校人数规模达933.43万人,预备学校在校人数为404.11万人。这一届的小学毕业生中,62%进入公立学校入学,29%的学生进入私立学校,9%进入爱资哈尔大学。而该年度埃及公立的普通预备学校在校人数占注册学生总人数的92%。(38)OCED and the World Bank, Reviews of National Policies fo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 Egypt, 2010, p. 61,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skills-beyond-school/44820471.pdf,登录时间:2019年11月3日。1992年,埃及立法机构颁布《私立大学法》,为私立大学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1996年之后,一批私立大学相继投入办学。教育市场的逐渐开放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至2008/2009年度,埃及大学数量增至34所,其中私立大学16所。(39)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新闻部新闻总署:《埃及年鉴(2009)》,北京:埃及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9年版,第129页。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私立教育规模的扩大不仅可以满足埃及民众的教育需求,也有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提升社会治理的成效,符合埃及政府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目标。尽管如此,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在教育管理权力下放和增加公民教育参与等问题上始终持谨慎态度,只是允许公众有限参与。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埃及政府担忧权力下放不仅会导致政府权力分散,而且会激化与少数族裔、宗教势力之间的矛盾。穆巴拉克长期独掌大权,世俗的反对派政党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则致力于挑战穆巴拉克政权的正当性,这使得包括教育在内的民生问题成为了埃及各派别政治对抗、巩固社会基础、拉拢人心的重要手段。其次,埃及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教育管理模式,地方治理能力的弱化影响了权力下放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教育问题正是埃及民生治理难题的缩影。
第二,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实行促进与抑制的两手政策。非政府组织是社会民间力量的重要构成部分。首先,非政府组织主动承担扶贫救弱,协助政府开展社会管理的职能。非政府组织可以协助政府进行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弱势群体救助,有利于构筑社会安全网,有效弥补政府职能的缺失与不足。其次,非政府组织有助于社会组织结构化以及治理民主化。相较于个体而言,非政府组织能够广泛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利益并为之发声,有利于对政府进行强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进而维护民众权利,鼓励更多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以及规模都相当可观,但是也受到了当局极为严格地限制。根据1999年的一项调查,埃及非宗教社会团体共雇佣了629,223名员工,年支出达15亿美元(约占GDP的2%)。(40)Kareem Elbayar, “NGO Laws in Selected Arab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t-for-Profit Law, Vol. 7, No. 4, 2005, p. 7.如果算上伊斯兰教以及科普特人非政府组织雇佣的员工数量,这一数字将高达75万人以上。(41)Lester M. Salamon et al., Global Civil Society: Dimensions of theNonprofit Sector, NewYork: Kumarian Press, 2004, p. 217.2002年第84号法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规范,对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了界定和区分。这两类组织都受埃及社会事务部监管,并受相关法律规定的约束。随着法律制度等相关规范的进一步确立,埃及对非政府组织的管控逐渐放开,相关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至2008年,在埃及注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约有26,295个,相较1990年翻了一番。(42)田文林:《西方对埃及的“和平演变”及其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3期,第52页。这些组织所掌握的资金规模约20亿埃磅,其中接受外国捐助约3亿埃磅。(43)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158页。埃及政府在利用国家强制力来影响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同时,有意促进部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一些非政府组织由于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受到了政府严格的制度和政策约束。通过促进和抑制的双重手段,穆巴拉克政权借由与非政府组织相互合作、协同治理,在向民众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有效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政府借由立法和相关政策工具迫使这些非政府组织依照当局的意志行事,利用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实现“分而治之”并稳固自身的权力。不仅如此,穆巴拉克还以放宽非政府组织运营的限制来改善政府的国际形象,借此缓解来自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力。
从穆巴拉克政权与非政府组织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穆巴拉克政权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培育强而有力的公民社会,而是确保其统治不受体制外力量的威胁。客观上来看,穆巴拉克时期埃及非政府组织发展较为迅速,为埃及公民社会的培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若干缺陷。在政府的政策干预之下,埃及的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并不完善。
第三,互联网治理严重滞后。互联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传统政治精英的权力垄断格局出现松动,各国政府都在主动加强互联网的治理,防止“网络无政府主义”对于国家稳定发展的冲击。从“一·二五革命”可以看出,穆巴拉克政府对于互联网技术的认知和治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埃及是北非最大的固网和移动互联网市场之一。2000年,埃及互联网用户约4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仅0.7%。至2009年,埃及互联网用户数量增至1,256.8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15.9%。(44)“Egypt: Internet Usag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ports,” Internet World Stats,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af/eg.htm,登录时间:2019年11月03日。在“一·二五革命”期间,穆巴拉克政权采取即时信息阻截的手段阻止敏感信息的传播,并未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埃及当局要求各大电信公司切断互联网、语音服务,同时迫使电信公司发送支持政权的宣传信息。尽管如此,互联网关闭只持续了五天,反而使更多不满的抗议民众走上了街头,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向穆巴拉克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直到穆巴拉克于2011年2月11日宣布辞职。
对于互联网治理而言,国家治理的重点在于治理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以及两者结合的“新世界”。互联网是中性的技术工具,但互联网安全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一·二五革命”催生了新兴的网络媒体、网络组织、网络社群,这些基于互联网技术所衍生的社交网络不仅为反对派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虚拟的政治舞台,从而催生了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同时也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得以利用信息、技术优势进行新形态的“网络外交”,干预埃及国内政治事务。外部势力以互联网为工具进行干预和介入,不仅削弱了穆巴拉克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力,同时也对埃及国家网络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冲击了埃及的国家认同与政府公信力,并最终破坏了埃及政局的长期稳定。
四、 结语
在穆巴拉克执政初期,埃及面临严峻且复杂的内外形势。经过其任内数十年的改革,埃及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相对严密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体系。从政治层面来看,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选举政治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依旧维持实行共和以来的威权主义传统,总统凌驾于国家之上,立法机构、司法系统对于总统的制约能力有限。在穆巴拉克任内,埃及形成了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借由自由化改革垄断了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侵害了埃及大多数民众的切身利益。从经济层面来看,埃及沿袭了萨达特时期确立的新自由主义外向型经济模式,依赖外国资本以及国际组织的发展援助,经济改革侧重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国内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让埃及经济实现了中高速增长,但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层萎缩、青年失业严重等结构性问题。从社会层面来看,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社会治理呈现变革滞后的特点。这一时期,埃及的民生治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民生治理体系依然不够完善。随着教育的快速普及,埃及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快速提高。但高学历却难以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酬待遇,社会阶层固化以及中产阶层规模萎缩现象显著。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部分弥补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缺失,但在政府的抑制与打压下,其社会治理的功能不够健全;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互联网普及速度加快,但互联网治理严重滞后,对埃及的政治稳定构成了挑战。
总体而言,穆巴拉克终结了萨达特遇刺所引发的动荡与危机,实现了埃及政局与社会的长期基本稳定,这一时期埃及的经济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提升了埃及的地区影响力。但由于穆巴拉克政权对威权主义统治的路径依赖阻碍了政府治理革新、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社会治理迟滞,导致在他统治后期埃及陷入严峻的治理困境,这也是引发2011年埃及“一·二五革命”,并最终促使穆巴拉克辞职下台的根源性因素。简而言之,国家治理成效不彰是导致埃及陷入动荡、政权更迭的主因,而经济结构性问题不断恶化是促使穆巴拉克下台的关键。在“一·二五革命”之前,埃及经济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率。然而,这种增长并不具有包容性,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在此期间尤为突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中产阶层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年轻人就业困难,上埃及等偏远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逐渐被边缘化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埃及的国家治理步入了正轨,社会发展逐渐向好,但依旧困难重重。穆巴拉克时代国家治理的诸多问题依然延续至今,唯有系统性的治理变革才能避免危机的重现。在政治治理上,在稳定有序的前提下,应不断完善总统制和议会民主的制度建设,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空间;遏制极端势力,逐步推动政党政治的有序改革;继续推动法治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腐败的问题。在经济治理上,应尊重市场规律,鼓励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注重发展的普惠性,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为不断增长的年轻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制定区域性扶贫开发政策以遏止贫困集中化的趋势。在社会治理上,应通过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来改善贫困家庭的民生困境;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普及互联网的同时强化互联网的日常监管和危机预警,推动互联网生态的有效治理。埃及的教训表明,中东国家亟待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正视自身存在的治理短板,从而增强国家治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