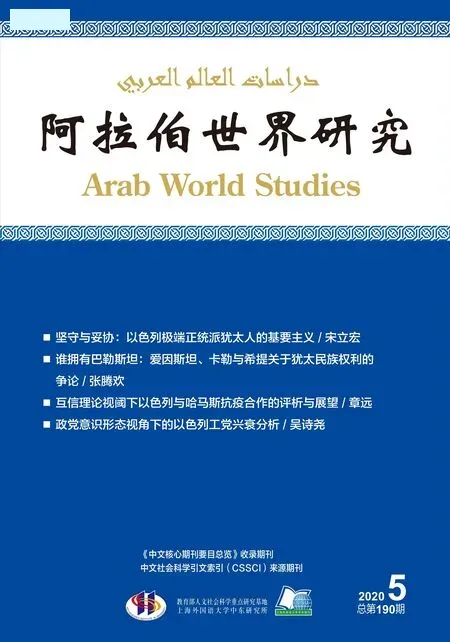谁拥有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卡勒与希提关于犹太民族权利的争论
张腾欢
1944年4月,围绕犹太人是否拥有对巴勒斯坦的民族平等权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埃里克·卡勒(Erich Kahler)与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进行了一场学术论争。时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物理学教授的爱因斯坦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努力,但反对建立犹太国。(1)Albert Einstein, “Our Debt to Zionism,” April 17, 1938, in Albert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54, p. 190.他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未来,是与阿拉伯人一道建立一个双民族国家(bi-national state)。(2)Gil Troy, ed., The Zionist Ideas: Visions for the Jewish Homeland: Then, Now, Tomorrow,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p. 31.卡勒时为普林斯顿大学文学批评家,是一名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爱因斯坦看法类似。希提是阿拉伯裔美国学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主任,是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美国阿拉伯研究的奠基人。
这场论争缘起于希提的一番言论。1944年1月,美国众议员詹姆斯·莱特和拉诺夫·康普顿提出,美国应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支持将巴勒斯坦建设为“一个民主的犹太共和国”。(3)Thomas Kolsky, Jews Against Zionism: 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 1942-194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2.随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该议案举行听证会。希提在听证会上称,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并无与阿拉伯人平等的民族权利。随后,爱因斯坦和卡勒对希提的言论做了批评性回应。
这场辩论由爱因斯坦、卡勒与希提的四篇文章组成,内容涉及阿犹两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和现实经济社会状况,基本体现了当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看法和分歧,反映了阿犹双方互不信任的心理,折射出双方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国内外学界以往对巴以争端的研究多关注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争斗和论辩,本文以阿犹双方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争论为观察对象,探讨双方的主要分歧和利益诉求,以期为研究巴以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4)这场论争至今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充分关注,笔者仅见丹尼斯·布莱恩、哈罗德·提克汀、丹尼尔·里肯巴赫对此有简略介绍。参见Denis Brian, Einstein: A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35; Harold Ticktin, “A Jewish State? Einstein and Opponents in 1944,” September 29, 2014, https://momentmag.com/jewish-state-einstein-opponents-1944/, 登录时间:2019年9月15日; Daniel Rickenbacher, Arab States, Arab Interest Groups and Anti-Zionist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urich, 2017。
一、 “阿拉伯人首先来到巴勒斯坦”: 希提的“历史优先权”论
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希提首先就“历史优先权”问题作了陈述。他认为,阿拉伯人在历史上先于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其理由是,当今5,000万阿拉伯人中的许多人是古代迦南人的后裔,在犹太人的先祖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前,迦南人就在那生活了很长时间。对整个穆斯林社会来说,阿拉伯人是先锋。希提还从宗教层面论证了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优先权”。他强调,在穆斯林眼里,耶路撒冷是麦加和麦地那后的“第三圣城”,早期穆斯林在面向麦加祈祷前,会先面向耶路撒冷祈祷;巴勒斯坦是经过一次伊斯兰“圣战”后,由真主安拉赐给阿拉伯人的圣地。
不难看出,希提是从“谁最先进入巴勒斯坦”来决定“谁拥有巴勒斯坦”。在他看来,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时间早于犹太人,巴勒斯坦自古以来属阿拉伯人所有,犹太人是“外来者”。由此,希提认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外来的运动”。(5)“Dr. Hitti Gives Views on Palestine as Jewish State,” The Princeton Herald, April 7, 1944.希提就此解释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由国际资助、受外力驱使,无望“取得最终的或永久的成功”。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希提围绕穆斯林反对犹太人建国的民族意识及其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进行说明。他指出,穆斯林组成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占据着亚非大部分区域。即使依靠英美的外交和军事支持,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有朝一日成为现实,但在充满敌意的伊斯兰世界,犹太国这一“外来的国家”并无生存机会。(6)Ibid.
希提指出,犹太民族家园在巴勒斯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这样的图景:它不是犹太民族强加在巴勒斯坦其他居民头上的不合理要求,而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帮助下,成为全体犹太人基于种族和宗教背景可以依赖的中心。希提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开明务实的人士,如犹大·马格尼斯(Judah Magnes)、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on)和朱利安·摩根斯坦(Julian Morgenstern)等人已提出,要注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文化和精神层面”,反对建立犹太国,并呼吁和阿拉伯人合作。(7)犹大·马格内斯时任希伯来大学校长,罗伯特·汉森是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朱利安·摩根斯坦时任希伯来联合学院校长。
希提还追溯历史,从阿犹两个民族、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亲缘关系以及阿拉伯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予以说明。在他看来,坚决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犹太国的主张不等于反犹主义。在世界主要民族中,阿拉伯人或许最无种族偏见,而且他们知道自己和犹太人都属闪米特人。阿拉伯人也知道,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亲缘关系最近,两者的亲缘关系之近超过了它们与基督教的亲近程度。在整个中世纪和近现代,没有哪个地方的犹太人比“穆斯林—阿拉伯土地”上的犹太人受到更好的对待。(8)“Dr. Hitti Gives Views on Palestine as Jewish State”.
从历史、宗教和现实政治等方面出发,希提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并无历史正当性,也无现实依据。和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样,希提不相信犹太人仅仅满足于取得巴勒斯坦部分土地,而是认为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和拓展,目的是要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基于上述理由,希提在听证会上总结说,莱特等人关于建立犹太国的议案损害了阿拉伯人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人、英国人甚至犹太人的利益。在巴勒斯坦出现一个拥有主权的犹太国实属“时代错乱”。(9)Ibid.
从当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犹太国的构想和现实政治主张来看,希提在听证会上关于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说法并不确切。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看来,阿犹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谈判解决,与阿拉伯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他们讨论了许多关于阿犹分治的方案。1942年5月,在纽约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联邦”(Jewish Commonwealth)的主张。(10)Walid Khalidi, ed., From Haven to Conquest, Volume 2: Readings i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Until 1948, Beirut: The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71, p. 497.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是与阿拉伯国并存的犹太国,而非犹太国独占整个巴勒斯坦。直至1944年,莱特等人提出的议案都是类似的表述。希提在听证会上的发言表明,他对“犹太国”的意涵所指存在明显的误解,故而提出历史优先权问题来否定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诉求。
希提关于巴勒斯坦的历史优先权属于阿拉伯人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阿拉伯人最先来到巴勒斯坦古代迦南的历史模糊不清,《圣经》记载和相关传说并不可信(11)Nicholas De Lange, ed.,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7, p. 3.;而从现代考古发现来说,也并无确凿证据表明阿拉伯人来到巴勒斯坦的时间早于犹太人。至于巴勒斯坦是由伊斯兰教真主赐给穆斯林的说法,其中掺杂着浓郁的宗教意味,难以作为可靠的论据。
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基本理念出发,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赖以借助的思想资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有多种不同主张,但基本都同意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并认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正是这种历史权利的体现。希提的观点无疑推翻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合法性,极易引发来自犹太人内部的反驳。
二、 “不存在历史优先权”: 爱因斯坦和卡勒的回应
希提的上述观点于1944年4月7日发表在《普林斯顿先驱报》(ThePrincetonHerald)上。看到希提观点的爱因斯坦与卡勒认为,希提的观点是片面的,两人决定联合作出回应,并于4月14日在《普林斯顿先驱报》发表了联合署名文章。在反驳文章的开头,爱因斯坦和卡勒说,他们此次撰文并非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辩护,而是以无党派归属的犹太人和普通人的态度来看待希提的观点。爱因斯坦和卡勒认为,从今天人们的基本认知出发,希提所言不符合历史真实,但他们愿意就希提的几个主要观点进行辩驳。(12)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Palestine Setting of Sacred History of Jewish Race,” The Princeton Herald, Friday, April 14, 1944.
针对希提关于阿拉伯人先于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的观点,爱因斯坦和卡勒反驳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传说中来源于同一个祖先,在亚伯拉罕时期来到迦南,所以无法确切地说两个民族究竟谁先来到迦南;后来,一部分“以色列人”移居埃及,其余人仍留在了迦南,所以希伯来人的先知约书亚率领的犹太人来到迦南时遇到的一部分迦南人也是以色列人。(13)Ibid.从爱因斯坦和卡勒的观点来看,既然谁先来到巴勒斯坦无法确定,那么希提论点的前提即不成立。
对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重要性,爱因斯坦和卡勒经过比较认为:“对阿拉伯人来说,耶路撒冷只是第三圣城;而对犹太人来说则是第一圣城,也是唯一的圣城,巴勒斯坦还是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神圣的宗教历史发生的地方。”(14)Ibid.他们指出,阿拉伯人只有在将他们的传统追溯到犹太人时,只有在阿拉伯人于637年征服耶路撒冷、岩石圆顶清真寺在犹太人曾经的约柜和所罗门圣殿旧址上建立起来后,才能说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的圣城;在先知穆罕默德主要依靠犹太人来支持他的教义之后,耶路撒冷才成为穆斯林礼拜的方向;先知穆罕默德实践的一些宗教规则也依循犹太教,比如伊斯兰教的斋戒便模仿犹太教的赎罪日。(15)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Palestine Setting of Sacred History of Jewish Race”.所以,在爱因斯坦和卡勒看来,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文明和宗教传统要比阿拉伯人久远。言外之意,在两人看来,若以哪个民族“谁先来到巴勒斯坦”以及“谁在巴勒斯坦的文明传统更悠久”作为判定优先权的依据,那么阿拉伯人并不拥有对巴勒斯坦的历史优先权。爱因斯坦和卡勒认为,对于某一土地的优先权问题,应该持这样的认识:“犹太人不会去争论谁拥有优先权。历史权利无法远溯。如果远溯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有权拥有他们现在所在的土地。”(16)Ibid.
针对希提所言巴勒斯坦是在“圣战”后由真主赐予阿拉伯人的说法,爱因斯坦和卡勒反驳认为,如果将阿拉伯人的征服行为视为合法,那么犹太人的和平建设更属合法。他们反讽希提:“对一个谴责和平的移民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的民族来说,将所谓‘圣战’赋予合法性是荒唐的。”(17)Ibid.从人口角度看,爱因斯坦和卡勒讽刺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二三百万,在希提那里却成了四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和四千万阿拉伯人的威胁。两人谴责道,希提关于人数稀少的犹太人是众多阿拉伯人的威胁的说辞,实际上与纳粹宣扬的说法无异。
希提认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态度要好于其他民族,而且犹太人问题的产生并非阿拉伯人所为,不应通过建立犹太国这样牺牲阿拉伯人权利的方式来解决。对此,爱因斯坦和卡勒指出:“通过圣战和对巴勒斯坦的征服,阿拉伯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犹太人对故土的权利以及制造了犹太问题——虽然必须承认,他们的所为没有其他民族严重。然而,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立场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是一样的。”(18)Ibid.爱因斯坦和卡勒感叹道,包括希提在内,“没有人理解为何要解决犹太问题”。两人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辩护称,当今世界已不存在没有民族的土地,对于犹太人这样没有土地的民族来说,他们为获得像其他民族一样的权利而进入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引发纠纷,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这是因为,“地球上每个地方都已被占据,无论犹太人在哪个地方获准得到一块土地,从而生活在公平的环境中,他们都会不断占有某些财产权和主权,还会面临与已经牢固居住在那里的人发生矛盾。”两人进一步指出:“5,000万阿拉伯人中只有90万人生活在巴勒斯坦,而小小的巴勒斯坦却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与犹太民族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19)Ibid.在这一认识上,爱因斯坦和卡勒的观点与此时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无异。当时,不少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除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无处可去,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可去其他阿拉伯国家。(20)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2, p. 596.正是出于这一判断,犹太复国主义者要牢牢抓住巴勒斯坦这一犹太人唯一的生命港湾。1944年,欧洲已经发生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这不但导致数百万犹太人丧生,还产生了大量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意义已不仅是复兴犹太文化,更是庇护犹太人生命安全的所在。
为进一步说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存在的合法性和天然权利,爱因斯坦和卡勒还着重阐述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及其给阿拉伯人带来的益处:“犹太人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将巴勒斯坦这一狭小的地方变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和文明的典范。过去数十年间,犹太青年从阿拉伯人那里接管过来沙漠、戈壁和贫瘠的土地,将其变成了欣欣向荣的农场和种植园,变成了森林和现代城市。他们创造了新型的合作定居点,提高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生活水平。”(21)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Palestine Setting of Sacred History of Jewish Race”.爱因斯坦和卡勒此言意在说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设是出于和平目的,并非如希提所说要通过移民和开拓殖民地进而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人并非阿拉伯人的威胁。
爱因斯坦和卡勒在文中称,这篇对希提观点的回应文章并非为了鼓吹民族主义。两人解释道,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诉求是正当的,因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目标是建立避难地,从而使犹太人摆脱迫害,获得应有的和其他民族一样的权利;大多数犹太人“不会因为民族的贪婪和自我虚荣而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因为那样将违背犹太教的一切传统价值”。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两人“才为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而辩护”,从而写下这篇回应文章。(22)Ibid.
最后爱因斯坦和卡勒总结说:“我们不愿提历史权利,不过如果存在类似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权利的东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可以对巴勒斯坦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不会诉诸暴力威胁,因为犹太人力量弱小;实际上,犹太人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群体。如果犹太人有任何力量,他们就能阻止数百万同胞被屠戮,就能阻止救助受纳粹迫害的无助受害者的最后一扇大门被关闭。我们呼吁的是基本的正义和人道主义。”(23)Ibid.两人此番陈述对希提的主要观点作了回应。首先,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要求不仅植根于历史,更基于现实。其次,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不是要最终排挤和取代阿拉伯人,犹太人无力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在爱因斯坦和卡勒看来,希提的论据透露出武力威胁和利己自私的情绪:“如果强权威胁、宗教利己主义和圣战的说辞继续主导未来的世界秩序,那么不仅犹太人,而且全人类的命运也将注定。”(24)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Palestine Setting of Sacred History of Jewish Race”.
爱因斯坦和卡勒在这篇文章中虽然不同意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但更反对希提关于阿拉伯人“历史优先权地位”的预设。爱因斯坦和卡勒没有仅从历史层面来说明犹太人的正当权利,而是辅以犹太人当前在巴勒斯坦建设的积极意义来论证其民族权利的合法性。他们认为,从历史上看,无法认定犹太人是巴勒斯坦的“后来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是巴勒斯坦的天然拥有者;从现实来说,在遭受种族灭绝的险境下,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唯一能够安全栖身的庇护所,而且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设促进了本地区的发展,推动了阿拉伯社会的进步。换言之,在爱因斯坦和卡勒看来,巴勒斯坦的归属应更多由现实状况来决定,而非从虚无缥缈的历史权利来判断。
三、 从历史权利到现实政治: 希提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批判
在爱因斯坦和卡勒的文章发表一周后,1944年4月21日,希提在《普林斯顿先驱报》撰文进行了回应。希提首先对爱因斯坦和卡勒关于“阿犹属共同祖先,自亚伯拉罕时来到迦南”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希提认为,即使对《旧约》不熟悉的人也知道,假定存在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时,他发现那里并非无人居住;所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基督徒“是古老本土血统的现代代表”,而“希伯来人来了又走了,本地人留了下来”。希提追溯犹太人的历史后指出,以色列人建立的希伯来王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灭亡犹大王国,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先后被俘虏。希提据此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被后来的统治者摧毁,其对巴勒斯坦的控制也永远不存在了。(25)“Palestinian Arabs Descended from Abraham, Says Dr. Hitti,” The Princeton Herald, Friday, April 21, 1944.
希提批评说,爱因斯坦和卡勒关于阿拉伯人剥夺犹太人土地、制造犹太问题的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他指出,公元7世纪,穆斯林打败拜占庭军队,征服了巴勒斯坦,在此之前,巴勒斯坦居住的是基督徒,而非犹太人。他往前追溯,指出拜占庭是罗马的继承者,罗马从塞琉古那里夺取了巴勒斯坦,塞琉古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亚历山大大帝从波斯那里夺得巴勒斯坦,波斯在前538年摧毁了迦勒底帝国,迦勒底帝国在尼布甲尼撒时征服了巴勒斯坦。希提讽刺说,稍微熟悉阿拉伯人的历史便会发现两人的这一错误,爱因斯坦对“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者问题”历史由来的了解并不比他对相对论的了解更深。
应该说,从种族层面来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究竟哪一方先来到巴勒斯坦是一个难以确证的问题,此处希提关于阿拉伯人先来到巴勒斯坦的说法并不严谨。不过,希提关于古代犹太人国家的历史叙述符合基本史实。在他看来,“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者问题”的历史由来应追溯至阿拉伯人之前的历代征服者,犹太人并非被阿拉伯人击败而失去巴勒斯坦,所以当今犹太人向阿拉伯人提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诉求也缺乏历史依据。
针对爱因斯坦和卡勒的观点,即“小小的巴勒斯坦却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与犹太民族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希提认为,移民和殖民是较为轻微的侵略形式。他回应说,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为例,尽管是和平的入侵,但却是公开的行为,这在莱特等人提出的议案中已有暗示:美国将最终帮助犹太人把巴勒斯坦的大门打开,使犹太人能够自由进入,应使犹太人有充分的机会去殖民,以便使犹太民族最终将巴勒斯坦重建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希提说,不仅如此,在英国的官方报告中也有此类表述:犹太人的渗透被阿拉伯人称作“缓慢的征服”(creeping conquest)。(26)“Palestinian Arabs Descended from Abraham, Says Dr. Hitti”.
爱因斯坦和卡勒提出的第三个论点是,犹太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接管过来沙漠、戈壁和贫瘠的土地”,通过劳动将其变为富饶繁荣之地。希提讽刺说,这一观点尽人皆知,因为“意大利殖民者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也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他指出,尽管如此,“巴勒斯坦的繁荣”只是大量人为宣传出来的假象,任何了解巴勒斯坦经济状况的人都会戳穿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巴勒斯坦犹太人至今仍靠慈善救济生活。希提比喻道,所谓巴勒斯坦的繁荣真相只是“涂抹胭脂的肿胀脸颊”。希提援引英美的统计数字说,巴勒斯坦犹太人目前自给自足率只有40%,每年单从美国流入巴勒斯坦用来资助犹太人的资金就有550万美元,若将这一资助停止,不难发现会发生什么。希提列举一组数字说,1926年至1927年,巴勒斯坦的进出口比例高达5:1,1937年至1939年间该比例已达到2:1,由此可见巴勒斯坦的经济不平衡状况。(27)Ibid.希提列举这些数字旨在说明巴勒斯坦并非像爱因斯坦和卡勒所说的那样繁荣。
爱因斯坦和卡勒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设惠及阿拉伯人,希提对此则不以为然。希提举出1929年8月犹太代办处在瑞士苏黎世签订的章程,该章程第2条规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取得的土地是犹太民族不可分割的财产”;“在犹太代办处承担或促进的工作或事业中,应雇佣犹太工人,这应被视为原则问题”。希提就此认为,这些规定“是对阿拉伯工人的永久抵制”。(28)“Palestinian Arabs Descended from Abraham, Says Dr. Hitti”.
针对爱因斯坦和卡勒关于犹太人的建设出于和平目的、不会危害阿拉伯人利益的说法,希提列举事实,作了如下反驳:“爱因斯坦和卡勒的声明……明显不符合最近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也不符合这些事实:走私军火、制造手榴弹和爆炸事件。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言人齐夫声称要‘让阿拉伯人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沙漠’;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茨曼(Chaim Weizmann)称,要‘促使’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转移出去;本·霍因(Ben Horin)更直白,他在《纽约时报》上作了整版宣传,声称要把巴勒斯坦以及外约旦的阿拉伯人转移到伊拉克,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腾出空间,从而一举解决问题。”(29)Ibid.基于这些事实,希提嘲讽道:“军事犹太复国主义的真实面貌与我的这两位杰出的邻居所理解的大相径庭。”(30)“两位邻居”指爱因斯坦和卡勒,当时希提和两人都工作和居住在普林斯顿。
希提上述所言大体属实,当时由于阿犹冲突持续恶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普遍主张坚决斗争,并积极发展犹太武装力量,以对抗阿拉伯人,并对英国人发动恐怖袭击,以保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设事业。在激烈的气氛中,甚至有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将阿拉伯人转移出巴勒斯坦。(31)Chaim Simons, Herzl to Eden: A Historical Survey of Proposals to Transfer Arabs from Palestine, 1895-1947, Kiryat Arba: Nansen Institute, 1994, p. 44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希提所论侧重于事实本身,即犹太人到底有无使用暴力手段;而爱因斯坦和卡勒所言犹太人“不诉诸权力”侧重于说明犹太人不会无端使用暴力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侧重于说明动机如何。从这一点来看,论辩双方的矛头所指并不相同,也就很难分出是非曲直。
希提援引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建立犹太国的理念指出,冷静和务实的犹太人认识到,正是基于军事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些行为,反犹主义才有了口实。希提最后以阿拉伯人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并愿意同犹太人和睦相处的观点来作为结束,他说:“阿拉伯人的自身利益和未来福祉要求他们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这些新来者进行合作。直到最后,一个新的巴勒斯坦将崛起,并配得上它的尊名和宝贵遗产。”(32)“Palestinian Arabs Descended from Abraham, Says Dr. Hitti”.希提的此番回应再次表明了他反对建立犹太国的愿望,也表达了和平友好精神。但他对犹太国的态度表明,他仍在误解犹太国的具体内涵,以为犹太人要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独占的国家,并以驱逐阿拉伯人为代价。
可以看出,在“历史优先权”之外,希提此次回应重在就爱因斯坦和卡勒所说的现实问题进行反驳。在否定爱因斯坦和希提关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设属于积极作用的问题上,希提所运用的例证数字本身基本符合事实。由于他给出的解释是站在那些反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阿拉伯人的立场上,势必引发爱因斯坦和卡勒的重新反驳。实际上,爱因斯坦和卡勒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提对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观点的描述也基本符合爱因斯坦和卡勒的思想取向。他对阿犹和平合作的肯定和倡导也是爱因斯坦和卡勒的主张,代表了阿犹民族中理性的声音。在分歧之外,双方也有共鸣,但分歧无疑远大于共鸣。
四、 重申历史权利和现实合法性: 爱因斯坦和卡勒的再度回应
在希提上文发表一周后,1944年4月28日,爱因斯坦和卡勒在《普林斯顿先驱报》上发表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要好过在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署名文章,再次反驳了希提的主要观点。他们指出,希提声称要戳穿真相,其实不然。(33)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Arabs Fare Better in Palestine Than in Arab Countries”.
爱因斯坦和卡勒首先讨论了历史优先权问题。两人认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据说源于在亚伯拉罕移居迦南之前就定居在迦南的人中间,而阿拉伯人在宗教传统上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这样一来,就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种族上同其他阿拉伯人分割开来了。不过,这些种族系谱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而完全是假设,极不确定。正如《圣经》中描述的,许多人在千禧年初涌入巴勒斯坦,许多移民混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阿拉伯人很难说是早期迦南人的后裔。由此,两人再次重申之前的观点:“在地球上的实际分配以及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上,这种优先权问题毫不重要。”(34)Ibid.
至于阿拉伯人继多支力量后征服巴勒斯坦的历史,爱因斯坦和卡勒同意希提所言。但两人指出,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征服已被宣称为一场“圣战”,由此确立了阿拉伯人对那片土地的控制诉求。甚至到了20世纪,这种说辞还诱导希提表达了如下观点:“巴勒斯坦是经过一次伊斯兰圣战后,由真主安拉赐给阿拉伯人的。所以,对穆斯林来说,放弃对巴勒斯坦的要求等于背叛了他们的信仰。”爱因斯坦和卡勒重申,在“圣战论”主导下,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征服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犹太人对家园的权利。
爱因斯坦和卡勒继而指出,希提关于犹太人后来离开巴勒斯坦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并非仅仅是“零星微弱的民族生活”。两人提出的论据是,在“巴比伦之囚”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第二个伟大的时代和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开始了。一方面,犹太人编撰了传统经典《巴比伦塔木德》;另一方面,犹太教孕育了基督教。两人据此认为,犹太社团依然不间断地在巴勒斯坦延续了下去,持续了千百年。(35)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Arabs Fare Better in Palestine Than in Arab Countries”.
爱因斯坦和卡勒列举了如下史实来论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存在的延续性:10世纪,阿拉伯作家穆卡达西曾抱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数量太多;从15世纪起,上加利利的萨费德市成为繁荣的犹太文化中心,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在那里讲授和走向完善,直到17世纪犹太人才被土耳其人赶走。此外,在遭到驱逐后,西班牙犹太人来到他们的故土巴勒斯坦避难;8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弥赛亚运动(Messianic Movement)旨在解放和重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活;而且,在全世界,不断有犹太人在感到大限将至时来到圣地朝圣,一直到去世后葬在那里。所以,爱因斯坦和卡勒总结认为,犹太人始终在巴勒斯坦生活,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存在从未中断。(36)Ibid.
应该说,爱因斯坦和卡勒所言阿拉伯人无法确定为早期迦南人后裔的说法更符合现代历史学的叙述。“巴比伦之囚”后,犹太人失去了在巴勒斯坦的政治主导地位,故希提所说犹太人不再拥有巴勒斯坦的控制亦属历史事实。爱因斯坦和卡勒没有否认这一点,他们不同意希提有关“希伯来人来了又走了,本地人留了下来”的说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说法不仅忽视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没有中断的史实,而且忽视了犹太人在遭受政权灭亡的命运后仍然在巴勒斯坦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史实。虽然在被大规模逐出巴勒斯坦并开始流散全世界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人数已经寥寥,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离开巴勒斯坦。据史料记载,在整个中世纪,巴勒斯坦仍生活着少量犹太人。(37)Fred Skolnik, ed., Encyclopaedia Judaica, New York: Keter Publishing House, 2007, p. 385.10世纪时在耶路撒冷定居的犹太人并不多,爱因斯坦和卡勒所引穆卡达西之说似显夸张。然而,15世纪萨费德的确是当时犹太文化在巴勒斯坦的一大中心,(38)Lawrence Fine, Safed Spirituality: Rules of Mystical Piety,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Mahwah: Paulist Press, 1984, p. 2.在1492年被西班牙国王驱逐后,当地的部分犹太人来到了巴勒斯坦。(39)Alisa Meyuhas Ginio, Jew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fter 1492,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245.种种事实表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文化创造一直延续着。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上,希提更多是从政治控制的角度来否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继而否定犹太人在历史上对巴勒斯坦的权利诉求,而爱因斯坦和卡勒则从文化生活的视角来反驳希提的观点。
希提把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称作“和平的入侵”和“缓慢的征服”,爱因斯坦和卡勒针锋相对地援引英国皇家巴勒斯坦调查团在1936年底的调查结论,来再次论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设对阿拉伯人的积极影响。英国方面的调查认为,犹太资本的进入繁荣了巴勒斯坦的工业和种植业,尤其是柑橘业;得益于犹太人的建设,阿拉伯工人的就业率提高了;犹太人建立的医疗卫生系统,提高了阿拉伯人的福利水准。(40)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Arabs Fare Better in Palestine Than in Arab Countries”.基于这些事实,爱因斯坦和卡勒不同意希提关于巴勒斯坦社会经济现状的负面说法。两人列举上述调查报告意在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在工农业、医疗和公共服务业等领域的建设,使阿拉伯人的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改善是确凿的事实,这已被英国官方的报告所证实。在犹太人的建设下,巴勒斯坦的发展进步并非如希提所言只是“涂抹胭脂”的假象。
希提谴责犹太代办处关于必须雇佣犹太工人的规定是在抵制阿拉伯工人,爱因斯坦和卡勒反驳说,犹太代办处旨在促进犹太事业发展,对犹太工人的惠顾理所应当,但这远不是为了抵制阿拉伯人。两人举例说,大量阿拉伯工人在私营的犹太农场和工厂工作;巴勒斯坦的人均工资水平是叙利亚的两倍多,是伊拉克的三倍。通过比较阿拉伯国家的上述状况,爱因斯坦和卡勒说,“伊拉克的阿拉伯农民非常穷”,他们引用美国土壤学家沃尔特·罗德米尔克(Walter C. Lowdermilk)的观点——后者在对伊拉克和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后指出,在伊拉克这样“人口稀少却潜力巨大的富饶土地”,其状况要比“人口众多的中国”还要恶劣。两人援引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厄内斯特·梅因(Ernest Main)的报道说,“阿拉伯农民和苦力阶层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支出不超过一便士……这个国家可能有两百万人处于这样的生活水平,可以想象他们的购买力如何,他们能缴纳多少税。”两人还援引了英国托管当局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爵士关于外约旦农民处境的说法:“由于纳税者的贫穷,政府只能靠补助金运转。”爱因斯坦和卡勒进一步指出,如果说阿拉伯农民和工人在巴勒斯坦没有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那么很难理解如下事实:一方面,1933年~1936年,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外约旦甚至阿拉伯沙漠的超过3万阿拉伯工人移民到了巴勒斯坦;另一方面,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移民是来自巴勒斯坦的两倍。(41)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Arabs Fare Better in Palestine Than in Arab Countries”.
爱因斯坦和卡勒批评说,希提教授对巴勒斯坦经济不能自给自足的指责是苛刻的。两人指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经济产业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他们购买的土地价格远远超过市值;虽然巴勒斯坦仍存在机器、肥料和原材料缺乏的困境,但“就连希提教授也不得不承认,1927年~1937年,进口上涨了50%”。对巴勒斯坦的前景,爱因斯坦和卡勒援引了英国学者查尔斯·沃伦爵士的观点,后者在1875年就指出:“如果巴勒斯坦有良好的管理,以提高人民的商业生活为目标,那么他们的经济就可以增长10倍,而且还有空间。”两人还引用了英国军官“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观点,后者曾说:“巴勒斯坦古时是个相当好的地方,也能很容易再次变好。犹太人越早在那里进行开垦越好,他们的殖民地是个美好的地方。”两人指出,“阿拉伯的劳伦斯”是阿拉伯人最要好的朋友,肯定不会有偏见。(42)Ibid.
依笔者所见史料,爱因斯坦和卡勒援引罗德米尔克等人的说法出自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和国联的调查。(43)American Palestine Committee, ed., Pamphlets on the Palestine Problem, American Palestine Committee, 1944, p. 22; League of Nations, ed., Permanent Mandates Commission, League of Nations, 1931, p. 105.若这些调查所言大体属实,那么说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设的确促进了当地阿拉伯人经济的发展。
阐述经济问题之后,对于希提犀利抨击的犹太人中的暴力行为,爱因斯坦和卡勒表示:“希提教授的说法中也许仅一点我们可以同意,即犹太人中间也有顽固派和恐怖分子——虽然犹太人中的这部分人的比例要远远比其他民族少。我们不会掩盖或谅解这些极端分子。他们是痛苦经历的产物。在当今世界,只有威胁和暴力才起作用,而公正、真诚和深思熟虑却得到最坏结果。”(44)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Arabs Fare Better in Palestine Than in Arab Countries”.
在这里,爱因斯坦和卡勒明确否认犹太人使用暴力的正当性,但又指出,在当今时代,这种行为实属无奈。在两人看来,犹太人使用暴力或有过度之嫌,但不如此便无法保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存和发展。从犹太人中的“恐怖分子”比例较低这一观点来看,爱因斯坦和卡勒或意在说明,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已属极为克制,并无根本不妥。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转移”阿拉伯人的言论,爱因斯坦和卡勒以魏茨曼为例来纠正希提的指控,两人为魏茨曼辩护称,魏茨曼从未使用驱逐手段来威胁阿拉伯人,希提引用的话应该是如下表述:“所有公民不分种族和信仰,都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此外,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内部事务享有完全的自治。如果有任何阿拉伯人不愿留在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将给予他们一切帮助,使其转移到众多阿拉伯大国中的其中一个。”(45)Albert Einstein and Eric Kahler, “Arabs Fare Better in Palestine Than in Arab Countries”.
将阿拉伯人“转移”出巴勒斯坦的提议早已有之,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1895年时就在日记中说要将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口移民,并在新的定居地为其提供生计。(46)Chaim Simons, Herzl to Eden: A Historical Survey of Proposals to Transfer Arabs from Palestine, 1895-1947, Kiryat Arba: Nansen Institute, 1994, p. 13.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在1914年提出购买叙利亚阿勒颇等处土地,使因犹太人购买而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能重新定居。(47)Etan Bloom, Arthur Ruppin and the Production of Pre-Israeli Culture, Leiden: Brill, 2011, p. 303.1940年,犹太民族基金会的约瑟夫·魏茨(Joseph Weitz)提出将所有阿拉伯人转移到临近的阿拉伯人国家,并为此专门设立巨额资金。(48)Moshé Machover,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Chicago: Haymarker Books, 2012, p. 204.至于魏茨曼的相关言论,笔者并未找到爱因斯坦和卡勒上述转引魏茨曼的观点,就笔者所见,魏茨曼关于“转移”阿拉伯人的言辞中并无暴力驱逐阿拉伯人的内容。(49)Nur Masalh, Expulsion of the Palestinians: The Concept of “Transfer” in Zionist Political Thought, 1882-1948,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92, pp. 31-35, 151, 155.至少从字面意思来看,当时多数犹太领导人都反对暴力驱逐阿拉伯人。
五、 结语
在爱因斯坦和卡勒的回应文章发表后,从公开的史料看,希提并无再回应,这场论辩也就此落幕。从爱因斯坦和卡勒与希提的文字交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历史优先权”问题,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道义”问题,其实质是拥有巴勒斯坦的“合法性”属于哪一方。论战双方都从历史、宗教、现实政治和经济社会等方面来为己方辩护,但显然,谁也无法说服另一方。
从时代背景看,这场辩论反映了巴勒斯坦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动。从国际局势来看,辩论之时,二战已进入尾声。战争结束后,其他国家面临的是恢复重建,而犹太人遭屠杀的事实则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从而使整个民族遭受的厄运不再重演。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勃兴的推动,此时他们的民族理想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然而,双方的民族主义愿景存在着冲突和强烈的互不信任,两个民族在心理上已形同陌路。英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不断移民和开垦建设存在“自然而然的恐惧”。(50)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p. 234.正如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弗拉迪米尔·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所说,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自然的,每个民族都反对外国人移入和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拓殖民地,无论动机多么高尚”,他的结论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不存在误解,只有天生的冲突。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犹太人达成协议断无可能”(51)Ibid, p. 257.。所以,无论犹太人的宣传和实际做法如何,阿拉伯人都很难接受。而在犹太人看来,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建国权利的否定意味着,在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设定上,犹太人只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里的一个民族。而在当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人口对比上,在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中,犹太人将是一个少数民族。然而,犹太人成为少数民族是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安排与犹太人在欧洲各国的处境毫无分别,将再次使犹太人处于受迫害的危险境地。(52)Ibid.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互不信任在此次论辩中也得到了明确体现。希提在否定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同时,并没有清楚传达其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前景的看法。爱因斯坦和卡勒有充分理由认为希提是在否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合法性,而此种合法性正是维护巴勒斯坦乃至全世界犹太人生命和尊严的基本保障,尤其是在犹太人遭受纳粹种族灭绝亟需在巴勒斯坦寻求安全避难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在希提那里,这种合法性却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希提对爱因斯坦和卡勒观点进行批评的基本认识前提在于,他认为巴勒斯坦自古以来属阿拉伯人所有,犹太人是外来者,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口数量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是在抢夺阿拉伯人的土地。既然犹太人的行为属外来者对本土居民的抢夺,爱因斯坦和卡勒关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设是出于和平目的的说辞便难以令希提信服。在希提看来,无论爱因斯坦和卡勒如何美化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设成就,如何力陈巴勒斯坦在解决犹太人生存问题上的重要性,都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在道义上也显得苍白无力,这或许是他未再对爱因斯坦和卡勒作反驳的原因。可见,双方的立场差异巨大,无论在历史权利问题上,还是在巴勒斯坦现实经济社会状况问题上,都很难说服彼此。论战双方的理念差异基本上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观点分歧,双方在论战中无法达成最大程度的一致,正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天然矛盾”无法调和一样,这也从学术争鸣的层面预示着未来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难解。
爱因斯坦、卡勒和希提并非完全蛰居书斋的学者,他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声体现出对公共事务“忍不住的关怀”,但他们很多时候是通过报纸和著述而非参与政治来表达观点,缺乏将此种论辩引向更广阔舆论场的影响力。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巴勒斯坦已被汹涌澎湃的阿犹民族主义浪潮所裹挟,“谁拥有巴勒斯坦”这种夹杂着神话、历史和现实政治纷争的论辩也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当阿犹矛盾很快演化为旷日持久的冲突乃至战争,学术争论也就被兵戎相见所取代。因此,这场由阿犹知识分子发起的大讨论更多地是知识界内部的争论,并很快湮没在阿犹—阿以冲突的宏大叙事中,最终仅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成为日后可能被发掘的“沧海遗珠”。
阿拉伯和犹太知识分子的这场论辩虽无果而终,但双方在往来交锋中所呈现的观点和论据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到了今天。实际上,“谁拥有巴勒斯坦”一直都是触及巴以问题的核心关切所在,其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巴以政坛和民间舆论场中,一直存在要求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独占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极大地制约着巴以和平进程。从现代国际政治理念出发,现代巴勒斯坦既不只属于阿拉伯人,也不只属于犹太人,而是阿犹两个民族共同平等拥有,这样的政治安排合乎阿犹民族历史和国际法准则。但在爱因斯坦、卡勒和希提的时代,这样的认识无法平衡阿犹民族主义之间的剧烈碰撞,由此也导致论辩无果而终。这样的结局也从反面说明,承认阿犹各自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地位,遵循联合国有关决议,将各自的民族权益从族群神话和强权政治的窠臼中剥离出来,摒弃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在此基础上充分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合理诉求,是缓和与解决巴以冲突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