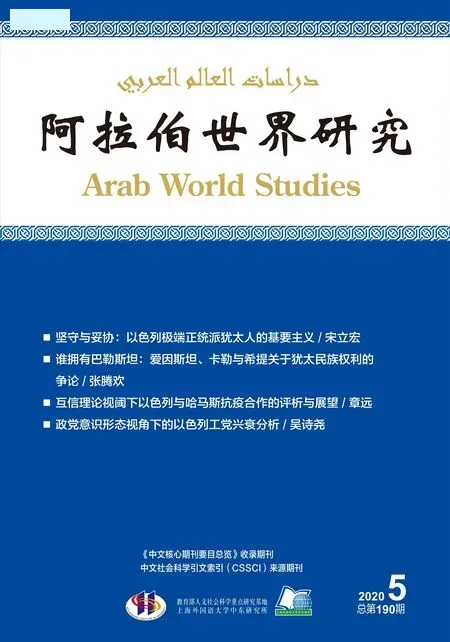坚守与妥协: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要主义*
宋立宏
一、 以色列的宗教复兴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虽有传统犹太教与神的应许之地的联系作为基础,但它本质上是世俗的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精神领袖赫茨尔(Theodor Herzl)对传统犹太教近乎一无所知;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等以色列建国先驱不笃信犹太教,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塑造出的以色列社会的中流砥柱,是以与传统犹太教的断裂来界定自我甚至引以为豪的。但这种情况眼下正在发生改变,宗教已重新回到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中,并持续发酵。(1)参见王宇:《犹太教在以色列的社会影响力上升》,载《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4期,第62-68页。自20世纪70年代起,教俗之间的矛盾和博弈已渐渐成为以色列内政中引人瞩目的问题,并愈演愈烈。
当今全球83.9%的犹太人口集中在以色列和美国两个国家,理解当今犹太教的整体面貌,尤其是犹太教在以色列的基本特点,首先要了解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和美国信教的犹太人之间的差异。(2)Sergio Della Pergola,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2018,” in Arnold Dashefsky and Ira M. Sheskin, eds.,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18, Volume 118, Dordrecht: Springer, 2018, pp. 361-452.在美国的犹太精神生活中,经过现代化冲击而赞成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即致力于传统犹太教和现代性相调适——的犹太教教派(如改革派、保守派等)是主流,这些教派充当了传统犹太教和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但这些教派得不到以色列国的承认,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几乎都是正统派。传统犹太教与以色列世俗社会一旦发生冲突,便会表现得十分激烈。
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迷恋传统,将传统作为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但一般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最多只是接受别人皈依;另一派则视自己为传统的守卫者,摒弃以官僚化、理性化、技术化、两性平等、共有价值观的弱化、个人信仰和性取向的多元化为特征的当代西方世俗文化,且坚持以自己的信念改变甚至统治世界。前者是所谓的现代正统派(datiim);后者常被称作“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但该词既不来自犹太教传统,在日常使用中还带有贬义,故如今一般用希伯来文称他们为“哈瑞迪”(haredim,单数是haredi)。(3)“哈瑞迪”是中性词,出自《以赛亚书》(66:2; 66:5),意为因神的话语而“战兢”的人。需要指出,“哈瑞迪”往往是外界对这些犹太人的称呼,他们有的更愿意用意第绪语称自己是“犹太人”(yidn)或“品行端正的犹太人”(erlicher yidn),意即他们才是遵循托拉及其诫命的真正的犹太人。历史研究表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匈牙利,然后散布到东欧和全球。参见Michael K. Silber, “The Emergence of Ultra-Orthodoxy: The Invention of a Tradition,” in Jack Wertheimer, ed., The Uses of Tradition: Jewish Continuity in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 1992. pp. 23-84。就着装而言,前者身穿普通人的衣服,男性头顶编织小帽(kippahscrugah);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男性蓄胡子、鬓角处留着一绺头发、穿白衬衫和黑色外套、戴黑色便帽或礼帽,已婚极端正统派犹太女性则剃掉头发,戴着假发或头巾,身穿遮盖大部分身体的朴素衣服。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都奉行所谓的“基要主义”(4)“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最初源自19世纪末的美国新教,在中文里又译作“原教旨主义”,现在广泛用于指称伊斯兰教保守派别。,学界对“基要主义”的界定向来众说纷纭。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布鲁斯·劳伦斯(Bruce Lawrence)的界定堪称妥帖:“基要主义是对宗教权威整体上的、绝对的确定,不允许批评和删减;它通过集体需求的方式来表达,即源自经典的具体教义和道德诫命应得到公开认可和依法实施。”(5)转引自[美〗撒母耳·海尔曼:《犹太人与基要主义》,载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3-204页。为便于学术讨论提出的基要主义概念具有理想色彩,并非每个活生生的基要主义者都能完全符合其描述。(6)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The Fundamentalism Project: A User’s Guide,”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 Observ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viii-x; Richard T. Antoun, 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ism: Christian, Islamic, and Jewish Movements, 2nd edi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p. xii.在以色列的语境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都是基要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基要主义者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例如,已解散但影响尚存的“信仰者集团”(GushEmunim)的成员是基要主义者,但基本不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主体更符合海尔曼所界定的“静态的犹太基要主义”。(7)与此相对的是“活跃的犹太基要主义”。详见[美〗撒母耳·海尔曼:《犹太人与基要主义》,第206-212页;Samuel Heilman, “Quiescent and Active Fundamentalism: The Jewish Cases,”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s: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173-196。本文研究的是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要主义。
以色列目前有112.5万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5%,人数虽不占优势,但该群体超高的生育率使其年增长率达到约4%。过去15年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妇女人均生育子女数达7个。该派人口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20岁以下年轻人占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总人口的60%,而同年龄段的其他派别在以色列犹太人口中只占30%。(8)Lee Cahaner and Gilad Malach, Statistical Report on Ultra-Orthodox Society in Israel, 2019: Population,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https://en.idi.org.il/haredi/2019/?chapter=29390, 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事实上,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整个犹太世界内部在过去数十年间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基要主义者尽管人数不多,但其影响现代正统派见解和价值观的能力却日益增强。以色列现代正统派在很大程度上已沉湎于基要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将在古老的犹太家园(约旦河西岸)定居视为最重要的宗教诫命和笃信犹太教的必要条件。相应地,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社会影响力日益上升,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在世俗生活的腐蚀下摇摇欲坠。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在反击,而且做得相当成功。
中国学界已关注到以色列相对活跃的犹太基要主义,如“信仰者集团”发起的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运动、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的政党活动及其暴力行为和拒服兵役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等。(9)汪舒明、缪开金:《信仰者集团崛起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第47-52页;冯基华:《宗教政党对以色列政局及阿以冲突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6 年第5期,第53-58页;王彦敏:《以色列政党政治演变中宗教政党角色地位的变化》,载《历史教学》2010年第24期,第50-58页;王彦敏:《论以色列沙斯党的崛起和发展》,载《理论学刊》2012年第11期,第88-92页;王宇:《在义务之外——试析以色列哈瑞迪犹太教徒的兵役问题》,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2期,第39-45页;王宇:《现代犹太宗教暴力的根源、特点及影响》,载《学海》2017年第3期,第183-190页;欧振华、傅有德:《信仰者集团与西岸犹太宗教-政治定居点问题研究》,载《山东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122-130页。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相对静态、保守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要主义,着重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构成与分化、作为基要主义者的特点与价值观、兴起的动因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自我调适等国内学界尚缺乏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
二、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历史源流、文化特征与政党政治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中国媒体和学界常被表述成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教派,这或许是由于关注点集中在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以色列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在这种视角下,他们似乎成了一个同质的社会群体,但这是一种外部视角。从内部视角来看,该群体更像是一种社会类型(social type),而不是一个教派(sect),或者说是由多个教派组成的。该群体内部在历史渊源、宗教特征和政治诉求方面差异显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缺乏一个中央机构来协调他们统一行动,呈现为诸多各自为政的小群体,只因都自视为犹太传统的捍卫者而松散地联系起来。在理解他们的共性之前,须先了解该群体内部的多元与差异,否则易混淆他们的身份与立场。
从内部构成来看,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分为三大群体。一是哈西德人(hasidim,意为“虔诚者”)。作为当前抵制世俗文化最强烈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哈西德人缘起于18世纪后半叶一些拥有个人魅力的犹太人在东欧尤其是波兰东南部发起的宗教运动。该运动主张,真正的虔诚首先应表现为忘我祈祷,而不是通过埋头苦读获得渊博学识,也不是一丝不苟地恪守宗教仪式。他们在东欧各犹太小镇自立门户,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形成各具特色的知识体系。这些宗教领袖被门徒称作“瑞比”(rebbe)(10)又称作“admor”,这是希伯来文“我们的主人、老师和拉比”的首字母缩写词。,他们成功将各自的追随者团结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紧密联系的小社会,接受信徒的效忠和尊敬,这构成了哈西德运动延续至今的标志性特征。瑞比能获得这种权威,是因为门徒相信他具有与神交流的超凡灵性,可以充当他们与神沟通的中介。但这种对各自瑞比的忠诚也是造成哈西德人内部分裂的根本原因。今天的以色列哈西德人内部教派林立,其中戈尔派(Ger)人数最多,维兹尼茨派(Vizhnitz)和贝尔兹派(Belz)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11)哈西德人内部各教派的名字都来自该派原来居住的东欧小镇的名字。关于以色列哈西德人的情况,参见David Biale et al., Hasidism: A New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644-651, 706-739。关于哈西德人的物质文化,参见Ester Munchawsky-Schnapper, A World Apart Next Door: Glimpses into the Life of Hasidic Jews, Jerusalem: The Israel Museum, 2012。
二是所谓的“反对者”(mitnaggedim)。这个沿用至今的历史术语所指代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最初正是因为激烈反对哈西德人重灵修而轻宗教经典学习的倾向而得名。反对者堪称犹太文化精英,始终强调传统的《塔木德》学习——其发展在立陶宛及其周边地区达到高峰,这里还是反对哈西德人的心脏地带。哈西德人与其反对者之间虽存在竞争关系,但在一个方面趋同:反对者的拉比(被门徒称为“拉夫”[rav〗)原先靠学识建立权威,但这种学识赋予拉夫个人魅力,渐渐使拉夫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和瑞比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相差无几。虔敬地追随一位“大人物”(gadol)即权威拉比的观念,于是在这两个群体中都牢固地建立起来。(12)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Religious Jews: The Case of the Haredim,”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 Observed, pp. 209-210.而随着现代世俗文化这一“共同敌人”的兴起,哈西德人与反对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最初势不两立的对立已大大弱化,即使两者在人际关系和政治倾向上的隔阂依然存在。(13)这是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内部分化的重要历史原因,详见下文。如今“反对者”一词已不够贴切,“立陶宛人”(Litvishe/Lita’im)这个中性词被更多地用以指代这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14)“立陶宛人”一词有局限性。历史上立陶宛也有哈西德人,但当地很多犹太人不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相对而言,立陶宛人的世界观没有哈西德人那么封闭。
以上两个群体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就族性而言,都是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m),即祖上来自法国北部、德国和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在日常会话中更多地使用意第绪语,希伯来语作为“神圣的语言”则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就政治表现而言,两者在2019年以色列大选中都集结在“托拉犹太教”(YahadutHatorah,英文为United Torah Judaism)这一由哈西德人诸教派控制的“以色列联盟”党(AgudatIsrael)(15)中文里常译为“以色列正教党”,但这个译名无法体现该党过去和现在的实质(详见下文),本文采用直译。与立陶宛人的“托拉旗帜”党(DegelHatorah)组建的联合政党之内,这表明哈西德人和立陶宛人这两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彼此之间在今天仍是泾渭分明的。
以色列联盟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最重要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政党。它最初是欧洲的正统派犹太人于1921年在西里西亚成立的联合会,从一开始就非常松散,既有哈西德人及其反对者,又有现代正统派,甚至包括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将这些形形色色的正统派犹太人团结起来的,仅仅是他们共同反对传统犹太教的改革者。该联合会曾在波兰以政党身份加入议会,积累了政治经验,至以色列建国前发展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运动,在耶路撒冷、纽约和伦敦设有三个中心。(16)“以色列联盟”运动曾于1941年在上海成立分支,参见[美〗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许步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83页。以色列建国后,该联合会成为一个政党,宗旨是“对于以色列地上的全体以色列人民,要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他们团结在托拉的统治下”(17)该运动领袖艾萨克·布鲁尔(Isaac Breuer)语,转引自Menachem Friedman, “Agudat Israel,” in Fred Skolnik and Michael Berenbaum, eds., Encyclopaedia Judaica, 2nd edition, Volume 1,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7, p. 505。引语中的“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是犹太传统对巴勒斯坦的称呼,很多坚持传统的犹太人只使用这个术语,而不会使用“以色列国”(Medinat Yisrael),以此表明他们对待世俗政权的反对态度。。虽然以色列联盟党后来完全成为一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政党,但其最初的成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正统派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977年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上台后,该党首次加入联合政府,(18)在以色列国首次议会选举时,以色列联盟党曾与其他正统派团体组成一个“联合宗教阵线”(United Religious Front)参与政府工作,到1953年时退出。在以色列的联盟政治中成为执政党拉拢的对象。现实政治要求其成员必须在政策问题上统一立场,原有的内部分歧遂变得日益难以弥合。至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联盟党内部便出现了分裂。
1988年选举前,身在纽约、一生从未去过以色列的卢巴维切派(Lubavitch)(19)该派也被称为“哈巴德”(HaBaD),是希伯来文“智慧、理解、知识”三词的首字母缩写词。哈西德瑞比梅纳赫姆·施尼尔森(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1902~1994)号召他在以色列的门徒和支持者给以色列联盟党投票,其中一个原因是挑战立陶宛人的精神领袖以利以谢·沙赫(Eliezer Menachem Shach, 1899~2001)拉比。沙赫此前阻碍施尼尔森在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中广有影响的报纸《通报者》(Hamodia)上付费刊登自己的教导,并要求在以色列联盟党内清除卢巴维切派的影响,但没有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戈尔派哈西德瑞比的支持。沙赫遂带领自己的党羽退党,另创立托拉旗帜党参选,由此招致施尼尔森对以色列大选的干预。这次分裂可看作哈西德人和立陶宛人的历史积怨在新时代的重新浮现,以色列联盟党此后便成为哈西德人的政党(20)并非所有哈西德教派都加入了这个政党。,至今如此。托拉旗帜党今天是非哈西德的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为确保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政治影响,以色列联盟党和托拉旗帜党自1992年起联合成托拉犹太教党参加以色列议会选举。
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中的第三个群体来自所谓的塞法迪人(Sephardim),这是一个与阿什肯纳兹人相对立的术语,指祖上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但在15世纪末遭驱逐而流散到北非、奥斯曼帝国领地、美洲、意大利和荷兰的犹太人。然而,塞法迪人的这种经典内涵并不适用于以色列的这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他们主要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从北非(尤其摩洛哥)、阿拉伯半岛、伊朗、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来的移民及其后代。这样,他们在以色列又常常被称为“东方犹太人”(Mitzrahim)。东方犹太人与塞法迪人在以色列的语境中往往混用。
来到以色列这个中东的西方飞地后,东方犹太人遇到很大的文化冲击,但这些冲击是在一个犹太国家中发生的,与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在欧洲经历过的与西方的现代性和同化作漫长斗争的历史过程有着本质区别。因此,东方犹太人在毫不含糊地忠于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使他们可以在安息日早晨参加完严格遵照传统的安息日宗教仪式后又能在当天下午现场观看足球比赛;使他们可以怀着近乎同样崇敬的心情看待一位神圣拉比的祝祷和一位政治领袖的行动,但却不会被表里不一的感觉所困扰。(21)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Religious Jews: The Case of the Haredim,” p. 245.这在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东方犹太人的文化保守性更多是以族群文化为导向,强调社群团结和家庭纽带,对待宗教的立场较前两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更富弹性。
初来乍到的东方犹太人完全处在以色列社会的边缘,无论政治和教育都依附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既有的体制。东方犹太人中文化精英的教育最初由立陶宛人控制,少数人就读于立陶宛人开办的经学院(yeshiva),更多人则在专门为东方犹太人开办但由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执教的经学院里接受教育。东方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基本上都接受立陶宛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拉夫的宗教权威,自然成为以色列联盟党的支持者。党内的阿什肯纳兹领袖却歧视他们,不允许他们有代表权;普通东方犹太人信徒则勉为其难地给非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投票。1977年,在东方犹太人选票的支持下,代表传统主义的利库德集团上台,打破了世俗的工党自建国以来对以色列政坛的垄断。人数已占以色列犹太人口多数的东方犹太人看到了通过政治手段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1984年,代表东方犹太人利益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沙斯党(Shas)(22)即希伯来文“Shomrei Torah Sefarad”(守卫托拉的塞法迪人)的首字母缩写。成立,带走了以色列联盟党中东方犹太人的选票。
沙斯党的精神领袖是生于巴格达的俄巴底亚·约瑟(Ovadiah Yosef, 1920~2013)拉比,曾在1972年至1983年担任过以色列塞法迪人的大拉比这一政府官职。由于宗教复国主义政党(Mafdal)的一项关于大拉比只能担任10年的议案获得通过,约瑟拉比未能如愿续任大拉比一职,感到阿什肯纳兹人背叛了自己,遂有心培植自己的势力。这得到了上文述及的后来创立托拉旗帜党的立陶宛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以利以谢·沙赫的祝福和推动。沙赫亦有自己的考虑,他眼看着以色列联盟党内哈西德人的势力日益壮大,哈西德人对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的影响又与日俱增,便想寻找盟友来对抗哈西德人的势力,于是选中约瑟。沙斯党虽然代表东方犹太人的利益,但最早也受沙赫的控制。1992年,沙斯党在加入拉宾领导的左翼政府之后,才开始摆脱立陶宛人的控制,并最终走向独立。
随着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和托拉旗帜党先后从以色列联盟党中分离出去,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延续至今的格局就此形成。需要注意的是,沙斯党的领导层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但其支持者中有很多非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这是它有别于其他两个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的地方,后两者无论是领导层还是支持者,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2019年以色列大选中,沙斯党和托拉犹太教党共获得16个席位,这使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在以色列政坛稳居第三大集团,是负责组阁的政党必然拉拢的对象。
三、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从严解释文本
哈西德人、立陶宛人(“反对者”)和东方犹太人(“塞法迪人”)三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在族性构成、历史渊源、文化传统、政治表现等方面虽然无法一概而论,但他们作为基要主义者在价值观上却拥有家族性的相似之处,这突出体现在他们对待宗教经典和以色列国家的态度上。
劳伦斯对基要主义的定义表明,基要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相信绝对正确的神圣经典,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文本对当前犹太基要主义者生活的规训功能日益凸显。犹太人号称“书之民”,此语精炼概括出犹太传统以文本为中心的本质。(23)参见Moshe Halbertal, People of the Book: Canon, Meaning, and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但在传统犹太世界,“什么是指导具体生活的犹太文本”却是一个在汉语世界引起广泛误解的问题,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是希伯来语《圣经》,其实不是。除《圣经》前五卷因是启蒙读物以及每年需要念诵一遍而可信手拈来外,很多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圣经》其他部分的了解颇为有限,基本上通过《塔木德》中的《圣经》引文和祈祷书获得,因为传统宗教教育的主干是《塔木德》及后来的犹太法典(24)这和以色列世俗犹太人的宗教教育以希伯来语《圣经》为中心截然不同。正因如此,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托拉犹太教党”译为“圣经犹太教党”、将“托拉旗帜党”译为“圣经旗帜党”并不合适。“托拉”的字面意思为“教导”,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圣经》,尤指前五卷;广义还包括《塔木德》等拉比文本。中文世界目前对《塔木德》全面可靠的介绍,参见[以色列〗亚丁·史坦萨兹:《塔木德精要》,朱怡康译,台北:启示出版社2015年版。,即哈拉哈(halakhah)(25)“halakhah”指拉比律法中被接受的裁决,也指《塔木德》中的律法内容。本文在使用前者的内涵时用直译“哈拉哈”,在使用后者的内涵时用“律法”。但两者的区别有时并不明显。汇编。这些法典将《塔木德》中极其繁琐却往往没有定论的律法讨论提炼成可用于实际生活的指导手册。因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拥护的不是《圣经》基要主义,而主要是《塔木德》基要主义。虽然他们有时也鼓吹《圣经》基要主义,如以色列一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议员曾以宇宙大爆炸论和《创世记》中的描述不符为由,试图阻止议会将一项蜚声国际的物理学奖颁给斯蒂芬·霍金。(26)Avishai Margalit, “Israel: The Rise of the Ultra-Orthodox,” pp. 115-116.日益依赖这类关于哈拉哈的著作来指导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当代犹太宗教社团的显著特征。
这种风气大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可以举个例子一斑窥豹。犹太人过逾越节时必须吃一定量的无酵饼(matzah),即至少吃一个橄榄大的量。但在1940年左右,当时影响最大的《塔木德》学者、哈拉哈权威哈宗伊绪(the Hazon Ish, 1878~1953)(27)此人本名为亚伯拉罕·耶沙亚胡·卡雷利兹(Abraham Yeshayahu Karelitz),“哈宗伊绪”(意为“人之所见”)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1911年)之名,讨论的是最权威的犹太法典《备好的餐桌》(Shulhan Arukh)。在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中,有用某个拉比的某部名作称呼他的习惯。哈宗伊绪1933年移民到巴勒斯坦,后定居在特拉维夫附近的贝内巴拉克(Bnei Brak),此城与耶路撒冷一起构成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聚居的两大中心。对此提出异议,论证了《塔木德》时代的橄榄比现代见到的要大。他据此主张现在过逾越节必须吃到两个橄榄大小的无酵饼才能达到最低量。这种做法在此后短短10年内便流行开来,被信教团体普遍奉行。一个核心犹太节日中一种维持了上千年的习俗在十多年间就被取代,无疑令人惊异。如果再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这种风气转变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了。一方面,历史地看,哈宗伊绪的这个见解其实早在18世纪中叶就有著名犹太宗教学者提出过,但当时只是作为律法运用的一种理论可能性被探讨,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发生在最保守的、素以最坚定的传统捍卫者自居的犹太群体中,这才更令人惊异。就律法问题提出新见解是传统犹太宗教教育的题中之意,但如果从严解释律法并以此挑战久已形成的习俗,会被传统的卫道者和犹太社团领袖指责为挑战前辈哈拉哈权威的裁决,是为大不敬,犹太律法领域有个专门术语管这种对律法的从严解释叫“污蔑先贤”(la’azalha-’av)。尽管如此,在哈宗伊绪的影响下,年轻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愿意把矛头对准律法和习俗领域内被普遍接受的标准。他们在宗教社团内发出批评之声,在自己的生活中将他们那些基于“从严”(le-humrah)解释文本的选择制度化。这种风气渐成气候,以致文本在当前已被赋予极大的权威性。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哪怕久已形成,如果被发现得不到文本的佐证,都有可能屈从于文本的权威。今天,无论在以色列还是美国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区,每逢主要犹太节日,那里的书摊上摆满了如何合乎哈拉哈奉行这些节日的书籍。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书本传统对生活传统的胜利”。(28)Menachem Friedman, “Life Tradition and Book Trad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Ultraorthodox Judaism,” in Harvey E. Goldberg, ed., Judaism Viewed from Within and from Withou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p. 236-238, 249, 250 note 4; Haym Soloveitchik, “Rupture and Reconstr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Orthodoxy,” Tradition: A Journal of Orthodox Jewish Thought, Vol. 28, No. 4, 1994, pp. 68-74, 83.
从严解释文本是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名片,相形之下,东方犹太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对宽容的伊斯兰世界,没有那种惧怕同化的传统,(29)参见宋立宏:《论“顺民”: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法律和社会地位》,载潘光、汪舒明主编:《离散与避难:犹太民族难以忘怀的历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5页。在做裁决时通常会“从宽”(le-kulah)解释犹太律法。最有名的例子是俄巴底亚·约瑟拉比在1973年做出裁决,判定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Falashas)是犹太人,为这些黑人移民以色列提供合法性,而阿什肯纳兹人的大拉比在这个问题上趋于保守。(30)[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9页。更多例子参见Zion Zohar, “Oriental Jewry Confronts Modernity: The Case of Rabbi Ovadiah Yosef,” Modern Judaism, Vol. 24, No. 2, 2004, pp. 132-137。但需要看到,直到今天,东方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精英仍在自觉地模仿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体制与文化,他们中的不少人,如沙斯党的政治明星阿里耶·德里(Arye Deri),仍把儿孙辈送到阿什肯纳兹—立陶宛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或类似教学风格的宗教学校就读,由此暴露出的后者对前者的歧视不时见诸报端。沙斯党内某消息人士表示,东方犹太人的当权派依赖于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当权派和托拉犹太教党,“这些阿什肯纳兹人就这样把我们留在了基层,造成了我们对他们的依赖,在塞法迪领导层中尤其如此”(31)Yair Ettinger, “The Shas Paradox,” Haaretz, January 31, 2008, https://www.haaretz.com/1.4986227, 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就整体而言,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宗教特征上仍具有鲜明的阿什肯纳兹风格。
四、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待国家的态度
文本虽然可以是安顿灵魂的圣所,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毕竟不只生活在文本中,他们还被裹挟在世俗的以色列社会中。以色列国是个现代民族国家,具有中央集权的特征,它需要为全体人民制定一部没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的法律;作为民族国家的以色列也占有领土,它的居民和公民是由他们的居住地来定义的,而不是由他们的种族或原籍决定。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坚持认为犹太国家只能建立在哈拉哈上,否则就无犹太性可言,而遵行哈拉哈是以信奉犹太教为前提的。哈拉哈是犹太人在没有领土的流散语境中得到发展并完善的,而历史上的犹太社团能够凭哈拉哈实行内部自治,需要依赖非犹太人提供公法和秩序。(32)这使得近代以前的犹太社团奉行“所在国的法律就是法律”(dina de-malkhuta dina)的政治原则。参见Michael Walzer, Menachem Lorberbaum, and Noam J. Zohar, eds., The Jewish Political Tradition, Volume I: Author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xxi-xxxi, 431-435;张倩红、胡浩、艾仁贵:《犹太史研究新维度:国家形态·历史观念·集体记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82页。哈拉哈一旦遇到拥有主权的犹太民族国家,便面临前所未有之境,(33)关于哈拉哈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反思,参见Aviezer Ravitzky, “Is a Halakhic State Possible? The Paradox of Jewish Theocracy,” Israel Affairs, Vol. 11, No. 1, 2005, pp. 137-164。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从邂逅缔造出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起就与后者矛盾不断。
因两者对国家和犹太人的定位与设想存在巨大差异,这种矛盾在意识形态上无法调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犹太人只有建立起民族国家,才能结束饱受异族迫害的千年流散,像其他民族那样屹立于世,实现犹太民族的正常化。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则认为,犹太国家只能是以哈拉哈为基础的神权国家,犹太人依然是神的选民,充当着“万国的光”(《以赛亚书》60:3)。现实中的以色列国如果从《塔木德》基要主义的角度予以审视,无疑是亵渎神明。《圣经》里有个模糊的观念,即大卫王的后裔会在一个新时代带来正义。进入罗马时期后,犹太人相信神会在末日复活大卫王的这样一个后裔,打破异教徒的枷锁,恢复《圣经》中的以色列王国,所有流散的犹太人此时都会回到这个王国。犹太教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弥赛亚概念就肇始于后《圣经》时代的这种构建,巴尔·科赫巴(Shimon bar Kokhba)领导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又使这种构建获得重大政治影响。但这次起义失败后,拉比犹太传统开始强调,弥赛亚时代何时来临最终由上帝决定,人只能被动等待,主动去恢复应许之地上的那个王国很容易带来欺骗和谎言,给犹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34)Fred Skolnik and Michael Berenbaum, eds., Encyclopaedia Judaica, 2nd edition, Volume 14, s.v. “Messiah,” pp. 110-114;宋立宏:《犹太集体记忆视域下的巴尔·科赫巴书信》,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7-119页。《塔木德》(BabylonianTalmud, Ketubot, 111a)将《雅歌》里的三句话(2:7; 3:5; 8:4)解释为神向犹太人要求的两条誓言:犹太人不可大规模有组织地移民以色列地(以加速弥赛亚的到来),也不能反抗非犹太人。(35)《雅歌》在犹太传统中被看作是神与犹太人关系的寓言。这三句话的前两句完全一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田野的羚羊、母鹿恳求你们,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吧” [中译文引自《圣经新译本》〗),最后一句与这两句基本相同。除了被拉比们解释出来的这两条誓言,还有第三条誓言,但是是神向非犹太人要求的(即要求他们不过分压迫犹太人。参见Norman Solomon, The Talmud: A Selec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351。相关讨论参见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1-34。这种解读成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宣扬政治上隐忍无为的信条。在他们眼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公然背弃了这两条誓言,妄想用人的主动行为取代神意,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异端邪说。
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初表现为孤立主义,即不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机构往来,在巴勒斯坦新犹太社会的建设过程中避免与之合作。孤立主义是在以色列联盟运动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是该运动的宗教和政治指导原则。此后这条原则遭抛弃,分化随之产生。
一些耶路撒冷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改初衷,坚持认为在巴勒斯坦建造世俗的犹太国家是悖逆神意的大罪。他们于1935年从以色列联盟运动中分裂出来,自1938年起得名“城市卫士”(NetureiKarta)。从匈牙利来的一些萨特玛派(Satmar)哈西德人也加入了这个团体。以色列建国后,“城市卫士”从不参加以色列大选,他们逃避交税,拒绝接受政府的福利和教育津贴——这在他们看来不啻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铸造的“金牛犊”(《出埃及记》32:1-14)。他们还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对全部圣地拥有主权。(36)参见官网Neturei Karta, https://www.nkusa.org/,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
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中的主流在实践中渐渐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妥协与合作,纳粹大屠杀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欧洲犹太人经过二战几近凋零,个别有幸逃到巴勒斯坦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精神领袖(即哈西德人的瑞比和立陶宛人的拉夫)摆脱不了愧疚之情——他们抛下追随者逃离欧洲,而被他们教导不得去巴勒斯坦的追随者却命丧于集中营的焚尸炉。面对这样指责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欲言又止。这种转变的另一个诱因,则是以色列联盟运动以前不注意在巴勒斯坦发展自己的教育机构和经济社会体系,在如何吸收纳粹造成的难民方面便捉襟见肘,需要依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筹款渠道。(37)参见Menachem Friedman,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for Religio-Political Accommodation in Israel: Fallacy and Reality,” in S. Ilan Troen and Noah Lucas, eds., Israel: The First Decade of Independ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57- 59, 72 note 19。1946年,以色列联盟内部就犹太国的建立征求重要拉比们的意见,但内部分歧很大,难以形成明确统一的观点,哈宗伊绪表示不知道也不会干预、不会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38)Menachem Friedman,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for Religio-Political Accommodation in Israel: Fallacy and Reality,” p. 60.
1947年6月19日,本-古里安连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另外两位负责人致函世界以色列联盟,表达即将成立的犹太国对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所处地位的基本立场:一是以安息日(周六)为犹太国的法定休息日,但也允许其他宗教的信徒每周依照各自传统的休息日休息;二是国家机构的厨房必须提供合乎犹太教饮食法的食品;三是尽可能满足宗教人士在婚姻事务方面的需要;四是政府将保障不同宗教教育体系的自治。这就是为以色列建国后处理政教关系定下基调的著名的“现状协议”。(39)对该协议历史背景、措辞的学术分析,参见Menachem Friedman,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for Religio-Political Accommodation in Israel: Fallacy and Reality,” 此文附有协议全文(第78-79页);反映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视角的解读,另见Ruth Lichtenstein, “The History of the ‘Status Quo’ Agreement,” Hamodia, December 31, 2013, https://hamodia.com/2013/12/31/history-status-quo-agreement/, 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现状协议”的名字具有误导性,其内容完全反映不出当时巴勒斯坦盛行的犹太人宗教的“现状”,既没有提及当时安息日的公共交通状况、剧场影院等娱乐设施在安息日能否营业(这两点直到今天都在争议),也没有规定这四个方面如何具体操作,因而只是一个表达意向的提议,恐怕连承诺都算不上,也就毫无约束力。但随着次年独立战争爆发,能否将经学院的学生征召入伍、军队中信教的士兵是否应当守安息日和吃犹太洁食等宗教问题随之凸显,实施协议的紧迫性被提上日程。以色列联盟与政府调停,推动协议内容制度化,在经学院学生和女信徒免服兵役这个日后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上使政府妥协。独立战争让这些恪守传统的人士看清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的必要性。战争结束后,“现状协议”于1949年1月获得正式地位,此时以色列联盟已从一个运动变成了以色列国的一个政党,其命运便和国家分不开了。
以色列联盟党的政治代表巧妙地操纵了以色列议会,能同时对左翼和右翼政党施加压力,从各届联合政府那里获得对其福利事业和教育、宗教机构的慷慨的国家支持,这是他们参与政治的最大动力。换言之,他们一般只满足于捍卫自己作为少数群体的权利。确保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办的经学院的学生免服兵役是该党近来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但参与政治并不代表在意识形态上妥协,他们继续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世俗倾向。为避免在政府做出违反犹太教规定的决定时承担责任,该党议员一般拒绝担任部长。以色列联盟党总体上对国家持一种既不公开反对、也不支持的模糊态度。
沙斯党在崛起后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大致相同,依然不关心外交或经济政策,其主要政治目标是改变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改变东方犹太人长期屈居阿什肯纳兹人之下的社会状况。为此,沙斯党热衷于创建一个能够有效接触并扩大其选民基础的草根社会组织的网络,比如日制学校、农民协会和妇女俱乐部,所以它对国家资金的争夺力度较以色列联盟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俄巴底亚·约瑟拉比鼓励沙斯党议员出任部长职位,允许议员竞选时上电视。此外,与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同,不少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参军,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觉得不信教的犹太人已偏离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应该回归宗教。在他们眼里,宗教与民族性是合一的。(40)Anita Shapira, Israel: A History, Anthony Berris, tran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2, p. 395。此书引用尼西姆·莱昂(Nissim Leon)的观点,认为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在东方犹太人原来居住的伊斯兰国家里,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合流,共同反对由英法殖民政府在当地鼓励的世俗化和同化。尽管与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存在这种差异,沙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要主义仍是毫不含糊的。一位沙斯党部长在评论以色列某市一起火车与校车相撞致死案时说,这是神对该市允许电影院在安息日营业的惩罚。(41)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Religious Jews: The Case of the Haredim,” p. 256.
1967年“六日战争”后,随着以色列占领了所有圣地,犹太人开始在被占领土上建造定居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也开始回应以色列的一个核心政治议程:要不要把占领的土地还给巴勒斯坦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鸽派、鹰派之分。以沙赫拉比和俄巴底亚·约瑟拉比为代表的鸽派,反驳了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后者认为,以色列军队占领圣地标志着弥赛亚时代已出现,因而不能将任何圣地还给非犹太人。(42)尤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参见Ian S. Lustick, For the Land and the Lord: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8;Gideon Aran, “Jewish Zionist Fundamentalism: The Bloc of the Faithful in Israel (Gush Emunim),”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 Observed, pp. 271-275, 288-295。鸽派坚持传统弥赛亚观,认为救世主没有到来。他们认为,犹太人就算定居以色列地,仍与昔日身处流散地没什么区别,没有强过非犹太人,所以还是不要得罪非犹太人。约瑟拉比更是在1989年去开罗会晤穆巴拉克总统,他在返回以色列后表示,只要犹太人仍有流血的危险,就得把土地还给巴勒斯坦人。(43)Israel Shahak and Norton Mezvinsky,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pp. 19-22;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pp. 145-180。约瑟拉比所持立场的根据是犹太伦理和哈拉哈的一条名为“拯救生命”(pikuach nefesh)的原则,它将拯救生命置于所有其他宗教诫命之上。不过,约瑟后来转向政治右翼,反对2005年沙龙政府从加沙地带撤离。以沙赫拉比的劲敌卢巴维切派哈西德瑞比施尼尔森为代表的鹰派,对待新占土地的态度与宗教复国主义者一致。(44)正因如此,今天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或有犹太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城市如希伯伦,常常能看到施尼尔森的头像。然而,研究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权威弗里德曼(Menachem Friedman)认为,所谓的鸽派和鹰派,看似对立,实则拥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截然不同。犹太人的千年流散给他们留下一种思维定式:“非犹太人想要杀死和毁灭犹太人,犹太人之间正当的差异只在于应该如何去应对无时不在的非犹太人的欲望。”当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这种定式有两种不同反应:
沙赫拉比说,既然非犹太人讨厌我们,我们需要保持沉默,需要克制自己,不提醒他们我们的存在,以免激怒他们。施尼尔森说我们应该强硬。这两个答案都源于一个共同的概念,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鸿沟。沙赫拉比不是[寻常意义上的〗鸽派,[后者〗相信人文主义,强调所有人和所有民族之间的根本平等,以及不同的人和民族之间的沟通能力。沙赫拉比却认为,与非犹太人交流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许只能忘记犹太人的存在。施尼尔森宣称,我们应该强硬,以保护自己不受总想毁灭我们的非犹太人的伤害。两人的差异可以用他们对[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条约的态度来说明。他们都说没有和平,也永远不会有和平,因为埃及人想要消灭我们。然而,沙赫拉比补充说,我们应该通过保持沉默来尽量减少犹太人的伤亡。施尼尔森则说,因为和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我们应该拒绝做出任何让步。(45)Israel Shahak and Norton Mezvinsky,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 p. 15.
可见,在神的救赎到来前,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基要主义者基本不会在意和侈谈中东和平。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世界说到底是以犹太人为中心的,对他们来讲,犹太国是且只是犹太人的国家。
五、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壮大的制度性因素:纳粹大屠杀之后的经学院
极端正统派犹太基要主义者的价值观以反对世俗和抵制现代性为底色。对于外部世界,他们在以色列要比在美国更容易采取孤立隔绝的姿态。在美国,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作为少数群体中的少数,可以不动感情地看待非犹太的主流社会。但在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国家,他们就觉得周围其他犹太人皆是异端,对自己更有威胁,因而更需要加强对外界的抵抗与斗争。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参政,重在争取资金,以发展独立的教育和福利体系,从而不受外界影响。以经学院为核心的独立宗教教育体系正是维持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会封闭性最重要的建制,它帮助在纳粹大屠杀中遭受重创的正统派欧洲犹太人在以色列重新恢复元气,并塑造出今日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本面貌。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理想是终身学习托拉,这被他们当作生存的全部意义。以色列建国后遵行“现状协议”的精神,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建立了独立的宗教教育体系(HinukhAtzmai),并予以政府资助。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享有极大自主权,基本不讲授与宗教无关的内容。本-古里安又给了经学院学生免服兵役的特权,使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到了参军年龄仍可以继续在经学院学习。不去工作,也就不会被军队里的世俗犹太人“带坏”,而军队恰恰是以色列这个移民国家进行最有效社会融合的熔炉。今天,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已形成大规模“脱产读经”的现象,用学界的术语说就是形成了“学者社团”(hevratlomdim):该群体大约从16岁起进入经学院,只要愿意可以一直全日制学到45岁以上,结婚后还能获得家庭补贴。(46)2018年,以色列经学院里有133,933名学生,其中70%是已婚学生。就读的年增长率达6%,高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人口整体的增长率(4%)。参见Lee Cahaner and Gilad Malach, Statistical Report on Ultra-Orthodox Society in Israel, 2019: Education, 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https://en.idi.org.il/haredi/2019/?chapter=29391,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有趣的是,“学者社团”最早是弗里德曼(Menachem Friedman)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学术概念,多少含有批判意味,但后来沙斯党党魁埃利·伊沙伊(Eli Yishai)将它当作该党的核心思想信条,公开说“我们的工作是保护学者社团”。参见Nissim Leon, Shas and the Peace Process: Leadership, Society and Politics (Research Paper 5),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June 2011, p. 5。这即使在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世界里也是特别的。美国和西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由于没有政府资助,通常24岁以后就要离开经学院谋生。
一般来说,经学院的一天分为三个单元:上午(约8:30~12:30)、下午(约3:00~6:00)和晚上(约8:00至学生筋疲力尽,有时甚至迟至午夜或更晚)。这三个单元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塔木德》,其间经学院也会安排一点时间学习犹太律法、《圣经》和伦理教诲(mussar)。这是立陶宛人经学院的典型学习内容。在哈西德人开办的经学院里,学生们会花大量时间学习各自所属的哈西德教派的思想和神学著作(hasidus)。高级学生,尤其是那些攻读拉比资格的学生,将会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系统学习犹太律法,即使如此,每日课程安排中也不能完全忽视《塔木德》。(47)Yoel Finkelman, “Ultra-Orthodox/Haredi Education,” in Helena Miller, Lisa D. Grant and Alex Pomso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ewish Educ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 1070。对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教育的一个生动的社会学田野调查,参见Samuel Heilman, Defenders of the Faith: Inside Ultra-Orthodox Jew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68-276,此书还包括对经学院之前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观察。哈西德人虽然一开始有不重视托拉学习的倾向,但从19世纪末开始也采用了立陶宛人的经学院制度,这是他们最终与立陶宛人合流成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又一表征,参见David Biale et al., Hasidism: A New History, pp. 548-553。
经学院里严格限制电视、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来源,而是采用结伴式教学。学员不分年龄地相互问答交流,积年累月地沉浸在文本营造的永恒而神圣的氛围中,向着犹太教理想中的“托拉学者”(talmidhakham,字面意思“圣贤的门徒”)迈进。经学院作为一种制度最充分地体现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以托拉学习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犹太教对其理想型学者的追求在这里被表达到极致。(48)以当代以色列著名经学院为样板对经学院作的一个整体描述,参见Moshe Halbertal and Tova Hartman Halbertal, “The Yeshiva,” in A. Oksenberg Rorty, ed., Philosophers on Education: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455-466。关于犹太教中的“托拉学者”,参见Louis Isaac Rabinowitz, “Talmid Hakham,” in Fred Skolnik and Michael Berenbaum, eds., Encyclopaedia Judaica, 2nd edition, Volume 19, pp. 466-468。哈宗伊绪曾说,经学院“是将门徒和‘托拉学者’培养成明日圣贤即他们那代托拉大师的设防堡垒”(49)Jacob Neusner and Alan J. Avery-Peck, eds., The Blackwell Reader in Juda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 p. 244.。这里不仅要教育年轻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世俗犹太人设防,更要让他们提防同样是正统派犹太人的宗教复国主义者,这些人也开办了自己的经学院,但将托拉学习和服兵役结合起来。(50)这类所谓的“安排经学院”(Yeshivot Hesder)目前有近70所。参见Yossef Slotnik, “Looking Backward: The Ideology of Hesder,” Tradition: A Journal of Orthodox Jewish Thought, November 5, 2019, https://traditiononline.org/looking-backwards-the-ideology-of-hesder/, 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宗教复国主义这类与世俗政权妥协的思想很早就被哈宗伊绪贬称为“中道”:“那些倡导中道和平庸而藐视极端的人,就是与弄虚作假者或蠢人为伍。没有极端就没有完美……那些承认从未尝过极端的甜头的人,也就承认了他们对我们宗教的基本原理的信仰不是全心全意的。”这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代言人直言,“我们的教育任务是教导极端,我们盔甲上的武器是蔑视和憎恶那些藐视极端的人。事实上,年轻人脾气暴躁,常常会过分地亲自攻击藐视者,但他们要成长为真正的托拉热爱者,就需要精神上的提升,不能让任何障碍阻挡他们通往天堂的道路。”(51)Jacob Neusner and Alan J. Avery-Peck, eds., The Blackwell Reader in Judaism, pp. 245-246.正是通过在封闭的经学院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团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经学院里不仅要对非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设防,还要自我反省和警戒。这很好地体现在他们对纳粹大屠杀的态度的转变上。如何记忆大屠杀构成了全球犹太人今天构建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大屠杀更是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关注”(52)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and the Holocaust,” The Jerusalem Quarterly, Issue 53, 1990, p. 86.,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也体现了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如上文所述,以色列建国前后,他们最初还为自己没有帮助甚至阻挠犹太人逃离欧洲多少感到愧疚。但从1950年代中期起,哈宗伊绪的追随者摩西·沈菲尔德(Moshe Scheinfeld)开始在经学院里宣扬他对纳粹大屠杀的理解。他声称,传统生活方式保证了犹太人在漫长的流散中生存,犹太人一旦背离传统生活方式,就会引起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纳粹对那些早已融入非犹太社会的犹太叛教者及其后裔的迫害,便是这种神学史观的明证。在他看来,纳粹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几乎就是纳粹的“同盟”。为了阐明这点,沈菲尔德发挥了哈宗伊绪曾转述过的一则寓言:有个犹太人倾其所有财富和精力去帮助一个掉进坑里的同胞,为此赢得周围所有人的尊敬,直到人们发现最初正是他挖了那个坑。沈菲尔德说,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挖下大屠杀的坑,最终让数百万犹太人掉进去。通过将全部责任推卸给犹太复国主义和建国前的犹太社团,沈菲尔德减轻了以色列联盟党成员的挫折感和负罪感。(53)Menachem Friedman, “The State of Israel as a Theological Dilemma,” in Baruch Kimmerling, ed., The Israeli State and Society: Boundaries and Fronti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pp. 179, 195-198; 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and the Holocaust,” pp. 86-114。关于1961年萨特玛派哈西德瑞比约尔·泰特鲍姆(Yoel Teitlbaum)发表的类似观点,参见Jacob Neusner and Alan J. Avery-Peck, eds., The Blackwell Reader in Judaism, pp. 246-247。这个观点在经学院里迅速流行开来,至今仍占据主流。2000年,东方犹太人的精神领袖俄巴底亚·约瑟做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广播布道,他宣称大屠杀是罪的结果——许多被纳粹杀害的信教犹太人乃是因为前世犯下了罪。(54)David Weiss Halivni, Breaking the Tablets: Jewish Theology After the Shoah,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pp. 3-4.关于大屠杀的这两种观点在当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团中最具代表性,它们的潜台词是相同的:非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信仰出了问题,坚持经学院中倡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才是正道。
经学院的大发展带来连锁反应。要维持这套建制,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经学院得到的钱越多就越发展,而越发展又越需要钱。这进一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越来越活跃,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议员热衷于担任议会的财务委员会主席,以便争取抢手的经费;二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之间对经济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各派系的利己意识显著强化,这是造成以色列联盟党分裂的又一重要原因。
尽管延续了犹太教关于托拉学习的理想,但今日的经学院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院。一方面,传统经学院更像是培养少数精英和社团领袖的高等教育机构,当前以色列经学院中的“脱产读经”却是整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团的集体行为。这意味着经学院的社会功能已经改变。在传统犹太社会,宗教虔诚来自原生家庭和街坊的耳濡目染,经学院对此只起锦上添花之效。但近代以来,面对世俗化大潮的种种诱惑,很多犹太父母的宗教虔诚已经淡化,经学院于是取代家庭和街坊,成为锻造犹太身份的避风港。学员在此一起吃饭学习,学习年限拉长,集体氛围浓厚,从经学院出来的学员自然比其父辈的宗教意识更强。因此,经学院经历了一个从培养精英到培养价值观的转变。而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会经历的一个戏剧性变化,即“越来越重视所有社会成员的正规教育。在传统犹太社会,高等正规教育是少数男子的特权,但在如今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会中,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男女,都会接受高等正规教育,儿童和年轻人由此获得所需的知识和文化适应,可以免受非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文化的诱惑”(55)Yoel Finkelman, “Ultra-Orthodox/Haredi Education,” p. 1064.。一言以蔽之,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可并汲取了现代社会的大众教育和福利国家的理念。经学院今天虽然仍在培养学者型人才,但更像是宗教机构而非以前的学术机构,成为滋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价值观的温床。考虑到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超高生育率,其价值观社会影响的与日俱增是指日可待的。
另一方面,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在经学院大众化的过程中,靠掌握文本脱颖而出的权威拉比身上的光环,非但没有黯淡,反倒更加光鲜了。托拉学习上的出类拔萃巩固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和领导地位。今天,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是所谓的“托拉的见解”(da‘attorah),即长期埋首经典而获得的智慧。凭借这种近乎神圣的智慧,该社团的精神领袖几乎对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拥有独家权威,哪怕他们的相关裁决未必有哈拉哈方面的理据作为支持。这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是以色列联盟党内的“托拉圣人理事会”(Mo’ezetGedoleiha-Torah),即该党的幕后决策机构。它由精通《塔木德》与哈拉哈的拉比组成,都是年高德韶、众望所归的“大人物”,它的决策过程不对外公开。1964年,该党正式宣告:“对托拉圣人理事会的绝对服从赋予以色列联盟特殊性质;即使联盟的反对者也不可避免地看到,它是唯一一个绝对服从至高无上的神圣托拉权威的运动。”(56)Menachem Friedman, “Agudat Israel,” p. 506.该党的所有活动理论上都要经过理事会批准,其议员实为傀儡,在公开场合需要毕恭毕敬地表示自己的决定已得到理事会许可。如前所述,以色列联盟党现已分裂为三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因而有了三个托拉圣人理事会(57)沙斯党成立后,约瑟也设立了该党的托拉圣人理事会(Mo’ezet hakhmei ha-Torah),职能相似。,拉比们引以为豪的“托拉的见解”让他们在同一问题上常常做出相互抵牾的决议,这就暴露出宗教领袖参政的弊端。诚如雅各·卡茨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每当宗教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他们的声音当然拥有特殊的份量。但当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就会受到引导,利用政权去维护宗教利益,从而造成双重灾难:政治决策的过程因为允许被宗教因素影响而遭到扭曲;同时,宗教又因为诉诸世俗性质的手段而信誉受损,这让宗教仅仅凭借其内在价值的号召力是靠不住的这一反对意见更具份量。”(58)Jacob Katz, “Da‘at Torah: The Unqualified Authority Claimed for Halakhists,” Jewish History, Vol. 11, No. 1, 1997, p. 49.
经学院这两种新特点的出现背后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历史动因,即19世纪以来犹太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它起于犹太人从东欧迁徙到美国,至纳粹屠犹前后达到巅峰,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又陆续迁至以色列。这种大规模流动意味着传统的移植和调整。以往根据地域来界定的犹太社团纷纷解体,新出现的是一个个自愿性质的犹太社团。宗教和传统对犹太人的约束力在这种新性质的社团里大大降低,这就为宗教领袖从严解释文本在经学院中获得制度化的表达开辟了道路。
六、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带来的挑战与前景
经学院里不提供世俗教育,没有受过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缺乏在现代世界生存的必要知识体系。一些人即使有心进入就业市场,也会发现自己无一技之长,因而机会寥寥,最终变得高度依赖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团提供的福利保障体系,难以脱离社团独立谋生。很多该派成年男子终日专注于托拉学习,养家糊口的角色通常由妻子承担。数量庞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就这样生活在有大量孩子的单劳动力收入家庭中,落入以色列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他们日益成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负担,还普遍拒服以色列的义务兵役制度,引起以色列民众和纳税人的强烈不满。2010年,时任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发出警告称,国家再不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人口将让国家的经济繁荣“无法持续”;时任财政部长尤瓦尔·斯坦尼茨(Yuval Steinitz)则说,如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大幅增加他们的劳动人口,国家经济“用不了20年就会陷入严重麻烦”。(59)Gwen Ackerman and Alisa Odenheimer, “Israel Prosperity Seen Unsustainable as Haredim Refuse to Work,” Bloomberg, August 2, 2010,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0-08-01/israel-prosperity-seen-unsustainable-as-haredim-refusal-to-work-takes-toll, 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
为应对这个问题,以色列政府采取措施鼓励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就业,希望改变他们的贫困状态,积极推动他们的社会整合。以色列政府以就业问题为突破口,引导他们参与世俗国家的经济建设,试图以经济手段弥合以色列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鸿沟。2010年,政府设定具体工作目标,从就业意愿、渠道、技能、补贴等各方面加以引导,计划至2020年使国内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就业人口达到63%以上。(60)具体措施详见关蕊:《现代转型中的以色列哈瑞迪派——以就业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4章。从最新统计数据来看,25岁至64岁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的就业率已由2002年的35%上升至2018年的近51%,同年龄段女性的就业率由同期的50%上升至76%。(61)Lee Cahaner and Gilad Malach, Statistical Report on Ultra-Orthodox Society in Israel, 2019: Employment, 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https://en.idi.org.il/haredi/2019/?chapter=29393, 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至2017年,43%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数字虽然很高,但已有所改善,因为在十多年前,这个百分比一直位于50%到58%不等。(62)Lee Cahaner and Gilad Malach, Statistical Report on Ultra-Orthodox Society in Israel, 2019: Welfare, 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https://en.idi.org.il/haredi/2019/?chapter=29392, 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数据变化是明显的,但这些措施能否实现初衷,实质性地缓解教俗矛盾,恐怕不容乐观,个中隐忧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的措施导致极端正统派犹太女性的就业意愿明显高于男性,这实际上加剧了该派就业模式中已有的性别不平衡。在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文化中,年轻女性应掌握一门最好不用过度暴露在外界文化中的手艺或职业,以便为日后的丈夫和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事实上,按照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公开教义,特别是在以色列,如果妇女在物质和情感层面上供养丈夫和家庭,她就可以从丈夫的托拉学习中分享到同等的荣誉。”(63)Yoel Finkelman, “Ultra-Orthodox/Haredi Education,” p. 1074.因此,女性就业率远高于男性不但没有拉近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与现代社会的距离,反倒有助于加重深层的隔阂。
其次,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传统就业集中在零售业和钻石加工业(64)关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传统职业,详见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in Israel: Who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Want?, Institute on American Jewish-Israeli Relations,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991, pp. 20-22。,但全球化的兴起使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下降。在政府的引导下,教育、医辅、企业管理、网页设计乃至程序员渐渐受到他们的青睐,而在其他以色列人中受欢迎的工程学却问津者寥寥。这显然是因为工程学对经学院出身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言门槛太高,同时也表明他们希望学习实用的应用学科,以便今后在自己的社团内找工作,不用和外界接触,避免男女同工等涉及宗教敏感的不便。在这类职业上越成功,他们的分离主义趋势越得到强化,因为就业本身很可能是他们更好地实践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价值观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政府的社会整合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
再次,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政治领域内持续发力,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让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议员割让既得利益,近乎空想。相关数据表明,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就业率的上扬自2015年起陷入停滞并走低,这是当年的执政联盟向沙斯党让步、将经学院津贴提高一倍的缘故。对经学院学生免服兵役制度的实质性改革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一直悬而未决。在反抗现代世界的斗争中,极端正统派犹太基要主义者也不断反击,并“经常吸收和利用现代成分,不论这些成分是政治手段、宣传策略抑或技术方法,它们都被用来为基要主义者服务,而这正是当代基要主义运动的一个普遍特征”(65)[美〗撒母耳·海尔曼:《犹太人与基要主义》,第207页。。
1952年,本-古里安会见哈宗伊绪,在宗教人士眼中,以色列当时教俗两界的这次“高峰会晤”不啻为《塔木德》中记载的亚历山大大帝去见犹太大祭司的当代重现。本-古里安问教俗如何共处?哈宗伊绪引《塔木德》中一则寓言作答:两只骆驼狭路相逢,一只满载货物,一只背上空空,这时,空载的必须给满载的让路。拉比的意思很清楚,卸空犹太传统的世俗犹太人要给虔诚沉稳的犹太人让路。本-古里安以他一贯的雄辩反驳:另一只驮着沉甸甸的诫命——神关于在应许之地定居的诫命,你所反对的那些守卫边境、保障生命的士兵不正在践行这条诫命吗?哈宗伊绪不为所动,说士兵们能活着多亏了我们在学习托拉。(66)David B. Green, “1952: Ben-Gurion Visits a Wizened Torah Sage,” Haaretz, October 20, 2013,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1952-ben-gurion-visits-a-torah-sage-1.5276483, 登录时间:2020年3月12日。一场寻求共识的会晤并未如预期获得共识。本-古里安可能向拉比投去怜悯的一瞥,在他眼中,这些宗教人士宛如昔日犹太流散传统在以色列地的回光返照,是新枝萌发的老树上行将随春风而去的旧叶。他根本想不到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渐渐开始大规模“脱产读经”,更想不到他们今天已经成为以色列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而他所设想的犹太国——一个犹太人的民主国家——遭遇了来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的全面挑战,他们不仅要重新定义“谁是犹太人”,而且想用一个基于哈拉哈的神权国家替代民主国家。与此同时,随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苦心孤诣维持的传统守护者形象已引发以色列社会尖锐质疑,最终恐怕要付出瓦解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会根基的代价。谁给谁让路?这个关乎以色列未来走向的问题在今天比在本-古里安时代更加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