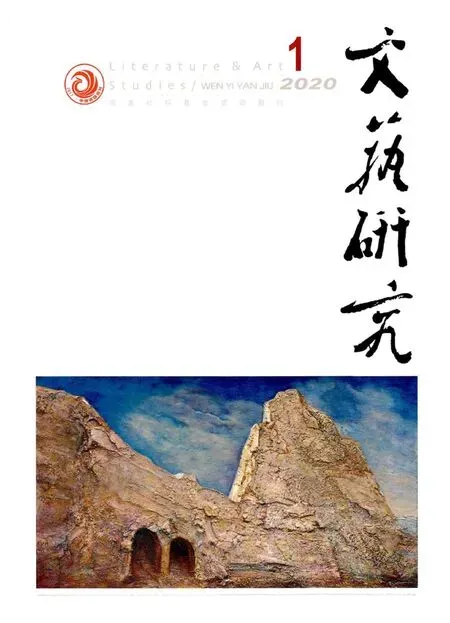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元代杂剧
——“依相叙事”形态演进路径上的元杂剧考察
徐大军
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元代杂剧,这要取决于元人编写什么样的剧本,又留下什么样的剧本,然而元人留下的剧本实在太少了。《元曲选》中的那类剧本已经过明人戏剧观念的过滤与增益,属于明人编改后的元杂剧阅读本①。《元刊杂剧三十种》虽然确为仅存的元人刊刻本,但对它的文本属性又存在节略本、演出本、单脚本等不同说法,诸说皆参照于《元曲选》中的那类剧本,认定“元刊本”存在科白的简略或缺失,这就有意无意地导向了元杂剧剧本另有原貌的设定。如此一来,“元刊本”的存在一方面证明了元代确有文体属性的“元杂剧”剧本,另一方面又勾起了后人对元杂剧剧本的诸多疑惑:说它们是元代晚期的剧本,那么元代早期的剧本又是怎样的?说它们是节略本,那么完整本又是怎样的?说它们是艺人演出本,那么文人编写本又是怎样的?
我们之所以执着于对元杂剧剧本形态问题的追索,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是:剧本是戏剧样式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角色扮演则是戏剧表演和剧本不可或缺的体制性内容。这两个戏剧的基本要素被普遍认为存在于元杂剧的生成发展进程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元杂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它首先应属于伎艺范畴,其书面形态和伎艺形态肯定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对应。比如角色扮演原生于伎艺表演领域,并非因剧本编写而产生。当角色扮演还只是一种伎艺体制因素而未被剧本编写考虑时,元杂剧的剧本到底采用了怎样的表述方式和编写体例呢?如果元杂剧存在着一个没有“文体剧本”的发展阶段,就像元代的“搬唱词话”那样,表演时虽有角色扮演形态,但采用的是没有戏剧格式的“词话本”,那么《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文本属性就不是什么节略本、演出本,而是增益本了。因此,“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元代杂剧”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元杂剧的演述方式及其所面对的伎艺族群生态,而元杂剧的演述方式在戏剧领域里的基本体制和特异形态,又皆缘于其曲词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
一、“扮词话”与“扮乐府”:两种词曲叙事的角色扮演形态
元代初年,当北方的城市勾栏里热闹地上演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这类曲牌体杂剧时,偏远农村的乡民们也在迎神赛社的庙台上自娱自乐地搬演着“脸戏”(即面具戏)《吊掠马》这类诗赞体杂剧。
“脸戏”《吊掠马》的出场表演者分两组:一组是“长竹”,即“掌竹”之意;另一组是“面具角色”,扮演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配合方式是,“面具角色一般只舞蹈,没有唱词念白等。唱词由一个叫长(掌)竹的在台口一侧吟唱”②。所以,这个“长竹”不是“脸戏”的角色人物,只是引戏人和曲词唱念者,类似宋代乐舞演出中的“竹竿子”,指挥“面具角色”上下场和动作表演。这段“脸戏”是河北固义大型傩戏《捉黄鬼》中的一个古剧剧目,被认为是宋元民间演剧形态的遗存③。这种保留于乡村迎神赛社仪式的演剧样式,明显不同于那些在城市勾栏里表演的曲牌体杂剧。虽然它们都表现出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但配合的方式却大为不同。在《吊掠马》中,全剧的唱词(包括讲述话语和人物话语)皆由“长竹”这个故事域外的艺人负责唱诵,而“面具角色”不唱不说,只以动作表演来配合“长竹”。值得注意的是,就“长竹”的唱词而言,在词曲类型上是诗赞体,在表述方式上是叙述体,在表演方式上是讲唱式。这种戏剧表演形态在现有民间古剧遗存中并非仅见于一地一域,山西上党的迎神赛社演剧《十样锦诸葛论功》、贵州的地戏《罗成擒五王》、安徽池州的傩戏《陈州粜米记》等,它们皆依据叙述体的词话而作讲唱式的戏剧表演。池州傩戏《陈州粜米记》,其剧本之唱词、说白与明成化刊本词话《新刊全相包龙图陈州粜米记》的前半部分《打鸾驾》几乎完全相同,“全剧不分出,只分五‘断’,全部为叙述体,七言唱词,夹有说白。与其说它是剧本,不如说是地道的唱本”④。
上述民间古剧所显示的演剧形态,一般被认为是承自元代文献中所说的“搬唱词话”⑤。《元典章》是元英宗时地方官吏纂辑的示范性法令文书汇编,记载了元世祖以来五十余年间一些具有典型性、普遍性的案例,其中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有这样一个案件:
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见人家内聚约百人,自搬词传,动乐饮酒。为此本县官司取讫社长田秀井、田拗驴等各人招状,不合纵令侄男等攒钱置面戏等物,量情断罪外。本司看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是为长便。⑥
此案件另见载于同是编定于元英宗朝而稍早的《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记为“般唱词话”⑦。二书所提到的“搬说词话”(或“般唱词话”)伎艺,曾引得当时的元朝官府颁令禁止,说明它在当时北方乡村的盛行之实,惜未留下具体的演剧描述,但由“搬说”“习学散乐”“面戏”之语,可知它是一种不同于元杂剧的表演形态。田仲一成认为,它“属于‘词曲’和‘假面’相结合的戏剧”,并把它类比于现存江西萍乡、婺源等县流传的追傩舞蹈中“花关索和鲍三娘”一段叙述体假面演剧形态⑧。由此可知,“搬说词话”(或“般唱词话”)与上文所述“脸戏”的表演形态相类,应是金元之际与曲牌体杂剧并行于世的一种戏剧样式。后世之所以称这样的演剧样式为诗赞体杂剧,是着眼于它所使用的词曲体制,非套曲,无曲牌,纯属讲唱的诗赞体词话;而元时称它为“搬说词话”(或“般唱词话”),则是着眼于它对词话的唱演呈现方式,即相对于单纯的说唱词话,它在词话说唱之上添加了角色扮演,故可称为“扮词话”。
“扮词话”之所以能归属于戏剧范畴,乃因为它有角色扮演的因素存在。至于“扮词话”的戏曲特点,则缘于其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方式。词曲唱演和角色扮演,是戏曲的两个核心的体制要素和表达手段——角色扮演能保证它有戏曲之实,词曲唱演能确定它有戏曲之名。
比照于“扮词话”,元杂剧在戏剧范畴里的标志性特征“一人主唱”,尽管也是由词曲唱演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体现的,但与“扮词话”不同的是,这里的“一人”乃指一个脚色(正末或正旦),它在元杂剧里的职责,最基本的是要扮演杂剧故事域中的人物,最重要的是要负责全剧曲词的演唱。比如关汉卿的《单刀会》在第三折关羽出场之前,正末在第一折扮演乔国老,在第二折扮演司马徽,分别讲述了关羽的功绩和蜀军的威猛(博望烧屯、隔江斗智、赤壁鏖兵),夸述了关羽的胆识和威风,劝说孙权、鲁肃不要对关羽轻举妄动,以免招惹祸端。乔国老面向配角人物“驾”和“外末”的唱述方式在元刊本中如下所示:
(等云了)(正末唱)
【那吒令】收西川白帝城,把周瑜送了。汉江边张翼德,把尸灵挡着。船头上把鲁大夫,险几乎间唬倒。将西蜀地面争,关将军听的又闹,敢乱下风雹。
(外末云住)(正末云)你道关将军会甚的?(唱)
【鹊踏枝】他诛文丑骋粗躁,刺颜良显英豪,向百万军中,将首级轻枭。那赤壁时相看的是好。⑨
就词曲叙事的方式来说,那些关于关羽丰功伟绩、英勇无敌的曲词,是从正末所扮演的乔国老这人物口中唱述出来的,而不是像“脸戏”《吊掠马》那样由故事域外的专职讲唱人“长竹”来负责的。另外,这段词曲叙事是处在一个对话场景中,由配角人物承应、挑动主唱人物唱述出来的。上面引文中的“等云了”“外末云住”标识,明编本的对应之处则是配角人物鲁肃的宾白“收西川一事,我不得知,你试说一遍”,“他便有甚本事”。明编本第一折中还有鲁肃的对于博望烧屯的“小官不知,老相公试说者”、对于赤壁鏖兵的“小官知道,老相公再说一遍者”之类的宾白⑩。就历史逻辑而言,鲁肃作为与蜀军对阵的一个东吴军事首领,不知关羽的英雄业绩是不可能的,所以,配角人物鲁肃的这类宾白完全是从故事的叙述需要来设置的,为的是挑动主唱人物乔国老的词曲唱述。这样的词曲叙事方式,要比“脸戏”《吊掠马》那样的“面具角色”不唱不说而由“长竹”专职唱述的方式显然更为形象、生动。
应该说,关汉卿《单刀会》所体现的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普遍存在于元杂剧作品的演述体制中。
按照元杂剧的规制,一部杂剧的曲词会付于正末或正旦这一个角色,他可以是故事主人公,也可以不是;可以在剧中只扮演一个人物,也可以每折变换而扮演多个人物,但无论怎样他都要负责曲词的唱演任务,其他角色人物只是以宾白或动作配合主唱角色把曲词唱演出来。比如《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它们的主唱角色都是杂剧故事的主人公,且曲词只付于一个人物,而《千里独行》的主唱人非关羽、《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的主唱人非薛仁贵、《哭存孝》的主唱人非李存孝、《襄阳会》的主唱人非刘备、《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的主唱人非陈季卿。至于某一折的主唱人非主人公的现象则更为常见,比如《黄鹤楼》第二折以禾俫为主唱人来描述社火场景,《气英布》第四折以探子为主唱人来描述项羽与英布对阵厮杀的场面,其他还有《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飞刀对箭》第三折的探子;有时这种探子类主唱人物会被赋予明确的身份,如《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渑池会》第四折的蔺相如、《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等。这些人物并非杂剧故事的主人公而被安排成主唱人物,很明显不是为了他们的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而是因为以其立场来进行曲词唱演可以方便故事叙述,尤其探子,完全是个功能性人物,他们的曲词唱演就是为了完成舞台上难以表现的盛大事件、繁杂场面(战争、集会、宴乐)的描述任务。
至于元杂剧的曲唱部分,它通常由四个不同宫调的套曲组成,曲词在元杂剧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在表演形态还是在剧本形态,无论是在科白缺少的元刊本还是科白齐备的明编本,皆非常明显。元杂剧的四大套曲所具有的叙事属性,表明它与“扮词话”一样,都是以曲词为表述手段和内容主体,只是它的代言体、曲牌体套曲与“扮词话”所使用的叙述体、诗赞体词话明显不同,它的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间的配合关系要比“扮词话”所表现的简单混合状态显得复杂而成熟。应该说,元杂剧与“扮词话”,二者在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上是精神相通的。就配合关系而言,如果立足于戏曲表演,就是角色扮演使用了词曲叙事手段;如果立足于词曲表演,则是词曲歌唱借助了角色扮演方式。因此,立足于词曲叙事的表演形态,我们即可看到二者在角色扮演以配合词曲叙事上存在着共同特性。
“扮词话”是词话说唱辅助了角色扮演。元杂剧则是散曲清唱融入了角色扮演。由于元杂剧乃直接借用了散曲套数的艺术成就,二者在曲乐、曲体、曲文方面有着血缘的承续性和一致性(后文详述);再参照元人无“散曲”之名,散曲通常被称为“乐府”⑪,因此清唱者可被称为“唱乐府”,而元杂剧是以角色扮唱之,故可称为“扮乐府”。
无论是“扮词话”,还是“扮乐府”,皆为词曲叙事表演的方式,由此体现了借助角色扮演以成词曲叙事生动形象呈现的规制。那么,词话说唱而借助角色扮演以成“扮词话”,散曲清唱而借助角色扮演以成“扮乐府”,其间的启导思维和动力机制又从何而来呢?
二、“依相叙事”与散曲唱演形态演进线上的“一人主唱”体制
元杂剧之“扮乐府”属性所涉及的词曲叙事、角色扮演两个核心要素,皆指向元杂剧故事呈现的目标,皆可视为达成这个目标的演述手段。如果我们不囿于戏曲领域而放眼宋元伎艺,这种以形象体(角色扮演属其中一种)辅助词曲叙事唱演的思路和方式,早前亦有先行者,并非“扮乐府”的孤明先发,比如宋金时期的连厢词和大曲歌舞,其中皆有词曲唱诵叙事而配合以真人扮演的形态。
连厢词是金代一种说唱与歌舞相互配合的表演伎艺。杨荫浏称其“有歌唱,有伴奏,分角色,也有表演;但还不是戏曲,而是一种有表演的说唱”⑫。根据毛奇龄《西河词话》的描述,其唱演的基本规制是把叙事与扮演的任务分付于司唱者、司舞者这两组人,他们各司其职,“舞者不唱,唱者不舞”;司唱者列坐台侧,“代勾栏舞人执唱”;司舞者“入勾栏扮演,随唱词作举止”⑬。如此一来,对于一个故事的讲唱任务来说,扮演者是辅助,其动作表演必须悉遵讲唱者的唱词说白而动止相应。至于宋代大曲歌舞的唱演形态,同样是《西河词话》所谓的“舞者不唱,唱者不舞”的体现者,比如其规制有“竹竿子”一职,专司致语祝赞以勾队上场、遣队下场。当大曲歌舞开始唱演故事时,“竹竿子”负责简单交代情节,司舞者则配合“竹竿子”和司唱者的故事讲唱而作舞蹈表演。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之“宋之乐曲”一章所列南宋史浩的《剑舞》大曲即为这种唱演形态的典型例证⑭。
如果角色扮演里的形象体不限于真人出场,则先行者更多,也更早,可溯至唐代的变文讲唱。变文的配图讲唱是一种重要的唱演体制。讲唱者负责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变相”图画的调度,用图画展现故事的关键人物、情节或场景,从而增强其讲唱的艺术感染力。变文讲唱对于宋元时期的故事唱演伎艺如影戏、傀儡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楷第即指出,变文讲唱时所利用的图像手段乃专为讲唱而设,“其由用图像改为纸人皮人者,谓之影戏”⑮。只是影人、傀儡初始出现时并非为了故事讲唱,而是因巫术、幻术而生,后虽为各种伎艺所取用以达成宗教宣传、逞显巧技或调笑逗乐的目的,但还未用于故事讲唱。北宋时,二者才开始被取用以辅助故事讲唱。李家瑞认为,早期影人的功用只是辅助说唱故事而已⑯,影戏被称为“弄影人”讲唱故事。而“弄傀儡”伎艺则在调笑、炫技风格的滑稽表演或杂技表演之外,发展出了以傀儡作为辅助故事讲唱工具的表演伎艺,成为了“一种正式的戏剧”⑰,它的最重要的演剧特征就是艺人为了故事讲唱的形象性和趣味性而调动了“弄傀儡”伎艺,概言之即提傀儡讲唱故事。
综上所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唐宋元时期的故事唱演伎艺在思维和表演方式上具有承续关系。我们把这种利用形象体辅助故事讲唱的思路和格式,概称为“依相叙事”。所谓“相”,一是取“变相”之“相”,即变文唱演时配合的图画;二是取形象之义,指故事唱演时所取用的各类形象体。
影戏、傀儡戏以影人、傀儡辅助故事讲唱表演的方式,与俗讲变文的配画讲唱格式,有着思维上的相通性。孙楷第认为,它们虽称戏剧,但与说话伎艺相比较,“唯增假人扮演为异,其话本与说话人话本同,实讲唱也”,可称之为“扮唱故事”⑱。至于连厢词,则可视作以真人替代影人、傀儡的故事唱演伎艺。李家瑞立足于角色扮演认为,打连厢是“一种用人做傀儡的戏剧”⑲。他在《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打连厢是用一人说唱一段故事,而另以若干人扮演故事中人物的举动,实在就是说书人用人作傀儡以表现他所说的书里的人物。”⑳而元杂剧的“一人主唱”体制,则被清人梁廷枏视为“连厢之法未尽变也”㉑,亦即毛奇龄所认为的连厢词唱演方式的进化形态——由连厢词之“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进化到元杂剧之“歌舞合作一人,使勾栏舞者自司歌唱”㉒。
应该说,元杂剧的“扮乐府”属性是基于“依相叙事”思维与格式应时新变的体现,它的扮演者总体上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形貌动作的表现者,一种是故事情节的讲唱者。动作表现者配合故事讲唱者,应合讲唱而行止。由于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这个故事讲唱者身份肯定要付于主唱人物身上,但动作表现者的身份则不固定,有时主唱人物边讲唱边表现动作,有时主唱人物讲唱故事,而其他角色表现动作。比如在《襄阳会》第二折中,主唱人物王孙一边讲述自己的偷马行为,一边以动作表演予以配合;在《刘行首》第三折中,主唱人物马丹阳负责唱述刘行首的发疯动作,刘行首则以发疯动作的表演与之相配合。也就是说,这两种身份有时合于主唱人物身上,有时则分付于主唱人物和其他角色身上。但是,不论分、合形态如何,这两个身份所承担的功能间的配合关系,统统表现出“依相叙事”的思维和格式㉓。
正因为这些宋元唱演伎艺在“依相叙事”思维与格式上存在着一致性和承续性,故可视之为“依相叙事”的不同演进形态。在此过程中,配合关系的双方皆应时变化,故事讲唱有自己的演进之路,那些作为“相”的形象体也有自身生成与发展的独立性,它们形态各异:变相、影人是平面的,傀儡、真人扮演是立体的;变相是静态的,影人、傀儡、真人扮演是动态的;影人、傀儡是不言的,真人扮演在连厢词中是不言的,在元杂剧则是能言的。至于这些不同演进形态中的“相”不断地被取用以缘饰故事讲唱,则表明故事讲唱伎艺一直存在着寻求形象呈现方式的内在需求,这就是“依相叙事”形态在形象体方面应时新变的内在动力,由此,各种时兴、新颖、高级的形象体被借用来为生动形象地呈现故事唱演伎艺乃至元杂剧服务。
在元杂剧的“依相叙事”演述形态中,角色扮演无疑是其戏剧体制的核心因素。以往我们倾向于从“一人主唱”来理解元杂剧的角色扮演体制。不过,如果参照“扮词话”的叙述体、讲唱式演剧形态,就会意识到“一人主唱”并非元杂剧固有的扮演体制,也并非单属戏剧领域的表述方式。在元杂剧时代,同属戏剧的表演伎艺,同样取用“一人主唱”方式者,还有“扮词话”;同属叙事的曲词唱演伎艺,同样具有“一人主唱”方式者,还有诸宫调和散曲套数。当然,在“依相叙事”思维的规制下,元杂剧的“一人主唱”有其独到之处,元杂剧的剧本形态和表演形态在主唱角色与配角人物、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之间的配合关系上,皆呈现出“一人主唱”的形态。具体体现在一部杂剧中,曲唱付于一个角色(正末或正旦),这个角色扮演着杂剧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通常是故事的主人公),四大套曲词即以这个主唱人物的立场来作文本编写和舞台唱演。因此,这个主唱人物有两个属性:一是作为虚构故事域的主人公(有时为次要人物),这就与诸宫调类说唱伎艺的说书人讲唱方式区别开来;二是作为外在于作者的故事人物,这就与诗词的作者自我叙述方式区别开来。主唱人物歌唱这些曲词来叙事,同时也由此塑造自己的形象。这种故事人物立场(典型者是叙事主人公立场)的曲文叙事放在角色扮演中来呈现的方式就是元杂剧的“一人主唱”体制,它是元杂剧的决定性体制和标志性特征。
其实,元杂剧所表现的这种故事人物立场的曲文叙事体制,早在叙事散曲中即已普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曲词唱演一端来考察元杂剧角色之间的配合方式。
散曲有着区别于诗词体例的叙事性,小令、套数皆如此㉔。散曲之讲究叙事,无论篇幅长短,皆重视对故事的过程交代,致力于把它首尾完整、情节连贯地表述出来。所以,散曲虽然被称为“词之余”,但却发展出别立于诗词体例的重要属性——叙事性,而且有自己的叙事品性和成就。叙事品性是指散曲可以虚构叙事,不像诗词那样要有写实的态度,注重作者对自己真实经历的表现。叙事成就是指散曲在叙事方式上的特别之处,或说创造之处,即叙事主人公身份的设置——散曲的叙述人是故事主人公,而且是一个外在于作者的故事人物。因此,散曲叙述人,并非像敦煌变文、宋元话本、金元诸宫调中的叙述人那样是故事讲唱者或编写者的化身,亦非如诗词的抒情主人公那样是作者抒情言志的代言者。如此一来,作为外在于作者的故事主人公,散曲叙述人就有着不同于作者的独立品格和情感,进而使得散曲形成了以故事主人公立场进行曲词表达手段的虚构叙事体制。
比如关汉卿的【双调·新水令】《楚台云雨会巫峡》由一个痴情男子讲述了他月夜约会的甜蜜回忆。这位男子正在月夜中等待着恋人来赴约,他从傍晚时分等到月上高天,由碧纱窗下转挪到荼架下,其间等候时的焦急、见到时的惊喜、亲昵时的欢爱、分别时的约定,都依次作了生动细致的叙述描写。更为著名的是,关汉卿的那篇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被普遍理解为关汉卿的个人抒情言志作品,其实更恰当、切实的属性应该是一篇虚构叙事作品,虽然其中的“我”这个人物有着关汉卿个人的情绪寄托和生活投射,但这篇叙事套数的属性仍是按照一个“浪子班头”的身份、性格、态度和情绪来组织语言、设计情节的,由此塑造了一个“浪子”形象。这两篇套数都是在一个故事场景中塑造了一个外在于作者的人物形象,前者是痴情男子身份的“我”,后者是浪子身份的“我”,他们是散曲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散曲故事的叙述人。这样的叙事散曲并非个例,在整个元代散曲中比比皆是,并且在早于关汉卿的年代已成体例(比如金末元初杜仁杰的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应该说,散曲的叙事体制要比诸宫调之类讲唱伎艺的一人说唱的叙述体更接近元杂剧的曲文叙事体制,尤其它还与元杂剧的曲文一样具备了北曲、联套等因素。
当然,曲词联套叙事的格式与能力,当时并不独散曲具备,赚词、诸宫调中亦都存在,此二者都体现出曲词联套叙事的完备性,甚至诸宫调还使用了北曲,这一因素即被视为元杂剧形成的先决条件(“元杂剧正是吸收了以上两种说唱艺术联套的特点,创造了它自己的联套形式”㉕)。元杂剧的“一人主唱”体制来自诸宫调这个观点亦是以此为基础而得来的。然而,在故事讲唱上,赚词和诸宫调所使用的叙述体讲唱方式,即与元杂剧彻底区别开来。至于曲体,北曲套数体式与诸宫调并无渊源关系㉖,而是来自唱赚㉗,只是唱赚用的是词调,散曲用的是曲调,也就是说,唱赚的套数体式已经被散曲借用而体现为北曲套数了。元杂剧直接借用散曲套数,不需要“变化”,也不存在“创造”,因为“散曲套数与杂剧套数是同一种套曲体式”㉘。由此看来,散曲的联套叙事是有其自身发展轨迹和承传系统的,它承续词之民间传统一路的发展线脉,在唱赚、诸宫调这些民间形式的“成套词”㉙进行叙事体套曲形式的讲唱之际,就已确立了以一个故事人物为立场和视角的曲文叙事体制,它的唱演形态呈现为“一个人物主唱”的体制。只不过,散曲的套数是“一人主唱“的代言体清唱,没有角色扮演的配合,不是如元杂剧套曲那样的“一人主唱”的代言体扮唱。但二者同样有叙事主人公的设置,同样是“一人主唱”,同样是代言体,元杂剧的曲词就是散曲中的套数,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表演方式不同而已。
散曲与元杂剧,二者之间如此的亲缘关系,如果放在角色扮演形态的演进框架中来认识,可以认为是元杂剧吸收、借用了散曲的艺术成就。但是,如果放在曲词唱演形态的演进框架中来认识,则是故事人物的曲词唱演借助了角色扮演方式来配合。如此一来,这个亲缘关系就蕴含了叙事散曲唱演方式朝着“扮乐府”演进的方向,而这个演进的方向之所以能够出现并成为推进的动力,一是前代故事讲唱伎艺所蕴含的“依相叙事”思维的不断促进,二是当时故事讲唱伎艺借助新兴形象体作为辅助手段的反复示范。于是,在散曲唱演方式的演进路线上,承续着故事讲唱伎艺追求形象呈现的内在动力,散曲唱演也借用了角色扮演手段,出现了“扮乐府”的形态。因此,元杂剧之“一人主唱”的“扮乐府”,作为一个伎艺发展方向,决定这个方向的关键要素是由唐宋讲唱伎艺延续而来的“依相叙事”思维;作为一个演剧形态,决定这个形态的关键要素是由散曲延续而来的以一个故事人物为立场和视角的曲文叙事体制。
三、伎艺领域与书面领域不对应状态中的杂剧词
元杂剧的“依相叙事”或“扮乐府”,实为曲词歌唱置于角色扮演中的呈现形态。曲唱与角色之间的配合方式,形成了元杂剧的演剧形态。由于二者来自不同领域,各有独立的演进线脉,故对于元杂剧属性的认识,因着眼点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结论。一者着眼于角色扮演,看到了元杂剧“伎”的属性,以及金元之际杂剧与院本的分流;一者着眼于曲文叙事,看到了元杂剧“曲”的属性,以及它与乐府诗词渊源相承的品格。对元杂剧属性的这两种认识,涉及两个领域:伎艺领域和文学领域,由此也关联了元杂剧的伎艺形态与书面形态。
当然,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元杂剧剧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已有呈现,在《元曲选》中更为清晰。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元杂剧的伎艺形态和书面形态肯定有诸多的不对应之处。比如角色扮演的体制因素不可能全部、原貌地落实于书面形态,这在元刊本中非常明显。伎艺领域和书面领域的不对应,在元杂剧形成的早期更为分明,因为当时角色扮演还只是伎艺领域的一种表述手段,其相关的体制因素并未成为书面编写的表述方式而落实于文本,成为元杂剧文体剧本的表述方式和编写体例。相比较而言,曲词叙事承续诗词民间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已有书面表达的规范和体例可遵循,所以,无论是诗赞体,还是曲牌体,曲词叙事的文本格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规范,也早已成为书面编写的表述方式了。
由此而言,虽然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二者配合而有了元杂剧的演剧形态,但在这种演剧形态出现的早期,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的承续传统、表述体例是分处于不同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各有承续传统,各有表述规范,各有体制类属,即使二者有所关联,也存在诸多的不对应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伎艺领域不需要用剧本来呈现角色扮演的具体方式。艺人扮演是按照伎艺规范,融合了角色、曲唱、科白等构成要件,虽然这些后来都成为了剧本因素,但是,在演剧形态发展的早期,这些伎艺的表述方式还不会即时地反映在书面文本中,也不会即时地成为书面编写的表述体例。艺人不需要书面文本呈现这些因素,因为这是他们的基本艺能,也是伎艺领域早已形成的家门、程式、格套,无需书面文本为其提供角色扮演的格式规范。即使现代的民间艺人也仍然可以进行临场口头创作,不必依据唱词、宾白、舞台提示等完备的剧本而从事即兴表演㉚。在当时,宋金杂剧已经形成了一套演剧的程式格套,比如《南村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条就提到了“外脚”的科白艺能:“副净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鼎新编辑,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至今乐人宗之。”并列举了他们的一些常用格套,分类汇集,如“卒子家门”列有《针线儿》《甲仗库》《军闹》《阵败》等格套,他如和尚家门、先生家门、秀才家门、大夫家门、卒子家门、邦老家门、司吏家门㉛。后世艺人可宗而用之,根据剧情临场发挥使用。
科白俱全的元杂剧明编本大量存在这类格套,官吏、书生、将军、士兵、医生、衙内、酒保、媒人等角色人物出场各有套语。比如无名氏《飞刀对剑》第二折净扮张士贵出场的一段念白,就被认为是“卒子家门”《针线儿》在元杂剧中的使用㉜;而得意书生的通用上场诗“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羡,十年前是一书生”,昏庸官吏的通用上场诗“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做一片”,则在《元曲选》各剧中相关人物的嘴里反复出现㉝。这些在阅读本中存在的格套并不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这倒并非因为元刊本没有能力来呈现这些内容,而是因为作为艺人的演出本,艺人本来已熟知这些角色的家门格套以及角色间的科白承应之法,无需在曲词文本上予以详标详述,故而角色分配信息、科白标识信息就显得极为简陋甚或缺无。比如元刊本《西蜀梦》《疏者下船》《赵氏孤儿》三本即科白全无,科白简略者如《单刀会》,则仅标“云了”“云住”之类的提示套语,而宾白内容皆略而不具。
其二,书面领域的曲词编写不可能使用尚仅属伎艺领域的体制因素。元杂剧既是伎艺概念,也是文体概念,其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既表现在表演形态中,也表现在剧本形态中。不过,这是后世对元杂剧体制的认识和总结。在元杂剧形成的早期,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纯粹发生在伎艺表演领域,艺人会按照其熟悉的程式和格套对联套曲词进行“伎艺语境化”,此时,角色扮演还只是伎艺领域的表述方式,并未落实于剧本之中,也并未成为书面编写的表述方式和文本体例。当时的曲文编写是承乐府诗词一路发展而来,则已具有了自己的属性认同和编写体例。
一方面,曲文的编写体例承袭自联套体散曲,其全部四套曲词皆是以故事人物为立场(典型者是以叙事主人公为立场)的联套体的曲文叙事体例,即使存在主唱人物变换的情况,每套曲词亦定制以一个故事人物的立场来唱述的格式。比如元刊本《气英布》第四折以探子的立场来唱述战斗场面,全为曲词而无配角人物的宾白承应标识,而明编本则添加了张良这个配角人物来对这套曲词予以承应或挑动;在舞台表演时,艺人只需按照演剧的程式和格套对它进行“伎艺语境化”处理即可。
另一方面,相对于伎艺属性的角色扮演来说,曲词编写处于尊贵地位,不会简单地因为某种伎艺的表述方式繁盛流行,便会采纳为书面编写的表述方式。伎艺领域的表述方式能否落实于书面文本的编写体例,除了伎艺表述方式的繁盛壮大外,更需要书面编写领域的变革、促动因素。在角色扮演尚处于伎艺领域时,曲词编写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伎艺领域的表述方式来为曲词文本提供相应的体例规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曲词编写当然更多还是受到书面领域的规范和体例的主导,即使为伎艺表演而编写的“杂剧词”㉞也要遵循书面编写的体例规范,使用书面领域的表述方式。清人梁廷枏《藤花亭曲话》曾立足于散曲自身完备的表述规范,认为元杂剧是散曲的再发展:“诗词空其声音,元曲则描写实事,其体例固别为一种……作曲之始,不过止被之管弦,后且饰以优孟。”㉟这条曲词唱演形态的演变线,从“扮乐府”形态的生成史来说,曲词编写起初只是为了清唱,后来被缘饰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这就像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言说唱艺人在讲唱三国故事时“加缘饰作影人”㊱,于是出现了元杂剧这种“扮乐府”的演剧形态。从曲词的编演关系来说,曲词编写只需遵循书面领域的表述方式和体例规范,至于在表演方式上是把它“被之管弦”,还是把它“饰以优孟”,那是伎艺领域的事了。这样的曲词文本所表现的体例和属性,简单而明确,一是只按一个故事人物的立场来编写联套曲词,二是不必体现角色扮演伎艺的格式因素,这是承续乐府诗词而来的“曲”,而不是“伎”。
因此,当时人自然会认同曲词文本具有“曲”的属性,把它与散曲归为一类,与诗词相承,亦与诗词同观。周德清在《中原音韵》自序中言:“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并以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幺篇】之“忽听、一声、猛惊”为六字三韵的样例,又在正文所举例中多取杂剧曲文,如【仙吕金盏儿】之定格取自马致远《岳阳楼》,【中吕迎仙客】之定格取自郑光祖《王粲登楼》,【中吕四边静】之定格取自王实甫《西厢记》㊲。元人把散曲、剧曲同归于“曲”,统称为“乐府”,除了表明其文统雅正、出身高贵之外,还为了强调它们的文人创作属性。罗宗信认为“大元乐府”的创作“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㊳。周德清指出:“凡作乐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谓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㊴钟嗣成则在《录鬼簿》中将那些编撰乐府(散曲)、传奇(剧曲)的名公才人合为一编,在论“乐府”名公时说“若夫村朴鄙陋,固不必论也”,在评“传奇”名公时着眼于其文学创作能力。他的自序以及其友邵元长的序言都在强调这些人皆以“词章”名世㊵。这同样可以说明乐府(散曲)、传奇(剧曲)之间有着前后承续的亲缘关系,它们同是词章,同为曲文,而不是伎艺的属性和类别,也未呈现伎艺的体制因素。这样的书面编撰,既具有文学创作的属性,也符合文人名士的身份认同,所以,金元之际的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一批文人才会欣然涉足于杂剧曲文的编写,并以曲家名重当时。故而,元人才会把元杂剧与诗词同观,这并非因为他们只看重元杂剧的曲词部分,或只看到了元杂剧“曲”之属性,而是实际上他们当时确实在撰曲,撰写的杂剧本子就是联套体的曲词形态,这与他们原先所撰写的散曲套数在形态、体例上是相同的,皆不涉及角色扮演伎艺的表述方式和体制因素。只不过他们原先所撰写的散曲套数用于清唱,后来所撰写的杂剧套数则用于扮唱了。
基于以上分析,元人称“元杂剧”为“曲”,为“乐府”,这不是观念引发的结果,而是事实引发的结果,或者说是元人基于事实归纳的属性认识。这个事实就是:在元杂剧发展的早期,杂剧本子就是按一个故事人物的立场(典型者为叙事主人公立场)来编写的联套体曲词文本,当与组套体叙事散曲的文本形态相类,它承续了宋代即已出现的书面编写的“杂剧词”,而不是《元曲选》那样的阅读本形态,也不是《元刊杂剧三十种》那样的艺人演出本形态。后世关于元杂剧的重曲观念即是延续了这个事实归纳和认识前缘,而并非针对《元曲选》那样的元杂剧剧本得来的观念。所以说,这样的联套体曲词文本乃承续词曲之民间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在元杂剧出现之前就已吸收、整合了当时已有的套曲体式、曲唱乐体、曲文叙事,由此发展出了一个故事人物立场的联套曲词叙事体制,形成了自己在书面领域的叙述体制和书面规范,而无需顾及伎艺领域的角色扮演的规范和格式。立足于这样的杂剧本子,可知元杂剧早期在书面形态与伎艺形态之间有着互不相通、互不对应的表述方式,各遵其道,各行其事。元杂剧的伎艺性因素并非一开始就能够进入书面表述体制,那些体现了角色扮演体制因素的杂剧本子是后来才出现的剧本形态,属于“剧体”意义上的剧本(至于伎艺体制因素如何落实到书面文本而成为剧本编写的表述方式和体例,需要另作探讨)。参照于此,《元刊杂剧三十种》并非元杂剧剧本的残本、节略本或单脚本,而应该是增益本。
① 参见伊维德:《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杜学德:《固义大型傩戏〈促黄鬼〉考述》,《中华戏曲》第18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参见李金泉:《固义队戏确系宋元孑遗》,麻国钧等主编:《祭礼·傩俗与民间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④ 王兆乾:《池州傩戏与成化本〈说唱词话〉》,《中华戏曲》第6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 乔健等指出,宋元以来民间迎神赛社所演的院本、杂剧,没有曲牌体杂剧的影子,而是“直接承袭宋金杂剧的‘诗赞体’杂剧,相类于宋元间的词话搬演,其表演形态上仍属宋金时期的原始形态,而绝非较规范成熟的曲牌体杂剧”(乔健、刘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⑥ 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杂禁》“禁学散乐词传”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8页。
⑦㊴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搬词”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41页,第64页。
⑧ 参见田中一成:《中国戏剧史》,云贵彬、于允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2页。
⑨ 徐沁君校注:《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61页。
⑩ 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页。
⑪㉘ 赵义山:《元散曲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第147页。
⑫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⑬㉒ 毛奇龄:《西河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82页,第582页。
⑭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6页。
⑮⑱ 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上杂出版社1952年版,第63页,第118、119页。
⑯ 参见李家瑞:《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王秋桂编:《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3、34页。
⑰ 李家瑞:《傀儡戏小史》,《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第1—11页。
⑲ 李家瑞:《北平俗曲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⑳ 李家瑞:《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第30页。
㉑ 梁廷枏:《曲话》卷四,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86页。
㉓ 此问题,另可参见徐大军《依相叙事源流论——以宋元叙事性伎艺为中心》,《文化艺术研究》2008年第2期。
㉔ 任中敏《散曲概论》“内容第八”指出:“词仅可以抒情写景,而不可以记事,曲则记叙抒写皆可,作用极广也……重头多首之小令,与一般之套曲中,固有演故事者,即寻常小令之中,亦有演故事者。”(曹明升点校:《散曲丛刊》,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7—1078页)
㉕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㉖ 李昌集认为:“诸宫调本身对北曲之形成无任何意义”,“诸宫调本无‘联套’之观念和事实。元杂剧之‘联套’的根源别有出处,绝非从诸宫调而来,因此,作为‘入曲说唱’而本质为传奇之文体的诸宫调,其本身对北曲之发生、形成无实质性的影响和意义。”(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6页)赵义山《百年问题再思考——北曲杂剧音乐体制渊源新探》(《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指出:“现存北曲杂剧以套为单位的演唱体制,实际上就是宋杂剧与覆赚一体的融汇结合,与诸宫调其实并无任何体制上的关系。”
㉗ 赵义山指出:“唱赚一体,是北曲套数之体式的源头,甚而可以说北曲套数是对唱赚体式的直接借用……‘赚’之一体,乃词中之‘套曲’;‘套曲’一式,乃曲中之‘赚’体。”(赵义山:《元散曲通论》,第39页)
㉙ 任半塘着眼于配乐演唱情况,把词分为散词、联章词,大遍、成套词和杂剧词,而“成套词”包括鼓吹词、诸宫调和赚词三种。参见任中敏:《词曲通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6—7页。
㉚ 参见郑劭荣、谭研:《辰河高腔“条纲戏”的编创及其演剧形态探究》,《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李跃忠:《试析湖南影戏“桥本戏”的文本形态》,《武陵学刊》2013年第5期。
㉛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6—315页。
㉜ 胡忌:《宋金杂剧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50页。
㉝ 得意书生的这首通用上场诗,在《元曲选》中的《荐福碑》第一折范仲淹、《醉写赤壁赋》第二折秦少游、《射柳捶丸》第一折文彦博、《王粲登楼》第一折蔡邕、《冻苏秦》第三折张仪、《小尉迟》第二折房玄龄、《玉镜台》第四折王府尹等人物的口中反复出现。昏庸官吏的这首通用上场诗,在《神奴儿》第三折县官、《魔合罗》第二折令史、《遇上皇》第一折府尹、《勘头巾》第二折大尹等人物的嘴里反复出现。参见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
㉞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谈到宋代瓦子里流行的“俗文学”种类繁杂,于“小说”等外,又有唱赚、杂剧词、转踏等;第七章《宋金的杂剧词》指出:“在杂剧词中大约以大曲为最多,实际上恐怕最大多数是歌词,而不是什么有戏剧性的东西。”(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245页)又,任中敏《词曲通义》从音乐表演方式着眼,将词体分为散词、联章词、大遍、成套词和杂剧词五种。参见任中敏编:《词曲通义》,第6—7页。
㉟ 梁廷枏:《藤花亭曲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278页。
㊱ 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条,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页。
㊲ 张玉来、耿军校:《中原音韵校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71—73页。
㊳ 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中原音韵校本》,第13页。
㊵ 浦汉明:《新校录鬼簿正续编》,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49、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