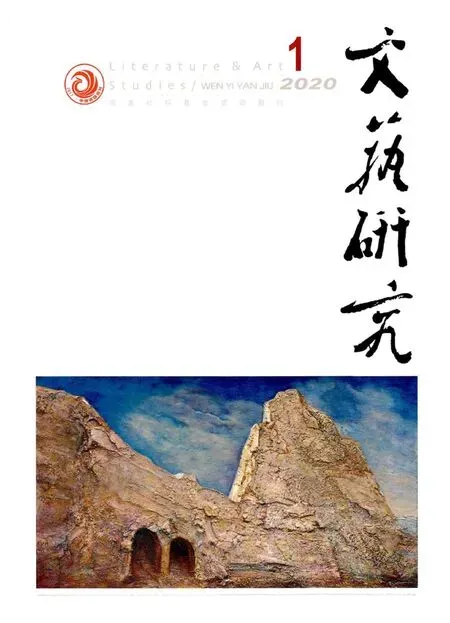陈寅恪、朱自清学术互动论略
——以1936年退稿事件为中心
孙羽津
20世纪前半期,在西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术全面开启了以学科分列、话语构建、观念变革为标志的现代转型历程,既体现着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与文化诉求,又难免坠入“西化—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和价值迷思。与此潮流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在打通古今中西的通观视域中,更加注重发掘中国学术与文化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质素,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索学术独立自强之路。那么,趋新与守正、崇西与持中的种种分野,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如何被表述?在不同主张的学术互动中又会产生何种影响与趋向?本文拟以陈寅恪与朱自清一段鲜为人知而又耐人寻味的学术公案为例,管窥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曲折历程及其间蕴含的典范意义。
同为20世纪文化名流,陈寅恪以史学见长,始终持守“中体西用”的本位立场,朱自清则为新文学名家。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史研究,不甚措意二人关系。事实上,他们有着长达二十余载的同事之谊。1925年,陈、朱先后受聘于清华,直至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陈寅恪不久南下①。在这段同事生涯中,朱自清对陈寅恪始终钦敬有加。早在入职之初,朱自清就去聆听陈寅恪的课程②。此后,朱自清还在日记中专门记录了陈寅恪的大量学术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来自陈氏著作,还包括他们在寓所、宴会甚至学生答辩会上论学的内容③。有一次,当友人提及陈寅恪的某篇论文时,朱自清尚未读到,竟为此感到“甚惭”④。试想,如果朱自清没有把陈氏论著视为不可不读的当代学术经典,恐怕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惭愧感。然而,陈、朱交谊也经历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一度改变了二人之间云龙相从的关系,那就是发生于1936年的《清华学报》退稿事件。
一、欲迎还拒:退稿事件及后世余波
1935年10月,朱自清受命兼任《清华学报》编辑部主任,诚恳地向陈寅恪约稿,陈亦欣然接受⑤。然而时隔一年,当陈寅恪向朱自清询问审稿结果时,却吃了闭门羹。朱自清1936年10月22日日记云:
昨日陈寅恪电话,询问彼寄投学报翻译哈佛大学某杂志发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之原稿,是否准备采用。因不易决断,故答以不采用。然恐已造成问题矣。⑥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曾由哈佛大学教授魏楷(J. R. Ware)译成英文,发表于1936年4月出版的《哈佛亚细亚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卷第1期。然而,朱自清并未因该文得到国际权威学术机构的推崇而放松审查,只可惜他没有把审稿意见写在日记里。即便如此,我们至少能从日记的语势转折中推断,陈文的某些观点大概是朱自清无法认同的,而朱自清自知约稿在先,遂形成“不易决断”的心理,即便最终决意退稿,仍担心“造成问题”——影响与陈的关系。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朱自清在退稿的第二天再次阅读了该文⑦,但仍未做出正面评价,退稿的决定自然也没有撤回。
自此之后,陈寅恪没有在他处发表此文的中文原稿,直到晚年还叮嘱弟子蒋天枢在编纂《陈寅恪文集》时不收此稿⑧。今行于世的《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已非朱自清所见原稿,而是退稿事件发生十一年后,由程千帆据魏楷英译本回译而成者,发表于1947年7月10日出版的《国文月刊》第57期,1984年曾收入程千帆《闲堂文薮》(齐鲁书社1984年版)。到了21世纪初,《陈寅恪集》问世,陈氏二女念及“父亲原意”,同时又为了“从不同角度反映父亲的学术生涯”⑨,将此文收入《讲义及杂稿》,而没有收入陈寅恪生前审定编目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等论文集中。
陈寅恪自佚原稿的背后或许有种种考虑,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文中的主要观点。陈寅恪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指出,中唐贞元、元和时期,“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韩愈早年即已深嗜小说,后来创作《石鼎联句诗序》《毛颖传》等,是“以古文为小说之一种尝试”⑩。十余年后,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深化了他的观点:
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⑪
从《韩愈与唐代小说》到《元白诗笺证稿》,陈氏把韩愈“以古文为小说”的论断拓展到古文运动与唐代小说的关系上。然而这一系列观点问世后,屡有人反对。比如,钱穆曾直言陈寅恪这些观点“不一定对”,并援引《旧唐书》中的传统观点否定了古文运动与唐代小说的关系⑫。李长之曾系统梳理唐传奇的发展历程,其间虽未直接否定陈说,但对沿用陈说的刘开荣、张长弓等的论述,皆不甚许可⑬。此后,黄云眉、王运熙等针对陈氏观点做了更为深入的批评:一方面指出,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在建立道统,排斥佛老”,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论说文“毋宁是更为重要的宣传文字”,而“这种论说文是无法以试作小说来做准备工作的”;另一方面指出,所谓韩愈的小说作品,陈氏仅举出《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两篇,而这两篇都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其时古文运动的高潮期早已到来,“从时间上讲,韩愈是不可能以这两篇文章为试验来兴起古文运动的”⑭。时至今日,古代文学研究者大多认同王运熙等的批评意见,而对陈氏观点持保留态度⑮。
反观1936年退稿事件,朱自清虽未详陈退稿原因,其看法恐怕不会与上述诸家有太大差别。退稿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年,朱自清撰写了《中国散文的发展》一文,分别讨论了唐代古文和传奇小说,虽然把它们都称作当时的“新文体”,但无一语论及二者间的关系,且明确强调传奇小说与“俳谐的辞赋”关系密切⑯,这显然不同于陈寅恪“以古文为小说”的论断。
二、时代禀赋:文体升降与文化隐喻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及其后一系列观点,虽然屡受质疑,却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价值和时代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以来的批评者大多从传奇与古文文体之别出发,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质疑。但实际上,陈寅恪的论述中似乎有意回避“传奇”这一传统文体概念,而是采用更具融摄性的“小说”一词。有学者指出,陈寅恪的“小说”话语蕴含着耐人寻味的西学背景,特别是唐代小说“文备众体”的论断,与西方文学“文体混用”的特质遥相呼应⑰。所谓“文体混用”(the mixture of styles),即打破崇高的悲剧文体、中等的论战讽刺文体、低等的喜剧文体在风格和主题上的层级界限⑱,这在《荷马史诗》直至19世纪欧洲小说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推动着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陈寅恪着意点出古文作为“雅正之文体”的特质,相比之下,小说为当时“非正统而甚流行之文体”⑲,可见韩愈“以古文为小说”之举,实则消弭了具有崇高文体色彩的“古文”与低等文体色彩的“小说”之畛域,与以“文体混用”为标志的西方文学发展潮流隐然相合。可以说,陈寅恪的这一研究,具有其自道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⑳之性质,他首选海外学术刊物发表《韩愈与唐代小说》,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陈氏这一融摄中西之运思,并非故作高深、哗众取宠,实有其复杂而微妙的时代背景。众所周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人有感于西方小说在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中的重要作用,发起“小说界革命”,小说便从传统观念中的低等文体被擢拔至“最上乘”的地位㉑。十数年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高倡文学革命,激切地宣布古文已死㉒,褫夺了它千百年来作为崇高文体的冠冕,还特别指出古文家祖师韩愈“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㉓。在时人看来,即便是不属于白话范畴的传奇小说,其价值也远胜于载道的古文。甚者如鲁迅更直接地把韩柳古文和所载的孔孟之道合起来批判,从根本上否定古文的价值:“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㉔
纵观清末民初文体价值观的巨变,先是小说地位急遽上升,随后古文地位一落千丈。这一颠覆性变化,缘于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西化—现代化”价值趋向,深刻影响着当时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开篇盛赞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旋即指出唐人小说“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㉕,而后强调像韩愈《毛颖传》这类“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作品“无涉于传奇”㉖。如果我们对鲁迅全盘否定古文的立场有着充分了解,便不难感受到他时时注意区隔传奇小说与韩愈古文的背后,潜藏着一种时代性冲动,即颇不愿让腐朽载道的古文染指生动优美的小说。古人“訾其卑下”的传奇小说,在鲁迅心目中实为崇高文体,而他所谓“韩柳辈之高文”一语,即便在看似严肃的述学语境中,也难掩个中的讽刺意味。稍后的郑振铎则不再像鲁迅那样小心翼翼地分辨唐传奇的特征,使它不受古文的染指,而是大胆宣称传奇是古文运动的附庸。客观地讲,传奇小说在唐代尚难比肩古文运动的声势,更何况对时下的文学革命而言,古文运动尚有相对于六朝骈俪文的革命合法性资源可供汲取。这样看来,在没有多少历史依据的情况下,把传奇说成古文运动的附庸,未尝不是借重古文运动塑造传奇小说历史地位的一种书写策略。然而,古文毕竟是载道的,韩愈“不仅仅要做一个文学运动的领袖,他还要做一个卫道者,一个在‘道统’中的教主之一”㉗,他便无法逃脱遭受严厉批判的厄运。相比之下,传奇小说“有若希腊神话之对于欧洲文学的作用”,“有一部分简直已是具备了近代的最完美的短篇小说的条件”,本质上与文学革命的时代精神相通。因此,郑振铎并未止于“附庸”之说,进而强调传奇小说“由附庸而蔚成大国”㉘,最终远超乎古文之上。要言之,鲁迅强调传奇与古文之别,在异中暗寓臧否;郑振铎则不惮把二者绾合起来,在同中直言高下。无论何种书写策略,率皆宣示着小说地位的优美崇高、古文及古文家的落后腐朽,这一附丽于“西化—现代化”价值链条上的表述,伴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鲁、郑二著的经典化历程,持续影响、塑造着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文学常识。
明确了这一时代背景,再看陈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研究,其研究目的恐怕远不止文学史个案考证,也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陈氏假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声势日隆的“文体混用”现象,揭示“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之机理,彰显古文无施不可的包容性与生命力,这与新文化阵营“古文已死”的宣判形成鲜明对立,意在化解“西化—现代化”思潮下古文与小说的紧张关系。陈氏的这一撰述宗旨,在其二十年后《论韩愈》一文中做了进一步发挥。该文开篇明言:“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讥之者之言则昌黎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㉙如果把论韩愈者分为古人和今人、“誉之者”和“讥之者”的话,那么古人中虽不无“讥之者”,却寥寥可数,在“讥之者”的队伍里,大多是清末以降“西化—现代化”思潮影响下激进反传统的今人。这样看来,陈寅恪“蚍蜉撼大树”的批评颇有所指,他不仅在研究历史上的韩愈,更是在回应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他在文中历数韩愈在文化史上的诸多贡献,首论其“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㉚。众所周知,儒家道统及载道的古文是新文化阵营攻讦最力之处,而陈寅恪意在证明韩愈建立道统的性质并非顽固保守地卫道、载道那么简单,而是在充分吸收佛教统系之说基础上的自我更新。次论“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谓韩愈之所以开启宋学途径,是由于“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㉛,在儒家立场上进行自我革命。由此可见,韩愈的卫道、载道,本质上具有“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㉜的性质,且其所卫、所载之道本身亦具革命性。相比之下,文学革命家把韩愈的革命性和载道性一分为二,先部分肯定,后从根本上否定,颇欠圆融,未见中华文化转折与发展之大势。在论证儒道的合理性之后,陈寅恪又以“改进文体,广受宣传之效用”㉝一章,论证古文的合理性。他总结梳理了以往有关韩愈与唐代小说研究的观点,强调古文原本施用于先秦两汉的高文典册,到了韩愈手上,却有意改作民间流行小说,使古文成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㉞。由此可见,韩愈“以古文为小说”的本质是打破雅俗界限,与时俱进地承载时代精神。通过建构这条与西方文学“文体混用”之特质差相仿佛的发展路径,陈寅恪与近代以来全盘否定韩愈及其古文价值的反传统论调展开隐性论争:韩愈古文既有意取径民间小说,便不能简单地视为“新贵族文学”,亦非“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韩愈古文既在当时“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与时下文学革命精神相通,那么,建设新文学便不必先置古文于死地,何妨效法韩愈当年打通新旧,“转旧为新”㉟。
总而言之,在近代以来“西化—现代化”思潮中,韩愈被认为是旧文化和旧文学的代表,而小说是新文化的载体和象征。陈寅恪以其“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文化自觉,以西学之道,还治西化迷思,着意通贯韩愈古文与小说之关系,为古文及其所载的儒道正名,以隐性的述学姿态回应时代思潮,参与文化重建。
三、陈、朱合契:雅俗共赏与新旧调和
由此反观1936年退稿事件中的朱自清,恐怕他也难以超脱时代环境的影响。朱自清早年入北京大学,师从胡适,积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新诗、小说、散文创作和西方文学译介,而且还在清华中文系成立之初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㊱,打破了古典文学课程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一时期,朱自清参加了新潮社、文学研究会、朴社等多个新文化社团,与胡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新文化阵营中各派人物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即由新潮社1923—1924年初版,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初版由文学研究会的衍生组织朴社1932年出版。这两部文学史可看作当时新文化阵营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作为这几个社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朱自清十分看重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㊲,且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郑振铎往来密切㊳,我们不难想象这些著作在朱自清个人知识体系建构中发生的影响。而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着意为古文正名,与新派文学史书写形成鲜明对立,这也意味着对朱自清的文学史常识构成了挑战。甚至,我们不能排除潜藏于新派文学史背后的推崇小说、贬抑古文的时代情感,会在更深层面促使朱自清做出退稿决定。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在陈寅恪遭遇退稿十一年后,即1947年7月,《韩愈与唐代小说》中译稿最终还是发表在由朱自清创办、编辑的《国文月刊》第57期上。就在三个月后,《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卷首刊发了陈寅恪《长恨歌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之一)》,这篇文章秉承并深化了《韩愈与唐代小说》的主要观点。同月,朱自清开始撰写《论雅俗共赏》一文,此文归纳并正面引用了陈寅恪从《韩愈与唐代小说》到《长恨歌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之一)》的主要观点:
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㊴
虽然我们无法确证此时朱自清已然参透陈寅恪假借“文体混用”之运思,但至少可以说,把古文与传奇小说的互动关系理解为雅俗共赏的趋势,确与陈文脉息相通。这里,朱自清不再像撰写《中国散文的发展》时如鲁迅那样严明古文与传奇小说之大防,他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发展新文学“并非打倒旧标准”,而往往要“新旧打成一片”,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㊵,在这个过程中,“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㊶。
朱自清在20世纪40年代的这一转向并非偶然,在他同时期出版的《经典常谈》和《诗言志辨》两部代表作中可以找到更多佐证。据朱自清日记记载,《经典常谈》原名《古典常谈》,出版前易“古典”为“经典”㊷。顾名思义,“古典”之名隐含着时代性和限定义,在激进的反传统思潮中,固难为读者所亲近;改用“经典”之名,则有意消弥古与今的对立,与陈寅恪以“小说”代称“传奇”的用意不殊,都是为了启诱读者发现文化传统中的永恒价值。正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㊸。为了让读者确切地了解文化传统,即便是书中各篇的次序,也都“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㊹。然而,朱自清岂不知早年投身的新文化运动“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攻击”㊺。可是,朱自清到了写作《经典常谈》的时候,仍把富于文学性的辞赋、诗文放在全书最末的位置,把载道的群经放在全书之首,而且介绍群经的篇幅几近全书二分之一。就这样,朱自清在践履“将中国还给中国”理念之际,慢慢地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原初路向。
如果说《经典常谈》只是重现载道的传统,那么《诗言志辨》则近乎推崇载道的传统。此书梳理了从先秦到近代的文学观念,意在证明中国文学的言志传统“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这一传统屡经引申、拓展,“始终屹立着”,“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其原实一”㊻。朱自清之所以着力论证“言志”与“载道”的同一性,其背后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他在书中明言:“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言志”与“载道”之所以形成对立,是因为现代人认为“言志”就是“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而“载道”是“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道——表现出来”。朱自清特别标注了这段话的出处:“邓恭三记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三七面、三四面。”㊼此书即新文化阵营又一重要著作,由邓广铭(字恭三)根据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讲演整理而成,当年9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后版权页题“讲校者周作人,记录者邓恭三”。可见朱自清笔下的“现代人”实即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周作人,大概考虑到观念上的针锋相对,才隐去了姓名。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中坦言,这部书不算学术著作,阐发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了表明自己“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又云“要说明这次的新文学运动,必须先看看以前的文学是什么样”㊽。在周作人看来,文学史上凡属载道派的,“便没有多少好的作品”,这包括被新文化阵营集矢的韩愈,他“仅有的几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记了载道的时候偶尔写出的”;而凡属言志派的,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三百多年后文学革命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㊾。就这样,周作人以“言志”接榫新文学,以“载道”统摄旧文学,为了标明“新”与“旧”的对立,便着意凸显文学史上“言志”与“载道”的对立。而朱自清之所以努力弥缝二者,主张言志“不离政教”,并指出历史上“文坛革命家也往往不敢背弃这个传统”,实是因为他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假借“言志”建设新文学的流弊——以一种玩世不恭的、逃避式的、消遣的、充满着个人好恶的“趣味”,在新文学的路上“越走越窄”㊿,难以为现实生活提供意义,难以为新文化指示方向。于是,朱自清转回头去,重新发现他和同人们曾经反对过的“文以载道”的价值,在历史大势中省察到“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51],进而形成了“新旧打成一片”“新旧双方调整”的文化立场。
可以说,周作人标举“公安”“竟陵”,与鲁迅、郑振铎标举传奇小说的策略一样,都是为文学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历史资源;而朱自清纠正周作人,也和陈寅恪与鲁迅、郑振铎的隐性论争一样,欲通过文学史的再度阐释,揭示传统相对于现代的种种价值,消释“新”与“旧”的紧张关系,为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合理性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出身于新文化阵营的朱自清最终和“不古不今”的清华同事陈寅恪渐行渐近。
结 语
事实上,早在1928年,以文学创作而声名大噪的朱自清就明确宣示了自己的道路:“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52]然而,国学与文学的关系已不可能再像古人所谓“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53]那样,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主从关系。正如朱自清所意识到的,“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54]。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处理中国固有思想文化与新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欲兼顾二者的朱自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此后不久,朱自清接掌清华中文系,他先是尝试着把自己的娱乐变成了职业的一部分,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转而认真听取了他的同事陈寅恪有关西方大学注重古典训练的“谲谏”[55],把更多精力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之中。在调和新旧、转旧为新的探索中,朱自清明确提出“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的理念[56],这与陈寅恪主张“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别无二致,且更加明确了“不忘本来”的基础性地位。1934年,朱自清把这一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学术理念正式写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之中,为变革时代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指示了方向。
然而,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文化自觉意识的确立与成熟,不仅体现在宏观学术理念上,更需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互动中不断扬厉时代禀赋、激活学术话语。如果说1934年《中国文学系概况》的诞生标志着朱自清的文化自觉意识在学术理念层面的确立,那么1936年退稿事件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他所保有的新文化阵营思想惯性的批判性延展。在此之后,朱自清渐渐褪去了新文化阵营的机锋,以其“不忘本来”的“职业”眼光,自觉反思昔年的“娱乐”活动,并通过对“载道”与“言志”的绵密考证与学理分析,出色完成了一次调和新旧、转旧为新的话语重构。在与陈寅恪渐行渐近的道路上,陈氏有关韩愈与唐代小说的系列论述,再次映入朱自清的学术视野之中。1947年的朱自清彻底摆脱了十一年前欲迎还拒的纠结心态,不仅接受而且推进了陈寅恪的学术观点,以文体混用的特质证成雅俗共赏的趋势,以文学研究推动文化研究,由隐性论争转向积极建构。至1954年,陈寅恪发表《论韩愈》一文,复以“外来”明“本来”,以“他觉”觉“自觉”,全面论证了韩愈建立道统及其载道古文的文化价值,为这场学术马拉松做出了精彩总结。
从陈寅恪与朱自清学术互动历程中,不难窥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曲折历程与复杂面相,其间多元开放的话语建构、融摄中西的学术境界、独立自觉的文化担当,值得我们在当下学术进程和时代语境中进一步体证、赓扬。
① 参见姜健、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2、310页;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9、250页。
②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俞大维等:《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
③④⑤⑥⑦㊲[55] 朱自清:《日记上》,《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8—209、216、246、264页,第268页,第387页,第442页,第442页,第6页,第263页。
⑧ 程千帆:《闲堂文薮》“题记”,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页。
⑨ 陈流求、陈美延:《陈寅恪集后记》,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00页。
⑩⑲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0—443页,第443页。
⑪ 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页。
⑫ 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220页。
⑬ 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第3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年版,第38、39页。
⑭ 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256页;黄云眉:《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文史哲》1955年第8期。
⑮ 参见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页;陈尚君:《转益多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崔际银:《诗与唐人小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⑯ 朱自清:《中国散文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⑰ 参见张丽华:《从“传奇文”溯源看鲁迅、陈寅恪的“小说”观念》,《岭南学报》2017年第2期。
⑱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⑳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㉑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35页;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十,第6—10页。
㉒ 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鲁迅:《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㉓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第137—138页。
㉔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4、15页。
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卷,第73页。
㉖ 鲁迅:《中国小说史大略·唐之传奇文(上)》,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㉗㉘ 郑振铎:《插图本白话文学史》第2册,朴社1932年版,第486页,第493页。
㉙㉚㉛㉝㉞㉟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㉜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㊱㊳ 姜健、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82页,第123页。
㊴㊵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第220、223页。
㊶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文艺复兴》1946年第6期。
㊷ 朱自清:《日记下》,《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㊸㊹ 朱自清:《经典常谈·序》,《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第5页。
㊺ 朱自清:《论严肃》,《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38页。
㊻㊼ 朱自清:《诗言志辨·诗言志》,《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135、169、172页,第130、172页。
㊽㊾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2—3、36页,第39、51—52页。
㊿[51] 朱自清:《文学的严肃性》,《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480页,第480页。
[52] 朱自清:《那里走·我们的路》,《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43页。
[53] 杜甫:《贻华阳柳少府》,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5页。
[54]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127页。
[56] 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