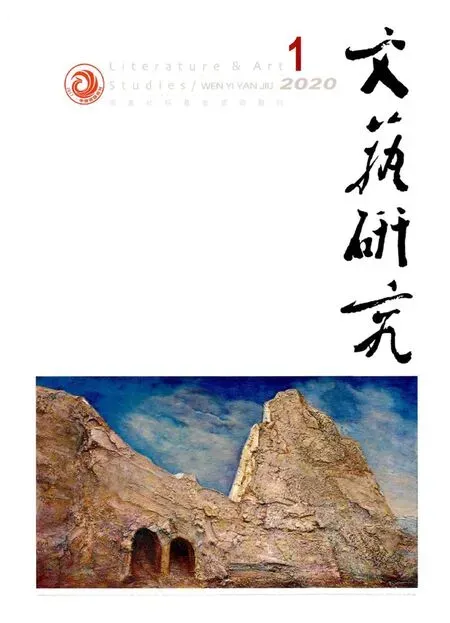转喻上海:后戏剧剧场时代的城市与表演性
蔡 潇
一、上海双年展“51人项目”①:被展演的日常
人与城的关系是上海双年展自诞生以来持续探讨的议题。自第一届“开放的空间”(1996)到第十一届的“何不再问?正辩,反辩,故事”(2016),人与城的关系以及空间探寻,越来越以实验与跨界的形式出现在展示项目中。2002年的“都市营造”已从保护城市鲜活而直观的记忆更进一步,让记忆转化为新一代都市主体的精神认同;2006年的“超设计”中,三个主题之一是“日常生活实践”,致力于让艺术成为日常生活实践之一,而非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个特殊领域。2008年的“快城快客”力图捕捉城市飞速发展中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与状态,其中,荷兰艺术家杰妮·范·黑思维克(Jeanne van Heeswijk)的《上海梦拥有一张城市金卡》②直接呼应迈克·皮尔森(Mike Pearson)和米歇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的“戏剧考古学”(theatre archaeology)③理念。2010年的主题是“巡回排演”(Rehearsal),标题直接使用戏剧修辞学概念,力图打通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这一设定可类比于米歇尔·德塞图对空间的“划界”(making out boundaries)概念,即以身体创造空间叙述行为,从而创造一个可以上演各种行动的现实剧场。这种剧场为即将发生或开始的行为提供空间,从而创造了一个领地,它是行动的“根据地”(base)和“剧场”(theater)④。
2016年上海双年展的外延项目“51人项目”(51 Personae,下文简称“51人”),以对51个民间人物行为实践的探询与记录呈现51段“都市加速”中的“慢生活”,从而构建出一个疏离于当下的“异时空”。这个项目难以定义之处在于,它的展演形式进一步模糊了戏剧、表演与日常实践之间的界限。该项目中所包含的愿景式的提议、城市考古学、身体与空间叙事等维度,聚焦的不仅是对城市生活的重新想象和发现,还有关于城市的历史和时间性的思考。这一系列作品几乎无意识地创造出一种“行走- 记忆- 考古”的征象,让表演与日常不可界定,从而在展场和街道之间开拓出新的领地。这些看似透明、散漫的日常实践,试图越过规划性的、确定情景中的政治意图,在都市加速中保有一种对乡愁的审慎追踪。它们成功地制造出熟悉城市的新民间地图,尽管这种地图并没有提供给观众任何一种抵达城市精神核心的路径,但却以民众随机组装和表演的偶发经验,构成关于城市精神的中介性思考。
在这个项目中,策划者的确关注到城市飞跃与乡村失落间的大片过渡空间(buffer zone)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处于边缘与湮灭过程中的生活形态,并以一种身体实践的方式回溯和呼唤过去的遗存。但是这种实践策略极易导致都市实存的奇观化建构以及日常的表演化痕迹,以致异化实质上与城市“时间同龄”(synchronization)的异质生活形态。作为一种实验策略,这种展演的意义不应限定为对一段前城市化的市民生态的怀旧或“悼亡”,乃至演化为一种都市怀旧之旅或对都市传奇的发掘与寻访。这种展演应该致力于激起这样的思考:是否有一种庞大的、犹如乡村传统一般的城市民间文化依然活跃,却正被都市化的速度和话语所覆盖。它真正的隐秘价值不是等待我们去发掘与展示,而是给予我们一条通道,在一座城市遗失的角落去测量我们已经到达的距离——不是在进步和改善的必然路径中,而是简单地经验变化的真实、时间的通道,以及那些某种程度上一直伴随我们的丢失了的日常形态。这是以一种微妙的、有想象力的艺术实践,去经历“过去”分离于“现在”的场面。因此,项目追求的就不仅是展现一种对于传统事物的记忆,而是要修复,要通过认知和理解过去来重新观照现在。这也是伊丽莎白·威尔逊所言的“唯有通过这种形式去连接城市变化的元素,通过承认变化既是失去也是丰富,我们才能够充分地接近生活于都市空间的经验”⑤。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试图从表演学的范畴出发,探讨现场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关系,以及这种关联如何发掘城市的文化面向并对之进行“考古”,并由此延伸至几个次属问题——什么是现场?什么是表演?什么是社会参与?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的核心,本文将聚焦于日常、民众与城市历史之间复杂而相互影响的变化与实践可能性,这是艺术与城市之间的内在动力,也是它们可以互为镜像和记录的档案学原理。
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20世纪以来剧场研究中的两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城市作为剧场的戏剧学历史,以及内在于它的剧场作为城市的档案学原理。这关乎身体、日常、节奏和流动所建构的叙事文本如何触及了微观的民间历史。行走的剧场、漂流之物与玩耍的地方不可避免地重合在城市的不同面向中,例如,街道并不是严格地从建筑中分离出来,而是与建筑构成一个连续的形式。这种活跃的连接因素,其基本原理是表演所暗示的时空运动。第二个要素是城市的面相学(physiognomy)——通过展演中看与被看的张力去解读蕴含在空间形式中的社会灵魂⑥。作家乔纳森·拉班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现代大都市存在着有别于从前的“柔软城市”的一面,不仅城市生活依赖表演,而且这些表演是频繁变化和难以把握的⑦。因此,我想要强调的是,表演同样依赖城市这一天然的舞台空间。在更内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城市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内在于城市的日常,并跨越街道与舞台的界限,将城市还原为一个包含着“柔软面向”的活的有机体,而真人实践项目必然是后戏剧(Postdramatisches)⑧构作(die Dramaturg)⑨中最具持续性、最深入生活的表演实践。
(一)时间性:磨刀人⑩
在“51人”中,有两个例证在不同层面上通过地理“划界”实现了从空间到时间的追寻。第一个是“骑自行车的磨刀人”。一小群志愿者跟随一位来自江苏淮安的磨刀师傅,体验他一天的日常生活,重绘了一份与都市消费空间截然不同的城市地图。在这份地图中,磨刀人出没的地方集中在弄堂口和居民社区深处,隔绝于不远处的购物中心和娱乐广场。但这些地方却又处于都市的腹地(新昌路与北京西路交汇处周围),因此他和他的日常劳作犹如一个对抗“都市加速”的寓言,嵌入城市日常,成为都市空间中一个异质性符号。然而,这个事实本身不具有任何戏剧性,相反,磨刀人的谋生姿态首先提示的是严肃而沉重的生存议题,其次才是它所负载的(失落的民间/乡村)文化符号。在这个项目的展演中,媒介(摄影机)的介入创造了令人不适的矫揉造作感,如果剔除摄影机的凝视,磨刀人的日常劳作中包含着深刻的日常美学,记录实质上破坏了这种美学性。这也是实践艺术的悖论——当具体而真实的生存实践被以戏剧或影像的方式强调,再现为一个被注目的“事件”时,它原来所携带的真实而苍凉的美学因素就被消解了。这种消解的本质源自观看对当下(the present)的破坏:凝视制造了距离,跟随者不再认定磨刀人与自己生活于同一个时间线中,现在/当下被过去/记忆所取代,联系着过去的日常行为成为表演和怀旧的符号,那原本属于他的真实与生之隐秘,因为观看的介入而失去了其独有的私密的见证价值。这里我无意展开讨论拍摄是否应该存在,而是想强调磨刀人的日常劳作中包含着深刻的表演性,城市街道构成了他的剧场。这种表演性并不需要被特别地提取出来,成为都市日常中的奇观(spectacle)。当它被提取和观看的时候,它的存在只剩下表演,这种表演便是可以被复制和制造的,它因此成为一个假象。但是,追踪和发现它仍然具有启示意义,一次追踪实践暗示出都市中某些日常已在原有秩序中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抗着时间加诸空间的强权,一个遗漏的时间与当下保持着距离,与加速的城市叙事保持着相反的方向。
理查·谢克纳在谈到“环境剧场”(environmental theatre)时认为,表演和观众之间的空间交换,以及两个群体间的整体空间探索——这种模式紧密联系着家园(home)和街道⑪。日常的街头生活是由运动和空间交换所标记的;街头范式是一种特殊的街头生活形式,取决于日常规章中日益增强的要求。谢克纳强调,街头表演中“事件”的定义取决于它对规则的保持或破坏,这种表演是对既有传统表演模式的超越和转换。赫尔曼·鲍辛格以民俗学的视野拓展了这一戏剧学概念,他认为,在时间加速中,时空之间并非平行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在空间上关注“乡愁”的运动,一般都要求时间上向过去铺展,而强烈的空间扩展一般都具有非历史的特点⑫。因此,聚焦于历史的表演才需要在常规之外尝试一种空间的时间性再现。
当大街成为“集体的居所”⑬,这种时间性便与多层次的感知相呼应,这种感知又会制造出多样的时间性:在实践者看来,之前未曾显现的历史层面浮到眼前,记忆掌权,而现代主义的时间则远不仅是创新的现代化逻辑⑭。正如本雅明所言,实践者是穿越时间的行者,城市是他的“记忆交通工具”⑮。磨刀人对时间的呈现,是实践者在双重意义上对历史元素再现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后果不能被误读为非历史的——它实质上是对超越时间的历史的一种修正,即,在历史因素的去历史化所造成的“本土异域风情”中瓦解关于历史有限的视域。例如,磨刀人文本中带有明晰的时间与空间属性:从淮安的村庄来上海十八年。这个语境唤起的不仅是一种都市加速中的乡村失落图景,也是城市在时间中的失落。空间上从乡村置换到都市,时间上从前城市化进入飞速城市化阶段,磨刀这种行为在双重的失落中使乡村空间与当下的城市街道重合了。淮安村庄的磨刀仍然是发生在从前的故事,磨刀人和他的劳作的消失一起构成乡村失落的逻辑,这个逻辑又被编写进城市时间的分岔中。也就是说,他其实伴随着村庄的消失而消失,这种消失首先是空间性的,其次才是时间性的。当他生活在都市的世俗社区时,他不是复活了某种技艺或传统,而是保存了既是城市又是乡村的记忆和技艺,磨刀人由此成为连接时间(过去/现在)与空间(城市/乡村)的交叉载体。
在《戏剧/考古学》(Theatre/Archaeology)中,尚克斯和皮尔森强调一种新的戏剧与城市研究方法是直接划出行走于城市的经验(如皮尔森在哥本哈根的例子)⑯。当代城市再生故事的艺术光环取决于展览主义,这也是本雅明拱廊计划的核心⑰。闲逛者明确、具体且有创造性地穿行于城市之中的行走方式是非指向性的,是在大方地浪费时间,这是19世纪巴黎的一项发达的文化技巧⑱。将这种自本雅明以来的“闲逛哲学”与当代的城市表演艺术相关联,并先在地假定日常实践可以通过当下的流动性给予表演一种生命力,这种方法是真人展演实践项目的核心,尽管这个思路在具体行动中很难完整贯彻。城市/乡村,过去/现在,日常生活实践的表演涉及历史与记忆作为档案时间的拓扑,人们可以装置时间并描述事件。这是一种类似于熟悉的网络或数据矩阵的时间景观,乡村与事件在几何学似的纷乱而又自我折叠的形式中被推远,而时间被拉近。在磨刀人的例子里,实践行为本身便是通过城市的行走实践对飘散的历史的把握和创造,这不在宏观的历史记录中,而在它之外。
卡罗·金茨堡将表演的辩证美学定义为对事件和世界遗留线索的预测性追踪⑲。这意味着表演实践必须尝试去关注和解释如何看待作为考古要素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我们社会纹理中一个忧郁的面向。在戏剧/考古学的维度,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日常实践所包含的当代历史性物质,这是经由过往和昨日留在当下的时间感,它是隐藏在人们所居住和观察的世界之中的历史的能动性。这种人类学观点附着在民众和事物所拥有的地方历史根源和社会纹理的理性风格之上。在背景上(在西方至少有两个世纪之久,在中国是近二十年以来)包括工业城市景观的经验、底层社会的观念和生活、罪恶及其记录、人们的身份获得与失去的信息特征。这些也是尚克斯所定义的“科学的过程”,其中,摄影的发明、客体凝视的概念、他者与相异性、文献的官僚性、新的公共与私人空间在现代是真实而具体的考古历史的主体性,也是我们自己的主体性⑳。“51人”恰是这种观念的一个试探性的注解,尽管它的考古意图没有那么明晰。可以从中提取的恰恰是这个项目有意无意忽略的面向,比如磨刀人作为一个活档案象征背后的失落与痛楚。这种痛楚是整个时代的痛楚,也是乡村和城市的痛楚。他不是作为奇观而存在,而是作为伤口。在这伤口之上,是实践行为丈量出的一个背向都市加速的距离。
(二)行程与划界:船长日志
在“船长:钱正峰”㉑的例子中,“划界”越出了上海的地域中心,蔓延到与上海相连的周边水域。这是一个典型的从中心向边缘的进路图,包含不曾进入都市核心视野的空间以及与此相连的生活形态:船与水构成的生活。这种形态天然地处于前现代时期。在今天,空间线路与生活形态依然存在,却处于一种没落的进程中,船长努力奋斗的目标也是实现从水到岸的跨越。在这个例子中,一次随船而走的实践便具有了空间考古的意义,进入了日常表演的范畴,就此而言,水上的漫游类似于磨刀人的都市行程:游历舒放了沿途的空间,这是一种由叙述、道路和脚步引导的编舞,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大空间移动描绘了一种地形图,一种空间阐释。
在这个旅程中,道路/河流连接着熟悉的地方并指引着重复行动的可能性,不同的码头和停靠点演绎着不同的地方传奇。出发与停留犹如一个文本的叙述行为,将地方记忆组合进一个事件的序列,实践行为提示先辈曾经行走于这些路途,而景观已今非昔比。如果日常对于未被接纳的眼睛是不可见的,那么行走就是以身体重新标记了祖先行动的地点,去游历这样的景观正如一个风景被记入存在,它伴随着人类意义的沉淀。正如朱利安·托马斯的表述,“道路是歌之版图,漫长的叙事之旅将会铭记地点于歌声中。去游历这些地点就是去歌唱这个世界再次进入存在”㉒。在现代都市加速的寓言中,船长的行程里包含了吸附功能——吸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遗忘和飘散的韵律,而今它们是萦绕在都市凛冽的加速轰鸣之外的回声与低吟。那些地点是时间韵律的碎片,随着航船的消失,它们从此失去最后的叙述者。福柯认为“航船”是出类拔萃的异托邦(heterotopia)㉓,它本身就表征着失落文明的乡愁。这一例证中的船长固守着最后的游牧之梦,从码头到码头,从河到岸,像一个行吟诗人踏着自己的行程,划出自己的地形图。这一地图本质上是反- 地图的,因为它重新复活了形象,恢复了对于行程的描绘。船长的航拍日志类似于一份水上的“步行日志”,以现代化的媒介手段展现旅程中的事件(用餐、停留、装载卸货)——这已经近似于“历史记录”而非“地理地图”。
这些创造地点的行程,通过追踪和重返去定义地点的记忆。在这样的划界中,实践者变身为一个空间的立法者,他在由水域管控和商业需求制造的空间领地中“游戏”行程,制造“例外”。这种非践履性(afformativ)的践履行为(formative act)㉔绘制了这样的欲望地图:作为对曾经喧闹、而今冷寂的空间的探询,航船带我们进入与地点的相遇。那些“消失之址”持之以恒地激活我们对于地方历史的诗意想象:它们的过去、重建、繁荣与湮灭以及民众的存在,或许确实应该被再现、言说并逆转。这些正趋消失的地方(places)而今看来过于类似异托邦了,它们的失去正被这样的践履行为重新修订,去阐明曾经的存在与当下的失落。甚至那些今天在地图之上缺席的地点也变得如同皮埃尔·诺哈的“记忆之址”(lieux de mémoire)㉕,在文化记忆的重走实践中被唤醒和再现。与这些地点任何方式的重遇都将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它唤起记忆,搅动记忆,越过阐释的所有权。如此,我们才有机会去揭示城市与地方如何进入文化和经济生产的过程,去面向过去的遗留,制造一些外在于当下的余响。
这种余响在培育文化记忆方面必然会成为重要的资源,有助于我们在建构和激励当下的身份认同上容纳一个丰富的文化生态学。实践者的脚步、空间的考古及其践履体验,可以在文献的模糊性、毁灭及记录的声音之外建构真实时间的记录。“表演本身是地址的重新连接:语言能回到一个在其之上和在其之内的阅读,表演引起再次的贯通。”㉖正是这些失落的地方通过非践履性的行走而被重新发现,以身体书写的形式去经验空间——经验它们因存在与消失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所有权、威权与记忆——被边缘化的地点是我们时代空间整体的一部分,实践行动在个人、公共、地方和认同的创造中唤起记忆和乡愁。事实上,在一次随船的行走中,空间的变迁有可能自由地去展示自己的断裂——以赤裸的、一览无遗的形式。
二、都市的特权:表演的剧场
城市表演研究学者尼古拉斯·瓦布认为城市是处于“活动中”(on the move)的,身体由于城市的移动而移动,反之亦然㉗。德塞图在这一层面走得更远也更深入,他区分了实践艺术中的诡计,认为人们在其中颠覆了限制。因此,犹如文本倚重于言说的轨迹,行走的证词(affirmation)、怀疑(suspect)、尝试(tries out)、越界(transgress),驱动人们阅读城市的文本,并通过运动获得自己的理解㉘。城市在其本质上是一个碎片化的空间,在与移动躯体不断的交叉中,转移空间身体(spatial body)进入身体空间(body in space)。这种行走常常拥有潜在的方向性,人们被拽回到重要的地方、熟悉的地方、难忘的地方,将它们编织进即兴的叙述中。以身体的移动定义城市的概念,即,事物和人如何移动和表现——这也是本雅明的核心议题,甚至是他关于欧洲地缘辩证的“思想体验”(Denkbilder)㉙。
在本雅明的理念中,“地点”(place)始终是一个处于活动中的不稳定存在。德文词汇中的“Schauplatz”是一个有着整体性不规则延伸的实用单词。字面上来讲,它是指“一个观看或展示的地方,但也意指一种剧场类型,在日常惯例中,指一个‘事件的地址’(event-site)或‘运转舞台’(arena of operation)”㉚。换句话说,它是这样的地方——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战役”的停顿或推进也可能在此发生。通过“schau-spiel-plats”这个术语,可以明确何种表演对于这样的“场面”或事件是本质性的。城市的“表演的地方”(Schauspielplats)是一个完整的场所,其中既有“舞台化的戏剧”或“为了演出的戏剧”(Schauspiel)也包括“玩耍/游戏”[playing/(Spielen)]。前者意味着官方导向,给予或基于观众/市民的利益,后者涉及观众/市民在广场中(Spielplatz)的参与,它是“非官方”的或无法用以阐释城市的。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散漫的法规,被假定发生或者被制定的,与非计划性的、随机的,有时侯是无政府主义的游戏,后者是由前者的失败、不公或不合适的结果所导致的。换言之,前者被预设在这样的观点中,等同于适用社会运转的维持——一个稳定的、运行的城市,一个服务于居民的需要、利益和渴望,而且它是代表社会公正的。因此,城市围绕着确定的协议被建立起来,运行的秩序致力于成为道德和实用空间。当它的结果出现彻底的偏差时,例如,当它背离于自身功能的履行或者含蓄地在多种方式上否定自身时,它就挑战了城市的权威,如涂鸦与它的衍生品,或居伊·德波的“异轨实验”㉛。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社会矛盾”㉜。在《书写城市》的论述中,他激进地断言,都市居民对于参与公民权的诉求是“节日复原的根本性是与表演的连接”㉝,这种表演只是“对于表演的服从而非对文化主义的严肃性表演的服从”㉞。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制度的介入,剧场变成了文化,表演在社会中失去了它的场所和价值㉟。因此,列斐伏尔设想艺术的功能应该是在市民的关系中创造性地生产城市。在剧场被有效地吞并和被特权模式化后,社会中的观众应该在街道上被定位和搜索(或相遇),对于民众来说,“城市的中心是移动的,不可预知的,充满可能和偶遇;它既是‘自发的剧场’也可能什么都不是……撇开再现,装饰和修饰,艺术变成社会刻度上的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㊱。
居伊·德波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漂移”“异轨”及“总体都市主义”等概念与列斐伏尔的城市观念相呼应,他针对乏味的景观社会提出,以一种放弃“寻常的城市使用习惯”的方式在城市中快速行走、游戏或基于对不同城市空间的心理感受,来对抗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教条划分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规训。在今日中国的城市化语境中,或许要对这些理念略做调整,去思考人与空间的协商性关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一理念出发,可以认为“51人”是对艺术与民众联动的城市空间生产的一次粗浅的尝试,尽管它在意旨上并未明确艺术与城市的“未来性”关系㊲,并且此种展演方式实质上回应了20世纪末以来艺术的“剧场转向”㊳——城市艺术家的“进程项目”(ongoing projects)——以不同形式触及城市中生活、情感、自然、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面向的深处。这种对日常行为的发掘,对城市民间叙事的坚持及其实验性的考古演绎,触及了都市隐蔽的角落。实践的自觉性与坚持,重点不是在存在的意义上“偶然”地重合“减速”的需求,而是在自觉的坚守中创造自我的书写与叙述,这种姿态呼应了居伊·德波早期的断言:事物改变我们观看街头的方式比起改变我们观看画作的方式更为重要㊴。这种预言性的判断与一些“进程项目”相互呼应,例如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ÿs)1997年的城市实践项目“实践的悖论”(paradox of praxis)所体现的“努力做无”与“努力做有”之间的悖论㊵。尼古拉斯·布西欧(Nicolas Bourriaud)的“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或许可以用来提供一种不同却相关的对于城市实践的启发——新艺术不应致力于呈现劳动的成果,而应呈现劳动本身或什么是劳动㊶。
“51人”回应于上述诸多理论,除了在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例证外,它还包括一系列对于城市日常实践的发掘与寻访,这些展示非常明显地以回望的姿势去揭示被都市加速的景观所覆盖和掩饰的断裂。这些城市纹理中的裂隙涉及不同时间的空间,带着不同的文化标记,以特有的精准去对峙于同质化与资本恋物主义的催眠效果,这是由于它们的文化差异与尖锐的民间性所造成的。这些特质触及了对市民精神的复原,以及最核心也最具战略性的“节日”“集体游戏”或“玩乐城市”(ludic city)等列斐伏尔的城市理想。在街头相遇的“瞬间”㊷,普通人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或节奏去重新发现城市的另一种精神,一种背离于加速的方向。
“减速”意象最早出现在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诗歌中,本雅明以“漫游者”一词来概括这一形象的精神与身体共有的分散特质。慵懒的闲逛者,混迹在街道的人群中,却保持着一个疏离的观察者姿态——这一形象紧密联系着波德莱尔和19世纪的巴黎,同时也呼应了20世纪20年代的剧场理论与城市研究。本雅明的城市书写几乎都可以被看作是漫游者的行走和具体反应相互关联的例证,一个流动的人影,倾向于散漫的走神,这些现代生活的碎片,从建筑的毁灭到平凡的事物,被忽视的和偶发的……边缘和遗忘的人与事物,犹如一种宏大精神被投进轻松之中㊸。这种感觉强调街道上发生的事件被以一种难以预料的视点所观察。这种观察也是布莱希特所追求的,即,不仅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更强调目击者的双重功能。他们既是妥协、有责任心的故事讲述者,也是角色和表演者。这样,布莱希特模式便与本雅明的漫游者相互重合:一个人物同时是街头现场中的表演者和观察者,街头现场是一个集体位所(collective site)㊹。布莱希特带来了最早的街头戏剧场面的转折,使戏剧不必指向严肃的文化主义的表演,而是与游乐、行走及节庆等日常实践相关联。
这种实践不仅对城市的细节予以一种特殊的观照,而且提供一种方法,即苏珊·桑塔格定义为阴沉的缓慢、忧郁的气质,“事物在一个有距离的、缓慢的移动中出现”㊺。这种方法允许“每个事物同步发生的感知都潜在地发生在单个空间中”㊻。这也是现代性通过注意力行为被迫地、有效地减缓速度的手段。对于本雅明而言,建筑、空间、纪念碑以及客体组成的城市环境,既是对自反式结构的反映,也是这种结构本身和人类社会行为的模式。建筑和行为相互渗透并塑造彼此,大都市结构了一个框架或有活力的剧场。“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它的内部设置,形成了活动的外观,在其中,人类主体留下的‘痕迹’,他们的过去印记,标记并提示他们存在的模式。”㊼这种痕迹,布莱希特称之为“遗产”,前东德戏剧家亨利·米勒认为这是作家所创造的一种缓慢的当代生活必然进程的隐喻㊽。悖论的是,今天后现代的步行者要接近这种变换,必须“快”才能获得由“减速”所产生的空间。这个悖论的可怕之处在于所有的遗存都是关于时间、速度或时间的飞逝,而没有太多的空间,“一个人必须要做的是去创造并占有空间而以此去反抗加速”㊾。因此,城市实践者的身体内在于城市空间的“存在”就如同一个作品,显示了阻碍以及在飞速的、渗透性的媒介经验中的滑脱。
“减速”与“滑脱”贯穿于全部“51人”的实践中,几乎无法确切分类,这些实践包括都市传奇、异域寻梦、空间丈量、方言收集、湿地存档等,犹如层集在城市舞台上的星群。而其中的个体无论处于沉落还是追赶中,无疑都反映了一种“滑脱”的经验。例如,“匍匐在刘行的快递站长”就是以速度寓言反证了“加速”的代价,呈现出一种追随城市加速度背后的个体的迷失与创痛㊿。“反抗加速”必然不能以追随的姿态,而应相反。再如“被堤坝围困的人”中的郑力敏,他的奔跑便是“给困住青草沙的水泥边界一个速度”,这一象征性的速度呼唤着都市加速中被忽略的面向:资源与水域、环境的破坏[51]。这也是“关心湿地的人——姜龙/科技馆湿地”哀悼的重音:湿地进入被开发、利用和消失的时刻,叙述和动作便成为对一片区域真正的档案记录[52]。他的记忆、经验和知识漫不经心地影响着这片区域,在这片区域留下一些现在可能已经杳然无踪的痕迹:打捞水草、清洗垃圾、与野生动物对话,这些也是区域叙述的工作。这种工作呼应于都市中的其他叙述,如存在于咖啡馆、办公室、高楼大厦或社区私人住宅中的叙述。如果说关于城市外围的叙述构成了都市加速中一个异质的档案和一次空间的“滑脱”,那么“暗黑城市的寻访者:张听雷”[53],便是在有形的城市之内制造了一个卡尔维诺的“无形的城市”。她利用漫画影像创造出另一幅静安地图,呈现出一个不同于官方宣传和规划的“黑色”静安。这张由洗脚店、按摩店和地下会所组成的地图是静安的另一种现实,充满罪与罚、常规与越轨。它罪状累累,却奇妙无比;它阴森暧昧,却令人着迷。这种叙述使城市变得可以想象,变得多元又充满尘世气息,尽管我们无从得知它们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城市,但它无疑是了解城市记忆的钥匙。
资本叙述的世界如本雅明所认为的那样向人们投掷了一个幻影,创造了一种疏离的、集体催眠的状态。“51人”中的民间调性便是极力挣脱这种催眠幻觉,在日常的路径中尝试唤醒资本世界之外的清醒时刻。这种清醒,在本雅明的维度上是革命希望的源泉,在蒂姆·艾奇斯的观念中,它“揭示社会和城市想象的无意识追求”[54]。如弗洛伊德认为的经验是认知冲击的记忆,挖掘与展演恰是通过“隐藏在城市梦想中的欲望和害怕”来完美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公度性:城市如梦,梦也如城市。
三、平凡的英雄与梦想
对资本造梦的修复是“51人”的潜在意图——它结构性、隐喻性地修复那些被资本碾压的街道上或居住区中小型的、私人的叙述。这种叙述必然具体化为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挽救——通过传播和记录在面包店、黄鱼面馆、商场、办公室、社区的私人公寓里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讲述的往事回忆。这种保存工作具有两面性,面包店里的私人叙事只有在互文于城市地标的“进步纪念碑”的同步追寻中,才能显示其叙述的张力与价值。因此,在“51人”之“寻找城市中心的人”中,瑞士摄影师塞德克·范·派瑞斯(Cedric van Parys)以异域视点拍摄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建筑地标,便成了城市梦幻中私人叙事的象征。他登顶高楼以捕获这些地标顶端的影像,提喻了德塞图式的野性梦想:城市的全景视野只是提示我们生活在不可见的“下面”,而在任何角度上,我们都难以企及城市的全貌[55]。派瑞斯的行为既像一个城市之梦的影像记录者,又像一个追随城市幻觉的无能为力的窥视者,他的实践行为悖反地表达着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的渺小与抗争。
除去其所刻意彰显的城市自身演变的时间性因素,这一行为复写了简·雅各布斯所反对的城市计划中一些官方结构的面向[56],派瑞斯实践着德塞图所关注的实践者如何承担一种“有效的思考”的问题,即,城市实质上多元的现实以及行走行为例证了这样一种现实:“城市普通从业者生活在被条条门框挡住了视野的‘下面’(down below)。他们行走或拍摄记录,这是一个经验城市的最基本的形式。”[57]而这些践履者利用“空间不能够被看”,生产出“无法辨别的诗……一个既无读者也没有观众复写的故事”[58]。德塞图着眼于通过城市空间绘制一个语言与运动之间的类比,特别是言语行为和行走行为。后者被认为是“一个表述空间……行走者转移每一个空间的能指到另一些事物……旋转短语的行为在构思一个路径的艺术中发现了一个等价物(tourner un parcours)”(按:这里可以参照他的《日常生活实践I:实践的艺术》中“行程”一节)。这暗示了一个有障碍的进程,协商性地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当代反响——在关于行程与地图的考察中,当地图丧失了对行程的描绘之后,空间叙述要展现的是一些在某个“强制”而非专有的地点中,能够把地点“揉乱”的行为[59]。
德塞图强调空间的偶遇与交叉,以及这种偶遇如何以“做(陈述行为)赋予行程的文本以生气”,城市的活力正是被它内部的这种叙述活动所激活[60]。在几何学的意义上,被城市规划定义了的街道被行人转变成空间,街道因此成为上演各种行动的剧院。德塞图延伸了福柯关于权力机构对空间规训的分析,提示我们一种都市观察的路径,即,通过分析微观的实践活动(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去发现这些模糊而又稳定的战略活动如何建立了日常的调节性与偷偷摸摸的创造性。在此战略中,步行者通过对“空间”语言的能指进行挑选,或者通过变动它们的实际使用方式,创造了空间的间断性。他们对某些地点遗忘或弃之不顾,却用其他一些地点组织起“罕见的”“偶然的”或者不合法的空间“表达方式”[61]。这一点牵涉到关于步行的修辞学,“修辞上的迁移带走并流放了城市化建设中具有分析性和连贯性的‘本义’,这是一种由大众创造出来的‘语义流放’(wandering of the semantics)”[62]。他们使城市在某些地区逐渐消失,在其他地区又被夸大,并且将城市扭曲、肢解甚至使其偏离了原来静止的秩序[63]。
德塞图显然涉及了新的漫游理念和漫游者,他们是城市空间中最普通的人,平凡的英雄,在行走过程中重新创造了空间,构建了消费时代的艺术。但德塞图并没有持续探讨这一维度,尽管他已明示城市空间中的日常实践就是一种表演。他的书写引导我们建立起一种关于日常实践活动、其使用的空间与城市之间令人不安的亲密关系的思考。他的“平凡的英雄”涉及本雅明“街道上的身体”的物质性,并将其特征化为一个现代的、具体的参与者/观众。本雅明揭示了漫游者作为一个可意识到的身体行为的精华:“城市被包含在凝视的眼,慵懒的手,移动的腿,不时触摸的墙,商店橱窗扩大的展示中。”[64]德塞图强调的是这些日常的实践无意识建构的行为美学与抵抗意义。这一点无疑应该包含在“51人”的空间追求中——整个城市作为展演日常行为的舞台,除了结构一种空间选择的可能性外,还身体性地再现了个体对于空间规范的逃逸与城市的民间考古的可能。“从橱窗向外窥探的商场工作人员”[65]是这个项目中唯一直接与戏剧相关的表达,它可以(更深一步地)被看作对日常抵抗实践的示范,在消费、物恋与凝视的幻境中,质询个体与城市的镜像悖论以及突围的无力。
参与者与实践者是历史的目击者,这种见证行为不像博物馆或书籍,他们没有语言。实际上,他们像历史本身一样运转,组成了当下的某种深度,他们不必驯化所有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陌生内容。他们所图绘的历史不再是“被抚慰的”(pacified)历史,也没有被语义学所殖民[66],它们以存在、疏忽、荒芜或随机的状态留存。这些转移确保了一种集合或个人经验的循环,他们在对城市复调的重视中履行一个重要的功能,呼应着意识形态。这种修复的基础伴随着对当下-过去的重现,以及被遮蔽的社区文化和边缘的乡村记忆。在这个框架之内,“51人”的“拯救”意愿被深沉地刻写,它复原了市声,混合了惯有的不同话语分类,让禁锢的城市从民间调性中复活。这一历程维持着过去的异质性,并保护着城市本质的方面:它的多元性与复调特征。
这种涉及不同层面的想象和实践组成的记忆之姿揭示了城市丰富而令人惊奇的过去。作为姿势的“个人语型”(idiolects)[67],提示童年或包含死亡秘密的街区如何使城市成为一个诗意激增的无边的记忆空间。这种行走、表演、记录或烹饪体验的无词的历史标记了区域的缺席;它们在目之所及之外,而今不再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童年的事物、普遍的传统、永恒的事件。这是纯粹的都市叙事,它们毗邻于由办公室和摩天楼所统治的当下的空间。这一实践系列为可见的城市揭示了那些掩藏在街头拐角的“不可见”的书写。伴随着脚步行走的变化,它们创造了另外的维度——持续中的断裂、明亮中的黑暗、加速中的减速……如果我们追随德塞图的诗意表述,“唤醒沉睡于街头的历史,它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有时又像仙女的纱衣一样折叠进顶针中”[68],那么城市(无论在具体还是抽象意义上)都是一个上演叙事争夺战的剧场。尤其在今日之中国,数字媒体、商业广告及有形的摩天楼的叙述,压垮并击碎了街道上或居民区中的微观叙述。必须通过修复工作来挽救这些叙述——幽暗的角落里不可见的声音,“51人”体现的正是这种修复的尝试,通过记录和传播面包店、面馆、社区与屋子里的往事,回忆激活曾被连根拔起的发生之址。行走、聚会、安排在居住区或大楼内的谈话和展演,这一切让叙述有了生根发芽的地方。“城市的历史只有在保持了所有回忆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去。”[69]
四、表演性与日常
行走与体验使艺术场馆扩展到围墙之外,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展场,一个表演实践的场所。物体(人)从一个实践系统(艺术馆高墙内)穿行到了另一个实践系统(城市街道)。在展演/考古学的意义上,城市规划的目的被日常的实践者所挪用,他们生产出新的空间:建筑从原来的使用意义过渡到舞台布景,并包含了多元的时间,它们的身份变得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幸存、并置、断裂于行走的脚步中,而没有线性的状态。行走因此变成一种包含着看与被看的挪用行为:从自由闲逛的诗意漫游者,到去目击和记录时间的场景和事件的表演者。
这种转变改变了原有的剧场(theater)机制,通过取消戏剧(drama)的文本意义,展示其自身的美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通过实践者的身体、情感、记忆、空间关系的再构,揭示参与和互动的种种可能[70]。比起再现、表现(即虚构的模仿)而言,这种模式更强调“存现”(即在现实中的“做”);比起结果来,更强调行为本身。这样一来,这整个艺术系列就如同汉斯- 蒂斯·雷曼所定义的那样,“必然呈现为一种过程,而不是已经完成了的结果;必然是一种创造和行动,而不是某种产品;必然是力(energeia),而不是功(ergon)”[71]。尽管这些行为表面上仍保有一种现代主义的特点,表演是由某种日常事件、讨论、公众行为、艺术宣言、集体记忆所组成的,然而这些事件已经越出了20世纪初的先锋派美学框架,而显现为阿多诺的“被产出逻辑”[72]。它们不再是单一地建构某种戏剧性(dramatic)故事,而是挑衅一种历史记忆,捕获那些事件、例外、偏离常规的个体的日常状态[73]。
这种实践最重要也最明显的特征是散漫地创造这样一种情境:所有人(参与者)都不能再将自己简单地置于被接受物的“对面”,而必须参与其间。在这种实践中,人工模拟的表象世界已经不存在,现实的世界就是展演的世界,表演与空间的边界被打破,日常空间成为剧场,普通人在空间中的行为成为表演,旁观者随时可以变身为参与者,参与者以“非扮演”的形式去经历城市的内部,就如同演员经历舞台的空间。这已经最大程度地接近了情境论者的“过程”(die Prozeduren)、“漫游”或“总体都市主义”等概念。这种展演实践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在于其越出了情境论者只为某一时间段而创造的环境,这里不存在“创造的环境”,而是把真实的环境当成剧场,展示我们所置身的折叠的世界。这个实践本身(尽管未曾直接地涉及政治)包含一种社会生活革命化的政治角度,在激发参与者自身的主动性方面,等同于剧场的事件形式。
当然,这种实践/漫游过程也是吉尔·德勒兹式的异质“块茎结构”[74]。它的每一个元素都指向剧场之外,指向现实生活。实践既是一种行为艺术,更是展示政治与日常生活的相互关联的场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剧场就在劳动生活中寻找着空间,以求找到它作为一种艺术与生活和工作实践的联系点,并从中获取创作灵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趋势得到了不断强化。人们不再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剧场创作的源泉,而开始更多扩展、超越审美的边界,用行为实践占领公共空间。这些日常实践被纳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教育学和空间理论的讨论,究竟是艺术从其他领域获取了灵感,还是艺术已经把自身归入社会学范畴的多种实践,有时已经分辨不清。实际上,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由普通人构成的日常展演,他们的实践究竟是不是戏剧的一部分,已变得不重要。正如尼古拉斯·瓦布所言:“城市概念本身即是作为一个表演和表演性整体而存在,或者基于人们或其他现象性表演进行文化生产,它被认为是表演性的,或者实际上容纳表演并被包含其中。”[75]在将上海整体性地变为“转喻空间”(metonymic space)[76]的过程中,整个实践可被看作一部关于城市姿势的寓言——无论这种姿势多么简单与平庸,它都包含着日常基本经验中的全部艰难。在撞破剧场幻象的时间与空间的壁垒之后,个人经验的感觉才能把现实看作一出戏剧,或者是一场独角戏,把重点放在微小的、个人行为形式的游戏空间上。在这样的戏拟中,我们这个时代所包含的令人惊惧的矛盾图景——加速的失重、恋物与操控、拟像的眩晕以及无法触及的权力板块——才有可能被折射与质询。
就戏剧的发展趋势来看,后戏剧剧场本身就是赫尔伯特·布劳所谓的“处于消失点之上的剧场艺术”[77]。这一论断清晰地表达出剧场表演与日常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后戏剧剧场展现了由其类别所决定的演出、集会、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甚至政治事件的性质,剧场艺术所努力的方向是与展演相反的[78],但正是这种相反性,使剧场与展演艺术逐渐接近、融合,边界渐趋消融。展演呈现出一种完全真实的行为性质,无需使用剧场的审美手段修正这种特性。这样,展演更加接近了日常,它成为事件或事物在时间维度中的扩展,它所具有的证言性力量以一种持续的、瞬间性的、共时的、不可重复的经验存留在进程中。这一行为本身不再局限于拥有一个秘密的逻辑尽头,而是把完成这一行为的时间过程作为剧场的过程,它弥补或者说悬置了剧场时间,更确切地说,它把时间的悬置变为一种绝对的悬置。
对于艺术的本质而言,这种实践行为带有明显的去物质性,即,它什么都没有制造,只是结构了一种形式,一种过程行为。这种看似“无事”的实践,以绝对的日常精神成为德塞图信仰的回声:日常生活中还有昙花一现的“无名英雄”所发明的无数东西等待我们去了解,城里走路的人、居住区里的居民、读书爱好者、梦想家、厨房里卑微的人,正是他们让我们惊叹不已[79]。这些行为存在的意义在于最终把实践艺术和生活艺术联系在一起,它们是简单的、不起眼的而又不可或缺的,正是这些使普通人不会感受到完全的生之痛苦,并使我们看到个体保持自由的可能——去“做”某事,从而与某种模式、系统或秩序的强权保持距离。如果这些实践产生了减速效果,那也并不在于它是否主题化了关于政治的议题,而在于它的感知形式,这也是剧场艺术与展演实践超越传媒拟像的地方:实践者、参与者与观者相互蕴含的关系是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他们彼此体验到感知与自身经验之间的断裂点,这种断裂是在脱缰的加速经验中无法获得的。这种经验有可能使审美体验的边界变得模糊,但它无疑具有伦理政治性。城市平滑的表面不会提供给我们跨越禁忌的可能,而艺术实践,无论以何种形式,在有关城市的定位、空间规划或社会理性的表达中,都拥有一种责任美学,去跨越禁忌,挑衅一切合理性断言,造影于历史间隙的空间。
① 2016年上海双年展期间,由陈韵与她的Raqs媒体小组策划并实施。在展览进行的17周内(2016年11月—2017年3月),每周邀请志愿者实践三个方案(行动、表演、聚会或其他形式),分别指向上海城市生活的51个不同面向,具体行动包括修补衣物、读书、散步、社区交谈、周边寻访等日常实践。
② 杰妮·范·黑思维克是致力于激活公共空间的张力与多样性创造的艺术家,她在2008年上海双年展上的这一项目同样以激发本土空间活力为目的。她在上海地图上撒豆子,然后按照豆子的随机落点,与在那里工作的人们进行日常交谈,并分发红色T恤给在这些空间中偶遇的人,目的在于激活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于空间变化以及人际互动的感知(https://vimeo.com/38160903;http://www.jeanneworks.net/projects/shanghai_dreaming/)。
③“戏剧考古学”理念由米歇尔·尚克斯和迈克·皮尔森在他们2001年的著作《戏剧/考古学》中提出。他们尝试去重新梳理表演的物质化,而不是重新结构它。尚克斯和皮尔森的兴趣在于重新界定表演的地理学设计、剧场的物质性意义及表演艺术所包含的地点特性,这种脉络化的研究带来了表演学与戏剧研究的新范式,是表演学领域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典范。Cf. Michael Shanks and Mike Pearson,Theatre/Archa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XI, XII.
④ 德塞图尝试建立的是空间与语言之间的关联,他在词根、仪式与表演之间进行了类比,认为人类创建行为的仪式犹如戏剧的彩排一样,为行动提供必要的范围。它发生在事件之前,为即将展开的活动开启空间、建立基础。我在此处使用这一概念,是因为2010年的上海双年展不仅在主题上将自身定义为一个反思性的表演空间,而且在形式上也采用“戏剧”的方式,把策展过程分为“展开”与“回归”两个步骤。“展开”部分是指从2010年7月至9月分别在纽约、西班牙与北京进行的展程;“回归”部分是指外围展程向上海主体展的回归,三次“巡回排演”构成主体展览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此处理论概念参见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Los Angeles: Berkeley, 1998, pp. 122-124。
⑤ Elizabeth Wilson,“Looking Back-Nostalgia and the City”, in Sallie Westwood and John Williams(eds.),Imagining Cities: Scripts, Signs and Mem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135-136.
⑥ 面相学(physiognomy)的字面意思是对关注身体(physis)本身的可见符号的解释和分析。本雅明的面相学不关注人类的身体特征(他曾对阅读和解释人类姿势和姿态有强烈的兴趣,这点除外),而是对集体实践的视觉表象感兴趣。他通过社会赋予自身的空间形式来解读社会的“灵魂”。也可以说,本雅明对社会的空间赋形分析从某些方面来说就是社会灵魂的面相学。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灵魂,除了其主导的意识形态暗流以外什么也不是。而本雅明感兴趣的意识形态的特定形式就是时间性宣言。换句话说,“社会的灵魂”就是能在社会空间形式下被分析的同历史的关系。参见约翰·哈特尔:《历史的身体:瓦尔特·本雅明思想中的空间想象》,马楠译,《新美术》2013年第10期;Walter Benjamin,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tiy Press, 1999, p. 207。
⑦ Jonathan Raban,Soft City: A Documentary Exploration of Metropolitan Life,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8, pp. 72-73.
⑧ 本文的“后戏剧”概念采用汉斯-蒂斯·雷曼的观点,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前戏剧(雅典悲剧)的典型模式失效之后,坚持在戏剧范围之外进行创作的一种剧场艺术。它并不是对戏剧传统的抽象否定或单纯背离,而是处于与旧有范畴的某种关联之中——或否定、或宣战、或解放,也可能只是某种偏离,或游戏性地试探这个范畴之外的可能性。参见Hans-Thies Lehmann,Postdramatisches Theater,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der Autoren,2005。中译本参见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0页。
⑨ 按照雷曼的说法,“戏剧构作”指剧场艺术所显示的美学特征,比如叙述风格、表现手段、场景设置等,而不是把意义构作当成目的,不再存在对意义构作进行综合阐释的可能性。参见《后戏剧剧场》,第16页。
⑩ 这个实践活动跟随的主角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李中华,他从淮安来到上海已经十八年,每天7点半从弄堂口出发,进入里弄和小区深处寻找需要磨刀的人。实践者跟随磨刀师傅一天,沿他走过的路骑行,去他去的地方,听他的吆喝声。
⑪ Richard Schechner, “6 Axioms for Environmental Theatre”,The Drama Review: TDR, Vol. 12, No. 3(Spring 1968): 41-64.
⑫ Hermann Bausinger,Volkskultur in der Technischen Welt.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GmbH, 2005. 中译本参见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135页。
⑬⑱ Walter Benjamin,The Arcades Project, p. 423, pp. 420-425.
⑭ 《历史的身体:瓦尔特·本雅明思想中的空间想象》。
⑮ 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 Vol. 1, ed. Michael Jenn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69-71.
⑯ Michael Shanks and Mike Pearson,Theatre/Archaeology. Cf. Michael Shanks,Experiencing the Past: On the Character of Archa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⑰ 迈克尔·凯尔斯:《瓦尔特·本雅明,都市研究,与城市生活叙事》,陈永国译,http://miniyuan.com/read.php?tid=4765。
⑲ Carlo Ginzburg,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⑳ Michael Shanks and Mike Pearson,“Introduction”, inTheatre/Archaeology, p. 2.
㉑ 船长钱正峰的老家在安徽怀远,他自1995年开始跑船,经历了整个长江水路的变迁,现在是两条船的船长。这个活动邀请已十几年没有搭船回家的钱正峰从上海回老家,随行者搭乘他的船沿黄浦江到吴淞口,进入长江,抵达淮河,最后进入涡河淮河交汇处安徽蚌埠市的怀远县。在这一周里,他将用航拍、照片和文字记录,完成这段700公里、贯穿江南水域的航海日志。
㉒ Julian Thomas,Understanding the Neolithi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35.
㉓ 参见福柯1967年在巴黎建筑研究会的讲稿(Michel Foulault,“Different Spaces”, inAesthetics, Methools, and Epistemology, trans. Robert Hurley, ed. James Faub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 175-185)。
㉔ 剧场(戏剧)本身并不是简单地做出断言、陈述观点,采用语言符号的方式来行动。剧场只是“做”(doing),连命题都不是,只是一种部分脱离了规定性、脱离了主动性的言说形式(参见《后戏剧剧场》,第237页)。这里借用文学理论家维尔纳·哈马赫的“非践履性”(Afformativ)概念,把剧场称之为“非践履艺术”(Afformance Art),以暗示剧场既是非践履性的,但又接近于践履。Cf. Werner Hamacher,“Afformativ, Streik”, in Christiaan Nibbrig(ed.),Was heiβt“Darstellen”?, Frankfrut am Main: Suhrkamp, 1994, pp. 340-371.
㉕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Representations, No. 26, Special Issue:Memory and Counter-Memory, (Spring, 1989): 7-24.
㉖ Michael Shanks and Mike Pearson,Theatre/Archaeology, p. 51.
㉗㉙㉚ Nicolas Whybrow,“Introduction”,inPerformance and the Contemporary City: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8, p. 3, pp. 6-8.
㉘[57][58][59][60][61][62][63][66][68][69]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 99, p. 93, p. 93, pp. 98, 100, p. 117,p. 99, p. 102, p. 102, p. 135, p. 142, p. 143.
㉛ 在《异轨作为否定和序曲》中,居伊·德波将“异轨”看作“一个新的组曲中出现的、可被反复挪用的艺术元素”。异轨具有特别明显的源自双重意义的能量,以及源自并存于新旧思想中的多数术语的丰富性,它是非常实践性的,因为它很容易被使用并且具有永不枯竭、能够被反复使用的潜能。这个术语一般会和“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漂移”(dérive)、“游戏”(jeu)、“心理地理学”(psychogéographie)、“情境创造”(création de situations)等概念一起出现。从“藐视”城市现有空间分区出发,通过一种类似游戏的方式无视既有空间认知和意识形态,进而实现对已经功能分化/固化的城市空间的反叛与转变,从个人的艺术、肢体实践过渡到城市空间概念/意义的转变,希望以此实现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的解放,即异轨与构境。Cf. Guy Debord,“Le détournement comme négation et comme prélude”, trans. Ken Knabb, in Ken Knabb(ed.),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2006.
㉜㉝㉞㉟㊱ 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trans.and eds.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 14, p. 168, p. 169, p. 171, pp. 172-173.
㊲ 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p.173.Nicolas Whybrow,Performance and the Contemporary City: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p. 11.
㊳ 当代艺术的“剧场转向”这一说法源自列斐伏尔,他在1996年的《书写城市》中就提出“艺术的未来不是艺术家的,而是城市的”;后来兰德尔在2006年的著作《艺术与建筑:地方之间》明确了“地方艺术趋向于作为艺术馆系统的批评以及艺术作为商品的功能”;罗莎琳·德切也强调空间战略发展了后现代艺术,使艺术家拥有一种手段去揭示包含美学与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Cf. 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 p. 173; Jane Rendell,Art and Architecture: A Place Between,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6, p. 25; Rosalyn Deutsche,Evictions: Art and Spatial Politics, MA: MIT Press, 2002, p. xvii.
㊴ Guy Debord,“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s”, in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p. 42.
㊵ 弗朗西斯·埃利斯以其多种手段记录的行为艺术作品闻名。一些行为非常简单,如艺术家本人在城市中行走;另一些行动则如同史诗事件,设置在极富张力的自然景观或政治空间中,涉及数百位参与者。“实践的悖论”(Paradox of Praxis)是他1997年的城市项目,内容是他本人推着一块冰绕着城市行走,直到冰完全融化。在关于这个项目的记录中,埃利斯以“努力做无/徒劳无功”(Sometimes Doing Something Leads to Nothing)作为最初的题记。联系他的其他一些实践作品,笔者认为埃利斯的努力是在反抗艺术的物质生产机制,同时反抗资本世界的物质生产与劳动效率。因为徒劳无功的反面可以是“Sometimes doing nothing leads to something”,即“不劳而获”。
㊶ Nicolas Bourriaud,Relational Aesthetics, trans. S. Pleasance and F. Woods with M. Copeland,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2002, p. 110.
㊷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的“瞬间”(moment)是短暂的,瞬息之间湮灭,但在这样的过程里,所有可能的方式(通常是决定性的及革命性的)都能够被揭示和实现。“瞬间”是连续的破裂点,是对可能性和强烈欣悦的彻底认知。Cf.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 429.
㊸ Anthony Vidler,Warped Space: Art, Architecture, and Anxiety in Modern Culture,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p. 116.
㊹㊻ 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 London: Intellect, 2002, p. 423, pp. 418-419.
㊺ Susan Sontag,“Introduction”, in Walter 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K. Shorter, London: Verso, 1997, pp. 13-14.
㊼ Graeme Gilloch,Myth and Met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London: Wiley, 1997, p. 6.
㊽ 在1995年的一次访谈中,米勒评论道:“在现代,何止是移动的社会,步行者如我,不像驾车者拥有自己的汽车‘保镖’,我更多地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甚至必须要比汽车还快,才能保证自己的幸存。”Cf.Heiner Müller,Theatremachine, ed. and trans. M. von Henning,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5, pp. viii-ix.
㊾ Hugo Glendinning, Tim Etchells and Forced Entertainment,Void Spaces, Sheffield: Site Gallery, 2000, p. 7.
㊿ 这是民间角度的一个中国快递业缩影,讲述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康睿宁从2012年起承包顾村刘行快递站点的故事。他的经历见证了中国快递产业的飞速发展及背后的代价。这个由他和家人、工人共同讲述的故事构成一篇快递从业者视角下的“顾村报告”: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电商?“江浙沪包邮”的快递费是如何做到比地铁票的费用更低?网购如何做到比家门口小店还便宜?
[51] 青草沙水库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江心水库,也是上海水质最好的水源地,它拥有总长43公里的环库大堤。这一活动是水库员工郑力敏邀请冬季长跑爱好者一起参观水库的展览馆,并在大堤上奔跑。
[52] 这个例证可以与“青草沙”构成相互呼应的关系。浦东张家浜河畔上海科技馆的西侧有一片不到3万平方米的小湿地。自2007年起,姜龙一直与志愿者一起保护这片湿地,十年后,这片湿地面临被开发和利用。这一活动邀请对“荒野”有兴趣的人,在世界湿地日跟随姜龙走访那片小湿地。活动意在唤起对于环境遗存的思考:城市理性的空间规划如何面对诗性气质的失落?
[53] 张听雷的创作类似于一种“街头之诗”的个人化城市实践,她对自家所在的街区抱有长期的“特殊兴趣”,将建筑绘图与色情漫画结合,画出一张由洗脚店、按摩店和会所组成的另类的静安地图。这种异质的城市实践与静安“高大上”的一面形成对比,并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城市街区的生命力?
[54] Tim Etchells,Certain Fragments: Texts and Writings on Perfor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46.
[55] 米歇尔·德塞图在《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行走于城市”一章最明显地涉及城市与身体的空间实践。这一章开始于一个开放的影像,描绘了纽约世贸中心11楼的城市全景视野,当然,如今它已被分割和碎片化。德塞图的文章是对“911”事件的一个特别回应。
[56] 简·雅各布斯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认为市区重建不尊重大多数市民的需求,她提出了一些城市改造中的社会学概念,如“街区的自然监控”“社会资本”等。Cf.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26-30.
[64] Walter 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p. 63.
[65] 南京路上的某商场职员陈歆汝自编自演的一出戏剧,通过她工作的南京路上的一面橱窗作为舞台,将橱窗内的世界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目的是探寻都市之于个人的意义。
[67] 字面意义指具有个人语言风格的语言变体,在此隐喻这一实践项目中的个人性与日常性。
[70] 1968年的“文化革命”(马尔库塞语)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剧场艺术家们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取消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让艺术不再是少数人在剧院、博物馆这些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才能享有的专利。同时,启蒙主义时代以来的美学最为关注的艺术“作品”也被作为权力作用下的“文化产品”从新的社会政治角度加以审视。理论界与实践者相互影响,使剧场艺术也出现了某种转向:从专注于作为“表达”(express)艺术家个人意图之途径的艺术作品创作,转向作为启发观众反思自身、反思社会(并希冀改变社会现状)的展演事件。在展演事件中,艺术家不再用各种剧场手段集中于一个中心点去制造现成的意义,制造某种幻觉真实,而着意让观众保持清醒的姿态,用自己的思考积极建构“作品”的意义。观众成为生成展演意义的重要推动者。参见李亦男:《当代西方剧场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页。
[71] Hans-Thies Lehmann,Postdramatisches Theater. 中译本参见《后戏剧剧场》,第129页。
[72] Theodor Adorno,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 39.
[73] 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德国的里米尼记录剧团(Rimini Protokoll)。该剧团从来不使用专业演员和剧本,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请上舞台,让他们展示自己(而非扮演角色)。他们的创作方法近似于福柯的剧场“异托邦”:创作者首先用“去上下文”(De-Kontextualisierung)的方法,把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提取出来,再用自己的理解、用剧场手段给它们“套上新的框架”(neue Rahmung)(Cf. Annemarie Matzke, Christel Weiler and Isa Wortkamp,Das Buch der Angewandten Theaterwissenschaft, Berlin: Alexander Verlag, 2012, p. 102)。但是“51人”项目并不完全等同于里米尼的表演项目,它祛除了里米尼所保持的“框架”,更彻底地走向真实的日常实践,即,使真实的生活空间——城市、乡村或河流生成为展演的舞台,日常与剧场的边界完全消失了。这种区别也是展演艺术与实验剧场之间隐晦而又本质的区别。
[74] Gilles Deleuze and Fele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 4.
[75] Nicolas Whybrow,Art and the Cit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22.
[76] 这是一个借自修辞学的剧场概念。在实验剧场中,当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时,剧场空间就从一种譬喻性、象征性的空间变为一种转喻空间。借用这种转喻或毗邻关系,我强调在这个实践中,实践行为完全破解了剧场的虚构世界,甚至打破了艺术馆的展场边界,而把真实城市当成剧场,把上海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转喻空间。其次,我使用这个词除了作为修辞格意义外,还想强调转喻本身所包含的认知机制与思想观念的含义,它被突出地用于电影、戏剧和文学等虚构领域。
[77] Herbert Blau, “Introduction”, inTake Up the Bodies: Theater at the Vanishing Poi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78] 展演艺术最惯用的手段是通过人工创造的视觉、听觉结构,通过扩展媒体技术去延长行为时间,扩展其空间,使其接近剧场艺术;而实验剧场通过加快接受的节奏、缩短剧情、去戏剧性与去情节心理的展开、演员不扮演角色等手段而变为“存现”。这样,两者的边界逐渐融合。
[79] 米歇尔·德·塞托(即米歇尔·德塞图)、吕斯·贾尔、皮埃尔·梅约尔:《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冷碧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