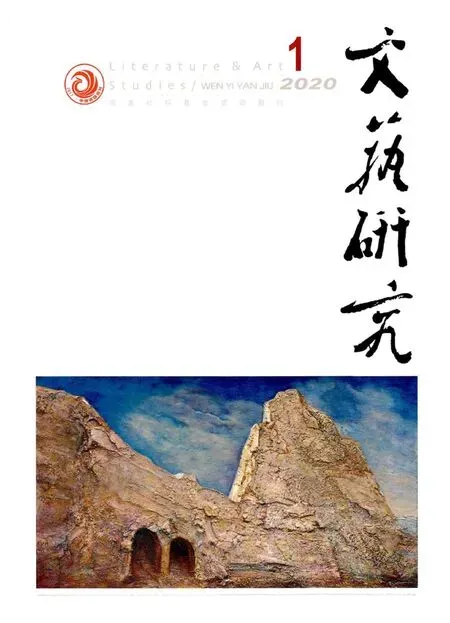文集校笺见笃实,诗画融通出新裁
——吴企明教授访谈录
吴企明,1933年生,江苏吴县人。1960年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苏州大学任教,现为该校教授。长期从事唐诗宋词、题画诗、诗画关系研究,主要著作有《唐音质疑录》《王建〈宫词〉研究五稿》《诗画融通论》《唐诗与绘画艺术》,并有《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辛弃疾词校笺》《刘辰翁词校注》《唐朝名画录校注》以及《恽寿平全集》《中国历代题画诗》(与杨旭辉、史创新合著)等古籍整理著作,参与《全唐五代诗》《中华大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唐才子传校笺》等的编修工作。其中,《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获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恽寿平全集》获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刘辰翁词校注》获2015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唐朝名画录校注》获2016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特等奖,《辛弃疾词校笺》《历代题画绝句评鉴》分获2018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二等奖、普及读物奖。本刊特委托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戴一菲博士采访吴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学承名师,文润葑溪
戴一菲吴先生,您好!今天到苏州大学来采访您,是受《文艺研究》杂志的委托。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据说,您大学是在南京师范学院读的,孙望和唐圭璋两位先生教过您吗?
吴企明孙、唐两位先生都教过我。唐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全宋词》,名满天下。我在南京读书时,很荣幸能够受其指教。我很喜欢听他讲宋词,也常登门请教。1986年,他出版了《词学论丛》,寄赠给我学习。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回母校去拜访唐先生,无意间谈到了辛弃疾词。他很认真地说,辛派词人中,刘辰翁很重要,可以好好研究。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李梦生来苏州组稿,有整理刘辰翁词的计划,于是我欣然接受了邀约。经过数年努力,《须溪词》终于在1998年出版,列入“宋词别集丛刊”之中。
戴一菲唐先生促成您整理、研究刘辰翁词,那么孙先生呢?他应该对您从事唐诗研究有所影响吧?
吴企明孙先生可以说是我进入唐诗研究领域的领路人。他给我们讲唐诗,很细,很深,带领我们进入唐诗的意境里,让人心窍顿开。有一次,我去拜访孙先生,恰巧程千帆先生也在。他们谈起一个问题,就是“一本书主义”。程先生认为,要搞通一本书,形成规范的研究方法、路数,为以后研究打下基础。这对我影响很大。回首过去,我在唐诗宋词研究上取得的微薄成绩,都应归功于诸位老师的教导。
戴一菲大学毕业之后,您就一直在苏州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苏州自古以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您从小就在那里生活吧?
吴企明是的,我的老家在苏州娄门,而我却出生在苏州城外吴县甪直镇,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吴中区。甪直古镇很有名,陆龟蒙曾在这里隐居,叶圣陶也在这里教过书。镇上文化人很多,我读中学时,读到当地书法家殷云林先生为鲁望中学书写的匾额“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铭记在心。镇上还有许多文化遗迹,比如许自昌梅花墅遗迹、保圣寺中唐大中年间的碣石等等。苏州文化深厚,我在读书、研究过程中常常与它“相遇”。譬如,查阅古书的版本,接触到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校勘唐诗,接触到许自昌刊刻的《前唐十二家诗》、席启寓所刻的《唐诗百名家全集》;参读诗歌名家的注释本和诗论著作,接触到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诗辑注》;查阅古代书画的收藏和品评资料,接触到张丑的《清河书画舫》、顾文彬的《过云楼书画记》;现在正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范石湖集》,又参读了沈钦韩的《范石湖诗集注》。总之,我的研究离不开苏州文化名人及其著作的滋养,作为老苏州,我感到很自豪!
戴一菲您曾经编写过《苏州诗咏》《诗画苏州》等书。苏州风物景观时常出现在您的著述中,比如您早年写过《吴门质疑录六题》。您对张继《枫桥夜泊》涉及的名物进行过考辨,根据前人史料笔记和苏州地方志,稽考“枫桥”所指,并考实唐宋时期“苏地寺院确有半夜钟声”。
吴企明是的。苏州素有东南名胜荟萃的雅誉,其地名人的学术文化思想、艺术思维方法,给予了我很多学术启迪和研究灵感。比如,明代“吴中四杰”之一的张羽,将自己的凉亭取名为“听香亭”;狮子林里有一座“真趣亭”,挂着乾隆帝题写的匾额。我由此得到启发,特地将“通感”中很独特的审美体验“听香”和强调景物逼真的审美情趣“真趣”,引入到诗画融通的研究中,使它们成为诗画融通理论中两个很重要的会合点。苏州网师园有“读画看松轩”,“画”为什么要“读”?如何“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探索,我逐渐领悟出“读画”在绘画审美中的重要地位。读画,就是将画幅中的笔情、墨趣、画境和绘画美慢慢品味、体识出来。后来,我便将这种审美思维方式运用到题画诗和诗画融通中来,并总结出“诗画对读”的独特审美方法,推介给诗画界的朋友们。
戴一菲您有一本诗学研究专著《葑溪诗学丛稿》,这个葑溪,应该就是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旧址旁边的那条护城河吧?
吴企明对。苏州大学校本部是原东吴大学旧址,就在苏州城东葑门内。墙外为护城河,古人因葑门的关系,称它为葑溪。明朝人韩雍官至两广总督,致仕后在葑门附近建造了葑溪草堂。当地名流经常在此园雅集,宴饮吟咏。明代画家刘珏画过一幅《葑溪草堂图》,可惜已经失传。1960年,我来苏州大学工作,一直居住在葑门附近。先是住在钟楼头,后来迁住十全街,又搬家到东小乔弄。直到2008年才迁至城南龙西新村。四十年来我生活于斯,工作于斯,对它很有感情。我《葑溪诗学丛稿》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葑门居住时思考、写作而成的,所以我结集出版时便以“葑溪”两字命名。
戴一菲听说您当年和钱仲联先生都住在葑溪附近十全街,钱先生住您楼上。您的《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提到,您编写《李贺年谱新编》,参照了钱先生的《李贺年谱会笺》,但是对李贺诗中反映永贞革新时事的如《金铜仙人辞汉歌》等诗作的系年,和钱先生看法不同。您当年和钱先生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吴企明钱仲联先生和我曾同住十全街的一个大宅院里。这本是陆姓状元的府第,很大,有四进。20世纪60年代后,成为苏大的家属宿舍。钱先生住二楼,我住一楼。他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我常去他家请教学问,联系工作。钱先生健谈,谈到一个问题,总是滔滔不绝、诲人不倦,使我深受教益。大约在1980年前后,我搬迁到东小乔弄宿舍区,钱先生搬迁到螺丝浜宿舍区,就不常见面了。2005年左右,我应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之约,为李贺集做注。我先把李贺诗逐一注释,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作品系年和生平交游中的问题,特别是对李贺南游吴会的年代有新的考辨。在此基础上,我才着手编写《李贺年谱新编》,这时已是2008年了。而钱先生逝世于2003年,我只能参照他的《李贺年谱会笺》思考问题,不可能当面请教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不过你提起葑溪,那里发生的往事很多,历历在目,特别有两件事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戴一菲人生总有一些重要事件和某一地点联系在一起,您留在脑海中的往事,一定和学术密切相关吧。
吴企明是的。1982年初,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从北京看书南还,特意到苏州东小乔弄寓所来找我,要我陪他到苏州博物馆查阅顾沅的《吴郡文编》。暇间问及我近来的写作,我告诉他近时读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发现了一些失误,因而写成《东坡乐府笺斠补偶记》。他很高兴,要我立即将此文寄给《杭州大学学报》,经他推荐,很快便发表在1982年第2期上。朔方先生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还有一件是和日本学者的交往。1992年,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岛洋一先生来苏州大学访学。他来舍间,要我为他讲唐诗,还让我用吴语吟诵唐诗,并录了音。后来,我陪他到东山紫金庵参观。在清幽的茶室里,我们边啜香茗,边谈古诗。当他得知我正从事中国题画诗的研究,便很高兴地告诉我,日本古代,相当于唐五代的时候,屏风画上也有诗。后来,他为我抄示了《古今和歌集》中的日本题画诗和《日本的古典》第4期里收录的白畑吉(“白畑よし”)的《屏风画与歌画》。经过研究,我认为日本屏风画和题画诗对我国宋代题画诗的发展曾发挥过重要促进作用。我将这一学术发现写入《论赵佶题画诗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渊源》一文中。中岛洋一教授的盛情可嘉,我们两国学者真诚交流、切磋的友谊,尤堪珍惜。
戴一菲很羡慕您们那一代学者彼此之间真诚的君子之交,学问上可以切磋砥砺,私交上并无嫌隙。您在参与《唐才子传校笺》和《全唐五代诗》编修的过程中,和傅璇琮、周勋初等先生的交往也是如此吧?
吴企明是的。我从事“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点校工作,就源于傅璇琮先生的赠书。我近来翻检藏书,发现《隋唐嘉话》和《朝野佥载》的扉页清楚地写着:“80年3月,傅璇琮赠。”这是两本好书,《隋唐嘉话》是程毅中点校的;《朝野佥载》是赵守俨点校的。我点校《桯史》《癸辛杂识》,就是出于傅先生的建议。工作时,我便参照两位先生的做法,因此点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心里意识到傅先生的赠书,是可以当作样书的。
二、质疑发轫,诗笺大成
戴一菲您是研究唐代文学出身的。早年,您的《唐音质疑录》甫一问世,就引起了极大反响。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几乎人手一本。您这本书应该算是较早对唐诗进行考辨、释疑的专门著作,主要谈了哪些问题呢?
吴企明我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接前人未了之绪”(薛雪《一瓢诗话》)。唐诗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前人已经注意到,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尚有失误,可以正之;尚有疏漏,可以补之;有些工作刚开了头,可以续之。如清人冯集梧作《樊川诗集注》,据《全唐诗》校补,增加《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然许多诗与许浑诗重出,我根据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所载《唐许浑乌丝栏诗真迹》,断定冯集梧补录之“樊川诗”,乃误将许浑诗当作杜牧诗。二是“言古人之所未及就”(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条)。唐诗研究中,有些问题还很少有人问津,我在读书钻研的基础上,时而钩沉探幽,时而考镜源流,发前人所未发。比如我在《读孟棨〈本事诗〉书后》一文中指出,孟棨《本事诗》之记事,大抵本于唐人记述,并非孟棨首创。其中许多记事,出于小说家言,或虚设其事,或缘事夸饰,不可轻信。《本事诗·情感》记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妻破镜重圆事,实出李冗《独异志》卷下。我认为,运用《本事诗》之资料,必须审慎考核,以决定取舍。你说此书“引起了极大反响”,我想起一件事。我与北大袁行霈先生之前从未谋面,一次在南京开唐代文学年会时,初次见面,他握着我的手说“一足矣”,指的便是《唐音质疑录》这本书。袁先生用了《韩非子》中“夔一足”的典故,让我印象特别深。
戴一菲您还参与了一些大部头古籍的整理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唐才子传校笺》和《全唐五代诗》。这两部书是唐代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能够参与其中,是对个人学术水平和能力的肯定。
吴企明还有《中华大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2008年,我还做了八部唐人笔记的点校,是应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之约渐次完成的。这八部书,正好属两类。我将李匡文《资暇集》、李涪《刊误》、苏鹗《苏氏演义》和马缟《中华古今注》编集成一书,即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氏演义(外三种)》,因为它们都属于考订名物、典章、制度一类。点校唐宋史料笔记的工作,练就了我运用考据方法解决疑难问题的功夫,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极有帮助。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件往事,还是在南京师范学院读书时,听过一位徐老师作报告,他说:“我在空闲时,右手一杯绿茶,左手一本笔记。”想不到数十年后,我竟然成为像他那样喜爱读笔记的人。
戴一菲爱之,则近之。而您尤善古籍整理,能够体察精微,辨析毫芒,拾遗补缺,纠谬正讹。您在2017年出版的《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感慨“笺注诗歌难”,所喜又为所擅,并非易事。
吴企明这句话实际上包含着“笺注难”和“笺注诗歌难”两重意思。难在哪里?先说“笺注难”。不管是历史的、文学的、画学的古籍,都不能光靠某一学科的文献。因为各门学问是互通的,史学古籍中有文学的内容,文学古籍中有画学的内容……某一学科的古籍往往会涉及许多学科的知识,诸如哲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艺术学、语言学、文献学等等。笺注者必须具备宽博的知识,这需要长期积累。我觉得三国时代孙权的话很值得我们借鉴。《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孙权要吕蒙读书,云:“学问以自开益。”吕蒙说自己军务多,无暇读书。孙权就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我们做学问就要多读书,读各种学科的书,拓宽见闻,这才有利于自己专业方面的精进。博与专、泛览与专精,是相互促进的,要妥善处理好它们的关系。
戴一菲但是现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博览”的问题似乎可以用电脑检索解决。
吴企明不全是。笺注古籍固然要使用辞书、类书等工具书或者电脑检索,但是光靠这些是不够的。从事古籍整理的学人必须靠宽博的知识和长期的积累才能做好,尤其是前面的研究恰恰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戴一菲是的,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无论是订正史传还是考辨生平,乃至论述学术问题,都广征博引古今各类文献资料,无不建立在广博深厚的文献基础之上。那“笺注诗歌难”又怎么说呢?诗歌和其他文体比起来,难在哪里呢?
吴企明“笺注诗歌难”的诗歌,专指文学古籍中的古典诗歌。笺注古典诗歌是很困难的。除了上面谈到的原因外,还有三个原因:其一,诗歌意象的多义性。诗歌意象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含义,笺注时容易混淆,甚而错注,必须慎重辨正、说明。其二,运用语典的变化性。前人写作诗词作品,运用语典时,常常变化运用,一变,笺注者不易看出,造成困难。我主张笺注者要学会写诗,掌握辞章之学,掌握变化运用前人语典之技法。其三是诗意的多义性。诗歌是形象思维的产物,靠形象说话,每多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或则运用比兴手法,寄托寓意。而且,有些诗歌、诗句里看不出具体的人事、地点和时间,很难考订写作背景。像杜甫的《佳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诗中之佳人“实有是人”,《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吴山民语曰:“当是《谷风》后第一首。”而旧说以为“托弃妇以比逐臣”,唐汝询《唐诗解》则以为“自况”,沈德潜评曰:“清洁贞正意,自隐然言外。”这些不同评价,实是由《佳人》诗之多义性造成的。“笺注诗歌难”,不是随意说说的,是我多年来笺注古典诗词著作、尝到甘苦后得出的结论。我说这句话,意在告诉我的同行朋友们,工作时要有谨慎、细心的品性和作风,要有迎难而上的决心和毅力。
戴一菲尽管“笺注诗歌难”,但您的《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却有很多新发现和新突破。比如《感讽五首》之二中的“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对“青蝇”的解释,纠正了王琦之误。辨正前贤时哲之误,在您的书里还有不少。
吴企明是的。我多年来研究李贺诗,陆续发现王琦《集解》和多种李贺诗注本中的问题,写成《王琦〈李长吉歌诗集解〉补笺辨正》,载入《唐音质疑录》。后来,又不断有所发现,便写出《长吉诗注辨误考证稿》(见《葑溪诗学论稿初编》)。比较典型的例子,像《老夫采玉歌》中的“村寒白屋念娇婴”,王琦袭用颜师古之误,释白屋为茅屋,我依据元代李翀《日闻录》和王先谦《汉书补注》中的考订,辨正之。又如《还自会稽歌》中的“脉脉辞金鱼”,吴正之注为“金鱼,袋也”。我据应劭《风俗演义》和李商隐《和友人戏赠》,考订此乃“鱼钥”。其他如《还自会稽歌》之“屯贱”、《仁和里杂叙皇甫湜》之“坚都”等,都有新的阐释。
戴一菲唐代诗人中,除了李贺之外,您还对王建有所研究。学术界对王建《宫词》的价值认识不够,您的《王建〈宫词〉五稿》可以说是改变了这一状况。
吴企明其实我对王建《宫词》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始于1978年在扬州买到一本《浦江清文录》。江清先生著作中有一篇《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谈花蕊夫人的《宫词》,必然会谈到王建《宫词》。江清先生对王建《宫词》是这样评价的:“观其描绘之细腻,遣词之新俊,用乐府通行之体制,寓史家纪实之笔墨,真一代之作家也。”这一论断与过去一些论家的说法截然不同。王建《宫词》的文学价值,历来评价不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说:“予阅王建《宫词》,选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脍炙者,数词而已。”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说:“意境不高。”各类文学史、诗史较为重视王建的乐府诗,对《宫词》评价不高,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我很不赞同这些说法。为此,我循着江清先生的思路,从文本出发,归纳出王建《宫词》八大文学特征和八大文化观,运用深度研究的方法进行解读,帮助读者客观认识、评价王建开创出的表现丰富生活内容的百首组诗这一诗歌新体式,在我国诗歌史上的重要意义。
三、打通唐宋,藉诗笺词
戴一菲您不仅研究唐代诗人,还关注宋代词人。2015年,您出版了《刘辰翁词校注》。2018年底,又出版了《辛弃疾词校笺》。当今学界,能打通唐宋两个朝代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前面您提到,笺注刘词是因为唐圭璋先生的建议,那么辛词呢?
吴企明我在中文系任教,一直讲授唐宋段文学史和诗词作品选,选讲辛弃疾词是我常年的任务。当时主要的参考书便是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长年累月,我在学习、使用邓著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查得了一些新的资料,因而随手记录,积少成多,写成一篇《稼轩词补注释例》,发表在1981年第1期《苏州大学学报》上。2012年,我对此文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收入拙著《葑溪诗学丛稿初编》中。我开始从事辛词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直到2014年,承上海古籍出版社约稿,我才下决心笺注全部辛词。简单地说,我笺注辛词,研究辛词,有一个学习、运用、质疑、析疑的过程,也逐步认识到研究辛词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才下大决心去完成这项工作量极大的研究课题。
戴一菲《辛弃疾词校笺》确实是一个浩大的研究课题,是近年来宋词典籍整理的一大力作。出版以来,反响很好,一再重印,成为研究辛弃疾的必备书。辛词前有梁启勋、邓广铭、赵万里等人的注本,您在前贤基础上再行作注,知难而进,令人敬佩。
吴企明我的《辛弃疾词校笺》有四个地方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我从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艺术渊源、词体运用、语言艺术等方面作深入考量,提出了辛弃疾是“集词家之大成”的杰出词人的观点。第二,校笺工作贯彻“取长、正误、补阙”的六字方针。事实上,我在笺注长吉诗时已运用过,到笺注辛词时,更为自觉和成熟,所以写“前言”时特作以上总结。比如辛弃疾《鹧鸪天·寻菊花无有戏作》中的“掩鼻人间臭腐场”,邓注引《孟子·离娄下》,仅出“掩鼻”意;引《庄子·知北游》,仅出“臭腐”意,然“臭腐场”仍未注出。按《世说新语·文学》中说:“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这里稼轩变而用之,称官场为臭腐场。第三,我强化了校笺工作中的词学元素,特别重视笺释稼轩词涉及的词史知识、词人生平、词体特征、艺术风格、词作技法等,使全书真正成为能体现词学著作特点的注本。第四,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手段,为95%的辛词做好系年工作。正因为有了这四点,本书才取得了新的突破。
戴一菲您笺注刘词和辛词,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进入到宋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什么心得吗?
吴企明我乐于从事刘词和辛词的校注工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素来认为:不熟悉唐诗,就难以搞宋词。因为宋词与唐诗有血缘关系。宋代词人运化唐诗入词的实例,实在是太多了,不胜枚举。我正好是长期从事唐诗研究的,比较熟谙唐诗,容易看出宋人词句中运化唐诗的地方。比如刘辰翁《木兰花慢·别云屋席间赋》云:“朝朝买酒,典却朝衫,尊前自堪一醉。”是运化杜甫《曲江》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可以说,我校注刘词和辛词,真正尝到了“搞宋词必须熟悉唐诗”的甜头。我愿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明白地告诉学界朋友,特别是从事宋词研究的朋友,希望大家多读一点唐诗,将十分有助于我们对宋词的深入理解。
戴一菲之前提到的《桯史》《癸辛杂识》,还有您年过八旬之后重新修订再版的《靖康缃素杂记》,都是宋代史料笔记。您还参与了《宋诗话全编》的整理,编纂过徐铉、黄朝英、岳珂、刘辰翁和周密的诗话。能简要谈谈吗?
吴企明20世纪80年代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靖康缃素杂记》,是有意为之。这本书是宋代笔记中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宋代考据之学发展、递变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此书已引起很多学者关注,如程大昌说:“辨正世传名物音义,多有归宿。”(《演繁露》卷三)后代黄廷鉴《西溪丛话校识》也说:“其书与《缃素杂记》、王氏《学林》相近,考据家多称之。”我当时正是怀着探究考据之法的目的去从事该项工作的。校勘古籍,读书要广,要触类旁通,将各种知识联系起来。我正在笺注《范石湖集》,石湖《送寿老往云间行化》诗中有“舍卫城”的地名,《词源》和《佩文韵府》均未收此词。我忽然记起以前浏览过季羡林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曾记载过印度的不少国名、城名,果然一检便得。
四、穷搜旁汲,深耕题跋
戴一菲您还将自己的研究拓展到明清两代,参与了《明诗话全编》的整理,选编过《清代题画诗类》等,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向后拓展的?
吴企明我诗学研究的特点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一主攻,二拓展。”“一主攻”,指唐诗;“二拓展”,指由唐向宋、元、明、清拓展。参与《明诗话全编》的编纂、选编《清代题画诗类》,是拓展的具体表现。虽说拓展至明清两代,但都与诗、画密切相关。选编《清代题画诗类》,是因为我常年使用陈邦彦的《历代题画诗类》,发现此书虽名“历代”,然独缺“清代”。我要收集清人的题画诗,不得不在清人别集中去寻找,很不方便。有鉴于此,我便决心自己编。先确定编纂的原则,从诸家清人别集和重要总集搜集题画诗;又从多种清代书画题跋记专书和清人题画诗专集中收罗题画诗,比如金湅的《瞎牛题画诗》、瞿应绍的《月壶题画诗》等。我还特别重视从中外各大博物馆和私家收藏的清人画幅中收集相关作品。经数年时间编成此书,共有六十卷,以续陈邦彦之绪余。
戴一菲您还以数年之功,查证考索,辑集材料,发现了一些前人从未提及过的文字,编纂成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恽寿平全集》,出版后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吴企明研究清代画家恽寿平,是我宏观考察诗画融通的历史进程的结果。清代是我国诗歌和绘画创作最为繁盛和成熟的时期,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考量,我认定恽寿平正是出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最善于交融诗、画艺术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艺术家。他画艺超群,既长于山水、树石,又擅画花卉、禽鸟;学古而不泥古,能变革创新而别开生面,完善没骨画法,开出我国花鸟画的新局面。同时,他又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诗思清绝、诗境隽永秀逸,受到吴伟业、王士禛、沈德潜的称扬,素负“三绝”之名。他画了大量的诗画交融的画幅,写了大量的题画诗、跋文。我很早便关注这位画家,尽力搜集他的资料,除《瓯香馆集》以外,还辑集到题画诗、画跋、书信等佚文十卷,最终完成了《恽寿平全集》的校辑任务,并为他编写了一份详尽的年谱。在搜集《瓯香馆集》版本的时候,有幸得到苏州国画院前副院长马伯乐先生的无私帮助,他借我道光二十六年(1846)蒋氏宜年堂刊本,对我的校辑工作帮助很大。
戴一菲您整理的《恽寿平全集》,不仅增收了恽氏书信,还辑录了很多刻石、手迹、画幅上的题写墨迹和书画题跋。仅佚文就有《瓯香馆集》现存文字的一倍左右。辑佚工作费时费力,您是如何进行的呢?
吴企明我校勘过许多典籍,从来没有一部书像此书校勘那样复杂,也没有一部书像此书那样获得如此丰富的校勘成果。除了《瓯香馆集》等文字资料外,一方面,我在众多的书画题跋著作以及其他典籍、近现代出版的书画图册里,搜集他的题画诗和题跋;另一方面,我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私家收藏的石刻手迹和藏画中搜集他的题画文字,如《爱石山房刻石》《松烟肥砚斋恽帖》等。查阅画幅有两种书很重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日本铃木敬《中国绘画综合图录》,双管齐下,收获确实很大。恽寿平特别喜欢一诗多处题、一物多处画,这造成其作品特有的“重复”。比如,他有一首绝句云:“断崖一片秋云横,小桥石底泉声过。何时种花青琅玕,碧雨泠然展书坐。”这是在苏州博物馆藏王翚《山水图》上看到的版本。但在上海博物馆藏王翚、恽寿平《修竹远山图》上,恽氏题诗又云:“断崖苍茫磵路深,茅亭石濑泉声过。风潭百顷青琅玕,碧雨泠然展书坐。”辨识手迹、甄别重复,也是恽寿平诗文补辑工作的难点。
戴一菲是的,辨识手迹文字,确实需要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和书法素养。您还对明人黄凤池的《唐诗画谱》进行了研究,出版过一本《〈唐诗画谱〉说解》。有人说《唐诗画谱》所绘之图的水平并不高,您觉得黄氏此书的价值何在呢?
吴企明我之所以研究《唐诗画谱》,是因为看到它在诗画融通史上有别开生面的地方,很想探索一下它在融通诗画方面有什么特色和贡献。我将研究心得写成《〈唐诗画谱〉说解》一书,以画谱所选各诗为对象,加上简明的注释,并逐篇简要评说其艺术特征,以帮助读者理解、鉴赏这些作品。齐鲁书社编辑阎昭典先生得知此书脱稿,便促成了它的出版。我在此书的“前言”中标举“诗中有画”和“三艺融通”两大特征,概要地介绍此书的文学成就。“诗中有画”是黄凤池遴选作品的美学标准。例如,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诗中富有画意,“宜入宋人团扇小景”(乔亿《大历诗略》)。黄凤池坚持这个选诗宗旨,所选作品都是“诗中有画”的,能让画家充分发挥绘画艺术的长处,将诗境转换成画境,创造出“画中有诗”的优秀作品来。
戴一菲确实,能入选《唐诗画谱》的,都是视觉性较强的诗歌。那么“三艺融通”呢?
吴企明“三艺融通”是黄凤池编集此书的明确目标。他选出一首唐诗,请书法家将该诗写成一幅字,请画家依据诗意画一幅画,有意识地将诗、书、画三种艺术融通、“合一”起来,就像程涓在《唐诗六言画谱序》中所说:“一举而三善备矣。”《唐诗画谱》确实完成了这个艺术任务。因此,《唐诗画谱》的刊行,对推广“诗中有画”的唐诗,很有意义;对弘扬诗画融通的优良传统,很有贡献。当然,也存在一些缺憾:所请书画家都不是当时的名家;所选诗作出现字误、诗题误、作者误等弊病,甚至还有伪作。我已在相关诗篇的注评中有所说明。毕竟此书的贡献很大,功不可没,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是瑕不掩瑜的。
五、诗画融通,史论兼顾
戴一菲上面谈到的您对明清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已经为您下一步的诗画融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让人感到震惊的地方:您进入古稀之年后,又在诗画关系研究上做出新的开拓,连续出版了《诗画融通论》和《唐诗与绘画艺术》两部专著,能说说您重点关注和研究了哪些问题吗?
吴企明我在诗画关系上,重点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横向研究。诗歌与绘画的会合,是由疏远、宽松向紧密、频繁的方向推进的。我的《诗画融通论》通过诗画融通的七种表现形态和六十余种会合点和渠道,着重考察诗画深层沟通、融合的轨迹。这是解决诗与画的关系问题。二是理性研究。从诗画家的艺术实践出发,将诗画创作感性经验的排比、积累、分析和理性认识的感悟、阐述、总结,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比如《诗画融通论》中探讨了“气韵”“真”“神”等八个论题,都是在绘画、题画诗创作实践中概括、抽绎出来的理论问题。这是重点解决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关系问题。三是拓展研究。我们不能停留在个案研究上,必须将它们拓展开去,以发展的眼光对诗画融通做宏观研究,综合论述诗画融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宋扬无咎画了一幅《岁寒三友图》,楼钥题了一首诗,我除了写出这篇题画诗的评论文字外,更注重探讨“岁寒三友”艺术群像形象创造的过程以及它在宋以后的发展和衍变。这是重点解决个案研究与宏观考察的关系问题。四是纵向研究。诗画融通有一个日益成熟的发展历程。考察历代对诗画融通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作家和创作群体、诗画融通的著名论述和相关著作,勾勒我国诗画融通的演进历程,这属于纵向研究,我计划写作的《诗画融通史》,便是这样的一本书。
戴一菲您最早对诗画融通进行研究,大概是从对题画诗的整理入手的吧?除了前面提到的《清代题画诗类》外,您还主编过《中国历代题画诗》一书,不仅对历代题画诗进行收集、整理,还进行注释和评说。我发现,您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谈韵文发展的文章中,已经涉及对题画诗地位的肯定了。
吴企明不错,我的诗画融通研究,确实是从题画诗研究揳入的,那篇文章是《唐五代:我国韵文发展的光辉时代》(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其实,我关注题画诗的时间还可以推前一些。去年,我有幸参加苏州大学文学院78级毕业生聚会,有位同学一本正经地跑来告诉我:“吴老师,您当年给我们讲题画诗,我至今还记得。”以此推算,我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题画诗了,或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或将它们作为教学内容,讲给本科生、研究生听。1990年,我与窗友金学智、姜光斗合作撰写《历代题咏书画诗鉴赏大观》,我在“前言”中就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重视诗画融通的审美理念。
戴一菲拜读您的著作,深为先生读书之多、用功之勤、考证之精、论辨之确所折服。您对画论和诗论的熟悉与汇通令人叹服,好像脑子里有个数据库可以自动检索一样,这应该都是几十年不断积累的结果。
吴企明对。除了你提到的《中国历代题画诗》外,从2003年到2007年,我先后出版过《题画绝句的写作与欣赏》《历代名画诗画对读集》《传世名画题诗品赏》《题画词与词意画》(与史创新合作)等等。最近,还有一套《历代题画绝句评鉴》(与杨旭辉、史创新合作)获得2018年“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奖。这些著作,选录、注释、评论了大量的题画诗,是我研究题画诗的学术成果。它们也可看作我为研究诗画融通特别是写作《诗画融通论》一书所作的长期准备。
戴一菲您刚才提到的《历代名画诗画对读集》,这个“对读”的概念十分有趣。前面您说“读画”是受到网师园“读画看松轩”的启发,那么“对读”又怎么讲呢?
吴企明画要读,题在画上的诗也要读,还要将画与诗对照起来读,这就是“对读”。运用“诗画对读”的审美方法,可以体悟出诗画融通的艺术美之奥秘。我们可以从两大类型的题画诗,分别体识出“诗画对读”方法的具体细节以及心灵和审美的感悟。第一类,诗画对应关系非常紧密。诗人采用白描手法,摹写画面具象,再现画境,题诗与画象有着类近的性格和密切的联系。例如王武《白头三友图轴》,画面上的松、竹、梅均从画幅右部出笔,向左部挺生,松枝上站立着一只白头翁,正回头凝视右方,好像正在看着松、竹、梅。王武自题一诗道:“雪尽亭皋松枝寒,忽闻春信到阑干。胭脂冻蕊垂垂发,头白人须仔细看。”题诗首句写画上之松;次句写画上之梅,梅花开放,带来春到的信息;第三句紧承上句,仍写梅;结句才扣到赠友的画意上。“头白”一语双关,既指画面上的白头翁,也指头白人“翔兄”。诗人说,请你仔细看看画中“岁寒三友”的画象和画家的匠心,希望与你共订“岁寒心”的盟约。读画人一边读画,一边读诗,逐渐领悟画面的外表形象和内在意蕴。
戴一菲这是诗、画在形象设置、表达意蕴方面比较一致的一种情况。那第二类呢?
吴企明第二类,诗画对应关系并不紧密,却有内在联系。诗人并没有直接、具体地描写画面,或则采用侧面着笔的手法,或则宕开画面,画外生情,或则画外生发,阐发画理。对于这些关系并不紧密的作品,尤应运用诗画对读的审美方法,细细寻绎题诗和画象、画境的内在联系,比较全面、深入地理解、欣赏这些作品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三昧。比如孙克弘的《雨景山水图》,这是一幅烟雨中的山野图景,云雾弥漫于群山中,极云烟变灭之奇。画家题诗云:“僧房十日掩柴关,闲看浮云自往还。无限天机心会得,起来磨墨写房山。”题诗一开头并没有描写画面,而是从画家的现实生活落笔,描写其在僧房中不出门,整日无事,闲看浮云在山中自由流动。诗的后半首,陡然一转,说画家从浮云的流动悟出无限天机,获得创作灵感,于是便磨墨挥毫,仿学高克恭的笔意,画出这幅《雨景山水图》。题诗似乎与画面关系不大,然而读画人对照诗画以后,自然能体味出题诗与画面的内在联系。像第二句“浮云自往还”,正是画象的恰当描写;又像结句,点出本图的美学特征和艺术渊源,来自高克恭。借助题诗来品画,使诗情和画意互相渗透,交会融合,这恰恰是“诗画对读”带来的审美效果。
戴一菲您对于诗画融合的研究,还有一本新著《唐诗与绘画艺术》。您专门将唐诗作为研究对象,是否因为唐诗较前、后代诗歌在诗画融合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企明确是这样。这首先应从唐代诗学、画学特别繁荣谈起。唐代的绘画艺术,画科众多,名家辈出,画风多样,画坛呈现出兰菊竞芳、异彩纷呈的可喜局面。现存的唐代画论、画史著作很少,且论述很简略,并没有全面反映出唐代绘画艺术昌盛的真实面貌。但唐代写到唐画的诗篇很多,它们深刻地揭示出唐代画家的生活和心态,阐述了唐人的绘画主张与画学思想,描绘了许多画幅的布局、意象、笔墨、色彩,再现了画幅的气韵和意境,真切地记录下唐代绘画艺术的发展轨迹,全面地展示了唐代绘画繁荣的历史面貌。
戴一菲您在《唐诗与绘画艺术》一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些诗歌史上地位不高,但是在画史或画论史上有着一定作用的诗人,比如方干,他的题画诗在荆浩之前已经关注笔墨并举的问题。您这方面的发现不仅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也填补了绘画研究中的不少空白。
吴企明你举出的方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画史、画论著作中根本没有论及的唐代画家,有一些却在唐诗里得到记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和信息。比如,花鸟画家毋丘元志,画史无载,白居易《木莲树图并序》云:“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写。惜其遐僻,因题三绝句。”其他如于邵、齐己、吴偃、于兴宗、方原、陈式等画家,画史上都无记载,我依据唐诗的记载,将他们勾稽出来,以补画史之缺失。
戴一菲除了勾稽绘画史上不应缺失的画家外,您还对画论中的某些观点进行释疑,纠正了前人的不少失误。
吴企明这是我在写作此书时努力追求的学术目标,也是我聊以自慰的地方。比如,我征引了大量唐诗,论证“画境”说受到唐代“诗境”说的催化和影响,在唐五代逐渐形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没有提及过“意境”,过去有人摘引郭熙《林泉高致·画意》:“境界已熟,心手已应。”认为“画境”说起源于宋代,这是不恰当的。透过诗境说画境,深入阐述唐五代已形成绘画意境学说,可以弥补画论之不足。还有“形生虚无”的画论,在以前的许多画学著作中,很少有人论及。我举出皎然《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他在诗中明确提出了“形生虚无”的画学观点,在中晚唐五代佛道、神鬼画像十分风行的时代出现,极有价值,对后代画家、画论家产生过深远影响。有些画论家的相关言论,实际上源于皎然,如宋代董逌、李廌,清代钱杜、钱大昕等,都有相似的论说。
戴一菲总结一下您的研究,真可以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来形容,“博”在于您的研究领域囊括历史、文学、绘画等多个门类,“大”在于您研究的朝代历涉唐、宋、明、清,“精”在于您笺注古籍之细致妥帖,“深”在于您深入沟通了诗画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您聊了这么久,我受益良多。最后,能用几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治学经验吗?
吴企明我出版的学术著作,都是自己写“前言”,将我的读书心得、治学经验融贯其中。概括起来,可以用五个“求”来表述我的学术追求,即“知识求宽博,思维求会通,论述求精深,考核求真实,积累求厚重”,说得文雅一点,便是二十个字:“学殖赅博,融会贯通,论说精深,务实求真,厚积薄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诗诗意在文人画中的呈现与嬗变”(批准号:18YJC751006)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