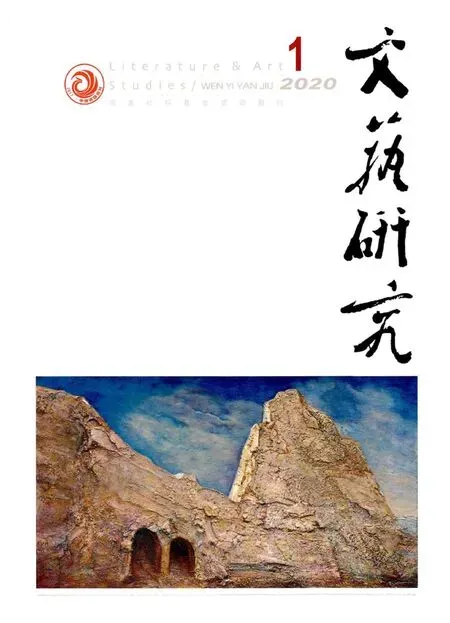《牡丹亭》蓝本为《杜丽娘记》补说
周明初
自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发现何大抡本《重刻增补燕居笔记》中收有《杜丽娘慕色还魂》、余公仁本《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中收有《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①,以及《宝文堂书目》中著录有《杜丽娘记》以来②,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的《牡丹亭》创作是有小说作为蓝本的。谭正璧猜测两种《燕居笔记》中有关杜丽娘的小说很可能就是《宝文堂书目》中所著录的《杜丽娘记》,从而认为它是戏剧《牡丹亭》的本事来源③。经过姜志雄对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所藏何大抡本《重刻增补燕居笔记》的认真考察和论证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为戏剧《牡丹亭》的蓝本,成了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⑤。当然,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但很微弱。刘辉认为,《牡丹亭》的蓝本是《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杜丽娘记》,它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不是同一种小说,而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是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影响下的产物⑥。后来,向志柱发现了明万历甲午(1594)胡文焕序刻本《稗家粹编》中收录有文言小说《杜丽娘记》,而《稗家粹编》的刊刻时间比《牡丹亭》问世的时间早两年,从而认定《牡丹亭》的蓝本是文言小说《杜丽娘记》⑦。但向志柱的观点遭到了坚持主流观点的伏涤修、陈国军等学者的反对⑧。最近张正学又提出,《牡丹亭》的蓝本是《杜丽娘记》与《杜丽娘慕色还魂》两者的综合体⑨。
在《牡丹亭》的蓝本问题上,学界之所以存在较大的分歧,关键还是在于目前大家对何大抡其人几乎一无所知,对他所编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的具体编刻年代也不是很清楚,虽然有学者认为该书产生于晚明时期,但因缺少过硬的证据而不被采信,从而在戏曲《牡丹亭》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聚讼纷纭。其实,除了《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外,何大抡还有两种有关《诗经》的著述现存于世。通过对这两种著述的考察,可以确定何大抡与汤显祖的门人李本仁交往密切,他的生活年代晚于汤显祖一辈,《重刻增补燕居笔记》成书于万历后期;通过对《杜丽娘记》和《杜丽娘慕色还魂》在语言形式和体式上的研究,大致可以确定《杜丽娘记》为正德至嘉靖年间的产物,而《杜丽娘慕色还魂》为晚明时的产物;通过对《宝文堂书目》的进一步研究,可以确定宝文堂所藏书籍大致不晚于晁瑮逝世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因此,《宝文堂书目》中所著录的《杜丽娘记》不可能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
一、何大抡的生活年代和《重刻增补燕居笔记》的成书年代
现存的《燕居笔记》有三种,均已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一为《新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一、二有署“芝士林近阳增编、书林余泗泉梓行”,卷三、四有署“闽芝士林近阳增补、萃庆堂余泗泉梓行”,通常称为林近阳本;一为《重刻增补燕居笔记》,正文前有《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引》,文末署“古临琴涧居士何大抡元士题”,通常认为此本为何大抡所编;一为《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卷一署“明叟冯犹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通常认为所谓冯梦龙增编为书商伪托,实际编者为余公仁。此三书均称“增补”,故学界推断当有原刻本,但现在已见不到。此三种《燕居笔记》,林近阳本没有收入有关杜丽娘故事的小说,而另两种则有收。
《新刻增补燕居笔记》的增补者林近阳为闽人,其余情况已不详,但梓行者余泗泉(又名余章弓德)是明万历年间活跃于福建建阳的书林萃庆堂的书坊主,卒于万历四十六年至泰昌元年(1618—1620)之间⑩,又余泗泉为余象斗之兄,而余象斗约生于嘉靖二十七年⑪,可知余泗泉生于嘉靖二十七年前,卒于万历末年。据肖东发《建阳余氏考略(中)》列表所作的统计,为“萃庆堂”或“余泗泉”“余彰德”刻书者所刻之书共31种,除《新刻增补燕居笔记》等少数几种所刻时间不详外,大多数可知刻于万历年间,且刻于万历九年至万历四十三年之间⑫。据此可推知林近阳本也应编刻于万历年间。陈大康认为该本与《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等小说一样,当刻于万历三十一年前后⑬,庶几近之。
《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的最后附有“余元长公仁编、魏邦达去非订”的《新编南窗笔记补遗》一卷和“书林余元长公仁著”的《南窗草诗集》一卷、《南窗草语录》一卷,可知《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的实际编者余公仁,字元长,何长江据《南窗草诗集》所收注明写作年份的诗作,已考出余公仁生于万历四十三年,并认为他是一位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遗民,他增补的《燕居笔记》编于明末易代之前而刊刻于清初⑭。又此文所据《书林余氏重修宗谱》,其中余泗泉有孙名元熹、元焘、元勋、元杰,而公仁字元长,从而将余公仁视作余象斗重孙辈,这是据旧说将余泗泉视作余象斗之侄所造成。实际上余公仁应当为余泗泉、余象斗的孙辈。
《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即通常所说的何大抡本,由于学界一直认为编者何大抡及刊刻者“金陵书林李澄源”的生平无考,此书成于何时分歧较大。姜志雄提出该本“涉及嘉靖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书中连一篇也找不到”,据此“可推断何本《燕居笔记》成书年代上限在嘉靖十九年”⑮,而陈大康则认为“何本《燕居笔记》之出应在林近阳增编本之后,且不避‘由’字,亦万历时所出也”⑯。
其实,编者何大抡的生平并不是完全无考。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何大抡所编的《诗经默雷》八卷和《诗经心诀》八卷两种,前者同时也藏国家图书馆。根据两书的序及序后所列对书稿“鉴定”人的名单,大致可以确定何大抡的生平活动时段⑰。
《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引》署“古临琴涧居士何大抡元士题”,而《诗经默雷》在“凡例”后署“古临琴涧居士何大抡谨识”,《诗经心诀》正文卷首题“古临何大抡元士父纂著”,可知三书的编者“何大抡”为同一人。
《诗经默雷》卷首有何三省、余有敬所作的两序,何序署“辛未长至日广昌何三省曰唯题”,署款后并有“辛未进士”“何三省印”两个篆文印章;余序署“丰城余有敬元礼漫书”,署款后并有“余有敬印”“甲子解元”两个篆文印章。何三省,《江西诗征》卷六三、《(康熙)江西通志》卷三五、《(乾隆)建昌府志》卷四四、《(康熙)广昌县志》卷四等均有传。据《(乾隆)建昌府志》结合《(康熙)广昌县志》,可知三省字曰唯,又字观我,号印兹,江西广昌人。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进士。授顺天府学教授,转国子博士,改礼部主事、晋郎中。出为广东提学。明亡后隐居不仕⑱。而余有敬,《(康熙)丰城县志》卷一一有传,据该传可知,有敬字元礼,江西丰城人,天启四年(1624)甲子科江西乡试第一名,后曾署东乡县学教谕,历吏部司务⑲。
何三省之序署款作“辛未长至日”,而序中又称“偶从观政之暇”,可知该序作于崇祯四年冬至日,其时何三省作为新科进士正在六部等机构中观政实习(明代新进士在正式授予官职前均需在中央机构各衙门中实习一段时间,称“观政”)。该序中称“元士,予侄也,祖于吾邑而隶于东乡”,可知何大抡祖籍广昌,后迁居于东乡,在辈份上是何三省的族侄。东乡县原为临川县东境,明代正德年间分临川县东境,并合原金溪、安仁等县的一部分组成,在明代与临川等县同隶属抚州府。由此也可理解何大抡所编三书,为何均署“古临”了。原先有学者称何大抡为杭州人,应当是将“古临”当成了临安即杭州的别称了⑳。
在何三省、余有敬两个序后,有《同订诗经默雷友人姓氏》,分“鉴定”“参阅”“同订”等三类,其中“鉴定”类,共有34人,列有“李愚公,讳若愚,丙辰,汉阳人”之类信息,显然第一项为姓氏及表字,第二项为名讳,第三项为鉴定年份,第四项为籍贯等。从鉴定人的籍贯来看,有三分之二以上为江西籍人,特别是抚州府及周边的人;从第三项鉴定年份来看,大多是在天启、崇祯两朝,而最早的为“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最迟的为“辛未”即崇祯四年。可知该书应当在万历三十四年前已成稿,刊刻于崇祯四年之后。
《诗经心诀》卷首有黄文焕、李学旻所作的序,黄序署“天启丁卯岁八月既望永福黄文焕维章甫题于金陵之万卷楼”,署款后有“文焕”“乙丑进士”两个篆文印章;李序署“天启丁卯秋月眷友弟李学旻本仁父谨识”,署款后有“学旻”“己酉解元丙辰乙榜”两个篆文印章。可知此两序皆作于天启七年。黄文焕,《(乾隆)福建通志》卷四三、《(乾隆)福州府志》卷五六、《(乾隆)永福县志》卷八等均有传。据《(乾隆)永福县志》可知黄文焕字维章,福建永福(今永泰县)人,天启五年乙丑科进士,授海阳知县,改番禺,又改山阳,皆有政声。崇祯年间召为翰林院编修,受黄道周劾杨嗣昌案牵连而下狱。事雪,侨寓金陵,以著书为业㉑。李学旻,《(康熙)江西通志》卷三四、《(康熙)抚州府志》卷一七、《(同治)临川县志)卷四二等均有传。据《(康熙)抚州府志》可知,李学旻字本仁,江西临川人,万历三十七年江西乡试己酉科举人,并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会试中名列乙榜,后就选峡江县学教谕,补饶阳。擢国子监学正,迁泰州知州,后因事贬为汉川知县㉒。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学旻。他不仅是《诗经心诀》的作序者,同时也是《诗经心诀》和《诗经默雷》两书的鉴定人。他对《诗经默雷》的鉴定是在己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可见此人与何大抡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相识并交往。从李学旻为《诗经心诀》所作序的署款自称“眷友弟”来看,两人为同一辈份,年龄上应当相差不大,而李学旻则是汤显祖的门人。李序中称:“夫温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诗者也。予口四始六义时,见诸父兄群而商咨嗟咏叹之意,以究音响节族之自然者,从旁识其一二语,亦不解也。后就汤若士师质之,师云……”汤若士即汤显祖(号若士),而汤显祖则有书信《与门人李本仁》㉓。
何大抡的《诗经默雷》成于万历三十四年前,刻于崇祯四年后,他人为此书作序和鉴定的时间则大多在天启、崇祯年间,而他人为《诗经心诀》所作的两个序也是在天启年间,可知何大抡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万历中后期至崇祯年间。而汤显祖门人李学旻又与何大抡以同辈相称,可知何大抡比汤显祖晚一辈,他大约出生在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最早也是出生在嘉靖末年。
何大抡所编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是他中晚年时成书的。他在《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引》中说:“举世皆尘冗也,不得一日之余闲,则此身此心,大半在奔逐间……悠悠忽忽,少而壮,壮而老……爰从幽窗,稍悟冷致。有一事焉,堪脍炙人口者,则笔之;有一词焉,堪耸动人听者,则笔之。而且为记耶,为传耶……靡不一一备载。一开卷间,而灿若指掌,烂若列眉。天下之美,尽在此矣。燕居时之所得,不既多乎?”㉔此引中,何大抡说自己平生一大半时间都在奔忙中,很快地由少年成壮年、由壮年成老年,终于到了能够燕居的时候,于是编了这部包含了各种文类的笔记。古人五十来岁,往往称自己为老年,如宋人孔平仲《相看一首寄芸叟》有题注:“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诗云:“相与同少壮,看看俱老人。”㉕王之望《醉花阴·生日》:“弹指片声中,不觉流年,五十还加二……休画老人星,白发苍髯,怎解如翁似。”㉖明人邵宝《理发见白有感》:“我齿邻半百,光阴逝江河。老至不自觉,自谓心无他。”㉗清人蒋薰《惊秋六首》之四:“生年半百老相寻,懒草玄文捉鼻吟。”㉘何大抡在引中称自己“少而壮,壮而老”,这部《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大约也是何大抡在五十岁以后所编,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后期及以后。
又上文已提到陈大康因为该书不避“由”字,认为该书为万历年间所出。今考该书,也不避“洛”“常”两字,如下层卷一《座客琼谈》“诗类”“相约一笑”条:“唐李泌,肃宗时召至,赐金紫,拜司马。贼平,隐衡山,后居洛。”上层卷一《天缘奇遇》:“生自与玉香合,精神倍常。”㉙明代避帝讳,起初松驰,至天启、崇祯两朝始严。《重刻增补燕居笔记》中不避泰昌帝朱常洛之御名,也不避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御名中之“由”字,可知此书不可能是天启、崇祯两朝所刊刻而是万历年间所刊刻。结合起来看,该书应当编刻于万历后期。
二、《杜丽娘记》和《杜丽娘慕色还魂》的产生年代
汤显祖的《牡丹亭》创作于万历中期,确切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这已经为学界所公认。《重刻增补燕居笔记》成书于万历后期,而收入其中的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不一定产生于《牡丹亭》之前,也可能产生于《牡丹亭》之后。如果《杜丽娘慕色还魂》产生于《牡丹亭》之后,则失去成为《牡丹亭》蓝本的可能性,这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向志柱通过对《杜丽娘记》《杜丽娘慕色还魂》和汤显祖的《牡丹亭》进行文本考察后认为:“《牡丹亭》的写作参考了文言小说《杜丽娘记》,而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在《杜丽娘记》的文字基础上,对《牡丹亭》中的《惊梦》《寻梦》《闹殇》等出的许多文字进行直接因袭。”㉚不过,遗憾的是,向志柱的文章没有对《杜丽娘记》和《杜丽娘慕色还魂》的产生年代进行考定,所以学界对他的结论信从者较少。笔者基本认同他的结论,这里对《杜丽娘记》和《杜丽娘慕色还魂》的产生年代进行大致的考证。
先看《杜丽娘记》。该小说收入《稗家粹编》卷二《幽期部》中,而《稗家粹编》有胡文焕在“万历甲午仲春望日”所作的序,序中称:“余恐世之日加于偷薄也,日流于淫鄙诬诞也,不得已而有是选焉。”“且是书,世既喜阅,则阅必易得……”㉛从序中所称该书为“是选”“是书”来看,万历二十二年甲午胡文焕写序时,该书已经编成,则收入其中的《杜丽娘记》至少也是在该年之前已经在社会上流传。
《稗家粹编》是一部文言小说集,所收小说,有许多可以从诸如《玄怪录》系列、“剪灯”系列及《鸳渚志余雪窗谈异》等小说中找到来源,但《杜丽娘记》则不知所出。作为“文言小说”,《杜丽娘记》与收入《稗家粹编》中的绝大多数文言小说,在语言方面的差异实在是很明显的。该小说多用双音节词语,“之乎者也”之类文言文中具有标志性的虚词出现得极少,且看开头一段文字:
宋光宗间,广东南雄府尹姓杜,名宝,字光辉。生女为丽娘,年一十六岁。聪明伶俐,琴棋书画,嘲风咏月,靡不精晓。忽值季春天色,唤侍婢春香,同往堂府后花园游赏。不免触景伤情,心中不乐,急回香阁。独坐无聊,俯首沉吟而叹曰:“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遂凭几昼眠。才方合眼,忽见一书生,年方弱冠,丰姿俊秀,于园中折柳枝一枝,笑谓小姐曰:“姐姐既能通书史,可作诗咏此柳乎?”小姐欲答,又惊又喜,不敢轻言。心中自忖:“素昧平生,不知姓名,何敢辄入于此?”正如此思间,只见一生向前,将丽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架边,共成云雨之欢娱,两情和美。㉜
这样的文字,与其说是文言小说的文字,不如说是话本小说的文字,如果在开头加上“入话”的一首诗或词,放入《清平山堂话本》中,其实也是合适的。像见于《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风月相思》等,其文言色彩比这篇浓厚得多。至于《杜丽娘记》下文中“今小姐天赐还魂,择吉日与孩儿成亲”,“孩儿”为白话口语化的词语,更非文言文词语。
《杜丽娘记》虽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南宋光宗年间,但这篇小说产生于明代,这从开头出现的“广东南雄府”这一地名即可知,两宋时的广南东路南雄州,在元代为江西行省南雄路,在明代始称广东南雄府。那么这篇小说究竟产生于明代什么时候呢?
在《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有一篇话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以林升的《题临安邸》一诗入话,“入话”后的正文部分,其语言形式与《杜丽娘记》较为接近,这里不妨也以开头部分作为对照:
话说弘治年间临安府旬宣街,有个富翁姓徐名大川,娶妻戴氏。俱以五十有三,止生一男,名徐景春。其年二十有六,善调诗韵,经营为业。其时春间天气,景物可人,无以消遣。素闻山明水秀,乃告其父母,欲往观看。遂分付琴童,肩挑酒垒(笔者案:疑“垒”为“罍”,下同),出到涌金门外,游于南北两山,西湖之上,诸刹寺院,石屋之洞,冷泉之亭,随行随观。崎岖险峻,幽涧深林,悬崖绝壁,足迹殆将遍焉。正值三月之望,桃红夹岸,柳绿盈眸。游鱼跳掷于波间,宿鸟飞鸣于树际。景春酒至半酣,仰见日落西山,月生东海,唤舟至岸,命琴童挑酒罇食垒,取路而归。㉝
从所录两篇的开头即可看出,此两篇文字双音节组成的词语较多,四字句较多,语言较为通俗易懂,文字介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而更趋近于白话文,但纯粹口语化的白话词语则又出现得较少。冯梦龙曾在《古今小说》的序言中指摘说:“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㉞这个评价,用在《杜丽娘记》上,也同样合适。
话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谓故事发生在明弘治年间,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也提及此篇谓:“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㉟又在卷二六《幽怪传疑》中略载孔淑芳事也谓弘治年间,可知话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产生于弘治之后,应当是正德至嘉靖年间的产物。语言风格与之接近的《杜丽娘记》,也可能产生于这一时期。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胡文焕《稗家粹编》卷六收有《孔淑芳记》,《古今清谈万选》卷二中《孔惑景春》则据此而来。此两种中所收小说为文言小说,不记故事发生的年代,故事中人物“林世杰”,在话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及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六中作“张世杰”,而《宝文堂书目》中也著录有《孔淑芳记》,与《稗家粹编》名称相同。可知文言小说《孔淑芳记》产生得较早,话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据此改编而来,并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定在弘治年间㊱。
再看《杜丽娘慕色还魂》。从小说中提到的“广东南雄府”“山西太原府”“四川成都府”这些行政地名来看,该小说产生于明代。“广东南雄府”上文已说过,而太原府在北宋时属河东路,金代属河东北路,元代为中书省冀宁路,明代始称山西太原府;成都府在两宋属成都府路,元代为四川行省成都路,明代始称四川成都府。作为话本,它与现存的刊刻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中的话本相比较,差别还是很大的。《清平山堂话本》中所收,有些是宋元时的话本,有些是明代的话本,如《风月相思》写洪武年间事,则肯定是明代的产物。这些话本,一般都有诗或词开场的“入话”,结束处有一首诗或两句诗作散场,而《杜丽娘慕色还魂》只有开头作为“入话”的四句诗,并没有“散场诗”。而刊刻于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的《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前三种也俱有“入话”及“散场诗”,只有最后一种《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有“入话”而无“散场诗”。《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可以确定为明代话本的是后两种,其中第三种《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即《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风月相思》,基本上用文言文写作,应当产生于明初至嘉靖年间这一时段中。而第四种《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上文已经说过是正德至嘉靖年间的产物,语言风格与《杜丽娘记》最为接近。如果将《杜丽娘慕色还魂》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相比较,在语言形式上,显然《杜丽娘慕色还魂》的白话口语化的色彩浓厚得多,如“有个官”“请个教读”中的量词“个”,“这小姐”“这柳衙内”“这柳夫人”“这杜相公”“这柳推官”中的指称代词“这”,还有“女孩儿”“孩儿”之类儿化音的词语,都是带有白话口语性质的。因此,同样是对宋元话本的模拟之作,《杜丽娘慕色还魂》在产生时代上比《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应当更迟。
再有,同样以一首诗作为“入话”,《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有“入话”两字,而《杜丽娘慕色还魂》不标示“入话”两字。收录《杜丽娘慕色还魂》的何大抡《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在卷一○下栏中也收有《柳耆卿玩江楼记》,前有入话诗,后有散场诗,且“入话”两字未删,可知《杜丽娘慕色还魂》不标示“入话”两字,并非刊刻时所删,而是原本就没有此两字。又“三言”“二拍”“一型”这几种成于天启、崇祯年间的话本小说集,均有作为“入话”的诗或词,但不标示“入话”两字,只有“二拍”用“诗曰”之类作标示,可知在入话诗前不标示“入话”两字,是晚明时改编原有的话本及创作拟话本时的通常作法。综合起来看,《杜丽娘慕色还魂》也应当是产生于晚明时期,更具体地说,应当是产生于万历中后期。
卓发之(1587—1638)《漉篱集》卷一二收有765字的《杜丽娘传》,传后有自评云:“此杜氏本传,未经临川更演者也。是余庚戌年所辑。少年著述,惟存此一篇耳。”㊲可知这篇为卓发之在万历三十八年所辑录,是卓发之年轻时所著述的作品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篇。据发现者陈国军及黄义枢、刘水云的研究,《杜丽娘传》辑录自《杜丽娘慕色还魂》㊳,则《杜丽娘慕色还魂》万历三十八年之前就已经产生。
三、《宝文堂书目》的成书年代
晁氏《宝文堂书目》为晁瑮、晁东吴父子的藏书目,因为著录了不少小说、戏曲的名称而为现今的小说、戏曲史学者所重视。这部书目,自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编著者为晁瑮后,现在一般相沿认为是晁瑮所编。但这部书目的著录,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殊妨检阅”㊴。例如卷上“文集”“诗词”两大类中总集、别集混杂,唐宋元明的别集混杂,诗集与诗文别集混杂,漫无头绪。《补斋诗集》《春岗诗集》《南坞诗集》《柘轩诗集》等明明是诗集㊵,却著录入“文集”类中而不是著录在“诗词”类中;卷中“子杂”类中笔记、杂记、各种小说(传奇、话本等)混杂在一起,而“乐府”类中既有词又有曲,其中词又与“诗词”类中之“词”部分重复。同一名称的书,在不同的类别中重复著录,如严嵩的《钤山堂集》,既出现在“诗词”类中,又出现在“子杂”类中㊶,实际上这是一部诗文别集,应当收入“文集”类。有的不光在不同类别中重复著录,在同一类中也重复著录,如高棅的《唐诗品汇》,不仅在卷上“诗词”类里二次出现,还在卷中“类书”里出现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此书稍早而同为嘉靖年间高儒的《百川书志》、更后一些的万历年间徐的《红雨楼书目》,同样是私家藏书目录,无论是分类还是著录,均比较好地遵循传统目录学中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分小类、小类下分子目的著录方式,虽然分类未必完全恰当,如《百川书目》中将小说、戏曲分在史志中的“野史”“外史”“小史”三类中,但无论怎样,著录得眉目清楚,不相混杂。晁瑮和晁东吴父子均是嘉靖年间进士,并先后入选过翰林院庶吉士,而晁瑮还做过国子监司业和司经局洗马,都是与文化事业有关的官职,其中司经局洗马掌东宫图书之事。按理来说,像他们这样翰林出身的人,接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不会对传统的目录学一无所知,如果对自家的藏书进行编目,不会如此混乱不堪。因此让人怀疑这部《宝文堂书目》是否真的是晁瑮所编。
好在晁瑮的墓志铭前几年已经在河南濮阳县出土,他的生卒年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这为我们检验《宝文堂书目》是否为晁瑮所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现已知晁瑮生于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丁卯,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享年54岁;其子东吴生于嘉靖十一年壬辰,卒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享年23岁㊸。现在可以晁瑮的卒年嘉靖三十九年为时间断限,看看《宝文堂书目》中所收书有无迟于该年刊刻的。如果嘉靖三十九年及以后所刊刻的书仍有收入该书目中,则说明该书目不可能是晁瑮所编,而是他的后人所编。
笔者以《宝文堂书目》卷上“文集”“诗词”两类作为查考对象,因为这两类所涉为诗文集,比较容易确定著述者,考查出著述者的生卒年以及著述在明代的刊刻情况。通过考查,笔者发现这两类中所著录的诗文集,无论是明代以前作家的还是明代前中期作家的,大多在嘉靖年间有过刊刻,《宝文堂书目》中所著录应当大多是嘉靖年间所刊刻的集子。而明代嘉靖年间在世的作家的诗文集,该书目中也著录有不少,如《薛考功全集》是薛蕙(1489—1541)的诗文集,《陆俨山文集》是陆深(1477—1544)的文集,《徐子仁诗集》是徐霖(1462—1538)的诗集,《朴庵诗集》是章拯(1479—1548)的诗集,这几位作家均比晁瑮早离世一二十年,他们的别集应当是嘉靖三十九年以前就已刊刻了的。也有些作家,虽然比晁瑮晚几年离世,但他们的文集在嘉靖三十九年前就已经出版了,如张含(1479—1565)的《张愈光文集》、许应元(1506—1565)的《许水部文集》、虞守愚(1483—1569)的《东崖文稿》等。有些嘉靖年间在世的作家的诗文集,借助《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之类目录学书,可以考知确切的刊刻时间,如皇甫涍(1497—1546)的《皇甫少玄集》刊刻于嘉靖三十年,浙江图书馆等有藏,后收入《四库全书》中;刘储秀(1483—1558)的《刘西陂集》刊刻于嘉靖三十年,《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有收;苏佑(1492—1571)的《谷原诗集》刊刻于嘉靖三十七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有收。
该书目中著录有《黼庵遗稿》,这是柴奇(1470—1542)的遗稿,刊刻于嘉靖三十九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为嘉靖三十九年刻崇祯八年递修本。《黼庵遗稿》卷首有邹守益在“嘉靖庚申孟夏”所作的序,序中称:“嘉靖庚申夏,益趋谒阳明先师于天真,温江浙之会。黼庵之幼子秩官薇垣,其孙辅喆判转运,以年家之谊持《遗稿》,以征言于卷端。”㊹邹守益与柴奇为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同年进士,“嘉靖庚申孟夏”即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其时邹守益在杭州,住在为纪念王阳明而筑的玉皇山天真精舍。天真精舍建成于嘉靖九年,其后春秋两季,王门弟子常聚会于此讲学并祭祀王阳明。邹守益此序写于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则《黼庵遗稿》最早也应当刻成于该年四月。而据《明故奉训大夫司经局洗马镜湖晁公暨配二张孺人合葬墓志铭》所载,晁瑮卒于嘉靖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㊺。考虑到当时书籍刊刻后的流通情况,在晁瑮离世前,得到并入藏《黼庵遗稿》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从“文集”“诗词”两类的调查来看,能够确定无误是在嘉靖三十九年以后才出版的书籍,也确实较难。
由上可知,《宝文堂书目》确实是晁瑮、晁东吴父子的藏书目录,宝文堂中所入藏的书籍大致不晚于嘉靖三十九年。从极少数书的后面简要注明有版刻情况来看,晁瑮父子生前可能有过简单的入藏记录,但该书目不是晁瑮生前亲自编定的,而是在晁瑮死后,晁氏后人利用原有的记录,加以补充编成。据《明故奉训大夫司经局洗马镜湖晁公暨配二张孺人合葬墓志铭》,可知晁瑮有三子:长子东周,早卒;次子东吴,也先晁瑮而卒,此两人为原配所出;三子东楚,继配所出,时为“德府典仪”。而晁瑮有孙五人,俱东楚所出。万历三十年东楚母张孺人卒后,与其父及先母合葬,东楚请南京兵部尚书周世选撰写此篇合葬墓志铭㊻。据该墓志铭,晁瑮的原配张孺人卒于嘉靖二十年辛丑,东楚为晁瑮的继配所生,则当生于嘉靖二十一年之后,在嘉靖三十九年晁瑮逝世时还不到20岁。他在万历年间担任“德府典仪”,即位于济南的德王府中掌礼仪的九品官员,可知他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没有取得什么功名,担任藩王府典仪这样的小官也可能还有父亲的余荫在起作用。《宝文堂书目》很可能就是在晁瑮离世后,东楚及其家人在原有入藏记录的基础上,清点父兄生前的藏书而编成的书目。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不熟悉古代典籍的传统分类目录,以致书目编得混乱不堪。
四、《牡丹亭》的蓝本不可能是《杜丽娘慕色还魂》
以上三部分的考证已知:《宝文堂书目》中所著录的书不晚于嘉靖三十九年,《杜丽娘记》大约产生于正德至嘉靖年间,而《杜丽娘慕色还魂》产生于晚明时期,因此《宝文堂书目》中所记载的《杜丽娘记》不可能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而是万历二十二年胡文焕刊刻的《稗家粹编》中被当成文言小说收入的《杜丽娘记》。
在《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里,与《杜丽娘记》相邻的一组小说依次为《绿珠记》《贾岛破风诗》《红莲记》《冯玉梅记》《郭大舍人记》《杜丽娘记》《萧回觅水记》《柳耆卿记》《孔淑芳记》《李亚仙记》《陶公还金述注解》《合同记》12种,这组小说的前后所著录的均为笔记、杂记之类。这组12种小说,有的很可能是话本,如《绿珠记》可能是《绿珠坠楼记》,《柳耆卿记》可能是《柳耆卿玩江楼记》,均见于何大抡本《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一○下栏中;也有的现在已经佚失,如《贾岛破风诗》《萧回觅水记》《郭大舍人记》《陶公还金述注解》等,没法确认究竟是话本小说还是文言小说;也有的在《宝文堂书目》“子杂类”中有相似名称的不同著录,如既著录有《红莲记》又著录有《五戒禅师私红莲》,既著录有《合同记》又著录有《合同文字记》,不知是重复著录还是确属不同的小说。
像《杜丽娘记》《孔淑芳记》,既有见于《稗家粹编》中的同名文言小说,又有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存世,笔者认为即使不考虑《杜丽娘记》和《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具体产生时间这一因素,《宝文堂书目》中所著录的也应当是见于《稗家粹编》中的文言小说,而不是话本。这是因为:(一)《宝文堂书目》之著录本来就如上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言“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毫无体例可言,因而很难找出著录规则来,不能因为这一组中有一些可以确定为话本,就认为这一组著录的全部是话本;(二)《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书不晚于嘉靖三十九年,而《宝文堂书目》编成应当在嘉靖三十九年之后,《稗家粹编》则刊刻于万历二十二年,中间只有三十四年的时间差,没有理由说两书中名称完全相同的小说不是同一种小说;(三)如果《宝文堂书目》中所著录的《杜丽娘记》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那么为何不著录为《慕色还魂记》或《还魂记》之类,而要著录为与文言小说同一名称的《杜丽娘记》呢?同样,如果《孔淑芳记》是话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那也应当著录为《双鱼扇坠传》或《孔淑芳传》才对,没有理由著录成与文言小说同名的《孔淑芳记》;(四)谭正璧、胡士莹、徐朔方等前辈学者之所以认定何大抡本《重刻增补燕居笔记》中的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即是《宝文堂书目》中所著录的《杜丽娘记》,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看到过也根本不知道胡文焕所刊刻的《稗家粹编》中收录了与《宝文堂书目》中所著录的同名小说《杜丽娘记》,如果他们看到或知道有这一小说,相信他们的结论也会随之而改变;(五)更重要的一点是,由唐宋元明时期包括传奇体、笔记体在内的文言短篇小说改编为话本或拟话本小说的例子在在有之,但从话本或拟话本小说反向改编为带有文言色彩的短篇小说的情况,在古代小说史中似乎没有出现过。因此,由尽管文言色彩已经不是很浓、但仍被《稗家粹编》作为文言小说收录的《杜丽娘记》改编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正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般发展状况。而认为先有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然后才改编为文言小说《杜丽娘记》的观点,是违背了古代小说发展的一般状况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向志柱发现《稗家粹编》之前近二十年,在根本不知道存在有文言小说《杜丽娘记》的情况下,刘辉就曾经敏锐地指出:“我们所以判断《杜丽娘慕色还魂》,绝不是《宝文堂书目》中著录的《杜丽娘记》,不仅在于篇名有异,主要因为这篇话本的文字风格与明嘉靖以前刊刻的话本迥然不同。以《清平山堂话本》所收各篇为例,它们的文字古朴,而不失其流畅,俚俗中而又露出生动。《杜丽娘慕色还魂》则平庸无奇,缺乏魅力,一见而知其为明末文人之作。”㊼而经过向志柱对汤显祖《牡丹亭》与文言小说《杜丽娘记》、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在文本方面的进一步比较研究,明确认定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是在文言小说《杜丽娘记》和戏曲《牡丹亭》双重影响下的产物㊽。汤显祖的《牡丹亭》创作于万历二十六年,在随后的几年里即风行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如此传播氛围里,原来并不引人注目的小说《杜丽娘记》,被人改编成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在改编过程中,还加入了戏曲《牡丹亭》中《惊梦》《寻梦》《闹殇》等出中的一些情节,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面貌,这应当是当时的实际情形,也是我们作出判断的基础。
结 语
以上几个方面,本文论证了汤显祖创作于万历二十六年的戏曲《牡丹亭》的蓝本,不可能是晚明万历后期才出现的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而应当是不晚于嘉靖三十九年的《宝文堂书目》所著录、早于《牡丹亭》问世四年而在万历二十二年已刊刻的《稗家粹编》所收录的文言小说《杜丽娘记》。这样的结论应当是可靠的。
杜丽娘还魂的故事,最初为文言短篇小说《杜丽娘记》所记载,它启发了汤显祖创作戏曲《牡丹亭》,又在两者的共同影响下,产生了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这样由小说—戏曲—小说的在题材内容方面双向交融,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而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写照。徐朔方说:“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的历史。它的特点之一是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㊾在《牡丹亭》的蓝本问题上,不少学者曾经出现过失误,如早先的学者曾将《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杜丽娘记》与出自《重刻增补燕居笔记》中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误判为同一种话本小说;而在文言小说《杜丽娘记》的文本发现后,仍然有人坚持《牡丹亭》的蓝本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而不是文言小说《杜丽娘记》。除了因材料不足而使研究受到局限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在思想观念方面,还没有意识到小说和戏曲之间可能存在着异常复杂的关系。
正确把握《牡丹亭》的蓝本来源,理清楚戏曲《牡丹亭》与文言小说《杜丽娘记》、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三者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汤显祖在蓝本的基础上创作《牡丹亭》的独特匠心,正确评估《牡丹亭》的艺术价值和在戏曲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之间同生共长、彼此依托的成长发展的历史。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137页。
②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3—84页。
③ 谭正璧:《传奇〈牡丹亭〉和话本〈杜丽娘记〉》,《光明日报》1958年4月27日;《汤显祖戏剧本事的历史探溯》,《戏剧研究》1960年第1期。
④⑮ 姜志雄:《一个有关牡丹亭传奇的话本》,《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6期。
⑤ 参见徐锦玲:《〈牡丹亭〉蓝本综论》,《北方论丛》2004年第4期。
⑥㊼ 刘辉:《题材内容的单向吸收与双向交融——中国小说与戏曲比较研究之二》,《艺术百家》1988年第3期。
⑦㉚㊽ 向志柱:《〈牡丹亭〉蓝本问题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⑧ 相关的批评论文有:伏涤修《〈牡丹亭〉蓝本辨疑——兼与向志柱先生商榷》(《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陈国军《新发现传奇小说〈杜丽娘传〉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3期),黄义枢、刘水云《从新见材料〈杜丽娘传〉看〈牡丹亭〉的蓝本问题——兼与向志柱先生商榷》(《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刘洪强《传奇〈牡丹亭〉的蓝本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2期)等。
⑨ 张正学:《〈牡丹亭〉“蓝本”新辨》,《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⑩ 陈旭东:《明代建阳刻书家余彰德、余泗泉即同一人考》,《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
⑪ 陈国军:《余象斗生平事迹考补》,《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2期。余泗泉与余象斗之亲属关系,若据清人余振豪等修、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之《书林余氏重修宗谱》,则余彰德为余泗泉之父、余泗泉为余象斗之侄,显误。前者陈旭东文中已作改正,后者陈国军文已作改正。
⑫ 肖东发:《建阳余氏考略(中)》,《文献》1984年第4期。
⑬⑯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78页,第779页。
⑭ 何长江:《〈燕居笔记〉余公仁小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
⑰ 何大抡这两种著作的收集者是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2级本科生刘静楠,本论文第一部分的写作吸收了她所收集的一部分材料。该同学于2016年春夏学期在笔者的指导下写作以“试析汤显祖《牡丹亭》蓝本问题”为选题的毕业论文,该论文认为《杜丽娘记》与《杜丽娘慕色还魂》均有受《牡丹亭》影响的痕迹,因此均有晚出于《牡丹亭》的可能,并揣测《牡丹亭》可能别有蓝本。
⑱ 《(乾隆)建昌府志》卷四四《人物传八》,《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830号第5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9—2010页;《(康熙)广昌县志》卷四《名贤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16号第2册,第356—359页。
⑲ 《(康熙)丰城县志》卷一一《人物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49号第4册,第1410—1411页。
⑳ 如魏同贤为《古本小说集成》所收录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所作的《前言》中称“何大抡生平无考,仅知其为杭州人”。
㉑ 《(乾隆)永福县志》卷八《人物传》,《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84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16页。
㉒ 《(康熙)抚州府志》卷一七《人物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27号第4册,第1641—1645页。
㉓ 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全编》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5页。
㉔㉙ 何大抡编:《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第2、10页。
㉕ 孔平仲等:《清江三孔集》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1页。
㉖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7页。
㉗ 邵宝:《容春堂集》前集卷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2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775页。
㉘ 蒋薰:《留素堂诗删》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1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㉛㉜ 胡文焕编,向志柱点校:《稗家粹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第109—110页。
㉝ 石昌渝校点:《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㉞ 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第3页。
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250册,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408页。
㊱ 向志柱认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在《幽怪传疑》和《孔淑芳记》的框架上,对《牡丹灯记》和《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等进行因袭和改写而拼凑成文。参见向志柱:《〈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5—118页。
㊲ 卓发之:《漉篱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页。
㊳ 陈国军:《新发现传奇小说〈杜丽娘传〉考论》;黄义枢、刘水云:《从新见材料〈杜丽娘传〉看〈牡丹亭〉的蓝本问题——兼与向志柱先生商榷》。
㊴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七,史部目录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44页。
㊵㊶㊷ 《宝文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第55、134页,第55、71、88页。
㊸㊺㊻ 张剑、王义印:《〈宝文堂书目〉作者晁瑮、晁东吴行年考》,《文史》2007年第3辑。
㊹ 柴奇:《黼庵遗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页。
㊾ 徐朔方:《我和小说戏曲》,《徐朔方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