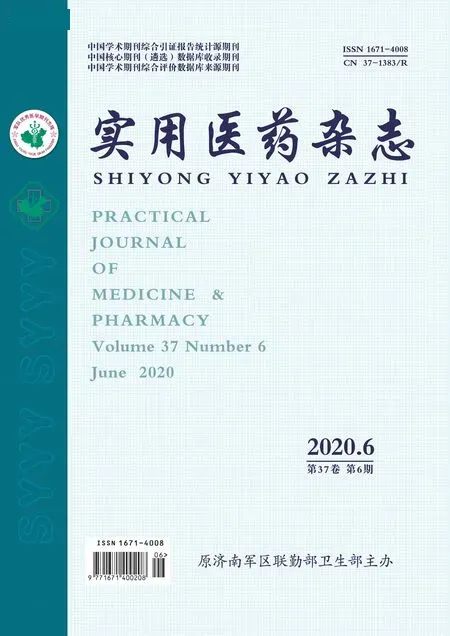P物质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刘 莎,许丛丛,潘信信,毕晓东
慢性荨麻疹(chronic urticaria,CU)是一种常见的反复发作的皮肤过敏性疾病,以瘙痒和一过性风团为主要症状,每周发作≥2次,病程持续≥6周。慢性荨麻疹可分为慢性自发性荨麻疹(chronic spontaneous urticaria,CSU)和慢性可诱导性荨麻疹(chronic inducible urticaria,CIndU)[1]。 后者的诱因包括机械刺激、寒冷、日光、压力及运动等。临床上以CSU最为常见,占CU的90%以上,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全年均可发病[2]。CSU的特征在于病变自然发生,大多数病例没有明显外因,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CSU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抗IgE自身抗体、Th1/Th2细胞因子失衡、补体活化、嗜碱性粒细胞与肥大细胞的分布异常、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个方面[1]。
神经肽是神经递质、激素或旁分泌因子的细胞外信使家族,多数为小分子肽,存储在囊泡中并且在钙离子内流时从周围神经末梢释放,通过与细胞膜上的G蛋白偶联受体结合发挥作用。速激肽是一类神经肽,参与许多的生物过程,并通过与G蛋白偶联的速激肽受体结合起作用,称为神经激肽(NK)-1,NK-2和NK-3受体,具有不同的亲缘关系。在速激肽家族的成员中,P物质(substance P,SP)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体内的十一氨基酸肽,由特定感觉神经末梢分泌,对各种刺激(如白三烯,前列腺素和组胺)发生反应,也可以由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树突细胞分泌[3,4],可与神经激肽(NK)1-3受体结合发挥生物学效应,对NK-1受体具有更高的亲和力。这种神经肽可调节许多病理生理过程,如免疫调节、炎症、疼痛、瘙痒等[5-8],在皮肤神经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被认为是引起皮肤神经源性瘙痒的重要炎症介质。
1 SP在肥大细胞介导的皮肤炎症中的作用
人体皮肤肥大细胞与感觉神经末梢密切相关,后者在受到物理、化学刺激和应激反应时可释放神经肽[9]。这些神经肽(包括SP)与肥大细胞的活化和脱颗粒有关。反过来,许多肥大细胞产物,包括组胺和类胰蛋白酶可以激活感觉神经,从而支持在肥大细胞引起的皮肤炎症反应中肥大细胞和感觉神经之间的双向串扰作用[10]。 Toyoda 等[11]证实,在特应性皮炎患者皮肤肥大细胞的特定颗粒内存在SP,从而首次证明了肥大细胞自身就能分泌 SP,SP又反过来作用于肥大细胞和血管,从而促使SP不断释放,形成病症的持续状态。
2 SP拮抗剂在皮肤反应中的作用
已有病例报道[12]证明,SP拮抗剂在药物性瘙痒、副肿瘤性瘙痒、结节性痒疹、皮肤T细胞淋巴瘤等疾病中具有显著止痒效果。
早在1991年,Wallengren就指出 P物质拮抗剂可抑制Ⅰ型和Ⅳ型皮肤超敏反应[13]。但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Wallengren等评估了阿瑞吡坦 (NK-1受体阻断剂)在Ⅰ型和Ⅳ型皮肤反应的作用[14],结果表明,局部应用的阿瑞吡坦可以渗透皮肤,但不抑制斑贴试验和点刺试验反应或相关性瘙痒。
3 肥大细胞上的SP受体
除了高亲和力的 IgE受体(FcεRI),肥大细胞还表达许多G蛋白偶联受体。作为SP的内源性受体,NK-1受体在肥大细胞上表达,并在小鼠的IgE和非IgE介导的免疫反应中起作用。尽管NK-1受体拮抗剂在小鼠实验中是过敏和炎症反应的有效调节剂,但尚未证明在人体中具有明显的抗过敏和(或)抗炎作用,提示存在其他未知的信号通路[15,16]。
有证据表明,SP可以介导一些炎症反应,并通过除了NK-1受体之外的Mas相关G蛋白偶联受体诱导瘙痒[16]。另有研究发现,SP及假过敏反应相关物质可激活肥大细胞表达一种新的人类Mas相关G蛋白偶联受体(MRGPRX2),尽管这已在人类LAD2 肥大细胞系中出现[17]。
4 SP激活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
皮内注射SP后可立即引起剂量依赖性风团和瘙痒反应并伴有嗜碱性粒细胞浸润[18-21]。上述两种病理过程可能与这些反应有关:直接作用于微循环,引起血管舒张和血浆外渗;SP刺激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组胺[19,20]。
现有证据[22]表明,SP可以在体外诱导肥大细胞脱颗粒,并可以增加肥大细胞对触发信号的反应性[23-25]。SP介导人体肥大细胞产生细胞因子的结果尚存在争议,可能与不同研究实验条件和肥大细胞不同亚型有关[26]。
Gibbs等[27]发现人体皮肤肥大细胞在受到IgE依赖性激活和SP、干细胞因子和复合物48/80等刺激后能够快速分泌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IL-8)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然而,与人体其他器官肥大细胞相比,在同等实验条件下,人体皮肤肥大细胞不能分泌IL-4,IL-5或IL-13。
Okayama 等的研究显示[28],使用原位杂交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IL-4,IL-5和TNF-α的mRNA是通过人类皮肤肥大细胞的免疫激活诱导的,但仅有TNF-α的mRNA由SP选择性诱导。
另外,Guhl等[26]报道,SP 不会改变人类皮肤肥大细胞中细胞因子mRNA的表达。事实上,SP的刺激不会影响纯化的人皮肤肥大细胞中TNF-α或IL-8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皮肤肥大细胞似乎通过脱颗粒和组胺释放以选择性对SP起反应而不是诱导细胞因子产生。在SP刺激后,上清液中IL-6的浓度反而降低,而在mRNA水平未改变,提示转录后抑制机制的参与。
SP亦参与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和募集[29]。SP被证明是体外人嗜碱性粒细胞的有效促炎性因子,通过嗜碱性粒细胞上的NK-1受体以及磷酸二酯酶和磷酸肌醇-3激酶在下游信号通路中起作用[30]。
5 SP的血浆水平
Tedeschi等[31]通过酶免疫测定法评估了117例CSU患者、40例特应性体质者(20例患有过敏性鼻炎,20例患有过敏性哮喘)和24例正常受试者的血清SP水平。所有CSU患者分别进行体内和体外组胺释放因子检测、自体血清皮肤试验(ASST)和嗜碱性粒细胞组胺释放试验(BHR)。CSU患者[(221.94±17.28) pg/ml]与正常受试者[(290.29±41.36) pg/ml]之间的平均血清SP浓度无明显差异。此外,阳性患者和ASST阴性或BHR阴性患者的血清SP水平无差异。特应性体质者组平均血清SP水平明显高于CSU患者。
笔者认为,大多数CSU患者血清SP水平并未升高似乎否定了SP作为CSU中组胺释放因子的重要作用,但并未完全排除。例如,SP血清水平未升高可能与皮肤释放量较低、快速失活或者与肥大细胞受体迅速结合有关。然而,Tedeschi[31]的研究表明,在 75例中有 3例血清 SP非常高 (910~1100 pg/ml),其ASST阳性、BHR阴性,结果提示SP在通常的CUS患者中并不是重要的组胺释放因子,而仅仅在个别病例中主动参与CSU的发病机制。
为了评估 CSU 患者血清 SP浓度,Metz等[22]进行了另一项研究,他收集了30例健康受试者,118例CSU患者和20例冷荨麻疹患者的样本。与健康组[(105±28) pg/ml]相比,在 CSU 患者[(491±24) pg/ml]中SP水平明显升高。冷荨麻疹患者也显示出SP水平升高[(280.3±24) pg/ml)],但明显低于 CSU 患者。这些结果与Tedeschi等[31]之前报道的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血液处理和储存方式的不同影响SP的降解,也可能是其他方法学因素或选择CSU 患者标准的差异,例如疾病严重程度[22,29]。 此外,Metz 等[22]通过荨麻疹活动评分(UAS7)证明 SP浓度与疾病活动之间直接相关性。在4例患有严重CSU的患者中发现SP水平明显升高,在健康受试者和患有轻度CSU的患者中SP水平并未升高。SP水平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具体取决于存在或不存在特定变量,即应激、焦虑、抑郁,这些都是CSU的潜在病因[22]。
王庆毅等[32]发现CSU患者血清SP水平均高于正常人群,提示SP可能参与了CSU的发生。王冬梅等[33]研究表明80例肝郁血虚型慢性荨麻疹患者SP评分均高于正常组,提示SP不仅参与了慢性荨麻疹的发病,而且可能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有关。Zheng等[29]的一项研究证实了CSU患者SP血清水平升高。15例CSU患者中的血浆SP水平比15例对照受试者的血浆水平高约3.5倍。同一研究表明,与对照者相比,来自CSU患者的血液中表达SP和NK-1受体的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显著升高。在CSU患者的外周血中观察到嗜碱性粒细胞的绝对数量与SP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另一项研究[34]评估了H1-抗组胺药对慢性荨麻疹患者神经肽(包括SP)血清水平的影响。22例患者口服西替利嗪10 mg/d和16例患者口服氯雷他定10 mg/d共治疗7 d。治疗前和治疗后SP水平无明显差异,但在抗组胺药治疗后,观察到对其他神经肽有显著影响,例如干细胞因子,神经肽Y,血管活性肠肽,神经生长因子的减少或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的增加。
6 SP引起的皮肤反应及在组胺释放中的作用
在一些患者中,天然食物成分引起的假性过敏反应与慢性荨麻疹的诱发和维持有关。一项研究[35]纳入了33例患有慢性荨麻疹和对食物假性过敏反应的患者,并对这些患者的皮肤活检标本进行体外肥大细胞组胺释放水平测定。与对照受试者相比,患者组发现总组胺水平和自发性组胺的释放量显著升高。体外组胺释放不是由番茄提取物本身引起的,而是通过番茄馏分与SP和补体5a(C5a)的组合增强(无抗-IgE参与),强调了IgE非依赖性机制参与假过敏反应。
与非特应性对照者相比[36],慢性荨麻疹患者对皮内注射神经肽(例如SP和血管活性肠肽)表现出增强的反应。SP诱导的风团和最强红斑效应可被H1阻滞剂抑制。Borici-Mazi等[37]对9例CSU患者和9例迟发性压力性荨麻疹患者及9例健康成人皮内注射SP后,进行皮肤反应的评估。CSU患者与对照组相比,风团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最强红斑效应比健康人更强烈、持续时间更长。迟发性压力性荨麻疹患者与其他两组相比,SP诱导的风团和最强红斑效应的幅度中等。Fujisawa等[38]研究表明,鉴于SP通过MRGPRX2激活人肥大细胞,与健康受试者相比,MRGPRX2在严重慢性荨麻疹患者皮肤表达上调。与肺源性培养的肥大细胞不同,皮肤来源的肥大细胞在细胞表面上表达MRGPRX2。SP引起的皮肤源性肥大细胞的组胺释放并不依赖传统的SP受体NK-1。另外,在MRGPRX2沉默的肥大细胞中,皮肤源性肥大细胞SP诱导的脱颗粒和前列腺素D2的产生显著减少。在人类皮肤源性肥大细胞中,MRGPRX2不仅是SP而且也是嗜酸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碱性蛋白诱导组胺释放的受体。郑文娇等[29]探讨了CSU患者中嗜碱性粒细胞和SP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了SP引起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的能力。加入SP后,可诱导CSU患者嗜碱性粒细胞高达41.2%的净组胺释放率,SP可能在一部分CSU患者中充当组胺释放因子。
综上所述,多项研究已证实SP可引发皮肤瘙痒和风团反应,诱导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以及增强肥大细胞对各种刺激的反应性,提示SP参与了慢性荨麻疹的发病过程。此外,与对照组相比,CSU组患者血清SP水平升高,SP阳性的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亦升高,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明显相关。Fujisawa[38]的研究还表明了在严重慢性荨麻疹患者皮肤中MRGPRX2受体表达水平的上调。
SP可能在假性过敏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并且在一部分CSU患者中充当组胺释放因子。SP通过MRGPRX2等受体激活人皮肤肥大细胞这一发现,可帮助进一步理解CSU及其他肥大细胞介导的皮肤疾病的发病机制,从而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尽管如此,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SP在CSU发病机制中的具体作用以及能否成为新的有效治疗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