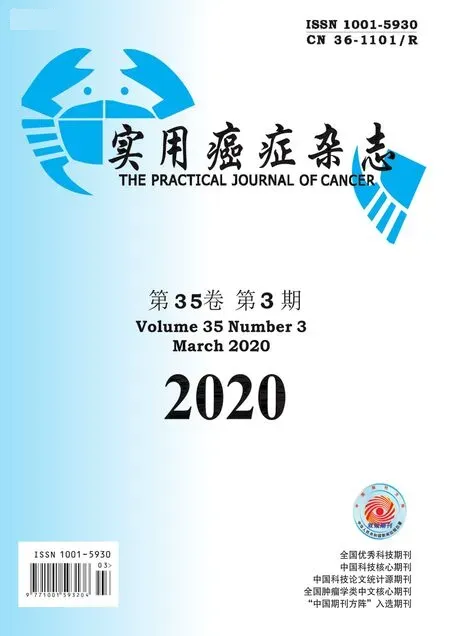CPG岛甲基化表型结直肠癌治疗进展
张晓飞 于 剑 曹秋婷 姜 媛 邹 玲综述 韩竞春审校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最常见的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恶性消化道肿瘤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有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我国的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1]。表观遗传改变是指基因表达的遗传性状改变而同时不伴有DNA序列的变化,导致转录基因沉默或者DNA修复基因和肿瘤抑制基因失活对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2]。近30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报道指出表观遗传改变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核小体定位,染色质环,小非编码RNA等在癌症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
1 CPG岛甲基化表型(CPG island methylatorphenotype,CIMP)
近年来,表观遗传改变中的DNA甲基化修饰即CIMP被广泛的研究,CIMP是DNA启动子区存在富含CPG位点的CPG岛并表现出1种高度甲基化的形式,通过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DNMT)从s-腺苷甲硫氨酸(SAM)转移催化导致某些区域DNA构象变化,从而影响了蛋白质与DNA的相互作用[4]。当甲基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区域DNA结构收缩,螺旋加深,使许多蛋白质因子赖以结合的原件缩入大沟而不利于转录的起始,从而导致转录基因沉默或者DNA修复基因和肿瘤抑制基因失活,从而导致肿瘤的发生4。CIMP已经被认为是结直肠癌研究的重要方向[4]。
2 CIMP与结直肠癌
2006年美国的Weisenberger 研究小组推荐用1种新型的、简便的、敏感的、准确的CIMP标记基因(CACNA1G,IGF2,NEUROG,RUNX3,SOCS1)去区分CIMP阳性的结直肠肿瘤以来,国外的科学家们已经证实了CIMP在结直肠癌中和某些特定的临床病理学表型相关,比如女性性别,高龄,家族遗传史,右半结肠癌发病,黏液性细胞分化,特殊的前驱病变,吸烟,并且CIMP和许多分子表型紧密联系,如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igh),Tp53野生型,KRAS野生型,BRAF变异,PIK3CA变异以及 MLH1甲基化[5-7]。并且有最新的研究证据表明CIMP和高度的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等免疫激活反应有关9。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暗示CIMP作为1种潜在的表观遗传学预测标记物或预后生物标记物可能有助于结直肠癌患者的个体化精准治[8]。
3 CIMP与结直肠癌治疗
3.1 CIMP与单药化疗治疗
5-氟尿嘧啶(5-Fu)作为治疗结直肠癌最广泛应用的化疗药物通过抑制胸苷酸合成酶从而影响DNA的合成,在2011年西班牙和韩国两个独立的针对Ⅱ~Ⅲ期的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对CIMP阳性患者的治疗疗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9]。西班牙研究团队通过对302例Ⅱ~Ⅲ期结直肠癌患者的研究发现接受5-Fu为基础单药化疗的CIMP阳性患者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劣于未给与化疗的患者(log-rank=0.02),对于所有CIMP阳性患者不能从术后给与5-Fu为基础的单药化疗中受益(hazard rate,HR=0.8;95% confidence interval,Cl=0.3~2.0)[13]。而来自于韩国的研究团队通过对245例Ⅱ~Ⅲ期结直肠癌患者的研究认为接受5-Fu为基础术后单药化疗的CIMP阳性的患者(n=17;3年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100%)无复发生存期(RFS)显著优于仅仅手术治疗的CIMP阳性的患者(n=7;3年RFS:71.4%)(P=0.022),该研究表明CIMP阳性结直肠癌患者可以从术后给与5-Fu为基础的单药化疗中受益[14]。另有研究将Ⅱ~Ⅲ期的CIMP结直肠癌患者根据微卫星不稳定、BRAF及KRAS分子表型的不同进行更细致的分组发现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le,MSS)、KRAS野生型、BRAF变异及CIMP阳性这组患者具有最差的预后(log rankP<0.0001),并且仅仅MSS、KRAS野生型、BRAF野生型及CIMP阴性这组患者可以从术后给与5-Fu为基础的化疗中显著受益(HR=2.06,95%CI=1.24~3.44,P=0.005)[10]。5-Fu作为结直肠癌化疗的基石单独作用于CIMP结直肠癌患者疗效并不确切,在国内外临床结直肠肿瘤治疗仍然有争议。
3.2 CIMP与联合化疗治疗
新型细胞毒化学药物奥沙利铂与伊立替康的发现及联合5-Fu化疗的应用使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期提高了近一倍。FOLFIRI (5-Fu+亚叶酸钙+伊立替康)和FOLFOX (5-Fu+亚叶酸钙+奥沙利铂)是两种重要的细胞毒性化学剂在临床中联合应用的化疗方案。美国的科学家已经证实对于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一线治疗给予FOLFIRI化疗方案二线给予FOLFOX化疗方案与反向顺序给药的临床疗效相同[11]。日本学者通过对125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使用化疗药物的预后评价研究发现一线给予含有伊立替康(CpT-11)的化疗方案二线给予FOLFOX化疗方案比反向顺序给药的化疗方案可以显著的使CIMP阳性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受益,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延长了8.6个月(mPFS=15.2月vs 6.6月,P=0.043)。在总生存期(OS)方面,前者也优于后者(mOS=20.8月vs 12.8月),中位总生存期延长了8个月,同时客观反应率(ORR)及疾病控制率(DCR)也有相似的结果[12]。以上的临床试验研究表明CIMP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相比CIMP阴性结直肠癌患者更能够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CpT-11受益。
美国的Grady WM教授肿瘤研究团队通过对615例Ⅲ期的结直肠腺癌术后使用包含伊立替康(CpT-11)方案化疗的患者的疗效研究显示给与含有CpT-11方案化疗时,CIMP阳性患者有增加OS的趋势(HR=0.62;95%Cl:0.37~1.05;P=0.07),而CIMP阴性患者并没有该趋势(HR=1.38;95%Cl:1.00~1.89;P=0.049),尤其对于CIMP阳性并且错配修复基因完整(MMR-intact)的患者更能够显著的使其受益(P=0.01)[13]。
美国的Grady WM教授肿瘤研究团队通过对293例Ⅱ~Ⅲ期的结直肠腺癌术后使用mFOLFOX6(5-Fu+亚叶酸钙+奥沙利铂)或XEL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方案化疗的患者的疗效评估发现CIMP阳性和CIMP阴性患者的总生存期(OS)没有显著差异(P=0.55),这项研究表明含有奥沙利铂的化疗方案不能使CIMP阳性或阴性的结直肠癌患者受益[14]。
法国的肿瘤学专家调查了1867例大样本Ⅲ期结直肠癌术后应用FOLFOX4±cetuximab方案化疗患者的CIMP情况发现CIMP阳性的患者的总生存期(OS,HR=1.46;95%CI:1.02~1.94;P=0.04)和复发后生存期(survival after recurrence,SAR;HR=1.76;95%CI:1.20~2.56;P<0.0004)显著缩短,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HR=1.15;95%CI:0.86~1.54;P=0.34)未见显著改变,而对于CIMP阳性患者中应用cetuximab这部分患者并未显著地对OS、SAR及DFS的统计产生不利影响[15]。这项研究表明CIMP阳性的患者术后应用FOLFOX方案化疗OS和SAR有显著劣势。
3.3 CIMP与靶向药物治疗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抑制剂西妥昔单抗(cetuximab)是特异性针对EGFR过度表达的IgG1单克隆抗体在转移性结直肠癌中有广泛的应用。日本的临床肿瘤专家通过对125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使用cetuximab药物的分析研究发现对于给与cetuximab抗EGFR单抗药物的KRAS基因野生型CIMP阳性患者相较于CIMP阴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有缩短的趋势(mPFS,2.1月vs.5.1月,P=0.11)并且药物反应率(response rate,RR)也有降低的趋势(20.0 vs.24.4%,P=0.90)[12]。尽管该项研究并未展现出统计学意义,但似乎提示CIMP表型可能是预测抗EGFR单抗药物疗效的生物学标记物。
同样来自日本科学家的研究使用更先进的Infinium HumanMethylation450 BeadChIP全基因组DNA甲基化分析技术区分了两组共计97例使用EGFR抑制剂的KRAS基因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DNA甲基化情况,分为高度甲基化组(HMCC)和低度甲基化组(LMCC),该研究分析认为无论是PFS(HR=0.22;95%CI,0.13~0.37;P<0.001)还是OS(HR=0.24;95%CI,0.11~0.53;P<0.001)HMCC患者显著劣于LMCC[16]。这项研究表明对于使用EGFR抑制剂的KRAS基因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CIMP阳性表型是疗效的负性指标。
3.4 CIMP与DNA甲基化抑制剂
两种最广泛被研究的DNA甲基化抑制剂地西他滨(Decitabin)和阿扎胞苷(Azacitidine)通过在DNA复制过程中取代甲基化的胞嘧啶靶点与DNA胞嘧啶甲基化转移酶(DNMTs)形成不可逆的复合物,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导致该酶的耗尽及胞嘧啶甲基化被动缺失,从而导致DNA低甲基化和抑癌基因沉默再表达,恢复增殖控制和凋亡敏感性,使癌变过程失活[17]。
波兰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了DNA甲基化抑制剂通过长时间持续地增加结直肠癌细胞HCT116和DLD-1对拓扑异构酶抑制剂敏感性,减少肿瘤细胞的活力及集落形成,并增加程序化细胞死亡,而并不增加明显的毒性[18]。
美国的肿瘤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应用DNA甲基化抑制剂Azacitidine表观遗传治疗可以在体外细胞(in-vitro)水平增加结直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CpT-11的敏感性,同时在体内细胞(in-vivo)水平联合使用CpT-11对于异体移植于免疫缺陷的小鼠的结直肠肿瘤具有协同增效的效果[19]。
美国的临床肿瘤学家通过20例小样本的KRAS基因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接受序贯decitabin和帕尼单抗(panitumumab)的Ⅰ/Ⅱ期临床试验证实患者对DNA甲基化抑制剂与抗EGFR单抗联合应用具有很好的耐受性,其中有2例先前使用过西妥昔单抗的患者出现了部分缓解(PR),有10例患者是稳定(SD)[20],尽管我们看到了一些成绩,但进一步的疗效需要更大样本的评估。
美国的肿瘤内科专家通过26例小样本的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接受Azacitidine和 CAPOX的Ⅰ/Ⅱ期临床试验证明CIMP阳性的患者对联合用药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且高度的疾病稳定率(SD),然而OS和PFS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改善[21]。
尽管在细胞水平DNA甲基化抑制剂与拓扑异构酶以自己的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并有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BLM蛋白的乙酰化对DNA甲基化及DNA损伤起重要调节作用[22],但在临床试验中DNA甲基化抑制剂对于CIMP阳性结直肠癌患者的疗效并不是十分明确。
3.5 CIMP与其他肿瘤内科治疗
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是1种新型抗微管药物,其干扰微管再排列,导致有丝分裂停止,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有报道称给与15例CIMP阳性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的临床试验发现紫衫类药物对于CIMP阳性结直肠癌患者并无疗效[23]。
一项针对评估160例CIMP阳性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的临床研究表明尽管CIMP表型与放疗后肿瘤退缩无显著相关(P=0.26),但21例(13%)CIMP阳性直肠癌壁患者相对CIMP阴性患者与壁外血管侵犯(EMVI)显著相关(P=0.028),而EMVI与不良生存率显著相关(P<0.001)[24]。这种预后意义是治疗前组织学检查所不易检测到的。
尽管CIMP的临床检查目前还没有大规培展开并且检测手段具有不均一性[25],但越来越受到各国肿瘤学者的重视[26]。通过本文了解了CIMP表型与结直肠癌内科治疗的最新进展。我们发现CIMP阳性表型的结直肠癌患者能够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CpT-11受益,而对于抗EGFR单抗靶向治疗具有负性疗效的提示,同时在DNA甲基化抑制剂及其他肿瘤内科治疗领域似乎也有发展的潜力。这些前沿的研究为结直肠癌精准治疗提供了更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