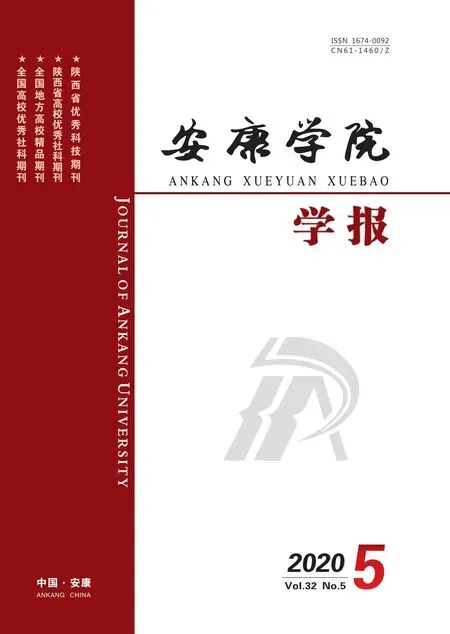以“正名”正名
——对孔子“正名”概念的一个辨析
祁斌斌
(1.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2.大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8)
一、孔子“正名”观念的两义性使用
“正名”概念的歧义性使用指的是“正”该作名词来理解还是作动词来理解,即“正名”是一个名词结构还是一个动词结构?可以把这一问题具体化:对孔子来说,“正名”是否只是单纯在动词意义下使用,或是可以、甚至必须在名词意义下来理解和使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那些周代礼乐制度尚未遭到破坏的国家来说,是否需要在动词意义上使用“正名”;对于那些周代礼乐制度受到破坏的国家来说,将要依据什么来“正名”(动词)?依据《论语》,“正名”既在动词下使用同时还必须在名词下使用,即“正名”(动宾结构)的目的是要恢复“正名”(名词结构)。如果这两种词性意义下的“正名”情况在春秋战国时代都存在,“正名”首先应该在名词结构下使用。但在一些学术著作中却首先将“正名”作为动词结构来使用。这样的使用,我们认为会造成动词结构的“正名”的真正意义不能显示出来,即“正名”的名词意义被遮蔽,从而失去名词结构“正名”的初衷,进而使“正名”(动词结构)失去方向,可能会混淆《论语》中“正名”的目的在于恢复周礼,即“正名”(名词结构)这一初衷。在《论语》中,“正名”(动词结构)的最终目的即是要恢复“正名”(名词结构)。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对《论语》中“正名”的两种词性结构所显示的不同作用和目的做简单辨析。
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这样使用和理解“正名”一词,“为政以‘正名’为本,即是说划定‘权分’为本”[1]。这句引文是对《论语·子路》中“子路问政”那段的解释,从中可知劳思光把“名”理解为“权分”或“分”,把“正名”当作动词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史》认为:“为了达到复周礼的政治目的,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举措,这就是正名。周代的礼乐制度对这种等级有很严格的规定,强调君臣、上下、长幼之‘位’,这种位代表着与各种等级相应的身份、权力、财产,要弄清楚人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就必须‘辨位’,以使每个人都居于自己之位,不乱来。当时很多人并不自觉恪守自己之位,老是僭越,做高出自己等级之位的事情,享受高出自己等级之位的待遇。孔子提出的正名的主张,就是要克服这种现象,让人们安于自己之位。”[2]从中可以看出,编者将孔子的“正名”理解为动词。在春秋时代周礼遭到破坏,恢复周礼就是要“辨位”、要正名,这种理解往往会使人忽视对动词“正名”的名词结构进行理解。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或著作将“正名”之“正”理解为动词。这样理解和使用,往往会使人忽视或遗忘动词语法“正名”背后的名词语法“正名”。我们来看看孔子对“正名”概念的使用。《论语》中记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187
孔子和子路这段对话是以卫国太子蒯聩和自己儿子辄的王位之争为背景,因此涉及名和位是否相称的问题。面对王位之争,子路实际是在问孔子卫国政治问题解决的方法,孔子回答以“正名”为先,此“正名”当作名词。通过后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可知,文中的“名”当为“正名”(名词),即礼乐制度,不然不能通过连锁反应到达礼乐。再者,孔子时期卫国的“名”或“礼”还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 《颂》各得其所”[3]125。这表明卫国礼乐制度等“正名”没有受到很严重破坏,还在人的言行、风俗和政治中保存比较完好,不像鲁国政权已经旁落三家,“名”和“礼”已经受到破坏,所以孔子回答“必也正名”。“正名”在这里作名词,意思是遵循传统礼乐,即按照既有的周代礼乐制度等“名”来处理政治问题就可以了。所以子路问在为政的许多方法中以什么办法为先?这是针对卫国的政治情况发问的,孔子的回答也首先是针对卫国的政治情况,但对其他国家政治问题的解决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为在其他国家,“名”或“周礼”已经被破坏。无论是对“名”保存完好的国家还是对“名”受到破坏的国家而言,在孔子看来“正名”仍首先在名词上使用,因为这样理解和使用关乎“正名”的实质和目的问题。即使在动词上使用“正名”也是要恢复“正名”或“复礼”。因此面对春秋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的“正名”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子路认为在许多为政方法中似乎没有以“正名”作为执政方法的,对此表示怀疑,并认为孔子迂腐,根本没有当政者这样做过,即以“正名”为先,并且说“正名怎么去正”?这里应该把“正名”作为名词来用。孔子批评子路不知道“正名”作为为政方法之说,因此从反面阐明“正名”的意义。“名不正”即是“正名”不行,即“名”不自天子圣王出。“正名”不行,就会言行不合道、不合理,即言行不合“名”。言行不合“名”即言行不正,则事不能成。事不能成,则礼乐不能兴。从经文可知,“正名”不行于言行中,礼乐兴盛就没有可能。因此“正名”是礼乐兴盛的基本条件。“正名”承载着恢复礼乐的作用。当礼乐制度兴盛或恢复起来了,人们的言行自然合乎“名”了。所以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也,即是言合乎礼乐或合乎“正名”。因此经文中的“名”应该是作为名词的“正名”。礼乐不兴,自然是仁义不行天下,从而大施刑罚,刑罚也没有了根据。“正名”、仁义等不行于天下,老百姓的言行也自然失去了轨范。故而必须以“正名”正人们的言行举止,让其符合“名”。所以经文中的“正名”应该作为名词的“正名”来理解,它承载着恢复仁义礼乐的作用。
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把“正名”作为名词用的例子或类似的例子。例如,荀子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已焉。故析辞而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4]882。从引文中可以知道,荀子把“正名”理解为名词,认为它承载着恢复仁义礼乐的作用,甚至“正名”即代表仁义礼乐。王者制定的“名”为“正名”,即代表仁义礼乐,老百姓不能擅自析辞制名,以乱“正名”。所以“名”或“正名”必自圣王出;同时“名”自圣王出才是“正名”,此外则是非“正名”或“名不正”。显然,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把“正名”作名词的惯例,代表着仁义礼乐等周代道德制度。“是以圣人之治,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5]其中“正名”作名词理解,意思是“正名”行天下治,天下无事。韩非子说:“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6]韩非子用“名”来审核“言”与“事”,作为恢复事“理”的方式或方法。
通过对《论语》和春秋战国时期“正名”一词用法的分析,笔者认为“正名”应该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而不是只能作为动词来使用。
二、孔子的“正名”观念
(一)孔子的“正名”概念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孔子的“正名”概念必然含有仁义道德的意义;且“名”的制定者是圣王,圣王也必须有大德和职分才可以制名、定名。因此“名”本身就是“正”或“正的”,即合乎仁义的。《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7]34从中可知,无德或无位者不能作礼乐或制名定名;制作礼乐和“名”者必须是天子圣王。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3]253在孔子看来礼乐制度应由天子制定和产生,不应由天子以下的人来产生,因为天子有大德,且其位和名都受自于天,所以天子有“天命”而得天位和“正名”。“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8]可见正名是圣王取自天地的。
“正名”也必须表达道德和位置或职分的要求。不同的“名”既表达不同的道德义务和职分要求,也表达特定的位置和身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3]177君臣父子各有不同的名分和相对应的职责,因此应该恪守自己的名分和职责,不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然既不能成教于家更不能成教于国。只有修己于正名,才能成教于家成教于国。《中庸》说:“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必受命。”[7]22“名”必源于“天命”,必出于“天子”,因此孔子的“名”也是“正名”或“天命”之名。
孔子所谓的“名”可以体现在《诗》 《书》《礼》 《乐》 《易》 《春秋》等古代典籍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3]93孔子把《诗》 《书》和礼看作雅言。既为“雅言”,也就应该属于“正名”的范畴。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12他认为《诗》三百让人思之无邪纯朴,因此也是雅言、正名。陈壁生说:“在《论语》中,孔子谦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因为在孔子身处的时代,‘圣人’的系统本来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德位合一的。孔子有德无位,非王,所以不敢称圣。”[9]8孔子有德无位,不能制名定名,不敢作礼乐。所以他好学圣王和古代典籍。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9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3]86孔子好古笃信,敏求不作,默而述之。“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3]86孔子学习古代典籍,乐而不厌,习而传之,有德有言,诲人不倦。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268这段话是孔子学《诗》的一些体会,学而传之,教诲他人。
作为“名”的这些古代典籍都承载着先王之道。面对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王官失守的时代,孔子虽无王位但德为圣人,忧于天下无道,百姓荼毒,于是对古代的一些典籍进行了删削,削删六经以定名“正”事“正”言,以使王道、常法和正名得以续传下去。“同样道理,孔子之前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但是,六书非经。而孔子删述之,遂为六经,于是‘经’字之义,也确定为常道、常法。”[9]8-9通过删减《诗》《书》 《礼》 《乐》 《易》 《春秋》而使之转化为“六经”,“六经”就是孔子的“正名”,它们用以复周礼,用以承续王道,用以化成天下。
(二)“正名”由学以知之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3]299显然孔子把文武之道作为“常师”“常道”,即作为“正名”来学习,认为文武之道还在人、在习俗中,人应该学习弘扬它们。《论语》开篇也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2“传不习乎?”[3]3“学”应该是包括学习古代典籍即六经;学而“时习”才能有得,故传必须先习其所学,以使经中之道或“正名”学记于心、时习而时行精熟于心,合于物宜,从而达到惟精惟一和传道的目的。所以《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7]29这段经文应该可以概括孔子学习古代典籍的精神和态度。
为了强调学习“正名”,他反对不学习古代典籍而好自专自用的行为。他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7]34自专自用,不从古道,自起名号,擅自行为,因而我行我素,道不贯一,自然与道背驰,必然遗祸于身。古道多用名载于典籍书册,不学者道乃不贯、思想行为无依无凭,自然自专自用于己。他反对意、必、固、我,也是对自专自用的一种批评,其目的还在于强调学习古代典籍,以复常道、大法。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3]82这也许是对包括他在内的君子的要求吧!学文的目的在于复礼,在于正名。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3]111孔子笃信文武周公之道,认为那是“正名”,应该好好学习“志学”于仁,至死不变周道。
三、以“正名”正名
(一)孔子“正名”之为“正”名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3]256由此可知,孔子的“正名”代表着周礼或“天命”,古代典籍是“正名”的载体。因此在他看来“正名”所承载的是一种“常道”。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常道”“大道”式微了,出现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0]的局面。世与道互丧的局面出现,天下非一周礼能一统。“周礼”非执古不变的常道、常名,可道者多了,可名者也多了,天下方术纷纷俱出。所以《庄子》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为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11]言道“无乎不在”者也表达了,作者想用“道”一统天下。这也是孔子和儒家对“周礼”所持的理想态度。这“无乎不在”者也应该是“古之所谓道术”,即“常道”或“常名”,孔子也是这样来看待周礼的。面对春秋战国礼坏乐崩,术出多端,“常名”受损的局面,孔子仍旧坚持常道、天命,主张恢复周礼以反对其他道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32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重在言“利”,孔子反对言“利”。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4]45《论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3]88显然孔子主张仁义行天下。他对学习典籍而不急于求利近禄的行为表示赞赏。他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3]110他在学以求道和求利之间,是支持前者的。《论语》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3]174在食、兵和信之间,孔子既不看重兵,也不看重食,而注重信义。孔子也不言兵。《论语》中还记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3]231孔子不言兵,反对杀戮的不义之战,而言仁义,主张恢复周礼。《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3]188从中可知,孔子认为学稼是小人求利之事,故“君子不器”,有道而已,道文武周公之道;在上位者好礼、好义、好信,则民悦诚服,天下归矣。所以孔子主张学周礼、恢复周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3]171可见孔子“正名”观念有别于其他学派,以学周道复周礼为目的。
(二)“正名”之损益
“名”用来“正”言和事,言和事随时代和人物在变化。因此“名”也应该因时制宜地进行“损益”。《论语》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22显然孔子认为周礼能流芳百世,岂止十世,因为周礼兼于夏殷二代,郁郁乎文哉,故“正名”、周礼所表达和承载的是常道;但“正名”因为是用语言表达的,会固化为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事实,所以“正名”要正名,依据常道进行“损益”,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变化,才能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言行。其变化在于圣人因时因道对“正名”进行损益,即进行增补或简化,其道不变。
为了损益前代礼乐,以“正”“正名”,孔子先对先代典籍进行了修订。“孔门所授‘六艺’是六部经典。这些经典在孔子之前便存在了,孔子仅做了编订的工作。‘今文经’学派有学者认为,六经皆始于孔子,这种观点虽非完全正确,亦非完全无理。保存至今的六经(实为五经)经过孔子修订,但他的工作仅限于编辑和整理。孔子晚年的工作包括:1) 编订《诗》和《书》;2) 编辑《礼》和《乐》;3) 注释《易经》;4) 修订《春秋》。”[12]孔子因时因世因道对五经进行了删减,这也可以看作孔子对“正名”进行正名的行为,以合乎时宜,以贯周道于万世,立周道为“常道”。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3]128这表明,“法语之言”有其必然让人遵从之处,但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以合乎物宜;“巽与之言”切乎人情,但也应该演绎出其合乎常情的因素,以体现“常道”。总之,应该根据道对“正名”进行损益加减,权变处理,以使其有效地规范人的言行。这样的“正名”也使“道”进一步传播有了可能性。
(三)“正名”之定名分
《论语》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25季氏在自己家里看八佾之舞,孔子认为这是乱了名分,天子之舞不能在臣子家里演出。“三家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3]25“三家”在祭祀自己祖先后演奏天子之歌,孔子认为这也是越名分。所以他说:“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7]24,应当区分不同的名分和职位。胡适说:“所以《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小,却称‘公’。践土之会,明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叫来,《春秋》却说是‘天子狩于河阳’。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旧大书‘春王正月’。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13]《春秋》仍发挥着“周礼”既有的作用,用以端正君王的政治行为,调节君臣之间的关系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四)“正名”之教化作用
“正名”可以衡量和规范人的言行事为。“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171显然,孔子把礼即“正名”,作为衡量视、听、言、动的规范和标准。“正名”也就具有了衡量事物的规范和标准的意义及其价值引导的意义。“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3]21这表明《书》具有道德规范价值引导的作用。“六书”转化为“六经”后,“经”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轨范。人们通过“学”和“习”“六经”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规范。“六经”所承载的“正名”作用和意义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权威性。李澄源说:“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之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令不过你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经为明道之书,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故吾以为以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9]9可以说,六书成经后,经成为规范一切言、行、思、念等的普遍和绝对的规制体系,当然“正名”也成为规范一切的标准。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189可见孔子赋予经的意义和作用何其宏大。“不学《诗》,无以言。”[3]259“不学礼,无以立。”[3]259显然,经或经学成为言行立世的规范和大纲。
孔子曰:“如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9]9-10可见孔子深习六经,并且知道它们的利弊得失。在孔子看来,“六经”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伦理规范作用,这体现了六经的教化“正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