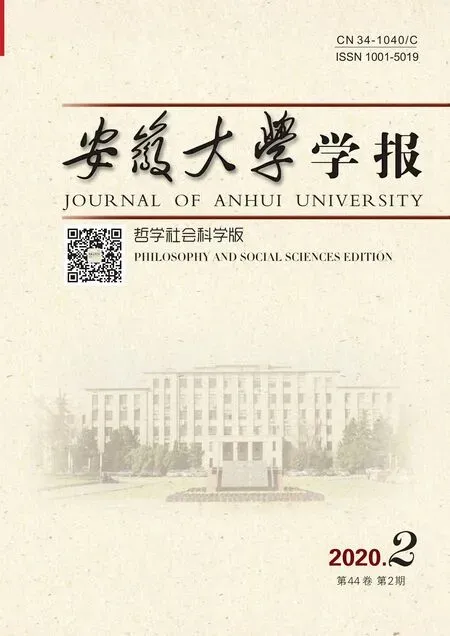康德论人性中的善恶共居
刘凤娟
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下文简称《宗教》)中提出了向善的禀赋和趋恶的倾向共居于人性中的思想,这是他集中地对基督教乃至传统哲学中人性观念进行改造的地方。康德的人性观念是其核心思想要素之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侧重从两个视角研究该论题,并且有越来越细致的研究趋势:第一,对定言命令式的第二个变形公式中的人性概念进行研究(1)Paul Guyer, Kant’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Reader’s Guide, London: Continuum Press, 2007; Oliver Sensen, Dignity and the Formula of Humanity,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ed. by Jens Timmerman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Jens Timmermann, Value without Regress: Kant’s Formula of Humanity Revisited,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4, no. 1(2006), pp. 69-93. 国内研究参见杨云飞《康德的人性公式探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4期;宫睿:《论科思嘉对康德人性公式的回溯论证》,《世界哲学》2014年第4期;王福玲:《康德哲学中的“人性公式”与尊严》,《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4期。;第二,对人性中的善恶本性进行专题性讨论,其中又以趋恶的倾向或根本恶为研究重点(2)Cf. Henry E. Alli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Propensity to Evil,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 36(2002), pp. 337-348; Seiriol Morgan, The Missing Formal Proof of Humanity’s Radical Evil in Kant’s Religio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114, no. 1(2005), pp. 63-114. 国内研究参见舒远招《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4期;白海霞:《康德论人性的善恶》,《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1期;胡学源:《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5期。。但学界目前的研究大多属于一种静态考察,而没有充分重视康德在该论题上呈现的动态的和历史性的维度。在康德这里,善恶两种属性不是在人性内部静止地对立着的,而是在全部人类历史进程中持续对抗,并辩证地达到统一的。这种动态的人性观是在康德先验逻辑的思维框架内展开的,并与他的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等具有相容性。而要洞悉这种动态人性观,人们就有必要搞清楚善恶两种属性在人性内部共居的方式。
本文的目标就是考察康德宗教哲学中向善的禀赋和趋恶的倾向在人性内部为何以及如何共居的问题,这是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和深入讨论的一个细节问题。对该问题的澄清有助于揭示康德动态视域下的人性发展观,并凸显其思想体系的融贯性。本文将以两个步骤展开论述,首先,基于《宗教》乃至《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下文简称《奠基》)等多个文本综合性地阐明向善的禀赋与趋恶的倾向的内涵;其次,详细分析这两种属性在人性中共居的方式。
一、向善的禀赋
《宗教》中关于人性的思想延续了康德一贯的调和基调。他不赞同各种哲学流派对善恶的非此即彼的机械理解方式,而是将善恶两种原则看作是可以共居于人性之中的。但由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二者如何共居呢?在解决该问题之前,人们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在人性之中共居的善恶原则究竟是什么?本节将重点阐明作为善的原则的向善的禀赋。
向善的原初禀赋(die ursprünglichen Anlage zum Guten)有三种:动物性禀赋(die Anlage für die Thierheit)、人性的禀赋(die Anlage für die Menschheit)、人格性的禀赋(die Anlage für seine Persönlichkeit)。其中,动物性的禀赋可以被归在“自然的、纯然机械性的自爱的总名目下,这样一种自爱并不要求有理性”(3)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这种纯然动物性的禀赋包含保存自身、繁衍种族、与他人共同生活三种本能。这三种本能又以社会本能为主,人在与同伴的共同生活中更能够保存自身生命和繁衍后代;而保存生命和繁衍种族不是为了使人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为了使其组成社会,并在社会中完善其自然禀赋。康德将这种社会本能看作是无须理性参与的,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人类最初组成社会不是出于理性的指导,而是出自其本能驱使。这种本能为人类在一种原始群居的环境中逐渐有意识地发展其自身提供了准备。
人性的禀赋可以归到“虽然是自然的、但却是比较而言的自爱(为此就要求有理性)的总名目下”(4)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5页。。理性“能通过把本身以更为间接的方式有利或有害的东西表象出来”,使人考虑“对于我们的整体状况方面值得欲求的、即好和有利的东西”(5)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这种理性还不是纯粹理性能力,而是充当为感性欲望的工具。但在这种工具性理性的作用下,人们毕竟可以对影响自身的各种感性因素进行比较、排序,总结出最值得追求的那种对象。这已经是对单纯动物性存在方式的超越。当然,工具性理性的比较功能不仅可以在个体内部施展,同时还可以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展开。自爱的实质就在于:“只有与其他人相比较,才能断定自己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6)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6页。。康德描述了这种自爱对人心的微妙影响:人最初只是在意他人的看法,并追求自己与他人的平等;但由此就产生出对其他人可能超过自己的担忧,为了打消这种忧虑,他就会产生“嫉贤妒能和争强好胜”(7)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6页。的心理。因此,这种基于比较的自爱会导向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人性禀赋就是一种建立在工具性理性之上的社会生存能力。每一个在共同体中生活的人都需要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氛围中得到成长,竞争是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社会性纽带。
人格性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做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8)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6页。。在康德眼中,道德法则和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就是人格性本身,而不是一种禀赋。但为了将对法则的敬重纳入其准则,人们必须先天地具有一种使其容易接纳道德法则及敬重的素质,这就是人格性禀赋。从人格性的角度思考的道德法则的内容就是“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这是纯粹理性颁布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并构成互为目的和手段关系的那种命令。康德指出,如果人格中的人性这一概念能够在人心中产生全部影响力,那么其他人要实现的目的也应当尽可能地成为我的目的。他并不否认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的那种关系,只是,与此同时,他们之间还应该互为目的。人与人之间的目的关系是平等的基础,只有在相互尊重的社会环境中,平等才能实现。这一道德法则表达式中所包含的实际上就是纯粹理性对最完美的那种社会秩序的要求,亦即所有人构成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和谐有序的、相互尊重的共同体。这种和谐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应当实现的终极目的。而为了实现这种完美的共同体状态,人们毕竟先天地需要一种对道德法则及敬重的易感性(或道德情感);这种情感就是人格性禀赋。由此看来,这种禀赋也就是使人趋向于最完美共同体的那种社会性禀赋。
康德对向善的禀赋的描述和区分隐含了一种历史性维度。人类种族是从一种动物性群居的社会状态过渡到基于工具性理性而相互竞争的不完善社会,最后才实现一种完全出自纯粹理性的、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社会。
在较早的著作中,康德对人性的理解不如在《宗教》中精细。《奠基》(1785)提到人类本性中的三种要素:“人类的特殊自然禀赋”“人类理性特有的、并不必然适合于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特殊倾向”(10)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33页。、“人格中的人性”。第一种本性是人的单纯感性禀赋,类似于《宗教》中所说的动物性禀赋。这种禀赋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但人们之间的感性欲求,甚至个体自身不同时间中的感性欲求都是千差万别的。第二种本性不是单纯的动物性本能,其中已经有人类理性在起作用。但这种本性同样不适合于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换言之,这种本性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并且有理性的参与,但仍然在个体之间具有根本区别。这种本性类似于《宗教》中的基于比较的自爱。每个人都具有自爱的本性,为了实现幸福,每个人也都需要一种工具性理性能力。但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仍是各不相同的。前两种本性的特殊性是由人的感性需要的特殊性决定的,即便每个人都具有感性需要,但他们所需要的对象是不同的。在所有人之间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的是其纯粹理性乃至道德法则。而能够为道德法则奠基的那种人性就是人格中的人性(人格性)。
康德在《奠基》中的任务是阐明道德法则,所以他重视的是人格性概念,而不是前两种人性概念。但《宗教》中的思想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维度的,人类在普遍历史进程中的本性是完整地包含上述三种类别的。在与《奠基》几乎同一时期的《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下文简称《普遍历史》)(1784)一文中,康德提出了人性中蕴含的“非社会的社会性”(die ungesellige Geselligkeit)概念(11)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其中,社会性指的是人使自己社会化的那种偏好。但他在这一文本中对社会性的论述并不深入。通过对康德不同时期多个文本的分析和比较,不难看出,他对人性中善恶两种要素的理解是逐渐变得清晰明朗的:《奠基》重视人格中的人性,《普遍历史》重视非社会性,《宗教》则完整地总结并详尽地解释了人性中向善的原始禀赋和趋恶的倾向所分别具有的三种类型。而康德所说的向善的禀赋归根结底无非是人性中的社会性属性。只是,这种社会性需要从动物性本能、工具性理性、纯粹理性三个层面来思考。接下来,笔者就对趋恶的倾向及其在康德不同时期文本中的演变过程进行阐明。
二、趋恶的倾向
趋恶的倾向(der Hange zum Bösen)具有三个层次:人的本性的脆弱(die Gebrechlichkeit)、人的心灵的不纯正(die Unlauterkeit )、人心的恶劣(die Bösartigkeit)。其中,本性的脆弱是由于人的感性偏好的影响相对于道德法则而言过于强烈,而不是由于他不愿意将善的法则采纳入其准则。在这个层面,人并没有主观上违背道德法则的意愿,只是没有足够坚定地遵守该法则。甚至可以说,人在主观上仍是愿意服从道德法则的,只是事实上由于感性偏好的影响而没有能够履行法则。所以,由此显现出来的结果是:“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12)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8页。,而我所不愿意做的,却正在做。这第一个层面的趋恶的倾向揭示了人性内部甚至个体自身的自我分裂:人心趋向于理性的法则,但其感性偏好却驱使着他做出不符合法则的行动。
而在心灵的不纯正层面上,人们合乎义务的行动“并不是纯粹从义务出发而作出的”(13)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9页。。换言之,人们在主观上是有意遵从道德法则的,但法则并不是其唯一动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动机混杂在其准则中。在这个层面,准则内部的多种动机(道德的和非道德的动机)并没有明确的排序,而只是被混杂在一起。康德认为,人们“也许在任何时候都如此”(14)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9页。。这就意味着,内在动机的不纯粹和外在行动的合法则性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常态,也是绝大多数人所处的道德层面。他在多处文本中描述了一种仅仅制约人的外在行动的法权原则:“要这样行动,使你能够想要你的准则应当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不管目的是什么样的目的)”(15)康德:《论永久和平》,《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2页。;“如此外在地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16)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康德所说的在心灵不纯正的基础上做出的行动,就是这种只遵循了道德法则的文字,而没有遵循其精神的行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层面的恶并不是就这种仅仅合法则性的行动而言的,而是就其内在动机的混杂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人心的不纯正与基于比较的自爱也许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合乎法则的行动就其部分的是由感性动机驱动的而言,必然包含了人们自爱的内心态度。而真正处于对立面的善恶要素是人格性禀赋与人心的恶劣。
趋恶的倾向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人心的恶劣、败坏、颠倒。虽然在这个层面“也总还是可以有律法上善的(合法的)行动,但思维方式却毕竟由此而从其根本上(就道德意念而言)败坏了”(17)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9页。。它与心灵的不纯正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意在违背法则,而是以其他动机来辅助道德动机,从而产生合乎法则的行动。道德的动机本来应当自足地、独立地规定意志;而与其他动机相混杂的道德动机不是完全不起作用,只是没有发挥其全部效力。但在一个败坏了的心灵中,其根本意图就是违背法则,使道德法则完全被置于其他动机之后。
通观上述三种趋恶的倾向,人的本性的脆弱使其做出不合法的行动,但其内心仍具有遵守法则的意愿,这是行动与其内心意愿的不一致。在动机不纯正的情况下,人的内心与其外在行动之间没有根本的不一致;他是自愿地做出合法则的行动的,只是他在该行动中还掺杂着其他动机和目的。这个行动的准则中道德动机和非道德动机之间不是正相对立的,而是共同发挥作用。这是还没有达到道德的最完善程度的绝大多数人的状态。人们无意于对其内心的道德法则和其他动机进行清晰区分和排序,而只是想要做出合法则的行动,并由此实现其主观的和自爱的目的。前两种趋恶的倾向中都没有主观自愿地违背法则的内心态度,这是它们与第三种恶的最根本区别。这三种趋恶的倾向构成了由低到高的递进序列,康德着重批判的是第三种恶,即将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纳入自己的准则”(18)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32页。。真正的恶不是就行动而言的,而是就人们内在意念中对道德法则的故意的违背而言的。所以,恶实际上是人心的败坏。
康德认为,人性中这种被败坏和被颠倒的心灵的恶是普遍地存在于所有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身上的。在此意义上,这种恶可以被称为“趋恶的自然倾向”(19)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32页。。但人们并不能由此认为,这种恶的倾向是由上帝造成的。人性的败坏是由人咎由自取的根本的、生而具有的恶。因为这种倾向存在于任意性意志的违背法则的准则中,而准则都是出自自由意志的;“一旦人表现出自由的运用,就会感知到它”(20)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38页。。所以,这种根本的恶的倾向是由于人先天地具有自由意志而被看作是生而具有的。但康德也指出:“它虽然也可能是与生俱有的,但却不可以被想象为与生俱有的”(21)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8页。。他的意思是:人虽然先天地具有自由意志,并因而具有作恶的能力,但趋恶的倾向和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恶习是其自己招致的。人不是生来就注定是恶人或无法改恶向善,而是虽具有趋恶的倾向和作恶的可能性,但仍能选择重新成为一个善人。
这也解释了这样一个表面的悖论:每个人都具有第三种根本的恶的倾向,但康德仍然承认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愿意服从道德法则的,尽管这种内心意愿也许并不纯粹。根本的恶在康德这里就好像人类弃恶从善的时间起点,而历史进程中的大多数人在完善性上,毕竟已经发展到能够在其他动机的辅助和影响下自愿作出合法性行动的程度。人们需要从发展的和历史的,而不仅仅是静止的视角来看待恶的倾向和向善的禀赋。
但如此这般微妙的根本恶,其根据在哪里呢?在康德看来,根本恶的根据“不能像人们通常所说明的那样,被放在人的感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偏好之中”,“也不能被放在为道德立法的理性的败坏之中”(22)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34页、35页。。为了说明这种根本恶的根据,感性所包含的东西太少,因为这种恶毕竟需要理性能力的参与。而一种似乎被败坏的理性或绝对恶的意志所包含的东西又太多,因为完全被败坏了的理性或意志如何有能力自行改恶向善呢?人的纯粹理性和道德法则本身是不能被败坏的,它们是借助人格性的禀赋不可抗拒地强加给人的。康德认为,根本恶或恶的心灵“产生自人的本性的脆弱,即在遵循自己认定的原则时不够坚定;而且与不纯正性相结合,没有按照道德的准绳把各种动机……互相区别开来”,甚至“只注意到行动与法则的符合,而没有注意到从法则中把它们引申出来”(23)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37页。。这说明:前两种趋恶的倾向(特别是人心的不纯正)是人们具有根本恶或颠倒的心灵的根据。人们总是将行动的合法则性看作是道德的全部内涵,而在康德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是心灵中一种根本性的颠倒了,即颠倒法则的精神和字面义。既然心灵可以在道德法则的字面义和精神实质之间作颠倒的理解,那么它就可能在道德的动机和非道德的动机之间也产生颠倒的考量。从人性的脆弱到人心的不纯正再到心灵的颠倒,这是一个递进的、自我招致的堕落过程。但这只是一种逻辑秩序。人性在其普遍历史中毕竟被看作是逐渐向善的和辩证发展的,而不是逐渐堕入最根本的恶。
向善的禀赋就是一种使人趋向于社会化的属性,趋恶的倾向则是使人个别化、孤立化的属性。这种倾向使人“想仅仅按照自己的心意处置一切,并且因此而到处遇到对抗”(24)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第28页。。正如上文所述,在人身上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其纯粹理性和道德法则,由此描绘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互为目的和手段的社会整体;而每个个体按照其私人意图行事,则会与他人产生不一致,甚至产生冲突和矛盾。“每个人在提出自己自私的非分要求时必然遇到的对抗,就是产生自非社会性”(25)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第28页。。就非社会性是人的本性中的根本倾向而言,它对应于康德在《宗教》中阐述的趋恶的倾向。
三、善恶共居于人性
康德在《普遍历史》中将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看作是一个整体,即“非社会的社会性”。这种看似矛盾的术语本身就表明善恶两种属性是共居于人性中的。由此就产生一些问题:人的本性中为什么同时需要善恶两种属性呢?这两者又是如何在人性中共存的呢?
善恶在人的本性中的共存使人性获得了自我驱动和自我完善的动力因。在康德看来,趋恶的倾向必然是能够被人自身克服的,因为它毕竟是每个人在其自由任性中自己招致的。这种观念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原罪思想有所不同(26)但这也不是说康德完全放弃了原罪思想。舒远招教授就曾指出:“康德的‘趋恶倾向’说就是同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相对应的”。参见舒远招《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4期。。奥古斯丁就曾指出,“上帝创造的人具有这样的自由意志,但是,一旦那种自由因为人从自由中堕落而丧失,自由意志就只能够由那个有权给予自由意志的上帝再次把它给予人”(27)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庄陶、陈维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因为,恩典以外的自由意志,只能犯罪,不能做其他事情。路德秉承了奥古斯丁的立场:“除了作恶以外,它是不自由的”(28)路德:《路德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36页。。与奥古斯丁—路德主义路径相反,伊拉斯谟认为:“人类意志的能力,足以使人从事导致或远离永恒救赎的事”(29)路德:《路德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98页。。这种解读方式也是对奥古斯丁时期其论敌贝拉基立场的呼应。贝拉基是公元5世纪初不列颠的隐修士,他否认从亚当遗传给世人的原罪,而是认为,行善或作恶取决于各人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并不因亚当的堕落而丧失。康德推进了贝拉基—伊拉斯谟主义路径,将人的本性中善恶属性的内在矛盾阐发为人类自由意志的自行改恶向善的驱动力。
康德在其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中的辩证思想的精髓就在于,“非社会的社会性的主要功能是个体的和社会的发展的激励要素”(30)J. B. Schneewind, Good out of Evil: Kant and the Idea of Unsocial Socialibility, Kant’s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 eds.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and James Schmid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4.。他指出:“一切装扮人的文化和艺术及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非社会性的果实”(31)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第29页。;甚至出自人的非社会性和恶的倾向的战争也是“一种动机”,“要把服务于文化的一切才能发展到最高的程度”(32)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但非社会性对社会秩序和人性完善的驱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与社会性的共存的整体中实现的。准确地说,人类历史和人性由恶向善的驱动力就是人性内部善恶两种属性的内在对立。这种内在对立演变为人们在整个社会和全部历史上的普遍对抗,并逐渐走向统一。人类历史就是善恶两种属性对立统一的过程。如果没有社会中的普遍对抗,“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尽管有完全的和睦一致、心满意足和互助友爱,一切才能却会永远隐藏在其胚芽里面”(33)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第28页。。康德在这里很明显批判了卢梭的发展理论。后者认为:“原始人所拥有的自我完善、社会美德和其他各种潜能”,“通过一系列可能不会发生的外部偶然因素”(34)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高修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48页。得到发展。康德将人性发展完善的动力置于其自身内部,并以善恶的对立加以阐释,从而使人类历史成为自我驱动的无限进程。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人类自身的主体能动性。
康德从矛盾的视角解释社会发展,这种思想也与其自然科学中对物质实体的原始运动力的描述相对应。相对于牛顿物理学中对万有引力的重视,康德更重视排斥力,“没有排斥,仅凭吸引力,就没有物质是可能的”,“排斥力与吸引力一样都属于物质的本质,而且在物质的概念中哪一方都不能与另一方分离开来”(35)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3页。。卡西尔也曾指出,康德“对物质体所主张的,对社会体也同样有效。社会不是通过个体意志的原初内在和谐而简单结合在一起(沙夫茨伯里和卢梭的乐观主义正以此为基础),而是像物质那样,其存在被置于吸引与排斥——一种力的对抗状态中。这种对抗构成任何社会秩序的中心与预设”(36)卡西尔:《康德历史哲学的基础》,吴国源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物质实体由于占据空间而具有吸引力和排斥力,这两种力的对立统一构成事物力学上运动变化的原始根据。这与牛顿将自然物体的第一推动因归于上帝的机械思想有本质区别(37)虽然康德哲学中也包含着机械的自然观,但他强调了物质实体之间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相互对立,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与机械论因果秩序相容的目的论因果秩序,就此而言,他对牛顿自然哲学有实质性的推进。。而在社会领域中,康德从人性的自我驱动的角度理解普遍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是对卢梭人性观的超越。
但是,物质实体在康德看来只是占据空间的事物,“没有绝对内部的规定和规定根据”(38)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第559页。。吸引力和排斥力都是物体借助于对空间的充实而具有的外部规定,它们之间的对立不构成物体的“内在矛盾”,因而也就不能充当一种自我驱动的力量。这就意味着,物质实体的运动变化仍需要外部作用(39)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讲到物质的两种力,一种是就物质充实空间而言的原始运动力(即吸引力和排斥力),而“充实这个空间的物质本身却不可以被看做运动的”;另一种是运动之中物质的力,这是事物在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力。康德分别在动力学和力学的名目下对二者进行描述,并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前提。换言之,物质在运动中之所以能够相互作用是由于任何物质都具有原始运动力;原始的运动力就好像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使物质能够推动其他物质运动,或者被其他物质推动。但原始的运动力并不能使某物自己动起来,因此,任何物质的运动变化都需要其他物质的推动。参见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第551页。。这是康德在自然观上仍未能彻底摆脱机械论立场的原因。与之不同的是,善恶两种原则被看作是在人性内部相互对立着的,这使人性能够在普遍历史进程中自我驱动,而无须外在力量的干涉。康德虽然在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中都看到了对立要素,但对它们的定位和描述仍具有本质区别。
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虽然人性内部善恶两种属性是以互相对立的方式共存的,但这两种要素并不是以同等权重存在于人性之中的。在康德这里,向善的禀赋始终是人性的主导的和应然的要素。趋恶的倾向虽被看作是根本的和自然的倾向,但并不由此就是应然的。毋宁说,人们基于自由意志不断向善才是其应然的存在方式。堕向罪恶或者始终为恶而不思向善是对人性本身的败坏。所以,在善恶共居的各种可能的方式中,善的原则不可能存在于恶的原则中,恶的原则也不能存在于善的原则中。因为善的原则必须自身是纯粹的和独立自足的。假如善恶可以相混合,那么善的禀赋甚至纯粹理性自身就被败坏甚至丧失了。在康德看来,“在我们身上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并不是获得一种丧失了的向善的动机;因为这种存在于道德法则的敬重之中的动机,我们永远不会丧失。要是会丧失的话,我们也就永远不能重新获得它了”(40)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46~47页。。
但两者也不是势均力敌地在人性内部对立着的。康德指出:根本恶乃至一切恶习都是“嫁接”(pfropfen)或“附着”(ankleben)(41)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6页、30页。在善的禀赋和任性的道德能力之上。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对于理解善恶在人性中的共居是至关重要的。这表明,人们偏离道德法则的一切行动和准则都不是其本来应当趋向的路径,正统的路径应该是遵循道德法则,按照其精神实质行事。即便人们现实中总是偏离正轨,但不能由此就将各种偏离的路线当作是与正道旗鼓相当的。趋恶的倾向乃至建立在这种倾向上的一切恶习,都是以附属的方式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它们绝不可能取消向善的禀赋的主导地位。正因为善相对于恶的这种正统性,具有根本恶的人仍然有能力重建善的禀赋的原始力量。善被康德解释为“注定”要战胜恶的。这种由恶向善的思想仍然是基督教道德观念的持续,只是康德认为,人“不是从根本上(甚至就向善的最初禀赋而言)败坏了的”(42)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44页。,从而人类依靠其自身的自由意志就能获得救赎。
但是,在三种向善的禀赋中,只有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上可以嫁接恶习。在人格性禀赋上,“绝对不能嫁接任何恶的东西”(43)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6页。。而且,即便恶习能够被嫁接在前两种禀赋上,也不能由此将善看作是恶的根据。毋宁说,一切恶习都产生自人性的软弱、动机的不纯甚至心灵的颠倒。进一步而言,嫁接在动物性禀赋上的恶的东西被视为“本性粗野的恶习”(44)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5页。,而嫁接在自爱禀赋上的恶的东西则是“对所有被我们视为异己的人持有隐秘的和公开的敌意”(45)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26页。。这实际上就是康德在《普遍历史》中所说的,由非社会的社会性所导致的普遍对抗的社会状态。
人性或普遍历史的辩证发展进程表现为,人类社会从其动物性的原始群居状态,逐步过渡到人们基于自爱甚至自私动机而相互竞争甚至普遍对抗的状态,最后实现人与人之间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完美共同体状态。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第一,非社会性或恶的属性是以自我扬弃的方式促进社会发展的,它“被自身所逼迫而管束自己,并这样通过被迫采用的艺术,来完全地发展自然的胚芽”(46)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第29页。。人们听从内心非社会性的驱使而偏离道德法则,但却由此锻炼了理性能力,成熟的理性能力则反过来规训人的非社会性和种种恶习。第二,恶作为历史驱动力中的关键要素在社会整体中导致了一种普遍对抗。假如没有动物性禀赋中的社会本能,人们不会过一种原始的群居生活;而在一切个体孤立地生存的场景中,非社会性和趋恶的倾向根本无法发挥作用。这揭示了社会性本能在历史发展中的奠基意义。
总而言之,恶的属性是以附着或嫁接在善的属性上的方式与善共居于人性中的。康德通过对善恶的共存和内在对立的描述,进一步阐发了一种人性自我驱动、自我完善的辩证发展观。人们通常关注的是“康德道德概念的先验性”(47)吴辉:《论马克思和涂尔干对康德道德思想批判性阐释的范式差异》,《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以及其道德形而上学视域下最完善的人性状态,或者倾向于对善恶两种属性进行静态分析。但康德的历史性视阈下的人性发展观也是值得关注的。这种历史性维度不是作为一种显性思想和普遍方法论存在于康德哲学体系中的,而是作为一种隐性思想相容于其先验思维框架;或者说,历史性维度及其思维方式只是包容在其先验的道德法则之下的“后续的原则”(48)李哲罕:《论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解体——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历史中的人性与理想状态下的人性无非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具有统一性的。由此,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与其历史哲学等思想也是具有融贯性的。
四、结 语
康德的善恶共存观念是对基督教原罪思想的批判性继承,而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善恶看作是在历史进程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善的禀赋无非是使人趋向于社会化的那种属性,趋恶的倾向则是使人孤立化甚至敌视他人的属性。人性中的善恶要素构成对立统一体,并由此驱动普遍历史的辩证发展。这种自我驱动和自我完善的人性立场,也是对卢梭的机械人性观的超越。但人性内部善恶两种属性并不具有同等权重,善的禀赋是人性中的原始属性,趋恶的倾向是人自己招致的。康德虽然秉承了基督教由恶向善的经典发展观,但在发展动力上,他并不求助于一种外在的恩典,而是认为,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作恶或行善。因而,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不是上帝由上至下、由外而内预定的,而是由人自身历史性地自我驱动的。这是他对近代启蒙精神的回应和推进。
但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在其人性观上的对立统一思想,并不表明他已经将一种历史性和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当作一种普遍方法论。毋宁说,这仍然是在其先验逻辑的思维框架内展开的。人性的发展进程合乎纯粹理性先验设定的道德目的,也符合反思性判断力的先验的合目的性原则;没有这些先验预设的概念或原则,人性内部两种属性的历史性和辩证性的统一是无法成立的。准确地说,这种历史性和辩证性思维方式是对其先验逻辑的辅助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