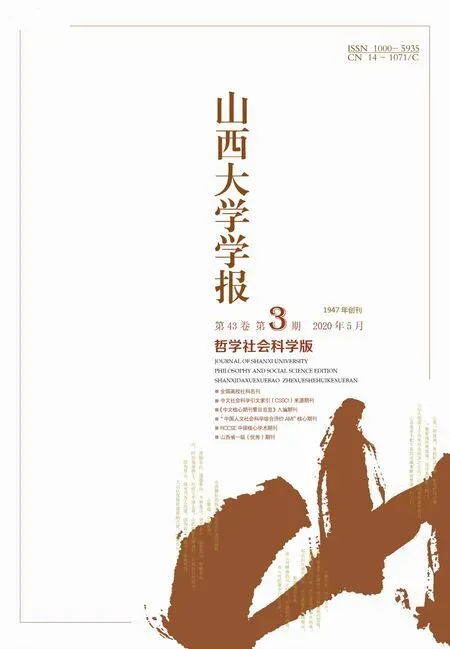现代“广告”观念的中国旅行
——基于全球传播思想史的视角
祝 帅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871)
全球广告史与广告思想史的研究,无疑是当前广告史研究中的两个热门领域,但以全球史视角关注中国广告思想史的研究还殊显落寞。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实践一种全球广告史的写作,只是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尝试往往浅尝辄止,并且带有某种程度的偏见[1]。作为一种全球广告史的叙述,如果忽略了中国将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众所周知,现代广告思想从一种美国观念的历史语境中脱颖而出,并最终完成与传统布告观念的历史断裂。在这种美式广告理论和实践对外输出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全球传播过程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个案,将会给我们的讨论带来许多新的发现。本文的问题是:美国式的现代广告理念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传入中国的?这种新式广告观念是如何在一种异文化的跨语际传播中被接受的?为此,需要分别考察现代广告理念的传入和现代广告实践的展开这两个关键环节。
一 西洋“广告”观念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关于中国广告的起源,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学说。在报人蒋裕泉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本版的广告学著作《实用广告学》中,第九章即为“中国之广告史”,并分为“广告之沿革”与“现代广告之趋势”两部分。蒋裕泉认为,广告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出现而产生,并将广告的起源上溯到夏商周三代,还从《容斋随笔》等文献中辑出大量广告史料。[2]无独有偶,1925年,商业教育家施督辉撰文也指出:“神农氏定日中为市之制,于是有物出售之人,乃列物于市廛,以供众览,而谋出售。此即以商品之实体,列置于市场,而作铺张广告之滥觞也。故广告之原始极早。此不过就广义而言。如由严格之意义言之,广告之滥觞,不在于印刷物未精之前,而在于印刷物已精之后”[3]。同年,李延春在《四明月刊》发表《广告的研究》一文,明确用一种“分期”的方式来区分古代广告与现代广告。他指出:“广告底(的)由来,不是最近的新发明,也不是专门的学识;自人类开始交易,一般小贩以及店铺都有广告所在,不过我们没有把它加以考察,到了欧美风雨东渡以来,我国人才把广告注意些了”,为此,广告“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期是最简单的,也是我们平常所不承认的,然我国人不叫它是广告,它的性质却是广告。例如,(1)小贩的叫卖声。(2)铺面的布置。(3)街市上的旗子。(4)货物上的花纹。(5)商品上的印子。(6)招牌。……第二期因常见这样,所以叫它是广告,这比第一期进步了”[4]。1928年,佚名发表的《广告浅说》一文,在论及“广告学的历史”时则似乎更加客观:“广告学原是一出老戏新做。因为广告学虽是商学中一种极新的科目,但是广告一物的历史,却很悠久了。从前的广告,不过用一种极简便的方法例如江北人卖糖,敲着一面小锣,敲锣便是一种广告。现在留兰香糖的广告,不用锣了。两方面用的方法虽是不同,但是用意却是一般”[5]。
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尽管把古代广告纳入广告史学研究的视野,但毕竟无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与现代广告的研究格格不入,像剑桥学派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看到的那样——史家的责任“是重觅过去,并把它呈给现在,而不力图用今天的标准去褒贬过去,因为这些标准既受视阈所限,也无永恒效力可言”[6]。我们在描述所谓“古代广告”的时候,也难免陷入一种在古代寻找现代广告对应物的倾向。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承认广告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而是人类交易信息的一种传递方式时,应该说广告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商业行为始终,在古代也一直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存在着。这样看来,一种类广告、泛广告的现象当然古已有之,与现代广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但的确贯穿于全球商业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由此可以看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在中国广告史上似乎仍然存在:即中国古代广告为什么没有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以代理制为基本形式的现代广告?
另有一种观点绕过中国古代广告,直接将广告视为新生事物。1920年,戚其章即在《复旦》月刊撰文指出:“广告在19世纪的前半叶已有了,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这种科学变得更加发达了,而又进步”[7]。1924年,解殳伯撰《商业广告之研究》,也指出:“广告法之关于营业盛衰也,至为重要。欧美设有专科之学校,精研数寒暑而后毕业焉。乃吾国不为专研之者,阗无其人。即此类书籍,亦颇罕觏。无怪我国商人,不知广告法之重要矣。以言商战,其何能胜”。[8]
相对而言,论及“广告学”的著作,更是以广告为近代以来的新生事物。1927年,徐霄汉在著名的《广告学与术》一文中指出:“广告学有人说是新闻学之一部,有人说是商用文之一部,诚然新闻纸上登广告,广告亦有新闻性质,商用文学甚多,……广告既以转移心理,普吸群众为目的,则与广告学有关之科学,如心理学,如美学等,不可不先述其应用于广告学之大概”。[9]留美广告学硕士陆梅僧在《广告》一书中,也采取现代广告学的进路对中国广告起源问题给出了全新的阐释。在该书第二章“广告的历史”中,陆梅僧直接跳过牌匾、招幌等原始广告形式的叙述,而是从一开始起就把广告和商业活动,特别是媒介发布的情况结合起来叙述[10]。
毫无疑问,这些作者接受了现代广告的理念,认为现代广告与古代广告相比断裂性大于延续性,因而他们的广告史叙述,并不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广告史,而是作为一个现代行业的广告代理业的历史。
1948年,上海新文化社出版署名“如来生”的著作《中国广告事业史》这本小册子。该书开始在介绍“广告”概念时,称“凡是要使多数人知道,而含有宣传作用的举动,都是广告。譬如像从前酒肆门前挂了一方旗帘,衙门贴出告示,药铺,南货店招牌子上印着坐南朝北,认明‘和合’为记的句子,以及各家商铺悬挂的市招,都是广告的行为,所以旗帜店的伙友,招牌店的漆匠,称为广告从业员,亦无不可”。但随后论及中国广告事业的“草创时期”时,如来生又以晚清为开端:“推溯中国广告事业之发轫,远在逊清末年”[11]1-6。可以见出,至少到了40年代末期,民国的广告史研究者,已经把旧式的“广告”和新式的“广告事业”看作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了。
当然,民国广告思想史始终体现出东西方观念的碰撞与融合,也一直存在着诸如“月份牌画”这样非西方广告的文化元素。这种诞生自中国本土的广告画形式与舶来自西方的“代理制”公司共同构成民国时期中国广告公司的两种主要类型。前者包括“稚英画室”“生生美术”等本土广告人所建立的公司,而后者则包括林振彬、陆梅僧等留美广告人所开创的“华商广告”“联合广告”等。这提醒我们注意到,有关现代广告思想与观念的中国旅行,还必须通过刘禾所说的一种“跨语际实践”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即注意到“学术研究的学科界限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模式,在处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和语言时,常常造成一些困难重重的诠释问题”[12]1。应该说,这一判断大体也适用于描述西式广告观念在中国的旅行。[13]
二 现代广告在中国本土的诞生
只是,毕竟以上述两类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广告观念与古代广告观念之间的“断裂”在中国广告史上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断裂”的过程是怎样,经历了哪些以往不为人所注意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环节,还是一个有待于深究的问题。如果按照福柯的观点,把词语和事物之间新联盟的形成看作现代事物与传统断裂的标志,[14]那么,就可以把“广告”这个词汇的启用看作是中国现代广告与传统的“告白”断裂的一个外在标志。刘禾指出:“在跨语际实践的语境中,历史变迁的具象恰恰就是新词语或者新词语的建构”。[12]43这样看来,最早出现广告字样的中文报纸及其具体观念为何,便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佐证。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广告研究者,还是今天很多中国广告史的教材,或是有所回避,或是以讹传讹。
关于“广告”一词在中国报章上的出现有多种说法。例如,说清政府的《政治官报》(1906年)章程中第一次使用“广告”一词者有之;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1899年4月30日第13期上率先使用了中文的“广告募集”和“广告料”(即广告费)者亦有之。前一种说法随着近年来近代报刊文献资料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建立不攻而破,因为尽管《申报》的章程中彼时仍在使用“告白”一词,但1901年前后,《申报》上的商业广告中就已多有出现“广告”二字。而后一种说法尽管于史有证,但问题在于,《清议报》作为一份创办于海外的华文报纸,且是在日文中出现了中文广告一词,因此其在中国本土商业领域的影响力终究有限。但不难看出,用“广告”一词来对应“Advertising”,既是日本外来语在现代汉语中之应用的又一例证,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接续起的是美式新型广告理念,而与描述广告物质性一面的“告白”一词拉开了距离。
近年来,随着电子报刊检索数据库越来越完备,使得中文广告起源问题得以正本清源,根据笔者最新检索到的资料,在中国本土最早使用广告一词的中文报纸为1900年的《湖北商务报》。2019年,有学者率先撰文报告了这一发现[15]。该报作为湖北地区第一份官方创办的报纸,于1899年4月30日在武汉创刊,由张之洞创设,汉口商务局刊行。在该报1899年第35期所载《局发文牍:商务局照会商董报册准收广告文》中,从名词到表述都明确而系统地引入了现代广告的观念:
为照会事,查东西洋商报,皆收广告。盖有商则农工各产,皆得资其流通。有广告则商业各情,皆得赖以传布。至于物品增一新货,制造创一良法,尤倚广告之力,乃得行远播众,速售畅销。商报许登广告,有利于商,并有利于农工,为益甚溥。且设报之意,专在启发商智,以振兴商力。许登广告,则商家之视报册,与有关系,可令辗转乐观,愈藉(借)以研究情形,开通风气,暗中收效尤远。[16]
在同期随后刊出的《计开馆定略例十二则》中,即明确说明“广告即俗称之告白。”“凡关于农工商各业者皆登,余事不登。”这里,一个新词引进的背后,自然有广告理念革新的意义在。并且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在这则章程中,似乎还特别注意到了美式“商业广告”与法式“分类信息”的区别,指出:“其有长篇之行规、章程等,关于大众公益之件,刊资自可再减,或竟可不归广告之例,由馆送登。唯此项减资及送登之例,须临时由馆酌定可否,不能预指。”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在现代广告观念传入中国之初,国人即意识到美式现代广告的“冲突型”特征背后的商业特质,及其与公益型的法式传统广告之间的差异。只是相对于中国古代广告而言,无论这里的公益广告还是商业广告,都属于一种“舶来品”而非中国传统的自然流变。
《申报》“本馆条例”中的“告白”二字历史性地变为“广告”却是1918年10月1日的事情。大概是《申报》影响力太大的缘故,以至于李文权在1912年发表的《告白学》一文题目虽然是“告白学”,但内文中却提及日本的“今日本亦研究广告术,以冀其商业之发达”。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前后,“广告”一词在中国媒体上普及开来。此后,留美的广告人林振彬、陆梅僧、叶建伯、汪英宾等,也开始在中国建立“代理制”广告公司的同时,受邀在国内各大学、中学讲授“广告学”课程[11]2。至此,美式的现代广告理念在中国业界和学界已经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专业在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出现也为现代广告业在中国的正名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20世纪初,心理学的发展和商业性广告研究的出现为后来的广告专业教育铺设了道路,此后营销学在50年代以后的大发展,又促进了广告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但无论是心理学还是营销学,都并没有使广告学在学科体系中获得清晰定位。广告学学科的大举建立和独立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传播学的奠基而展开的。直到广告找到传播学的归属后,才使得它彻底摆脱了在商学和心理学边缘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
在中国,整个民国时期,广告专业之所以没能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无法确切获得自己在学科格局中的定位。在特殊的年代中,1956年中国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虽然设有装潢系,但该系的商业美术专业可谓与广告学失之交臂。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接触到传播学这个新兴的概念。随着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初便被引介进中国,在施拉姆的弟子、香港传播学者余也鲁的帮助之下,中国内地首个新闻传播系和首个广告学专业于1983年在厦门大学建立。有了传播学的学科归属,此后中国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在短时间内快速成为显学,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 美式代理制的中国实践
广告掮客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众所周知,最早的中文报纸是19世纪初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虽然是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定期出版物,但在刊登新闻之余,除宗教教义的信息外并没有出现商业广告,当然也不可能承担起建立现代广告观念的重任。考察现代广告观念在中国的旅行,对《申报》无论如何都不该避而不谈。相对而言,《申报》引入现代广告的实践非常早,但该报长时间以来使用的却是“告白”一词。在创刊号(1872年)上即有“本馆条例”,其中提到的“卖报人”,即是中国最早的“广告掮客”,也是后来媒介代理机构的前身[17]。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这种接受还仅仅停留在“观念先行”的思想启蒙阶段,在现实中无论是林振彬的“华商广告公司”,还是陆梅僧的“联合广告公司”,这种全案代理型的美式广告公司都仅仅是星星之火,那种加工生产古代广告的月份牌画美术公司、美术工作室还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民国时期老上海的广告代理业,主要由林振彬、陆梅僧等留美广告人建立,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荣昌祥广告公司等。尽管这时候本土的广告主(如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仍然青睐于“月份牌画”这种前现代的广告形态,然而只要一与报纸这种现代传媒打交道,“代理”便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广告业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分工:实行代理制的新型广告公司只管“代理”,不管设计制作;而各种本土的美术公司,如稚英画室、生生美术公司等,虽以美术设计见长,却不从事媒介代理。以至于早期广告主通过代理公司发布在报纸上的广告,其创意设计竟然很多时候是由广告主自己完成,广告公司只负责联系媒体发布事宜。而对于径自找上门来的“直客”,媒体也常常是“来者不拒”,只是创意设计仍须由广告主亲力亲为。
据如来生《中国广告事业史》记载:“因为广告代理商可从报馆方面获取折扣及回佣,客户直接到报馆送登广告,折扣是比代理商为高。所以,像以上几家的广告,为便利经济起见,后来都委托广告代理商代理的”。[11]6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广告界对于代理制的理解还仅限于“交易模式”而非“服务模式”,这时候的“代理”还仅限于“媒介代理”,这是旧式“广告掮客”规模化延伸的必然产物。尽管如来生宣称“凡献身广告事业的人,如仍以掮客自居,未免自己看轻自己”[11]3,但必须承认这种观念在当时还很有市场,一种建立在市场营销基础上为广告主提供全面服务的“全案代理”观念还并没有真正形成。
这里以民国时期《农林新报》的广告代理情况为例。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1926-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下辖之南京《农林新报》社档案,可以看到其与当时的一些主要广告主,如上海中华书局、慎昌洋行等的往来书信、票据等。其中,慎昌洋行(Anderson&Meyers Co.Ltd.of China)作为外商,其报纸广告系通过位于上海圆明园路6号的中国广告公司(The China Advertising Service,Inc.)来代理发布,且随附往来票据、书信等甚详。其中,既包括报社刊登广告后向广告公司的催款函,也包括广告公司对报社自行续登的广告“实难付款”的委婉说明①《金陵大学档案》,1926年,全宗号:六四九,案卷号:21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关于“中国广告公司”,在广告史中的相关记载并不多,就连如来生1948年《中国广告事业史》后附的“上海市广告同业公会会员名录”中,也仅有一家位于汉口路263号的“中国广告公司”(该书正文中称为“中国广告社”)。圆明园路上的这家公司虽并非沪上最大的三所新式广告代理公司之一,但是,因为服务国际客户,故尚能够严格执行代理制——为广告主制定媒体发布计划,并代替广告主向广告媒体定期付费结算。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对外商进行媒介代理的交易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贸广告业务中还得以保存,新中国率先成立的外贸广告公司——上海广告公司的业务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就与老上海的这家“中国广告公司”极其类似,而且上海广告公司的地址一度同样设在圆明园路。只是在60-7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广告中,“出口广告”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进口广告”,故而新中国的外贸广告公司比之民国时期,只是增加了一些设计方面的人力资源。
上海中华书局在该报刊登的农业、林业类书籍广告,却似因系中国本土企业,则未经代理公司中介,由中华书局内设的“推广部(Publicity Department)”和事务所下属的“广告课(科)”分别与报社联系。其中,推广部由陆费逵的三弟陆费叔辰负责,广告课则由沈鼎从负责。从字面上来看,这里的“推广部”和“广告课(科)”的职能,恰似法式广告和美式广告的区分,但实际上二者并非同级部门,其“推广”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营销”,广告作为营销手段之一属于其下级部门,投放和设计业务均由推广部负责管理与计划,广告课(科)具体负责执行设计和发布。在该卷宗中,有1926年未署年月陆费叔辰、7月22日沈鼎从分别写给《农林新报》负责人李积新的两封信札。这两封信札的重要性在于,广告主在与广告媒体提到广告费的同时,还都提到了广告的设计稿(广告底稿/铅版)。陆费叔辰的信中说:“广告底(的)稿兹据广告部云已于21日寄出,目下谅可收到。”而沈鼎从则写道:“遵嘱将敝局广告刊登九期。附上农林书广告铅版一方,请连登三期,其余六期当再另换新版”①笔者2008年5月对章汝奭先生的访谈记录,未发表。。可以看出,这种由广告主自行设置的“In-house”的广告创作部门,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承担了本该由第三方代理公司承担的专业服务的工作。这种交易制度在当时刚刚引入了“代理制”的理念,在仅把代理制理解为一种收费形式而非专业核心竞争力的当时中国广告界,应该说很普遍。
在国际范围内,这段时期广告学的研究也主要还是拉尼奥所说的心理学的研究,尚缺乏营销学、传播学理论的介入。广告研究存在的形式也只是俱乐部、期刊以及心理学和商业领域的研究,而缺乏高等院校中广告学专业的建置[18]。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广告业获得了极大的进展,广告教育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只是由于50-70年代特殊的制度环境,使得国人一度对20世纪后半叶西方代理制和美国广告专业化的发展几无所知。这种情形在中国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重新打开才发生改变。
四 思想史视野中的当代中国广告
广告思想史的发展,也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尽管有多种广告学著作的出现,无论是在中国的高校还是美国的高校中,20世纪上半叶都还没有出现正式的广告学学科名称。因此,除了考察19世纪末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现代“广告”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我们还必须深究一下20世纪上半叶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两次对西方现代广告理念,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广告实务进展的导入进程。我们的看法是,尽管19世纪中叶美国式的代理制已经初见端倪,但它的大举扩张进而为全球广告业所普遍接受,还是20世纪中叶之后的事情。5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的许多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广告研究中闻所未闻的新术语、新理念,如“创意”“营销”“传播”等,对于中国大陆的广告界,无论学界还是业界,应该说也都是在70年代后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到的。
在“营销”方面,尽管20世纪初期霍普金斯的“科学的广告”,20世纪中叶大卫·奥格威等人的“创意革命”都可看作是营销理论,但营销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壮大,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中国,尽管50-70年代的国情使得美国大学广告学专业在建立的前三十年内无缘与中国接触,但一旦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营销类课程就率先在中国大学中设立。由于在7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国际贸易,所以中国外贸系统的高校、广告公司和广告人在这个过程中首当其冲。1981年,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章汝奭、黄燕,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罗真耑三人率先在大学课堂上开讲当时还被称为“市场学”的营销课程①。从此,“广告是营销传播的手段之一”这一概念界定,既成为中国广告人应有的常识,也成为中国广告界以世界现代广告观念取代“广泛宣告”这一表层理解的重要标志。
1980年11月,日本电通广告公司的专家玉木彻志来到北京,并与土桥纠夫、八木信人等一道用“以销售为目的,统一的、有计划的市场活动”来向中国外贸广告企业的广告人系统地讲解市场营销(marketing)这种让国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曾任北京广告公司总经理的姜弘回忆说:“马克丁(marketing)理论引入中国是中国广告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广告从商品或服务的推销手段到市场营销重要组成部分的转折点。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广告人与徐百益、丁浩等老一辈广告人广告经历上的根本不同”①笔者2017年9月对姜弘先生的访谈记录,未发表。。应该说,尽管美国营销协会早在30年代就已经成立,但是用营销的理念来理解现代广告,的确是中国广告界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完成的历史使命。
在“创意”方面,中国大陆的接受也比西方至少晚了30年。查民国广告学期刊文献,并没有发现“创意”的字样。50年代在西方轰轰烈烈的创意革命,还是改革开放之后通过日本电通公司这个中介才为中国广告人所熟知。1984年,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广告公司总经理的姜弘,在受到日本电通专家授课的启发后,在全公司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以创意为中心,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的经营和服务理念。1986年在陕西咸阳召开的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上,姜弘以同样的题目向大会发表了主题报告。姜弘的报告引发了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等其他内贸系统广告公司的积极响应和效仿,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量内贸广告公司对自身只能“画广告牌”和“做霓虹灯”的业务定位。时隔多年之后,时任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广告人唐忠朴回忆说,姜弘的理念在80年代的中国广告界掀起了一场“创意风暴”②笔者2017年9月对唐忠朴先生的访谈记录,未发表。。
需要说明的是,80年代中国广告界的这场“创意风暴”,要比1996年中国广告代表团“兵败戛纳”之后内地掀起的“创意热”范围更广,含义更丰。1996年之后中国广告界短暂兴起的设计热和创意热,说到底还是针对广告设计作品本身的“创意”,而在姜弘这里,“创意”却是用来与现代的“营销”理念相配合的执行工具。从此后北京广告公司在服务国内外企业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广告运动来看,其“创意”并不仅仅限于作品的创意,而是涵盖从市场调查到投放的整个广告策划过程的一种服务理念。无论如何,现代广告代理业要打破“广告掮客”的刻板印象,从媒介代理走向真正的全案服务,则“创意”就必然和“营销”“文案”“品牌”“市场调查”等一道,成为体现广告公司专业价值和服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概念的引入,现代广告理念迅速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还要归功于美国广告公司在全球的跨国界营销。至此,在全球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只要有美国的企业,美国式的广告理念就随之无孔不入。广告观念经过了法国式公共服务的代理走向美国式的商业代理制的认知过程,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带动,一种适合全球化的新形态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形成。这样看来,美式现代广告理念在中国的加速传播,除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广告界和广告学界对于西方20世纪后半叶新兴广告理念的接纳,还有以4A公司为代表的美国跨国广告公司在中国的主动输出。这种输出的一个起点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跨国广告主开始进入中国拓展其海外市场。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当时的广告公司并不能够满足外商来华企业“全案代理”的需要,跨国公司携带自己的4A公司进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4A公司也开始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与中国的广告企业合作[19]。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的广告业也逐渐向外资敞开怀抱,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允许国外广告公司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在华开展业务、允许设立私营广告公司,到“入世”后广告业对外资的全面放开和大举进入,美式广告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尽管不乏误读和改造,但最终完成了对于中国广告的征服与收编。
五 结语
本文在全球广告思想史的思路基础上结合现代广告观念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的案例进行了讨论,探索广告思想从广义的、存在于社会文化思潮中的广告观念,到现代广告观念生成后来自于广告专业领域的广告学术思想演变的过程。这种广义的“思想史”不仅包括精英层面的思想家和业内人士对于广告行为自觉的反思,也包括存在于更加广袤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大众观念。总的说来,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在论述西方传统广告思想从古典广告形态向现代广告形态的流变时,需要侧重于考察西方一般社会文化思想对广告现象的影响;而在论述二十世纪中国广告思想发展史时,则需要侧重于对彼时已经从西方传入并在中国发挥作用的广告学术思想与广告形态变迁的互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广告史的古今之变形成清晰的认识,并由此对未来中国广告发展的规律形成理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