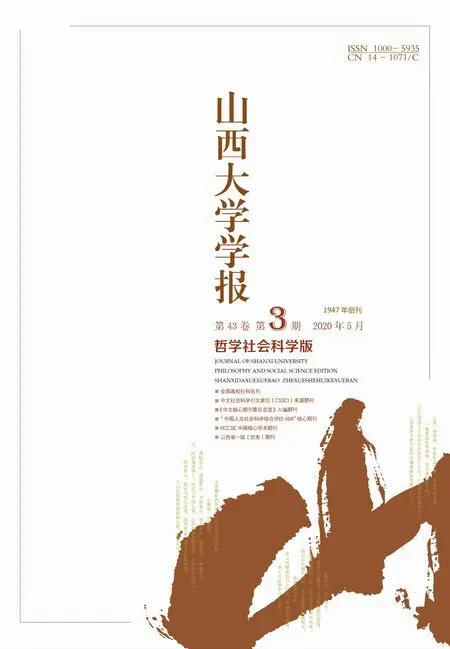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怨刺诗类型演化
邵炳军
(上海大学 诗礼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444)
所谓“怨刺诗”,即“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汉郑玄《诗谱序》)之作①本文所引《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论语注疏》文,俱见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1815—1816)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阮校十三经注疏本,不再逐一标注。,也就是指反思历史、针砭时弊、感叹身世、抒发怨愤情怀以及具有鲜明政治批判精神的诗作。其产生于西周后期,兴盛于春秋时期,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截至目前,当代学者认定传世《诗经》中的怨刺诗大致有106首①就笔者所见,自1984年起,先后有翟相君、刘毓庆、傅正义、蒋立甫、彭 昊、葛立斌、王 红、杨 简、李清文、章岿然、毛志伟、刘素琴、洪 琨、文航生、罗 慧、翟 云、刘怀荣、姜云蕾、孙元元、孙董霞、李亚丽、张 慧、王玉婧、刘子珍、王向华等先生,发表专文进行讨论,此不俱引。。据笔者考订,春秋时期比较典型的怨刺诗有107首(包括《诗经》88首,逸诗19首)②本文所涉诗篇之作者、诗旨及创作年代,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邵炳军.德音斋文集·诗经卷[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文中不再逐一标注出处。。这些诗篇,就怨刺对象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言,可分为怨刺天子、国君、卿大夫和家臣等四种基本类型。春秋时期这些怨刺诗类型的演化进程,都与当时政治生态环境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依次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篇》)变迁历程密切相关。
一 怨刺天子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此类作品凡23首,怨刺对象主要为周天子,涉及幽王宫涅、平王宜臼、携王余臣、桓王林及“奸(干)王之位”(庄公二十年《左传》)的王子颓等。就所怨刺的内容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天子近小人而远贤臣导致西周覆亡,像《小雅·节南山》《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小雅·四月》《小雅·青蝇》《大雅·瞻卬》等。比如,《节南山》为周王室宰夫(下大夫)家父(家伯父)刺幽王重用太师尹氏皇父(皇父卿士)乱政覆国之作。全诗十章,前三章直陈时弊,中三章说明事理,末四章感叹抒情。特别是诗人在结尾用“以究王讻”这一点睛之笔,把皇父之乱政与幽王之昏愦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使批判锋芒直指周王室的最高统治者。再如,《正月》为周大夫刺幽王致使宗周(即西周都邑丰、镐,亦称丰京与镐京,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两岸)覆亡之作。全诗十三章,一、二、五、八四章写西周亡国之象,三、四、六、七四章自伤沦为“臣仆”而“无禄”之茫然心态,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五章以宗周覆亡历史教训戒勉平王,表达了诗人冀望其任贤以止乱之动机。又如,《十月之交》为周大夫刺幽王宠信褒姒以致灭国之作。全诗八章,前三章重点描写月食、日食、雷雨、山崩之天灾,后五章重点叙写“艳妻煽方处”之人祸。足见诗人认为天灾为果,人祸为因,故侧重点在人祸;而正是天灾与人祸并行,终于导致西周覆灭。
二是王室不能合族保民而渐次衰微,像《王风·扬之水》《王风·中谷有蓷》《王风·兔爰》《王风·葛藟》《王风·采葛》《唐风·鸨羽》《桧风·匪风》《小雅·沔水》《小雅·谷风》《小雅·采绿》《小雅·苕之华》《小雅·何草不黄》等。比如,《兔爰》为周大夫闵桓王之命不行于天下之作。全诗三章,上两句分别以张罗、罦(覆车)、罿(覆车)捕雉(锦鸡)起兴,言小人放纵致乱却以巧计独免,而君子忠直无辜却获罪得祸;下五句皆抚今忆昔,抒厌世之情,发悲愤之怨,言君子不乐其生之由:周室衰微,诸侯背叛,人祸横行。再如,《葛藟》为周王族大夫刺平王东迁雒邑(即王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时弃其九族之作。全诗三章,皆以连绵不断的葛藟尚能蔓生于水中比兴,先写水由浅入深:浒(水岸边)→涘(水边)→滣(深水边),再写人由近及远:父→母→昆(兄),以“终远兄弟”贯穿全诗,描写出王室同宗族人被王所弃后流离失所的窘境,进而从平王东迁时弃其九族之亲这一侧面,揭示出王室艰难而周道衰微之兆。又如,《鸨羽》为晋国人刺周桓王命虢仲伐曲沃(本晋故都,时为穆侯庶子、文侯仇之弟桓叔采邑,即今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武公而立晋侯缗之作。全诗三章,前两句分别以鸨(野雁)栖息于草木丛生的栎树、酸枣树、桑树上起兴,喻君子不得安居;后五句皆为叙事与抒情:诗人叙因“王事”服役于外,抒不能种稷黍以奉养父母之憾,发“怨天尤王”之叹。
三是王族嫡庶屡争而渐次微弱,像《王风·君子阳阳》《小雅·雨无正》《小雅·小旻》《小雅·角弓》《小雅·菀柳》等。比如,《雨无正》为携王余臣暬御之臣表达自己面对“二王并立”政治格局时怨忧情绪之作。全诗七章:首章名言天灾而实指人祸,次章写“周宗既灭”后“靡所止戾”之具体表现,三章以呼天自诉申述前两章文意,四章言天王宜臼与携王余臣兄弟相残,五章以忠介之臣“不能言”与巧佞之臣“能言”进行对比,六章将“不可使”与“可使”进行对比,卒章总括全篇诗旨。足见诗人以“各敬尔身”为主线谋篇布局,以呼天起笔发端,以推本探源落笔,借怨天以刺王。再如,《角弓》为周大夫忧平王宜臼与携王余臣兄弟相残之作。全诗八章,以“教”为主线贯穿全篇,前四章重在刺王不亲兄弟,导致诸侯乃至国人自然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两大政治营垒;后四章重在刺小人谗佞得逞,致使万民所“胥效”的同姓兄弟闹得“相怨一方”“如蛮如髦”。又如,《菀柳》为携王近侍之臣中有功者获罪后所怨刺携王之作。全诗三章,选取“柳”“鸟”二物象,采用反兴之法,以至高无上之神明“上帝”的地位、权势来影射周王,亦即携王余臣,写诸侯与王公大臣不敢、不欲、不愿朝王之事,进而自伤携王刑罚不中而放逐有功之臣。
上述23首怨刺天子的诗篇中,春秋前期(前770—前682)创作的有《扬之水》《中谷有蓷》《兔爰》《葛藟》《采葛》《鸨羽》《匪风》《沔水》《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谷风》《四月》《青蝇》《角弓》《菀柳》《采绿》《苕之华》《何草不黄》《瞻卬》等22篇,占96%;春秋中期(前681—前547)创作的仅《君子阳阳》1篇①关于笔者春秋时期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说,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9-11.,占4%。足见春秋前期怨刺诗主要怨刺对象为周天子。
这主要与当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以王权为中心密切相关。其具体特征主要有三:一是通过册立诸侯、策命孤卿、巡守诸侯、朝觐天子、遣使聘问等方式,天子对诸侯依然可以实施有效的政治控制②本文列举史实,除特别标注者外,皆出自《春秋》《左传》《国语》《论语》《礼记》《韩非子》《孔子家语》《史记》《列女传》《吴越春秋》,不再逐一标注出处。;二是王室依然具有号令诸侯的基本能力,天子依然可以主征伐,王室中央集权化统治形式得以延续;三是以郑庄公寤生为代表的区域性“小伯”,既想称霸于诸侯,又不能完全超越周王权威,自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维系王权的社会根基,王权在君权的严峻挑战中得以维系。故这一时期,无论是家父、凡伯、卫武公等王室公卿大夫类诗人,还是佚名周大夫、郑大夫、周暬御之臣、近侍之臣、乐工、士卒、晋国人等王室、公室贵族及平民类诗人,其怨刺的关注点都依然聚焦于先王幽王与时王平王、携王、桓王身上。
二 怨刺国君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此类作品凡66首,怨刺对象为诸侯国君,主要涉及桧仲、郑庄公寤生、昭公忽、卫庄公扬、宣公晋、惠公朔、懿公赤、灵公元、晋昭公伯、献公诡诸、惠公夷吾、文公重耳、齐襄公诸儿、景公杵臼、鲁庄公同、哀公将(蒋)、曹昭公班、共公襄、秦穆公任好、康公罃、陈灵公平国以及陈文公圉庶子公子佗(陈佗)、卫宣公太子伋(急子)、宣公夫人宣姜、鲁庄公夫人文姜等。就所怨刺的内容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一是国君失道以亡国,像《邶风·泉水》《王风·大车》《魏风·园有桃》《桧风·羔裘》《桧风·隰有苌楚》等。比如,《泉水》为许穆夫人自伤思归宁父母兄弟而不得之作。全诗四章:首章以泉水之得流于淇,兴己之欲归于卫;次章由出嫁女子思归宁父母兄弟而不得,回忆出嫁时别离母家诸姑姊妹之情景;次章与三章由设想若归卫时饯行之处,言愿疾至于卫,不远礼义之害;卒章言我作为卫女而今嫁于许,如肥泉之源同而分,然思母国而不能忘。足见诗人正是在赤狄(隗姓,属戎狄部族,疆域大致西临河、汾,东近齐鲁,南界卫郑,北接燕地)入卫的情境下,在自伤怨夫之情中,寄寓悼亡母国之哀。再如,《羔裘》为桧大夫刺桧国之君桧仲失道之作。全诗三章,每章前两句通过赋体笔法铺陈状写人物服饰,来描写桧君逍遥游燕的生活,反映出桧君失道的亡国之象;后两句则层层递进抒发诗人对这种亡国之象的伤感情怀,进而反映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又如,《隰有苌楚》为桧国人嗟叹国破家亡而民逃之作。全诗三章,分别以乐苌楚之“无知”“无家”“无室”,反兴人之有知、有家、有室而不乐。正是由于桧破民逃,国人莫不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莫不饱受妻离子散之痛。而导致国破、家亡、民逃之祸者,当然为桧国国君。故诗人自然要发泄对其的强烈不满。
二是国君无礼以乱政,像《召南·小星》《邶风·绿衣》《邶风·日月》《邶风·终风》《邶风·匏有苦叶》《邶风·旄丘》《邶风·简兮》《邶风·北门》《邶风·北风》《卫风·考槃》《卫风·芄兰》《郑风·子衿》《齐风·东方未明》《魏风·葛屦》《魏风·硕鼠》《唐风·杕杜》《秦风·黄鸟》《秦风·晨风》《秦风·权舆》《陈风·防有鹊巢》《曹风·蜉蝣》《曹风·候人》及逸诗《狐裘歌》(见僖公五年《左传》)《舆人诵》《恭世子诵》(皆见《国语·晋语三》)《龙蛇歌》(其一,见《吕氏春秋·介立篇》)《龙蛇歌》(其二,见《说苑·复恩篇》)《莱人歌》(见哀公五年《左传》)《浑良夫噪》(见哀公十七年《左传》)《责稽首歌》(见哀公十七年《左传》)等。比如,《绿衣》为卫庄公夫人庄姜伤己嫡妾失位之作。全诗四章:首章以衣之表里为色失常,喻妻妾之礼遇厚薄;次章以衣裳之上下为色失常,喻妻妾之尊卑颠倒;三章以汝治丝为绿衣,喻贱妾之得宠;卒章谓絺(细葛)绤(粗葛)本以避暑而今以御寒,喻夫人之失所。足见庄姜在自伤之情中,寄寓了怨刺庄公之意。再如,《芄兰》为卫大夫刺惠公初即位时骄而无礼之作。全诗两章,分别选取芄兰(萝藦)之枝(所结尖型荚子形似觿)与叶(下垂而向后微弯形似韘)起兴,言这位少年国君(时年十五六岁),虽是有成人佩觽、佩韘华贵外表的贵族少爷,实则为一个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的纨绔子弟。又如,晋舆人(隶仆之属)所作《舆人诵》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1]315此刺惠公许诺赐大夫里克、郑丕赂田以纳之为君,入而不予;许诺秦穆公以赂地以立之为君,入而背之;故自然会自取其咎,以致祸乱。
三是公室嫡庶相争而弱国,像《邶风·击鼓》《邶风·二子乘舟》《鄘风·鹑之奔奔》《郑风·将仲子》《郑风·叔于田》《郑风·大叔于田》《郑风·有女同车》《郑风·山有扶苏》《郑风·萚兮》《郑风·狡童》《郑风·扬之水》《郑风·出其东门》《唐风·椒聊》《唐风·绸缪》《唐风·山有枢》《唐风·羔裘》《陈风·墓门》等。比如,《邶风·击鼓》为卫伐郑士卒怨卫嬖人之子公子州吁弑其君桓公完自立后伐郑之作。全诗五章:首章言南行之事,次章言南行之故,三章写士卒消极厌战,四章写士卒相互约誓,卒章写士卒嗟叹。足见全诗描述南行远征异国之士卒,独留防守,因对死亡恐惧所产生出一种孤独感与焦虑感,而这正是由于公子州吁贸然发动“平陈与宋”的伐郑之役使然。再如,《大叔于田》为郑国人刺庄公故意放纵其母弟公子段(公叔段、大叔段、京城大叔)不义而得众之作。全诗三章,每章先写“叔”田猎于郊野时之善御,次写“叔”田猎于郊野时之善猎。诗人所赞美的这位本领高强、能骑善射、品貌出众、态度从容之“大叔”,正是封于京邑(郑大邑,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南二十余里)而欲夺其母兄庄公君位的公子段。所以,诗人在对“叔”表示崇敬与赞美时,在对其表露爱慕之意时,彰显出对庄公不教而诛的怨刺之旨。又如,《椒聊》为晋大夫刺昭公封其叔父公子成师(桓叔)于曲沃之作。全诗两章,分别以花椒树结出的一嘟噜花椒籽繁盛,谓公子成师大都耦国而厚施得众。足见诗人正是由泛指丰硕强壮而肌体丰满的妇女多子取义,进而专指公子成师子孙敷衍盛大,以刺昭公封桓叔于曲沃,其子孙必将有晋国。
四是国君荒淫以乱国,像《邶风·新台》《鄘风·柏舟》《鄘风·君子偕老》《鄘风·蝃蝀》《鄘风·相鼠》《齐风·东方之日》《齐风·南山》《齐风·敝笱》《齐风·载驱》《齐风·猗嗟》《陈风·东门之池》《陈风·东门之杨》《陈风·月出》《陈风·株林》及逸诗《娄猪歌》(见定公十四年《左传》)等。比如,《邶风·新台》为卫国人刺宣公烝其庶母夷姜(庄公妾,太子伋母)而夺其儿媳(太子伋妇)之作。全诗三章,分别以“蘧篨(蟾蜍)”“戚施(癞蛤蟆)”借喻年老丑陋、老而不死、贪色乱伦之卫宣公,谓我想嫁个如意郎却嫁了个丑老公,来讽刺卫国上层贵族贪恋美色、寡廉鲜耻之丑行。再如,《南山》为齐大夫刺襄公与鲁桓公夫人姜氏(文姜)兄妹私通淫乱之作。全诗四章:首章以高大的南山(即齐都邑临淄之牛山,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之上雄狐往复徘徊发兴,隐喻齐襄公淫其妹为鸟兽之行;次章以无论是贱者之服葛屦(麻布鞋)还是尊者之服冠緌(两条帽带下垂胸前之冠)都是上下各自成双发兴,隐喻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男女配偶成双亦当有别;三章以种植麻之田地需多次纵横熟耕发兴,言娶妻虽有父母之命,无补夫道之穷;卒章以无斧头则难以破木劈柴发兴,言娶妻虽有媒妁之言,无救妻恶之极。又如,《娄猪歌》为宋野人刺卫灵公为夫人南子(宋女)召宋公子朝(即宋朝,宋庄公冯庶子)之作。其歌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此以“娄猪”——发情求子的母猪喻南子,以“艾豭”——老公猪喻南子旧情人公子朝。当时,卫灵公为夫人南子召公子朝,适逢齐宋洮(曹地,即今山东省菏泽市甄城县西南五十里之桃城)之会,灵公世子蒯聩(庄公)献盂(卫邑,即今河南省濮阳市东南之敛盂聚)于齐,过宋都邑郊外之野,故宋野人作此歌以刺。
上述66首怨刺诗,春秋前期创作的有《小星》《绿衣》《日月》《终风》《击鼓》《匏有苦叶》《旄丘》《简兮》《北门》《北风》《新台》《二子乘舟》《柏舟》(《鄘风》)《君子偕老》《鹑之奔奔》《蝃蝀》《考槃》《芄兰》《大车》《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扬之水》(《郑风》)《东方之日》《东方未明》《南山》《甫田》《敝笱》《载驱》《猗嗟》《椒聊》《山有枢》《羔裘》(《唐风》)《墓门》《羔裘》(《桧 风》)《隰有苌楚》等40篇(为这一时期传世诗歌总数229篇的17%),占60%;春秋中期创作的有《泉水》《相鼠》《出其东门》《葛屦》《硕鼠》《绸缪》《杕杜》《黄鸟》(《秦风》)《晨风》《权舆》《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蜉蝣》《候人》《狐裘歌》《舆人诵》《恭世子诵》《龙蛇歌》(其一)《龙蛇歌》(其二)等22篇(为这一时期传世诗歌总数69篇的32%),占32%;春秋后期创作的有《子衿》1篇,占2%;春秋晚期创作的有《娄猪歌》《莱人歌》《浑良夫噪》《责稽首歌》等4篇,占6%。
由此可见,春秋前期诗人不仅聚焦于怨刺天子,同时也涉及国君;尽管春秋中期传世的怨刺国君之作绝对数量要比春秋前期少,但相对数量却比较多,表明这一时期怨刺聚焦点已由王权转变为君权,它们都是当时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即以霸权(君权)为中心的艺术再现。其主要特点有四。
一是周王室经历了惠王阆与其叔父王子颓、襄王郑与其异母弟王子带(叔带、大叔带、甘昭公)两次“二王并立”,王室内乱加剧,天子权威业已式微。
二是霸主在“尊王”旗帜下称霸,天子依然要采用赐胙与赐命方式认可了其天下诸侯“共主”地位,霸主依然得借助天子名义以获得像后世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载亮《隆中对》)一样的政治优势[2]912。
三是霸权逐渐取代王权,填补了王室衰微后形成的政治权力真空,彻底改变了西周以来构建的礼乐制度与政治架构,反映出社会关系与政治生态的巨大变化。
四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王室氏族宗庙政治开始解体,霸主所推行的霸政逐渐取代德政,不断冲击着西周以来构建的伦理政治观,为建立新秩序提供了政治基础。
故无论是许穆夫人、陈公子完、晋士蒍、舟侨及佚名卫大夫、晋大夫、秦大夫、陈大夫、曹大夫等公室中上层贵族诗人,还是晋介推、舆人、国人、魏国人、缝衣女、郑国人、秦国人等下层贵族及平民诗人,其怨刺的关注点都完全聚焦于包括秦穆公、晋文公这些诸侯霸主在内的国君身上。
三 怨刺卿大夫与礼乐征伐“自大夫出”
此类作品凡14首,怨刺对象主要为王室与公室卿大夫,涉及卫公子顽(昭伯)、孙蒯、郑高克、公孙侨(子产)、陈夏姬、周暴辛公(桓公)、鲁臧孙纥(臧纥)、季孙斯(桓子)、宋皇国父等。就所怨刺的内容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一是卿大夫专权以弱公室,像《郑风·清人》及逸诗《朱儒诵》(见襄公四年《左传》)、《采芑歌》(见《史记·田世家》)等。比如,《清人》为郑公子士刺其大夫高克危国亡师之作。全诗三章,分别叙写清邑(郑邑,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西)之师在彭、消、轴(皆郑地名,位于黄河岸边,今地皆阙)三地游戏而不归之情状。足见正是由于“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致使“文公恶而欲远之”(《清人》毛《序》),终于导致发生了“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闵公二年《左传》)的严重后果。再如,《朱儒诵》为鲁国人刺其大夫臧孙纥(臧纥)救鄫(一作“缯”,姒姓国,故城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七十余里)侵邾(一作“邾娄”又称“邹”,曹姓国,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而败之作。其歌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言鲁襄公幼弱(时年六岁)不能致国事,任凭大夫专征伐而自取败,致使国人逆丧者众多不能备凶服而皆髽(麻发合结)而已。故国人作此诵以怨刺之。又如,《采芑歌》为齐国人刺其卿士陈常(田常、成子)与公室夺民之作。其歌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3]1477起句以夸张修辞手法状写连妪(老年妇女)所采的芑菜(野菜名)皆归入陈常之家了,更何况其他贵重之物呢!以刺齐公室之政将归于陈氏之家。
二是卿大夫非礼以乱政,像《小雅·何人斯》及逸诗《子产诵》(见襄公三十年《左传》)、《丘赋歌》(见昭公四年《左传》)、《去鲁歌》(见《史记·孔子世家》)等。比如,《何人斯》为苏(己姓国,都邑即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西南三十里之故温城)君苏成公(一作“苏信公”)刺王室卿士暴辛公(“暴”为其采地,其地当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原武镇境)谮己以绝友之作。全诗八章,前四章极力描摹小人以谗言伤友之情形,五、六两章则直接诘责暴公过门而不入,七章今昔对比——昔日政治上的同僚、艺术上的同志、友情上的知交,如今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要出三牲来诅咒;卒章叙作诗缘由——“以极反侧”。足见诗人认为暴公谮己有违朋友之间人伦道德规范,故自己要与之绝交。又如,《丘赋歌》为郑国人刺公孙侨“作丘赋”(昭公四年《左传》)以推行田赋制度改革之作。其歌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此以“虿尾(蝎类毒虫之尾)”比喻郑执政卿公孙侨进行丘赋改革(在原有一丘,即十六井出马一匹、牛三头的基础上,再增加田赋),是以重赋来祸害百姓,必将会像其父公子发(子国)一样不得善终,表达了国人对郑国田赋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又如,《去鲁歌》为鲁司寇孔丘刺执政卿季孙斯受齐女乐而怠于政事之作。其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3]1502此歌先用一个对偶句,表达了对鲁季孙斯受齐女乐而怠政祸国的极度愤慨与担忧之情;后连续用两个感叹词“哉”,表达了在仕不遇后周游列国以度余生的坦然心态。
三是卿大夫残民以误国,像《魏风·汾沮洳》《魏风·伐檀》及逸诗《诅祝歌》(见襄公十七年《左传》)、《訽孙蒯歌》(见襄公四年《左传》)等。比如,《伐檀》为魏伐木者刺不劳而获的“君子”之作。全诗三章:首章以伐檀木发端,刺“君子”之“不素餐(白吃饭而不干事)”;次章言伐檀为辐(车轮中凑集于中心毂上的直木条),刺“君子”之“不素食”;卒章言伐檀为轮,刺“君子”之“不素飧”。足见此诗极力抨击贪鄙在位的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下层民人,属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宣公十五年《公羊传》何休注)之作。再如,《诅祝歌》为宋筑台者刺卿士太宰(总摄六府群职,在六卿之外)皇国父为平公筑台而妨于农收之作。其歌曰:“泽门之晳,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此将“泽门之晳(皇国父)”与“邑中之黔(乐喜)”两人进行对比,怨刺皇国父为平公筑台而妨于农功(收割庄稼),赞美执政卿司城乐喜(子罕)谏平公请俟农功之毕。此歌一“诅”一“祝”,表明了筑台役人对两类卿大夫的鲜明态度:怨刺嬖臣之媚君伤民,赞美忠臣之谏君爱民。又如,《訽孙蒯歌》为曹重丘(曹邑,当今山东省聊城市荏平县西南约二十里)国人刺卫大夫孙蒯饮马于重丘而毁其瓶(陶制汲水器皿)之作。其歌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此责骂卫卿士孙林父之子蒯,为何不去反思其父逐君之罪,反而越境至曹进行田猎?足见在国内专权之卫大夫,甚至损害到邻国国人的利益了。
四是卿大夫淫逸以乱家国,像《召南·江有汜》《鄘风·墙有茨》《陈风·泽陂》等。比如,《江有汜》为召南贵族弃妇哀怨自慰之作。全诗三章,皆以长江比兴其夫,以长江支流比兴其夫之新欢,分别表达望其夫能够悔悟之情,能够与己相安之意,能够与己相欢之愿。足见这位贵族弃妇在丈夫喜新厌旧而另觅新欢之后,依然幻想他能够回心转意而回到自己身边。其实,我们透过这位痴心女子惆怅伤感而哀怨自慰的心情,看出其对自己丈夫的怨刺情绪,进而折射出卿大夫淫逸以乱家的历史状况。再如,《墙有茨》为卫人刺齐人强迫公子顽(宣公庶子、惠公庶兄)烝于君母宣姜之作。全诗三章,分别谓以宫中闺门阴事“丑”“长”“辱”,故固不可率而言之,更不可夸张言之,尤不可公开诵言之。足见诗人怨刺齐人依然残存氏族社会群婚制或亚群婚制“烝”“报”婚姻遗俗,公然违背周代婚姻礼制,强迫公子顽烝其君母宣姜,进而折射出卿大夫淫逸以乱国的历史事实。又如,《泽陂》为陈大夫御叔妻夏姬侍女伤夏姬之作。全诗三章,巧妙地将客观物象组合在一起,来描写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宣公孙御叔之妻,夏徵舒之母)面如荷花、丰满高大、气质高雅的贵族美妇人形象;当然,在写其形“美”的同时,又写其情“伤”——夏姬之夫御叔早亡后,其沦为陈灵公与卿士孔宁、仪行父宣淫的玩偶,终于导致亡子丧国而自己成为楚囚的严重后果。
上述14首怨刺诗中,春秋前期创作的有《江有汜》《墙有茨》《何人斯》等3篇(为这一时期传世诗歌总数229篇的1.3%),占21%;春秋中期创作的有《清人》《汾沮洳》《伐檀》《泽陂》《朱儒诵》《訽孙蒯歌》《诅祝歌》等7首(为这一时期传世诗歌总数69篇的10%),占51%;春秋后期创作的有《子产诵》《丘赋歌》等2篇(为这一时期传世诗歌总数9篇的22%),占14%;春秋晚期创作的有《去鲁歌》《采芑歌》等2篇,占14%。
由此可见,此类怨刺诗春秋前期已经出现了,春秋中期已经非常兴盛,而尽管春秋后期传世的此类诗作绝对数量比较少,但相对数量则比较多,它们从一个层面展示出这一时期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即以族权(卿大夫)为中心政治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特别是中原诸侯国,公室卑弱而大夫专权现象非常普遍。就专权的卿族与公室的血缘关系而言,包括“公族”“同姓世族”“异姓世族”三种类型。其中,像郑之罕氏、驷氏、丰氏、游氏、印氏、国氏、良氏七族,为穆公庶子后裔别族为氏者,号称“七穆”,属公族共政,意味着公室小宗当了大宗的家。上述《子产诵》《丘赋歌》所怨刺郑正卿公孙侨,正是郑“公族”中“七穆”国氏宗子专权者。由于他在维护井田制度和村社制度的前提下,推行田制整顿与改革举措,开始实行国家授田制度,导致旧贵族“丧田”,以实物剥削取代劳役剥削,促使土地关系与剥削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仅承认个体生产者合法,而且赋予其作甲士的资格,使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客观上促进了族权经济基础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礼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自然会引起以士为核心的国人等下层贵族与平民阶层的不理解,甚至不满,遂作诗以怨刺之。
四 怨刺家臣与“陪臣执国命”
此类作品仅《南蒯叹》《南蒯歌》(俱见昭公十二年《左传》)《凤鸟歌》(见《论语·子罕篇》)3篇,怨刺对象主要为大夫家臣,涉及南蒯等。比如,《南蒯叹》为鲁费邑(季孙氏采邑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西北二十里)乡人怨刺费邑宰南蒯将叛季氏以如齐之作。其歌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当时鲁南蒯将叛季氏以如齐,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故作此歌刺其以家臣而图人君之事。再如,《南蒯歌》亦鲁费邑乡人怨刺费邑宰南蒯将叛季氏以如齐之作。其歌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当时,南蒯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作此歌以刺,表达了费乡人对南蒯以费叛季氏如齐表示极其失望之情。又如,《凤鸟歌》为鲁孔丘慨叹自己未遇圣王祥瑞之作。其歌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言圣人受命则有祥瑞之兆:凤鸟至而河出图(八卦);今为乱世,故己不得见,乃自伤时无明君而庶人议政。
上述3首怨刺诗,皆为春秋后期创作的诗篇,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阶段政治生态基本特征就是“庶人议政”。这一时期,除秦、楚、吴、越等少数诸侯国之外,绝大部分中原诸侯国的政治生态基本特征由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时代,进入“陪臣执国命”时代。这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来推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确立了封建制度。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家臣”取代“公臣”秉国政,二是“家族”取代“公族”而立国。就鲁国而言,家臣叛主现象,实际上早在阳虎(阳货)之前已经发生了,如叔孙豹庶子牛(竖牛)乱叔孙氏之室,季孙氏费邑宰南蒯以费叛,等等。就是在阳虎奔齐之后,这种现象依然持续发生,如叔孙氏郈邑(即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东南四十里郈亭之故郈城)马正(家司马)侯犯以郈叛,季孙氏费邑宰公山不狃(公山弗扰,子洩)以费叛,孟孙氏成邑(即今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东北九十里之故钜平城)宰公孙宿(成子)以成叛于齐,等等。可见,正是随着鲁君实力逐渐被削弱,而三桓势力却过于强大,三桓家臣的实力也随之迅速增强。故至春秋晚期,竖牛、南蒯、阳虎、侯犯、公山不狃、公孙宿等先后起来反对三桓,阳虎甚至一度执掌鲁国大权。这种政治变革自然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到平民阶层之类的社会生活。故鲁季孙氏采邑费之乡人作《南蒯叹》《南蒯歌》二诗来怨刺邑宰南蒯以费叛季氏如齐;而鲁孔丘作《凤鸟歌》正是在自伤未遇圣王祥瑞之情中寄寓了对“陪臣执国命”乱世的怨刺之意。
总之,春秋时期怨刺诗类型演化进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当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依然以王权为中心时,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天子身上;当由以王权为中心向霸权(君权)为中心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君身上;当由以君权为中心向以族权为中心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卿大夫身上;当由以族权为中心向“庶人议政”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家臣身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方面,政治生态环境为怨刺诗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客体,进而引导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渐次下移,直接影响了怨刺诗类型的演化进程,使怨刺诗由贵族化的庙堂文学逐渐转化为平民化的世俗文学;另一方面,怨刺诗作为政治生态环境的创作载体,并非是政治的附庸,不仅是政治的见证者,而且是政治的参与者,自然间接影响了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的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