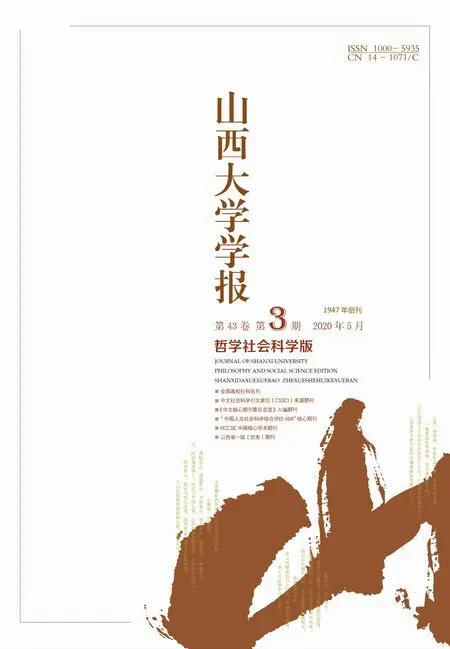全球化真的会削弱国家认同吗?
——已有研究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
殷冬水,张 婷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全球化是20世纪末世界发展趋势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建构、巩固和强化国民对本国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赖以维系国家统一、提升国家内聚力,提高国家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和管控风险的能力,增强国家能力的重要途径。[1]全球化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成为国家建构研究的重要议题,受到比较政治学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既有研究主要基于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视角,采用规范理论和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考察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使得“商品、服务、金钱、人员、信息和文化的跨境流动增加”[2],给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带来巨大的挑战。然而,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虽然在国家层面挑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性界限,但也重塑了主权性权力的现代性特征;虽然在个人层面提供了人们体验多个“自我”的可能性,但也强化了人们寻求身份归属的需求。显然,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明确了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存在削弱、强化和复杂化等三种关系,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为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提供了背景性知识。
一 全球化削弱国家认同之论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等学者基于全球化的流动性、同质性、多元性等特征,认为全球化进程削弱了民族国家塑造和维持国家认同的能力,打断了传统的基于领土的国家认同建构,增强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整体意识,使身份认同呈现出同质化、非领土化和分散化的新形式,这些新兴的身份认同会冲击甚至消解国家认同。
第一,全球化挑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性权力,削弱了民族国家塑造和维持国家认同的能力。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商品、服务、金钱、人员、信息和文化的跨境流动,深刻影响了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控制。在经济方面,跨国公司的兴起,削弱了民族国家对生产、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控制[3];在政治方面,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使政府不再拥有社会话语的垄断权[4];在文化方面,无线网络的普及,使政府越来越难控制公民[5]。在此意义上,民族国家的主权性权力受跨国公司、社会组织及全球性通信网络的牵制,主权的行使范围出现了重大变化。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削弱了民族国家塑造和维持国家认同的能力。从国家认同的需求角度来看,国家对政治实体控制力的下降,意味着弱化了民族国家在国内重新分配财富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这种冲击,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的危险,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难以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全球化在冲击民族国家的同时也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构成冲击;风险的全球化造成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抗拒风险方面的失效。”[6]当民族国家无法回应、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需求时,难免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消极影响。从塑造国家认同的权力关系来看,国家控制力及治理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国家的整合能力有所削弱。“全球化造成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7]国家的“空心化”给各种次国家组织提供了拓展“空间”的可能性,地方、族群或宗教等社会身份就可能诉诸“承认政治”或“差异政治”,鼓励民众另觅替代认同。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也在此意义上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是从现代社会及其制度的废墟中涌现出了生产、消费和通讯的全球化网络,另一方面是社群又回复了原状”[8]。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身份认同,如地方认同、族群认同、宗教和社群认同等分流和消解着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第二,全球化通过对多元身份的重塑,挑战了基于领土的国家认同。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使社会性的成分得到了复兴……无论是从地域上讲还是从观念上讲,民族国家都已不再能把社会性局限在它自己的疆界之内,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9]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人员的跨境流动,民族国家中出现大量多元身份的移民。例如,德国的土耳其人、英国的巴基斯坦人、美国的西班牙人和拉美人,他们通常生活在不同国家的领土之间。这些多样的族群身份超越了领土与身份之间同构原则和空间的纯粹原则,使得语言、习俗、信仰、种族等借以区分民族国家独特性的要素越来越相互渗透和影响,使民族国家的界限日益模糊。与民族国家外部“他者”的威胁性不同,内部的“他者”族群是在“污染”整个国家。[10]移民群体和外来族裔侵蚀着国家身份“内部”的统一性和真实性,社会成员对“同类”的感知变得日益混杂,对同质性国家身份的依恋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全球化构建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随着全球性的互联网社交的普及,人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远距离的和不同文化的他人进行互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扩大了他们对其他地域的认同,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认同偏好。
第三,全球化进程增强了个人的自我意识,转变了人们构建认同的方式。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教育的普及、信息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多样化,丰富和拓展了人们的物质性、认知性和社会性资源。随着这种客观存在性约束的消逝,人们的自主性意识也逐渐增强,诸如个人主义、自治等价值观念推动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自我价值来识别自己,而不是根据他们在特定领域群体中的地位来确定自己。人类的价值观“从集体纪律转变为个人自由,从群体整合转变为人类多样性,从国家权威转变为个人自治。”[11]王琰(Yan Wang)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rey,简称 WVS)(2010—2014)的数据,也从经验上证实了全球化加强了后物质主义,并更加重视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不是民族主义与安全。[12]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来自社会成员如何看待这种群体身份的价值或意义。社会成员可以同时通过性别、种族、文化等身份将自己进行归类。在这些社会身份中,国家身份依然强大,但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这些身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国家身份。劳伦·朗曼(Lauren Langman)认为里约狂欢节、美式橄榄球以及刺穿和纹身等极端身体变形,就是人们在荒诞的仪式中叙述和庆祝不同于传统政治和文化关系的自我身份。[13]在此意义上,人们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对身份的界定不再基于既定的社会角色,而更多的是依据自己对社会角色的主观认知和地位处境。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变化使得个人属性如专业知识、洞察力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家的历史传承和传统文化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14]在此意义上,身份选择的自由性所产生的个体认同的混乱,客观上削弱了国家认同。
第四,全球化强化了社会成员的整体意识,从超国家层面分流和消解着国家认同。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中,商品、信息以及文化的跨境流动,不仅为大众创造了统一的交流领域,而且让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大的集体身份。正如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说,全球化“既是对世界的压缩,也是对世界整体意识的增强”[15]。随着全球变暖、艾滋病流行、恐怖主义盛行等全球性治理问题的出现,不断强化了人们对生活在日益紧密的世界中的认识。在全球层面,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全球激进主义浪潮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政治共同体开始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得到重新想象,淡化了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促使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向超国家层面转变。“全球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高于传统和权威。因此,那些较多接触全球性文化的个人更偏向于认同那种,不强调地方性归属特征的公民形式的国家认同。”[16]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分析了1981年至2007年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欧洲价值观调查(EVS)的数据,涉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证实了超国家身份和国际公民身份正在增加的说法,指出社会成员的全球性经验与民族主义态度的弱化密切相关。[17]欧盟是地区性超国家共同体的一个典型代表。肖恩·凯里(Sean Carey)基于对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Eb)调查的分析,指出在当时所有的15个欧盟成员国中,欧洲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与对欧盟的支持水平显著负相关。[18]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同质性文化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符号,削弱了个人对当地区域和民族国家的依恋。例如,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治理需求提出“普世伦理”认同,诱导和消解着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
二 全球化强化国家认同之论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等学者认为,全球化对国家认同并非完全是一种消极力量。他们从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强调了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积极意义。在国家层面,全球化进程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与经济发展,为塑造国家认同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在个人层面,全球化的流动性与多元性强化了社会成员对身份归属的心理需求。他们认为,全球化虽然给主权国家带来了国家认同的挑战,但也创造了构建国家认同的发展空间。
第一,尽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诸如欧盟之类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但民族国家依然是现代社会中塑造认同的主体性力量。一些学者认为,首先,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并没有被全球性趋势取代,反而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从1980年的157个增加到2018年的197个。其次,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并没有丧失权力,只是转变了民族国家的权力中心。“权力并没有从国家转移,而是在国家内部转移,即从工业或劳动部转移到经济部和中央银行。”[19]再次,全球化重新定义了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的现代特征,强化了民族国家塑造认同的能力。尽管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的全球化流动突破了领土的界限,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国内网站上浏览和观看烙印着民族国家印记的节目。塔玛·阿舒里(Tamar Ashuri)调查了关于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的电视纪录片在英国、美国和以色列的播放方式,结果表明,每个国家的电视台都对该节目进行了调整,使其更适应本国特殊的国家话语和情境。[20]
既有的研究也从实证角度证实了,即使在国家主权性权力发生变动和多种形式的身份政治出现的背景下,以民族国家界定身份仍然是人们理解自己和他人的主要方式。例如,马可·安东尼斯(Marco Antonsich)基于对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Eb)的数据分析了二十年间西欧4个地区民族国家依恋的演变,指出这一期间西欧的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依恋也呈现稳定趋势。[21]荣格(Jung)使用 1981年至2001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分析了43个国家中普通公民在二十年间对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的态度变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指出虽然年轻一代确实保持了更高比例的超国家认同,但是这种态度不会贯穿其一生,生命周期的变化使得,期望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际化态度和超国家身份会大大增加是一种神话。[22]罗伊·戴维森(Roei Davidson)等人使用同一组数据分析了全球精英的两个变体,即世界主义者和资本家的超国家认同取向,得出了类似的推论:全球精英所持有的超国家依恋是暂时的,并非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增加,并没有证据表明全球正在朝着超国家认同的方向发展。[23]
第二,全球化促进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塑造国家认同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一些学者认为,从社会认同的需求角度看,社会认同的产生与人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密切相关。“公民个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取决于国家满足领土内居民基本社会需求,保护与发展公民基本权利的程度。”[24]在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资料、技术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促进了民族国家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意味着国家有能力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和安全需求,有能力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使“个体行动者对对象世界连续性和社会活动构造抱有信任感”[25],增强民众对国家的满意度,从而显著提升个体对于国家认同的程度。
人们物质生活与生存条件的满足与国家认同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迈克·莫里森(Mike Morrison)等人通过分析128个国家样本,指出在人均GDP越高、日常生活越便利、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国家,人们对国家的满意度越高。[26]因此,全球化为人们带来物质生活与生存条件改善的同时,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的认同。
第三,全球化的流动性和多元性突出了民族的独特性,强化了人们寻求身份归属的需求。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流动多元性消解了一些惯常的生活情境,无论是在区域还是在民族国家,不确定的社交网络使传统身份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流动的空间逻辑”下,个体对“追寻根基”“划定边界”的意愿比以往更为强烈。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的心理归属感,是通过感知自己与其他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来实现的。民族国家是承载着人们集体记忆、文化、历史和文明的最重要的实体,蕴含着“有力的故事和信念”,传达着一种不同于全球化流动的空间逻辑的安全、稳定和简单的图景。个体在不断追问“我是谁”,反思国家的意义和功能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了自我的民族独特性。[27]因此,尽管全球化的新技术压缩了世界的空间,弥合了陌生人在空间上的距离,但当所有人都处于匿名的、原子化、扁平化的空间位置时,具有同一民族特性的人们之间往往会建立、维护并加强联系。“全球化并没有终结民族主义,没有终结民族主义冲突,也没有终结民族主义范畴在组织普通人在世界上寻求归属感中的作用。”[28]例如,泰纳(Tyner)和库尔克(Kuhlke)通过分析散居全球的菲律宾侨民所建立的54个网站,发现互联网和在线社区可以帮助菲律宾侨民与自己的祖国保持多种联系,并促进菲律宾泛民族认同的建立。[29]沙维特(Shavit)对欧洲的年轻穆斯林的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互联网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工具,被用来加强宗教和民族联系。[30]因此,他们认为,随着对象的流动性的提高、认同的多元化,人们对国家的依恋感并不会减少。虽然全球化可能将特定国家的部分人口推向世界主义,但其他部分人口将结成“抵抗身份纽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感不是国家塑造的结果,而是个体自我反思选择的产物。
三 全球化使国家认同复杂化
罗伯特·库诺维奇(Robert Kunovich)、加尔·阿里利(Gal Ariely)等学者则认为,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线性关系,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弱化或强化的关系。他们基于国家认同的具体内容和情感倾向、全球化水平、民族构成及族际关系以及各国的结构性情境,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在国家认同的内在属性、生成渊源和变迁动力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考察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关系时不能依据其中的某一因素就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第一,全球化到底是削弱国家认同还是增强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具体内容和情感倾向有关。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描述的是社会成员对自己国家的感情强度和亲密程度,可以体现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中不同方面的心理维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国家认同应该考虑到认同内容和情感取向的多维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认同的内容来看,每个人的国家认同都包含着民族属性(ethnic attribute)和公民属性(civic attribute),只是在程度和形态上存在差异。①参见:Smith A D.National Identity[M].London:Penguin,1991;Jones F L,Smith P.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in National I-dentities: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Patterns[J].Journal of Sociology,2001(37):45-63;Shulman,Stephen,Challenging the Civic/Ethnic and West/East Dichotomies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2(35):554-585。前者的国家认同形式中,公民的政治自豪感与血统、种族或文化背景相关;后者的国家认同形式中,公民的政治自豪感与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和社会福利制度相关。从认同的情感倾向来看,公民的国家认同可以区分为盲目的(blind patriotism)与建设性的(constructive patriotism)。[31]前者是一种对国家不加批判的忠诚,体现了国家认同感中感性的、盲目的和服从的一面;后者是一种质疑性的国家依恋,体现了国家认同感中理性的、批判性的和不服从的一面。需要注意的是,认同的两方面内容和情感的两种取向都呈现出一种正交关系(orthogonality),两者的区分在于,个体在国家认同的心理边界上的侧重点不同。[32]
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基于对国家认同不同维度和范围的划分,设计了不同的问题作为测定公民国家认同程度的指标。例如,巴塔尔(Bar-Tal)和斯托布(Staub)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国家的依恋表现为归属感、热爱、忠诚、自豪和对群体和领土的关心。[33]埃尔达·戴维多夫(Eldad Davidov)和罗伯特·库罗伯特 (Robert Kunovich)把对国家的依恋感、优于其他国家的感觉、对国家的自豪感、族裔观念以及对国家的忠诚程度等方面,作为衡量公民国家认同感的指标。①参见:Davidov E.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N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in the ISSP:34 Countri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Political Analysis,2009(17):64-82;Kunovich R.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9(74):573-593。他们认为当个体对描述特征词进行等级评定时,可以表明公民更赞同国家认同的哪种成分,以及公民为支持这一内容而具有的情感倾向,进而证实全球化与不同维度的国家认同的关系。例如,罗伯特·库诺维奇(Robert Kunovich)分析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I(2003)中31个国家/地区的国家认同模块的数据,指出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中的民族属性负相关,与国家认同中的公民属性正相关。[34]加尔·阿里利(Gal Ariely)分析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03)及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05)中63个国家的数据,指出全球化的影响并没有削弱人们对国家的依恋感和民族主义态度,但确实削弱了他们的族裔观念,降低了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和忠诚程度。[35]埃尔达·戴维多夫(Eldad Davidov)分析了22个国家在ISSP统计中1995和2003年的数据,指出在过去9年中,有8个国家的理性爱国主义显著提高了,有7个国家的感性爱国主义显著降低了。[36]
在此意义上,他们认为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的某些方面正相关,与某些方面负相关,与其他某些方面无关。那些将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归为弱化或强化关系的产生矛盾性结论的研究,只是关注和测量了国家认同的某些维度和范围。
第二,全球化到底是削弱国家认同还是增强国家认同,与国家的全球化水平有关。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涉及人员、信息、思想、资本和货物的相互联系,但各国在市场、政府政策、思想等元素相互依存、全球性流动的侧重点及程度具有差异性。因此,在全球化的发展层面上,可以分为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发展程度上,可以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证研究中,研究人员编制了几种全球化指标,例如,科尔尼(A.T.Kearney)咨询公司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编制的科尔尼外交政策全球化指数(A.T.Kearney/Foreign Policy Globalization Index)、马滕斯(Martens)修正后的全球化指数(MGI)、新全球化指数,以及瑞士联邦苏黎士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的KOF全球化指数(KOF Globalization Index)等。这些全球化指标尽管在概念和度量上存在差异,但都高度相关。其中,KOF全球化指数单独显示了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的数据,通常在实证研究中被用作考察全球化水平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罗伯特·库诺维奇(Robert Kunovich)采用KOF全球化指数分析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03)中31个国家/地区中国家认同模块的数据,表明了全球化3个维度对公民国家认同形式的差异性影响:在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国家程度较高的国家,人们公民属性的国家认同比民族属性的国家认同程度更高。其中,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很难评估它们对国家认同的独特影响。而在政治全球化国家,人们在公民属性和民族属性的国家认同上差异不显著。[36]哈德勒(Hadler)和迈耶(Meyer)利用了KOF全球化指数分析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5)和 II(2003)中 44个国家的数据,指出不同的全球化指标与公民对国家边界政策态度的差异性。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INGOs)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数量(IGOs)都是列入KOF衡量全球化的一个指标,但是前者与人们强调国界的意愿负相关,后者与人们对国界的态度无关。[37]加尔·阿里利(Gal Ariely)在第六轮和第五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以及2008年欧洲价值调查(EVS)的数据中,抽取了138个国家/地区的89个国家样本的跨国调查数据,用KOF全球化指数来度量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程度,检验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程度与个人的国家认同及全球认同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的消极关系更显著;在全球化指数变动较大的国家中,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的消极关系更显著。[38]因此,他们认为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讨论的是何种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何种指标下的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和稳定性。
第三,全球化到底是削弱国家认同还是增强国家认同,与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有关。一些学者认为,认同是自我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国家认同不仅关涉个体对某一国家(nation)的认同,也涉及“我们”与“他者”的区分,只有通过界定“他者”,国家认同这一术语才有意义。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常在感知到群体地位或价值受威胁后调节自身的社会认同。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趋于多元化,族际关系日益复杂,“族群”是形成“他者”最为常见的形式。
一些学者考察了族群规模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中的公民作为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不同。吉姆·西德尼乌斯(Jim Sidnius)等人评估了美国的四个族群: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的学生的族群依恋和国家依恋,指出在国家处于支配地位的族群中,个体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在从属的民族中,个体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呈现负相关关系。[39]克里斯汀·斯塔克雷(Christian Staerkl)等人通过分析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03)中33个国家中不同规模的族群的国家依恋感,也证实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公民作为多数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感显著高于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感。[40]
一些学者考察了“他者”威胁性来源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个人对“他者”的威胁性感知是源于群际内部还是群际外部,对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选择不同。贾辛斯卡娅-拉提(Jasinskaja-Lahti)等人以来自原苏联的293名芬兰移民为被试对象,并历时8年对其行为选择进行的追踪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当原苏联裔感知到源于芬兰外部的威胁时,会强化对芬兰的国家认同;而在感知到源于芬兰内部族群的歧视或威胁越多时,他们的族群认同越高,而对芬兰的国家认同越低。[41]贾辛斯卡娅-拉提等人认为在面临群际内部的排斥时,族群会通过提高群体认同来缓解群际威胁所带来的心理伤害,在行为上与其他群体保持距离,不愿融入主流社会,从而阻碍了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同时,源于群际内部还是群际外部的威胁,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不同。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等人将阅读不同内容新闻的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为实验组呈现“9·11”恐怖袭击新闻,为控制组呈现哥伦比亚大屠杀新闻。结果表明,被试者在感知到外部威胁时,比对内部威胁的感知,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国家认同。[42]事实上,族群规模及个体对威胁性力量的感知,体现了地方认同、国家认同与超国家认同相冲突的一面。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多重社会身份共存的可能性,将超国家依恋理解为“公民”对不同地域的依恋性,这种依恋感可以从地方、国家延伸到全球。超国家身份的这种多重性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超越,而是它与地方和国家身份的共存,将其称为“嵌套身份”。“由于全球化,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发展出一种双文化身份,其中一部分身份根植于当地文化,另一部分则源于对与全球文化关系的认识。”[43]梅德拉诺(Medrano)和古铁雷斯(Gutirrez)通过分析西班牙民众的话语,指出在西班牙,民众以非常积极的方式构架了欧洲身份,并没有与国家或地区的身份相冲突。[44]因此,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必假定区域、国家和超国家身份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公民可以维持自己的地方性或国家认同,同时又具有越来越多的超国家依恋感。
第四,全球化到底是削弱国家认同还是增强国家认同,与各国的结构性情境相关。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基于对国家认同内容的区分,认为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存在公民属性和民族属性的国家认同形式,但这两种属性的比重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所以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不同个体的显著性和影响力也有所不同。例如,斯蒂芬·舒尔曼(Stephen Shulman)选取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中15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并将这些国家分为西方和东方两个部分。①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荷兰、挪威和瑞典被归为西方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被归为东方国家。德国依据东德和西德的划分将其放入西方和东方两个部分。通过分析社会成员对国家成员标准和对同化、移民等国家政策的态度,证明了东西方国家认同的差异。他指出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国家”的西欧国家的人民更倾向于国家认同形式中的民族属性,而通常被定义为“民族国家”的东欧国家的人民更倾向于国家认同形式中的公民属性。[45]加尔·阿里利(Gal Ariely)分析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03)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05)中63个国家的理性爱国主义,也证实了理性爱国主义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族群身份认同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35]482一些学者从个人层面的特征,如公民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微观因素解释了这种差异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这些因素实质上受制于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因而将这种差异性归因于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是体现了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因此,不同因素对不同国家、不同个体的显著性和影响力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情境极其复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此意义上,在考察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关系时不能依据全球化对某一或某些国家的影响状况推及为普遍性结论,需要考虑到特定国家具体的结构性情境。
四 结语
通过梳理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既有的研究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解释。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公民的全球化经历会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如诺里斯(Norrris)和英格哈特(Inglehart),但另一些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荣格(Jung)。这种差异性,一方面源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出现了线性解释和多元解释的差异。既有的研究中主要采用规范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规范理论研究通常基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全球化等相关理论,得出线性的推论性结论。实证研究则主要基于问卷调查、田野调查进行量化的、跨国的比较研究。通过编制不同的测量指标,实证研究可以关注到更为微观的影响因素。同时,在实证研究中,被试者通过对问卷中的描述词进行排序或评级,可以在微观层面呈现出不同变量影响程度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源于理论预设的不同,出现了冲突甚至矛盾性的解释。在规范理论研究中,研究者由于对全球化、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和范围的侧重,会得出一些不一致的推论。在实证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采用KOF指数来衡量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程度,采用了诸如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National Identity,简称 ISSP)、欧洲晴雨表调查(Eurobarometer)、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 WVS)、欧洲价值观调查(European Values Surveys,简称EVS)等调查问卷,这些调查项目中都包含着全球化和国家认同的有关数据,但各个调查项目对其测量指标和具体的提问方法不同。事实上,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究者对变量的选取,对测量指标的编制的不同,也反映了关于全球化、国家认同的不同理论预设:全球化是现代性向全球范围的扩展还是新时代的开始?国家认同是社会建构的还是历史建构的?如果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性延续,那么全球化的程度和国家认同的水平可能都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结果;如果全球化不同于现代性,那么全球化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可能是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国家认同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公民的身份认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如果国家认同是历史建构的,那么公民的身份认同体现在根基深厚的民族传统中。
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国家认同的建构涉及我们如何界定全球背景中的社会、经济和权力关系,以及我们如何理解世界范围内认同、忠诚和归属的含义。我们也看到,在真实的政治世界中,影响某一变量的因素很多,既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变量归为全球化影响的结果,也不能将这些变量进行简单的累加,形成对各国民众国家认同的解释。深入理解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需要处理好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与宏观层面的理论统合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