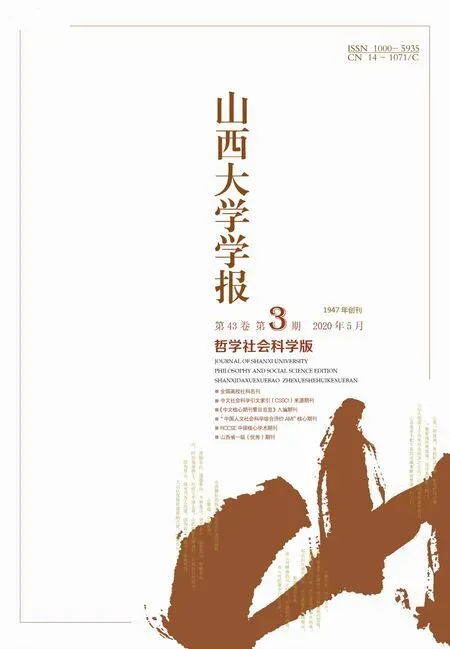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中国”想象
温庆新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作为近代学制变革与学术变迁重要缩影的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其编纂不可避免要受近代趋时求变的动荡时局与“中西交通”的复杂环境所影响。有鉴于此,探讨以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如何通过“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来回应彼时“中西交通”的学术冲击,进而分析时人如何借助编纂中国文学史的方式来进行文化自信的建构,便有了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此类探讨有助于深入了解20世纪初期的学术史衍变。
一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想象“中国”的意图与方式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的异样编纂态度及其意图导向,使各自在想象“中国”形象时的话语使用和阐释架构,往往会形成不同特色。这就涉及“想象”与知识的关系,意即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对“中国”的想象,必然建立在当时现有的各种知识条件的控制上[1],通过由各种学识所提供的“想象”,使得他们的“想象”过程必然涉及以什么方式展开和想象的目的两大方面。也就是说,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编纂文学史的两种主要探究工具——受到知识制约的“想象”与通过“想象”而具有丰富意义的知识,将会决定什么样的材料能够进入文学史视域,以及使用相关材料时的加工方式。
而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存在的主要身份是教材,其直接导向的是彼时的课堂教学之用。林传甲就明确指出所编纂《中国文学史》系“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故而,必然要符合“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2]的相关要求。此举正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十六篇第十八章“国朝骈文之盛及骈文之终古不废”所指出的:“今中国文学,日即窳陋。古文已少专家,骈体更成疣赘。湘绮楼一老,犹为岿然鲁灵光也。传甲窃谓泰西文法,亦不能不用对偶。见赫德辨学启蒙。中国骈文,亦必终古不能废也。特他日骈文体之变体,非今日所能豫料耳。文者国之粹也,国民教育造端于此。故古文骈文,虽不能如先正之专一,其源流又何可忽耶”[3]209-210。林传甲试图通过对历代各种文学样式的源流梳理及其知识的合理定位,来突显能够进行教育启迪的“国之粹”作品的重要价值,从而为彼时的教育提供反映历代“中国”形象衍变的历史凭藉。黄人《中国文学史》作为教会学校东吴大学的“国学课本”[4],则试图基于“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来求得“中国”历史的“既往之因,求其分合沿革之果”[5]3。黄人甚至指出:“文界不无间接影响于政界之事,然必政界之现势,有以启之,文界仍为助因”[5]15,以强调“文界”应对“政界之事”进行呼应。此类认知使得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无法回避彼时教育启智的时代呼吁与受动荡时局左右的现实,从而必须以积极的态势回应教育启智的本质与时代需求所提出的民族富强、国家兴盛的话题。这就导致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进行“中国”想象的直接意图与重点,主要集中于如何在“中西交通”的背景下进行“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自信建构,想象历代文学史中可以展现民族文化与国家形象的精神特质的文本证据,来建构相应的历史经验,以便确立在中西文化相交汇时能突显国家自信与民族自强的学术诉求。
那么,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是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中国”想象的呢?
(一)黄人《中国文学史》:“作为进步的历史”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代文明视域中的固定化思想理论而展开的。即黄人以世界向前进步及关注人类的视角为中心,并认为“就我国现象之一二部观,非特不进化,且有退化者;统全局论之,则进化之机固未尝少息也”[5]4,由此基于“作为进步的历史”的角度来建构中国文学史中的“中国”形象。在进化论的刺激下,黄人首先以“历史”上专制、腐朽的国家形象作为反面教材而试图想象彼时社会发展、民族命运等现实所需要的“国家”之内涵、形象及应当隐含的实际意义。它是一种从“外部世界”的角度,以中国历代文学的衍变史迹为切入视角,来看待“中国”在彼时世界化、近代化过程中所存在的弱项与缺点。比如,黄人在《中国文学史》“文学之目的”中,认为文学“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5]故而,黄人希冀能藉此“谋世界文明之进步”,进而实现以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来探求历史“兴衰治乱因缘”的意图。此类编纂主要为了试图改变时人“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风,多美此而剧彼,初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5]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重新建构“中国”形象,不仅有助于改变时人好高骛远的局限,而且能够使中国文学史著述充分发挥起“俾国民有所称述,学者有所遵守”[5]3的典范意义。所谓“使‘国民有所称述’,指的便是文学史可以为国民提供一个有关国家文学的叙事。”[6]由此,黄人试图从“进化之公理”的角度梳理历代文学作品中“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的部分,以书写“国史”的态度来编纂文学史,从而展现历代文学中“中国”形象的进步之一面;同时,试图纠正“国民好大迷信之习”等“不诚”的“社会之弊”,以此描写历代作品中“去不诚而立其诚者,则有所取鉴而能抉择”的作品,[5]5从而称赞历代文学中“中国”形象的不断自我完善之一面。
在黄人看来,“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5]4。故而,其在《中国文学史》中进行的“中国”形象建构,是一种以探索者且自觉地带有某种“求富强”的心态,来重构当时国家与社会发展所需的新的话语体系。这是黄人在与西方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的对比与思考之后所做的抉择。如黄人认为历代“文学全盛期”出现的重要原因,在于“冲决周公、孔子以来种种专制之范围,人人有独立之资格,自由之精神,咸欲挟其语言思想扫除异己,而于文学上独辟一新世界”[5]12,积极肯定历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独立、自由且积极向上的“中国”形象的重要价值,从而使得其基于历代文学作品而想象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指向明确的意义联结与积极向上的形象特质。《中国文学史》第二篇《略论·文学之反动力》更是指出“民贵君贱之陈言,至异族为主而始悟;自由平等之新理,与他人入室者偕来。白日青天之招揭,而大厦已倾;风云沙线之分明,而全舟将覆。言语思想,虽超乎九天之上,而种族社会,旋陷乎九地之下。区区新文学界,必以国界为交易,乃仅得之,其代价不过昂乎?”[5]20强调不能因“异族为主”与“他人入室”等“以国界为交易”而后才换来“新文学界”,而应超越“种族社会”的种种桎梏,以便在历代文学作品中详细揭示“民贵君贱之陈言”与“自由平等之新理”等进步思想的当下意义。
这种做法是在彼时的世界知识秩序下,以西学知识来反思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在当时的指导价值乃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适应问题。如果说侧重历史进步的做法使时人更多看到了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乃至促使时人产生深刻危机意识的话,那么,侧重进步的历史记忆的描述方式,将更看重“中国”悠久且辉煌的历史及其对当下的启示价值。此举是试图以历代文学的反面形象来唤醒时人的思想觉悟,故其反复强调需要知晓历代文学的衍变,以“示之文学史,俾后生小子,知吾家故物不止青毡,庶不至有田舍翁之诮,而奋起其继述之志。”[5]可见,黄人想象“中国”的最终意图,是以“人”促情,以唤醒时人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自信感,希冀时人能走出“黄祸之说”的心理阴影,进而达到“示以文学史,庶几知返”的目的。[5]4-5表面看来黄人是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增进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深层看来他们在强化国家认同感的同时,已产生了抵斥“西学”知识的情绪,甚至滋生了一种潜在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从而带有近代中国早期民族文化保守派的影子。故而,黄人又说:“西方之有远识者,亦颇服膺我国之旧伦理,他日儒墨两家,必有为全球宗教、教育、政治之一日”[5]121。
所谓“颇服膺我国”云云,使用了一种极具国家自豪感的词汇,以此表达中国旧有伦理观念具备随时进行自我更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品格,其间蕴含着民族自强的心态与信心。可见,黄人《中国文学史》试图以历代文学的衍变史迹为线索,向时人展现一种需要在与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视域下对落后、腐朽的国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以便确立既能承继儒家经典传统又可适应当下民族自强所需的“中国”形象。
(二)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作为历史的记忆”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则试图塑造一种“作为历史的记忆”之国家形象,而且,更多体现于一种历史缅怀、甚至沉浸于历史记忆之中的形象再现。正如林传甲自言其所编纂《中国文学史》的策略是“甄择往训,附以鄙意,以资讲习”。所谓“甄择往训”是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为指导的,故而其直接导向则系“练习文法之用,亦教员之义务,师范必需之课本”。[3]1此类导向就决定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历代文学与学术的梳理与建构,必然呈现出一种简单的历时性文献堆砌。亦即促使林传甲势必将书写重点放在能够深切“往训”的历代作品之上,以见“国朝文学昌明”[3]24之意。由此形成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文学”(即杂文学观)与学术的衍变历史为书写重点,进而试图呈现历代“中国”纷繁复杂演进过程的话语建构体系与形象展现的聚焦范围。“国朝文学昌明”云云,就试图推动彼时学生能够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促使学生从“昌明”的文学作品中深切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此暗示或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
虽然林传甲划分小学、史学、文章之学、群经之学等若干类别来进行“中国”历史演变源流的概述,但上述若干类别的概述落脚点仍集中于历代“文学”之关于经世致用与利于教化的焦点上。比如,第四篇“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就以“治化”与“世运”为中心,详细勾勒出历代文学作品中有关“治化为文”的情形,以说明“治化词章并行不悖”,认为:“治化出于礼,词章出于诗,孔子之教子也,以学诗学礼并重”,而“中国杂识武弁,多不识字者,外人恒见而非笑之,良由词章之士,务艰深而不务平实也。日本明治维新,说者谓其黜汉学而醉欧化。今读其战争文学,见彼陆海师团、走卒下士,所为诗歌,或奇崛如李,或雄健如杜。中国词章之士,苟读之而愧奋,中国庶几中兴乎?”[3]51由此,林传甲认为是可从历代“文章”中窥探“中国”的民族气节与国家形象的。第十二篇第十章“光武君臣长于交涉之文体是以中兴”,亦指出:“光武御制之文:《敕冯异》《报隗嚣手书》《赐窦融玺书》《与公孙述书》。观其驾驭英才之略,周旋列强之际,庙算明远,交际文牍之最优者也。读《窦融责让隗嚣书》,见事勇决,措辞英敏;马援《与隗嚣将杨广书》,婉语周详,陈义恳切。《朱浮与彭宠书》,谕以大义,动以利害,雄快劲直,耸然可听。《班彪乞优答北匈奴奏》,则深沉有大略,不愧为应变之才矣。光武既明于外交之道、和战之机宜,又得诸贤以佐助之,其致中兴也宜矣。其内治之整饬,如桓谭之《上时政疏》、杜林《论增科疏》、张纯《正昭穆疏》、郑兴《日食疏》,大旨重本抑末,尊祖敬天。其文皆泽以经术,有渊古之色,亦见中兴之气象矣。”[3]149-150即是强调可从历代君王与群臣的“文章”中品悟出相关作品所意图弘扬的“中兴之气”的国家形象,以使汉代能够“周旋列强之际”而获得“庙算明远”的历史训诫。在林传甲看来,正是由于历代“文章”所蕴含的文学精神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求真诉求,使得历代“文章”所体现的“中国”形象过于柔软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中兴。这种聚焦亦是基于与诸如日本等域外“国家”的向上形象的比较中获得的。林传甲认为正是明治维新才促使日本走上中兴之路,而日本的中兴之路又促使其“战争文学”等作品中的文风与形象充满阳刚与向上之力。因此,林传甲认为可以通过对历代“文章”的“治化之力”的梳理,来展现历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之弊,并最终起到发人思进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林传甲在梳理历代“文章”的衍变时,一方面要排列出书写柔软“中国”形象的作品及其弊端,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历代“文章”对国家形象的刻画亦需有与时俱进之一面。这种强调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及落脚于“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的育人立人目的——如第六篇第十八章“论事文之篇法”云:“论事之文,于科学为近。东人于奏疏亦归之此类,不归之治事类为协也。日本拙堂之言曰,叙事如造明堂辟雍,门阶户席,一楹一牖,不可妄为移易;议论则如空中楼阁,自出新意。但拙斋谓宜先学论事文为便,鄙意则以为习纪事为便,而治事文尤为切用。敢质之海内外教育家,以为何如”[3]77。由此促使林传甲主要梳理历代文学作品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基本史实,并以批评的态度待之。这就导致其更多导向于展现历代文学作品中“作为历史的记忆”的国家形象。“甄择往训”云云,即是此类想象思路的典型。
甚至,前文所言林传甲强调对历代各种文学样式的源流梳理及其知识的合理定位,希冀以此类文本来突显能够进行教育启迪的“国之粹”作品的重要价值。凡此种种,表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进行“中国”想象时,更侧重对文学基本知识的梳理,促使时人全面了解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的衍变脉络,从而以忠于历史的态度,向世人展现突显教化式国家形象的历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国之粹”的当下意义。此举试图将历代文学作品视作知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导致其著所描述的并非文学活动的内部关系与影响研究,而是在“甄择往训”的国家认同感下,将历代文学作品置于提高时人爱国认知等教育启迪中,进行知识的重组与文学价值的重构。
统而言之,相较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而言,黄人《中国文学史》更强调国家形象作为中国历史衍变进程中的主体“身份”,及其对中国文学史衍变的重要影响。它最终有助于引起时人基于特殊时局而在阅读文学史著述的过程中、抑或在课堂教学的施行环节中,增加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可,从而增强对“中国”之“身份”的认同。而对“中国”之“身份”的认同,并非一定要强化中国历代文学史中的“爱国”题材,而是强调历代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进步的方式,不断凸显“中国”的国家形象如何冲破封建专制的藩篱而适应彼时社会变革所需的原素。此举有助于将“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与彼时社会的“中国”形象乃至基于彼时特定文教环境而想象的“中国”形象,三者放在同一条平行线上,以便清楚发现“中国”形象的历史内涵、现实价值及未来意义。这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国家构建自我形象及获得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故而,此举导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在想象“中国”形象时,必然强调历代“中国”形象的柔弱之处以及柔弱之后的涅槃重生。由此,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往往被塑造成缺陷与奋进并存的面貌,亦即一种缺失了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的缺陷描述及其如何奋起改变的自励过程。它试图以历代文学作品所独有的文本形式及相应的文字记载方式,对“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加以知识学的书写与形象概述。而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如何富强的话题,则随编纂者的自我认知而呈现出想象与建构的差异性。黄人《中国文学史》就曾说“我国之学,多理论而少实验,故有所撰著,辄倾向于文学而不自知。”[5]3因此,黄人等人认为以历代文学作品所描绘的“中国”形象为基础,将能够改变“我国之学,多理论而少实验”的缺陷,从而最终在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中,以直观且感性的触摸方式来详细获知历代“中国”的形象。从这个角度讲,民族自强的呼吁与文明进化视域下的“中国”想象相结合,成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建构“中国”及其“形象”历史意义的“范式性例证”[7]。可以说,从想象“中国”形象的不同侧重点及其差异性,可以发现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因对国家形象的异样期待与民族命运的不同预估,使得编纂者有关“中国”形象的想象往往伴随着建构思路,呈现出两大演进路径:或是对“中国”的国家历史形象的再现与批判,或从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国家形象塑造的可能内容与实践方式来建构未来的国家形象。
二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想象“中国”的影响因素与呈现面孔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往往将教育启智、“代表文明之要具”等塑造人心向善的文学史纂修意图,与“中国”的形象及其职责联系在一起进行书写,以便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建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历代文学作品中有关“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历史衍变情形的分析与组合,来实现建构国家自豪感与历史认同感的目的。[8]黄人就曾说勾勒历代文学作品的终极导向是“使服从之文学变为自由之文学,一国之文学变为世界之文学”,以使初学者从中充分领略那些书写平等、自由思想的文学作品,从而促使近代的“改良之志”具有充分的民意认同。[5]3据此,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中国”形象塑造,是以历代文学衍变过程中的经典作品为基础的,以此强化时人对“中国”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它试图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展现历代文学经典的生命力,以便促使“中国文学史”能够成为介入彼时学人公共生活和意识领域的重要媒介(暂且不论这种建构过程的实际成效)。
而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书写与文学史编纂者个人经历的有机融合,使得文学史编纂者能够通过阅读历代文学作品来寻求一种古今的“关联度”,从而感知或想象历代文学作品中所建构或塑造的“中国”形象,以至于将文学史编纂者所意图建构的“中国”形象作为历史上“中国”的真实形象。也就是说,通过承认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者干脆认为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就是历史上真正的“中国”形象,文学史编纂者通过对相关作品进行遴选与排序等方式,最终建立起一种包含文学史编纂者个人经验、历代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历史上部分真实的“中国”形象等多重主体与多元内涵层次的“中国”形象。而这种建构的关键之处是受文学史编纂者基于个人经历、时代需求与编纂文学史意图等融合而成的价值观念、甚至对未来的“中国”形象所设想与期望等主观愿望的主导。正如尼采所言,“个人及集体对于自身的历史,对于清清楚楚呈现、并以物的形式展示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存在一种情感性的联系”[9]。因此,文学史编纂者在共通的个人经历与情感导向下所书写的“中国”形象,就具有了一定普遍意义与时代特色。具体而言,黄人、林传甲等人有感于彼时民族颓败、国家沦落被欺凌而形成的“心灵创伤”记忆,促使他们迅速将此类“心灵创伤”记忆融入文学史的编纂中,从而以相似社会经历所形成的包含“受益人和责任人的双重身份”的“代记”记忆[10],来描述这种记忆下有关“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的形象问题。
(一)以教育为事业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中国”想象
林传甲在民国初年出任黑龙江巡按使署政务厅的教育科专员后,致力于兴办黑龙江的教育事业,曾指出教育应包括“教之修身、国文、算学、体操、图画、手工”[11]282等多种课程;且教育应以塑造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发展为本职,故其以为“现当社会教育进行之始,……务期作共和之鼓吹、协文明之声律。既隐防诲淫诲盗之端,亦默示德育智育之准,于人心风俗无不裨益也”[11]291。所谓“作共和之鼓吹、协文明之声律”,就强调教育应成为塑造国家正面形象与积极向上的教育意义的重要凭藉。甚至,林传甲还认为“凡民族国家、国民主权、国体正体”等“共和(即民国)国民应有之知识”,尤赖“国民常识为教科必需之书”的支撑。[11]343据此反观林传甲早年任职于京师大学堂教习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可知上述以国家主义为教育重点的思路,亦贯穿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始末。作为林传甲知交的江绍铨,在《〈中国文学史〉序》中曾指明林传甲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包含“为学问者无穷之事业,人类者进化之动机”。甚至,林传甲亦自言“国朝文学昌明,尤宜详备甄采,当别撰国朝文学史,以资考证”[3]1。此类编纂思想即含有彰显“中国”的国家形象之意。尤其是,对再现“国朝”(清代)文化与历史现状的“国朝文学”的“详备甄采”,即试图建构“国朝文学史”中的“国朝”形象在彼时的积极意义。据此,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所言的“国朝”与入民国之后所谓“共和”,皆是以再现国家昌明与培养民众爱国向心力为指导,并进而以之为相应的价值归宿。
为此,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四篇“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第五篇“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七篇“群经文体”等篇目,多谈及历代文章、群经、史学的发展对于修身的重要意义。第一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第二篇“古今音韵之变迁”、第三篇“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等篇目,就探讨文字之变迁及其对学好国文的重要性。而第九篇第四章“九章算术文体之整洁”等,就涉及挖掘历代“中国”中的算术学统。此类篇目设置与内容安排,就试图从历代文学史中挖掘“修身、国文、算学、体操、图画、手工”的相关成分,以此说明近代诸多西学知识,中国古已有之。如第十二篇第十二章“张衡天象赋两京赋文体之鸿博”云:“日本多地动,因祀张衡。近人有谓平子地动仪即西人地动日静之说者,则附会矣。地球绕日,中国旧所谓地有四游是也”[3]151。更甚者,第十四篇第十六章“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所言:“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不究科学而究科学小说,果能裨益名智乎?是犹买椟而还珠耳。吾不敢以风气所趋,随声附和矣!”[3]181-182这是一种以强烈的责任感来批判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所写,虽然能使人从中获得愉悦感等“受益”,却不利于“裨益名智”,更是与改革图强的时代“风气”相背离。此类文学样式与文学史衍变的史实,无助于再现或彰显正面意义的“中国”国家形象,更无法成为“作共和之鼓吹、协文明之声律”的重要凭藉,故而应加以批评。
当然,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在历代文学作品的书写视域下进行“中国”形象建构,主要是一种强调积极向上的国家形象的论述式理论展现与作品式直观再现。因此,林传甲最终试图强调历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仍具有垂范后世与有利当下的典型意义。如第六篇第一章“高宗纯皇帝之圣训”云:“传甲谨按,周孔为儒教之元圣,至圣万世师表。不但汉唐宋之贤君皆尊周孔,即辽金元入中国后无不尊周孔焉。日本自王仁献《论语》后,千余年传习弗衰。明治诏书亦尝征引周孔,盖圣泽之及人深矣”[3]66。这种“中国”形象的建构方式,主要是再现或叙述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书写,希冀读之者能够从中获得认同“中国”国家形象的情感。也就是说,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书写,主要是一种以图像呈现或文字描述,或形象塑造,或批判及建构的方式而展开的,属于历史真实的范畴。然而,当文学史编纂者在共通个人经历与情感导向的作用下,基于“为富强致治之规”的特殊考量,往往会以一定的取舍标准与排列顺序,来重新挑选历代文学作品有关“中国”形象等书写部分的展现方式与呈现面貌,以此形成一种在部分再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塑造合乎彼时之需的非历史实有与曾有却是历史或有的“真实”的“中国”形象。
(二)“上救国策”经历与黄人《中国文学史》的“中国”想象
黄人曾有“上救国策不见行”[12]366的痛苦经历,使其十分强调保存国粹的重要性。不仅编纂了《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等书籍,以展现“饷馈学界、裨补教育,与所以助成法治之美”[12]364的雄心壮志,更是借任教于东吴大学之机,以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实际行动,来回应彼时“朝廷锐意改选,以图自振”[12]364的时局需求。甚至,从后来“武汉兴师,君奋然欲有树立”,却因“两足忽蹇”不得参加而“愤闷不自聊”的经历[12]358,反观黄人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心理状态,不难发现:黄人以自强发愤的心态在《中国文学史》中所提出的以“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来破除“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的时人偏见,带有黄人希望民族自强与国家昌盛的强烈呼吁。
在这种个人特殊经历的作用下,黄人《中国文学史》在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往往基于特定的细节场景,来勾勒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作品对“中国”形象的表现语寓,试图从历代文学作品中建构一种注重自我进步与自我促进的“中国”形象。比如,黄人《中国文学史》曾指出《虞初》《齐谐》等作品之所以能“穷社会之状态”,是因为常受“政治、习俗实使之然”的影响;故而,文学的演进应重视文学作品如何书写当时人的“言语思想之自由”,也该批评政治与习俗如何限制当时人的“言语思想之自由”[5]5,以最终从文学作品所存留的记忆来展现文学的社会责任。典型之例,《分论·中世纪文学史·两宋文学·绪论》就认为南北宋之际的文学:“沉陆猾夏之愤,迥殊于楚弓楚得,故崖山与煤山劫后,世界腥羶,文界特馨逸,非汉唐之际能及也”[5]227,从而具备展现阳刚且抗争的宋朝国家形象。由此,《两宋文学》在“北宋诗派之分”中,除列“西昆体”之外重点罗列“江西诗派”,指出“江西诗派多尚清劲,与西昆正相反”;并详细附录“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于后,试图强调“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对宋代社会的写照价值及其对“西昆体”的矫正意义,从而突出诗歌创作应反映一时代之士风。在黄人看来,宋代的文学创作:“语录为积极之真的一方面,诗余为积极之美的一方面,而四六以美表真,成辞命之新种,皆创观也”[5]14。此类文学样式与创作现象表明:宋代文学在塑造求真求美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王朝的宋代“因仍改革”的积极形象。
再者,黄人在《中国文学史》所进行的“文学全盛期”“文学华丽期”“(文学)暧昧期”“第二暧昧期”等文学史分期,就是依据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书写“中国”形象时,所体现出来的反抗专制与文明进化之程度与意义的差异而做的区别,以强调不同时期文学作品所书写国家形象的异样特质及其对当下的不同启示。这种分期也是从历代历朝政教环境与文化内涵的内部变迁角度,来探讨历代文学作品书写“中国”国家形象及其政治衍变的不同特征。比如,黄人认为“(文学)暧昧期”中的明代文学较多体现着明人“清议”的风气,反对“腐败之时文、表判、策论”,然“于国计之盛衰,反多漠置”而“致生政府之猜嫌”。这种创作现象使得具有文学突破专制的端倪,体现出一种“光明”的迹象[5]17-18,从而展现不同时期的政府形象。
可见,黄人《中国文学史》对历代文学中突破“专制之势力”且表达“言语思想之自由”等作品的强调,是受其希冀借此“以图自振”等图强意图的指导。[5]15这就促使黄人有关中国文学演进史迹的建构思路,往往是强调历朝历代的文学如何突破专制等腐朽思想的制约而表达出自由平等的思想,最终试图建构出历代文学作品中那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局之需的“中国”形象。这也是一种通过塑造历史“真实”的方式来强调历史的“真实”性。
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试图透过想象与建构的方式,将“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历代文学作品的书写史迹为切入口,以“中国”形象的国家化建构替代对历代文学作品的政教化评判,从而促使时人深切感知出一种具有强烈集体认同感的文化记忆[13],最终获得一种包含历史真实与塑造真实两重面孔的“中国”自立自强的历史图景。此举是通过有特殊针对性的选择与作品解读,来建构彼时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所需的社会本质及其历史凭藉,最终借以启迪时人。
三 余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国”形象建构到底是该讲文化传承还是强调文化变异性呢?从发生结构主义的角度讲,20世纪初期的有志之士在担忧国家、民族及社会的前途时,往往表现出一种文化的焦虑与精神的困顿。这种焦虑的出现,就是因彼时社会政治与国家环境的冲突而产生、甚至遗留的。因此,有志之士在提出变革思想与价值诉求时,他首先要解决有志之士自身的精神困惑与文化焦虑,甚至进一步将他们自身的困惑推而广之到同时代之人,最终展现的面貌是具有普遍性的时代焦虑感;在此基础上,才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而这种解决措施在试图以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纂、讲授等形式进行焦虑心态的排遣与缓冲苦闷感时,往往导致在梳理历代文学演变史迹的过程中加进有志之士心目中的理想化思索及其相应的解决措施。这种做法使得彼时有志之士往往会在现实诉求无法满足时,转向在编纂过程中建构一种补足相应理想的想象,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感。也就是说,彼时有志之士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是将国家、民族与社会的认知结构与其自身的认知方式放在同一层次,从而试图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行为当作一种对彼时时势进行有意义反应的举措。它最终试图消除此前的学术史建构学术的常用方法、一般原则、惯性思想及其意义指向。因为此前的学术史建构范式,已不能很好满足近代中国的国家、民族及社会的变革需求。这就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进行“中国”想象的初衷与意义所在。
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试图消解传统学术建构体系中不适应彼时现实需要的部分,而意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需要的学术史建构体系。因此,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中国”想象与建构时,所进行的历史真实与塑造真实等建构方式,往往存在一种类似于“以论代史”与“以论带史”等价值先行的特征[14]。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必然要进行传统的传承建设,以此增加时人或者中国文学史教材学习者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此举将原本试图解决文学史编纂所实际面对的对象,径直转向想象文学史编纂可能面对的所有对象,从而将文学史编纂的对谁与为谁两个问题相杂糅来建构文学史的当下意义。而编纂者试图促使时人增强文化自信,最终目的是在彼时动荡的世界背景中寻求中国的国家自强与自立。故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进行“中国”形象建构时,并不能也无法完全讲求传承,亦需要建构一种变异的思路:采用观念先行的思路,以西方文明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来观照、继而改造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从而对彼时的“政界之事”进行呼应,以此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中国的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由此看来,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中国”形象建构所呈现出来的变异方式,是一种受时局现实制约的必然结果。
不过,因过于突出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规劝与借鉴意义,使得20世纪初期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往往过于突显目的意图与方法手段,反而多所忽略建构“中国”形象的具体内涵与面貌特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通过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又进一步说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已超越了因学术而为学术的套路,反而从20世纪初期中国的国家前途等现实需求出发,充分发扬文学史编纂者所一再强调的“文以载道”[5]2传统,以使20世纪初期的政治变革、教育改革、人才培养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紧紧融合成一体。故而,仍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