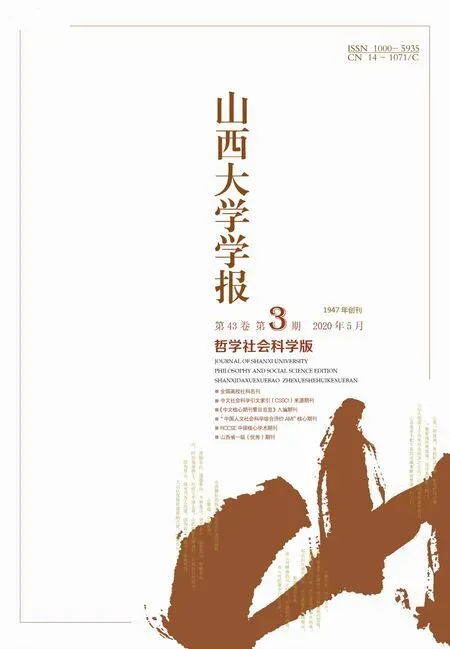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的艺术特性
——从近代文学革命的政治初衷谈起
陈 颖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笔者曾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反侵略战争叙事》一文中对以近代历次中外战争为题材的晚清小说,按照作品所描写的战争事件做了内容上的条分缕析[1],本文将结合近代文学革命的政治初衷,着重对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的艺术特性进行阐析。
一 近代文学革命的政治初衷
如果说,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的内容解析离不开中国近代历次中外战争史实,那么,对这些作品的艺术阐析则必须结合近代文学革命的政治初衷。近代文学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动荡大变局的时代。此时的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已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轰开,接踵而至的无战不败的战争一方面令清朝的统治陷入风雨飘摇中,国人深刻感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另一方面随战争而来的域外先进思想和器物也让长期沉睡在世界中心迷梦的国人为之震撼和惊醒,由此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求变强国的愿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重要转折点,而此前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属于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争,或者说是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战争。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已经在政治、思想、文化和工业科技等各方面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西方战胜东方尚属情有可原,而同文同种的东邻小国日本千百年来向以东方大国中国为师,却在短短几十年悄然崛起,且不费大劲就把貌似强大的中华帝国打趴地上,这让国人的神经大受刺激。痛定思痛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发现了日本后来居上的奥秘是向西方先进学习的结果。于是,甲午战争后的第四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联合年轻的光绪皇帝企望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就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是为“戊戌变法”。但傀儡皇帝光绪个人命运尚且在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掌控之下,又如何能左右国家的命运!“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不可能,先进知识分子转而寻求自下而上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文学革命于是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变革途径。
近代文学革命是一场急功近利的思想政治革命,因为这场革命的目标并不在文学自身,而在于社会政治。“文以载道”虽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但文学的社会功能向来不被人们所重视,中国传统封建文人甚至视小说和戏曲为“诲淫”“诲盗”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鲁迅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2],“向来是看作邪宗的”[3]。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学,发现了文学的巨大社会价值乃至政治功能。晚清维新派的旗帜人物、来自最早开放门户广东的康有为就对小说的社会功能倍加推崇: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今中国识字人寡,能深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4]
晚清维新派的另一旗帜人物、康有为的同乡、学生梁启超于1898年在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更是大力推崇欧美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5]
梁启超认为,欧美日等各国的政治小说广受大众欢迎,是人们从政议政的最佳寄托,是促进政治进步的最佳工具,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大力倡导文学革命,尤其推崇“小说界革命”。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6]
梁氏把小说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几乎把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全部希望都寄望于小说革命上。从本质上说,小说不过是供世人茶余饭后消遣的一种精神娱乐或思想寄托,本不堪承担如此沉重的社会责任,晚清时代国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准也不可能提供小说实现这些超文学功能的社会历史条件。
不可否认,小说作为通俗易懂为大众相对容易接受的一种文学种类,具有感化人心、愉悦身心的独特艺术感染力,这是小说胜于经史律例之所在,但让千百年来盛行于“瓦舍勾栏”的传统小说猛然成为拯救国家危亡的利器,不免给世人病急乱投医的感觉。而真正给国人造成审美障碍影响大众阅读接受的小说语言问题本身,梁启超等人并未真正彻底解决。虽然梁启超也认识到文学进步的关键是将“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并认为“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虽然,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7]。梁启超试验的结果依然是文白夹杂的近代小说语体,如钱玄同所言“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8]。只有到了十几二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倡导现代白话文,才真正完全确立了白话文的正宗地位,彻底解决了中国小说艺术的语言表达及其大众传播问题。因此,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意义也仅限于文化启蒙,于社会政治改革以及文学自身的改革影响有限,离梁启超等人倡导文学革命的初衷相去甚远。当代学者认为:“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为了挽回民心、启迪民智和新民,欲借小说唤醒民众。这种文化启蒙工作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但他为了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作用,把昔日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和未来国家的兴亡,均归咎或寄托于小说,这种认识显然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9]。
二 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对文学革命政治初衷的艺术践行
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者,而且也是实践者。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新小说》杂志,并亲自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小说界革命”倡导的影响下,晚清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1898年至1919年间,创作小说有7 388种,翻译小说有2 525种,20年间发表的小说占近代全部小说的99%。①参见: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329.这其中有少量小说是直接或间接反映近代历次中外战争的,如描写鸦片战争的《罂粟花》《鸦片之战演义》《芙蓉外史》《黑籍冤魂》;描写中法战争的《死中求活》《中法失和战史》《中法大战演义》;描写中日甲午战争的《梦平倭奴记》《中东大战演义》《中东之战》《旅顺落难记》;反映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的《救劫传》《邻女语》《庚子事变演义》《剑腥录》,等等。还有《孽海花》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对近代反侵略战争进行了片段描写。
论者一般认为,晚清小说作品虽然数量繁多,但公认优秀的作品却不多,能够被研究者关注并经常提起的只是寥寥可数的几十部作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恨海》《邻女语》《中东大战演义》《海上花列传》《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等等。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性艺术性相对较高的小说多数为所谓的“谴责小说”,也即大体上属于梁启超所大力推崇的“政治小说”范畴。“谴责小说”或“政治小说”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官僚体制和世风日下的社会各阶层。中国近代战争小说数量不多,但类型丰富,有直接描写战争过程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有通过个人或家庭变故间接反映战争灾难的短篇小说,还有借助梦幻或神魔故事的形式曲折反映战争的神话小说。然而,不管何种类型,中国近代战争小说与近代许多“谴责小说”或“政治小说”一样,充斥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情绪,如王德威所言“面对急遽变化的文化及历史情境,晚清作家显示出传统小说中前所未有的迫切感,想要记录重大事件与当代人物,由此呈现国族当下的危机”[10]65。因此,社会批判声浪的无处不在构成了中国近代战争小说比较显在的一个艺术特性。
(一)以写实笔法寓批判精神于战争人物和故事的叙写中
中国近代战争小说的绝大部分作品是以中国传统小说之历史演义的叙事法来描写战争人物与战争故事的。这些战争人物既有在庙堂上参与议政决策的王公贵胄,也有主政一方的地方军政大员和在前线御敌的将帅士卒,还有乘坚船携利炮前来踹国门的敌酋,当然更少不了战争中枢与焦点人物——金銮殿上的最高统治者。
中国向以世界中心自居,鄙视周边蛮夷之国,但近代中外战争,晚清政府在与洋人的对抗中却屡战屡败,割地赔款、被迫开埠通商成为战争结局之常态,清政府颜面尽失。老大中国究竟病在何处?这是小说家们十分关注并努力通过作品的人物言行和故事情节铺衍而试图回答的问题。近代中国战争小说的人物塑造虽乏善可陈,但毕竟反映了时代的基本真实,其对清朝廷豢养的一批豪门权贵毫不留情,竭尽揶揄嘲讽之能事。须知,这是在清朝统治尚未彻底崩溃的前夜,小说家们的意志和胆识还是令人钦佩的。
地方军政大员和战争前线人物是中国近代战争小说描写最多的人物,也是被小说家抨击或赞美最频的对象。鸦片战争开局中国曾占上风,是有赖于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指挥若定、调度有方,近代描写鸦片战争的若干小说对林则徐均褒扬有加。《罂粟花》(又《通商原委》25回,观我斋主人著,1907年刊行)小说开头有一段“弁言”:
……烟之为祸,虽由天劫,实由人谋之不藏。彼国有奇人知烟之能祸中国,我国亦未尝无奇人知烟之能祸中国,其人为谁,则深识远见、智勇足备之林文忠公是也。公督两广时,英人商船夹带鸦片,公严禁之,前后焚烧烟土为数甚巨,英人惭愤,以兵力从事。公洞悉夷情,相机御敌,着着制胜。卒以邻省失败,宵小媒孽其短,坐公偾事。呜呼!公之才之学之识,既见得到,自然办得到。假当年委任不疑,俾奏奇绩,何由厄我黄人,沦斯黑籍,中土脂膏几竭,外人势力愈强,致现今日如斯之险象哉!奈何海疆重寄,坏汝长城,庸劣无谋,一误再误。乐毅去而骑劫代将,廉颇废而赵括覆军,千古丧师辱国,如出一辙也。[11]279
这段“弁言”一方面赞扬林则徐的才能胆识,另一方面对当朝统治者听信宵小谗言、重用庸劣无谋者提出强烈批评。庸劣无谋者谁,乃琦善之流。小说作者对以琦善为代表的一班奸臣妒贤嫉能、媚敌误国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每每在小说的行文中夹叙夹议,直把小说当檄文写。如小说写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阿将定海失陷的责任归咎于林则徐在广东闯祸肇事,请旨要求重办林则徐及坚决抗敌的福建总督邓廷桢,作者义愤难抑:“你道这班奸臣,不顾国家的大局,趁着他这张尖嘴搬弄是非,全无天理,岂不可恨?那时天子得了奏本,便下了一道圣旨,把林钦差邓总督一并革职。这个信息传出,天下百姓都称冤枉。咳!自古到今,忠臣都是如此。朝廷有了这班奸臣,国家就送在他们手里。”又如,小说对清政府各级官员畏敌如虎、对洋人一味退让、唯恐惹外生非竭力嘲讽:
京城里总理衙门怕外国人如同老虎一般,无论外省一个教士,一个洋商,一些事情,打一个电报到总理衙门,立刻照办。官场中见了外国人案情,知县摇头,知府不管,道台不敢响,臬台不敢说,藩台说声外国人是,抚台说声外国人不错,就此好了了结,不好了也巴不得含糊了结。[11]288
诸如此类文字,通篇小说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与《罂粟花》不同,《中东大战演义》(又《说倭传》33回,洪兴全著,1900年刊行)对于战争人物的臧否较少做情绪化的主观评说,而是通过客观描述或人物内心活动加以展示。如小说第四回至第六回,叙中秋之夜,驻守釡山清军贺节,放枪鸣角,日军误以为清军开战,遂杀将而出,清军借酒劲回击,大胜日军。可是清军统帅叶志超却闷闷不乐,认为是侥幸获胜,竟下令让釡山清军大部退守牙山,釡山遂被日军占领。日军乘胜追击又连克仁川、汉城,兵临牙山城下,叶志超闻之胆战心惊。小说通过叶志超畏敌怯阵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一个贪生怕死的清军懦将的形象和盘托出:
……叶志超败了一阵,心中忧闷,暗想有一日从军,必有一日丧于倭人之手,到(倒)不如假言战死,远远逃去,尚可保全,又虑将来沿途上,或有人认出破绽,一时传扬出去,岂不是反为不美,遂心思一计,伸报朝廷,假传牙山大捷,连日逃出韩邦,走往别国。那时人皆以我牙山大捷,谁疑我逃走,沿途定必无阻,庶几可以脱身。[12]149
作为驻朝清军的统帅,叶志超带头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全线溃败,朝鲜全境遂为日军占领。这些心理活动显然是小说作者从全知叙角进行描述的,多少带有域外小说影响的痕迹。
晚清众多战争小说尽管批判锋芒毕露,但多指向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对于当朝最高统治者还是有所顾忌,不敢直言指责,只有到了辛亥革命清朝统治被推翻直至“五四”前后问世的近代少量战争小说才对清朝皇族的战争责任进行追责。代表性作品是《消闲演义》(程道一著,1921年前后刊行),这部演义小说历述了近代历次中外战争,对战争过程的描述和战争人物形象的刻画相当细腻,尤其对道光、咸丰、慈禧等帝王人物在战争中的乱作为提出严厉批评。如写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积极抗敌的林则徐和消极防御的琦善先后两任钦差大臣都被道光皇帝问罪后,粤海防御陷入了拉锯战,水师提督关天培等英勇御敌壮烈殉国,英军也遭到重创。英国领事义律寻求通过美国领事从中斡旋,请准予英人通商乞和,参赞大臣杨芳等顺水推舟,奏报朝廷批准。可是道光皇帝却战和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前脚刚“览奏深堪嘉慰。杨芳着从优叙议,长春、段永福均着赏戴花翎,并给巴图鲁名号”,后脚即严厉斥责“杨芳、怡良等只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殊失朕望!杨芳、怡良均着先行交部严议”。
皇帝深居庙堂九重之上,不了解前方形势变化,为撑朝廷脸面,而决意开战,既不知己亦不知彼。此时就连先前抗敌意志最坚定的林则徐都认为“若要挽回大局,很是不易。因为时势变迁,今非昔比。目下我国军事虚实洋人尽知,海中要塞均为洋人所夺,反客为主,一经开战,终难取胜。照此看来,还是以和为是。”可是,道光昧于情势,错误决策,结果导致清军一败涂地,宁波、上海、镇江等江防重地接连失陷,英军直逼南京城下,清政府不得不忍辱签下了《南京条约》。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小说作者的一段议论令人五味杂陈:“中国以屡败之后,急望休兵,再者论武不是人家对手,论文又没有外交才学,只好任凭英人所拟条约,不敢稍事驳诘。虽名双方和议,大抵惟命是听”。先例既开,此后就如多米勒骨牌,清政府每战败一次,就签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也许,在清朝统治者眼里,中国地广人多,割一两块土地并不算什么,他们在乎的是朝廷的脸面和天子的威严。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和朝廷一班大臣觉得中国吃亏太甚,需要补充条约,但所补充的条约,却尽是要求洋人“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洋人进京须着中国服饰等面子上的繁文缛节,并为此在外交上纠葛不休。可洋人偏偏不给面子,不但频频割疆占地,连皇宫圣殿都照样侵占和焚毁,直把皇帝、皇太后逼到荒郊野岭去。《消闲演义》和陆士谔的《孽海花》等小说都对慈禧太后昏庸贪婪无知专断的丑行尽情揶揄。如“庚子事变”(即义和团运动)中,朝廷重臣袁昶(太常寺卿)、许景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兵部尚书)、杨立山(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联元(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五大臣先后被斩决曾轰动一时,《消闲演义》《孽海花》对此都有所反映,所不同的是《消闲演义》更多的是将陷害忠臣的罪责归于端王载漪等一班庸臣,而《孽海花》则将忠良之冤死直接归咎于慈禧的昏庸无知。按小说所叙,清军和义和团久攻洋人使馆不下,礼部尚书启秀主张请一“法力无边”的和尚前来助战,袁尚秋(即袁昶)当即进谏反对此荒诞不经的建议,却惹恼了慈禧,当即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许景澄替袁尚秋求情,亦被视为同党,一统被杀。
在慈禧独揽大权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两次大的战争劫难,有关这两次战争的小说作品中,除了写慈禧妄杀忠臣外,还将其阴毒的女性心理刻画得十分到位。作为女性最高统治者,慈禧对于光绪皇帝身边的年轻女性特别嫉恨,总要伺机发泄。《消闲演义》两次写到慈禧对光绪皇帝身边的瑾、珍二妃的莫名惩罚:第一次是正当慈禧要大肆操办自己的60岁生日时,前方败耗传来,眼看自己的寿辰大典就要被搅黄,却把一腔怒火撒到与前方败战八竿子打不着的瑾、珍二妃子头上。乃因珍妃少时老师文廷式是上书主战的大臣之一,而今败绩连连,便连带瑾、珍二妃也遭殃,云“祖宗的江山,不能败坏在他们两人手里。今天每人杖责百下,儆戒儆戒他们,以后知道谨慎,不敢再有妄为”[12]。第二次是八国联军即将进京,慈禧挟光绪帝仓皇逃离北京,临行前仅因光绪帝挂念囚在三所的珍妃,慈禧竟索性叱令太监当着光绪皇帝的面将珍妃残忍淹毙于水井中,以绝光绪帝恋情,其泯灭人性之残暴令人发指。
上述以写实笔法践行社会批判功能虽构成了中国近代战争小说的艺术主流,但运用夸张和讽刺笔法描摹人物的丑态却更具艺术光彩。
(二)以夸张和讽刺笔法刻画战争人物形象
夸张和讽刺笔法是近代中国政治和历史小说创作中比较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法之一,它给近代若干小说带来不朽的声名,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对于官僚政治腐败和社会人心涣散、道德堕落的讽刺,将中国小说讽刺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的若干主要作品运用夸张和讽刺笔法描写战争人物,也为作品的艺术成就添辉增色。
夸张和讽刺具有因果关系,夸张是手段,讽刺是目的。由于近代中外战争清政府打败战是常态,战争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这是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不时在追问的问题,但包括作家在内的时人不可能从历史的视角上升到世界大势的高度来认识,也未能意识到战争失败的根本责任是在统治中枢,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敢诉诸作品中,于是众人谴责的对象多是那些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帅朝臣们。叶名琛、张佩纶、吴大征等封疆大吏是晚清战争小说中常遭讥讽的对象。
叶名琛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著名历史人物。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遇到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因为按照中英《南京条约》,广州属于对外开放通商的城市,但咸丰皇帝对于这个兵临城下不得不订立的耻辱条约根本不想认真履行,因此以叶名琛为首的广东地方官员只能屡以英人若进广州城会引起广州市民强烈反抗为由,将要求开埠通商的英人拒之门外。作为两广地方军政大员,叶名琛一方面不敢违抗当局的旨意,另一方面又自知理亏,且在军事上不敌英夷,于是采取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政策,对于英国人的所有要求均采取打太极拳的方式应对,英人忍无可忍终以炮舰回应。广州城破,叶名琛不躲不藏,任凭英军俘虏,最后竟被囚禁客死印度的加尔各答。
对于近代这个重要的战争历史人物,时人及后人贬多于褒。同样,在近代战争小说中,叶名琛也是一个白鼻子的丑角形象。《消闲演义》之《鸦片战争演义》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据,通过艺术夸张,塑造了一个愚昧顽冥又自以为是的昏官形象。叶名琛素信吕祖,打仗决策靠占卜。“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人借机要求入城,叶名琛不允。英军炮轰黄埔炮台,叶手下的巡抚、藩司早已慌乱不堪,叶名琛却不慌不忙,不调兵不遣将,原来他已向吕祖求乩示兆,乩语云“洋人空入即退”。已经攻入广州城的英军果如乩语所示半途而退,是因为印度士兵作乱,英军被临时调援印度平乱,才让广州城解了围。叶名琛不无得意地向部下吹嘘:“我家数世供奉吕祖,每遇大事,便求吕祖神乩指示,无不应验如响。就是兄弟科考以致出仕为官,都凭神乩示兆,以为进止”[11]。但吕祖的保佑终究敌不过英人的意志,广州市民焚烧洋人商馆洋行的鲁莽举动,又把叶名琛推到了风口浪尖,叶名琛依然以不变应万变,将英、法、美三国照会搁置不理,祈告吕祖,求乩示兆。英法联军于是发兵开战。
名琛迷信神道,总以为吕祖圣灵,能以飞乩示兆,吉凶祸福,均可先知,天定胜人,决有把握。所以英法联军已下战书,他依然置之不理。事关国家兴败,自己的生亡,这等重要紧急之事,竟当作儿戏一般。[11]436
只因上次英军攻入广州城,乩语云“空入即退”,并应验,这回乩语是“十五日,听消息,事即定,毋焦急”,到了第十四天乩语果然应验,却是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的坏消息。事事听凭吕祖乩示的叶名琛这回却不得不听任英夷的摆布。历史的真实是,叶名琛虽然一方面迷信吕祖的乩示,另一方面还是做了积极迎战准备的,“除了发布告示悬赏杀敌外,他还下令整备团练二万余人。各地民团积极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忾’”[13]。可见,小说是夸大了叶名琛消极的一面并加以艺术渲染,而忽视了其积极和无奈的一面。
比叶名琛更冤的是张佩纶。如果说叶名琛是由于过度迷信而导致身败名裂,客死异乡,多多少少是咎由自取,那么张佩纶则是因为认真执行高层的旨意而导致失败,实际责任在中枢,然而,时人却不依不饶,非追究其战争责任不罢休。晚清反映中法战争的若干小说都把张佩纶作为箭垛人物,刻意加以丑化,如《消闲演义》、王炳成的《中法大战演义》、曾朴的《孽海花》、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均将张佩纶作为讥讽的对象。
翰林出身的张佩纶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同为“清流”,以弹劾大臣而闻名。由于抗法意志坚决,张佩纶受命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因此,恃才傲物、弹劾大臣的张狂和马江战役的败绩成为张佩纶遭受非议的两大焦点。《消闲演义》之《中法失和战史》是如此介绍张佩纶的:
这张佩纶由两榜出身,恃才傲物,笔下既然雄豪,谈锋又复犀利,论笔墨,讲谈吐,简直无人敢敌他。由翰林起首,不数年已升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年纪不过三十上下,已是文职二品大员,少年气盛,目中自然无人。内则朝廷大臣,外则各省督抚,他都看不上眼。每遇各省督抚递进来的奏折,皇太后阅览已毕,发交内阁传抄,他便拿看这奏折,指疵摘瑕,批评得一文不值。往往他谈起文事来,周召二公不过如此,讲起武备来,孙吴两子还要退避三舍。[14]一个张狂自负的少年得志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孽海花》则以莊仑樵这个人物来影射张佩纶。虚构人物莊仑樵自然不能与历史人物张佩纶等同。历史人物张佩纶疾恶如仇,以其锋利的笔触弹劾了许多贪官污吏,本应青史留名,却因树敌太多和后来的马江败绩,成为众矢之的。小说中的莊仑樵几无值得称道之处,却突出其好胜虚荣的性格缺陷,如作者着意虚构了莊仑樵发迹前穷困潦倒到无钱买菜招待友朋,不得不将衣物拿去典当换些小钱,却被债主上门追债的窘态。明明欠钱未还理亏,却死要面子,要将上门讨债的伙计捆起来,“拿我的片子送坊去,请坊里的老爷好好重办一下子,看他还敢硬讨么?”[14]作者采取先抑后扬的艺术手法,为莊仑樵后来的狂妄作了铺叙。当上翰林后的莊仑樵靠他那犀利的笔端“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明日劾九卿。……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就是他不在那里,也只敢密密切切的私语,好像他有耳报神似的。仑樵却也真厉害,常常人家有房闱秘事,曲室密谈,不知怎地被他囫囫囵囵的全端出来,于是愈加神鬼一样的怕他。说也奇怪,人家愈怕,仑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公卿倒屣,门前车马,早晚填塞”[14]。
马江海战的失败让张佩纶的人生仕途发生重大转折。客观说,马江战役的败绩是当局决策失误和用人失当所致。像张佩纶这样只有笔头功夫和嘴上功夫而缺少实战经验的文人根本不应当被派到战争前线担当军事大任。《消闲演义》和《孽海花》等小说均抓住张佩纶的性格缺陷,大肆渲染他在马江战役中的不作为。声名显赫的张佩纶到福州上任是带着十分的傲气去的,“所过府厅州县,文武官员全都相迎,望尘下拜,张佩纶睥睨一切,岂能答礼这些小官”,到了福州,与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相见,“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何、张两人索性“将全省军务都推在钦差大臣身上,使他一手经理。佩纶毫无推辞,坦然自任”。“但是钦差上任后,本应发号施令,简阅兵马,不想他任事数月,并没有整顿军防,终天饮酒吟诗,围棋挟妓。好架弄事的人,有说这是名将风流,大都这样,有说这是胸有才能,故作文人狂态。”当法舰进逼闽海,前线紧急军情接二连三传来时,张佩纶却饮酒赋诗如故,训斥传递军情的中军道:“徒滋纷扰,有天大的事,还能误我饮酒么?”并责备部下“太不镇静了。跟着我手下当差,不要这样胆小。”还严令“他(按:指法国军舰)无论怎样挑衅,不准先行开炮”。五更时分,法舰向福建水师开炮,将酩酊沉睡中的张佩纶震醒,他大怒道:“这是何人造反!”当得知“所有舰队丧亡几尽”,这才“开了后门,一溜烟的紧紧逃去”。[14]历史的事实是,马江海战的爆发是在午后二时,并不在五更,且张佩纶执行的是朝廷不准向法舰先行开炮的命令。[15]可见小说是用了漫画式夸张的艺术手法将张佩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他反映中法马江海战的小说涉及张佩纶事迹的部分均大同小异,此不赘述。张佩纶的文学形象实为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
如张佩纶这样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官,他们靠的是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对于军事多为门外汉,一旦将他们置于战争前线,通常会洋相百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湘军统帅吴大征也是典型代表。吴大征是晚清著名书画家、金石学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爱国心切的吴大征自动请缨出征。作为湖南巡抚,吴大征手下固然有训练有素的英勇湘军,“惟吴大征乃是文官,从翰林中出身,未尝亲临战阵,故视战事为儿戏”。究竟如何“视战事为儿戏”,《中东大战演义》对此有精彩片段描写,其中最能代表以文代武的中国封建官僚轻慢做派的是吴大征亲自撰写的对日军的劝降告示:
……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官兵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缴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之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民人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开诚晓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计……[12]168
口气之大俨然必胜之军对疲败之旅。告示张贴后,“倭人视为没字碑,全不畏葸,绝无来降者”。待到正式开战,吴大征闻隆隆炮声早已吓破胆,湘军一战即溃。湘人深以为耻,认为吴大征“闻风先溃,致贻三湘子弟之辱”,欲阻挡其回湘复任。后人赋诗讽刺:“书生厌乱起雄心,阵上忘携退敌琴。寇氛未灭先遭败,谅此忠诚亦可钦”[12]。
《孽海花》同样写到了吴大征这一贻为笑谈的告示,不仅如此,还描写了吴大征(小说中以珏斋影射)在前线摆花架子,虚张声势,极端轻视倭寇的言行。珏斋统率湘军到了田莊台,每天上午带着他的三百护勇练习打靶,下午则邀几个清客“画山水,拓金石。一到晚上,关起门来,秉烛观书”,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对于自己延宕三个月迟滞不前的怯阵行为,珏斋大言不惭地辩称:“这不是本帅的先勇后怯,这正是儒将异乎武夫的所在”,“胜仗搁在荷包里,何必急急呢?”并声言他读了《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后,“彻悟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完全和孟子仁者无敌的精神,是一贯的。所以我的用兵,更上了一层,仰天地好生之德,不愿意多杀人为战功。只要有确实把握的三大捷,约毙日兵三五千人,就可借军威以行仁政,使日人不战自溃”。他还把杀敌制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精心训练的三百虎贲身上,不惜花巨资奖赏那些打靶精准的士兵,自己也带头举枪射靶,连中五枪。正在“唱凯歌,留图画,志得意满”的当头,却收到了廷寄的御史参文,指责他“逗留不进”“滥用军饷”“虐待士兵”。[12]可怜这个满腹文才独缺武略的文官到了两军真正对决时,根本不是倭寇的对手。
民国纪元前十三年,公历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其循例之游艺会中加演话剧。是役也,不特为学生演剧之先声;亦即为话剧输入中国之嚆矢。剧凡三:一曰《禀见得妻》,取材于昆曲《人兽关》之《演官》,而多所损益。属混沌初开,因简陋特甚,既无布景,又乏灯光;而上场有诗,下场有对,犹未尽脱旧剧窠臼。其二则为系西洋短剧,纯以英语出之。至剧名为何,已不复能举矣。[4]32
上述晚清时期富有代表性的战争历史人物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批判和讽刺的对象,首先是因为他们均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直接责任者,史实昭昭无可逃遁;其次,本文所评析的这些战争历史人物均是担负军事指挥责任的文官,他们文或许能安邦,武却定不了国,加上他们身上比较典型地遗存着中国封建文人尚空谈不务实的痼疾,这些文人通病被作家们置于战争特殊环境下用文学显微镜加以放大观察,于是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学革命背景下社会公众无情嘲弄的对象。
三 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的艺术缺憾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部分实现了近代文学革命所倡导的政治批判功用,但文学革命的本源目标却未能完美践行。首先,从小说文体看,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中的历史演义类作品与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基本无异,如多采用章回体形式,开头有“弁言”类的引述文字,每个章回结束多有七言律诗作结并有“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其次,从叙事风格看,多数作品沿袭了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线性叙事法,即严格按照战争发展的过程逻辑和时间线索编织故事情节,取全知视角,以历史事实为主要依据,兼采“齐东野人之言”[16]。近代文学革命初起时,作家对于历史小说写实与虚构的关系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较少受域外先进思想的影响。《中东大战演义》的开头,作者的一段自述颇能代表当时作家们在处理战争现实和文学创作关系时的复杂心态:
从来创说者,事贵出乎实,不宜尽出于虚,然实之中虚亦不可无者也。苟事事皆实,则必出于平庸,无以动诙谐者一时之听。苟事事皆虚,则必过于诞妄,无一服稽古者之心。是以余之创说也,虚实而兼用焉。[12]135
虚实兼用本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常规方法,但近代作家为什么会对此纠结,是因为中国近代历史太难看,太耻辱了。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堂堂天朝大国竟败给日本蕞尔小国,国人情感上难以接受。《中东大战演义》创作于甲午战败五年后,累累伤痕历历在目,所以作者接着道出了内心的纠结:
至于中日之战,天粧台畏敌之羞,刘公岛献船之丑,马关订约,台、澎割地,种种实事,若将其详而遍载之,则国人必以我为受敌人之贿,以扬中国之耻,若明知其实,竟舍而不登,则人又或以我为畏官吏之势,而效金人之缄口。呜呼!然则创说之实,亦嘎嘎乎难之矣!至若刘大帅之威,邓管带之忠,左夫人之节,宋宫宝之勇,生番主之横,及其余所载刘将军用智取胜,桦山氏遣使诈降等事,余亦不保其必无齐东野人之言。……然事既有闻于前,凡有一点能为中国掩羞者,无论事之是否出于虚,犹欲刊载留存于后,此我国臣民之常情也。故事有时虽出于虚,亦不容不载。余之创是说,实无谬妄之言。[12]135
丑事、耻辱事有损国家形象,但那是事实无可回避,而英雄行为、光彩事迹则应适当添油加醋加以粉饰,以提振国人自信心。晚清时期的近代历史演义小说在处理历史与文学的虚实关系上大都遵循这样的套路,但后期的历史演义小说愈来愈勇于揭露时弊,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丑事、耻辱事不但不回避不忌讳,反而大肆渲染刻意曝光。正因为主要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因而乏善可陈,众多历史人物像过眼云烟,几无性格刻画,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历史演义小说太拘泥于史实,限制了作者的艺术想象空间,反倒是那些纯虚构的小说更富艺术魅力。文言小说《梦平倭奴记》(高太痴著)写一狂生梦皇上召见自己,询战和之策,生对以“中华大国,义不当输诚纳款于东倭”“但知有战,不知有和”等梦呓之语。皇上深以为然,当即授狂生兵部侍郎之职。生于是率大军直捣东京,克广岛,俘倭主,复朝鲜,收回旅顺、威海、营口、台湾、琉球等失地,强迫日本订立十项条约,规定“朝鲜、琉球两国永远不准倭人入界”,日本“赔偿兵费八百兆元”并以长崎、横滨、大阪、神户为质,以及将伊藤博文等日酋斩首等,完全将清政府失败的现实移植到日本头上。[12]这篇读起来痛快淋漓,掩卷后潸然泪下的文言小说是当时知识分子内心极度苦闷和情绪高度压抑的一种宣泄,反映了国人雪耻强国的强烈愿望。
近代文学革命的目标是强国新民,途径是通过改良文言文,实现浅近化、白话化和不避骈偶的语言表达,以拉近文学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更好地向国民传播新思想新理念。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的绝大部分作品问世于20世纪初“五四”文学革命前,是近代文学革命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表现在作品的语言上是典型的文白夹杂的近代体。试择取《中东大战演义》的某段战争场景叙写和“五四”新文学革命后现代战争小说“战争三部曲”(孙席珍著)①“战争三部曲”由《战场上》《战争中》《战后》三部中篇小说组成,于1929年至1930年间先后在上海真善美书店、现代书局和北新书局出版。类似场景描写加以比较,就能够看出二者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
这是《中东大战演义》中记述朝鲜战场上清军将领左宝贵身先士卒、英勇牺牲的战斗过程。从行文看,首先这是一段平实叙述的文字,而非描写,场景简略概括,过程完整;其次,语言表述虽有大量浅近白话,但仍夹杂着少量文言,如“乃”“遂”“亦”“甚”“者”“溘然”等,同时保留着个别文言句式,如“有……者”“乃即……”等,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言文文字少而信息量大的某些特点。
经过“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洗礼后,现代白话文完全取代了文言文,同样描写战争场景,“战争三部曲”就大异其趣:
曙色确定地露出了,而战争也更加紧凑活泼了。
忽然一颗大开花弹,乘着一股牛劲,排山倒海而来,声势浩大,似乎要想一下子便把那群峰完全都铲平一般。那蠢家伙随后在不知什么地方轰然开裂了,接着便是一道迁延不定的白色烟雾向上冲出,而和大堆的奇形怪状的从各种巨炮的口径里所吐出来的乌云混合。
炮声越转越高,狂飙也越来越猛烈了,从这端到那端,都被那硝磺气味所凝结的烟雾所覆盖,而几千支几万支火箭便在这当中忙碌地穿来又穿去。这些火箭,团团打转飞了一顿之后,又紧紧地在他们的四周缠绕着,好似夏夜的蚊虻,又好似秋收时的蝗虫。
炮弹的挖掘工作,毫不休息,地下的泥土沙石,都被它冲荡而喷射在他们身上,有时那较大的鹅卵石夹脸掷来,而被掷中的人竟以为自己是中了弹了……
一种可怕的爆裂现象,在他们旁边发作,那蓬勃的不规则的野火,竟将他们的眼睛完全眩住。于是,大家心胆俱碎,这个向那个扑去,那个又向这个扑来,乱七八糟,搅做一圈;有些离开爆裂处所较远的,便将全身蜷屈,脑袋藏在两腿之间,双手紧紧地把握着泥土……
慢慢地,待那白烟自行消散以后,他们才敢略略把不放心的脑袋伸一伸……这时,那嗜杀的残酷的连长,混(浑)身渗着血,瞪着最后的慈祥的眼,正在呆望这幅场景……又是一阵排炮,一阵枪声,一阵暴风,一阵急雨……大家头脑沉重而又空虚,什么也糊涂了……[17]
这段描写热兵器时代战争场景的文字已经完全摒弃了文言句式,是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而且行文中大量采用了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以及心理描写,虽然只是写了某次战斗中炮弹炸裂的可怕景象和连长的牺牲,但却以十分逼真细腻的文字进行描摹,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果用电影镜头来借喻,则《中东大战演义》是远镜头,“战争三部曲”便是近镜头,甚至是特写。或者用绘画来比喻,《中东大战演义》犹如中国水墨画的大写意,“战争三部曲”更像西洋油画的细腻写真,纤毫毕现。
最后,用台湾学者王德威对于晚清小说的一段评论来结束本文,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乏善可陈,‘积弊’却处处可见:如过多的眼泪与笑声、不必要的夸张、声嘶力竭的政治宣传等等。因此根本不可能纳入五四话语所规画出来的文学典范模式”[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