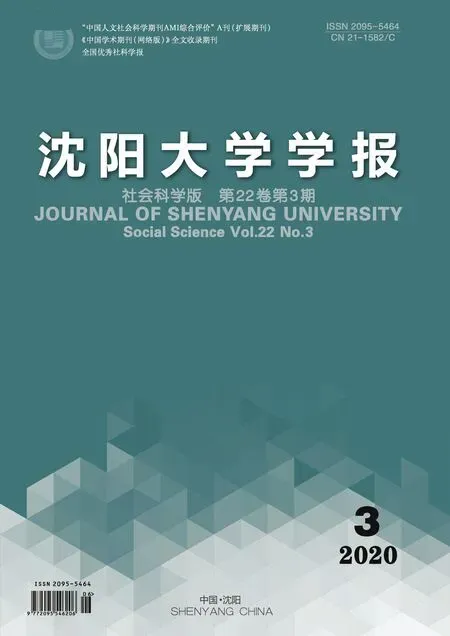清末小说《缙绅镜》文体考辨
文 迎 霞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缙绅镜》是清末《新闻报》连载的一部长篇小说,自1908年4月30日开始刊载,于1909年4月6日止。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刊登了37回,是一部未完成之作。连载之初,读者被告知《缙绅镜》译自一位德国人的日记:“这部小说乃是一个外国游历中国的绅士所撰的日记,编小说的将他翻译出来的”“未加删削,就只把地方、人名改换过了”[1]作品并未标明作者和译者,只在小说篇名上方标识为“社会小说”。小说内容显示,日记主人是一位名叫显理的德国伯爵。他年近花甲但关心世界局势,喜欢去国外游历、考察政治。他通过报纸得知中国朝廷要预备立宪,遂前往中国。他还聘请了一位名叫华子才的中国翻译,小说内容即为两人游历中国的所见所闻。初看起来,这是一部翻译小说,但纵观全篇会产生很多疑惑。首先,从文体形式看,作品是典型的章回小说,并非日记体小说。小说不但未以显理伯爵的口吻叙事,而且在以全知视角叙事时,也超出了日记体小说应有的视角限制,出现了大量有关华子才的心理描写及不少显理伯爵不可能知道的见闻。其次,小说的情节安排也有诸多令读者费解之处,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情节。再次,从小说的主旨看,《缙绅镜》是一部典型的揭露中国缙绅怪现状的作品。笔者认为,这部未完之作貌似翻译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国人自创的社会小说。
一、 叙事规范
如作者所称,“编小说的”曾告诉读者这是一部译自国外绅士游历中国的日记,且翻译时对原文并未进行“删削”。如果译者所言属实,那么原著应是日记体,但译作却是章回体小说体裁,两者的文体形式差别极大,《缙绅镜》完全以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出现。该作共刊载了37回,每回均有着工整的七字对偶回目,每回末都基本以“正是”加两个对偶句,以及“且听下回分解”的形式结束。小说往往通过全知视角进行叙事,有的回首即以“话说”或“且说”开头,“看官”等字眼也间或出现。即使是译者考虑国人的阅读习惯,将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日记体改为以第三人称叙事的章回体,也要受到原著叙事规范的限制。日记体叙事的规范制约叙事的内容,日记的内容只能是显理伯爵的见闻和感想。译作在转换为第三人称叙事时,应该只转换叙事视角,而内容要受到日记体限制。但《缙绅镜》在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时,出现诸多超出显理伯爵感知范围的内容,如有不少对他人隐私或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以及对伯爵不在场时发生的事件的描写。这些内容完全突破了日记体的叙事限制,只可能是“编小说的”自行创作而成,而非出于原著。
首先,小说把华子才的个人隐私全盘托出。小说叙述了显理伯爵要请中文翻译,委托前德国领事就此事询问华子才,得到后者的同意。华子才的生平经历本可以通过前者告知显理伯爵,但小说以全知视角将属于华子才的个人隐私、心理活动直接叙述出来。《缙绅镜》在第2回开篇不但交待了华子才的籍贯,而且指出他的举人资格来自枪手代考。他的好友黄之彦精通英语、德语,在洋行做买办,手头阔绰,生活奢侈放荡,令他艳羡不已。华子才随好友学习德语,并成为一个洋奴,专门替洋人沟通中国官场,赚利益以自肥。之后,华子才在天津无法立足,求洋人推荐在胶州德国领事署做文书工作,并与领事交好。领事离任后要回国,邀请华子才同往。华子才考虑到可以利用出洋经历回国后谋取肥缺,欣然随同领事前往。小说中的华子才利欲熏心、工于心计,德国领事和显理伯爵无法了解他的上述隐私。这些叙事内容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产物,不可能来自日记。
其次,小说有多处关于华子才心理活动的描写,如华子才一直在揣测显理伯爵游历中国的目的。小说中多次对此记述,如第2回和第3回,华子才在以铁路、开矿、侦探等话题试探显理伯爵后,仍无法确知后者的真实想法。华子才捉摸不定,只能把疑问埋在心里,准备回中国后再留心观察。华子才一面诉说中国绅士的腐败,一面又有意选取中国绅士要求官府惩办官员的几条新闻翻译给伯爵听,来抬高中国绅士的身份,借此显示自己的身份,以免被伯爵看轻。显理伯爵与华子才初次相逢,不可能洞悉后者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些内容也不可能出自其日记, 只能是“编小说的”所创作。
再次,《缙绅镜》中出现了很多伯爵不在场、不知道的信息,这在小说前7回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第3回两人到达天津后,显理伯爵去拜谒本国领事,华子才则去熟悉的绅士那里转了一圈。华子才对绅士们吹嘘自己的出洋经历和自己与伯爵的关系,绅士们的回应和期待结识伯爵的心理等内容,伯爵完全不知情,不可能出现在伯爵的日记中。再如第4回伯爵和华子才到达北京后,伯爵经常独自一人外出,华子才则到处逍遥,有时还与认识的外务部人员联络,打听机密要事来讨好伯爵。当一位外务部人员因结交使馆中的人员,泄露机密被拿办并访查同党,华子才吓得魂不附体。江浙铁路风潮中,有的乡绅既赞成商民拒绝政府的借款,又赞成政府向商民借款,用两面讨好的手段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受此启发,华子才写下禀稿,把显理伯爵说成德国的秘密侦探,自己有意为显理做翻译,做侦探之侦探,监视显理伯爵的活动。另外,还写了几个留德学生的名字当作革命党。华子才希望这样能免除前案的株连,也能以此作中南捷径。他带着禀稿找到知己吴京官帮忙,这位京官哈哈大笑,把华子才的如意算盘分析得一清二楚。离开吴京官后,华子才却又良心发现,认为这是害人性命的事情,万一暴露,必然被革命党追杀。此外小说第11回,在前往洛阳途中下车休息时,华子才通过与村农交流得知此处费大老爷勾结官府,在此地横行霸道的劣迹。这些情况并未告诉伯爵,只是随口轻描淡写地说了此处刚开始禁烟,并不十分认真,以后认真办理就可以弊绝风清了。上述华子才与村农交流的情节显理伯爵无从知晓,与其说译自日记,不如说来自创作。
二、 情节安排
《缙绅镜》的情节安排有诸多不符合日记特点之处:
1.前7回的情节不能合理体现显理伯爵游历记录者的身份
前7回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华子才作为中国翻译展开的,如华子才的出身经历,出国缘由,做翻译的考虑,打探伯爵游历目的从中为自己牟利的打算,到达天津和北京后的社会交往等等。这些情节重在刻画华子才善于钻营、工于心计的形象。伯爵既无法获知华子才的隐私和心理活动,也无从了解华子才社会交往的具体情况。第5回主要情节是华子才与姜立恭两人会面的情景,华子才走入客厅,见到人影,疑心是革命党人来杀他,吓得心惊肉跳。仔细一看,是自己旧友姜何愚的兄弟姜立恭。姜立恭首先展示其兄提出利用美国归还庚子赔款的溢收款建设海军的条陈,希望华子才代为转达高层。华子才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官员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作官,根本不会考虑复兴海军一事。之后姜立恭还拿出姜何愚建议收回胶州湾的万言信,希望华子才劝说伯爵回国游说德国政府。华子才认为胶州半岛的事情也不用管,顶多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些情景显理伯爵并不在场,无法洞悉华子才因告密而畏惧革命党暗杀的心理,更无法知道华子才与姜立恭交谈的具体情况。华子才也未向伯爵透露此情景,这部分内容出现在小说中是非常不合理的。上文举例分析了前7回类似情节的不合理,此处不再赘述。第8回开始,显理伯爵才发挥游历当事人的作用,小说情节才与他的见闻相匹配。
2.显理伯爵获取中国缙绅信息的过程太顺利、太巧合,不符合常理
小说情节专注于暴露中国各地缙绅的怪现状,有些是显理伯爵自己在各处游历时亲见的,更多是在游历过程中听他人转述的。这些见闻的产生过程,多借助巧合穿插其中,似乎显理游历中总能遇见了解中国绅士情况的各色人物。这些人不论什么身份,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显理伯爵真正开始游历中国始于第8回,不仅每到一处都能目睹当地缙绅界的乱相,而且总能通过所遇之人了解各地缙绅的所作所为。如第8回到达河南开封后,遇到一英一德两位教士,通过他们得知河南巩县和济源县的绅士兴办学堂的怪事。随着一位教士朋友摩矿师的到来,以勘矿为话题,显理伯爵又得知了湖南、安徽缙绅的狡猾。初次见面的摩矿师,还邀请伯爵随他同去了洛阳,伯爵有了更多发现。教士和摩矿师的出现以及离开都神龙见首不见尾,似乎都是为配合伯爵所要了解的见闻而出现的。在从汉口前往湖南游历时,显理伯爵与湘乡(地名)缙绅刘星台同行,通过后者了解到湖南缙绅的权力,受到湖南缙绅的殷勤款待。显理与刘星台分手后前往长沙,又遇到旧友濮伦德,获悉刘星台款待背后的谋利动机及湖南绅界、学界的更多劣迹。从长沙返回汉口后,显理伯爵又应本国领事邀请,前往四川为其打探与当地缙绅合作寻觅盐地的虚实。同船前行的重庆米客余少甫提供了大量信息,余少甫大谈四川官绅勾结对米价的影响和缙绅肆意鱼肉百姓的情况,认为四川的各类缙绅都对地方无益。到达成都后他们又巧遇华子才的同乡兼同年史伯通,引出了关于浙江缙绅兴办学堂和四川、湖南、江西等处绅士修建铁路的诸多评论。返回客栈后显理又遇到了朋友玛礼森,玛礼森不但描绘了四川陆军学院学生的荒唐举止,还带伯爵经历了与四川绅士进行军装买卖的过程,了解更多绅士的劣迹。从第8回至第37回,显理对中国各地绅士的了解几乎都是通过类似渠道获得的。情节太过巧合,失之穿凿。
3.小说中有不少情节不合理
如第21回,显理与朋友玛礼森去灌县找绅士李伯存订立军装买卖合同,李家村私塾里的一位老学究毫不避讳地把李伯存“浑名李天王,又叫作李阎罗”横行霸道的劣迹告诉他们。这位老学究居然是李伯存的从堂叔祖,他所以愤愤不平地告诉旁人上述信息,是因为自己曾经经营当地的积谷,却都被李伯存取代了。可当李伯存设宴招待显理一行人的时候,这位村塾先生居然受邀前来陪客。看来两人的关系还算和谐,不像前述那么对立的感觉。这样的情节安排实在不合常理,一位长辈当着陌生人,包括两位外国人的面大揭孙辈的老底,是因为利益受损而非出于良知。同时暴露了李伯存的“阎罗”行径,自己的形象也并不光彩。一方面,老学究既未顾及亲戚关系,也未考虑“李阎罗”的威势;另一方面,老学究不知道伯爵等人的身份,更不清楚他们与李伯存的关系,怎么贸然说出这些激愤之语呢?再如第32回、33回,显理一行人从江山县出发,路经杨家村时听到枪声和一片喊杀声,之后这些声音渐渐平息。他们又走了两里多路,停下来休息,几位背包旅客也在旁边休息,正在谈论方才开枪的事情。原来岭下杨家村有位绰号“杨一霸”的乡绅,平时与官场声气相通、欺上瞒下,在村中开设赌场营利。若县里散差和营兵下来打抽丰,也会赏给他们一些酒钱。但此次杨一霸进京,其子仰仗父亲的势力,对打抽丰的人一毛不拔。县里一个名叫“小太岁”的差役心生一计,悄悄到盐捕营禀告营官,说当天有大盐枭在杨家村开设赌局,自己可以带路前去捉人,彼此分肥,没提及杨一霸其人。营官利令智昏,派了七八名盐勇随“小太岁”下乡,逢人便捉,见钱便抢。赌场中的人开枪拒捕,营勇开枪对敌,两边各有伤亡,“小太岁”也被击毙在地。最后,寡不敌众的营勇抱头鼠窜逃回城中。这种情节安排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枪战刚刚发生在岭下杨家村的赌场中,这几位背包旅客怎就迅速获知了前因后果?尤其是他们口中那位出谋划策带领盐勇进村的“小太岁”当场被击毙,那些幕后的信息怎么轻易被外人得知?再如第35回,作为陪着显理从德国来到中国,一起游历了七八个省的中文翻译,华子才不但没有告诉显理中国的新年来临了,还在新年第一天擅自外出,让显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诸如此类不合理的情节,在《缙绅镜》中还有很多。
三、 小说主旨
这部作品旨在暴露与批判中国绅界的腐败,是清末谴责小说大军中的一员。《缙绅镜》题名本身就表露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在小说缘起中也表露无遗:“这绅士把在中国所见所闻的怪现状登诸日记,藉资考镜。编小说的把他翻译出来,并非要谤毁绅士,使一般贪官污吏,借此小说作为把持政权的话柄。只为绅士里头,公而忘私的虽多,假公济私的却也不少。有这本书穷形极相的描摹他们的丑态,如明镜照物一般,使绅士与绅士互相规勉,引为殷鉴,也是长进人格,造成立宪国民的一法。”[1]与此相应,小说中公而忘私的缙绅难见踪影,假公济私的缙绅比比皆是。显理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他的中文翻译华子才,后者恰恰是一位人格卑微,自私自利,善于钻营的中国缙绅。进入内地后,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显理了解到的绝大部分中国缙绅都热衷权势,利欲熏心。他们或者坑蒙拐骗,或者横行霸道。如第8回描写河南济源县缙绅与地方官串通,借筹措学费名目,搜刮民脂民膏。除原有的一所义学之外,没有添办一处学堂。上司查问时,赶制许多学堂匾额挂在城内各处神祠佛寺门口,问明视学员查阅学堂的顺序,让义学的学生轮流跑到视察地点等候,在视学员离开时馈赠厚礼。巩县缙绅提取公款办学,由县中幕僚、两学教官及本地几个老岁贡等担任监督、校长和教员,但只挂名领钱,并不到学堂授课。第10回摩矿师谈到他的朋友被湖南的韦姓举人以购买矿山名义骗去8 000两银子,拿去捐了道员,通过贿赂高官得到肥差,刮了几万两银子的地皮。德国传教士则说他的一位朋友是上海洋行鼎鼎有名的大班,陷入安徽几个大缙绅以开矿名义设下的圈套。他劝东家投入的十万两银子被骗,最后气愤地开枪自尽。第15回重庆米客余少甫说到四川官绅串通,涨米价卖给平粜局从中渔利,导致平粜局米价贵过市价。四川总督丁文成为讨好皇帝,在朝廷结束捐饷后仍要求四川百姓再捐饷3年。各级官吏则巧立名目,甚至出现税银不满一两却勒派至十几两的情况,百姓苦不堪言。第21回湖南缙绅叶龙阳上万言书参劾李文忠,花钱收买李文忠身边的人,后来居然拜在李文忠门下,把李文忠玩弄于股掌之上。中日讲和之后,叶龙阳把10万两银子军饷挥霍一空,却骗上司自己被日本人劫去,深陷囹圄两个月之久才逃命出来。另一位龚姓缙绅奉命验收兵舰,私下收受洋人巨额贿赂,将旧船改造的破绽百出的兵舰汇报成工坚料实的兵舰。小说中欺行霸市、私设刑堂、瞒天过海、穷奢极欲、悭吝异常等中国缙绅的形形色色行径,不一而足。
缙绅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显理无穷的感慨,如在第6回,伯爵道:“我晓得了,贵国的绅士都是官场中人。不是已解职的官,便是将出任的官。平日间在地方上又与官一鼻孔出气,所以只重官权,不重民权。那要求开国会的事是办不到的”[2]。在得知商人与官绅的关系后说道:“原来贵国绅就是官,官就是商。分不出什么界限的”[3]。又如第12回,显理认为如果中国实行立宪,各省自治,绅士即便参加选举也“不过借着公举的美名助他专制的势力罢了”[4]。再如第19回史伯通谈到绅士办事不牢靠,显理认为中国是官绅一体:“中国的绅士只怕官长专权,每说官场靠不住。中国的官场最忌绅士分权,又说绅士靠不住。其实据外人看起来,却如一丘之貉,无论是官是绅,都是靠不住的”[5]。第20回显理对于一条铁路有几个总理,难以明晰责权发表看法:“据我看来,贵国的政府乃是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因此,总理铁路的绅士也是些不负责任的绅士……贵国当此专制与立宪过渡的时代,昔年的官权已渐变而为绅权,然而贵国绅士却仍脱不了官场的积习。办事的专制固然像官,就是这些不负责任的地方也很似个官。官是政府的代表,绅士又是官的代表”[6]。还有第34回,显理得知绅士们借自治名义骗钱自肥后,认为“假公济私乃是贵国官绅素来的习惯”[7]。显理伯爵的见闻和批评无一不与其揭露缙绅弊病以资借鉴的主旨相对应。
晚清谴责小说流行,对社会怪现状的揭露与批判是这类小说突出的特点。《缙绅镜》标志为“社会小说”,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异曲同工,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事实上,日记主人显理伯爵为了解中国立宪状况而游历中国,其视野不可能局限在描摹缙绅丑态上。日记内容与其说是显理的客观见闻,不如说是“编小说的”带着强烈创作倾向的谴责小说。
四、 结 语
通过对叙事规范、情节安排和作品主旨的考辨,笔者认为《缙绅镜》名为译作,实际上是国人自创之作。从已刊37回的内容来看,这部作品带有清末谴责小说的鲜明烙印。鲁迅先生较早指出这类小说的风行时间、产生原因及艺术特点:“光绪庚子(1900)年,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8]《缙绅镜》的作者有意宣称是译作,也体现出创作求新的意图。首先,译作的写作者是德国的显理伯爵,与清末其他谴责小说以国人作为社会怪现状见闻者的身份不同。其次,《缙绅镜》借助洋人在中国游历的所见所闻,便于展开中西政治的对比,使作品对中国缙绅的批判更有力量。再次,把小说的来源定位为洋人游历中国的日记,以译作的形式出现,有助于增强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翻译小说对清末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