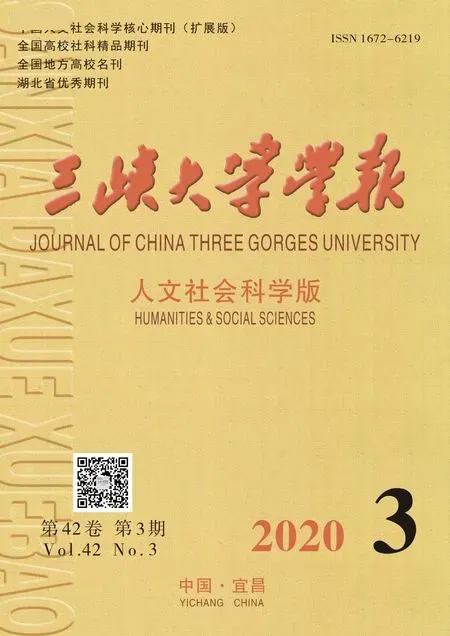商业性对邵氏明清小说题材电影创作的影响
王凡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台湾导演蔡明亮曾在论及港、台两地电影时说:“香港是极度商业,台湾有一点文艺气息。”[1]可以说,香港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很重视商业性与票房价值,这首先缘于港英当局对待电影制作、经营采取了既不扶持,也不过度钳制的基本方针,因而,香港电影一直努力依照市场规律来进行运作,以求适应观众的需求,体现出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与市场开拓力度。同时,这也与香港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香港一直是一个重商的社会,一切以实利为重,较少受意识形态的羁绊。随着60年代经济的转型,70年代经济的起飞,传统社会的道德束缚日渐宽松,生活方式加速西化,‘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在60年代后也逐渐让路给‘电影就是娱乐’、‘娱乐就是宣泄’这样的理念和简单的供需关系。”[2]275而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公司)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香港制片公司,其依据多部明清小说改编的影片既折射了当时的香港电影艺术家对于这些古典名著的独特认知,也直观地反映了商业性对此类艺术实践的多元化影响。
一、电影商业性对原著情节改编的影响
故事情节是电影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原著的情节改编也同样是名著影像再创作的重要部分。邵氏导演在改编明清小说时,十分注意将这些古典名著丰富的情节内容生动呈现于观众眼前,这既与导演本人的改编理念有关,更受到电影商业性的内在影响。
1.对原著情节择取的影响
邵氏导演在改编明清小说时,多选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这类长篇巨著作为再创作的对象。由于这些作品篇幅宏大、情节复杂、人物丰富,因此邵氏导演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浓缩”或“节取”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改编,如张彻拍摄的《快活林》(1972)、《水浒传》(1972)、《荡寇志》(1973)都取自小说《水浒传》的部分情节,李翰祥导演的《风流韵事》(1973)、《金瓶双艳》(1974)则取自《金瓶梅》的部分情节,这些改编创作都是以原著情节的取舍为前提的,选取原著中的哪些情节来进行影像再创作便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纵观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其虽是由不同导演创作的,但他们几乎都是将书中富于戏剧性的曲折情节作为首要的改编对象。如小说《水浒传》中的“武十回”即武松故事被改编为影片《快活林》,“曾头市”“大名府”等情节被改编为影片《水浒传》,而征方腊的情节则被易变为影片《荡寇志》的主体情节。何梦华拍摄的《西游记》(1966)、《铁扇公主》(1966)、《盘丝洞》(1967)、《女儿国》(1968)等邵氏“西游记”影片分别源自“四圣试禅心”“三借芭蕉扇”“盘丝洞”“女儿国”等情节。上述影片择取的这些原著情节都极富曲折盘桓之趣,有着很强的戏剧性,不仅非常适合电影改编的需要,也相对更贴近现代观众的电影欣赏需求。
2.影片中暴力、情色元素的凸显
美国电影学者理查德·沃尔特在论及电影编剧时曾说:“编剧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主要是通过娴熟的手法来创作和塑造色情暴力。当然电影不仅仅是暴力和色情,但这些是首要内容。”[3]这一认识虽显绝对,但也道出了色情与暴力元素在商业电影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这同样反映在邵氏公司拍摄的商业电影中,“当全世界的娱乐片愈来愈注重强烈的感官刺激时,邵氏当然也不甘人后,在发展古装武侠片的同时,大拍黑帮打斗片、特务动作片和软色情片。而当性和暴力成为票房灵丹后,男演员继续雄霸四方,女演员则自然成为被男性剥削蹂躏的次要角色。”[2]262正因如此,邵氏导演以获取高额票房为基本出发点,在将明清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基本都突出暴力、情色元素。张彻作为新派武侠片的重要导演,其电影中“总少不了轰轰烈烈的血战场面”“一般都有尸横遍野和惨烈血腥的场面”[4],凸显出张氏武侠片硬桥硬马、阳刚不羁的影像气质。在将《水浒传》《三侠五义》等小说搬上银幕时,张彻就铺排了大量的武斗暴力情节,这既是源于他所秉持的“阳刚电影美学”及武侠片的基本类型属性,更与武打暴力元素对于观众的吸引不无关系。如在根据《三侠五义》改编的影片《冲霄楼》(1982)中,张彻就重点展现了江湖侠士们几次潜入冲霄楼,欲对襄阳王反迹一查究竟,却被楼内机关所伤的情节。这些武艺精湛的侠客奋力拼杀、身中暗器、伤重而亡的画面凸显了他们不畏艰险、虽死无惧的气概,影片更通过他们血染衣襟、搏杀群敌的场景渲染了强烈的暴力色彩,这在白玉堂身陷铜网阵的情节中体现得无以复加。这种不乏血腥意味的画面提供了强烈的视觉感官刺激,成为吸引观众走进影院、宣泄其内在情感的潜在要素。
与此同时,情色元素也时常被邵氏导演植入到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中,例如何梦华的“西游记”系列电影就在重现原著相关情节时,有意构筑了诸多富于情色意味的画面。影片《西游记》在表现“四圣试禅心”的原著情节时,就有猪八戒偷觑荷花池中女性沐浴的远景画面;《铁扇公主》亦有铁扇公主裸体背身步入浴池的镜头。虽然这些场景时间短促,但这“惊鸿一瞥”中的“风月”意味也无疑潜在地满足了观众的“观淫癖”。李翰祥拍摄的《金瓶双艳》在重现《金瓶梅》中西门庆盛衰之变以及他与众妻妾的复杂情感关系时,也展现了西门庆与李瓶儿最初的偷情、与潘金莲“醉闹葡萄架”这类情欲描写段落。与何梦华、李翰祥在古典名著改编中对情色元素的含蓄呈现相比,孙仲、牟敦芾等人导演的《红楼春梦》(1977)的情色描绘则更为粗鄙、直露,该片一方面将《红楼梦》“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痴丫头误拾绣春囊”等情节段落重现于银幕,另一方面又刻意羼入了大量的情色化书写,如贾珍偷窥秦可卿沐浴并将其强暴、贾瑞在“风月宝鉴”镜中幻想自己与王熙凤欢爱、司棋与潘又安夤夜偷欢等情节,这些段落都无一例外地将男女“云雨”场景直呈银幕,毫无遮掩,完全是通过露骨的情爱场景与女性胴体的裸露来制造噱头,以此来吸引观众。
二、原著改编的类型电影整合
所谓“类型电影”,就是“按照不同类型(或称样式)的规定要求制作出来的影片。”[5]65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图解式的视觉形象”[5]65等方面。作为一种影片制作方式,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占据了统治性地位,这一成熟的电影制作方式也成为现今世界通行的商业电影模式。而“从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影片,凭借着文学经典作品的光环,首先降低了制片企业的经济风险;在文学化改编的过程中,无处不受到类型电影的商业原则的规制,带有强烈的类型意识。”[6]导演大卫·里恩(David Lean)就将《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成功拍摄为史诗片,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则将《雾都孤儿》(Olive,1968)改造为成熟的歌舞片,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亦使《闪灵》(The Shining,1980)成为经典的恐怖片,他们都较好地将名著题材影片整合为票房、口碑俱佳的类型片,此种范例不胜枚举。正如美国电影学者路易斯·贾内梯所说:“类型片也是一种集中和组织故事素材的适当方式。”[7]就邵氏公司来说,其从一开始就移植了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依照其成熟的商业电影模式进行运作,以明星制、类型片理念来制作电影。正因如此,黄梅调影片、古装武侠片令其获得了丰厚的票房利润,而喜剧片、恐怖片、警匪动作片乃至间谍片、战争片等其它各类片种也都蕴藏着不俗的商业潜力。
故此,邵氏导演在将明清小说搬上银幕时,都不自觉地将这些影片加以类型化,令其凸显出类型电影的基本特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黄梅调影片的整合
黄梅调电影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香港影坛占据主流的戏曲片类型,“这黄梅风潮维持了足有二十年,直到80年代初才全面消失,邵氏从《貂蝉》(1958)到《金玉良缘红楼梦》(1977),总共拍了三十多部黄梅调片子,可说是执类型生产之牛耳,质精量多,影响极大(片子多番重映仍然卖座)。”[8]105这类影片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其对当时观众心理需求的适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观众生活简单,缺乏娱乐,难免时感枯燥,充满梦幻色彩的黄梅调电影正提供了一条让他们找寻浪漫、宣泄情感的途径。”[8]109同时,黄梅调影片也以古代中国图景的影像描摹疏解了海外华人的怀乡之情,令其在观影时将自己潜在的家国之思映射其中。正因这类影片的卖座,邵氏导演在改编明清小说时,就十分注意在片中融入黄梅调元素,令这些影片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黄梅调影片的审美特征与类型风格。作为对黄梅调电影的兴盛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导演,李翰祥根据明清小说拍摄的多部影片都烙下了黄梅调的深刻印迹,这些影片可以说本身就是邵氏黄梅调电影的代表作。如《貂蝉》一片既是邵氏较早的一部《三国演义》题材影片,更是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先河之作。相映成趣的是,《金玉良缘红楼梦》不仅是邵氏“红楼梦”电影的代表作,也是邵氏黄梅调电影后期的代表作。在这期间亦有根据《醒世恒言》的同名篇章改编的影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罗臻、薛群导演,1964)、根据《水浒传》改编的《阎惜姣》(严俊导演,1963)、《潘金莲》(周诗禄导演,1964)等影片,这些明清小说题材影片都可以说是成熟完备的黄梅调电影。总体上看,上述影片一方面体现了影片主创者将文学、电影、戏曲三种艺术有机融合的匠心独运之处,另一方面也为邵氏公司早期的明清小说改编提供了一定的票房保障,为此类影片之后的拍摄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武侠片的整合
当“黄梅调”电影逐渐式微时,新派武侠片日渐兴起,张彻、胡金铨及楚原等人导演的一系列古装武侠片成为其中的代表作,这些影片在上映后取得票房佳绩,邵氏公司也由此将这类影片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向,这一类型影片便占据了当时香港影坛的主流市场。因此,无论是邵氏高层,还是影片主创者都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向武侠类型贴近、靠拢,力求以此实现票房的盈利。在这一创作趋势下,邵氏导演在将一些明清小说改编为电影时,就有意对影片进行武侠片的类型化整合,其中最为典型的无疑是张彻的改编实践。张彻的电影“在情节上总是安排男主人翁/阳刚英雄实践其生命价值的过程,触发这一过程的原因,则以‘报仇’或‘报恩’的主题为多,强调传统的伦理观念及忠义精神”[9],其在改编小说《水浒传》时,将原著人物身上潜隐的阴暗面淡化,如武松“血溅鸳鸯楼”的残忍枉杀色彩被稀释,梁山集团征伐中的屠戮行径也被删去,而是着意强化了这些梁山人物如江湖豪侠一般嫉恶如仇、讨贼报国、以身殉义的英雄一面,为此甚至不惜改易原著人物的命运轨迹。如《荡寇志》这部影片“可以说自始至终都被打斗所贯穿着,不仅有陆战,而且有水战,其中破涌金门水闸的搏斗最为惊心动魄。”[8]260片中武松、燕青为擒方腊浴血奋战、力战而死,李逵、张青、孙二娘也在攻打杭州的巷战中力拼群敌、伤重而亡,彰显出传统武侠片中侠客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精神。这种意在趋近武侠片的类型改造也同样反映在张彻导演的《神通术与小霸王》(1983)一片中。该片改编自《三国演义》的“小霸王怒斩于吉”一节,在这段原著情节中,孙策因怒气攻心而毒发身亡,《神通术与小霸王》则彻底重构了孙策之死的情节,令其在全片结尾如侠客一般鏖战而死。这些电影与武侠片的有机融合既与导演本身秉持的独特影像风格有关,也与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所透射出的男性阳刚色调和武侠片的高度贴合不无关系,更与当时武侠片的盛行息息相关。
3.“风月片”的整合
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邵氏旗下的许多导演都在自己的影片中融入情色元素,刻意暴露女性肉体与男女“云雨”之景,显现出“风月片”的典型特征。如在武侠片中,《埋伏》(何梦华导演,1973)就有女性花园裸浴的画面,《天涯明月刀》(楚原导演,1976)中妓院老鸨“高老大”也频频暴露自己的身体;在警匪片中,《香港奇案》系列(程刚、桂治洪等人导演,1976-1977)充斥着女性被侵犯的暴露镜头,《暗渠》(蓝乃才导演,1983)有男性嫖妓的露骨画面;在恐怖片中,《索命》(何梦华导演,1976)、《风流冤鬼》(招振强导演,1984)等影片在冤魂复仇除奸的故事主线中也多有女性被强暴的画面;在喜剧片中,《声色犬马》(李翰祥导演,1974)、《多嘴街》(王风导演,1974)等影片在社会丑态的无情鞭挞与人性弱点的温情嘲讽中,同样不乏“香艳”画面。甚至在战争片《女集中营》(桂治洪导演,1973)中,也有女战俘在集中营被日本军官折磨、蹂躏的露骨段落。可以说,为了迎合普通市民阶层的猎奇心和“观淫癖”,进而获取高额的票房,邵氏导演在不同的类型片中羼入了大量暴露女性身体、描摹男女欢爱的场景画面,这一创作倾向也同样反映在明清小说题材电影中。作为香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李翰祥“对香港电影史的一大贡献是开创了风月片潮流”[10],其拍摄的《大军阀》(1972)、《风月奇谭》(1972)、《声色犬马》(1974)等都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风月片”的重要作品。而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家,他对古典名著也十分钟情,曾将《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搬上银幕,其中《金瓶梅》就曾被他先后5次改编,其在邵氏旗下拍摄的《金瓶双艳》《风流韵事》则是开《金瓶梅》影像改编之先河。他在上述两片中一方面通过独特的视听语言巧妙含蓄地呈现了《金瓶梅》中西门庆与妻妾床第之欢的男女声色之相,另一方面又在原著的基础上多向度地突出了潘金莲、李瓶儿等女性人物,彰显了他一以贯之的女性主义意识,并在“风月”意趣的表层书写下折射出他“对性别、两性关系与权力”的独特思考①,体现出他在商业电影机制下的电影“作者”意识。与李翰祥对《金瓶梅》的“风月片”改编所透射出高超影像技法与严肃改编态度相比,《红楼春梦》一片在呈现《红楼梦》若干情节时,则是一味通过影像画面来铺陈情色内容,完全沦为纯以票房盈利为目的的低俗之作。可以说,同为古典名著的影像再创作,由于导演艺术水准与改编理念的差异,原著风貌与“风月片”或是较好融合,在满足观众潜在心理欲求之际,亦可进行一定的艺术探索,实现了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调和,或是将电影商业性对名著改编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放大,令改编实践归于失败。
4.喜剧片的整合
喜剧片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电影,也在邵氏电影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邵氏导演同样将喜剧片特征与其他类型电影有机融合。如张彻70年代后期的创作已表露出武侠、功夫与喜剧元素的融合,《金臂童》(1979)、《叉手》(1981)等影片都是如此,桂治洪导演的《邪斗邪》(1980)、《邪完再邪》(1982)则是将喜剧风格与恐怖元素有机融合。而邵氏导演改编明清小说时,也常融入诙谐意趣与幽默桥段,令这些影片呈现出一定的喜剧片特征。何梦华的“西游记”系列影片就大力发挥原著本身的诙谐意趣,如影片《西游记》中孙悟空变为高翠兰巧赚猪八戒,《铁扇公主》中铁扇公主欲与孙悟空变幻的牛魔王亲热,而后者倍感尴尬、托辞不就,《盘丝洞》中孙悟空假变蜘蛛精、捉弄猪八戒等喜剧段落都是如此。影片《金瓶双艳》虽在喜剧片特征上不及“西游记”系列影片那样显著,但同样不乏诙谐幽默的奇趣书写,如影片中郓哥因看不惯王婆的行迹而故意捉弄她,王婆在西门庆向其打听潘金莲之事时故意东拉西扯的调侃式对答都在这方面极富典型性。在上述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中,虽然整部影片并未因诙谐性段落的融入而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片,但其却在丰富影片的影像表现手段、强化影片的观赏性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艺术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受众的不同审美趣味,向类型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向整体的融合方向发展,即把各种类型的元素加以综合。”[11]8由于邵氏导演在改编明清小说时注意融入各种类型片的特征、风格,这就使得此类邵氏电影呈现出类型混杂的特质。影片《西游记》在1966年上映之初,就有时评认为:“《西游记》影片的故事,选自这部通俗神话同名小说的最精彩情节,香艳、滑稽、紧张、惊险,兼而有之,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娱乐性巨片。”[8]240可以说,此语既是对影片的褒奖之辞,又道出了该片兼具神话片、喜剧片、武侠片乃至“风月片”的不同特征。张彻导演的“水浒”影片则是将武侠片、喜剧片甚至战争片的特征相互兼容,李翰祥导演的《倩女幽魂》(1959)、《鬼叫春》(1979)等“聊斋”影片亦是融合了恐怖片、爱情片、武侠片的影像元素。这种类型杂糅一方面折射了香港电影创作的某些后现代文化趋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邵氏导演为最大限度地赢得观众而做出的努力。
邵氏明清小说题材电影的类型片整合反映了邵氏公司对于好莱坞类型电影模式的有意借鉴及其在这方面已形成成熟的体系,体现了该公司“自一开始起就将电影视为一种产业,而且是一种娱乐产业”,并“认定电影的制作和营销,必须以市场的需要来不断进行产品的调整、策划和包装。”[12]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整合为当时明清小说的影像改编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票房保障,增强了邵氏高层的投资信心,有利于他们继续投拍同类影片,从而在客观上保证了在当时的香港,明清小说影像传播的持久性与稳定性。
三、商业运作中的原著人物扁平化
伴随着影片的类型化整合与商业化运作,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中的原著人物也呈现出商业机制影响下的人物塑造理念。类型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基本都是以模式化、定型化的方式来展示给观众的。正如美国电影学者托马斯·沙兹所说:“一部类型电影——不管是一部西部片或歌舞片,一部神经喜剧片或一部黑帮片——都是由熟悉的、基本上是单一面向的角色在一个熟悉的背景中表演着可以预见的故事模式。”[13]11可以说,“在每一种类型电影中都会有明显的标志性人物,会高频率地出现一些着装、个性比较相似的人物形象。”[11]29诸如西部片中的牛仔、言情片的富家女、科幻片中的外星人等。而由于邵氏导演在改编明清小说时,都将某一种或几种电影类型融于片中,使得这类影片凸显出类型化的特征,与之相应的是,片中的原著人物也都基本呈现出诸种类型片中的人物形象特征。以人物塑造的武侠类型化为例,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张彻对于《水浒传》《三侠五义》的影像改编,片中人物本身都是英雄传奇小说或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武松,还是白玉堂,这些原著人物侠义英豪的形象侧面在张彻武侠片中被放大、彰显,而他们在原著中潜存的缺点乃至人性阴暗面则被完全淡化。在此,这些文学形象已被张彻彻底改造成了传统武侠片中锄强扶弱、义薄云天的正义侠客形象。再如人物塑造的戏曲化倾向,黄梅调电影时常运用戏曲演唱来代替人物的语言对白,或是抒发人物自我的内心情感。邵氏导演曾先后3次改编《红楼梦》,分别是袁秋枫的《红楼梦》、李翰祥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和孙仲、牟敦芾等人合导的《红楼春梦》,虽然3部影片是由不同的主创者拍摄于不同时期,所投射的改编理念与影像风格也差异较大,但其都不约而同地将戏曲唱段融入人物对白,令这些艺术形象更富传统戏曲人物的审美特质,由此体现出黄梅调影片对这些导演的深刻影响。周诗禄导演的《潘金莲》、严俊导演的《阎惜姣》等邵氏“水浒”题材影片也都表现出这一特点,是典型的黄梅调电影。此外,何梦华的邵氏“西游记”系列影片也适度融入了传统戏曲元素,在孙悟空与妖怪打斗的段落中不仅有节奏感较强的戏曲伴奏,而且人物打斗的动作也不乏戏曲打斗的写意化色彩。
英国作家、学者福斯特在论述小说人物形象时,将其分为“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前者是指具有复杂内心情感与丰富性格层次的人物形象,后者则是指性格结构较为单一的人物形象,而类型电影人物基本都是善恶分明、性格单调的艺术形象,是典型的“扁平人物”。正如托马斯·沙兹所说:“类型角色在心理上是静止的——他/她只是一种态度、一种风格、一种世界观,还有一种预先决定的并且在本质上不变的文化姿态的肉体化身。”[13]32沙兹在此含蓄地揭示了类型电影人物的定型化、模式化特点,这类形象缺乏多侧面的性格刻画与心理变化的艺术观照,其更多地表征着一种特定的类型审美风格和价值观。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中的人物形象由于影片本身的类型化整合而同样呈现出上述审美窠臼。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武侠片导演,张彻在改编《水浒传》时淡化了武松、李逵等人残忍嗜杀的形象缺陷,凸显了这些人物的正面形象与侠义精神,但从客观上看,小说《水浒传》的血腥嗜杀描写“既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又是上古文化传统的产物,同时亦是当时小说写人艺术由‘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之幼稚与蒙昧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进阶”[14]。这类情节也同样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来审视张彻“水浒”系列影片对原著人物阴暗面的完全淡化,这一艺术处理虽有助于彰显其自身独特的导演风格,有助于突出梁山人物的正面形象,让普通观众更易接受,但这一改编创作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水浒传》人物原貌完整性的缺损,令其在被完全正面化之际,也由原著中正反兼具的真实丰满形象蜕变为类型化、扁平化的单面人物形象。与张彻标举武侠类型风格造成《水浒传》人物的扁平化相比,影片《红楼春梦》则因影片主创者追求商业票房价值而刻意放大了情色内容,片中的人物如王熙凤、贾珍等人也都被塑造成或放荡、或猥琐的负面人物,这些“红楼”人物善恶兼有的复杂形象色调被彻底遮蔽,他们已由丰满鲜活的圆形人物变为了形象单一的扁平人物。
四、结语
作为诞生仅百余年的现代视听艺术,电影有其特殊的属性,它“既是艺术品又是商品,它必须通过商业渠道才能提供给观众消费(观赏),而且只有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才能收回成本,获得赢利,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推动电影业的发展。”[5]18正因如此,名著改编类影片在情节、人物等主要方面也都必然受到电影商业性的潜在影响,其也必然会被改造成为类型片来加以商业运作,而这些在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中体现得尤为鲜明。邵氏导演通过择取原著情节,融入暴力、情色内容及类型电影整合来增强明清小说题材影片的潜在票房价值,折射了商业性对香港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多重浸透。可以说,对这一现象的科学解读一方面可管窥香港电影产业化对名著改编创作的特殊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为客观地审视、考察明清小说在现代传播历程中所受到的商业性浸染,为全面了解、探究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艺术家对于中国古典名著的整体认知与特殊诠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注 释:
①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香港学者游静的论文《一场紧暖香浅的误会——李翰祥风月片对“女”与“色”的礼赞》,载黄爱玲主编的《风花雪月李翰祥》,香港电影资料馆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