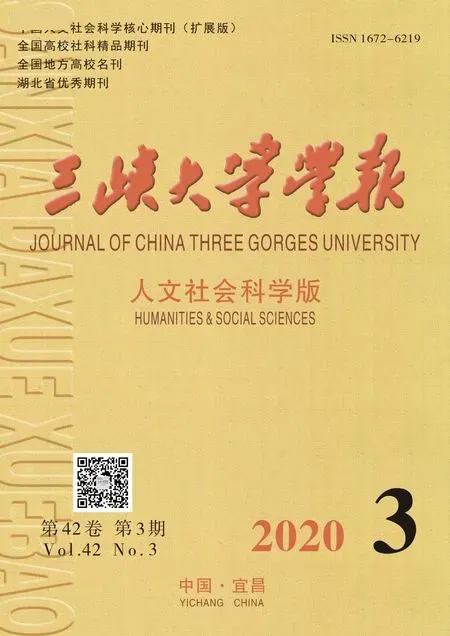媒介语境下作家与影视关系辨析
文玲, 左其福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与影视媒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王朔为代表,张贤亮、刘恒、苏童、余华、莫言、池莉、叶兆言、刘震云等传统作家,率先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影视。莫言是第一个因“触电”而走红的当代作家,1988年,由张艺谋导演,根据莫言《红高粱》和《高粱酒》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让莫言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王朔是第一个成立影视公司的当代作家,1988年因王朔4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被称为“王朔电影年”。1989年,苏童和莫言、刘震云等人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室”。之前知名度并不高的小说《米》,被改编成电影《大鸿米店》后,成为2003年夏天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为了适应视觉文化的特征,小说创作从细节到整体都呈现出较传统文学诸多的异象,写作主体、审美内容、读者趣味、传播媒介、发行渠道、消费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触电”后,作家不同程度参与影视产业中,不但催生了影视小说、影视同期书等新文学形式,作家身份也发生了转变。刘恒、郭敬明、韩寒开启了作家转型当导演的时代,刘震云、周梅森、海岩等身兼作家、编剧、制片人三重身份。
一、为迎合影视进行剧本创作
王朔创作初期,主要以小说为主,创作了一系列通俗小说,如《我是你爸爸》《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等。1990年,由王朔和郑晓龙联合策划、李晓明编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打破了中国电视剧收视率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被称为中国长篇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次堪称“奇葩式”的创作,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王朔现象”也成为文坛热议的话题。之后,由王朔参与主要策划、赵宝刚导演的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上映,引发了轰动效应,这部电视剧后来被看作中国情景喜剧的开山鼻祖。1992年之后,王朔小说创作逐渐处于“停滞”状态,但与此同时,由他创作的剧本越来越多地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王朔承认他是用商人的眼光去审视整个文化市场,所以他懂得迎合观众的审美心理进行创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期,看电视剧成为人民群众重要的娱乐方式,他抓住商机,担任电视剧、电影的编剧。正如自己所说:“我这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还没有真正打响,我还需要强有力的广告推介,要打开市场,除了既有的文学人口还要唤醒潜在的文学消费者,用时髦的商业口号说,‘引导消费’制造需要。”[1]因此,王朔被称为“中国当代进行商业创作的第一人”。
接着,王朔与王海鸰、冯小刚等早期作家、导演以策划影视剧、开影视公司为目的而聚集,共同探讨影视剧本,将影视剧本改编为小说,首次将文学与影视捆绑在了一起。在王海鸰与王朔共同策划电视剧《渴望》后,《孽债》《牵手》《篱笆、女人和狗》等这一系列以家庭情感生活为主的影视剧迅速成为影视和文学共同仿写的对象。这些作家集群仅仅是为了影视投资创业,而非文学创作,也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创作风格,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类型化小说雏形的初步形成。
王海鸰是一名集文学、影视、话剧于一体的三栖作家,被称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海鸰发表了小说《星期天的寻觅》《爱你没商量》和话剧《我想跟你说句话》等多部作品。随着影视媒介的兴起,审美呈现多元化趋势。大众文化的现代性、世俗性、商业性、娱乐性等特性使传统文学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王海鸰依然怀有言说的热情和欲望,并渴望尽可能地为人所知。可是在坚持传统小说创作理念下,读者对她的关注度日益降低,作品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首次“触电”前,王海鸰近两年没有创作出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正是读者对她的淡忘和自身创作遭遇瓶颈让她在创作上选择了“妥协”。王海鸰意识到视觉时代的到来,“图像”因其快捷、浅显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人直观的审美需求。因此,王海鸰根据大众审美的变化,对文学创作进行了相应的改变。
王海鸰从传统作家向编剧的成功转型,源于她“妥协”的创作姿态。在新浪博客访谈中,她浅谈了自己剧本创作的心得,认为剧本首先得写,但是由于剧本内容在拍摄成电视剧的过程中会有许多的限制,因此需要不断修改以做出相应的妥协。王海鸰称“剧本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在各种妥协中顽强表现作者对生活认识的过程,所谓‘戴着镣铐跳舞’。”[2]在她看来,任何艺术形式的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镣铐的束缚,她自称是一名善于妥协的编剧。
郭敬明不仅是作家,还是出品人、编剧、导演、文化商人,身份的多重性让他在当代文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以商业为目的的文学创作,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多次上了福布斯名人榜。评论家房伟称“郭敬明是80后第一个,或者说最成熟的一个将文学写作与商业元素、资本结合的典范。”[3]近几年,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作家的生存方式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作家不会把眼光只停留在印刷媒介,逐渐转向电影、电视、网络等新媒体。郭敬明是转型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以尖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一形式的发展前景,迅速把握这一商机。
《小时代》是郭敬明作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五亿的票房令其成功踏上导演之路。《小时代》系列电影已经上映4部:2013年6月27日《小时代1:折纸时代》上映,2013年8月8日《小时代2:青铜时代》上映,2014年7月17日《小时代3:黄金时代》上映,2015年7月9日《小时代4:灵魂尽头》上映。短短3年4部电影,这样高密度拍摄和上映史无前例,总票房超越了18亿元人民币。《小时代》四部曲把郭敬明推向高潮,原著《小时代》十分畅销,也将郭敬明的文学创作更好地呈现给观众,使更多人通过电影了解到郭敬明的文学创作,被他的文学作品所吸引,从而“路转粉”,这种营销方式让郭敬明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郭敬明并不只把眼光局限于作家这一个身份,他涉足的领域十分广阔,有杂志、出版社、电视综艺节目,其中还与影视保持密切关系。郭敬明创办的“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前出版是公司的重心所在,而现在越来越偏重影视方向。2005年7月24日郭敬明成为电影《无极》同名小说的改编者。《无极》是陈凯歌和郭敬明共同创作的作品,既有导演的文字精华,又有新锐作家的创作才气。《无极》的热播,吸引了大批读者再次阅读小说《无极》。而郭敬明再版的《无极》更是笼络了大批的读者,这里不仅有郭敬明的粉丝读者,还有陈凯歌导演的影迷,小说版《无极》的畅销可谓是轻而易举。
二、采用影像化写作以便于影视改编
随着影视产业迅猛发展,影视产业和小说的关系愈发紧密。但是,小说与影视在表现形式、社会影响等方面各有不同。小说家可以进入人物的心灵,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直接叙述人物内心冲突,银幕剧作家却不能,因为小说借助的是语言,而电影借助的是影像。语言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如说到“花”这个词语,我们只知道“花”这个概念,却看不到一朵具体的花,电影却能向我们展示一朵具体的花,这正是图像与语言的不同之处。在电影中,形式与内容不可分,一个优秀的导演善于通过艺术构思,使得每一个影像具有多种含义,成为一套“图像符号的表意系统”。投映在银幕上的影像不单单像照片那样是“现实物的复制品”,它通过艺术加工以再现的方式向观众展示某一特定含义,或是隐射含义。即便是最简单的记录片、最简单的新闻镜头都已经是一个或优或劣的艺术品。用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的话来说:“文字语言只有在表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表达,而电影语言只有在进行表达的情况下才能表意。”[4]因此,要让小说迅速搬上荧幕,作家必须主动改变叙事策略,使得小说具有影像化的特征。
海岩被称为“影视小说第一人”,他曾公开表示“我认为我们已经从阅读时代进入电视时代,原来的文字读者不停地被瓦解。有很多人不看小说,但很难说有人不看电视。小说读者的阅读习惯被电视媒体的特点改造了,文字给视觉补充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故事必须适应这种欣赏习惯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写小说,必须在写作方法上做出调整,来适应这种新的思维习惯和欣赏习惯。这不是取悦读者,而是因为时代不同,文本的特点和风格也必然不同。”[5]自《便衣警察》被改编成影视一炮走红后,海岩的小说与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影视写作”成为海岩的创作动机,《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玉观音》《永不瞑目》《舞者》《河流如血》《深牢大狱》等小说具有明显的影像化特征。
书面文化通过语言文字传情达意,影视则是通过画面和声音讲述故事。巴拉玆在《可见的人 电影精神》中称:印刷术的发明逐渐使人们的面部表情看不到了,可见的精神变成了可以用文字表达的精神,视觉文化变成了概念文化。人的躯体变得没有思想,空虚起来。电影改变了书面文化的特征,使得埋葬在概念和文字中的人重见阳光,变成直接可见的人[6]。可见的人表现在可见的形体、可见的表情、可见的言语和可见的动作。为表现可见的人,海岩小说借鉴了电影的分镜头、蒙太奇等技巧、手法,主要通过形体、动作和对话来展示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
海岩说:“现在的作家和过去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差别,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要使文学和最普及的媒体结合,这就是电视,一部小说销售三十万册已经相当好了,假如每本书有五个人看,读者是一百五十万,而一部好的电视剧会有上亿观众。”[7]30海岩为“影视写作”的创作观念,使其创作的小说成为影像叙事的典型文本。离奇的故事情节、通篇的人物对话、空间的不断转换令其创造了每部小说都被改编的奇迹。海岩坦言自己在创作时“选择那些可以改成电视剧的做故事,这样导演看上就喜欢,因为容易改。”[7]47这一刻意迎合电视媒体的创作姿态,也使得小说具有商品消费的弊病——人物扁平化,情节类型化。主人公大多是俊男美女型,男主人对女主人的追求迎来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以牺牲情节的连贯性和真实性为代价,追求视觉化效果,以娱乐、消遣作为审美目的。
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后深受人们喜爱,文学与影视发生猛烈碰撞,擦出了新的火花:“类型片”与“类型小说”走向融合,逐渐诞生了风格相对固定的影视作家群。所谓“类型片”,电影史研究专家邵牧君认为其是“按照不同的类型(或样式)的规定要求创作出来的影片”[8]。电影类型化现象,早见于西方电影领域:“美国好莱坞在电影领域的制作、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喜剧、言情、科幻、战争、恐怖等多种电影类型,并在20世纪中期得到发展、成熟”[9]。可以说,类型化不但是一种标准化的规范,还是大众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因而“类型小说”也在新世纪以后崭露头角。“类型小说”在我国的首次提出是在“21世纪初期,通过中国电影出版社‘好看文丛’的问世而被明确提出”[10]。这系列丛书包括了“赵凝的言情小说《有毒的婚姻》《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余以链的悬疑小说《死者的眼睛》、丁天的恐怖小说《脸》等等系列”[11]。随后,2005年被出版社命名为“类型小说年”,这源于“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选编了一套‘中国类型小说双年选’丛书,包括:《校园小说卷》《幽默小说卷》《奇幻小说卷》《官场小说卷》《言情小说卷》等等”[12]1-2。同时标志着类型小说从朦胧走向了清晰。尽管这还只是一种类型小说而非文学类型,但从小说的创作和生产来看,小说创作的确进入了类型化阶段。这种“类型小说”模式使得小说越来越好看,作家的创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同时还易于改编为影视剧作品,引起影视剧制作公司的注意。出现了一批专为影视而创作的作家,进而形成了创作风格相对稳定而相似的影视作家群,如“以张欣、王海鸰、方方为代表的家庭伦理作家群;以石钟山、都梁、徐贵祥为代表的军事小说作家群;还包括了以麦家、龙一为代表的特情小说作家群”[12]3-5。
近年来,特情影视剧的出现深受人们追捧。而特情影视剧近年来银屏大热,屡创收视新高,这与特情影视作家群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是改编自同名小说,自其上映以来,把文学作品作为创作母本、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的这一做法,时至今日仍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条重要途径,二者已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麦家的小说情节安排所具备的故事性非常符合影视剧改编的要求,所以这些作品在后来无一例外地由麦家亲自担任编剧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在麦家率先将特情小说改编为影视剧取得成功的典范后,众多作家深受影响,争相模仿创作故事性极强的小说,使得特情小说逐渐模式化、产量化,龙一便在麦家的影响下走上了特情小说创作之路。特情小说不仅为特情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同时像麦家、龙一这样知名度高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成为制片方、投资方优先考虑的对象,影视剧的走俏会给原著图书出版带来新的生机,刺激消费。在特情小说与特情影视双赢的互动下,特情题材小说极易被改编为影视剧面世,带来了特情小说与特情影视剧领域的繁荣。
特情作家的集群促进了影视及图书出版行业的繁荣,使文学创作的难度有所消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作,无论是作家、制片方、还是受众,都有获益。尽管有如此优势,但也无法避免长期模式化创作使得创作题材和素材具有重复性,情节的大致相同导致受众对其具有可预见性,并且故事发生的特定背景、宣扬的作品主题总是启示人们回忆过去,目的在于力图安抚观众的心灵,所以使得小说、影视作品具有特定的怀旧性、功能性。就连麦家自身对此也有深刻感受,他曾表示:在最后一部特情系列作品《刀尖》完结后就封笔,原因主要在于“目前这一类型的小说和影视剧大量批发上市,质量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令他深感失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多年从事特情题材的写作,已经尝试过各种技巧和故事,很难再超越自己的前作”[13]。
三、借助影视叙事策略扩大小说表现力
后来真正让文坛承认的影视作家群则为表现出相近创作风格的新写实小说派,代表作家如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也正是在此之后文学创作进入真正的类型化创作阶段。新写实主义作家群作为最早的影视作家群,受到影视界的青睐,小说被改编的频率较高,刘震云的小说屡次被改编,并搬上荧幕。1995年,小说《一地鸡毛》首次“触电”,由冯小刚执导,改编成电视剧,让他从此走上编剧之路。随后《我是刘跃进》《温故1942》《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陆续与观众见面。方方的《桃花灿烂》被改编成话剧,《万箭穿心》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池莉的《来来往往》《不谈爱情》《小姐你早》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刘恒更是与影视联系密切,多次担任电影的编剧,如:《秋菊打官司》《红玫瑰白玫瑰》《西楚霸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新写实主义作家推崇“生活流”的写作形式。“生活流”原本是西方新写实电影艺术中的一种手法,主张让生活如摄像般直接进入电影,无需故事、人物、情节等艺术构思。后来,这种创作手法被运用到了小说创作中,即生活流质结构创作手法。
刘震云在中国新闻网的采访中提到:“从前,那些视觉效果好、撒狗血胸大无脑的(电影)还能赚些票房,这两年那些电影已经骗不了观众,他们喜欢看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有内容的电影。”[14]因此他的小说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原生态的生活,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他在《刘震云谈“著名编剧”称谓:我几个剧本写得非常差》中提到:“文学也从电影中吸取了很多营养。电影跟文学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故事和人物,而在于时间。电影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人物和故事背后的见识讲出来,这和用20万字写出来是非常不一样的。它要求对话要非常的精粹,如果把这一点搁到自己的小说创作里,小说质量会有极大地提高”[15]。刘震云的小说《手机》是先由编剧刘震云和导演冯小刚合作拍成了电影作品,票房不错,观众反响也很好,然后才有了小说《手机》。《手机》根据剧本改编,有很多对白的语言,具有台词化的效果,通过对《手机》的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手机》实际字数117302字,加引号的人物对话1562句,平均每107字中包含一句人物对话[16]。
池莉现在对电影的态度十分明朗,她谈到:“我从小只迷恋文学,我从来都认为只有文字才可以表达一切。现在我不这样看问题了,电影艺术运用色彩、光线等效果,把现实与想象、时间及空间统统揉和在一起,现在电影的表达空间、市场价值更有巨大潜力。”[17]由此看来,增强画面震撼力和感染力离不开色彩的鲜明这一重要元素,池莉为了更好地展现日常化叙述镜头,不仅具有动作化的效果,而且非常讲究色彩感觉,这对形成影视画面十分重要。池莉在描摹色彩构图上,尤其注重小说中人物装扮的刻画,对衣物颜色的修饰上,敢于选用冷暖色形成鲜明对比,更突出反映生活普遍及冷艳的一面,让画面显得尤为突出,给观众以更明晰的视觉感受。
也有作家在积极借鉴影视叙事手法的同时,对影视持有警惕的态度,此类作家以莫言为代表。莫言善于运用色彩词写人叙事,巧妙地让作品更加生动、形象,加大对读者视觉的冲击力。张艺谋曾说过:“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色彩的描述,那是一种非常写意的感觉。”[18]在光与影的世界里,色彩成为最能凸显作者艺术创作主旨的部分,莫言正是一位色彩搭配的美学家。他尤其看重画面的美感和色彩的搭配,用颜色装饰画面的语句比比皆是,例如在《红高粱》里,莫言对于环境的描写就格外注重对色彩的着笔,血海般的红高粱,蓝天白云,紫红高粱穗,暗红的人,“红”“蓝”“白”“紫”4种颜色,让原本抽象的文字鲜活起来,黑白的铅印文字映射到读者脑海中时,却成了一幅“秋日艳空图”,满眼都是天高云淡、心旷神怡带来的笑意。实际上,这正类似于电影中介绍场景时所常用的远景、大远景,它能将文字瞬间转化为影像,再配上巧妙的修辞手段,其互相映衬更加增强场景中生动性、视觉性,无形中让小说的艺术延展内容得到极大补充,变黑白为彩色,变纸张为天地。莫言小说中一大亮点就是他笔下绚丽多彩的大自然,这一亮点,和他自如地使用各种代表不同颜色的词语分不开,和他擅长用描绘颜色来刻画环境、背景分不开,如此运笔,使小说更富有真实感和生动感。
自从电影《红高粱》被搬上大荧幕,一举获得众多奖项,莫言成为最早因“触电”而走红的当代作家,后续也有更多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如今,许多小说家为了生存或利益,将影像化小说创作趋于商品化,莫言却并非如此。虽然莫言的小说常常被改编成影视剧,但是他从来没有为影视剧改编而写作。他不反对将小说影像化,但不以影视化为目的,正如他所言:“有才华的导演感兴趣的是小说纯正的艺术性、思想性。”[19]而且,他知道怎样保留小说原本的文体特征,使自己创作的小说不至于成为影视的附庸,他懂得如何借助影视的叙事元素及叙事策略,去更好地实现自己文学创作上的更高艺术感受,让文学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如对欲望的书写。在这个被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人的欲望渐渐被发掘和展示出来,欲望的书写如火如荼。罗兰·巴特说过:“大众文化是一部展示欲望的机器。这部机器总是说,这一定是你感兴趣的东西,好像它猜想人们自己无法发现自身的欲望一样。”一部影视剧的优秀与否可以通过卖座率体现出来,为了吸引更多读者,作家常通过最易展现人物欲望的身体写作来提高卖座率。莫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欲望化地写作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如《丰乳肥臀》,原名为《母亲与大地》,毋庸置疑,作品名更改后更加吸引读者。
随着影视在20世纪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很多作家希望利用影视赚钱,不约而同地进行剧本创作。但有的作家为了提高销量,吸引人眼球,刻意放大对欲望的描写,甚至以肉体作为卖点,刻意迎合市场需求,导致文学越来越通俗化、世俗化、媚俗化。此时,莫言表态道:“小说家不应该跟在导演的屁股后边,一个电影导演与一个小说家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契合。”[20]莫言的文章虽然含有描述关于人形体的内容,但其并非是为了表达性欲望而写,如:
我吸出了混合着枣味、糖味、鸡蛋味的乳汁,一股伟大瑰丽的液体。母亲抱着我站起来,掀起衣襟,把一只乳头塞到我嘴里,沉甸甸的乳房覆盖着我的脸,我停止哭泣。母亲奶水充足,奶汁质量高级,催得我又白又胖。[21]
虽然内容包括了一些关于人体的文字,但是字里行间,文化品味并不低俗,反而饱含深意,把用乳汁哺育众多儿女的母亲上官鲁氏喻作圣母,她用母性的光辉照亮着儿女,所展现的母性光环是丰满而肥硕的。
莫言在写作中常常表现人物的欲望,但他没有迷失在欲望化写作的俗流里。他所表现的欲望,不单单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而是把欲望当作展现人原始本性的存在,借此来表现主题和人物。如:
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22]
这场野合无疑是整部作品中最为经典的一部分。爷爷、奶奶在不相识、未相知、无言语的情况下在野地里相亲相爱,纯粹是欲望使然,这是人类最原始、简单的对于性的欲望,但在莫言的表述中,这里的欲望,却是纯洁而美好的。在这段描述中,奶奶的形象比之前完整许多,灵魂也突然有了深度。她不羁狂野,在命运中自由奔放,勇于打破封建镣铐,敢于寻求自我内心所渴望的情感。在这一点上,爷爷与奶奶达成了共识,他们相通的内心,比他们交欢的肉体更为亲密。莫言不赞成为了影视改编而进行写作,反对文学屈从于影视,让文学成为影视的附庸。实际上,他敏锐地感知着时代发展趋势,扬长避短,擅长利用影视使文学传播得更为广阔,加速文学发展。
从为迎合影视投资进行创作,到主动运用影像化创作手法便于改编,到借鉴影视创作手法扩大小说表现力,作家不断探索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作家由最初的影视创作集群,逐步走上类型化创作的道路,最终形成了被文坛所认可的新写实主义作家群。可以说,作家不断摆正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从对影视俯首称臣,到借鉴影视促成文学自身的发展,文学适应了新形势下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作家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运用语言文字思维进行写作的方法,创作活动和叙事策略也相应转变,影像化的创作方法为写作方式提供了另一种新的渠道。正如米尔佐夫说:“新视觉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23]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格外注重文字思维和视觉思维的结合,将色彩、声音等一切能对人造成强烈冲击的视听元素进行融合,营造强烈的画面感。在摒弃模式化、产量化的弊端后,小说和影视实现了“双赢”,小说创作积极吸收影视表现技巧,使文学得以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