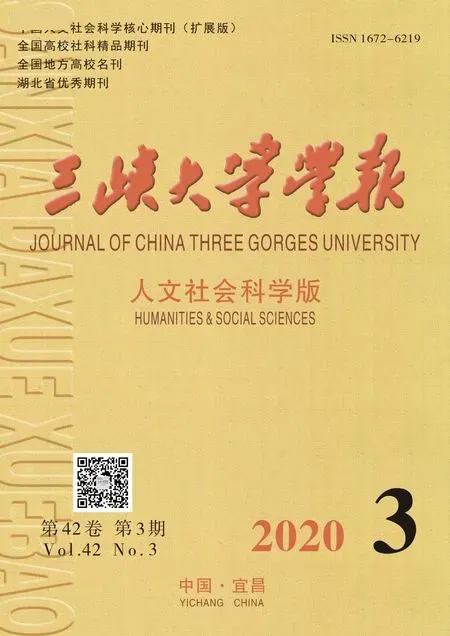论清代鄂西容美土司对辖区的社会治理
陈文元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或受限于史料、研究旨趣及史学“惯性”,学界多是从国家层面来探讨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而对土司如何治理地方的论述尚不够充分,较少从土司自身的治理方式和方法上探讨土司制度。且多认为,进入清代,土司制度已经“衰微”,土司已难较好地控制和治理辖区。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眼光向下,从土司的视角来看待土司制度与土司治理,会有不一样的制度面向与理论认识。不仅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土司在治理地方时所施行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手段对土司社会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可从清代鄂西容美土司的治理方式粗略窥探这一面貌。作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众多土司之一,鄂西容美土司不仅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得以保存,而且能够保持治内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其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政治策略与治理方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基于此,笔者拟对清代容美土司的社会治理策略与控制方式作粗略探讨,以期为容美土司研究添砖加瓦,丰富土司治理议题的相关探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与北方土司不同的是,南方土司都有自己的辖区,境内土地、人民皆属土司管理。容美土司治理范围主要位于鄂西鹤峰县,地处武陵山区,境内多族群分布,文化交互,治下土民亦兵亦农,是典型的南方溪峒社会。自明以来,容美土司是鄂西较大土司。“(容美宣抚司)领长官司五:盘顺长官司(后属施州卫直辖)、椒山玛瑙长官司、五峰石宝长官司、石梁下峒长官司、水浕源通塔平长官司。”[1]卷44《地理五》由田氏世袭。明末因军功升宣慰司。进入清代,容美土司势力不断发展,辖地扩大,对内的控制力提升,又积极发展经济,构建内外政治关系,一跃而成为鄂西诸土司的龙头,与湘西永顺土司(彭氏)、桑植土司(向氏)、保靖土司(彭氏)并列为湖广四大土司。
一、容美土司的社会治理方式和措施
土司制度与羁縻制度具有较大差异,但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土司对所辖领地有较大的治理权限,可自行设置职官和实施治理策略,中央王朝并不过多干涉。清代,容美土司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对外关系等层面,采取了多种治理方式,保持了辖区的长久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1.内控外驭:构建牢固的权力体系
自秦汉以降,土家族先民聚居的湘鄂川(渝)黔区域形成以冉、向、田、覃等为代表的蛮酋大姓,容美土司田氏是其中之一。土司制度即是建立在这些土著大姓统治的基础之上,某种意义上是中央王朝对其势力与治理范围的政治确认。容美土司由田氏家族世代承袭,受中央朝廷承认,具备法定意义。传至清代田舜年,已是第十一代第十六任土司,存续近四百年。宗族是南方民族地区土司管理结构中的核心,也是土司制度得以存续的重要基础。不仅宣慰使承袭,土司内的一些重要职位也是由田氏宗亲掌管,构成了容美土司的政治结构与权力谱系。“土司的统治机构是完整而等级森严的军政合一的组织。”[2]容美土司将军事权力集中于土司一人,分属宗亲,掌管各营,他们是容美土司社会的高级武官,属权力核心阶层。如《百顺桥碑记》(后文简称《碑记》)记载,田舜年弟乃石梁安抚司兼左营副总兵官,子辈田炳如领中营副总兵官,田遂如领右营副总兵官。容美土司利用宗族力量牢固控制治内社会,体现了南方民族地区土司典型的家族式管理与血缘性传续。而对下属四司,则通过武力、姻亲等方式以子婿领之,加强控制。水浕、椒山、五峰、石梁“皆容美属邑也,向俱外姓,今君使其子婿遥领”[3]43。上文已提到田舜年之弟田庆年乃石梁安抚司安抚使(后由其子田琨如袭领),而五峰安抚使司田耀如(后传子田召南)、水浕安抚使司田图南(容美土司田丙如子,田舜年孙)皆为田舜年子孙,椒山安抚司安抚使刘跃龙则是田舜年的二女婿。对原各安抚司家族,则以长官司安置。容美土司还利用姻亲的方式布施区域社会的政治网络。如田舜年大女婿田昀是忠峒土司宣抚使,三女婿覃承彦是东乡土司安抚使,而施南末代土司覃禹鼎则是容美末代土司田旻如的女婿。不仅如此,容美土司与湘西保靖、桑植等土司也有姻亲关系。容美土司以王朝权威通过宗族、姻亲构建地域权威,不断巩固和维持其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牢牢的控制着辖区。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土司制度,是以更深入治理的同时,又秉持“因俗而治”“怀柔远人”的治理思想,在“核心”与“边缘”之间进行良性的互动,体现了传统中国治理地域民族社会的经验和智慧。而这一经验和智慧得以施展的前提则是诸土司在治内社会开展有效的控制和对中央王朝较好的向心力。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将南方民族地区强宗大姓纳入国家权力体系,诸土司又以宗族、姻亲力量内控外驭,使得这些“隙地”逐渐被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当中,而这一过程往往又是“合法”进行的。除此之外,土司还可自行设置职官。从上述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容美土司“巧妙”地利用宗族、姻亲将权力触角植入到土司上下层社会,构建了牢固的权力体系。
2.兼收并蓄:制定适宜的管理模式
历经元明时期的发展,土司的治理方法日加成熟。土司周边分布有卫所、州县,相应的管理模式影响了土司治理。容美土司周边区域有施州卫、九溪卫和巴东县、建始县等,自然也会不同程度地借鉴、它们的管理模式。州县管理模式可追溯至明初明廷在容美土司社会设置的经历、吏目。“置湖广容美、忠建、施南、散毛四宣抚经历、知事各一员。”[4]容美土司下属四长官司(清代为安抚司)则置吏目。“置湖广容美宣抚司之水尽源通塔坪、石梁下洞二长官司流官吏目各一员。”[5]除此之外,容美土司自行设置了芙蓉州、大里州、龙家坝州等三土州。《碑记》中载有“芙蓉土知州:向大成、大里土知州:□安正、龙家坝知州:龙进云”。芙蓉土知州治容美宣慰司中府。不过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顾彩游容美时,州治已撤,官印由土经历领之。大里、龙家坝二土州则是入清后容美土司侵占邻境建始县大里、龙家坝等地后所设。
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容美土司就侵扰长阳、巴东二县,巴东县清江以南地区皆渐属容美土司。容美土司又先后侵占附近建始县革塘、永福二里和长阳县约一百余里的县地。“明季流氛荐祸,容美土司乘机肆虐。革塘等里在清江河以南,皆被侵扰”[6],以北的大里、龙家坝等地被容美土司占领后设置了大里、龙家坝二土知州。甚至更远的松滋县也曾遭容美土司染指。“旧治相传,邑之杜家沟四周皆水,即当年土司盘踞地。”[7]明末清初,容美土司更是趁乱积极扩张,吴三桂叛乱时,趁势袭占巴东红砂堡等大片土地,所辖土地甚众,成为鄂西诸土司的龙头。但因其不顾王朝法治肆意武力侵占,因而与周边府县关系颇为紧张。
明代设置卫所,实乃监控土司。不过,缓至明末,卫官与土司勾结,二者已形同一体。土司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与卫所“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社会属性不谋而合。《碑记》中“景阳千户:黄文光,南团千户:谭天辉,王家村千户:黄祖□,寨龙指挥司:刘方品”等明显带有卫所职官头衔的是容美土司采取卫所管理模式的重要体现。与附近施州卫类似,容美土司将辖区内的土民编为旗军,分列旗号,设置旗官,俨然卫所建制。“容美土司抑勒土民,分风、云、龙、虎等官为旗。旗有长,上有参将、游击、守备、千把总各官,下又有大头目,分管旗长若干千户,皆有执照。”[8]田敏先生认为,土家族土司以旗为单位来组织、管理土兵和征战,可能是对卫所军队建置的一种摹仿[9]。不仅如此,土司家族阶层的某些职官(如土舍)或与卫所制度有关。如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提到有“武职应袭支庶,在卫所亦称舍人”的记载[10]。容美土司吸收借鉴卫所军事建置,构建了强劲的军事力量,以作守土保境、对外扩张之用。
显而易见,容美土司的土司、州县、卫所三种管理模式,是基于现实政治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特点,借鉴中央王朝制度因地制宜的实践探索,是对王朝制度的变通运用[11]。王朝设置土司,是将土司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秉持“汉夷分治”“流土有别”的政治逻辑下思考如何治理土司,体现了传统中国治理地域民族社会的多元化方式与弹性机制。而土司在承接中央王朝政治控制与制度设计时,将地方性知识融入其中,依循自身社会环境构建治理秩序,不断实践探索,彰显了土司的政治智慧。
3.开放进取:实施多元的经济政策
长期以来,土民以游耕[12]为主,兼有渔猎采集及养蜂、种茶等,土司社会较为封闭落后,故有称“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但这一经济形态和社会交往格局至明末清初战乱有所改变。明末清初,时局动乱,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等势力更迭,兵事波及鄂西,“惟容美一隅可称净土”[13],诸多外地人士避乱于川湖之域的容美土司。大量外地人口进入容美土司地区,容美土司适时调整政策,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接纳外地人口,“爱客礼贤,招徕商贾”[3]5,以其所操技艺安置,竟使得“客司中者,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技艺来,皆仰膳官厨,有岁久不愿去者,即分田授室,愿为之臣,不敢复居客位”[3]47。外地人口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与较为先进的汉族农耕技艺,有些还被编为客兵。人口的多元带来的是辖区内社会经济类型更加多样。
容美土司将辖区的土地分给民众,招佃收租。“土司时,田地多系荒山,招佃开垦,先出银钱若干,一切修筑皆佃之费,田主但收其稞,以完粮赋。土司官田则分,所收以资兵食用度。”[6]发展农耕的同时,还有手工业,如容美土司平山爵府“后街长二里许,居民栉比,俱以作粉为业,有织纴者”[3]64。商贸也有一定规模。明代容美土地司地区商贸一度繁盛,清代虽未恢复明初极盛之时,但大体规模亦有之。“当明盛时,百货俱集,绸肆典铺,无不有之。流寇入扰,民遂离散,今六十年,元气未复。”[3]39土司阶层还利用自身经济实力,出资在外地拓展“业务”,如田舜年在湖广省城武昌购买了房产和商铺,田旻如在周边府县亦置有田产。容美土司地处武陵山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适合种植茶叶。容美土司有较早的茶叶种植历史,茶叶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诸山产茶,利最溥,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3]90民间流传:“白鹤井的水,容美司的茶。”总体而言,清代容美土司社会经济“是以种植农业为主,以采集、狩猎、捕鱼、养蜂、种茶、作粉等副业为辅,手工业有一定的基础,商业贸易也有初步的发展”[14],辖区内的社会经济类型较为多样。
改土归流的方式有武力改流与和平改流,如果土司地区发展水平较好,可比之“内地”设立郡县,既而中央王朝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以流官制度来替代具有割据性的土司制度。这一情况早在明初已有先例。明初思州田氏土司过早改土归流,除了二司仇杀之外,经济因素也是导致其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历经长久经营,思州、思南田氏实现了辖区的较好治理与经济发展,所以改土归流过程中并未出现过激的冲突,这一结果甚至推动了贵州省的建立(不过,二司地区基层社会发展整体上仍较为低下,所以,除了将二司上层势力清除设置州府后,其下属小土司仍然保持。这也说明,明代尚不具备实现全面改土归流的条件,时机尚不成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落后的社会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必然随之改变,改土归流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必需。”[15]清代雍正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过程中,也有很多土司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从清廷在雍正年间对容美土司顺利改土归流,以及之后流官治理与开发容美土司地区的平稳进程,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在改土归流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4.礼法并用:推行双轨的约束机制
容美土司在推行儒家文化、以“礼”治理辖区不遗余力。土司阶层以身作则,积极主动学习儒家文化,田氏家族先后出现了9位文人。明末清初是容美土司文化发展的高峰,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三位土司有诸多诗言流传于世。《碑记》不仅反映了田舜年较高的儒学素养,更体现了其对皇权的忠诚,是儒家忠君思想的切实反映。容美土司田氏“造谱”现象与家族诗人辈出更是土司精英阶层对儒家文化推崇备至的结果,在吸收、学习汉文化,接受汉文化的濡染,容美土司田氏家族走在这个进程的最前列[16]。容美土司还将家族子弟送到附近“汉地”府州县学就学,并积极与汉族士大夫交往(如文安之、严首升、顾彩)。在土司阶层影响下,儒家思想观念在容美土司社会逐渐形成,忠孝节义、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伦理纲常观念进入民众内心。“土民追求的人生价值观越来越得到了内地汉民和王朝国家的认同。”[17]顾彩在容美时,受礼甚厚,“余于中营,旗鼓以礼接之;四营以下,则下马,侧立让道,虽或时同席,不敢对坐,盖敬期主人之客,如事主也”,因而得出“国中属员皆讲君臣礼”的结论[3]44。此外,容美土司还利用饱含儒家气息的戏剧、先贤事迹传播民众顺从、忠于司主的忠义精神[18]。
容美土司积极发展儒学是内外因共同促使。一方面是中央王朝的法定要求。明朝曾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规定:“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领入学,渐染华风,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1]卷310《土司》承袭土司职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清朝更具体明令:“今后土官应袭,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19]另一方面,还有土司自身对儒家文化的崇尚和“脱蛮入儒”的文化理想。不仅容美土司,清代湖广永顺彭氏土司、四川酉阳冉氏土司、贵州水西安氏土司、广西忻城莫氏土司、云南丽江木氏土司等都有较高的儒学素养。
容美土司还拥有自己的一套刑罚,严格管理辖区内的土民。容美土司的刑罚特色打上地区社会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烙印[20]。“其刑法,重者径斩,当斩者,列五旗于公座后,君(此处指田舜年)先告天,反背以手掣之,掣得他色皆可保救,惟黑色则无救;次宫刑;次断一指;次割耳。盖奸者宫,盗者斩,慢客及失期会者割耳,窃物者断指,皆亲决,余罪则发管事人棍责,亦有死杖下者,是以境内懔懔,无敢犯法,过客遗剑于道,拾者千里追还之。”[3]5通过以上材料显示,容美土司有较为严苛的刑罚制度,其刑罚等级,分为斩刑、宫刑、断指、割耳、棍责,施斩刑时土司还要祭天。刑罚中既映衬着王朝国家的律法规范,又带有地方文化的特色。其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与严苛峻法,使土民“无敢犯法”,境内形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
5.因势利导:发展多重的对外关系
明清鼎革之际容美土司五位司主苦心孤诣,审慎把舵,制定政治去从的决策[21]。当清廷势力未触及鄂西时,容美土司选择拥护南明政权。而当清军已然控制湖广,经略西南之际,容美土司旋即归顺清廷。“(1655年)湖广容美土司田吉麟(田既霖),以所部二万投诚。上(顺治帝)嘉之,命所司速叙。”[22]但同时容美土司又与南明保持相应的联系(如与施州卫关系和与文安之交往等)。吴三桂反清之时,容美土司接受其伪令和封爵(承恩伯),至其势衰,又转投清廷。
在与卫所、“夔东十三家”以及周边府县、土司的关系处理上,容美土司区别对待。田舜年之妻刚氏即九溪卫麻寮土千户所巡捕千户刚一帅之女。与同处鄂西的施州卫,容美土司选择主动交好,一体共存。明末天启年间容美土司田楚产向施州卫赠奉观音与韦驮佛像各一尊,佛像中的铭文直观显示了容美土司与施州卫较为密切的政治关系。“明天启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容美宣抚使司宣抚使信官田楚产施铜一千斤,于四川保宁府南部县观音矶文昌祠铸造观音大士、韦驮一尊。田玄,和尚官元。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唐符一,指挥同知石美中……李一凤……”①清初,鄂西等土司与施州卫共同抵抗李过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后与鄂西地方武装合称为“夔东十三家”)犯境。“四年(1647年)李过……入施州卫,肆屠掠,与土司、卫兵战于城南(施州城)。”[23]“夔东十三家”虽打出“拥明反清”的旗号,但容美土司与其并非一体。1655年容美土司投靠清廷后还遭到“夔东十三家”刘体纯部的劫掠。因自身实力有限,容美土司只能选择隐忍,不与之正面交锋。
明末清初,容美土司侵占周边府县较甚。前文已提到,明清之交,容美土司已侵占周边府县多处土地。清初,巴东县知县齐祖望就因治理边界问题与容美土司田舜年发生过激烈争吵。最后,齐祖望上奏朝廷,提请清廷严整边防。“窃照容美土司侵占巴属连天关以北、桃符口以南一十三图土地人民,屡经望详各宪,叠蒙抚部院移咨提镇,照依旧制,酌拨官兵十百五十员名,分设红砂堡、连天关、桃符口、苦竹溪等汛。”[24]建始县被侵占土地更多,清江以南革塘、景阳和以北的大里、龙家坝等处,至清代竟成容美土司辖区,置官设兵把守。不仅如此,就连长阳县和更远的松滋县的一些土地也遭容美土司染指。为此,清廷设立“汉土疆界碑”以规范约束。
前文已述及,容美土司与鄂西东乡、忠峒、施南等土司是姻亲关系。与南面的湘西诸土司,容美土司或利用姻亲拉笼,或结盟。容美土司与保靖土司世姻结盟,与桑植土司是世姻却又是世仇的关系。时永顺土司司主尚年幼,容美土司与保靖土司常谋攻打之。“初,四大土司惟保靖与容美交好,其永顺隶岳州府,主幼不治事,国内殷庶,君常与保靖谋讨之。其桑植与容世姻,实世仇也。”[3]53-54后容美土司又与桑植土司和好,联姻如初。
明末清初,各方势力角逐,如何生存是首要问题。所做的抉择不仅要符合大的政治环境,还要依据区域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时局在复杂的势力纠葛中审时度势,注意策略和方法。明末播州土司被改土归流,重要原因即是内外关系处理不善;而清初明正土司能够重新崛起,与其妥善处理与清廷和周边番汉关系有着莫大的关联。容美土司能在明清乱世中得以保存并一跃而成为鄂西诸土司的龙头、湖广四大土司之一,发展多重的对外关系是重要原因。
二、容美土司社会治理方式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清代容美土司多维治理策略的形成原因,细究之,区域社会政治生态的改变和汉文化的影响是重要原因,土家族所处的地域环境与经济形态也有一定影响。土司制度的包容性则给容美土司治理策略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其治理特点表现为宗亲是其治理结构核心,治理方式、方法多样,良好治理成效一方面却又增加了割据性。当然,形成这一状况是历史积累的结果,而非清初一时之选。
1.治理方式的形成原因
政治生态的改变。政治生态是事物发展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鄂西的政治生态复杂,明末清初因时局变换更甚之。一方面,明末清初,鄂西多方势力角逐,无论是明廷还是清廷均无力顾及地方动乱,对土司的控制也多为遥领。国家权力的消退,对应的是容美土司自主权的扩大。从《碑记》中可知其官制与明代永乐定制相比,已有较大变化,所记五十七位职官多为“私授”,说明自主权在扩大。容美土司乘明末清初政局动乱而扩张发展,并在占领土地过程中实践探索出多种治理方式。另一方面,经过数代发展和局势变化,容美土司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明初,卫所政治地位强于州县,州县强于土司,而后州县居于卫所之上,土司政治地位未变。可到明末清初,王朝更迭,政局动荡,地方兵乱横行,由于土司在军事上的强势与区位上的优势,相比于州县的孱弱、卫所的颓废,土司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已居于二者之上,更有实力和资本,治理架构更完备。外在的“宽松”环境和内在的积累使容美土司积极实践探索出适宜的治理策略。
汉文化的影响。容美土司地处川湖之交和江汉文化辐射地带,周边又有卫所和州县,有较好区位优势和条件吸取汉文化。汉文化的主流地位以及相对土家族文化,其文明程度更高,汉文化和汉文化地区对容美土司社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美土司之所以大肆侵占邻之建始、巴东二县领地,除了土地和人口,“汉地”优越的经济文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容美土司与施州卫的互动交往,无形中对卫所管理制度吸取和借鉴。“卫所与土司并存,实际上是同一个区域内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两种文化共存于同一个区域内,必然会发生对流和互动。”[25]除此之处,容美土司向中央王朝朝贡、受中央王朝征调,田舜年甚至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等等。这些因素使得带有浓厚汉文化的典章制度、文化礼仪、风俗习惯等逐渐深入容美土司社会,进而实践传承,治理策略就是其中之一。
土家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地域环境上,施州地区“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阻,蛮僚错杂,自巴蜀而瞰荆楚者,恒以此为出奇之道”[26],以笔者实地调查鹤峰县,走访容美土司历史遗迹的经历,深觉境内山地环境更甚之,群山万壑,沟涧纵横,是典型的溪峒社会形态。土司时期的溪峒社会往往一峒数溪,一溪数司,寨落在山间分布,居住分散,聚合程度低;经济方式上,容美土司虽在明末清初战乱时期发展情况比卫所、州县地区稍好,经济类型多元,但受限于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土民仍以游耕为主,居止无定,如果纯粹采取州县编户齐民的管理方式则十分困难,多种多样的治理方式更符合容美土司社会的实际情况。治理结构上,容美土司社会是军政合一政治统治系统,土司是身兼军事、行政的长官,土民亦兵亦农,土司地区的溪峒社会与州县、卫所对应的经制社会、屯堡社会相比,有着不同的“区”与“界”。这些涵盖土家族社会民族性与地域性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施行以土司制度为主、辅之相应的治理方式是较为适宜的。
土司制度的包容性。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对一些尚处在“化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因俗而治”,将其部族首领纳入国家职官体系的同时,又给予较大的自主权,体现了传统中国统治结构中的弹性机制与多元化的治理方略,也使得土司制度具备包容性特质。对此,《明史·土司传》亦有云:“……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1]卷310《土司》《明史》乃清人所修,“然其道在于羁縻”充分体现了明清继承土司制度的政治用意。明代正统年间,广西地区“蛮乱”迭起,土酋莫祯遂向英宗建议“设土目以约蛮众,改军备以严边防”。明英宗采纳,并说:“以蛮攻蛮,古有成说。今莫祯所奏,意甚可嘉,彼果能效力,省我边费,朝廷岂惜一官,尔其酌之。”[1]卷317《广西土司列传》由此可见,基于土司制度,中央王朝关注的核心焦点是“赋役”“忠心”与“稳定”,至于土司的辖区事务及土司如何治理辖区,并不作过多的干涉。也就是说,中央王朝赋予了土司更多的职责权限,以何种方式治理辖区并不作强制规定,诸土司可依据自身情况采取多种的治理方式和方法。清代容美土司,一方面其积极效忠清廷,履行应有的职责;另一方面以宗亲力量为核心,积极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对外关系等层面实践探索治理方式,并施行了土司、州县、卫所等多种管理模式,保持了辖区社会秩序稳定,展现了土司制度的包容性。
2.治理方式的特点
一是治理核心人员是土司宗族。容美土司由田氏家族世袭,自称“自汉历唐,世守容阳”。元代设置土司后,容美田氏依据中央王朝赋予的王朝权威和自身的实力,将区域社会的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且不说司主由田氏直系宗亲世代承袭,土司还将司内的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权力依据宗亲血缘亲疏分属族内成员,确保土司社会稳固。不仅如此,容美土司还利用联姻扩大土司宗族势力,如以女婿统领下属土司而不是让外姓管理,以及与周边土司结盟、联姻等。如此一来,容美土司构建了一个核心与边缘的宗族势力架构,以血缘扩及地缘,实现区域社会的控制与治理。
二是治理策略和方法类型多样。学界一般多认为土司治理辖区表现为军事控制,治理方式单一,其实不然。对清代容美土司社会治理情况的粗略考察可知,在权力分配与政治控制上,体现了南方民族地区土司浓厚的家族式管理与血缘性传续,同时又积极吸收借鉴州县、卫所的管理模式与方法,将自身的治理体系纳入到王朝国家的治理结构当中;经济形态上,以游耕农业为主,兼及渔猎采集,适时发展商业和手工业。而当卫所屯政破败、“民逃夷地”和明末清初外地汉民不断涌入的情况,容美土司又适时接纳他们,并依其技艺,妥善安置,地区内经济形态日益多样化;容美土司还建立了一套礼法双轨并行的约束机制。一方面,土司境内刑法严苛,若有土民触犯条例,必受惩治;另一方面,历任司主都注重汉文化的学习,注重对土民的礼仪教化与儒学熏陶,可谓软硬兼施。
三是治理结果引发了地方割据。较之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进步性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控制更深入的同时又能弱化地方豪酋的军事力量,使之不能与中央王朝争雄。不过,土司制度毕竟是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间接统治制度,土司拥有较大自主权,容易产生地方割据。容美土司在辖区开展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措施,使土司境内的民众较少受到明末清初的乱战之苦,土家族文化因而得以传承和沿续,区域社会的经济较少遭到破坏,社会秩序较为稳定,这是它积极的一面。客观来说,不能因为土司制度的割据性而否定它的历史贡献[27],但与此同时,容美土司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手段和方式,土司社会日益发展,积极扩张,与周边府县关系紧张,区域社会政治生态恶劣,势力壮大的背后更是土司的割据性增强。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其目的是要将土司归入到王朝国家的统治秩序当中,如果土司势力坐大,势必难以控制,引发地方动乱,甚至危及王朝统治。这一情形,元明清三朝的诸多土司作乱早已证明。也因于此,中央王朝为加强土司管理并最终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治理,就必须消除土司割据,实行改土归流。
注 释:
① 该佛像现存于湖北省恩施州博物馆,文中引用是佛像背部的铭文。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