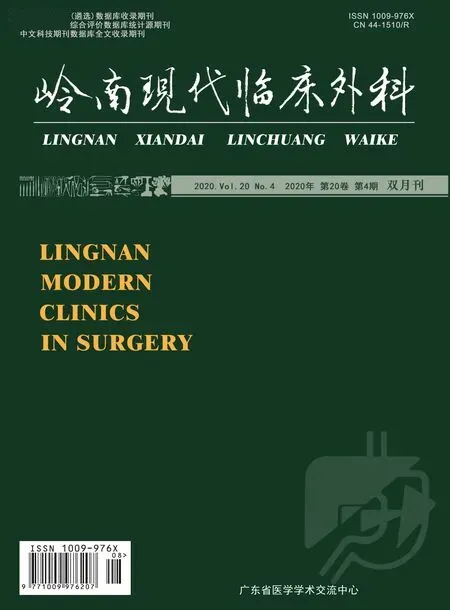Neuropilins在肿瘤中的多功能作用机制
刘想梅,徐卫国*
癌症是由正常细胞通过一系列遗传和表观遗传变化而产生的,这些变化影响着驱动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表达和功能。神经纤毛蛋白(neuropil⁃ins,NRPs)最初被认为是胚胎发育中的神经元指导信号,现在被视为组织形态发生和体内稳态以及癌症进展的主要调节剂。NRPs 参与多种信号传导途径,尤其与癌症的发生发展联系密切。然而,NRPs 在癌症中的确切作用机制很难确定。重要的是,它们促进EMT 并维持未成熟或癌症干细胞表型,如下所述。由于它们的多功能性,从肿瘤的发生到转移,神经纤毛蛋白很可能参与了癌症生物学中的主要步骤。多项研究表明,NRPs 可以通过多种机制促进癌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粘附和转移。然而,近来,一些报道表明,多种受体在调节基因表达和细胞表型可塑性方面具有新颖的功能。
1 NRPs 的特性及对肿瘤的影响
神经纤毛蛋白(Neuropilins,NRPs)为分子量120~140 kDa 的多功能跨膜糖蛋白,迄今为止,在脊椎动物中已经鉴定出两种NRP 同源物:NRP1 和NRP2,在所有脊椎动物中均有表达[1],涉及广泛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包括发育、轴突传导、血管生成、免疫以及病理状况。NRPs 在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临床疾病中通常被上调,继而调节肿瘤微环境以增强肿瘤生长,诱导血管、淋巴管生成以及增加肿瘤细胞的致癌活性[2]。Semaphorin 3A(Sema 3A)最初被确定为神经系统发育中的调控信号,一些研究报道,NRP1 通过自分泌Sema 3A 信号传导,包括肿瘤抑制因子和肿瘤启动因子,调节癌细胞的迁移,侵袭,转移扩散、血管生成及肿瘤生长[3]。同样,其他研究表明NRP1 通过HGF/SF 自分泌途径促进肿瘤的生长[4]。Yaqoob 研究团队证明,NRP1 促进成纤维细胞与可溶性纤连蛋白之间的缔合,进而帮助α5β1 整合素依赖性纤连蛋白原,并促进基质硬度,从而促进肿瘤生长[5]。实际上,在肿瘤发展过程中,癌细胞经历了几种表型变化,信号量及其受体也起着基因表达和细胞表型可塑性调节剂的重要作用,Semaphorin 对细胞形态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与细胞底物粘附和细胞骨架动力学有关[6]。这种可塑性超出了基于肿瘤发生的遗传学改变的范围,暗示了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和适应性变化以及代谢和信号通路的失调[7]。这导致了NRPs 在多种生物学功能方面的新研究领域,例如肿瘤的生长和发展以及免疫系统调节以及EMT 和纤维化中的重要作用[8]。
2 TGF⁃β1 信号通路在肿瘤中的作用机制
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是多效性配体家族的成员,许多优秀的文章详细介绍了TGF⁃β1 从抗肿瘤效应因子向促肿瘤效应因子过渡的分子基础[9-11]。多功能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1 在癌症中具有双重作用,在体内稳态和癌症早期阶段具有生长抑制和抗炎作用为积极的预后因素出现,然而,在晚期肿瘤中异常激活TGF⁃β途径将促进侵袭和转移从而导致不良预后[12,13]。表观遗传和细胞事件的积累驱动使TGFβ反应性降低和TGFβ配体表达或激活增加的表型相反,从肿瘤抑制物到启动子的明确“转换”尚不明显[14]。据报道,TGF⁃β信号传导在癌症进展的的作用包括上皮到间充质转变(EMT),细胞干性,侵袭和逃避免疫系统[15]。然而,在癌症中,TGFβ的生长抑制作用最终可以通过其受体或相关转录因子的下游信号靶点的抑制而失活[16]。在TGFβ途径中,功能突变的丧失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在胃肠癌、胰腺癌的侵袭中起重要作用[17]。功能失活的TGFβR2 与高微卫星不稳定性癌相关[18]。最近的研究表明,NRP 是多功能的共受体,具有结合不同蛋白家族的能力,包括TGF⁃β1 和其他生长因子[19]。因此,NRP/TGF⁃β相互作用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大量的生物过程。肿瘤细胞中的PDGF 与NRP1 相互作用,NPR⁃1 充当共受体以增强PDGFR 与PDGF 的亲和力,促进肿瘤细胞的运动性[20,21]。据报道,NRP1 结合并激活潜在形式的TGF⁃β1,因此推测它也可以作为TGF⁃β1 共受体,在成纤维细胞从静止阶段向激活阶段过渡期间调节TGF⁃β1 信号传导[22]。在多种细胞类型中已证明NRPs 增强TGF⁃β诱导的反应的能力,包括成纤维细胞[22],肝星状细胞(HSC)[23],内皮细胞[24],T 淋巴细胞[25],心肌细胞[26]和各种类型的癌细胞。
3 NRP 在肿瘤EMT 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上皮间质转化(EMT)是常见的细胞生物学过程,与胚胎发育密切相关,通常被癌细胞劫持以获得组织侵袭能力,EMT 过渡对于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组织形态发生至关重要,但它也经常与上皮细胞获得侵袭性/转移特性有关,是最著名的细胞可塑性程序,通过使上皮细胞丧失或减少细胞⁃细胞和细胞⁃基质的粘附并转变为更接近间充质的表型,从而促进迁移,侵袭和转移扩散[27]。EMT 被定义为典型的上皮功能丧失和间充质细胞表型的获得[28]。E⁃钙粘着蛋白的丢失,通常位于细胞⁃细胞粘附连接处,对于维持上皮表型至关重要,是EMT的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上皮细胞失去其形态和粘附能力,并获得间质表型,促进癌症的进展[29]。原发性肿瘤细胞可通过EMT 获得迁移和侵袭能力,并形成转移灶。EMT 无疑是肿瘤发展的重要过程,它为肿瘤细胞适应肿瘤的微环境提供了可能。EMT 的激活条件是多种多样的,适当的细胞环境,细胞因子和细胞外信号均可能诱发EMT。此外,EMT 相关转录因子(EMT⁃TFs)对于激活EMT也至关重要。存在三种最有希望的阳性EMT⁃TF,锌指转录因子SNAIL 家族(SNAIL1,SNAIL2 和SNAIL3),ZEB 转录因子(ZEB1 和ZEB2)和转录因子TWIST family(TWIST1 和TWIST2)[30]。在这种情况下,基因表达调控被一系列与EMT 相关的各种转录因子严重修饰,导致主要的形态和功能变化。这些修饰是动态的和可逆的,具有一系列中间功能状态[31]。值得注意的是,NRP1和NRP2可促进癌细胞表型可塑性并调控EMT 过程。由于其具有多种配体结合能力,NRP1 调节与EMT 相关的四个主要信号通路,即TGF⁃β,Hedgehog,HGF⁃/⁃cMet 和PDGF。NRP2 在TGF⁃β刺激诱导的人肝细胞癌细胞和NSCLC 癌细胞EMT 中显著高表达[32]。此外,沉默转录因子ZEB1 可降低NRP2 的表达水平[33]。在结肠癌细胞中,NRP2还可以作为TGF⁃β1 的共受体并促进其信号级联反应促进EMT 过程[34]。
4 NRP/CSC 在肿瘤中的关系
近年来,然而,关于肿瘤的发生机制产生的癌症干细胞(CSC)假说。CSC 通常被称为肿瘤起始细胞(TICs)或致瘤性癌细胞[35]。CSCs 首先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发现[36],最近在实体瘤中被发现它们对于转移极为重要[37]。癌细胞的增殖与凋亡之间的动态平衡控制着转移的生长。一些研究表明,肿瘤的复发可能是由具有自我更新和启动肿瘤能力的CSC 所引起。值得注意的是,上皮细胞干性与被称为“部分EMT”的非典型表型有关,并且诱导EMT 的信号与癌细胞干性的增强相关[38]。而且,CSC 特征和EMT 都与癌细胞转移潜力的提高密切相关。癌细胞的迁移是早期转移的关键,肿瘤细胞的变化(由EMT 获得)和微环境是帮助癌症干细胞(CSC)从原发部位逃逸的两个主要因素[39]。许多报道表明,神经纤毛蛋白广泛参与CSC 的调节。例如,人和小鼠髓母细胞瘤干细胞表达高水平的NRP1,通过破坏PI3K⁃/⁃Akt 和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MAPK)通路使CSC 标志物下调[40]。在小鼠模型中,Wnt⁃/⁃b⁃catenin 信号级联可以诱导NRP1 在乳腺癌CSC 中的表达,相反,NRP1 沉默会严重抑制NF⁃kB 活性[41],抑制肿瘤的生长。NRP1 的过表达促进人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中NF⁃kB 的活化,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和CSC 的生长、分化和增殖、侵袭[42]。尽管可能存在多种细胞自主和非细胞自主机制来维持CSC,NRP 表达与更具侵袭性的肿瘤有关,并且在CSC 中的优先表达。已经证明NRP1 能够使CSC 保持其特性并帮助其信号传导[43]。其他研究表明SOX2 调节鳞状细胞癌中NRP1 的表达[44],并且有证据表明特定microRNA 可调节肝癌CSC 中NRP1 的表达[45]。研究证明NRP1 与髓母细胞瘤CSC 的关联及其在自我更新中的作用[40]。 Hamerlick 等人[46]发现VEGF⁃VEGFR2⁃NRP1 信号传导促进胶质母细胞瘤CSC 样细胞(CD133+)的活力和肿瘤的生长。NRP2在三阴性乳腺CSCs 上优先表达,而VEGF⁃/⁃NRP2信号转导对于CSCs 的产生和肿瘤的发生发挥重要作用[47]。此外,VEGF⁃/⁃NRP2 信号传导通过人前列腺癌干细胞中的PRex1 诱导Rac1 激活,从而上调干细胞标志物的表达[48]。另外,NRP2 可以与乳腺癌细胞中α6β1 整联蛋白相互作用并起共受体作用,从而作为乳腺CSC 的标志物[49]。因此,针对NRPs 的深入研究有助于阻碍CSC 或者阻断其自我更新信号通路。
5 NRPs 在癌症治疗中的意义
癌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其中肿瘤细胞异质性以及肿瘤细胞与周围基质细胞和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决定肿瘤进展和治疗反应的关键因素。肿瘤转移是癌症致死性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渐进,多因素,多步骤的动态过程,包括从原发肿瘤中分离,侵入周围组织,侵入血液、淋巴循环系统中的生存,从血管中渗出,远处器官转移等[50]。近年来,靶向药的研发使肿瘤的治疗方法出现了新的选择[51]。而且,发现NRP 在肝癌细胞中诱导对阿霉素的化学敏感性[52],以及对人口腔鳞状细胞癌中顺铂耐药性[42]。而且,在人类乳腺癌细胞中,NRP1 信号通过Wnt/β⁃catenin 信号轴促进CSCs 特性和化学药物抵抗[53]。相反,下调NRP1的表达可以阻碍CSCs 特性而增强了骨肉瘤对阿霉素的敏感性[54],并且发现在多种人类癌细胞中干扰NRP1 的表达可以增强对5⁃氟尿嘧啶,紫杉醇或顺铂的化学敏感性[55]。在人类NSCLC 细胞中,抑制NRP1 的作用显着增强了对放疗的敏感性[56]。在黑色素瘤模型中,发现胎盘生长因子激活NRP1可驱动对VEGF 靶向治疗的耐药性[57]。而且,据报道,EGFR 和NRP1 的联合靶向克服了胰腺导管腺癌细胞中对EGFR 阻断抗体西妥昔单抗的耐药性[58]。最近,Rizzolio 及其同事表明,黑色素瘤和乳腺癌细胞中的NRP1 上调分别产生了对靶向突变BRAF 和活化HER2 致癌激酶的特异性抑制剂的抗性,重要的是,通过干扰小分子和纳米抗体的NRP1 功能,可以延迟耐药性的发作,并使肿瘤对治疗重新敏感[59]。最近发现,相反,癌细胞中NRP2 的下调可以触发对c⁃Met 癌基因靶向治疗产生耐药性的新型EGFR 依赖机制[60]。
6 展望与前景
近年来的一些报道强调了上述信号分子不仅调节细胞⁃基质粘附和触发细胞骨架重组,而且还可以控制基因表达并诱导细胞表型可塑性。尤其是某些信号量和神经纤毛蛋白,如Sema3C、Sema4C、NRP1 和NRP2 可以引发表观遗传调控功能,从而促进肿瘤的进展。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肿瘤细胞可通过EMT 获得转移和侵袭能力,导致不良预后甚至死亡。神经纤毛蛋白在癌症中以及在正常发育中的相关性可能远远超出了迄今所认为的范围,并暗示了对细胞干性,分化和可塑性的长期影响。这些发现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涉及神经纤毛蛋白或相关受体的下游或潜在涉及跨膜信号蛋白的胞内结构域的相关机制和效应途径。总体而言,这些数据提高了在抗癌组合疗法中靶向抑制神经纤毛蛋白,以预防或延迟耐药性发作的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对NRPs 作为新的治疗靶标的兴趣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