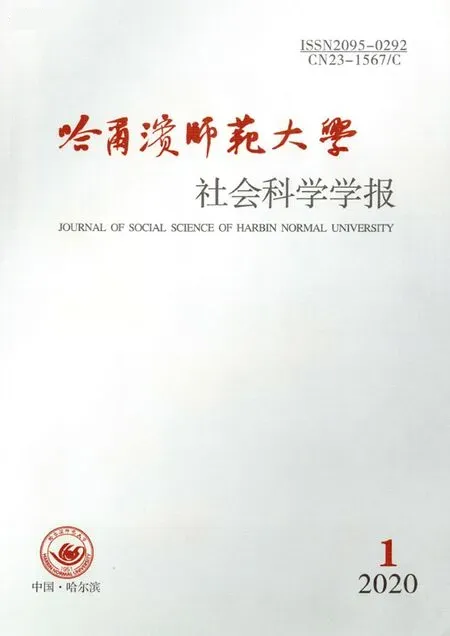终始五德推演与“斩蛇著符”文本的生成
——兼论斩蛇故事《史记》掺入问题
王洪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终始五德(又作“五德终始”)是战国阴阳学派邹衍提出的有关历史演进规律的理论主张,经过邹衍及其后学的推广传播,在战国末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秦统一六国,建章创制,即采纳了邹衍终始五德学说。终始五德的理论依据是五行相胜,也就是五行相克,即《革》卦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主张。春秋时的观点,五行相克,五行也相生,于是西汉出现了与邹衍理论相悖的,以五行相生为理论基点的新终始五德说,两套终始五德理论并行于西汉的中晚期,也就决定了西汉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显然,在历史发展潮流面前,西汉的思想界选择了五行相生的温和,王莽禅代则成为不可抗拒的政治趋势,而无关篡废。
依据五行相胜与相生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两种终始五德学说,其目的都是在为汉代寻找天命所归的理论支撑,也是在为汉代寻找“圣宗”的血统。前者解决了历史统继问题;后者推导出汉为火德,寻找到了汉为尧后的理论线索,并催生了高祖斩蛇故事,史称“斩蛇著符”。斩蛇故事是在西汉末期完成的,《史记》出现斩蛇故事,是汉儒有意识掺入的结果,本文将就此展开详细论述。
一、是承秦制,还是“斩蛇著符”?汉初德性的史料冲突
有关汉德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探讨秦人的德运开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需要为偌大帝国创立新的政治制度,从“处士横议”时代走来的诸子思想,迎来了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契机。秦始皇集比其义,在制度方面选择了阴阳家的学说,在行政层面选择了法家的体系。邹衍后学以为,周人火德,秦战胜周,是水胜火,秦当为水德。而五行之德是有征兆的,征兆又被称为符瑞。昔年秦文公打猎,获得了一条黑龙,这样的历史记载被方术士们挖掘出来,视为秦人水德的符瑞。水德朝代应有的特点是,岁首在十月,服色尚黑,数为六,音为大吕。秦始皇一并采纳,又改河水为德水。秦人称百姓为黔首,以及称经以六为胜,都表现出秦人水德的文化特征。水主阴,水德即为阴德,阴德主刑杀,故而秦始皇施行了严刑峻法,又趋入了法家的思想藩篱。
从匹夫而为天子的刘邦,骤然由汉王而建立汉朝,并没有来得及做好思想以及文化的准备,建国伊始,沿袭了秦人的政治制度,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申明了这一点:
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1](P1159-1160)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2](P1260)
以上两则史料说明,汉高祖刘邦建国,兵革未息,庶事草创,简单明了地承继了秦人的行政制度,尤其是“正朔服色”一仍秦旧,即以十月为岁首,服色尚黑。《封禅书》建黑帝祠的历史记载,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汉王)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3](P1378)
此为司马迁《历书》所谓“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说法之所由来。实际上,不啻刘邦亲自认定了汉朝的德运及服色。汉初因袭秦代的水德,服色尚黑,《史记·张苍传》也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4](P2681)张苍在秦做过御史,掌管四方文书,因而熟悉图籍,尤其擅长律历,确立了汉代的水德制度。南朝史学家沈约的观点,给予本论述强有力的支持,他说:“张苍虽是汉臣,生与周接,司秦柱下,备睹图书。且秦虽灭学,不废术数,则有周遗文虽不毕在,据汉水行,事非虚作。”[5](P259)张苍之言的可信,是最有说服力的内证,说明汉初未实行火德。
然而,班固的《汉书》却强烈质疑,甚至是批评,《律历志》谓:“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6](P974)《汉书·郊祀志》赞又曰:“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7](P1270)班固所谓“正朔服色,未睹其真”以及“卒不能明”,是说历法使用与服饰颜色选择是不正确的。仅就服色而言,站在班固以及东汉统治者的立场上来看,衣服颜色应该选择赤色,这是汉为火德的标志之一。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汉初德运采用的实际情况与西汉末期以及东汉的德运截然不同。所以,《史记》出现的有关汉初为火德的历史记载就变得相当可疑。
《高祖本纪》云:
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8](P350)
《封禅书》曰: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3](P1378)
“色上赤”是火德的标志,潜藏着汉为尧后的政治密码,其与西汉末期至东汉所崇尚的汉德是一致的,却又与司马迁反复强调汉初因袭秦制,以水德为汉德的记载完全背离。《史记》记载得如此龃龉错乱,使我们怀疑高祖醉酒斩蛇故事出现的实际时间以及历史背景。
《高祖本纪》完整地记载了高祖醉酒斩蛇的本末: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至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8](P347)
事件的核心就是赤帝子杀白帝子,班固称之为“斩蛇著符”,即以高祖剑斩白蛇为汉火德的符瑞。裴骃《集解》引应劭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秦自谓水,汉初自谓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8](P348)就这段史料而言,应劭的分析是不错的。秦居西戎,为金德,色尚白,主祠少昊之神,所以有秦为白帝子之说。相对而言,赤帝子就是刘邦。赤帝为南方之帝,五行为火,色尚赤,祭祀炎帝。根据邹衍终始五德理论,火克金,所以,赤帝子杀掉白帝子,隐喻着刘邦灭掉了秦朝而建立汉朝。那么问题来了,《史记》明确言说,秦人水德战胜了周人的火德,这里又出现了秦为金德一说,深为史家称道的司马迁,竟能出现如此的舛错吗?答案是否定的。另外,《封禅书》清清楚楚地写着“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也有《周本纪》赤乌流于王屋的记载,史料之间如此抵牾,如何通天人之际?所以,高祖醉酒斩白蛇史料的出现是突兀的、不合逻辑的,是后人掺入的。其理由如下。
司马贞《索隐》引《春秋合诚图》云:“水神哭,子褒败。”[8](P348)此为谶纬的内容。纬书《春秋汉含孳》也有类似的记载:“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东方,阳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阴所立,义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击秦,枉矢东流,水神哭,祖龙死。”[9](P593)高祖斩蛇故事与此有着明显的内在关联,只是我们无法确知二者是如何分化的,前者的影响比后者要大得多。细审《高祖本纪》,其中存在不止一处谶纬的内容,如曰:“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8](P341-342)儒家经典中不乏感生神话,在纬书中却是大书特书的内容,我们所熟知的古帝王都有自己的感生神话,其中不乏刘邦的感生神话,这正是让人怀疑的地方。刘邦感生以及醉酒斩蛇的故事有如下可疑之处:
一是感生神话。《高祖本纪》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8](P341)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谶纬有关刘邦的几则感生神话。《春秋握成图》云:“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9](P603)《诗含神雾》云:“执嘉妻含始生刘季。”又云:“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也。”[9](P259-260)执嘉是刘邦父亲的名讳,这是刘邦父子两代人的感生神话。刘邦的感生神话又与尧的感生神话形式相同。《诗含神雾》曰:“庆都与赤龙合昏,生赤帝伊祁,尧也”[9](P258), 其比附的意义非常明显。《史记》《汉书》《汉纪》都没有记载刘邦父母的名讳,纬书却又言之凿凿。司马贞《索隐》曰:“姓字皆非正史所出,盖无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温氏’。贞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贞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复,沉叹古人未闻,聊记异见,于何取实也?”刘邦起兵时,其母已经去世,所以,颜师古云:“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宁有刘媪本姓实存,史迁肯不详载,即理而言,断可知矣。”[8](P342)可见,有关刘邦父母名讳的纬书内容出现得较晚,《宋书·符瑞志》记载得尤为详细。所以,刘邦感生是后人掺入的,有人改动了司马迁的《高祖本纪》,这反而增加了醉酒斩蛇故事的可疑性。
二是圣人异表,这是谶纬极力宣扬的内容之一。高祖“隆准而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对于如此丑陋的形象,汉代人却认为是圣人的表征。《诗含神雾》云:“代汉者,龙颜珠额。”[9](P260)《春秋合成图》云:“赤帝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多黑子。赤帝之为人,视之丰,长八尺七寸。丰下兊上,龙颜日角,八采三眸,鸟庭荷胜。”[10](P765)刘媪感朱鸟或赤龙而生刘邦,那么刘邦自然非其父之相,身体像鸟,面如龙颜,前额突出如珠,这是朱鸟与赤龙感生神话的混合体,出现必然晚于单一感生神话。黑子,今天俗称痦子。刘邦身上长有很多痦子,有七十二个之多。为什么是七十二个?《易纬坤灵图》告诉我们:“五帝:东方木色苍,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黄,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10](P310)这里的五帝是指五行之帝,即苍、赤、黄、金、黑五帝,各主东南中西北五方,每帝主七十二日,所以七十二是五行帝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刘媪感赤龙而生刘邦,刘邦龙颜,左股又有七十二黑子,都是五行帝赤帝的象征。五行帝是谶纬的重要内容,其说起源较晚。所以,陈盘认为:“今《本纪》述高祖之感生及其体貌之异,完全以尧后火德之思想为其背景,盖史迁以后人所羼乱。”[11](P28)此为确论。
三是追随高祖者不记。虽然《史记》经过多人多次补作,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班固说:“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12](P2737)显然,《史记》汉初史料的来源是《楚汉春秋》,该书作者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陆贾,这是一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汉书·艺文志》著录《楚汉春秋》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楚汉春秋》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九卷,宋以后该书亡佚。奇怪的是,无一家典籍,包括类书,记载《楚汉春秋》撰有高祖醉酒斩蛇故事,而陆贾的另一部著作《新语》,也没有记载。七十年后,司马迁写作《高祖本纪》大书特书高祖醉酒斩蛇故事,而在整个西汉只有《史记》存有高祖斩蛇故事,其他文献只字不提,这是非常奇怪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刘邦一介布衣,并不能预测自己当皇帝,即便造作神话,不当出现在汉初,其时刘太公尚在;刘邦建汉袭秦水德,文帝时才有水德与土德之争,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曾参与了武帝的太初改历,汉始改为土德;西汉末年才出现火德之说,然而并未被官方认可,直至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正式颁布汉为火德,色尚赤,火德才正式写入国家法典。《史记》出现斩蛇故事以及有关刘邦的感生神话,这是不恰当的。最早在南朝时就有人开始怀疑“神母夜哭”故事,被沈约记载于《宋书·律历志》:
难者云:“汉高断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杀白帝子,然则汉非火而何?”斯又不然矣。汉若为火,则当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义况乎?盖由汉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则汉以土为赤帝子,秦以水德为白帝子也。难者又曰:“向云五德相胜,今复云土为赤帝子,何也?”答曰:“五行自有相胜之义,自有相生之义。不得以相胜废相生,相生废相胜也。相胜者,以土胜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义岂相关。”[5](P259-260)
五行相胜,五行也相生,仅从“白帝子”“赤帝子”角度看,沈约的曲为之解释是可以讲得通的。白帝为金德,其子为水德;赤帝为火德,赤帝子为土德。秦为水德,汉就是土德,这是利用了五行相生的理论。秦为水德与司马迁的记载相符,汉为土德是贾谊、公孙臣提出的,彼时汉朝已经进入到文帝统治时期,却未能实行,直至汉武帝才改水德为土德,这是沈约解释所出现的漏洞。另外,土德尚黄,《史记·高祖本纪》“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与《史记·封禅书》“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都提到了尚赤的问题,并且是因为“赤帝子”而尚赤,与尚黄产生了矛盾。司马贞考证说:“《春秋合诚图》云:‘水神哭,子褒败。’宋均以为高祖斩白蛇而神母哭,则此母水精也。此皆谬说。又注云:‘至光武乃改’者,谓改汉为火德,秦为金德,与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8](P348)从汉代建国始,直至光武帝二年(26年),汉才改为火德。五行火克金,水克火。若汉为火德,秦人不当为水德而应是金德;若汉为水德,秦人就是火德。所以,司马贞才判断为谬说。不仅唐人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宋人也表示了怀疑,《黄氏日抄》曰:“白帝子注谓指秦,叶碧庵先生以为西楚”[13],是为又一说。《史记》斩蛇故事的出现,造成了理论上以及逻辑上的混乱。然而,人们似乎是选择了相信《史记》的记载,鲜有人怀疑此则材料的可靠性。
二、水德,抑或火德:两种思想、两个前途的选择
德运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生成的,离开了具体的政治与思想环境,德性就变得虚无了,也就没有研究的必要。在绵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的古代历史确实存在“惟时”或曰“阴阳”理论指导历史发展规律总结而产生的新的理论学说,即战国时期思想家邹衍终始五德说。由于历史语境的丧失,邹衍的理论未能流传下来。《文选·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一首》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五行相胜、五行相次用事是邹衍五德终始的核心理论,与之相关的论述,《吕氏春秋·应同》篇有记载,历史发展次第如下:黄帝金德尚黄→夏禹木德尚青→商汤金德尚白→周文王火德尚赤,又云:“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14](P284)邹衍的终始五德理论创立在战国中期,他只提出了历史运行的规律,并不知道哪个诸侯国能够代周而立,但是即将出现的新王朝为水德是确定无疑的。当秦人战胜六国而获得统一的政权,五德终始由学术假说变成了现实,由理论变成了思想,充分发挥了历史作用。《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15](P237)这就是秦为水德的理论来源。
刘邦建汉沿袭了秦人水德尚黑的制度,得到了深通“历谱五德”[16](P510)张苍的支持。实际上,终始五德理论指导下的新的历史排序,暗含着承不承认秦人政权的问题:汉为水德,是就周人的火德而言,即汉的水德取代了周的火德,而非秦之“夷狄”,汉代周是历史正统间的政权更迭。无视秦政权存在的思想,显然有悖于历史常理,故明习终始五德理论的公孙臣首先起来反对。《汉书·郊祀志》载:“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17](P1212)汉文帝把此事交给北平侯丞相张苍商议,结果自然遭到张苍的反对。文帝十五年(前165年),黄龙见于成纪,被看作土德的符应,于是文帝拜公孙臣为博士,再议土德之事,其中包括巡狩、封禅、易服色、改制度等。在西汉,文帝时的公孙臣、贾谊以及武帝时的司马相如、公孙卿、壶遂、兒宽、司马迁、董仲舒都提出了“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的问题。元封七年(前104年),在群臣的鼓噪下,汉武帝开始改制,即太初改历。《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18](P199)《郊祀志》又曰:“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7](P1270)由此,以邹衍终始五德理论推衍出来的汉代土德制度,开始践行自己的政治使命,秦人水德的历史地位最终得到了承认,这是汉代儒生历史观的一种进步。汉初的德运之争,是汉代统治者无法获得政治安全感的体现,儒家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理由很简单,就是其能为汉家皇帝提供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理论庇佑,从而获得自足感。然而,即便是改了土德,革新了正朔,看来并未真正消除汉代统治者内心深处的不安,因为血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以《诗》《书》传家的楚元王一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解决了汉代帝王的血统问题,这就是出现在西汉的后期,并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的刘向父子的新终始五德理论。
《汉书·郊祀志》记载:“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7](P1270-1271)荀悦《汉纪》也有记载:“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19](P2)“以母传子”与“以子承母”意义相同,就是五行相生。五行相生并不是刘向的发明,而是相沿于战国时期的学术观点,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已经有过论述。“东方者木……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本朝。”[20](P362-363)五行相生的理论就是“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五行顺逆》曰:“火者夏,成长,本朝也。”[20](P373)这里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五行相生的理论,以木为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形成了一套自足相生的循环模式。这与刘向父子的“母传子”的运转方式是一致的。董仲舒反复强调“火也本朝”,最早提出了刘汉和火有关的理念,但却是指南方之帝而言,并不是指五行中的火德。还有一个现象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就是“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21](P1348)的问题。《史记·陈余传》载,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22](P2581)刘向云:“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23](P1964)班固则把这一天文异象看作汉代的受命之符,这和刘邦建黑帝祠自认为获水德之瑞以及张苍“河决金堤”之符有本质上的不同。班固曰:“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24](P1301)关于东井,《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孔颖达疏曰:“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连四方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则壁在室东,故称东壁。郑称参傍有玉井,则井星在参东,故称东井。推此,则箕、斗并在南方之时,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25](P462)也就是说,东井就是井星,而井星隶属于南宫朱雀,是为井、鬼、柳、星、张、翼、轸七星之一。
《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东井为南方的星宿,配属南方的古帝是炎帝,神是祝融。炎帝,《逸周书·尝麦解》《淮南子·时则训》又称为赤帝。祝融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是为火神。“五星聚于东井”的天文异象已经暗示刘汉政权火德的五行属性,这才是汉代应该选择赤旗、赤服的天道依据。故徐兴无说:“井宿所在,为南宫朱鸟之首(鹑首),南为火,为赤,这一切都为汉为火德之说提供了依据。”[26](P187)实际上,汉代为什么要选择火德,刘向已经告诉我们缘由:“高皇帝既灭秦,将都洛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23](P1951)汉“依周之德”,周为火德,汉也就为火德,这是刘向所认为的汉为火德的由来。刘向运用五行相生的理论,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汉代火德的依据,最终着眼点在于为汉代皇帝寻根,寻找刘氏的古帝血统。刘向的努力一旦成功,汉刘宗族就会从平民而变为贵族,即有着高贵的血统,政权的合法性自然不会被质疑。显然,刘向做到了这一点。
刘向《高祖颂》记载:“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27](P81)刘向把刘氏的始祖定为唐尧,并且大致勾勒了刘氏的迁徙过程。实际上,刘为尧后并不是刘向的发现,汉昭帝时眭弘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其言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28](P3154)汉家尧后与汉为火德是西汉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只是没有引起汉代帝王、儒生足够的重视罢了。昭帝时兴起的汉家禅让说,成帝时甘忠可倡言汉家再受命说(赤精子之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威压,迫使儒生博士在即将到来的历史大变革面前思考:是血淋淋的暴力革命,还是温和的禅让。刘向、刘歆父子二人给出历史的答案。
刘氏父子按照五德相生理论推导出来的帝系谱,保存在《汉书·律历志》,我们将所涉及的古帝依次排列,得到古帝循环运转的图式:
太昊(伏羲氏)木德→炎帝(神农氏)火德→黄帝(轩辕氏)土德→少昊(金天氏)金德→颛顼(高阳氏)水德→帝喾(高辛氏)木德→唐帝(陶唐氏)火德→虞帝(有虞氏)土德→伯禹(夏后氏)金德→成汤(殷商)水德→文武(周室)木德→高祖(刘汉)火德→王莽(新)土德→
其中,在太昊(伏羲氏)木德→炎帝(神农氏)火德之间多出了并不十分知名的共工,又没有给予足够的历史地位,刘歆的解释是:“《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29](P1012)显然,共工在此起着衬托的作用,提示秦的水德所处的位置不当,所以无法进入五行运转的图式。即在上边的图示中,秦在文武(周室)木德与高祖(汉)火德之间,显然其间不是水德之位,顾颉刚以为:“共工之所以得列入古史系统,只因他曾有争为帝的传说,恰与秦相近似,可以作为闰统的先例。故秦既为水,他亦只得为水;秦既为伯,他亦只得为伯。故‘为水师’及‘伯而不王’诸说必出于重排五德终始表之后。”[30](P432)前一部分是有道理的,后言“诸说必出于重排五德终始表之后”,稍显牵强,不足为说。
汉为火德,汉帝尧后,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若建立二者之间的关联,必须寻找一种理论承担起这样的职能。邹衍的终始五德说无法完成这个使命,从黄帝开始的古帝,越过了司马迁《史记》所及的颛顼、帝喾、尧舜,直接承继夏代,很难建立起尧与火德之间的联系。刘向对于阴阳五行理论是有专门研究的,著《洪范五行传论》,今佚,仅存的残章断句,令我们无法得见其全部内容。而《律历志》所载五行相生理论所生成的帝德谱系,即便刘歆有所增益,刘向的遗意还是可见一斑的。也就是说,刘向用五行相生理论建立起了汉为火德、汉帝尧后的理论联系,确立了汉代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刘姓圣人之后的高贵血统。
然而,用五行相生理论搭建起刘姓尧后、汉为火德的津梁,刘向的努力并没有使汉家江山更加稳固;相反,加速了汉帝国的灭亡,成为刘汉政权的噩梦,这是刘向所始料未及的。汉为火德尧后,虽然没有引起刘汉皇帝的过分重视,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学术假说还是有影响的。汉成帝时期,地质灾害多发,天象变异,异常天象和五行相生政治假说的配合,又有《春秋》为佐证,王莽认为“汉九世火德之厄”。“汉家尧后”,尧有禅位于舜之举,所以,“有传国之运”。按照刘向五行相生的理论,尧火德,传位于土德舜。依同此理,刘汉火德,要传位于土德舜的后人,合乎这样条件的人选,非王莽莫属。
王莽自己罗列的家族谱系曰:“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31](P4106)王莽自以为是舜的后裔,代刘氏为皇帝,自然之理。“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禅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31](P4108)班固记,王莽受命之时在丁卯日,解释说:“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31](P4113)王莽始建国,改正朔,易服色,“服色配德上黄”,国号为新,开始了两汉之际短暂的政治统治。
汉武帝太初改历之后,终西汉一代,虽有汉哀帝改元易号的插曲,都是以土德自居的。刘向父子以五行相生理论推导出的新的五德说,否认了汉为土德的祖制,提出了汉为火德说,同时推导出汉家尧后,二者的结合是汉代儒学理论及政治话语的巨大突破。高祖醉斩白蛇的故事必然是在这一理论形成之后被掺入《高祖本纪》的,同时也有着谶纬的痕迹。
而汉初有没有尚赤的问题?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汉初确实采用过红色的服饰。我们排除赤帝子杀白帝子依此形成的尚赤文献,还有如下的赤色服饰记载。《高祖本纪》载:“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其中,“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是解释旗帜为何尚赤的,应该是注文混入正文。《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32](P2616)杨权遂以为:“尚赤,意味着汉人认为自己属德为火;军旗用赤,则是按火德立制的表示。”称之为“准火德制”[33](P105)。对此,陈盘比较谨慎,认为:“高祖起兵,旗帜尚赤,虽史汉历历言之,可能是事实。然恐当时本出偶然,未必即寓帝德观念……然则仅据赤帜一事,以为高帝已以火德自居,吾未敢承。”[11](P28)钱穆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汉初尚赤,只是仓促起事,承用民间南方赤帝西方白帝的传说。”[34](P626)有学者也认同“没有实行火德制度”的事实[35](P185-186)。虽然军旗使用赤色,但汉初无火德说,研究者基本达成共识。
三、高祖斩蛇文本生成的时间及其传播
汉高祖刘邦斩蛇故事,如若流传在西汉初年,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大儒的著作以及《盐铁论》将会或多或少言及,但是在西汉,除了刘向父子提到,并未见诸记载。《汉书·郊祀志》曰:“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7](P1270-1271如果排除《史记》的记载,这是最早记载高祖斩蛇故事的文本,嗣后这一故事才流传开来。需要说明的是,《全汉文》辑录张良《与四皓书》,其中有言:“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间,志凌造化之表,但有大汉受命,祯灵显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此文出自《殷芸小说》,严可均认为“非秦汉人语”,是伪作[36](P137),此论甚确。因为“神母告符”不当出现在汉初,此系东汉班固之语。《汉书·叙传》曰:“皇矣汉祖,纂尧之绪……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37](P4236),词源即在此。
张苍在秦时为御史,掌管四方文书,归汉后,屡相诸侯王。汉六年(前201年)因功封北平侯,迁计相,以列侯身份辅佐相国萧何,高后八年(前180年)迁为御史大夫,文帝四年(前176年)拜为丞相,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免相。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公孙臣上疏欲改汉为土德,以黄龙见为瑞应,色尚黄。时为丞相的张苍,认为汉是水德,“河决金堤”是汉的符瑞。司马迁说:“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38](P1409)刘邦元年是公元前206年,汉兴39年,即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黄河之水在金堤溃决。当公孙臣提出土德尚黄的问题时,张苍强为之对,次年(前165年)黄龙见成纪,张苍自绌称病老。萧何在高祖左右建言献策,熟知高祖身世。张苍在萧何相府任官,如果其时有高祖斩蛇故事,岂能不知?何用“河决金堤”作为汉之祥瑞以难公孙臣?且言之凿凿曰:“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3](P1381)高祖以降之西汉诏书、群臣奏议以及儒生博士著述未见高祖斩蛇故事的记载,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汉人信奉符瑞,汉武帝甚至发诏书探问三代符瑞之事,诸大臣竟无一人言及高祖斩蛇故事,如若司马迁写在了《史记》里,怎能秘而不宣?
除了刘向父子,西汉几乎再无人提及高祖斩蛇的故事。新莽末,班彪作《王命论》以规谏隗嚣,曰:“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39](P4208)又曰:“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39](P4211-4212)显然,班彪继承了刘向父子的说法,同时也可以看出,高祖醉酒斩蛇的故事已经非常成熟,“神母夜号”典故直接写进《汉书》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传承让我们不得不探讨刘氏父子与班氏家族的文化渊源。
从《汉书·叙传》可知,班斿博学有俊才,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共校秘书,并且负责向成帝奏告校书之事,后受诏为汉成帝读书,深得成帝器重,“赐以秘书之副”。也就是说,皇家有的书,班斿家存有副本。《宣元六王传》云:“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39](P4203),大将军王凤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眀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40](P3324-3325),坚称不许。至此传递出三个信息:班斿曾与刘向一起校书,熟悉汉代典籍掌故;班氏家族藏有刘向校书的副本;《史记》流传不广,尤其在民间还没有传布开来。这就为增删《史记》提供了可能。
班彪是班斿的侄子,其从父辈或者是刘歆处得知高祖醉斩白蛇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班固是班彪的长子,《汉书》充斥着斩蛇的故事,是有其学术渊源的。同时,班彪自身就是个史学家。《后汉书》本传称:“继采前世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41](P1324)朱东润以为:“从赞论下面,可以断定一部或全部为班彪作者共六篇:《元帝本纪》、《成帝本纪》、《韦贤传》、《翟方进传》、《西域传》、《元后传》,其中偶有一两字底变更,这是写定时的订正。”[42]又考证说,《武五子传》《萧何曹参传》也是班彪所作。东汉王充说:“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太史公乙。”[43](P615)王充是班彪的弟子,其说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后汉书·班昭传》明确记载:“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44](P2784)班昭也对《汉书》进行了补作。实际上,一部《汉书》凝结了班氏家族两代人的心血。班彪《王命论》最早言及的高祖醉斩白蛇故事,被写进《汉书·高祖纪》是顺理成章的。
斩蛇故事传播过程中还出现了两个关键性人物:一是班固称其为“父党”的扬雄,其与刘歆同朝为官,又是刘歆之子刘棻的老师,即校书天禄阁,也经常造访班家观书,扬雄也是熟知《史记》以及高祖斩蛇故事的。扬雄曾经批评说:“《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45](P3580)《法言》之《问神》《君子》《渊骞》不同程度地对《史记》展开了批评,王充甚至认为扬雄续补了《太史公书》,即“录宣帝以至哀平”(《论衡·须颂篇》),具有良史之才。可以说,扬雄对于《史记》是熟悉的。《剧秦美新》有云:“若夫白鸠丹乌,素鱼断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来甚勤。”[46](P544)“断蛇”即为高祖斩蛇故事的概括,也就是班固所说的“断蛇著符”。如果高祖醉酒斩蛇故事此时尚未写进《史记》,那就说明,该故事恰好在西汉末期流行,王充的著述可以说明这一点。二是班彪的学生王充。《论衡》之《吉验篇》《初禀篇》《宣汉篇》《恢国篇》《纪妖篇》不同程度地记载了高祖醉酒斩蛇故事,以《纪妖篇》为最详,其与《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祖纪》记载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王充是在讥讽该故事的虚妄,隐含着对于《史记》以及《汉书》记异的批评。
﹝是﹞何谓也?曰:是高祖初起威胜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妪忽然不见也。不见,非人,非人则鬼妖矣。夫以妪非人,则知所斩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为蛇夜而当道?谓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为蛇,赤帝子为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为蛇,或为人。人与蛇异物,而其为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蛇为白帝子,则妪为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后宜备;帝者之子,官属宜盛。今一蛇死于径,一妪哭于道,云白帝子,非实,明矣。[47](P924-925)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王充是在《史记》还是在《汉书》读到的高祖斩蛇故事,只能判断出该故事的编造已经完成,并且写入史书。而对于高祖斩蛇故事的批评也见诸朱熹,他以为司马迁有“穿凿”之嫌,“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看此等书,机关熟了,少闲都坏了心术。”[48](P2952)清人编次《评鉴阐要》也批评说:“斩蛇夜哭,云气上覆,多史臣附会兴王之词。然以此而惑众煽乱者,亦有之矣。”[49]从《史记》成书至今,鲜有人怀疑斩蛇故事是被人有意识地掺入《史记》的。如果我们删除斩蛇故事,恢复《史记》记载的原貌,这样的批评是不成立的。
东汉初期,杜笃作《论都赋》曰:“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50](P2598-2599)杜笃为京兆杜陵人,系世家子弟,高祖杜延年为宣帝朝御史大夫。其客居在美阳(扶风的一个县)。第五伦上疏汉章帝有言:“笃为乡里所废,客居美阳,女弟为马氏妻,恃此交通。”[51](P1399)可知,杜笃与马氏有姻亲关系。这里的马氏系指马援次子马防这支。《后汉书·马防传》载,马防兄弟“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52](P857)。章帝建初三年(78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以杜笃为从事中郎,杜笃战死。
《论都赋》使用了高祖斩蛇典故,作为东汉政治的边缘人,一个平凡的读书人,杜笃是如何知晓高祖斩蛇故事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将二者勾连起来,这就是马援。国师刘歆有一个属官——隗嚣,因通经而被举为国士。王莽败后,隗嚣回归故里天水,被推举为上将军。我们知道,刘歆曾与班彪的叔父班斿共校秘书,因故旧之谊,班彪往依隗嚣。此时,马援也在西州。隗嚣“甚敬重之,以援为绥德将军,与决筹策”[53](P829),甚至与马援共卧起。班彪上隗嚣《王命论》言及有关汉帝的内容,马援当是熟知的。建武四年(28年)冬,马援出使洛阳,其对高祖说:“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53](P830)马援所谓“同符高祖”,是指汉光武帝刘秀“赤伏符”(1)《赤伏符》系刘秀同学强华从关中带来献上的,文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认为这是刘秀受命之符,自此称皇帝。与高祖所谓“赤帝子斩白帝子”(赤帝之符)在理路上是一致的。显见,马援是熟知高祖斩蛇故事的,其来源即在班彪的讲述。而杜笃马氏府中听闻高祖斩蛇故事的,然后以此典铺排入文章之中,就不足为奇了。
围绕高祖醉酒斩白蛇故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人物图谱,刘向、刘歆与班斿共校中秘书,高祖醉酒斩蛇故事已经开始流传;成帝将《太史公书》等中秘书赐予班斿,班斿的侄子班彪作了《王命论》,以规谏隗嚣。时马援为绥德将军,与隗嚣共卧起,是熟知《王命论》“神母夜号”故事的。马援家族流传着高祖斩蛇故事,马援次子马防的姻亲杜笃客居在马氏门下,知道了该故事,写进了《论都赋》里。大儒扬雄是班固的父党,经常往来于班氏,遍观班氏藏书,自然熟知故典。《论衡》多次提及高祖斩蛇故事,因为王充是班彪的学生。西汉末期到东汉,有文献记载的使用高祖斩蛇故事的不外乎以上数人,又都与刘氏父子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史记》高祖斩蛇故事出现的时间问题。顾颉刚肯定地说:“神母夜号的符瑞,自然应当待刘向父子发明了汉为火德的主张之后而才出现,可以无疑了”[30](P339),诚为确论。
四、高祖斩蛇文本掺入《史记》的两种可能
高祖斩蛇故事有神化高祖的命意,客观上说明汉为火德,但是从邹衍五德终始理论角度讲,汉人不承认秦的历史地位,以为汉直接承继周代而来,汉则为水德,这样就造成了实际上的汉承秦制。从汉高祖刘邦建汉一直到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都是水德,十月为岁首,服色尚黑。同年,贾谊、公孙臣从尊重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即承认秦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环,再推邹衍终始五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汉就是土德。汉相张苍断然否定了这一说法,认为汉是水德,只是服饰变成外黑内赤。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黄龙见成纪,出现了公孙臣预言的祥瑞,因为术士行诈被发觉,文帝土德改制便没有实行。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才实行了汉为土德的制度,新颁太初历以农历一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汉代因之进入五经博士时代。因此,以邹衍的终始五德理论,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汉为火德。汉不为火德,赤帝子斩杀白帝子的故事就不成立,也就是说,汉初不会有高祖斩蛇故事生成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背景,这个故事是后人加入的。谁有能力及条件将故事加入《太史公书》呢?有两种可能,即刘歆、班固等都有条件将斩蛇故事掺入《史记》。
第一种可能,刘歆加入《史记》之中
我们知道,汉代正朔问题一直困扰着儒生博士。王者受命改正朔,这是儒学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刘邦建汉并没有改正朔,而是一切承袭了秦制,这是儒生所不满的。所以改正朔的事情,时不时被提上政治议程。汉武帝太初改制,既是以国家法典的形式规定的,也是切实实行了的。然而,汉儒宗师董仲舒总结先代五行学说,在肯定五行相克的同时,也强调了五行相生的观点。刘向在此基础上,“以子承母”的规律,重推五行之运,即重构了太昊伏羲氏以来的帝德谱系,得出汉为火德的结论。元帝、成帝时期,天象骤变,灾祸屡至,皇权合法性备受质疑,汉家再受命说蜂起,刘向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大胆理论假说,是有其深刻命意的,即在理论上推导出汉为尧后,阐明汉代皇帝的血统问题,消弭天命的质疑。需要说明的是,刘向父子提出的汉为赤帝之后即为火德的理论,正史未见西汉有改火德的记载。颜师古注引邓展语曰:“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7](P1271)王莽禅汉,做足了准备工作,也未敢改汉之土德为火德。从赤精子之谶的传播来看,似乎仅是在民间流传着汉为火德的说法,遂成为王莽禅汉的依据。
最先提出汉为尧后的,是汉昭帝时符节令眭弘,他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28](P3154)眭弘所谓“汉家尧后”的论断不知所出,却为刘向所接受。《汉书·高帝纪》述汉帝谱系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54](P81)由此可知,刘向延续了眭弘的说法,以为汉帝出自尧后,并且用新终始五德说加以证明。刘歆则用文献证明了乃父观点的正确性。
刘氏得姓迁徙,见于《左传》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上文有刘向补足的成分。在河平中,刘向父子共校秘书,接触到了内府所藏的《左传》,父子曾经质问《左氏》大义。《汉书》记载,刘歆接触到了《左传》,“大好之”,开始向丞相史尹咸、丞相翟方进受经,质问大义。“《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23](P1969)。“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23](P1967)。所以不待贾逵才提出,刘歆是知道的,甚至是刘歆加入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周为唐杜氏”,孔颖达云:“(刘)炫于处秦为刘,谓非丘明之笔,豕韦、唐、杜,不信元凯之言,已之远祖,数自讥讦,必将见嗤。”[55](P1979)前人已经怀疑刘歆于《左氏》中作伪,疏通证明刘氏的渊源,案底宛然在目,何况刘歆的篡改,一方面为刘氏增添光彩,另一方面,证明了汉家尧后、火德的正确性。
班彪的学生王充《论衡·案书篇》记载:“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56](P1164)与刘歆同朝为官的桓谭《新论·正经篇》也说:“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57](P39)从侧面说明了刘氏父子对于《左氏》的熟悉程度,然而我们并未看到其他文献记载刘向、刘歆父子二人论述刘氏为尧后,最早提出刘氏为尧后有文献证明的是班彪《王命论》以及汉章帝时贾逵。
贾逵是刘歆学生贾徽之子,刘歆授贾徽《左氏春秋》,贾徽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传授贾逵。建初元年(76年),贾逵对汉章帝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58](P1237)此时,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所以,汉家尧后的文献详细出现在《汉书·高帝纪》就顺理成章了。
刘氏父子对于《左传》的精熟程度,附以新终始五德说,从而使眭弘汉为尧后的观点变得有理有据。汉高祖醉酒斩蛇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具体起于何时,但在《新序·杂事》里有与之相似的故事。
晋文公出猎,前驱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闻之,诸侯梦恶则修德,大夫梦恶则修官,士梦恶则修身,如是而祸不至矣。今寡人有过,天以戒寡人。”还车而反。前驱曰:“臣闻之,喜者无赏,怒者无刑。今祸福已在前矣,不可变,何不遂驱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祸福未发,犹可化也。还车反,宿斋三日,请于庙曰:“孤少,牺不肥,币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猎,无度数,罪二也;孤多赋敛,重刑罚,罪三也。请自今以来者,关市无征,泽梁无赋敛,赦罪人,旧田半税,新田不税。”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梦天帝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为,而罪当死。”发梦视蛇,臭腐矣。谒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奈何其无究理而任天也,应之以德而已。”[59](P215-219)
此故事不见《国语》《左传》《史记·晋世家》,贾谊《新书》卷六《春秋》有记载。虽然内容不同,但是两个故事的结构相近。同时从侧面说明,汉初对于蛇的认知,依然停留在邪恶、灾难层面,而不是祥瑞。《新序》所载孙叔敖杀两头蛇的故事则是最好的明证。蛇为龙子的传说,是汉成帝以后,谶纬大力宣扬的内容之一,与感生神话有关。刘向生活在宣、元、成帝时期,刘向卒后一年,成帝崩。这一时期是谶纬酝酿发育阶段,平帝以后开始大规模流行;刘向是汉室的忠臣,其所创立的新终始五德说,是为汉室服务的;从刘向著述不载高祖斩蛇故事,恰恰说明该故事尚未成形。从文献整理角度来看,刘向谨守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圣训,校勘、整理,最后缮写出定本,并无改编增补文献的记载。所以,高祖斩蛇故事掺入《史记》的最大嫌疑人就是刘歆。
刘歆则有与刘向不同的政治立场,他是亲王莽的,在新莽代汉的政治操弄过程中,给予王莽最大的理论以及学术上的支持,这就是《世经》的出现。《世经》从法理上确立了汉为尧后、汉为火德的理论体系,为“王莽禅让”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一理论成熟时期,也正是谶纬兴起之时,赤帝子杀白帝子就有了双重的意味,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是确立了汉皇的血统以及正朔问题,二是承认了历史发展的禅让规律,而后者恰恰是王莽代汉最强有力的依据。所以,高祖醉斩白蛇的故事出现得较晚,尤其是谶纬内容的附会,是其明证。而刘歆具备掺入《史记》的条件,即河平中就与其父刘向一起校中秘书,将其写入《史记》是顺理成章的。成帝曾将《太史公书》副本赐予班氏,如果将高祖斩蛇故事掺入《高祖本纪》,必然要在《史记》录副本之前。如果秘书本与班氏副本记载不统一,很快会被阅读者发现。从班彪《王命论》使用高祖斩蛇故事情况来看,班氏藏《太史公书》已经存在该故事。所以说,高祖斩蛇故事是在刘歆校书时加入的,扬雄也使用过高祖斩蛇故事,也可证明这一点。那么,有能力和条件加入《高祖本纪》的就是刘歆。
刘歆曾经关注史事,拟补缀汉书。《后汉书·班彪传》载:“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章怀太子贤注曰:“好事者谓杨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41](P1325)所以说,刘歆也有补《太史公书》的行动,故刘知己说:“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60](P314)于此更增加了刘歆增补《高祖本纪》的可能性。《陔余丛考》“班书颜注皆有所本”条曰:“葛洪云: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完本,但杂记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王鏊因推论之,谓班书实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选》中所载多不称,何其长于史而短于文?及观葛洪所云,乃知《汉书》全取于歆也。”[61](P106)班固全取于刘歆《汉书》的观点是不准确的,然而,刘歆《汉书》与班氏《汉书·高祖本纪》有渊源是可以肯定的,资料来源基本相同。此可以从侧面印证刘歆有篡改《史记》的机会和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范晔云“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显然,已经有西汉末期敷衍的故事被补入《史记》之中。
第二种可能,班固等人增补
司马迁所作《史记》,藏在自己外甥杨恽家一部副本。班固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62](P2737)也就是说,西汉成帝时期,民间流传着《太史公书》。五凤二年(前56年),杨恽以妖言大逆不道罪腰斩,杨家藏本不知所踪,元成帝以后基本无人提到高祖醉酒斩蛇故事,说明民间几乎没有《太史公书》,即便有《太史公书》流传,《高祖本纪》也未载高祖斩蛇故事,这就出现了该故事篡入《史记》的第二种可能。
除了刘向父子以外,最早提及高祖斩蛇故事的是班彪《王命论》。其文曰:“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这时正是谶纬流行时期,谶纬的痕迹宛然在目。班彪曾经采择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史记后传》数十篇,史事未竟而卒于官。《史通》记曰:“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60](P314)其子班固踵继其事,同时班固还有另一项使命——在东观典校皇家秘书。《后汉书·班固传》记载,汉明帝奇其才,“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吏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63](P1334)。高祖醉酒斩蛇故事有可能是在汉明帝永平中期以后,班固等人东观校书,将后起的故事掺入《史记》相关篇章,使其与《汉书》的记载相一致。汉为火德的内部纽带最终得以确立,形成了汉高祖与光武帝在法统上的一致性,东汉建立的政权自然有其合法性。既达到了宣扬汉为尧后火德的政治目的,也有谄谀“今上”——汉明帝的意味存在。与班固在东观一起校书的,此时还有贾逵、杜抚、杨终、刘騊駼等,在一定意义上说,高祖斩蛇故事就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
综上,汉初承秦制,沿袭故秦正朔服色,并无火德之说。也就是说,没有赤帝子斩杀白帝子故事产生的思想与政治语境。只有当汉家尧后与汉为火德之说充分结合,做到水乳相融后,高祖醉斩白蛇故事发生的条件便具备了。刘向、刘歆父子二人的新终始五德说以及《左传》的出现,成为二者契合的津梁。刘向提出新学说的目的是在为汉代君主寻找法统与血统的理论依据,稳定处于舆论旋涡中的汉室江山。而刘歆则是王莽的辅弼,尧后火德背后潜藏的是“禅让”的深层政治思考,父子不同目的的同一论证结果,恰好出现在谶纬出现并流行的时代,高祖感生、醉斩白蛇的故事便应运而生,而后被掺入《史记·高祖本纪》,同时进行一系列的改编,政治目的昭然若揭。最有资格与条件将高祖斩白蛇故事掺入《史记》的,一是刘歆,二是撰作《汉书》的班固以及同在东观校书的贾逵等人。前者在《史记》录副被赐予班氏之前必须完成,两本《史记》才不会有差异。后者是在创作《高帝纪》时将高祖醉斩白蛇的故事写入,以校书之便,将其掺入《史记》,并改动了相关篇章,使公私所藏的两本《史记》以及《汉书》的记载,达到高度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