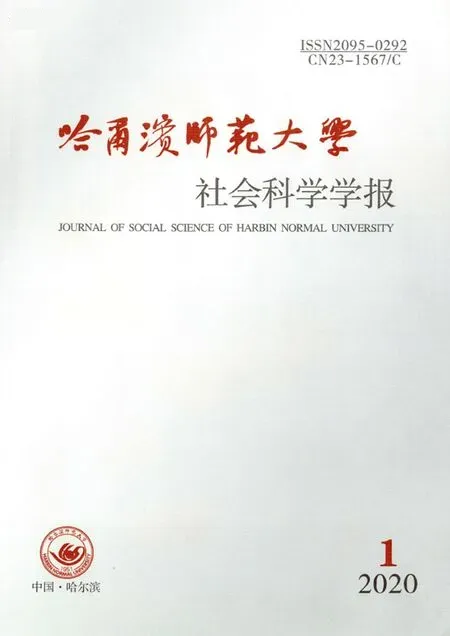卡夫卡《变形记》与布尔加科夫《狗心》的变形设计比较
李聪慧,高建华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年)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作家之一,他生前鲜为人知,作品在其去世后由友人布罗德整理后出版。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年)是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其作品曾一度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发表,直到80年代伴随着“回归文学”的浪潮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虽然卡夫卡和布尔加科夫的创作经历不尽相同,但对二者来说,写作不是为了取悦大众,获得赞誉,而是为了个体精神的需要,是个人生命体验的结晶。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主要讲述了推销员格雷戈尔·萨姆莎一觉醒来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布尔加科夫的代表作《狗心》主要讲述的是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把一只流浪狗带回了家,把刚死亡的三弦师的脑垂体和性腺移植到狗的身上来进行实验,结果这只狗渐渐进化成人,却秉承了三弦师的所有恶劣秉性的故事。《变形记》和《狗心》都是涉及变形的作品,这两部作品虽然创作背景不同,但在艺术设计上却有颇多相似之处。通过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对“变形”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类似的应对策略和不同审美取向,以及20世纪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的精神面貌和作者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
一、变形对象的选择
变形对象的选择与叙事环境息息相关,也影响到作品的叙事视角。在两部作品中,作者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变形对象作为故事主体,但这两个变形对象具有一个共同点,即二者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沙里克这只流浪狗的境遇甚至连底层人物都不如。二者都承担了来自社会的层层压力,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境况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位作者都将叙事范围缩小到普通人的范畴。
《变形记》的变形主体格雷戈尔是一名旅行推销员,他的生活环境恶劣,长期处于被压榨的状态。为了还清父母的欠款,格雷戈尔不得不在公司上班,“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生意上的烦人事比在家多得多,还得忍受旅行带来的痛苦,倒换火车老得提着心,吃饭不定时,饭菜又差,交往的人经常变换,相交时间不长,感情无法深入”[1](P45-46)。《狗心》的变形主体是一只叫沙里克的流浪狗。虽然“沙里克”在俄语中意为“圆球”,但是沙里克却骨瘦如柴,不仅时常挨饿还饱受欺凌。在故事的开端,它被中央经委职工标准营养食堂的炊事员用一桶热水烫伤,在门洞中伴着暴风雪哀号。与它的形象相平行的是一个女打字员,这个女打字员拿着最低的工资,为了拿到一点钱备受欺辱。沙里克的境况却连她都不如:“我可怜她,可怜!但我更可怜自己……她总还有个家,回去可以暖和暖和身子,可我呢,我呢……我上哪儿暖和去?”[2](P101)《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小人物的代表,他们越是辛劳就越是陷入无法挣脱的贫困的窠臼,人生充满荒诞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社会充满了竞争和压力,因而这样的弱者内心充满着焦虑感与灾难感,带着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苦闷情绪。而沙里克是只流浪狗,动物作为在生物中比人更弱小的存在,其生存状况也可以反映出社会的道德状况和经济情况:人们的善意和恶意都会投射到这弱小的动物身上,社会的繁荣或是衰败也影响着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
因为变形的发生,主人公便在不同时段分别体验了动物与人的生存模式和生命视角。因此变形主人公的选择还影响到视角的选择。在这方面,卡夫卡和布尔加科夫有着相同的考量,即用非人的视角展现出不同的观察点。《变形记》中格雷戈尔在故事伊始便是虫形,因此其观察都是从甲虫的角度出发,只有回忆的视角是属于人的视角。从虫的角度来看人,便能将自身剥离于人类社会复杂关系网络之外,用非人类的角度来审视人类,将其本原状态如实呈现。《狗心》中狗的视角是人类所没有发现的真实的视角,作者通过狗的视角如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真实状况。在文中,狗的视角并非一直存在,主要出现在开头与结尾。当狗变成人,他便不再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的视角便融入人类社会,同人的距离消失而不再有发现事实的眼睛。狗的视角的消失,也代表着狗为社会环境所同化。沙里克得到了人的身份后,便以社会人的姿态被纳入人类社会,由善良的狗心变成丑陋的人心,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环境和人的本性的辛辣讽刺。格雷戈尔由人变成虫,则是被排除于社会之外,充满寓意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孤独的精神状态。
二、变形情节的设计
《变形记》和《狗心》变形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有着差异,但设计的核心都在于通过主体的变形来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在主体的变化体验中透露出深刻的讽刺意味。卡夫卡借虫的孤独写出了世界的孤独和扭曲,布尔加科夫借狗心批判了社会制度的残缺僵化与道德的衰落。两部作品不同的变形设计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和审美倾向。
《变形记》中未交代变形的原因,并将人物的变形置于故事的开头:“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莎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1](P45)事情的起因莫名其妙,荒诞而无迹可寻。在这里,变形是一切的开端。而在《狗心》中,变形是故事的转折和高潮的起点。流浪狗沙里克变形成人也是有理有据的:这只狗被菲利波维奇教授选中作为恢复青春实验的试验品,他把死亡的三弦师的性腺和脑垂体移植到狗的身体里,狗日益变化最后变成人。变形的原因容科幻性与现实性于一体。
在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设计中,因变形而引发的变化是最引人深思之处。在《变形记》中,随着自己变身为虫,格雷戈尔的生活习性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喜欢新鲜的食物,而对腐烂的食物情有独钟。他不再睡在床上,而更爱在天花板上爬行。他的生活习性经历了从人到虫的转变。除此之外,格雷戈尔的精神世界也越来越趋向虫性。格雷戈尔的妹妹将他的房间搬空即是通过观察格雷戈尔的变化而做出的举动。而格雷戈尔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希望房间空出来便于自己爬行。房间的一切就像是格雷戈尔的记忆,是格雷戈尔与人世间的联系,是他作为人类和过去相连接的存在。格雷戈尔真的希望房间空出来,是因为他失去了语言能力,使得他不能与人类保持联系、与过去保持连贯,他已脱离了人类社会而不能称之为人。这也隐喻着现代人逼仄的精神空间及与他人沟通断绝的精神孤岛状态。从见到格雷戈尔变成虫的那一刻,格雷戈尔的父母便不再和蔼可亲,父母对格雷戈尔这个异类是惊恐和排斥的。每当格雷戈尔走出房间,全家人便如临大敌。没有人去碰触格雷戈尔,父亲甚至用一个苹果将他打成重伤。而格雷戈尔的母亲对于儿子除了害怕便没有别的情感。在格雷戈尔被妹妹的琴声吸引爬出房门吓跑房客后,门内和门外的矛盾就达到了高潮。一个失语的人的行为只能由门外掌握话语权的人来定义,因此当格雷戈尔被家人判定为是威胁和危险品后,格雷戈尔只能留在房间里等待死亡。
在《狗心》中,狗变形前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变形前,它比人活得跟艰难。人们将它作为欺凌的对象,用虐待的方式在它身上发泄情绪。中央经委标准营养食堂的炊事员用热水泼在它身上,将它烫伤。作为局外者,它将制度掩盖下的腐败与不公看得清清楚楚。它还有着同情心,可怜那个薪水微薄的女打字员,清楚地了解她的处境。在做完手术后,狗变成了人。他不仅继承了三弦师的恶劣秉性,注意穿着打扮和吃喝玩乐,插科打诨,调戏厨娘,欺骗女职员的爱情,甚至还与公寓管委会的人共同对付恩人,得寸进尺毫不餍足。在讨论到办身份证明以备服兵役等需要时,沙里科夫大喊道:“哪儿打仗我都不去!”[2](P173)而这样的人却当上了“莫斯科公用事业局清除无主动物(野猫之类)科科长”[2](P208),既荒诞可笑又充满讽刺意味。在公寓管委会的施翁德尔等一些人的影响下,沙里科夫肆无忌惮地享受着作为无产者的身份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却没有理解革命和政治宣传话语的精髓,“布尔加科夫用沙里克由狗变人的整个过程来讽刺布尔什维克创造具有集体人格的‘新人’的过程。这些‘新人’大多是过去的下层民众……革命之后,这些底层人民进入体制,被打上印记,成了名义上的统治阶级,不仅解决了温饱,还获得了一定的权力,便从此视自己的同类为低自己一等的异类,肆意践踏,而缺乏素养也使得他们被体制左右,失去了应有的良知和价值判断,被推搡着前进,成为一股盲目又可怕的力量”[3](P48)。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教授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原来认为爱抚才是与动物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因此在对待沙里科夫的态度上一再忍让,认为自己可以将其训化,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痛心地把沙里科夫恢复原样。用教授的话来说:“问题的可怕在于他现在长的恰恰是人心,而不是狗心。在自然界各种各样的心里面就属人心最坏。”[2](P204)因为人心,所以教授做了恢复青春的实验;因为人心,狗变成人后继承了人的恶性;因为人心,人生产恶而又自食恶果。
从变形结局来说,《变形记》的最后,格雷戈尔不知不觉死在了已变成杂物间的自己的房间,被佣人随意处理了尸体。直到生命的终结,格雷戈尔也没有得到人们一丝善意的同情和怜悯。他和周围的杂物一样失去价值而被人遗忘: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意味着金钱,一切都被估价,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都是件商品。而同样的命运也将发生在格雷戈尔的妹妹葛蕾特身上,人的命运在不断延续。《狗心》的最后,教授实在无法忍受变成人后的沙里克,通过手术将他变回了狗。沙里克躺在主人坐着的沙发旁的地毯上,感到心中惬意而又美好。作品在狗儿沙里克对幸福的憧憬中结束,体现出作家对人类和谐安宁生活的期盼。
两位作家在变形设计上的不同,体现了他们所继承的不同的文学传统与以及对传统的革新。《变形记》是现代文学的典型之作,情节上更加荒诞,追求内在性,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相应和。在《狗心》中,作者将时代热门问题,如肌体年轻化手术和住房紧缩以及翻身成为名义上统治阶级的“新人”这些现实问题熔于一炉,继承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呈现出怪诞、幻想与现实交融的风格。两部作品都将作者对各自社会的反思以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既荒诞而又发人深省。
三、变形主体的身份问题
变形问题必然牵扯到变形主体的身份问题,即原有的身份和现在的身份问题。卡夫卡和布尔加科夫的作品虽然有不同的变形设计,但是都展现了对这个焦点问题的关注。
在《变形记》中,作者将格雷戈尔与社会的关系一一消解。对于父母来说,格雷戈尔是儿子。为了还清父母的欠款,格雷戈尔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从事旅行推销员的职业。为此,他没有长久交往的朋友,没有享受过美食和阳光。当格雷戈尔变成虫后,他为自己无法工作养家感到深深的愧疚,但父母却不再亲切对待他,并且视其为家庭境况变差的罪魁祸首。格雷戈尔作为儿子的家庭关系被消解了,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其实是金钱关系的实质也被揭露出来。而唯一同情他的妹妹,也因为兄长吓走房客,而否认格雷戈尔的身份:“或许你们看不清楚,可我是看清楚了。在这怪物面前我不愿说出我哥哥的名字,所以我说:我们一定得设法弄走它……”[1](P79)
格雷戈尔一觉醒来变形成虫,然而他心中想的却是怎么去上班,按时赶上下一班火车。“就算他赶得上这班车,老板照样也会大发雷霆……那么请病假好不好呢?……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公司的特约医生来,还会为他的懒惰而责怪他的父母。所有的借口都会因为医生的在场而被反驳掉,对这位医生而言,世界上根本就只有磨洋工泡病号的极为健康的人……”[1](P46)在工作中,格雷戈尔的价值被最大限度地压榨,他个人的生存空间被紧缩。在变成虫的格雷戈尔见到公司代理后,他立即失去了工作,因为他已经无价值可言。合理的雇佣关系的实质,其实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
所有人都知道格雷戈尔变成了虫,然而却没有人会说格雷戈尔曾经是个人。在别人的肯定与否定中,格雷戈尔的现在被确认了下来。当格雷戈尔的房间被清空,他的现在与过去便被割裂。当最后的亲人即妹妹否认格雷戈尔,格雷戈尔便不再是个人,也不曾是个人。也许格雷戈尔的妹妹也会变成虫,人类都会变成虫。人们经历着社会发展的变革,却未曾注意自己与畸形社会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契合着现代社会人类丢失自我存在价值的身份危机,其深刻的身份焦虑融入了弥漫世界的人类共同的迷惘无助”[4](P162-163)。
在《狗心》中,同样也涉及身份问题。沙里克是一只狗时就对自己的身份十分在意。刚开始时它是只流浪狗,女打字员为它取了个名字叫“沙里克”,意为“圆球”。对待这个名字,它是这样想的:“叫这个名字,该是圆圆的,胖胖的,傻乎乎的……可它呢,又高又瘦……不过是条无家可归的野狗。话说回来,这名字不赖,单为这个也得谢谢那个小妞儿。”[2](P102)可见一只狗也对自己的姓名极其重视,名字便是身份的一部分。而当他遇见教授后,他对自己的定位不再是流浪狗,而是贵族家的狗,并且开始追溯自己的血统,认为自己有纽芬兰潜水狗的血统:“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是个有眼力的人,不会随便捡到一条野狗就捡回来。”[2](P137)等沙里克进化成人后,他除了衣装打扮披上“文明的外衣”以外,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身份问题:“没有证件怎么行?这事儿,我可是抱歉了。您自个儿也知道,没有证件的黑人是不准存在的。”[2](P168)公寓委员会的施翁德尔要求教授为沙里克开具证明帮助他拿到证件,施翁德尔说:“证件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2](P172)而教授对此直言批评:“见鬼!我根本就反对领这种愚蠢的证件。”[2](P172)沙里克从狗到人对身份的在乎,讽刺了当时社会重要的“身份”问题。没有身份证,个人的存在就无法证明。鲜活的个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就寄托在薄薄一张纸上。
对身份问题的关注,反映了时下人们精神上的迷惘。奥地利与苏联可以说是两种社会制度的代表。然而在这两种制度的架构下、在宏观的经济发展下,个体的生命体验却被忽略。《变形记》和《狗心》可以说是两位作者对普通人的生命困惑和生存困境的表达。
在布尔加科夫写作时期,斯大林政治体制集权不断强化,思想意识趋于统一,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日益加强,知识分子游离于意识形态边缘失去话语权。《狗心》即是因为对现实强烈的讽刺而遭查禁,但即使在无法言说的情况下,布尔加科夫仍然坚持文学创作。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个人遭遇,让卡夫卡对社会的体悟与布尔加科夫有所不同。卡夫卡短暂的一生经历了一个极为黑暗、沉闷的时代。他目睹了奥匈帝国的土崩瓦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苦难,父亲的专横让他压抑,犹太人的身份让他感到漂泊无依。这一切让他感到精神上的苦闷与孤独,写作更是他个人的精神需要。布尔加科夫和卡夫卡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但是二者在面对社会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似的艺术设计,将其社会经历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化成变形的虫与狗的形象,充满象征和寓意,意味无穷。这二人创作的相似与差异,体现了两位不同国度的作家不同的审美风格和艺术倾向以及相同的社会责任感,反映出不同制度下人们所面临的共同的精神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