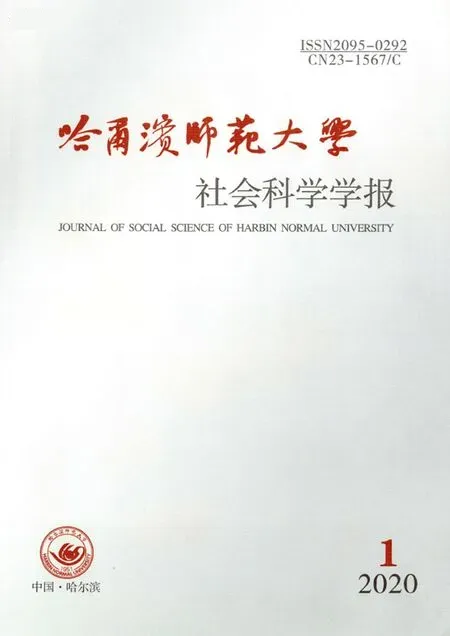唯物史观的三维透视
刘文杰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在表述唯物史观时,马克思用的是“制约”一词,而不是“决定”一词,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P591)。恩格斯曾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例诠释这个论断,哲学与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当时德国经济虽也高涨但绝非最先进,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但在哲学上却演奏第一小提琴。就是说没有经济的高涨就没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繁荣,但在经济都高涨的前提下,经济状况最好未必在其他领域也最先进。这意味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产相适应,但并不完全一致,这便是“制约”一词的内涵。至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缘何与物质生产存在不一致,可从三个视角予以解析。
一、事物对物质资料的需求有额定值
世界的改变最终要靠物质力量来实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必定需要物质资料,即便马拉松跑、歌唱等可以不要辅助工具,还是需要生活资料以维持主体生存,但事物对物质资料的需求有额定值,物质资料并非越多越好。
生活资料对于主体可谓生死攸关,但随着其量的变化,生活资料的效用有明显转折。毫无疑问,生活资料为零且不再生产时,人类的一切早晚都会变为零,就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2](P289)为维持生命活力,人必须每天都摄入食物以获取能量,但这里有一个正常需要值。这个正常需要值就成为一个阀值,在阀值之下,食物摄入量不足,生命状态随摄入量的增加而改善,二者正相关,大体上成正比;当达到阀值时,生命处在最佳状态;超过阀值时,营养摄入过多反而对健康不利,生命的状态从最佳往下滑落,二者为负相关关系;而且摄入量有一个上限,人不可能无限地进食。这样,摄入量在阀值时生活资料的效用最大,营养过剩与饥寒交迫皆非最佳状态,所谓过犹不及。毋庸置疑,生命状态会影响人在所有领域的活动,摄入量超过正常需要值的人的活动成效反而不如正常状态之人,如健康者要比肥胖者跑得快。当然,并非生活资料富余就必定超量摄入,人可以控制自己别超量,这样的话,在每个人的生活资料都富余之后,个体的生命状态与生活资料富余得多还是少就没什么关联了,这引起连锁反应,使得很多事情与物质条件不一致。一般说来,个体是在生活得到保障后才能超越物质条件;但对社会而言,在生活资料不足以满足全体成员所需时,也能有所超越,因为存在社会分工。进入阶级社会后,人类生活的丰富性由不同的职业来体现,像吟唱、舞蹈等不需要外在工具的艺术只要主体能生存就能繁荣发展,而且它们主要由统治阶级来供养,所以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差,在这些领域却能取得璀璨成就,远超那些发达国家。
生活资料之外的物质资料被作为工具使用,它在作用机制上与生活资料有所不同。生活资料的效用主要决定于量而非质,只要能吃饱,普通食物与高档食物差别就不大。而工具的效用主要决定于质而非量,生产力水平先进的工具的效用高于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不言而喻,收割机优于镰刀,飞机优于牛车,导弹优于弓箭。由此可见,在质上落后就很难发生超越,但在同质的前提下,又确实可以发生超越,还是因为事物对物质资料的需求有额定值,满足额定值就可以跨过门槛。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专注于某个领域,满足该领域对物质资料的需求,在该领域取得突破,就能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先进国家,如“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后中国的军事地位就高于当时其在全球的经济位次,这便是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综合而论,正是因为具体事物对物质资料的需求有额定值,经济上的落后者才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超越经济上的先进者。
二、其他客观因素的扰动引起偏离
我们知道,经历数百万年,古猿才进化为人,处在二者之间的是过渡生物。过渡生物已不再采集而是通过生产来获得生活资料,从而区别于动物。过渡生物开始只有三类活动:物质生产、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繁衍)。这三类活动是并列的,“从历史的最初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3](P532)。“同时存在”意味着物质生产、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相互外在,不存在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这是一种横向的外在,物质生产只通过自己的产物——物质资料——影响自身生命生产和他人生命生产。也就是说,物质资料是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的规律中的一个因素,但仅仅是诸多客观因素中的一个,还有其他的客观因素(如时间、空间、运动、睡眠、信息等)也发挥作用。这意味着,现实中不存在物质资料孤零零发挥作用的情形,自始之初就是多种客观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人类的一切都是由最初这三类活动衍生出来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3](P186)。这里就来探讨其他客观因素对物质生产的作用的影响。
物质生产既然对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横向外在,那毫无疑问,对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的衍生物依然是横向外在。物质生产自身也有衍生物,可视为物质生产的高阶子系统,在遵循物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有着更特殊的规律,其实就是一个复合函数(物质生产函数的函数)。就像恩格斯所言:“货币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并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2](P595-596)这和化学规律之下有生理学规律、生理学规律之下有心理学规律一样,如此,物质生产也是外在于它的高阶子系统,只不过这是一种纵向的外在,物质生产通过高阶子系统本身那个更特殊的规律对子系统产生作用。还有物质生产、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等三类活动的共同衍生物,它是物质生产、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共同的高阶子系统,在遵从物质生产、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规律的前提下有着更特殊的规律,这其实还是物质生产的一个高阶子系统,只不过遵从的前提要更多一些,所以,物质生产对它的作用方式与上一种情况相同。
总之,物质生产或横向或纵向地外在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其他客观因素与之伴随也在这两种情形下发挥作用。横向外在某领域时,物质生产仅通过物质资料发生作用,物质资料与其他客观因素处于同一层次,平等并列,可以视为同一函数的多个自变量。在其他因素的干扰下,物质资料对该领域的正比例促进关系会被破坏,使得物质资料对该领域只能说具有制约作用。纵向外在某领域时,物质生产在该领域之外发挥作用,有其他客观因素在该领域内部发挥作用,“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2](P658)。物质生产及其结果必须进到这个高阶子系统的规律中才能产生影响,若进入不了,无论如何变动都没有用;而内部诸客观要素的变化直接影响该领域,如“货币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2](P595)。如此一来,高阶子系统的变化不再与物质生产的变动一一对应,物质生产的作用也只是“制约”而非“决定”。
对于上述结论,若不管横向外在和纵向外在的具体作用机制,从宏观上解释更容易理解。当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时,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予以干扰,使得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只有制约作用;当物质生产对政治生活发生作用时,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予以干扰,使得物质生产对政治生活只有制约作用;当物质生产对精神生活发生作用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予以干扰,使得物质生产对精神生活只有制约作用。
三、类特性使得人能够超越物质条件
上述最初这三类活动衍生出更多生产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进化的过程,通过对象性活动,过渡生物发展出语言、审美、爱等,直到意识出现,标志着人类正式生成,具有了独特的主观特质。作为动物,人具有自然规定性,如饮食男女都是自然需要;但通过自身实践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又超越了动物,获得了动物所不具备的先天特性,“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P162)。自然规定性使得人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所以必定与物质生产存在关联,而自身的类特性使得人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质条件,使得经济仅具有制约作用。
人的类特性里有三个关键词:自由、有意识、活动,这是一个属+种差的定义,活动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实际上人只在自由、有意识两个方面异于动物,我们分别予以考察。
首先来看自由。所谓自由,就是不受强制自我规定。这样的话,出于自身意愿又不是为了满足肉体需要才是自由,如未被异化为谋生手段的艺术,只有这个领域是自由的,其他领域都是不自由的。在不自由的领域中,人类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因为人能抗拒外来强制,就如黑格尔所言:“唯有人才能抛弃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生命在内,因为人能自杀。动物则不然,动物始终只是消极的,置身于异己的规定中,并且只使自己习惯于这种规定。”[4](P17)正因为如此,人虽也有生存压力,与动物还是不一样,能超越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总有人宁肯饿死也不抢劫、偷盗,这就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而舍生取义、虽不可亦为之则体现得更明显。马克思也承认这一点,只不过认为能做出超越的只是少数人,“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把它们全部加以克服。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5](P58)。不管这样的人多么少,都说明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质条件,不与物质条件严格对应。
其次来看意识。动物有活动而无意识,人类既有活动又有意识,既然是由动物进化为人,那只能是活动生成意识而不是相反。意识一生成,人类就有了本质直观的能力,在1848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3](P576)这里的“似乎”二字表明他对意识的时间超越性还有所迟疑,到1868年则明确指出:“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2](P290)诚然,一种社会制度在其蕴含的生产潜力完全发挥出来之前绝不会灭亡,但在其生产潜力完全发挥出来之前人就已认识到该制度的不合理性,从而起来反抗它。而且,正是通过革命来检验社会制度是否还有生产潜力,革命成功意味着已没有生产潜力,革命失败意味着还有生产潜力。既然检验活动总是超前,那最先进行检验的国家未必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因为革命可能会失败。这样,政治生活就与物质生产存在不一致,其他生活亦是如此,“有意识”这个类特性也能造成人对现实物质条件的超越。
四、结语
事物对物质资料的需求有额定值为超越提供客体基础,自由而有意识的类特性为超越提供主体能力,其他客观因素的扰动为超越提供外部襄助。现实中三者纠缠在一起同时发挥效力,使得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都能与物质生产存在不一致,如黑格尔就说人不因有了笔、颜料就是画家,当然最明显的例子还是战争中以弱胜强、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文明国家,但我们不能顾此而失彼,一味地强调不一致;实际上其他领域只是可以与物质生产不一致、有时与物质生产不一致,而非必定与物质生产不一致、总是与物质生产不一致。从量上来看,物质资料短缺的时候,一致的情形更多,如重新争夺生活必需品时陈腐污浊的东西必然死灰复燃,最起码在物质生产为零时,人类一切终将归零,零点坐标处二者绝对一致;从质上来看,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一致的情形更多,手推磨必然产生封建社会,蒸汽磨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为了包容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形,才用“制约”二字,就像数学上用正相关包容成比例和不成比例的两种同向变动。
“制约”二字使得唯物史观仅仅成为研究指南,而非现成公式。这就为我们带来了难题,必须自己判断何时一致、何时不一致以及为何不一致。对此没有什么捷径,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2](P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