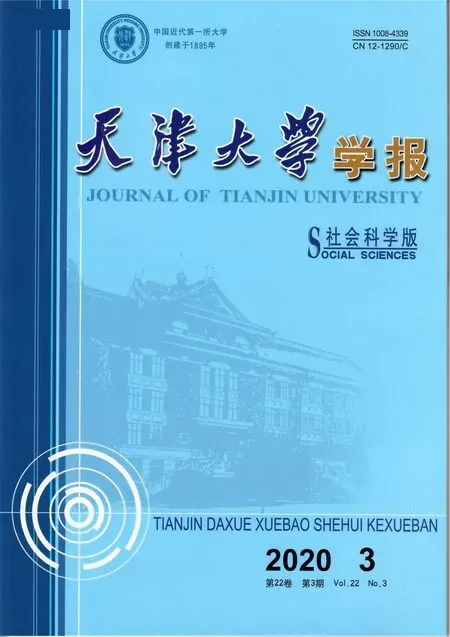《文选》对选本学的垂范及引发的后世选家思考
于 堃, 张 洁
(1.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桂林 541004; 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541004)
“选本”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价值,它暗含了选者或选者所处时代的文学批评观并且传递和影响着后世。我们可以从“选本”中窥探到当时社会背景的样貌,当时作品的艺术成就或对当世、前世作品的评价与接受情况,还可体现出选者的选录标准、目的、喜好和体现出的文学观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从《文选》为“选本”提供的示范意义出发,讨论《文选》的“选本”性质、内涵和用途以及后世人们围绕着《文选》对“选本”的正向影响和后人反向的现实思考等问题。
一、 《文选》确定了历代选本的性质
何为“选”?《说文解字》曰:“一曰择也”[1],即选择之意。所谓“选本”,是指选者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一代或数代文学作品有选择性地汇集为集。挚虞《文章流别集》被《隋书·经籍志》称为总集之首: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是为《流别》。[2]
这也得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认可,卷一八六《总集类·序》:“《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哀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3]。挚虞《文章流别集》其书虽佚,后世的文集总钞都是“继轨”挚虞《文章流别集》的,《文选》也不例外,也是经过“采擿孔翠,芟剪繁芜”,即经过“选”的过程,成为“选本”和现存编选最早的文学总集的,即“总集之存于今者,以《文选》为最古。鸿篇巨制,垂范千秋”[4]。
《文选》能“垂范千秋”,有其内在原因,首当因“用彰公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集部三十九》云:
然文章论定,自有公评,要当待之天下后世。何必露才扬己,先自表章。……考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何逊犹在,不录其诗。盖欲杜绝世情,用彰公道。今芮挺章与楼颖一则以见存之人采录其诗,一则以选己之诗为之作序,后来互相标榜之风,已萌于此。[3]1688
四库馆臣于此,一是批评了芮挺章编《国秀集》“以己作入选”“露才扬己,先自表章”,因为文章的论定,后世自有“公评”;二是批评因楼颖为之作序就选录其文章,“互相标榜”的不良之风开始盛行。而以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何逊犹在,不录其诗为例,对“选本学”提出了“杜绝世情,用彰公道”的要求,也侧面赞赏了《文选》的选录原则。因为萧统是主动追求文学“文质彬彬”的文学风格,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5]。应该说,具有如此文风的人是较为能够容许各种文风的,其所编纂的总集也能够容纳各种文风的作品[6]。也正是因为《文选》所录作品能够容纳各种文风,“用彰公道”,是魏晋南北朝公认的历代名作,是时代的公论,得到了天下后世自有的“公评”。因而,才能为后世学习、编纂选本提供可供学习的垂范意义。
否则,不是所有选本都能得到这样的认可。如果选本不“用彰公道”,人们也不会盲目随从,如《旧唐书·裴潾传》载:
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7]
可见,后世选者的品质和所选作品的品质也自有公论和客观论断。裴潾拟昭明太子《文选》的《通选》未达到“用彰公道”,虽然“集历代文章”,但因其选文看中作者是否与其交好,“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且“所取偏僻”,故而其选也未能得到后世的认可,以致于“时论咸薄之”“不为时论所称”。于此,叶燮《选家说》:
古文辞赋之有选也,自梁昭明始。……昭明不求诸人而求诸文,……文选一律也,人选则不一律也。或以趋附,或以希求,或以应酬交际,其选以人衡,何暇以文衡乎?不以文衡,于是文章多弃人,天下多弃文矣。……吾愿,自不能效法圣人,其亦不失梁昭明之意,斯亦可矣。[8]
叶燮一则肯定了“选自昭明始”;二则赞赏萧统编纂《文选》“不求诸人而求诸文”的标准,即“文选”,不因为趋附、希求或以应酬交际而“人选”;最后对后世的“选古之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选本”应该学习的参照,即使“不能效法圣人”,也要达到“不失梁昭明之意”,即以萧统编选《文选》为最基本的参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文选》为后世选家、选本彰显的最可供学习的示范意义。
《文选》不仅能起到“垂范千秋”的作用,而且因“菁华毕出”而成为“文章之衡鉴”。关于总集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总集类·序》云: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3]1685
由此可知,这是对总集编纂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就《文选》而言,第一层意义来说,《文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辑佚学的著作;第二层意义来说,《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集。《文选》是以“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为出发点,辑集零章散篇,尽量求全求备;以“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为落脚点,编成总集。
若归结于选本的性质来说,《隋书·经籍志》说挚虞编纂总集是因为“苦览者之劳倦”[2]1089,《文选序》言明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9],《四库全书总目》说要成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3]1685。可以这样说,《文选》作为总集,萧统编选的目的有二:一是“网罗放佚”,为了尽量追求全面,使录入的作品成为“著作之渊薮”;二是“删汰繁芜”,为追求精简菁华,使编选的作品成为“文章之衡鉴”。“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既是编纂的过程,也是其最终成果形式[6]106。当然,《文选》最后的落脚点显然是属于“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一类,这也符合《文选》作为选本的编纂目的和内在要求,即作为选本的《文选》不仅是“著作之渊薮”,更在于达到“文章之衡鉴”。选本不仅要满足于文献学上的辑佚,即总揽文章,让“览者”欣赏;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学批评,有评论文章的意味,具有文学批评的意义。总之,《文选》确定了选本的性质,以后的选本均须如此,仅体现文献学意义上的辑佚功能还不够,因为选本并非全集,还要有文学批评意义,即要达到文献学意义和批评学意义的统一。
《文选》出现后,出现了《文选》“李善注”,“自从有了此书,《文选》学就应该是《文选李善注》之学。《文选李善注》之学包括《文选李注》的文献学,《文选李注》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文选李注》的文论学”[10]。俞绍初、许逸民二先生的《文选学研究集成》序论及“新选学”认为,“新选学”之范畴约略包括注释、校勘学、评论学、索引、版本、文献、编纂、文艺等8 个方面的“学”[11],后则又有“文选文体学”“文选类型学”等。其中,《文选》作为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文选》作品的注释、解读,对选文标准的探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作家身份的认可,对文学思潮的引领和反思等方面,通过这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功能,使选本成为构建文学批评体系的方式,此为《文选》选本的最重要内涵和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文选》才能从“内质上”具有经典垂范的作用,作为选本,在所选作品和“选”的方法上被后世不断主动学习、模仿。
二、 《文选》奠定选本作为文章写作样本的用途
《文选》奠定了选本作为文章写作学习文本的用途,顾大韶《海虞文苑序》云:“昔者昭明之为《文选》也,论世穷乎八代,取材极于九垓,囊括今古,包裹鸿细,然后鉴之以神识,裁之以体格,辨之以源流,审之以声韵,才累理者必去,疵间醇者必削,其用物也弘矣,其持法也严矣,故能继六经而垂世,并二曜以经天也”[12]。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七下·文宗下》载:“壬辰,集贤学士裴潾撰《通选》三十卷,以拟昭明太子《文选》,潾所取偏僻,不为时论所称。”[7]553讲的是出现了集贤学士裴潾拟昭明太子《文选》撰《通选》的情况。又,张九龄《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载:
(徐坚)盖尝注《史记》,修《晋书》,续《文选》《大隐传》,及有文集三十卷。[13]
说的是徐坚除了注《史记》、修《晋书》,还有续《文选》之事。唐代还有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等模拟《文选》或续《文选》之作。
宋初文人对《文选》的摹拟现象从杨亿《二京赋》可见一斑,据袁褧《枫窗小牍》载:
杨亿作《二京赋》既成,好事者多为传写。有轻薄子书其门曰:“孟坚再生,平子出世。《文选》中间,恨无隙地。”杨亦书门答之,曰:“赏惜违颜,事等隔世。虽书我门,不争此地。”余谓此齐东之言也,杨公长者,肯相较若尔耶?[14]
可见,宋初模拟《文选》作品的盛况。又,《集选目录》《直斋书录解题》曰:“案:《文献通考》‘集选’作‘文选’。丞相元献公晏殊集。《中兴馆阁书目》以为不知名者,误也。大略欲续《文选》,故亦及于庾信、何逊、阴铿诸人”[15]。《文献通考》甚至把《集选目录》称作《文选目录》,陈振孙也说大概因为想要续《文选》的缘故,所以才选庾信、何逊、阴铿诸人作品。另外,朱熹在《跋病翁先生诗》说:“此病翁先生少时所作《闻筝》诗也。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辈流少能及之”[16]。朱熹认为病翁写诗学习了《文选·乐府》,高度肯定了《文选》之于学习写作文章的典范作用。此外,还有元代陈仁子《文选补遗》,明代刘节《广文选》,《清史列传》也载有薛寿“著有《续文选古字通》二十卷”[17]等模拟《文选》、续《文选》、补《文选》之作。
后人为什么要拟《文选》、续《文选》、改编《文选》呢?明胡应麟《诗薮》曰:“萧统之选,鉴别昭融。”[18]《文选》作为诗文写作的标准范本,后人通过模仿方能求得神似,而拟作、续作和改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写作、属文的方法。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选》作为文章写作学习文本来用,可以说《文选》的用途已经由鉴赏而入模拟了。文人通过拟写、续写或补写的手法学习写作、属文由来已久且渊源有自。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创造主义与仿古主义》中说,“六经底文章,一部分一部分地来看,乙模仿甲的,也是有的。就《诗经》来看,例如《鲁颂》的《閟宫》有模仿《商颂》《殷武》的形迹,这早已为学者承认,所以,仿古主义与创造主义相并着,是早早有了的。”[19]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20]
刘孝标注云:“湛《集》载其《叙》曰:‘《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20]279可见,夏侯湛作的诗也是《周诗》的“补”,而《世说新语》说是“作《周诗》”,潘岳“遂作家风诗”,则“补”或“拟”在当时和“作”的界限区分不明。正可通过“补”“拟”“续”来学习写作。《扬雄传》载:“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21]可知,扬雄经常模拟司马相如作赋,他又模拟《离骚》作《广骚》,模拟《惜诵》以下至《怀沙》作《畔牢愁》。其中,“拟之以为式”就是古代文人学习写作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后人也有沿袭。如《七谟序》载: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琦、李龙、桓鳞、崔骃、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22]
枚乘作《七发》,“属文之士”傅毅、刘广世、崔琦、李龙、桓鳞、崔骃、刘梁、桓彬分别“承其流而作”《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等文章,以至有了“七”这种文体。
对此,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第十四》也说:“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23]。由此可见,“枝附影从”极言当时模仿学习的风气之盛;“十有余家”则指其后的模拟者之多。
又,陶渊明《闲情赋》序曰:“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24]何(孟春)注云:“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玚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者也。”[24]153由是可知,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是为“定静之辞”,后来的“属文之士”就把这两篇当做学习写作的范本,“奕世继作”已经成为了时代之风气。
于此,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曰:“白壁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5]200以上可知,萧统不录《闲情》赋也是当时的时代风气所致。“时代的审美趣尚规约着选家个体的审美趣味,引领具体文本的选取与评鉴,使选本表露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映现出选本所处时代的审美趣尚。”[25]萧统只是认为《闲情》赋不适合当作学习写作的范本,也就是说不是“定静之辞”,因而就没有录入《文选》,也“体现齐梁时人共同之审美要求与昭明本人审美意向之切合”[26]。这在陶渊明本人那里也可以得到验证:“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24]153陶渊明作《闲情》赋也是遵循时代风尚,为练习属文而写作的拟作。
李白也拟《文选》,就是为了学习写作文章。《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有载:
(李)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27]
词选即《文选》。关于李白三拟《文选》,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李、杜无所不学,而《文选》又唐人之所重,自宜尽心而学之,所谓‘转益多师是吾师’也。若其志向之始,成功之终,则非《选》诗所得而囿。故谓太白学古兼学《文选》可,谓其复古为复《文选》体则不可。”[28]虽然潘德舆不同意李白复古是为了复《文选》之体,但他肯定了李白“学《文选》”的不争事实。朱熹也评价李白、杜甫的诗写得好是因为学习了《文选》“诗”才好:“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16]4321-4323
所以,宋代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说:“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湮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29]。即是说,昭明《文选》能大行于世,得益于士子能学而致用,即通过拟写、续写、改编《文选》学习写作、属文。从学习写作、属文的更深层次的动因来说,拟《文选》、续《文选》、补《文选》、改编《文选》的大量出现,也奠定了其作为选本的另一种用途,说明后人把《文选》作为文章写作学习文本来用,《文选》作为选本的功用已经由鉴赏而入模拟了。当然后人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文选》的选本示范意义,从选本作品的选录上、从选本的编纂体例方法上或者是选本的编纂思想上。
三、 《文选》为后代选本提供编纂方法
无论从编纂体例、分类,还是编纂思想上,《文选》都为后世的选本提供了选本编纂方法的垂范意义。首先就编纂体例和分类上来说,萧统《文选序》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9]2。这里,萧统提出了《文选》作为选本的编纂方法,即“次文”,一是以文体分,二是文体之下以类型分,三是类分之中,再各以时代相次。《文选》所录700 多篇作品按照赋、诗、文三大文体分,每一种文体再按类分,赋分为15 类,诗分为23 类,文分为35 类。《文选》次文类“各以时代相次”可以分为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与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两个层次[30],但作品最终还要体现在作家层面上来。其次就编纂思想来说,《文选》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9]2的选本,即把历代有所定论的优秀作品集合而成总集[6]52。但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萧统编纂《文选》的宗旨。“《文选》选文的立足点在‘入耳之娱’与‘悦目之玩’,故一切不以‘能文为本’者,不得入其域中。”[31]体现了《文选》选文的价值准绳。
“《文选》是一部成功的总集,它不仅取代了《文章流别集》居总集之首的地位,也淘汰了萧衍、萧秀和萧统自己早年所编的那些类书、总集,而且还为此后的总集编纂、文论写作导乎先路。它在一千多年前出现的最早总集中岿然独存,冠冕众制,是历史对它所作出的公允评价。”[10]40明陈衎《选编序》称“自昭明《文选》行,文始有选。”[32]后世的选本编次体例多有效仿《文选》者,如《文苑英华》:“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烦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3]1691。宋人的其他几部文章总集如《唐文粹》《宋文鉴》等大致都采用了《文选》的编排体例。《成都文类》:“凡一千篇有奇,分为十有一门,各以文体相从,故曰《文类》。每类之中,又各有子目,颇伤繁碎。然《昭明文选》已创是例,宋人编杜甫、苏轼诗,亦往往如斯,当时风尚使然,不足怪也。”[3]1699《选诗》:“(从)《文选》中录出别行,以人之时代为次”[15]451;又,元代刘履编《风雅翼》,《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八《集部四十一》云:
是编首为《选诗补注》八卷,……次为《选诗补遗》二卷,取古歌谣词之散见于传记、诸子,及乐府诗集者,选录四十二首,以补《文选》之阙。次为《选诗续编》四卷,取唐、宋以来诸家诗词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为“文选嗣音”。[3]1711
不论是补《文选》之阙的《选诗补遗》,即按《文选》选文标准再选,还是选唐宋诸家诗词的《选诗续编》,都是依《文选》标准体例而行。明顾大韶《海虞文苑序》云:
昔者昭明之为《文选》也,论世穷乎八代,取材极于九垓,囊括今古,包裹鸿细,……才累理者必去,疵间醇者必削,其用物也弘矣,其持法也严矣,故能继六经而垂世,并二曜以经天也。今子之为是集也,封域不出百里之内,人物不踰书世之近。其用物太窘,则不能无姑息;其持法太宽,则不能无假借。[12]544
顾大韶认为昭明之为《文选》,不仅做到了取材“极于九垓,囊括今古,包裹鸿细”的“用物弘”,而且达到了剪裁上“才累理者必去,疵间醇者必削”的“持法严”,才能让《文选》“继六经而垂世,并二曜以经天”。他据此批评时人选集“用物太窘”“持法太宽”,实则是体现了时人对选集提出以《文选》为标准的呼声。
明人王文禄对此则更为明确、更为集中,甚至是怀着更大的文学“野心”,提出为文、选本选文都要宗法《文选》的,并多有论述。其《文脉》曰:“《文选》,文统也,恢张经、子、史也。选文不法《文选》,岂文乎?”[33]王文禄认为《文选》是文章的正统,选本选文不效法《文选》,就不能称为文了。他又说:“罗圭峰、李空同、康封山、崔后渠法两汉、先秦云,自是知宗《昭明文选》也。……夫文也者,文也;华也者,霞天花苑,锦章也。”[33]1703虽然某种程度上,他是在为复古明代的文风而推崇《文选》,但他认为文应是“锦章”,要有文采,这与萧统选文保持了一致。他对不宗法《文选》的选本,《皇朝文衡》的选文之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弃华而取质,岂选文之法乎?”更是从选本史学意义上肯定了《文选》对后世选本的垂范作用,建议师法《文选》作历代之“文选”总集:“夫《文选》尚矣,莫及焉。……一仿《文选》之例增选之,自六经后,始曰《战国先秦文选》,曰《三国文选》,曰《六朝文选》,曰《唐文选》,五代附之,曰《宋文选》,曰《元文选》,辽金附之,我朝曰《皇明文选》。……如选矣,一代成历代之美,文运之光乎?”[33]1692-1693可见,王文禄是心怀“一代成历代之美”以期达到“文运之光”的伟大理想甚或是文学“野心”的。当然,其前提是严格师法昭明太子《文选》的标准来增选《战国先秦文选》《三国文选》《六朝文选》《唐文选》《宋文选》《元文选》《皇明文选》。
另外,还有不少后世选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文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而作。如高仲武《大唐中兴间气集序》云:“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榷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正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繇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34]他对前人选本有所褒贬,认为昭明《文选》“《正声》最备”,同时又对僧慧静所编《续古今诗苑英华》、李康成编《玉台后集》、崔融编《珠英集》、殷璠编选《丹阳集》等选本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和期待。
又如,芮挺章编选《国秀集》,楼颖序称:“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35]。可知,“谴谪芜秽,登纳菁英”是承《文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而来,又加入了“可被管弦”的新标准,即可以合乐歌唱。
又如,姚合选《极玄集》,自序仅存四句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35]318。意思是说,所选21 个诗人都是“诗家射雕手”,即高手,“更选其极玄者”,即是极妙极好之意。可见,姚合选诗注重“选精”——集其清英,正如蒋易《极玄集序》所说:“唐诗数千百家,浩如渊海。姚合以唐人选唐诗,其识鉴精矣。然所选者仅若此,何也?盖当是时以诗鸣者,人有其集,制作虽多,鲜克全美。譬之握珠怀璧,岂得悉无暇类者哉?武功去取之法严,故其选精。选之精,故所选仅若此”[35]318。
综上,《文选》的编纂方法被后世选本或多或少继承和发扬,对选本的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走向,使《文选》作为选本在史学意义上影响深远。
四、 《文选》提供对选本走向的思考
后世不乏从对《文选》的贬抑与质疑出发,引发思考——即选本该走向何方?
一是质疑萧统的认知水平拙劣、理论素养不高、编次无法、去取欠精。如苏轼《答刘沔都曹书》:“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36]《题文选》又说:“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36]2092-2093苏轼对于萧统“拙于文而陋于识者”和《文选》选文去取的评价,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而言未免过于激烈而有失偏颇。
明人彭时《文章辨体序》:“今传于世,若梁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固已号为掇其英、拔其粹矣。然《文粹》《文鉴》,止录一代之作;《文选》虽兼备历代,而去取欠精,识者犹有憾焉。”[37]彭时此言《文选》去取欠精,留有遗憾,也委婉批评《文粹》《文鉴》止录一代之作。明人陈山毓《总集序》:“总集者,辑文人学士人所论著,撰而录之者也。萧氏《文选》重,而诸家之撰录殆废。然昭明识最下,独贵绮丽,尚堆叠,词赋如灵均诸什,疏议如谊、舒、错、向,概多弃置,幸他书且存,故俾后世犹获睹其梗概耳。……故予尝以为《文选》一书,是古文词一巨蠧也,亦一厄运也。”[38]以“昭明识最下”,甚至认为《文选》是古文词的巨蠧和厄运。清人毛先舒《诗辩坻》云:“《文选》诗、赋须分代读之。其分类者,昭明之陋耳,遂使风格升降混淆,诖初学不少。”[28]71认为《文选》分类因萧统之陋而使“风格升降混淆”,贻误后学。
其实萧统是具备编撰《文选》的文学才华、理论水平、校勘古书的经历与经验和“泛览词林”的基础的[6]5-8。不管出于何种文学等目的,如果把后世的批评从选本的角度来看,实则以选者编纂更好的选本为鹄的,对编选者本人提出了更高的诗文素质、理论水平、编次体例等的要求。
二是略嫌《文选》编选还不够精简,还可有很多删减之处。如明人车大任《又答友人书》云:“仆自幼阅《文选》一书,……然其篇帙浩烦,典故错出,今人既不能作,亦不能读,非不能读也,不能作,虽读如未读也。……今人读未终篇,而倦焉思卧者,比比是已……”[39]认为《文选》“篇帙浩烦”,今人“既不能作,亦不能读”,以至于出现了还没读完一篇就疲倦想睡觉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实则是后人对选本提出要更精当的要求。
三是对《文选》不录“经、史、子、语”的反思,提出质疑。关于《文选》选录作品,萧统《文选序》云:
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9]2
众所周知,萧统于此指出了《文选》的选文总体标准和大致范围。周公、孔子所编之“经”地位崇高,不能“加之剪截”;老庄等诸子之作,“立意为宗”,不“能文”,亦略而不录;贤人、忠臣、谋夫、辨士之作,虽“美辞”,但“繁博”,亦不录;“史”除赞、论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皆不录。总的来说,萧统《文选》范围是基本不选经、史、子和语,选文总体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此言总体标准而非统一或唯一标准。于此,章太炎说:“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且‘沉思’孰若庄周、荀卿,‘翰藻’孰若吕氏、淮南?总集不摭九流之篇,格于科律,因不应为之辞”[40]。其言甚是。
后人对《文选》不录“经、史、子、语”提出反思,认为随着文学的发展进步,这种选本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明人董其昌《餐霞十草引》:“自汉至唐,脉络不断;丛其胜会,《选》学具存。昌黎以经为文,眉山以子为文,近时哲匠王允宁、元美而下,以史为文。于是诗赋之外,《选》学几废。”[41]言后世已经发展为“以经为文”“以子为文”“以史为文”了,《文选》学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清人潘耒《明文英华序》:“文之有选,自梁昭明始,综揽八代千余年,成书止三十卷,诗赋复居其半,为文仅二百余篇,可谓隘矣。又所取多骈辞俪句,偏于一体,非文章之极则。”[42]是说《文选》所取“偏于一体”,非“文章极则”,过于狭隘了。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人对《文选》的选本典范意义提出了质疑,对“选本该走向何方”提出了新的思考。
另外,还有后人认为萧统《文选》选文的去取过于苛刻了,导致有些“自有定价”的文章被舍弃了,但也不能因为《文选》未选录而掩盖其美或就此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如宋人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五云:“王右军《兰亭序》不入《文选》,王勃《滕王阁记》不入《文粹》,世多疑之。……然则二文之不入《选》《粹》,毋亦萧统、姚铉偶意见不合,故去取之过苛欤!虽然,二子之文不入《选》《粹》而传至于今,脍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价,所谓瑕不掩瑜,未足韬其美也。”[43]
以上,可以说是从对《文选》的贬抑与质疑出发,对选本提出了正向和反向思考——选本该走向何方?即:对编选者本人提出了更高的诗文素质、理论水平和编次体例等的要求;要求选本要更精当;对文学选本提出了新的反思——要求选本要录经、史、子、语。明人李长祥《与董文友龚介眉书》:“古来之文选、诗选代有其人,皆代兴代没,今传之者惟昭明《文选》,又读之者半,诋之者半。其诋之也,终读之;其读之也,终诋之。”[44]是说对《文选》“读之”与“诋之”参半,即两种情况都有。当然,不管如何,后人是以提出反思来促进选本的深度发展和宽度拓展的。
五、 余论——《文选》的选本学意义
《文选》作为选本,其性质和内涵,开启了选本的各个方面,是后世研究选本的标志,成为研究选本不可逾越的开端,后人对选本又有所发展。则选本和对选本的研究,可统称为“选本学”。《文选》的选本学意义不言自明,它奠定了上文所述四个方面,又奠定了“选本学”的学问,即《文选》选本学——围绕选本理论来讨论和实践之学。
《文选》所录作品“用彰公道”,是魏晋南北朝公认的历代名作,是时代的公论,因而,才能为后世选本提供了垂范作用。而萧统编选《文选》,本身又是有发展眼光的,即所谓“增冰为积水所成”[9]1,又“总集之存于今者,以《文选》为最古。鸿篇巨制,垂范千秋”[4]1,自然会被后世选家所效仿,但必是受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即“昭明太子生于其世,沿时代之风尚,踵昔贤之成规,乃集《文选》,以行于代”[4]5。自然也难以逃脱时代的圈囿,也使后人对选本发展有了新的思考,即反思选本如何走出一条有异于《文选》规范下的新的发展之路。
阮元《与友人论文书》:“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45]提出了《文选》选文的标准之问题。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又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着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其不合之处,盖分于奇偶之间。经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选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45]608后世必会走出一条“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之路,即与《文选》相异的路,这也是选本的必由之路。
于此,骆鸿凯也说:“而总其大旨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此昭明自明入选之准的,亦即其自定文辞之封域也。”[4]11总集的编纂既可以达到“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效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文体观念[46]。但“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这也给“经、史、子、语不入《文选》”提出反思,也为后世跳出《文选》“经、史、子、语不入《文选》”的选本框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即以后的选本要录经、史、子、语。这种反思具有文学批评的意义,而“文学批评的开展有利于文学接受观念的树立,文学接受观念的树立促进文学交流”[47]。这也是《文选》给选本立下规矩之后,后世思考选本新的发展方向和《文选》选本学的时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