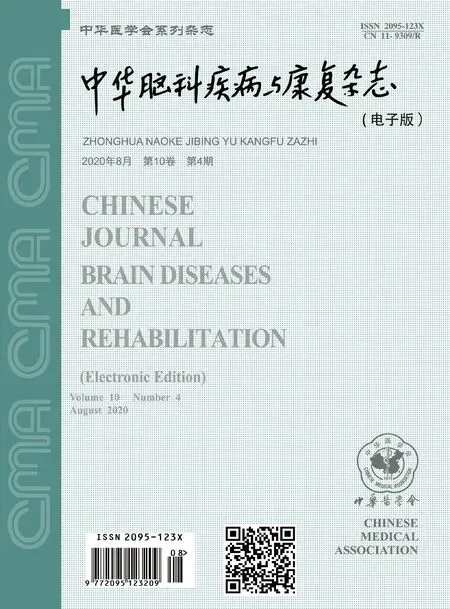积极开展髓母细胞瘤分子分型的研究
陈立华
髓母细胞瘤(medulleblastoma,MDB)是一种胚胎性神经上皮肿瘤(WHO Ⅳ级)。根据激活的信号通路不同,MDB 可分为4 个分子亚型,按照其表现出的细胞通路激活或基因组改变而命名。不同分子亚型的生物学表现、临床特征及预后均有明显差异,分子分型重新定义了MDB 的风险分层。目前,迫切需要建立基于分子生物学特征的危险分级,并开展个体化治疗策略。MDB 的4 种分子亚型具有不同的起源、好发解剖部位、人群分布以及预后和治疗选择。
一、MDB 的分子分型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将MDB 分为WNT 激活型、SHH 型(SHH 激活TP53 突变型,SHH 激活TP53 野生型)、第3 组和第4 组(合称为非WNT/非SHH),分别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点。YAP1 是癌基因转录的辅助启动子,能促进细胞增殖和转化,在MDB 的WNT 和SHH 亚型中高表达,而在其他亚型中没有观察到。相比之下,GAB1 属于Gab 家族,在MDB 细胞的SHH 信号通路中具有特异性。YAP1 是WNT 和SHH 型MDB共有的特异性标志物,而GAB1 只是SHH 型MDB的特异性标志物,这有助于二者之间的鉴别。在WNT 型MDB 中,其特异性生物学标志物还有6 号染色体单体、CTNNB1 突变、β-catenin 核强阳性;而在SHH 型MDB 中,常伴有9q 的缺失和PTCH 突变;第3 组和第4 组的特点是MYC 和MYCN 癌基因扩增,预后较差。
(一)WNT 型
WNT 型最为少见,约占全部MDB 的10%,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4~15 岁),6 号染色体单体(儿童WNT 型)、CTNNB1 基因的稳定突变是最常见的遗传改变。绝大多数WNT 激活的MDB 具有典型的形态,这表明其是一种低风险的肿瘤。该亚型较少发生肿瘤转移,预后优于其他亚型,5 年总体存活率(overall survival,OS)>95%。WNT 型MDB 缺乏完整的血-脑屏障,化学治疗药物可以高浓度聚积在肿瘤病灶内及其周围,化学治疗效果较好。在组织学水平上,WNT 亚型几乎均为经典型髓母细胞瘤(classic medulloblastoma,CMB)。CMB 均存在明显的WNT 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致使该通路效应因子β-catenin在肿瘤细胞中大量积累并逐步进入细胞核内表达,进一步激活下游靶基因,从而引起该亚型肿瘤的发生。同时伴有6 号染色体单体的MDB 的预后更好。
(二)SHH 型
SHH 型MDB 可分为TP53 突变型和TP53 野生型,约占MDB 的30%,可见于所有年龄段,但更常见于0~3 岁婴幼儿和≥16 岁的青少年或成人。SHH型MDB 可表达p75NGFR 和Gab1 等特异性靶蛋白,与WNT 型MDB 共同表达核Yap1,但缺乏Otx2 表达。组织学上,SHH 型MDB 主要是为CMB、促纤维增生/结节型MDB (desmoplastic/nodular MDB,DNMB)和广泛结节型MDB (MDB with extensive nodularity,MBEN)。SHH 型MDB 具有完整的血-脑屏障,导致化学治疗容易产生耐药性。在SHH 激活的MDB 中,由于对治疗决策有重要影响,应对TP53 进行测序,以明确区分有无TP53 突变。TP53 野生型SHH 激活MDB 更常见于结缔组织增生/结节状形态,可能与PTCH1 缺失和10q 缺失有关。免疫组化结果显示,抗GAB1 抗体在SHH 途径激活或PTCH 突变的肿瘤中呈阳性表达,而YAP1 抗体的阳性表达仅见于WNT 型和SHH 型。SHH 型MDB 的预后优于第3组,次于WNT 型,其5 年OS 为60%~80%,婴儿SHH 型的预后明显优于儿童。不同SHH 亚型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根据SHH 型MDB 生物学的差异性不同可进一步分为α、β、γ、δ 亚型,其中α 亚型的SHH 遗传学标志物为TP53 突变联合MYCN 扩增,极易发生转移,预后最差;而δ 亚型的SHH 主要为成人SHH,预后相对较好。
(三)非WNT/非SHH 型
非WNT/非SHH 型MDB 的组织学类型主要是CMB 和LC/AMB,最终表达Otx2,但缺乏其他标志物。MYC 扩增被认为是非WNT/非SHH 型MDB 的一个重要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大多数非WNT/非SHH 型MDB 可通过表达或甲基化谱进一步细分为临时的第3 组和第4 组变异体。
第3 组约占全部MDB 的25%,仅发生于婴儿和儿童,最具侵袭性,也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亚型,预后最差,常伴肿瘤转移扩散,5 年OS 为20%~30%,主要遗传学特征是MYC 基因的扩增、1q 和等臂染色体17q (i17q) 的扩增以及16q 和17p 的缺失等。MYC 和i17q 扩增是第3 组MDB 的主要生物学预后标记,若存在则表明预后极差,5 年OS<20%;而无MYC 或i17q 扩增且术前无转移的MDB,预后较好,其5 年OS 可达55%~67%。
第4 组约占全部MDB 的35%~40%,可累及所有年龄组。i17q 在第4 组MDB 中更为多见,约占80%,而第3 组中少见,这一特点可用于鉴别第4 组和第3 组MDB。与其他亚型相比,第4 组的预后中等,较WNT 型和SHH 型差,5 年OS 为75%~90%,伴有i17q 和MYCN 基因扩增者易发生转移,预后很差。
二、MDB 分子分型的临床意义
明确MDB 的分子分型对于靶向药物筛选、预测生存率以及制定治疗方案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MDB 具有高度异质性,组织病理分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同一类型的MDB 预后存在的差异。MDB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进展,证实不同分子亚型的MDB在分子遗传学、临床及预后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原因是各亚型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核内β-catenin和TrkC 的mRNA 表达水平、MYC 扩增水平及染色体等可以用来预测其治疗转归。MDB 分子分型直接影响其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分子亚型不同,其临床流行病学和肿瘤组织学特点不同,且具有显著的特征差异,临床上可准确评估危险度分级,针对性选择靶向治疗方案和预测预后[1]。
(一)组织病理分型的局限性
MDB 是一种高度恶性的胚胎性肿瘤,WHO(2016)将MDB 分为4 种病理学类型:CMB、DNMB、MBEN、间变/大细胞型(anaplastic/large cell,LC/A)。LC/A 的临床预后差,DNMB 和MBEN 的预后相对较好,优于CMB,但组织学分型与临床表现很多时候难以完全对应,与预后也不存在密切的相关性[2]。因此,依靠单纯组织病理分类来预测预后是不全面的。如果遗传背景不同,即使是同一病理类型的MDB,其预后也可能有所不同。分子分型研究的不断深入,显示MDB 的预后与分子分型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分子基因的标志物能更好地判断MDB 的预后,亦可为肿瘤分子治疗寻找特殊的、敏感的治疗靶点。明确MDB 的分子分型对于MDB 的临床治疗、预后评估和靶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二)危险度分级
风险分层治疗是目前MDB 的主要治疗方案,个体化、靶向治疗则是MDB 未来研究的方向。MDB的危险度分级与患者的治疗模式及预后密切相关。基于组织病理学分型的MDB 分级方法是将MDB分为高危(high risk,HR)组和标准风险组(standard risk,SR)风险或低危组,分级的主要依据是有无蛛网膜下腔转移、患者的年龄及术后残留的大小。年龄>3 岁且无转移性疾病(M0)、术后残留肿瘤<1.5 cm2、组织学上无间变性的患儿被归类为SR,其余的被视为HR。存在蛛网膜下腔转移和年龄<3 岁是预后的影响因素,而术中全切除或近全切除并不影响患者的预后,理由是MDB 在病理学上无明显边界,术后残留<1.5 cm2经术后辅助放射治疗可以完全杀灭瘤细胞。
MDB 分子分型的深入研究,使得基于这些肿瘤分子亚型的MDB 风险分层成为可能,基于分子表型的危险度分层更为准确,有助于指导临床治疗和确定临床预后。2016 年,Ramaswamy 等[3]提出一种基于肿瘤分子分型的新的风险分层方案,主要以术后5 年OS 为定义标准并考虑疾病异质性和分子亚群信息,分为4 个风险分层组,即极高危组(OS<50%)、高危组(50%≤OS<75%)、标危组(OS 75%~90%)和低危组(OS>90%),并根据新的风险分层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不同的危险分级术后需要采用不同的综合辅助治疗方案。转移性第3 组伴MYC 基因扩增和SHH 型伴TP53 基因突变的患儿预后较差,归为极高危组;转移性或MYCN 基因扩增的SHH 型和第4 组伴脑脊液播散的患儿,为高危组;无MYCN基因扩增和无TP53 基因突变的SHH 型、无MYC基因扩增的第3 组和无第Ⅱ号染色体缺失的第4组,归入标危组;非转移性WNT 型和非转移性第3组,为低危组。根据新的风险分层,MDB 手术目的是最大程度地降低颅内压,在不引起严重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切除肿瘤。基于肿瘤分子分型的个性化治疗更加具有针对性,可以减少治疗的不良反应。
(三)预后预测
虽然MDB 患者的术后生存率显著升高,但现有的治疗策略往往忽略了个体差异,如何利用个体差异进行更精准的治疗、减少不良反应、改善MDB预后,成为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MDB 的预后差别非常大,5 年OS 为20%~100%[4]。不同分子亚型的MDB 具有明显不同的分子遗传学、临床及生存结局。WNT 型MDB 的预后最好,第3 组的预后最差,SHH 型和第4 组的预后介于WNT 型和第3 组之间。不同年龄的MDB 患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分子遗传学和临床预后差异,婴儿MDB 预后明显差于儿童和成人;成人MDB 仅有SHH 型、WNT 型及第4 组,缺乏第3 组。SHH 型MDB 约占50%,且成人SHH 型的预后优于儿童。WNT 型MDB 占所有MDB的10%,通常为经典型,多见于7~14 岁儿童和成人,且男女比例相当,在诊断时很少转移,预后最好,5 年OS>95%。SHH 型MDB 约占25%~30%,多为DNMB,是婴儿(<3 岁)和成人(>16 岁)的主要分子亚群,其中伴MYCN 和GLI1 扩增或TP53 突变的预后差。第3 组MDB 占20%~25%,在婴幼儿中尤为常见,男性是女性的2 倍,转移率高,是MDB 预后最差的亚组,5 年OS<60%。第4 组MDB 最为常见,占所有MDB 的35%~40%,占青少年MDB 的约50%;男性多见于女性(男∶女=3∶1),约1/3 的病例术前已发生转移。Thompson 等[5]对787 例MDB 患者进行分子分型(WNT 型86 例、SHH 型242 例、第3 组163例、第4 组296 例),对OS 和无进展生存率进行了多变量分析,发现WNT 型、SHH 型或第3 组MDB患者,在更大程度的切除范围内,没有明显的生存效益。对于第4 组MDB 患者,与次全切除相比,完全切除可提高无进展生存率,尤其是转移性疾病患者。然而,与第4 组MDB 患者相比,完全切除对OS 没有影响。
(四)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尽管手术联合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的治疗方案能够有效提高MDB 的预后,然而根据病理组织学和临床放射依据制定的风险分层治疗,由于在疾病进展及预后上存在明显差异,将导致无法预测的复发和治疗失败,而基于分子特征的个体化治疗可以揭示这些失败的原因。MDB 分子分型的研究已经明确这些亚组内的显著异质性,不同的亚型MDB 被鉴定出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生物学特性,需要根据MDB 的分子风险分层,为每例患儿制定个性化分层治疗方案,以期提高生存率和减少复发[1]。4 个不同的分子亚群都具有不同的组学(即基因组学、表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和临床特征。临床方案已将分子亚组策略应用于常规诊断、治疗分层和患者选择以进行分子靶向治疗。
目前迫切需要通过分子生物学分型研究来探索新的治疗手段,同时也为更优化的个体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在基因水平上对MDB 进行分子亚型的分类,增加MDB 分子分型的可操作性,强有力地推动了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根据分子分型评估MDB 的危险度分级,针对不同的分子分型筛选出有效的、新的靶向治疗方案,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已有研究将MDB 的分子分型与术前是否有肿瘤转移、染色体失衡等多种因素相结合进行风险分级评估,以期提高MDB 的生存率。尽管目前为止还没有标准的靶向治疗方法,但针对不同分子亚型的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正在逐步开展,以便更好地进行个性化治疗。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