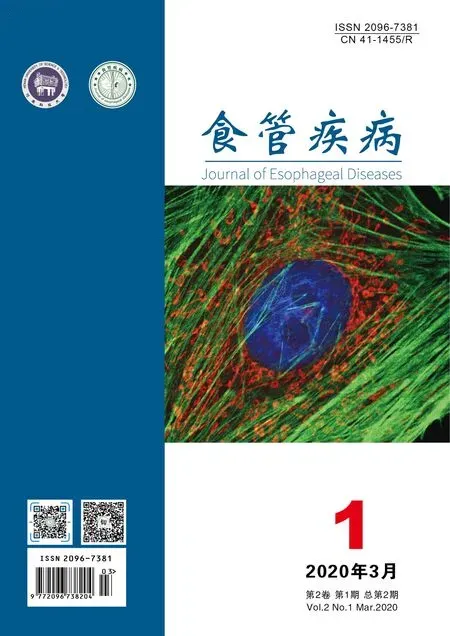牙龈卟啉单胞菌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兰子君,原 翔,张 灏,王立东,刘雅莉,詹启敏,高社干
人类菌群在正常的生理活动和致癌作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常口腔中存在700多种细菌,其中包括至少11种分枝杆菌和70属,其中红色复合物(red complex)是牙周疾病的重要致病菌,红色复合物包括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gingivalis,Pg)、齿垢密螺旋体(Treponemadenticola,Td)和福赛斯坦纳菌(Tannerellaforsythia,Tf),都是革兰氏阴性厌氧细菌,它们可以表达毒力因子来干扰机体免疫系统,侵袭和破坏牙周组织[1]。
Pg是一种重要的致病细菌,是成人牙周炎的关键病原体[2]。该细菌还与许多口腔外感染相关的疾病有关,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早产、肺部疾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在Pg中,最重要的毒力因子是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菌毛、牙龈素和外膜囊泡,其主要的致病机制包括:产生致病菌群,引起免疫防御功能异常,尤其是可侵袭口腔上皮和内皮细胞,诱导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干扰正常的生理代谢,抑制细胞凋亡,这也是其作为肿瘤潜在危险因素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Pg与口腔癌、胃肠道癌和胰腺癌密切相关[3]。几项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研究发现,牙周疾病或牙齿脱落与肿瘤进展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口腔癌、胃癌、胰腺癌,甚至胃癌癌前病变。Ahn等[4]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第三次全国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HANESⅢ)研究中发现,消化道肿瘤的死亡率与牙周炎和血清Pg的IgG有关,与牙周其他疾病无关。这些研究表明,Pg在原发性消化道肿瘤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旨在系统地拓宽对Pg与原发性消化系统肿瘤之间关系的最新认识。
1 Pg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关系
1.1 Pg与口腔鳞状细胞癌
口腔癌是世界第六大常见癌症,也是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占口腔癌的90%以上,具有高发病率和复发率及预后差的特点。OSCC的主要致病因素包括饮食习惯、不良生活习惯(例如吸烟、酗酒、咀嚼槟榔等),致癌病毒感染和遗传因素,然而,仍有15%的OSCC患者其致病原因无法以上述因素解释[5]。
一项Meta分析表明,牙周炎患者发生口腔癌的风险比正常人高2.66倍,牙周炎是口腔癌的独立风险指标[6]。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牙龈鳞状细胞癌组织中,Pg的感染率明显高于正常牙龈组织(P<0.05),牙龈鳞状细胞癌肿瘤组织石蜡包埋样本中同样富含Pg,这表明Pg与牙龈鳞状细胞癌之间存在潜在关联,而正常口腔细菌戈登链球菌(Streptococcusgordonii,Sg)结果与之相反[7],这项研究没有提供有关合并症因素的信息,宿主细胞感染Pg与细胞癌变的先后顺序尚待明确。
1.2 Pg与食管鳞状细胞癌
食管癌是全球第八大最常见的癌症,也是全球癌症死亡的第六大常见原因。Gao SG等[8]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在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中检测到高丰度的Pg,即ESCC中的61%及癌旁组织中的12%,而在正常食管黏膜中未检出,赖氨酸特异性牙龈蛋白酶和Pg的16S rDNA也检测出相似的分布情况,在此之前,尚无确证的证据证明ESCC中存在特定的微生物感染。
ESCC的常规血清标志物,如SCCA、CEA、CYFRA21-1和CA19-9对食管鳞癌的早期发现和诊断没有足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9]。在后续的研究中,Gao SG等[9]发现ESCC中血清抗Pg的IgA和IgG的水平明显高于食管炎和健康对照者,而IgA对于早期ESCC的诊断比IgG更具价值(54.54% VS 20.45%)。此外,血清抗Pg的IgA或IgG抗体的水平升高与ESCC患者的预后较差有关,尤其是在0~Ⅱ期或淋巴结转移阴性的患者中,高IgA和IgG水平的患者预后最差。因此,将IgA和IgG结合使用可提高诊断并改善预后。以上研究结果表明,Pg可能参与了ESCC的发病,几种Pg血清生物标志物的组合使用比任何单一生物标志物的诊断更加灵敏特异。因此,Pg血清生物标志物可能对ESCC早期诊断具有重大意义,并可能改善诊断和预后。
Peters BA等[10]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发现,漱口水样本的16S rRNA基因测序所检测的口腔微生物组可能反映食管癌的预期风险。高丰度的Pg倾向于发生ESCC的风险较高,而Tf与食管腺癌(adenocarcinoma of esophagus,EAC)的风险较高相关,其他细菌如奈瑟氏球菌和肺炎链球菌与较低的EAC风险相关。Gao SG等[8]同时还发现Pg还与ESCC淋巴结转移和生存期相关。
Yuan X等[11]的研究表明,Pg在食管癌和癌前病变标本中广泛定植,在癌旁组织中则丰度相对较低,而在贲门癌或胃癌中的含量很低或没有,这种差异可能归因于Pg对pH酸性环境的低耐受性。
1.3 Pg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nlous cell carcinoma,HNSCC)是全球第六大最常见的肿瘤,生存率为50%~60%。Utispan K等[12]发现,Pg脂多糖活化的巨噬细胞条件培养基促进了源自Ⅰ、Ⅲ和Ⅳ期HNSCC的原代和转移性细胞系的侵袭,而HNSCC细胞系HN4细胞的增殖被抑制。其致癌性侵袭可能是通过EGFR信号通路诱导巨噬细胞产生一氧化氮而介导,但深入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4 Pg与胃及结肠癌前病变
在接受胃镜检查并进行活检的患者中,约有1/10的不典型增生将在20 a内发展为胃癌[13]。在牙周疾病高水平的人群中,尽管不能确定口腔病原体的DNA水平与胃癌前病变的存在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在牙菌斑中检测到的牙周病原体与胃癌前病变的风险增加相关,且不受混杂因素的影响[14]。Sun J等[15]发现口腔中牙周病原体的负担和口腔中细菌的多样性是造成胃癌癌前病变的重要因素,然而,该研究未能采集用于直接微生物分析的胃组织样本。
1.5 Pg与胰腺癌
2018年,全球约有45.9万胰腺癌新发病例,这使其成为发达国家中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九位的最常见肿瘤。据文献报道,胰腺癌患者唾液微生物群与慢性胰腺炎之间存在显著差异[16],牙周病和Pg对胰腺癌的发展可能及其重要[17]。牙周病原体可能单独或与其他胰腺癌危险因素(例如吸烟、肥胖和ABO基因变异)共同作用,导致胰腺癌的发生[17]。
最近的一项前瞻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表明,Pg和聚合放线杆菌(Aggregatibacteractinomycetemcomitans,Aa)阳性与胰腺癌的风险增加有关[18]。该研究基于361名胰腺癌患者和371名配对对照组的口腔漱口水样本,对参与者进行了将近10 a的监测,以评估口腔微生物群与胰腺癌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潜在的混杂因素如何,口腔微生物群都可能在胰腺癌的病因学中起作用,与阴性人群相比,Pg阳性人群罹患癌症的风险增加了59%,而Aa阳性人群则增加50%的风险。该研究表明,口腔微生物(Pg和Aa)生态失调早于癌症的发生。同样地,在欧洲的一项包含404个胰腺癌病例和410个对照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发现,Pg菌株ATCC 53978的高IgG抗体水平(>200 ng·mL-1)与牙周膜的破坏密切相关,去除已知危险因素干扰后,统计显示Pg的IgG抗体水平升高使胰腺癌的风险增加超过2倍[19]。根据上述研究,Pg有可能感染到胰腺并促进胰腺癌发生。
1.6 Pg在动物模型中影响致癌作用
在针对牙周炎相关的口腔肿瘤发生的小鼠模型中,Binder GA等[20]证明了在口服致癌物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QO)的作用下,Pg和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nucleatum,Fn)引起的慢性感染可促进OSCC细胞的转化,并激活IL-6-STAT3信号转导通路,从而诱导效应子驱动OSCC细胞的增殖和侵袭性。该研究结果指出,Pg可通过激活JAK2-GSK3β信号通路促进上皮细胞产生IL-6,Pg和Fn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引起上皮细胞产生IL-6,与口腔上皮细胞的直接相互作用来刺激肿瘤发生。此外,口腔病原体还刺激了OSCC的增殖和肿瘤发生过程中关键分子的表达,如细胞周期蛋白D1、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9)和乙酰肝素酶。
Geng F等[21]建立了另一种体外模型,将人类永生化的口腔上皮细胞以低感染复数暴露于Pg,持续5~23周。结果表明,持续暴露于Pg会引起细胞形态变化,延长S期,提高增殖能力,并促进细胞迁移和侵袭。进一步研究发现,肿瘤相关基因如NNMT、FLI1、GAS6、IncRNA CCAT1、PDCD1LG2和CD274是长时间暴露于Pg后细胞肿瘤样转化的关键调节因子。因此,Pg的慢性感染可能是口腔癌的潜在危险因素。
2 Pg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作用机制
2.1 Pg诱导肿瘤细胞逃避宿主免疫反应
有关Pg诱导肿瘤细胞免疫逃逸的研究目前较少,主要集中在影响免疫共调节受体和免疫检查点分子表达方面。
B7-H1(PD-L1)受体在大多数人类癌症细胞中表达,引起活化T细胞的无反应性和凋亡。B7-H1受体在癌细胞或转化细胞上调,干扰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上的PD1受体,从而阻断PD1受体对肿瘤上皮细胞的细胞毒活性,使肿瘤细胞克服宿主免疫反应。Groeger S等[22]研究发现,在分别感染了两个Pg菌株(W83和ATCC 33277)后,OSCC细胞SCC-25和BHY以及人原代牙龈上皮细胞的B7-H1和B7-DC受体均上调。但该实验结果的生理重要性和特异性尚待进一步验证。该团队在体外培养实验中发现,Pg的膜结构导致口腔鳞状细胞癌和牙龈上皮细胞中免疫调节受体PD-L1的上调,提示B7-H1表达可能有助于逃避免疫反应,这可能是导致Pg长期感染的重要因素[23]。
另外,Yuan X等[24]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Pg定植于食管癌细胞后,可诱导其高表达免疫检查点分子B7-H4及组蛋白去甲基化酶KDM5B。两分子通过协同抑制效应CD8+T细胞活化及降低肿瘤局部趋化因子浓度,阻碍免疫细胞向肿瘤组织高效、定向传递,从而使Pg感染的食管癌微环境变成一个“冷”环境,降低感染及肿瘤特异性的CD8+T细胞免疫应答。
2.2 Pg诱导上皮间充质转化
Pg可通过促进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从而驱动肿瘤发展。
Ha NH等[25]的体外实验表明,长期感染Pg导致OSCC细胞的形态延长,EMT特异性上皮标记物的表达降低,而肿瘤干细胞标志物CD44和CD133的表达有所增加。该研究揭示Pg对OSCC EMT特性以及迁移和侵袭特性的影响。
Lee J等[26]研究发现,Pg感染促使人原代上皮细胞中EMT的重要调节剂磷酸化-GSK3β显著增加(P<0.01),与此同时,Slug、Snail和ZEB1等EMT相关的转录因子的蛋白质和mRNA表达显著增加(P<0.01)。在Pg感染的120 h内,口腔上皮细胞中波形蛋白,间充质中间丝蛋白的表达显著增强,而黏附分子E-cadherin表达显著下降(P<0.05),膜定位以及β-catenin减少,而长期感染期间,MMP-2、-7和-9明显增加。Pg感染还促进了宿主细胞的迁移。由此可知,Pg持续感染诱导人原代口腔上皮细胞获得了与EMT一致的分子和细胞起始变化。尽管原代上皮细胞中Pg的持续存活水平与上述表型变化密切相关,但是,又有其他研究关注于细菌分泌的效应物,如核苷二磷酸激酶(nucleoside diphosphate kinase,NDK)或结构毒力因子(如菌毛和脂多糖)是否可以独立地促进EMT。已有研究证明这些特性有助于细菌免疫逃逸以及在上皮细胞中长期定植[23,27-28]。
Abdulkareem AA等[29]的研究表明,Pg感染可能通过上调细胞因子来诱导上皮细胞间质转化,Pg促使OSCC细胞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1,TGF-β1)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等细胞因子显著上调,这些细胞因子参与了EMT的诱导和转录因子锌指蛋白SNAI1的激活,引起EMT的间充质标志物上调、上皮标志物的下调,从而导致体外培养的上皮细胞层特性改变。因此,Pg感染促使OSCC在分子水平上发生上皮特性与EMT特性的改变。
Sztukowska MN等[30]发现,在永生化的牙龈上皮细胞(TIGK细胞)中,Pg感染诱导了控制EMT的ZEB1转录因子表达与核定位,缺少FimA纤维蛋白的Pg菌株诱导ZEB1表达的能力下降,Pg在具有Fn或Sg的双物种群落中同样会引起ZEB1表达的增加。ZEB1表达增加与ZEB1启动子活性增强有关,ZEB1的水平与包括MMP-9和波形蛋白在内的间充质标志物的迁移增加,以及上皮细胞向基质的迁移增强有关,用siRNA敲低ZEB1抑制了Pg引起的间质标志物的增加和上皮细胞的迁移。体外实验中,感染Pg的小鼠口腔牙龈组织中的ZEB1水平升高。
综上所述,FimA驱动的ZEB1表达可能部分解释了Pg对OSCC的促进作用。上述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Pg可能与其他口腔细菌协同促成间充质表型,从而驱动肿瘤的发展。
2.3 Pg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
MMP9与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有关,舌鳞癌细胞系SAS细胞可持续分泌MMP-9酶原。Inaba H等[31]研究发现Pg激活ERK1/2-Ets1、p38/HSP27和PAR2/NF-κB途径以促进SAS细胞MMP-9酶原表达,而Pg的牙龈蛋白酶随之激活了MMP-9酶原,从而增强了OSCC的细胞系的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这些发现提出了OSCC进展和转移可能与牙周炎相关的新机制。
Ha NH等[32]研究发现,Pg对MMP的上调作用,依赖于白介素8(IL-8)。Pg感染可促使OSC-20和SAS等OSCC细胞MMP上调,侵袭能力增强,却不能引起SCC-25细胞MMP水平及的侵袭能力改变。进一步研究发现,OSC-20和SAS细胞中,Pg感染后IL-8分泌显著增强,但在SCC-25细胞中却没有增强。当IL-8直接作用于SCC-25细胞时,细胞的MMP水平和侵袭能力显著提高。相反,感染Pg的OSC-20和SAS细胞中IL-8的下调会降低其侵袭能力和MMP水平。因此,Pg通过依赖IL-8的MMP上调来增加OSCC细胞的侵袭性。抑制剂如苹果多酚(apple polyphenols,AP)、蛇麻草多酚(hop polyphenols,HBP)和HBP的高分子组分(HMW-HBP)可以阻止OSCC的MMP-9活化和扩散,这些抑制剂可能是预防此类肿瘤侵袭的候选细胞抑制剂[33]。
2.4 Pg加速细胞周期并抑制宿主细胞凋亡
细菌调节宿主细胞的细胞周期,使其自身能够在宿主细胞内存活并表达其毒力因子。细胞周期蛋白(cyclin),p53和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3-激酶(PI3K)等蛋白在真核细胞周期中具有多级控制功能,Kuboniwa M等[34]的研究表明,Pg诱导了这些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和磷酸化状态的改变,被感染的人原代牙龈上皮细胞的增殖速率增加,S期进程加快。Pan C等[35]也证明了Pg通过促进G1/S转化来影响人牙龈上皮细胞的周期,这暗示着细胞周期蛋白D和细胞周期蛋白E的上调。因此,尽管细胞癌变是一个漫长的多阶段和多因素过程,但不应忽视促进细胞增殖的细菌对癌变的影响。
热休克蛋白27(heat shock protein 27,HSP27)可以通过抑制caspase蛋白的激活来抑制细胞凋亡。Inaba H等[31]的研究同时发现,Pg感染后,口腔癌细胞中HSP27的表达增加,并且HSP27在感染细胞中对MMP-9具有活化作用。HSP27在许多类型癌细胞中过表达,并导致不良预后,或成为癌症治疗中新的治疗靶点[36-37]。最近,Lee J等[38]的一项研究首次发现了细菌效应子Pg-NDK对HSP27的磷酸化作用,赋予了人口腔原代上皮细胞抗凋亡表型,HSP27可能是促进口腔黏膜中Pg清除的重要靶标。此外,NDK-HSP27相互作用可能为近期与Pg相关的癌症的靶向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在短期原代培养的牙龈上皮细胞中,Pg通过上调抗凋亡分子Bcl-2和下调促凋亡Bad蛋白来抑制细胞凋亡[39]。Yilmaz等[40]报道,Pg通过激活pPI3K/Akt信号通路来阻断细胞凋亡并促进原代牙龈上皮细胞的存活。后来,Mao S等[41]提出,Pg可通过操纵控制线粒体细胞死亡途径的PI3K/Akt和JAK/Stat通路来阻断牙龈上皮细胞的凋亡。此外,Yao L等[42]也证明Pg可通过Akt使促凋亡的Bad蛋白失活,抑制细胞凋亡。Akt是Pg刺激的抗凋亡途径的主要组成部分,还可以通过连接P2X7受体抑制ATP诱导的牙龈上皮细胞凋亡[43]。Pg中的miRNA-203可抑制SOC6,后者在调节线粒体动力学和随之而来的细胞凋亡事件中具有重要作用[44],miR-203对细胞周期的调节可能会影响某些癌的病理表达[45]。因此,线粒体依赖性细胞凋亡的抑制可能是Pg在牙周组织中生存的重要策略,也是其致病性的关键特征。
2.5 Pg诱导肿瘤细胞周期停滞并促进自噬
尽管已发表的多项研究均涉及Pg对口腔上皮细胞的作用,但对其在癌细胞的作用却知之甚少。当口腔癌细胞被Pg菌株FDC 381感染时,细胞周期G1期被阻滞,细胞的增殖受到抑制,细胞凋亡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增加了巨自噬[46]。研究表明,口腔癌细胞巨自噬的增强,是其应对Pg入侵,限制细菌毒性的一种适应机制,自噬反应的增加通过活性氧(ROS)的形成来激活,可能抑制细胞增殖。此外,Pg还可通过加速细胞周期或调节细胞凋亡来促进细胞增殖[46]。在这些分子事件中报道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使用了正常上皮细胞与肿瘤细胞这样不同宿主模型系统进行研究,这可能揭示有关肿瘤发生的关键信息。与此观点一致,有报道证明Pg感染原代口腔上皮细胞后可调节和抑制线粒体与生物膜衍生的ROS,以确保自身在细胞内成功生长和存活[47-48]。此外有研究表明,Pg还可能通过选择性自噬,输送至富含内质网的自噬体中,以便在人原代上皮细胞中复制并持续存活[49]。
2.6 Pg促进肿瘤远处转移和化疗耐药
Pg可能通过Notch通路介导OSCC对紫杉醇的耐药。前述Ha NH等[25]的研究发现,当OSCC细胞反复暴露于Pg 5周后,对化疗药紫杉醇产生了抗药性。另一组研究表明,Pg的持续感染促进口腔癌向肺的远处转移以及对抗癌药物抵抗,由Pg感染的OSCC细胞组成的肿瘤异种移植物通过Notch1胞内结构域(NICD)激活表现出对化疗药紫杉醇的更高耐受,这表明Pg可能在OSCC的化疗耐药进展中起作用[50]。因此,靶向Notch信号通路可用于克服肿瘤治疗耐药性,推荐与常规化疗方法联用[50-51]。
2.7 Pg促进肿瘤细胞增殖
防御素是人体中一类重要的抗菌多肽,Hoppe等[52]表明口腔病原体如Pg和Aa通过影响人防御素的基因表达来改变口腔肿瘤细胞的增殖特性。用Pg和人α-防御素孵育口腔肿瘤细胞会导致细胞增殖加速,而Aa则导致细胞死亡增加。因此,这些牙周病原体对口腔肿瘤细胞的增殖具有相反作用,但是两者对增殖速率产生的作用都是通过改变致癌相关的α-防御素基因的表达水平实现的。由于人防御素通过EGFR信号转导通路影响细胞增殖,抗菌多肽可以作为肿瘤发生和感染之间的分子链接。
Zhou Y等[53]报道,通过牙龈蛋白酶依赖的蛋白水解过程对β-catenin信号的非经典激活可能是Pg促进肿瘤发生的潜在机制,因为牙龈蛋白酶对β-catenin的非经典激活和β-catenin破坏复合物的解离可能会诱导增殖表型。这可能是Pg通过蛋白水解加工破坏口腔组织动态平衡的新机制。
2.8 Pg将乙醇转化为乙醛
乙醛是酒精的初级代谢产物,是人类与酒精饮料的摄入有关的一类致癌物[54]。与口腔卫生良好的个体相比,口腔卫生较差的受试者唾液体外实验中由乙醇产生的乙醛升高2倍[55-56]。Pg将乙醇转化为乙醛可能导致DNA损伤、突变和上皮细胞过度增殖,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酗酒和某些癌症相关[54]。
2.9 Pg表观遗传修饰对炎症的作用
慢性牙周炎是人类最常见的炎症疾病之一,炎症的刺激和持久性受到复杂的机制调节,其中表观遗传途径受到特别关注。表观遗传修饰包括DNA和相关蛋白质的化学变化,可能导致染色质重塑和基因转录的激活或失活[57],此类变化可导致癌症、自身免疫和包括牙周炎的炎性疾病。在牙周炎中已检测到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这两个主要的表观遗传学调控,并且其基因表达也会受到DNA甲基化的影响[58],多项研究在牙龈组织中发现了异常的DNA甲基化[59-60]。最近的研究表明,Pg脂多糖显著调节与表观遗传机制有关的基因[57]。
2.10 Pg产生肽酰精氨酸脱亚氨酶在癌症发病机理中的潜在作用
Pg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产生肽酰精氨酸脱亚氨酶(peptidyl arginine deiminase,PAD)的病原体,该酶可将蛋白质和多肽中的精氨酸残基转化为瓜氨酸,从而修饰细菌和宿主蛋白质[61-62]。蛋白质瓜氨酸化通过改变蛋白质的原始空间结构和功能来调节宿主的炎症信号网络[63]。宿主可通过编码5种钙依赖性PAD家族基因而具有瓜氨酸化的固有功能,宿主PAD与各种人类和动物肿瘤相关[64-65]。Kholia S等[65]报道,在肿瘤相关微囊泡刺激前列腺癌细胞(PC3)的过程中,PAD2和PAD4的表达水平以及细胞骨架肌动蛋白水平升高,使用泛PAD抑制剂Cl-am抑制PAD酶活性显著降低了微囊泡的释放并降低了细胞骨架肌动蛋白水平。PAD家族,尤其是在多种浸润性肿瘤中过表达的PAD4,在肿瘤的进展中似乎起着重要的作用,而PAD抑制剂可抑制肿瘤进展和炎症症状[65-67]。
口腔感染及炎症与癌症之间的直接关系逐渐被人们接受、认可,牙周炎和消化系统肿瘤的相关性成为这种关系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即使在考虑了诸如吸烟、体质量指数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混杂因素之后,这种关系仍然存在,而其中潜在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最近,牙周炎相关致癌作用的小鼠模型显示,长期慢性细菌感染通过经由Toll样受体与癌及癌前口腔上皮细胞直接相互作用而促进OSCC。口腔微生物可能直接刺激OSCC增殖并诱导肿瘤产生相关关键分子,例如NF-kB、IL-6-STAT3、cyclin D1、MMP-9以及细菌牙龈蛋白酶。Pg有可能与已知危险因素结合促进肿瘤发展,在存在诸如酒精和烟草滥用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常见的口腔微生物种群可能在口腔癌的发病机理中具有协同作用。尽管可以明确这些公认的致癌因素在肿瘤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它们不能作为独立因素解释每年发生的大量癌症病例。
本文讨论了牙周炎的关键病原体Pg发挥致癌作用的几种可能的机制。Pg可能不是多种细菌共同感染的口腔微生物群中的唯一致癌物,并非每个人都携带可能诱发肿瘤且可能与预后不良有关的Pg。实际上,针对Pg的血清抗体可用于改善癌症的诊断和预后。胰腺癌和胃癌可能与Pg有关,这一事实表明口腔细菌分泌的效应分子,炎性细胞和介质随唾液和血液传播到远处,并诱发全身性致癌作用。Pg血清IgG水平升高与消化系统肿瘤有关的发现也支持了这一点。令人信服的是,在Pg与消化系统肿瘤之间可能存在直接关系,其中致癌作用的原因可能是口腔微生物继发感染其主要部位口腔之外、在解剖学上连续的部位。需要开展更多、更广泛、更可控的队列研究和分子流行病学及实验研究,来揭示其中的分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