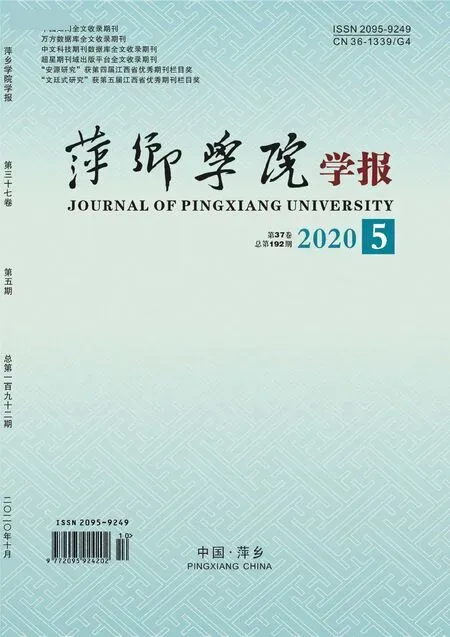什么是教育理论进步的动能——基于对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和杜威教育思想之发生比较的角度
谢武纪,文健
什么是教育理论进步的动能——基于对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和杜威教育思想之发生比较的角度
谢武纪1,文健2
(1. 长江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408100;2. 萍乡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江西 萍乡 337000)
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和杜威堪称近代以来教育学术史上被公认的三位“标杆式”人物。通过对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和杜威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承续的分析及观点比较,可以发现,对科学的追求、对人文的执着和直面实践需求共同构成了推动教育理论进步的三个关键要素,也是促进教育理论持续发展的动能所在。其中,科学反映了教育理论的逻辑依归,人文代表了教育理论发展的价值追求,实践体现为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力之源。
教育理论;进步;科学;人文;实践
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和杜威堪称近现代教育学术史上三位“里程碑”式人物,虽然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境遇及所选择的理论基础不同而在对教育的认识中显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进路,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影响,但他们在教育学史上的贡献及表现出来的知识旨趣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大抵体现了近现代教育学共同的学术旨趣和追求,也是推动教育学理论发展的核心动力所在。
一、科学:教育理论进步的逻辑依归
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不仅成为一种对知识的理性追求,也逐渐成为人们思想和知识生产的规范,同时构成了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核心旨趣。受科学目标的驱使,教育学才得以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尽管教育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的久长,人们对教育的阐发也可谓是源远流长,但将真理(可靠性)明确为教育研究的标准却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事情。在这方面,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当推首功,并奠定了其在近现代教育学史上的“先行者”地位。在《大教学论》开篇中,夸美纽斯先后用两个“可靠”表达了自己的知识抱负,“每个基督教王国的一切教区、城镇和村落,全都建立这种学校的一种可靠引导,使青年男女……懂得科学,纯于德行,习于虔敬……它还指出了一种简易而又可靠的方法,使它能够称心地实现出来”[1]3。要实现这一目标,夸美纽斯认为首要的是找到一个确定性的准则,即根据“事物本来不变的性质”以“先验的方式”(a-priori)去达成证明,如此教育学方能从昔日那种完全基于个人经验总结的、后验的、互不联系的碎片化痼疾中彻底脱离出来[1]3~4。夸美纽斯将“教育适应自然原则”确立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准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教育方法。但作为牧师的夸美纽斯的确表现出了矛盾性的一面,他一方面高度肯定了感觉经验的作用,“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1]168,但另一方面,他对这一原则的论证则诉诸了“神启”,如果稍稍浏览一下《大教学论》及夸美纽斯其他时期的著作,人们不免会对大量充斥其中的诸如“上帝”“圣经”“虔信”等宗教语汇印象深刻。细读起来,会发现夸美纽斯所提出的每一条教育原理背后几乎都有来自《圣经》的理由和证据,“神启”始终构成了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支点”。夸美纽斯教育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宗教神秘色彩,成就了后世对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理论基础的所谓“不彻底性”和“矛盾性”的评判。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因为从当时的社会语境来看,假如夸美纽斯放弃了这种先验原则,那么在当时宗教氛围依旧浓厚的欧洲社会,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使他的理论得以推广的,更不能赢得世人的呼应。值得一提的是,夸美纽斯笔下的人之所以与上帝的其他造物不同,乃在于人这一造物先验地渗透了“普遍神的预见”,天然具有“可教性”品质。至于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感受并履行“神旨”,取决于人在感觉中去发现和领悟;取决于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现并尊重“自然秩序”;取决于教育的理性化。所以,教育引导人从感觉出发去认识万物和将《圣经》视作为认识的源泉在逻辑上是内在融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夸美纽斯的宗教理论基础不仅不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败笔”,相反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点睛之笔”[2]。
真正构建了系统的教育学知识体系并切实奠定教育学在学科之林中的“科学”地位的,当赫尔巴特莫属。赫尔巴特认为,只有在教育学自身具有相对稳固的理论基础,并形成必要的知识规范的基础上,才能摆脱“受外部的治理”的困境;只有当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强有力地说明自己方向的时候,教育学和其他学科同侪之间才能产生取长补短的交流[3]9~10。否则,教育学永远称不上是一门成熟的科学,也无从彰显自身的合法性。赫尔巴特教育学所致力的,就是将教育学纳入进科学轨道[4]。其实,单单从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标志之作《普通教育学》的书名看,“普通”一词其实已经表达了赫尔巴特教育知识“普遍性”的抱负和对于知识“科学性”的追求。赫氏承续了夸美纽斯对零散的、经验性的教育研究的批判,所不同的是,在理论基础上彻底否定了神学色彩,将教育学知识建立在伦理学、心理学(统觉)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赫氏这里,教育学就是一门超越社会——文化的语境、反映了教育之普遍规律的科学。这也是赫尔巴特被后人冠以“科学教育学之父”的缘由之所在。赫氏这种学术信念和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张扬以及对科学的信奉密切相关。实际上,这种对于教育学知识普遍性和一般性追求其实也是后期实证主义教育学的主要渊源和内在特征。但与后者相迥异的是,赫氏意义上的普遍性、一般性并非是自然科学上因果关系确定性的体现,其所服膺的是哲学,“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乃是哲学的任务,而且是整个哲学的任务”[3]420在“真”的问题上,赫尔巴特坚定地和经验主义站在了一起,称自己是个彻底的经验实在论者。在赫尔巴特看来,一切表象或观念(知识)的源起,并不是对内置于心灵的先验范畴“整理”的结果,而是“不可知”的外部实体与同样“不可知”的心灵实体相“遭遇”而发生反应的结果,是经验和时间共同作用的产物[5]。换言之,经验才是知识产生的根本,知识是否为真,需要接受实践和经验的检验。
杜威是站在实用主义理论立场上去理解真理的。实用主义并不否认传统认识论“真理是观念与事实的符合”这一基本的立论基础,但强调的是动态意义上的符合而非静态意义上的符合,因而他对于理论的认识和传统符合论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实用主义这里,理论的意义是即时性、工具性的,并不是对对象世界的普遍意义的摹写和映射,“理论称为我们可以依赖的工具,而不是谜语的答案”[6]。“我采取的主张是:一切知识或证实的可断言性都依赖于探究,而探究确实是和有问题的东西联系着。……这个主张也提供了或然性并在拒绝一切内在教条主义的陈述时决定了或然性的程度。唯一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就是主张真理的检验和标志在某种后果之中。”[7]可见,杜威并不关心观点、学说的客观性以及它们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主要是从观点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效用和实际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因而杜威所倡导的真理观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实践——探究基础上的情境性真理观。关于实用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内在特质,哈贝马斯将其总结为“拒绝屈服于任何种类的科学主义”[8]。这其实也解释了杜威为什么始终将“经验的不断改造”置于其教育哲学的核心地位,并将教育厘定为“生活”并反对将学校和社会区分开来的原因。具体到教育学知识真理观,他以“行动达致真理”过程逻辑出发将教育学知识何以可能导向了实践之路,将教育学知识真理观向社会民主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刘放桐因此认为杜威思想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想理路存在内在一致性[9]。
二、人文:教育理论进步的价值诉求
从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到杜威以来的教育学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继承、批判、建构构成了近代以来教育学知识发展的基本图景,不同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对教育发展造成了影响,但是,“成人”这一价值取向始终都是教育研究不变的追求和出发点。
在夸美纽斯教育学中,“完人”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于其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夸氏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思想的限制,但他坚信,在上帝的造物中,人始终是“最崇高、最完美、最美好的”。上帝代表了全知全能,那么作为上帝的宠儿的人理应向上帝靠拢,因此“完人”构成了夸美纽斯教育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夸氏同时注意到了人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强调因材施教,实际上也蕴含了深刻的人之解放的启蒙理性之光。“我们常常容易犯错误,我们想用每块木头雕出一尊雕像,没有注意自然的意向。结果,好些人学习他们没有天赋的学科,没有得到良好的结果,在副业方面的成就反而大于他们所选的正业。”[1]227
“教育性教学”是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根本出发点。在赫尔巴特看来,没有“无教育的教学”,也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其中所传达的意思是:真正的教学必须以“育人”为目的;必须是“成人”的伦理活动。换言之,那种完全不关心一个人会变好还是变坏的所谓“教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在将道德确立为教学的根本目的之后,教学该如何影响人的德行便是赫尔巴特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使人“明智”是实现道德目标的不二之选,“愚蠢的人是不可能有德行的。因此头脑必须得到激发。”[10]202那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又该怎样让人变得明智呢?他将注意力聚焦到人的身心发展的特征上,突出学生兴趣的培养和发展便成为其教学理念的基石,“教学的最终目的虽然存在于德行这个概念之中,但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教学必须特别包含较近的目的,这个较近的目的可以表达为‘多方面的兴趣’”[10]217~218。可以看出,赫尔巴特在为研究教育的行事成人提供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方法与路径的同时,其中所内蕴的人文意义也是毋庸赘言的。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后来人往往将“非人道”的“控制论”教育和赫尔巴特联系起来,并直接将板子叩在赫尔巴特的身上。值得一提的是,赫尔巴特却是康德“人是目的”原则的坚定拥护者,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和康德哲学主体性思想之间有着高度的承续性。至于因抹杀学生的主体性而备受诟病的传统“三中心”,即“教师中心”“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不过是后人从作为赫尔巴特教育学变体的凯洛夫教育学中所归纳出来的,赫氏终其一生都没有提出过所谓的“三中心”之说[11]。倒是赫尔巴特反复所强调的五种道德观念(俗称“五道念”),即内心自由、友善、法、完美性、公正,直接反映了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价值性和人文性。其中的“内心自由”更是直接指向了人摆脱外部束缚的倾向,服从于人的意志自由和判断理性诉求。内心自由有益于情感,它能使人心情舒畅和愉快,“拥有真正的自我”[17],而人的“心灵的充实——应当视为教学的一般结果——比其他任何细枝末节的目标更重要”[3]109。
杜威直接高扬民主的大旗,他的价值理念和人文主义思想相较于夸美纽斯和赫尔巴特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杜威认为,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社会制度的共同目的就是为了每一个社会个体能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不管这个人的性别、种族、职业和经济状况如何,民主社会的道德意义“是它们对社会每个成员的全面发展所作出的贡献。”[13]因此良好的教育首先应具备现实性特征,必须建立在学生现实活动和需要之上。在杜威看来,教育性诉求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教育的实践和行动标准始终需要坚持“出乎教育”和“合乎教育”的统一,需要将手段与目的综合起来进行考量,不能割裂开来。“儿童是太阳”,好的教育设计始终是围绕着儿童的主动性发挥和个人创造性的发展而进行的,好的教育标准不是强加的,亦非是千篇一律的。在杜威看来,教育的过程既是促进人的个性化过程,也是促进人的社会化过程,最终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教育学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分析,解释教育情境中的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和谐共处的目的。
总之,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和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获得了广泛认同,原因并不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的先进性上,或者理论贡献上,根本意义上则是内蕴于其理论之中的人文价值关怀。“当教育研究的人文情怀广泛地深入人心的时候,为了一切人、一切为了人和为了人的一切成了大多数教育研究者的基本理念。”[14]
三、实践:教育理论进步的不竭源泉
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再到杜威,我们看到,个人因素固然是推动教育学发展的重要一维,但无一例外都将自身融入历史感中,并渗透着浓郁的时代创新意识。这种从时代出发的敏感性和创新意识可以说构成了教育学知识的前进动力之源。
近代以来,教育实践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得日趋复杂,传统的教育目标、内容、组织形式和管理的体系化遭受到了挑战。夸美纽斯敏锐地意识到建立规范化的教育实践体系,开展教师培训和实现教育普及的重要性。夸美纽斯之所以将“教育适应自然”作为教育的根本指针,乃在于夸氏认为“在此之前没有一所完善的学校”[1]60,而这些学校之所以不完善,归根结底是当时的学校教育不符合教育的自然规律。针对传统教育的对象仅仅限定在少数贵族及资产阶级上层子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上层精英阶层这一客观现实,夸美纽斯认为这和时代发展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他的“泛智”思想教育正是出于对此问题的纠偏。针对中世纪学校的教育组织工作松散,内容和进度不一,教学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的情况,夸美纽斯进一步论证了班级授课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同时也对教育普及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赫尔巴特科学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其目的是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性理论,帮助教育学摆脱“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的治理”的困境,从而终结早为夸美纽斯所体认到的教育研究的混乱状态。在赫尔巴特看来,有且仅当教育学自身获得了和临近学科一样的稳固的学理基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彼此之间才有平等对话、取长补短的可能,否则教育学不过是被各种意见所充斥的“大杂烩”,自然就谈不上合法性,更遑论在现实中的指导力了。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再只是对教育实践作简单的经验性描述和规定性陈述,而是以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为基础搭建起了一般性、形式性、系统性的超越社会—文化的语境的教育理论大厦,彰显了教育学的普适性追求。到赫尔巴特这里,教育学学科基本的理论框架已经成型。这也是人们将赫尔巴特标举为“科学教育学之父”的原因。
科学教育学经过赫尔巴特后继者的进一步发展,慢慢跟经验实证主义合流而走上了一条工具—手段的“技术主义”路线:在活动之先预设某个目标,然后根据目标来选择那些最有价值的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再制定相应的教学方式和手段。这实际上已经将教育学降格为一种工艺或操作,其将关注点主要聚焦在了教学的程序、方法和相应的教学结果之上,并以其作为衡量教育学知识科学与否的标准。此举不仅偏离了赫尔巴特“独立使用自己理性”的精神,也违背了他的教育学本质上指向判断力培养的初衷。然而,恰是因为这一变异了的教育学的所呈现出的“应用性”旨趣,使得曾经一度默默无闻的赫尔巴特教育学很快在世界各地广泛地流行开来。
教育技术主义、程序主义随着工业文明的持续推进而愈演愈烈,教育文化专制倾向越来越明显,杜威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趋势是和民主社会背道而驰的。他站在社会民主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立场上,以“教育无目的”论的设定反对教育实践中成人社会对儿童的专制,突出个体经验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以“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三个著名命题突破了传统教育观念的藩篱。杜威认为,“学校是一个个小社会,在这些小社会中,儿童通过实践学会如何促进自己的生长,别人的生长和整个社会的生长”[15]。杜威在其所创办的芝加哥实验学校中,充分践履了他的教育信条。但杜威教育学并没有简单抛弃知识“普遍性”的追求,从他对于赫尔巴特的贡献评价中,我们会发现这并非虚言,“赫尔巴特的伟大贡献,在于使教学工作脱离陈规陋习和全凭偶然的领域。他把教学带进了有意识的方法的范围,使它具有特定目的和过程的有意识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灵感和屈从传统的混合物,而且把教学和训练(或译‘训育’)的每一件事,都能明确规定,而不必满足于终结理想和思辨的精神符号等模糊的和多少神秘性质的一般原则。”[16]只不过,在杜威这里,人的个体性和人的社会性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人的社会性是个体性的目的之所在,但人的个体性却是形成社会性的前提。也就是说,不重视儿童个体经验的养成,是谈不上所谓的社会性目标达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积极倡导儿童在“做中学”和相互协作,其目的是为了让儿童在学校教育中,能习得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相关的知识、技巧和经验,养成独立、宽容、反思的品格,具备民主社会公民应有的意识。
[1]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M]. 傅任敢,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2] 李润洲, 楼世洲. 宗教信仰:败笔抑或点睛——对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另类解读[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6): 94~97.
[3] 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M]. 李其龙, 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4] 陈桂生.“普通教育学”研究旨趣[J]. 中国教育科学, 2015(3): 37~77.
[5] W. Boyd,E. J. King.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M].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75: 340~341.
[6] 威廉•詹姆士. 实用主义[M]. 陈羽纶, 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45.
[7] 杜威. 人的问题[M]. 傅统先, 邱椿,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56.
[8] Jurgen Habermas “Reflections on pragmatism", in Mitchell Aboulafia, et al(eds.): Habermas and Pragmatism[M]. New York: Route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228.
[9] 刘放桐. 再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兼论杜威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同一和差异[J]. 天津社会科学, 2014(2): 3~12.
[10] 赫尔巴特. 赫尔巴特文集•教育学卷[M]. 李其龙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1] 张廷艳, 伍叶琴. 教育史人物研究中不在场的“人文精神”及回归[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26~32.
[12] 易红郡, 缪学超. 论赫尔巴特的伦理学思想体系[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5): 71~77.
[13] 杜威. 哲学的改造[M]. 许崇清,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100.
[14] 孙俊三. 教育研究的境界——论教育学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的追求[J]. 教育研究, 2005(11): 11~17.
[15] 内尔•诺丁斯. 教育哲学[M]. 许立新,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41.
[16]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75~76.
What is the Developing Motiva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 Based 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Comenius, Herbert, and Dewey’s Educational Ideas
XIE Wu-ji1, WEN Jian2
(1.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Chang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2. Primary School Attached to Pingxiang Normal School,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Johann Amos Comenius,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and John Dewey are recognized as three contemporary “benchmark”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academy.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educational ideas, we can find that the pursuit of science, humanistic care and practical care commonly compose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pedagogy, which are also the academic motivation of pedagogy development. Science reflects the logic motivation of pedagogy, humanism represents the genuine pursuit of pedagogy, and practical care demonstrates the impetus of pedagogy.
educational theory; progress; science; humanities; practice.
G40
A
2095-9249(2020)05-0077-04
2020-09-22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2017BS44)
谢武纪(1975—),男,湖北随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
〔责任编校:吴侃民〕
——评《批判教育学的当代困境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