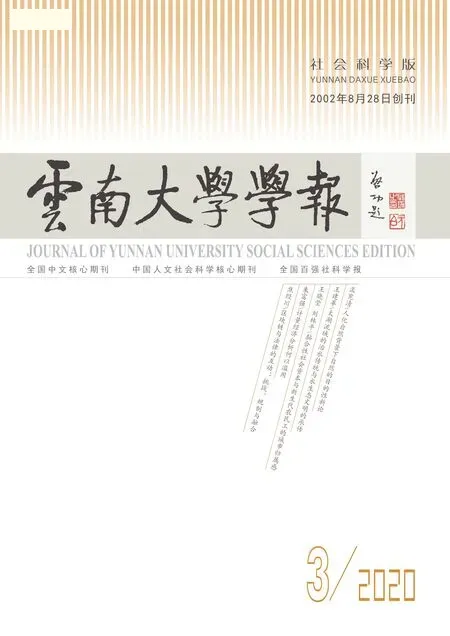洛克与莱布尼茨关于语词任意性的争论
张励耕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洛克与莱布尼茨的争论是西方哲学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这其中比较为人熟知的是“天赋观念”问题:双方各自的观点被视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代表,而是否存在“天赋观念”这一点则成了论战的焦点。不过与这样的核心问题相比,两人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交锋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意图处理的是他们关于语词任意性的争论。
一、洛克与莱布尼茨的基本观点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是两部针锋相对的著作,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各自的观点上,也体现在著作本身的篇章结构中。两本书的第三卷都是讨论语言及语词等问题的,其中的第二章则都是讨论语词意义的,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但两人的基本观点可谓大相径庭。
在《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第二章开篇,洛克提出了一种在他看来符合常识且成立的观点:
尽管一个人有五花八门的思想,而且他人和他自己都可以从中得到利益和愉悦;不过这些思想都是在这个人心中的,对他人而言是不可见的、隐藏的,不可能自己显现出来。如果没有思想的交流,那么社会的舒适与优点便无法被人拥有,因而人们有必要找到这样一种外部的可感的符号(external sensible signs):它们是关于那些构成人们的思想的不可见的观念的,而又可以被其他人知道。针对这一目的,无论就丰富性还是便捷性而言,都没有比清晰分明的声音更合适的东西了,人们可以轻松而多样地发出这些声音。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语词——它们就其本性而言如此适合上述目的——如何被人们当作观念的符号来使用;这不是由于在特殊的清晰分明的声音和特定观念之间存在任何自然的关联(connexion,原文即如此拼写),因为那样一来人世间就应当只存在一种语言;这应当是由于一种自发的强制(voluntary imposition),而一个语词以此被任意地(arbitrarily)(1)在下文所引用的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ook III Chapter IX § 4的一段话里,洛克又使用了“arbitrary imposition”这个术语,由此可以推断出他几乎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arbitrary”和“voluntary”这两个词的。但实际上 “voluntary”(自主或自发)与“arbitrary”(任意)并不一定是完全同义的。比如一个人“自主”做出某种行为通常还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并可以被他人预见的;而“任意”做出的行为则可能是没有理由并难以预见的。根据洛克的立场来看,使用“arbitrary”一词似乎更为合适。当作一个观念的记号(mark)。因此,语词的用途就在于作为观念的可感的记号;而它们所代表的观念就是其特有的、直接的意义(signification)。(2)Locke,John(1975)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A. C. Fraser,Dover Publications,INC. New York,Book III Chapter II & 1,着重号为原文中所有。本文所引的译文均为笔者自己所译,以下不再一一赘述。
由于年代相距较远,洛克的一些术语会让今天的读者觉得有些生疏,不过其核心观点的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在他看来,语词的作用在于作为观念的符号在交流中的使用:观念是隐藏在人心中的,对于他人而言不可见,因而人们无法直接交流观念;作为观念之符号的语词则是可见的,可以被他人知道,能够起到交流的作用。在《人类理解论》中有不少类似的表述,体现了他在语词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在上述引文里,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语言符号之任意性的一个推论:在语词是观念的符号的前提下,如果语词与观念之间的结合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关联,那么这种结合就必定不是任意的,这样一来人世间应当只有一种语言;可既然语言有很多种,那么这种结合就应当是任意的,因而不可能是出于自然的关联。这种非任意的结合,被洛克称为“自发的强制”,即它是经过人们自发选择之后再“强加”给人的。不过,至于这种“强制”具体如何发生,洛克并未详加阐述。或许在他看来这并不重要,因为既然语词与观念的结合是任意的,那就没什么规律可循,不必费力去加以研究。
世界上的语言的确是五花八门,所以洛克的推论乍看上去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实际上,这里仍有可争论的空间。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莱布尼茨便直接引用了洛克的论点,并提出了与之相反的看法,他说:
我知道,在学院和其他任何地方人们都会说语词的意义(signification)是任意的(3)这里的“任意的”一词,英译本为“arbitrary”,拉丁文原文为“ex instituto”。根据陈修斋译本的解释,其意为“出于定制的”,而陈本的翻译是“武断的”,这种解释和翻译之间的差异可能有些令人费解。结合上下文来看,直接译为“任意的”(arbitrary)似乎更为合适。,而且它们的确并不由自然的必然性所确定;但它们还是出于一些理由(reasons)而被确定:有时是自然的理由,其中偶然因素起了一些作用;有时是道德上的理由,这涉及人为选择的问题。或许有一些人造语言是纯然选择的结果和完全任意的,比如中国的语言就被认为曾经是这样,还有乔治乌斯·达尔格奴斯和已故的彻斯特主教威尔金的语言。(4)这里所提及的两个人物提出了关于普遍文字的想法并深深地影响了莱布尼茨。详细情况请参阅《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02页注释1。此处保留了陈本对他们名字的翻译。但那些据我们所知是从已知语言中构造出来的语言,则混合了人为选择的特征与那些已知语言中自然的和偶然的特征。(5)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996)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2nd ed.),edited by P. Remnant and J. Benne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Book III Chapter II。
尽管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要称中国的语言为人造语言,但莱布尼茨对自己基本观点的表述还是如同洛克一样清楚。他并未主张语词的意义是由自然所确定的,也即并未否认其中的任意性,但却认为意义的确定是有“理由”的,至少对于非人造语言来说是如此。与洛克的断言相比,莱布尼茨的主张显得较为温和。他所谓的“偶然因素”并不是与“自然因素”相对立的另一种因素,而是后者的一部分。比如一个语词可以在历史的流变中被引申用来表示不同的意思,这是有偶然性的,但每次引申肯定都有一定的理由,因而不会如洛克所说那样被任意地当作某个观念的记号。此外,他所列举的“从已知语言中构造出来的语言”的例子是一些盗贼发明的江湖黑话,由此可以推断,他所谓的“已知语言”应当指与人造语言相对的自然语言,如拉丁语、德语等。正是在这些自然语言中,语词与意义的结合既有人为选择的部分,也有非人为选择的、出于自然的理由(尽管其中会有偶然因素起作用)的部分。如此一来,洛克的观点就是不成立的。
可见,两人争论的焦点问题可以被概括为:作为符号的语词与作为语词之意义的观念之间的结合是否是纯然任意的?洛克认为这是纯然任意的,莱布尼茨则认为这其中有非任意的部分,而且人们可以给出相应的理由。至于孰是孰非,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
二、对双方分歧的进一步分析
尽管最后的结论分歧很大,但双方的一些出发点却是一致的。两人各自拥有一套完整的“语言哲学”理论,其中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语词是一种符号,需要同观念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意义,或者说观念就是语词的意义。这种立场被洛克称为“双重契合”:语词直接标示观念,观念直接标示事物;由于语词不能直接标示事物,二者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所以语词的意义只能是其所标示的观念,而不可能是事物。(6)关于“双重契合”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阅张励耕:《〈 人类理解论〉中“隐秘的指涉”》,《哲学研究》2016年第1期。就本文讨论的话题而言,莱布尼茨也基本赞同上述看法。
通常认为,洛克与莱布尼茨最根本的对立在于是否承认天赋观念的存在:洛克认为不存在这种东西,一切观念都来源于经验;莱布尼茨则主张有一些观念是天赋的。不过,两人关于语词任意性的观点似乎并不与他们各自在天赋观念问题上的立场相对应。如果一切观念都来源于经验,那么语词与意义的关联应当也是偶然的或任意的,因为经验本身就是偶然的;即使天赋观念存在,也并不意味着这种关联一定也是天赋的。因此,在语词任意性的问题上,经验论立场与洛克的观点是内在相关的,但天赋观念论立场与莱布尼茨的观点则可以相互独立。
这意味着,双方分歧的关键点并不在于对语词本质的看法,也不在于观念的来源,而在于一个事实性的问题,即语词与意义之间是否实际上存在着自然的关联。人们不能靠纯粹的哲学思辨来解答该问题,必须考察语言的真实情况。就这一点而言,莱布尼茨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博学有力地支持了其论点。
在本文第一节所引用的论述之后,莱布尼茨用大量篇幅对语词做了诸多具体的考察。在笔者看来,这些考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词源学(etymology)的考察,主要梳理当时各种欧洲语言的历史源流和单个语词含义的演变。比如“Coaxare”是一个与青蛙相关的拉丁语词,本是表示青蛙叫声的,在德语中却被后人引申来表示无聊的空谈,因为这与噪音般的蛙鸣有相似之处;也被引申来表示有生命之物,因为鸣叫本就是有生命的体现;最后甚至在英语中引申为表示迅速的副词“quickly”。词义的演变里的确有各种偶然因素存在,但每一次的引申却又有一定的理由,这是对莱布尼茨立场的很好的证明。
第二类则是音义学(phonosemantics)(7)“音义学”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概念,指关于声音与意义之间天然联系的研究,由语言学家沃罗宁(Stanislav Voronin)于1980年在Fundamentals of Phonosemantics一书中提出。莱布尼茨当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如今看来他的这些考察可以被归于这个领域之下。的考察。莱布尼茨分析了字母R、L、A等所代表的声音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说明了很多单词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被构造出来的。比如R天然地表示较为激烈的运动,L表示较为柔和的运动,而A则可以跟h组合来表示呼吸。这种考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显然与词源学的考察不同,并不是在探究每次词义演变中的理由,而是在剖析声音与意义之间本就具有的天然联系,这些联系与历史演变中的各种偶然因素无关。在莱布尼茨看来,这当然也是确定语词意义的“理由”,而且在笔者看来,它们比那些出于偶然因素的理由更具约束力。
相比之下,洛克并没有做出类似的考察,而只是在《人类理解论》第三卷开篇提到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精神”一词的本意是“呼吸”。他关于任意性的观点显得有些武断,更多地与其经验论立场有关,而在词源学考察上的粗略性进一步削弱了他的论证。与此相对,莱布尼茨采取了更为温和的说法,对实际语言现象的考察更为细致,其立场也更容易得到辩护,如果他所举的那些例子所言不虚,那么我们几乎就可以宣告他的胜利了。
但在笔者看来,莱布尼茨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的词源学考察和音义学考察的效力是不一样的:前者不足以完全驳倒洛克,后者才是致命武器。结果是他在词源学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但并没有在音义学上乘胜追击,这给他的论证带来了一个潜在的缺陷:他并没有充分解释人类语言被初创时,声音与意义是否完全是出于天然的关联而被结合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尽管我们所见到的自然语言中的确包含各种非任意性,但最初的语言有可能还是被任意创造的。这种缺陷给洛克的主张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使得他有机会在关于语言初创阶段的情形下扳回一城。
在当时欧洲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倾向于把《圣经》的记载当作是真实的历史,因而所谓语言的初创阶段常常就被认为就是指亚当在伊甸园中给各种东西命名的时候。洛克在《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第六章“论实体的名称”部分也以亚当作为“思想实验”的对象,但他的目的是说明各种混合样态(mixed modes)是如何获得名称的。洛克设想,亚当出于对真实情况的误解而创造了“kinneah”(嫉妒)和“niouph”(不忠)这两个概念,他认为对亚当来说,“kinneah”和“niouph”所对应的复合观念(complex ideas)是恰当的(adequate),因为它们是由他心中的简单观念构成的;但亚当的子孙们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则必须使得它们所代表的自己心的观念契合于他人心中的观念,这就比亚当的处境困难得多。洛克的结论是,这些词的创造是亚当任意而为的,而他可以只凭借自己的思想就来制造混合样态的复合观念;更进一步地说,其他人也都具有亚当那种用任何新名称来表示任何观念的自由,只是对后来的人而言,由于已经存在一种既定的语言,他们在改动语词意义的问题上不得不更谨慎罢了。(8)See Locke,John(1975)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A. C. Fraser,Dover Publications,INC. New York,Book III Chapter VI &44-51。
亚当被选择作为案例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据洛克研究学者阿尔斯莱夫(Aarsleff)所说,当时存在一种与洛克的观点相对立的立场,即“亚当主义”,其大致主张是:有一种为亚当所创造的“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而人类的所有语言都是由此继承来的;借用洛克的术语来说,亚当具有关于事物的“真观念”,对他而言语词—观念—事物之间的契合是完美的。(9)关于对阿尔斯莱夫所谓的“亚当主义”的概括,请参阅Hacking,I.(1988)“Locke, Leibniz, Language and Hans Aarsleff”,Synthese,Vol. 75,No. 2,p. 140。关于阿尔斯莱夫自己的解释,请参阅Aarsleff,H. (1982)From Locke to Saussure: Essay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Minneapolis,p. 27,pp. 42-83;以及Aarsleff,H.(1964)“Leibniz on Locke on Language”,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 1,No. 3,pp. 179-185。“亚当主义”可能会引出与洛克观点相反的结论:由于在亚当那里有这种完美的双重契合,我们通过研究亚当创造的“第一语言”就可以知道名称所指涉的观念,进而知道观念所指涉的事物。(10)See Hacking,I.(1988)“Locke, Leibniz, Language and Hans Aarsleff”,Synthese,Vol. 75,No. 2,pp. 141-142。在阿尔斯莱夫看来,正是对这种主张的批判推动了洛克语言哲学观点的形成。
莱布尼茨也使用了类似的术语“亚当式的”(11)英文为Adamic,参阅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996)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2nd ed.),edited by P. Remnant and J. Benne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 281。,根据他的转述,这个概念曾由一位叫波墨的德国神秘主义者提出,指人类最原初最纯粹之物。(12)关于对波墨的详细介绍,请参阅《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06页注释2。这里保留了陈本对波墨名字的翻译。莱布尼茨并未简单地投向“亚当主义”的怀抱,而是坚持着更为精致的论点。他对那种“第一语言”是不是一定存在的问题存而不论,但又承认五花八门的人类语言可能是同源的,并谨慎地在我们的语言是派生的前提下探究语词的词根。可见,他小心翼翼地与洛克所批判的观点保持距离,而又巧妙地吸收了其中的合理之处,这使得洛克的论证很难命中其立场的要害之处。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充分发掘莱布尼茨所做音义学考察的意义,就可以进一步加强不利于洛克的论据,并最终驳倒他的论点。尽管洛克引入亚当案例的目的是讨论实体名称的获得,笔者却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其中的另一个方面,即亚当所做选择的任意性。对亚当而言,用“zahab”指称“金”的选择真的是“任意的”吗?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相比,亚当的处境较为独特,因为缺少其他交流者来帮助他确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恰当,一切都是由他自己说了算。(13)实际上这种假设是有问题的,我们会在第四节解释这一点。可如果他也需要依据一些“自然”的理由来选择,那么怎么还能说这是任意的呢?莱布尼茨关于声音与意义之间天然联系的例证恰恰可以证明,即使对于亚当来说,他的选择也不可能是完全任意的,而是必须遵循那些天然联系。所以,如果把莱布尼茨的音义学考察恰当地推广到语言初创的情形,洛克就真的很难有还手之力了。
上述分析使我们看到,无论就自然语言还是“第一语言”的情形来说,洛克都处于下风,但离开了必要的语言学研究,莱布尼茨也是无法彻底驳倒洛克的。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与此相似的一幕就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上演了。
三、相关争论的历史脉络
洛克与莱布尼茨并不是讨论此类问题的先行者,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中,赫摩根尼与克拉底鲁就进行过相似的争论。
对话的参与者包括赫摩根尼、克拉底鲁和苏格拉底三人,讨论的主题是名称的正确性。简言之,赫摩根尼持一种约定论立场,认为名称正确性没有除了约定俗成和人的一致同意之外的原则。(14)参阅柏拉图:《克拉底鲁篇》,载于《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384D。本文中只给出柏拉图原著的页码编号,以下不再一一赘述。克拉底鲁的立场较为独特,他除了认为名称是出于自然的之外,还认为名称永远正确而不会出错(15)柏拉图:《克拉底鲁篇》,载于《柏拉图全集》第二卷,429B,430E。。苏格拉底给出的“裁定”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部分赞成克拉底鲁的立场,认为名称并非完全出于约定,而是由少数“立法家”在“辩证法家”的指导下依据事物的本质所确定的。另一方面,他部分赞同赫摩根尼的立场,即认为命名术有好坏之分,名称是可错的,而“习俗和约定对表达我们的思想有贡献”(16)柏拉图:《克拉底鲁篇》,载于《柏拉图全集》第二卷,435B。。三人立场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既有相互交织的部分,又暗含着各种分歧,体现了当时“习俗”与“自然”之间的对立。(17)参阅宋继杰:《柏拉图〈 克拉底鲁篇〉中的“人为—自然”之辩》,《世界哲学》2014年第6期。由于《克拉底鲁篇》内容丰富且研究的文献非常多,在此只能做出十分简略的概述。关于该著作中的相关问题及其在语言哲学等方面的影响,笔者会另做专文加以讨论。
除了上述裁定外,苏格拉底还详尽地考察了各种希腊语词汇的源流,并且谈到了某些声音会固定地与某些意义相关联,比如字母“ρ”的发音需要最大限度地活动舌头,因而常被用来表示各种运动,字母“λ”因为发音时舌头的滑动而被用来表示平滑性,“ν”则因为发音出自后腭而被用来表示在内部(18)柏拉图:《克拉底鲁篇》,载于《柏拉图全集》第二卷,426C-427C。。这些分析与莱布尼茨的音义学考察惊人的相似,使得洛克与莱布尼茨的争论看上去像是赫摩根尼与克拉底鲁争论的翻版。但需要注意的是,莱布尼茨的立场更接近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非克拉底鲁,洛克的立场更接近赫摩根尼,而在两人那里很难找到严格意义上的克拉底鲁思想的回声。
在历史上,试图解答类似问题的人远不止上述这些。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类似的探讨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语言学的领域内。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索绪尔同样谈到了语言中存在的任意性,不过他说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发明的术语,简单地说,它们分别指音响形象和概念,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组成语言符号。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关键主张在于:“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页,黑体文字为原书中加着重号的文字。可见,洛克与莱布尼茨的争论并不只是两人诸多论争中的一段小插曲,而是一部更宏大的交响乐中的精彩乐章。(20)一些学者已经梳理了语言任意性问题在历史中的脉络。如Joseph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完整地分析了从《克拉底鲁篇》到近代语言学研究中的相关讨论,参阅Joseph,J. E.(2000)Limiting the Arbitrary:Linguistic Naturalism and Its Opposites in Plato’s Cratylus and Modern Theories of Language,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类似的梳理还见于Magnus关于语言学的博士论文What’s in a Word?: Studies in Phonosemantics的第二章“Overview of the Phonosemantics Literature”;参阅Magnus,M. (2001)What’s in a Word?: Studies in Phonosemantics,Dissertation,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此外,还有很多哲学家多多少少涉猎过类似问题,比如霍布斯和贝克莱,请参阅Ott,W. R.(2004)Locke’s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 13,pp. 121-124。出于篇幅和话题相关性的考虑,本文不做更多讨论。
从上述历史脉络可以看出,在相关的问题上的立场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种:第一种可以被概括为“克拉底鲁—亚当”传统(21)“Cratylic-Adamic tradition”,see Dawson,H. (2007)Locke, Language and Early-Modern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 151,p. 160。,支持者包括柏拉图笔下的克拉底鲁以及莱布尼茨提及的波墨,他们认为语词出于自然而非约定;第二种立场可以被称为一种“名称约定主义”(22)“Name-conventionalism”,see Hacking,I. (1988)“Locke, Leibniz, Language and Hans Aarsleff”,Synthese,Vol. 75,No. 2,p. 142。,支持者包括赫摩根尼、洛克和索绪尔,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语言符号由社会的约定俗成决定;第三种立场介于前两种之间,苏格拉底是其典型代表,他认为语词中同时包含出于自然的部分和出于约定的部分,这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更为精致的“本质—自然主义”(23)参阅宋继杰:《命名作为一种技术——柏拉图名称理论的形而上学维度》,《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我们也可以将莱布尼茨划归到这种立场之下,毕竟他的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思路都与苏格拉底十分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讨论几乎都是在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中进行的,在默认条件下语词自然就被等同于声音。而这样一来,语词任意性的问题实际上已被转化为声音与意义的结合是否是任意的问题,这属于第一节中所说的音义学的范畴。《克拉底鲁篇》中的苏格拉底和《人类理智新论》中的莱布尼茨实际上都是在做关于音义学的初步探究,而如第二节所指出的那样,一旦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天然联系被确证,赫摩根尼、洛克和索绪尔这个阵营的论点就摇摇欲坠了。
不过洛克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在《人类理解论》中,他同样明确表示自己关注的就是声音和观念之间的任意性,他说:
既然声音与我们的观念之间并没有自然的关联,而它们的意义都是由人们的任意强制(arbitrary imposition)而来的,那么它们意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在此所讨论的那种瑕疵——就更多的是源于它们所代表的观念,而非源于一个声音相较于另一个声音的在指示任何观念上的无能(incapacity):就此而言,声音都是同样完美的。
作为声音,语词不能在我们心中产生除了那些声音之外的简单观念;而除非声音和声音常被用于的简单观念之间的自发关联,已经使得它们成了那些观念的符号,否则也不能激起我们心中的任何观念。(24)Locke,John(1975)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A. C. Fraser,Dover Publications,INC. New York,Book III Chapter IV &11,Chapter IX &4。
虽然我们可以赞同洛克所说,单纯作为声音的语词的确不能激起人心中的观念,但“声音都是同样完美的”的说法显然存在问题。我们首先会想到拟声词(onomatopoeia)这样较为特殊的词项作为反例。比如在汉语里我们用“喵”来模仿猫的叫声,用“咩”来模仿羊的叫声,其他声音显然并不同样胜任这样的角色,不可能“是同样完美的”。当然,这毕竟只是语词中的特例。与这种简单的反例相比,无论是词源学的考察还是音义学的考察,都可以给出更为精致的例证。比如莱布尼茨所说的R与L在表示运动上的差异的例子,显然是洛克的立场无法解释的。这进一步扩大了莱布尼茨阵营的优势,使得与洛克持相同立场的人面临更多的困难,比如索绪尔,而他的理论的确已经遭到了来自语言学内部的众多质疑。(25)这些质疑涉及的内容广泛,请参阅Magnus的博士论文,我们在此不便展开更多的论述。就目前的情况看,在上述三种立场的相互对垒中,苏格拉底和莱布尼茨是胜出的一方。
不过,这些人物所说“任意性”的含义还是略有不同的:在《克拉底鲁篇》中,任意性存在于名称的正确性之中;在洛克与莱布尼茨的讨论中,任意性存在于作为声音的语词和语词所代表的观念之间;而在索绪尔那里,任意性存在于音响符号和概念之间,两者都是心理上的事项。这三种不同的“任意性”的确很相似,但澄清其间的差异还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并更清晰地看到相关问题演变的历史。这些对历史的梳理也显示,关于语词是否在本质上是一种任意性选择的讨论,从古希腊一直持续到现代。它最初以《克拉底鲁篇》中的样貌呈现,到近代语言学诞生后发展为关于声音与意义之间天然联系的研究,而洛克与莱布尼茨的争论正是这长长的历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从古希腊时期的讨论框架向近代讨论范式的演变。
四、关于任意性的辨析
尽管莱布尼茨阵营的立场似乎更为合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观点无懈可击。由于没有充分发掘音义学考察的意义,洛克在“第一语言”的案例中还保有一线生机。实际上,在双方的论证中还隐含着更深刻的共同的缺陷。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第二章中所谓的“自发的强制”的主体究竟是谁,其实是不清楚的,他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动作的主体都是个人。可一个人不可能既“自发”又“强制”地让自己去做一件事件,换言之,“强制”肯定要发生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对于单独的个人来说无所谓强制与否。因此,他在设想个人创造语言的同时又不经意地把他人引进来了。与此相似,莱布尼茨似乎也默认已知语言如同人造语言一样可以由某个个人创造出来。可是,他列举的很多语词在创造和演变中得以成立的理由,也预设了他人的存在,比如不管是谁对一个语词的词义加以引申,都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更准确地说是得到共同体的认可。无论洛克还是莱布尼茨,在设想个人创造语言的同时又都无意间预设了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因为无论“强制”还是理由都在共同体中才得以成立。
由此可见,自然语言可以由个人创造这个假定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的。自然语言真的是由个人创造,然后再由其他人参与改造而形成的吗?这个问句的后半段是正确的,前半段则不然。创造语言、提出理由都必须确定标准,但标准本身并不是属于个体层面的事项,它的存在总是要求共同体的存在。比如洛克说亚当关于语词的标准是由他自己确定的(26)See Locke,John(1975)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A. C. Fraser,Dover Publications,INC. New York,Book III Chapter VI &46。,可一个人自己确定标准自己遵守,这其实就是没有标准,而真正的标准只能存在于共同体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做出共同体与个体这两个层面的区分。
在我们的经验中,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存在于共同体之中的,他的一切合理行为实际上都以对语言的学习掌握为基础。在这种意义上,共同体是“先于”个人的。因此,在自然语言中,语词选择的“任意性”其实是对共同体而言的,个人并没有这种选择的权力,尽管他可以在接受自然语言的基础上自主地做出一些“微调”。这正如索绪尔所说:“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27)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6页。人造语言的创造者似乎是个例外,但他其实也已经是一个共同体之中的人,充分掌握了自然语言以作为创造的基础,莱布尼茨和他所提及的达尔格奴斯、威尔金都是这样的人。总之,在我们的经验中不存在亚当这样“先于”共同体存在的个人,而且假定这样的个人的存在必定会引起各种困境。因此,创造的语言的主体只能是共同体。尽管关于语词任意性的争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做出共同体和个体两个层面的区分显然有助于我们更恰当地理解语言。
一旦接受了这种区分,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洛克和莱布尼茨的争论。两人所说的“任意性”只能是对共同体而言的任意性,对个体而言不存在这种任意性;他们在很多时候把共同体层面的“任意性”替换成了个人层面的“任意性”,结果引起了不必要的混乱。比如洛克在总体上误以为个体可以具有共同体的那种任意性,所以得出结论说大家都可以像亚当那样随意地选择语词。可实际上,亚当不过是人类共同体的一种“化身”而已。共同体本就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每个共同体都可以任意地选择语词(声音)来标记意义,这也就可以解释洛克在自己立场出发点提出的质疑,即世上的语言为什么并不是只有一种。莱布尼茨和苏格拉底似乎也默认语词的演变是出于个人(比如“辩证法家”)的选择,这其实仍旧是共同体的别称或“人格化”。可见,恰当地区分共同与个体,可以帮助这些思想家把各自理论中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剔除掉。
在当今语言哲学的讨论中,共同体与个体两个层面的区分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述。比如在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遵守规则”问题中,关于规则是否被遵守的标准最终是要诉诸共同体的,个体无法提供这种标准。笔者在此并不是要苛求古代和近代哲学家去构想出在当代才出现的区分,而是意图表明,在那时的讨论框架下,大家的观点其实都是不够完备的。
关于这场争论最后的“裁定”,笔者的意见是:从总体上来看,莱布尼茨的看法更为合理,但双方的观点都需要做出修正。结合之前的讨论,我们可以提出如下更为合理的说法:个人无法任意地选择语词,甚至对于共同体来说这种选择也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存在着各种有偶然性掺杂其中的理由,其中就包括声音与意义的天然联系,这一点也已经被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所证实。(28)例如,在What’s in a Word ?: Studies in Phonosemantics的摘要(Abstract)部分作者总结道:“音义间的关联(phonosemantic correlations)比我最初预期的要广泛得多……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关联的一般性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s)在语言中是极为有效的……符号并不是完全任意的,我们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完全与语言自身形式无关的关于该语言的抽象的表现”(Magnus,M. (2001)What’s in a Word?: Studies in Phonosemantics,Dissertation,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尽管音义间的关联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就目前的成果来看,人们已经很难否认这些关联的广泛存在。更进一步地说,语词(或者说声音、符号)与意义的结合,既包括出于任意的部分,也包括出于自然的部分;那些出于自然的部分体现了人类所具有的某种共性,可以为我们更充分地理解语言的本质提供必要的基础。
莱布尼茨完成针对《人类理智论》的《人类理智新论》之后不久,就得知了洛克去世的消息,因此不愿发表书稿。这本书的正式出版已经是莱布尼茨也去世后五十年的事情了。两位哲人在生前并未进行过真正的论辩,尽管洛克曾读过一些莱布尼茨所写的针对自己著作的评论,却并未有过任何回应。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位英国人最终会如何反驳来自欧陆学者的质疑,以及他是否会接受笔者做出的“裁定”(当然他很可能对此更是不屑一顾)。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肯定会继续散发生命力,因为其中还有很多谜团尚未解开。比如,仅仅依靠声音与意义间的天然联系就可以创造出语言吗?这种联系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我们语言的样貌?既然语词与意义的结合中包含任意的部分,那么人们(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就这些部分达成一致?这些谜团包含着哲学的因素,但也离不开语言学的考察,对它们的进一步解答需要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交汇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