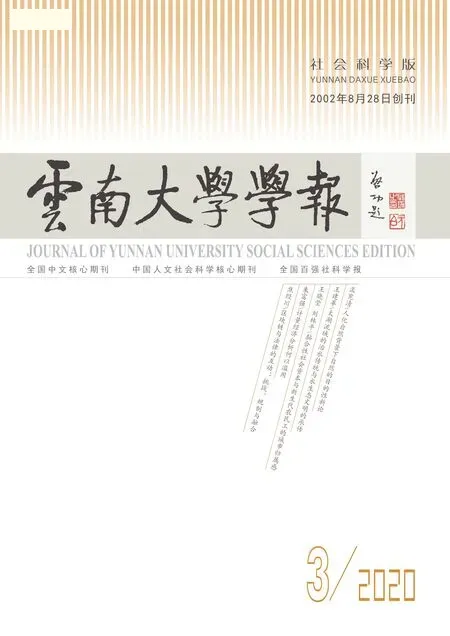环境史研究的 “在地化”表达与 “乡土” 逻辑
——基于田野口述的几点思考
耿 金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环境史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环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互动关系的探讨难度也在升级。对于当前环境史的发展走向,有学者提议应该进入微观层面,倡导环境史研究要关注具体时段中的事件形成、发展、演变过程。(1)参见赵九洲、马斗成:《深入细部:中国微观环境史研究论纲》,《史林》2017年第4期。环境史属于历史学分支,基本的研究方法仍旧是文献解读法。但传统文献经常在许多微观的环境史研究中“缺位”,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取从事精细环境史研究的替代材料。即当前的环境研究史,不仅要充分解读已有文献还需要走入田野,到基层挖掘环境变迁背后的深层逻辑,以深入到更细致层面,而田野调查是环境史研究者获取这种“环境感”的必要方式与手段,也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而走进田野就要与当地人群触,这不仅可以挖掘民间丰富的环境信息,还能感知本地人群在环境演变中的细微变化。这里的“人”区别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中的“人”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体人群。口述访谈是田野调查中经常使用的资料搜集方法。历史学领域已有比较成体系的口述史,区别于依赖传统文献资料为主的史学研究,口述史通过口头叙述或依靠口头叙述材料来展示历史。(2)朱志敏:《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目前对口述史的缘起、定义,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关系,以及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价值、局限等内容,已有众多学者展开了系统探讨与分析,(3)参见杨祥银:《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曹辛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并倡导建立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4)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相比传统史学,虽然口述史在许多方面仍处于摸索阶段,但已有成果不可谓不多。尽管如此,口述史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物或人群历史的追溯,而对于环境变迁及对当地人群影响的关注仍然不够。笔者认为,口述访谈作为从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或许还可以借此延伸出口述环境史的概念。目前学界对口述环境史的内涵与外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认知,从字面上看,可能会形成两种直观认识:或将其视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阶段,与基于传统文献开展的环境史并列;或将其视为环境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与新路径。笔者虽然也认为口述环境史与传统文献基础上的环境史研究有所区别,但更愿意将其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一种手段和路径。如果仅将其视为方法论,则这方面的成果已多有展现。(5)如周琼在对历史时期瘴气演变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田野调查中,通过对当地老人口述访谈的形式揭示瘴气的存在以及消亡过程(参见周琼:《寻找瘴气之路(上),《中国人文田野》第一期,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寻找瘴气之路》(下),《中国人文田野》第二期,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此外,张玉洁基于环渤海渔民口述访谈而开展的海洋环境变迁研究(《海洋环境变迁的主观感受——环渤海20位渔民口述史》,中国海洋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郑玉珍以口述史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渤海海洋环境变迁状况(《捕捞渔民对海洋环境变迁的主观感受——青岛市S区渔民口述史》,《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3期)等,都是有益的探讨。而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中,也有学者借助口述史方法复原古建筑周边的“环境”(如蒲仪军:《陕西伊斯兰建筑鹿龄寺及周边环境再生研究——从口述史开始》,《华中建筑》2013年第5期)。除此之外,对田野、口述对于环境史研究的价值还可以进行更系统的思考,笔者不揣浅陋,结合在云南大理洱海北部弥苴河下游所进行的田野调查,通过访谈本地人群,从“乡土”(走入基层)视角来看区域环境变迁的内在逻辑,乞请方家指正。
一、地理感知:环境变迁“在地化”与口述表达
地理感知(Geographic perception)是人群对外界地理环境在感觉上的反应。要讲地理感知,首先要确定感知来自于谁,是外来客体的还是本地人群的。环境变迁有外来者的观察感受,也有本地人的细微认知。但外来者的观察更多是一种置身世外的旁观视角,而本地人群的感知则是基于切身参与的经验视角。从探究环境变迁的角度看,要深入细部、探知区域环境变迁的内在逻辑与生态链条,就必须挖掘本地人群的环境感知,而这种感知是需要长期在此居住、生活才能形成的,笔者将其称之为“在地化”。(6)段义孚对外来者与本地人对环境与空间的认知差异有系统论述,他将人群对居住空间与环境的自我认同与感知过程,以及因人对空间赋予情感属性而变成了“地方”,从而具有的情感称之为“恋地情结”,也有本地人群“在地化”感知当地环境的内涵在其中。(段义孚著,志承、刘苏译:《恋地情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这种当地人群的环境认知,可以借助口述访谈来获取,可称之为“在地化”表达。
明确了本地人群作为感知主体后,还需要确定人群的空间尺度。环境史研究的核心是围绕人而形成的周边环境变迁轨迹,而人的单位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因此,研究环境史首先需要明确环境核心“人”的尺度与范围。就群体而言,可以是以区域为单位(省市县等)形成的地区人,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国别人,以及以地球为单位的地球人。对于区域环境史、国别环境史以及全球环境史研究,更多是用大尺度、大范围、粗精度的环境变迁史料。对小尺度空间的环境史研究,史料本身的缺乏需要走入田野,通过田野调查来弥补。以田野口述方法开展的环境史研究,可以是围绕某一个人开展的个体环境感知研究,也可以是基于一个聚落群体与环境互动过程的研究,这种研究在精度上比前者要高很多,就空间尺度上说,属于“小尺度”的微观研究。这种微观研究,既能呈现出区域环境变迁轨迹,更能让当地人群实现自身对环境认知的表达。
田野调查及口述访谈,可以呈现当地人群对本地环境演变背后的细微地理感知,这种感知需要熟悉当地的水土环境、气候波动及微地貌变化知识,这往往是外来者很难轻易获取的。而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可以很好地弥补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的不足。但当地人群对本地的环境感知大多停留在本地生活场域之中,本地人要实现其环境感知的表达,仍需要研究人员的现场参与。而且现场口述访谈,对研究人员和被访谈者也都十分重要。首先,研究者需要在与当地人的访谈过程中体会当地人的环境认知;其次,访谈对象也需要在特定环境场域内,才能准确表达环境变迁的历史信息。特别是对于后者,要求访谈活动最好是“在地化”进行,更换访谈地点可能会直接影响访谈信息的准确性。
“在地化”感知首先体现在地貌空间与当地环境互动关系上,即地理感知与环境变迁之内在细微关系。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基于对云南大理洱海流域北部的田野调查,主要考察洱海北部主要水源河道弥苴河下游(8)本文的弥苴河调研集中在下游河道,大致从今上关镇镇政府所在地至河流入洱海口段。生态演变与人群生计的互动历史。研究者本身也是外来者,要获得当地环境的信息,最直接方式仍是文本、数据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可以帮助自己形成对调查研究对象(时空)的认知框架。文本材料对研究区域的介绍大致可以归纳为:
弥苴河是洱海最主要的补给水源,上游有两条南北流向相反的弥茨河与凤羽河,在茈碧湖出水三江口处汇合,此后进入下山口段后称为弥苴河。从上游支流北源的弥茨河发源地至弥苴河入洱海口,全长71.08公里,高差达1215.53米,河流比降较大。弥苴河在下山口以下为弥苴河主干,全长22.28公里,河床在泥沙淤积过程中不断抬升、延长。(9)洱源县水利电力局编:《洱源县河湖专志集》,1995年,第93-97页。弥苴河下游在历史时期经常因河道溃决而泛滥成灾,因此也有“小黄河”之称。(10)对于历史时期弥苴河流域水患灾害情况,可参阅杨煜达:《中小流域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清代云南弥苴河流域水患考述》,载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53页。另一方面,下游在当地也有“鱼米之乡”美誉,文献称“享渔沟之饶,据淤田之利”。“渔沟”成了当地最为重要的生计场所,渔沟中有大量鱼类生长繁衍,其中以“弓鱼”(11)又名大理裂腹鱼(学名:Schizothorax taliensis Regan),属鲤科裂腹鱼亚科,裂腹鱼属,喜欢生活在静水环境的中上层,食物以浮游生物为主。产卵时要求流水环境,每年4-5月繁殖季节溯水上游到沙砾河床的河流或湖底地下水出口处产卵。卵需在流水中孵化,当地渔民利用弓鱼溯河产卵的习性,在河口设竹箔拦捕。在历史文献中,“弓鱼”又称“公鱼”“工鱼”,对于名称考辨,请参阅方国瑜《大理工鱼》,载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0-423页。产量最多。围绕着“渔沟”中的弓鱼捕获,当地形成了丰富的人群与环境互动关系史。20世纪70年代末,弓鱼逐渐灭绝,当地渔沟生境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渔沟”是当地人群适应、改造弥苴河水文环境的产物。弥苴河下游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升,明清时期在主干河道上设闸分流,以保障下游河道不溃决。在常年的泄水过程中,从西闸河至河尾长5.9公里的下游地段先后开辟了排灌兼用、农渔结合、年产弓鱼21.5万斤的渔沟18条,呈扫帚状从弥苴河两侧的江尾三角洲散向洱海分散水流。(12)洱源县水利电力局编:《洱源县河湖专志集》,1995年,第109页。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18条渔沟兼具泄水、灌溉功能,之所以冠以“渔沟”之名,主要是因为这些沟渠中有大量鱼类分布,其中以洄游性的弓鱼为主。20世纪70年代后期弓鱼逐渐灭绝后,渔沟也变为单一的排水、灌溉沟渠,并不断被侵占而失去原本面貌。笔者在当地调查过程中,即期望从当地人的认知中获得“弓鱼”消失的生态逻辑,以及伴随着这种生境变化而引起当地民众生计变化的过程。
文献资料的记载在当地田野过程中仍可验证,外来者却缺乏对“渔沟”分布空间与当地环境内在联系的细微认知,即对笔者而言,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渔沟为什么只分布在清索以下的弥苴河两岸?该问题看似简单,其实隐含了丰富的乡土知识与地理信息。走访中,大多数人的回答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渔沟一直只在这片区域有分布。这种回答看似无效,实则折射出渔沟形成背后反映的人对环境的塑造与适应过程,是该区域历代先人对当地环境感知及对改造环境限度认知的知识累积。渔沟开掘与弥苴河河床高度、沿岸农田及河水高差等因素有关,对这种细微变化的把握,是建立在当地人对区域微地貌感知基础上的。
对于历史上18条渔沟的名称,稍微年轻一点的本地人很少有了解,但上了年纪的老人对渔沟的分布与历史,渔沟中的“弓鱼”生境如数家珍,而这种历史时期特定空间范围内的环境感知,只能通过对经历者的访谈获取。但这种访谈复原方式也存在缺陷,即记忆与认知的时间尺度不长,溯源性问题还是需要文献史料支撑。咸丰年间的《邓川州志》中记载了当时的渔沟名称与分布情况,并记载了渔沟的一些基本信息:“鱼有工鱼,又惟工鱼为多……产洱海中。渔者就弥苴河傍海处开沟通水,曰鱼沟。”(13)咸丰《邓川州志》卷四《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第43页。弥苴河西岸从上至下分别有西闸渔沟、上江尾沟、土官渔沟、大排渔沟、张家渔沟、李家渔沟、徐家渔沟、苏家渔沟、吴家渔沟、李家渔沟、王家渔沟、小沟;东岸有东河口沟、李家渔沟(两条)、小沟(三条)。(14)咸丰《邓川州志》卷首《河工图》,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第9-15页。总共18条渔沟。笔者在当地也核实了渔沟的名称,与文献记载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有部分沟渠的名称稍有差别。渔沟本身具有地理空间属性,某条渔沟对应与弥苴河主干河道的空间关系,以及围绕渔沟而形成的聚落空间结构乃至地域人群的社会关系等。此外,渔沟在传统时期有产权属性,当地家族在本地形成的时空过程也隐藏在渔沟的名称中。因此,理解区域环境变迁需要对构成环境各种要素间的耦合与分离关系有清晰把握,而这种把握就来自于当地人群的地理感知。
当地人群有对本地环境感知的本能,但如何引导访谈对象将这种细微的感知表述出来,却考验着研究人员的访谈技巧、信息鉴别、归纳综合等素质。此外,如何在基于口述环境变迁的大背景下抓住细节,并保证细节变化的准确、客观,这也是从事环境口述访谈经常会碰到的问题。笔者在洱海北部区域对渔沟中弓鱼生命史的访谈中,时有发现口述资料与传统文献记载有出入,如何判别二者对错,似乎成为棘手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是研究过程可重复与结论可验证。但历史时期环境变迁后,外在环境、人群结构都无法复原。如何界定口述者的描述是真实客观的,是一大难题。当然,扩大口述访谈人群范围,通过互证可以作为一个途径。但对具体的区域环境变迁问题,并非所有人群都会关心,或因与访谈对象无直接关系,即使访谈对象与要研究的环境问题在同一个时间断面,其也不一定了解真实情况;其次,在小生境研究中,口述访谈难免会出现因最佳访谈对象的离世而造成某种知识的彻底缺失,而这直接影响着研究者对当地环境演变的细微感知与把握。
口述访谈中同一聚落人群对同一环境问题的感知程度也是有差别的,在对弓鱼的调查过程中,历史时期临近渔沟的人群对弓鱼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楚;而原本远离渔沟、传统时代主要以农耕为生的农户,对弓鱼的消亡过程就不是十分敏感。
二、地方经验:乡土知识中的环境逻辑
环境史研究中的田野口述方法,可以最大限度挖掘基层人群的乡土知识,这种知识是当地人群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地方经验(local experience)。管彦波、李凤林指出:“乡土知识是各民族在长期生存与生活实践中,围绕着与生境资源的关系而构建的一种比较完备的环境认知体系,其本身是一种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论。”(15)管彦波、李风林:《西南民族乡土传统中的水生态知识》,《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73页。从技术层面上看,乡土知识大多是通过口传方式或身教的方式展现,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施加影响。这种乡土知识是特定人群对周围小环境的认知,是当地人群长久积累的集体经验,具有潜在的生态价值。
笔者在洱海北部的田野调查中关注弓鱼的消失过程,并试图探讨其对当地百姓生计带来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弓鱼就已基本灭绝,在当地的走访中,1960年后出生者已经很少见过大量弓鱼,1950年后出生者有不少人能描述一部分弓鱼的生长情况,而主要的经历者以1940年后人群为主。随着这些见证者的逐渐逝去,对历史时期弓鱼生境的认知及渔沟这种具有复合生态价值的历史遗迹,也随着新环境对人群的塑造与影响而消失。对于弓鱼消失的原因,有些文章中提到与银鱼引进有关。但从对当地20世纪90年代最先开始捕银鱼的村民的访谈中,笔者理清了弓鱼与银鱼之间的逻辑关系:“当时(80年代)洱海还有一些本土高产的鱼类,但由于产量减少了很多。到1990年以后开始从外地引进银鱼,后来就开始自己繁殖,没有往洱海里投放。银鱼的繁殖能力很强,到1991年我就开始捕捞银鱼了。这种鱼当时老百姓不叫银鱼,叫玻璃鱼,这种称呼在当地那个时间段的渔民都知道。银鱼含高蛋白,到一定季节就自然死亡,死亡后沉入水底,腐烂后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越干净的地方银鱼越多,整个洱海里的数量非常多。银鱼捕捞要晚上见光才能捕到,捕鱼船上要有照明灯,鱼会跟着灯光走,于是就很容易打捞到。银鱼成熟时最长也就7~8厘米,不会更大了。用我们本地人的说法,一条银鱼的营养价值顶两个鸡蛋。”(16)受访者DZF,1965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从事打鱼行业。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该受访者是第一批开始在洱海里打银鱼的渔民,据其所称,洱海里引进银鱼是在1990年左右,此时弓鱼早已灭绝,因此弓鱼与银鱼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弓鱼最终灭绝可能与其他物种的引进有关:“弓鱼的消亡,可能还跟弥苴河中的虾、小花鱼繁殖有关。弓鱼产卵在沙地、沙滩上,小虾、小鱼就把鱼子吃掉了。这些虾和小花鱼都是外来物种。”(17)据DZW口述。DZW,1944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洱海出水河道西洱河上建起多座水电站,应该是导致弓鱼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70年代后期弥苴河下游还有弓鱼,但是数量已经比较少了,为了弥补弓鱼减少对当地生计造成的冲击,于是从外地引来了一些鱼虾,可能最终导致弓鱼的消失。
此外,一些乡土现象一般很少进入文本材料中,而通过口述访谈获得的这些信息却是极佳的研究素材。渔沟形成之初是为分泄弥苴河主干河道的洪水,并灌溉农田,鱼类资源为其附属产物,因此渔沟排水不畅就会出现下游河道溃决、淹没农田的现象。当地人提及,在上下游河道工程系统整治前,弥苴河下游沿岸的农田在水稻收割季节经常出现江水漫灌现象:“过去经常会有撑船割稻谷,原因是部分年份洱海水位高,或田相对较低,缺少排涝沟渠。水稻成熟期过了不收割,会发芽,一定要抢收,即使是农田里积有大片的水,也要收割。在本地,水稻的秸秆用来喂牛。如果水稻被淹的时间过长,秸秆就不能再用于喂牛。”这种由于渔沟排水不畅而形成的灾害生态及农民的应对措施,很少在传统文献中出现。此外,当地对于田间的排涝沟渠也有专门的名称,蕴含着生动的生态知识与环境信息:“水沟在本地有几种名称,取水口在弥苴河的为渔沟,在田间排水的沟渠称排涝沟,本地人称黑泥沟,因常年淤积,土质成黑色。”(18)ZBS主讲,DZW补充说明。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ZBS,1968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在上关镇从事水务管理工作。当地还有一种引水沟渠,称龙洞,民国时期陆鼎恒在当地调查中记载了这种水利设施:“还有若干由湖滨向内开的半截沟,并不通到弥苴河,则名叫龙洞,以捕杂类小鱼。”(19)陆鼎恒:《洱海的工鱼》,《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这里“龙洞”与“渔沟”并列,渔沟与弥苴河相通,而龙洞则只与洱海相通。在走访过程中,村民带笔者查勘了各种龙洞,然而现存的龙洞却与弥苴河直接相通,与清至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有极大差别,其作用主要是将水引进村子,并进入农田。现在龙洞引水口很窄,靠钢制的水闸控制水流,在干旱少水时节,则要依靠水泵提水引入龙洞。相比于渔沟的退出,龙洞在当地仍在发挥着作用。这些基层生态的细微转变过程以及其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不断搜集、整理,这不仅是出于本体研究的需要,也是为以后从事相关研究保存史料。
三、口述史料中的技术与环境
环境史研究首先应该关注人是如何生存的。从本质上说,人如何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史的问题。环境史研究为何要强调技术的作用?技术史虽研究技术自身的演变过程,但技术本身的形成与演化离不开外在环境。一般而言,人是在理性引导下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故而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20)杨耕:《“人的问题”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而实践反馈回的环境信息也直接影响着区域人群的环境认知。
首先,技术(technology)依赖于环境存在,也是环境得以维系、平衡或失衡的重要因素。环境是技术产生的基础,它影响技术的形成与演变,而技术也在每一次的改进中影响着环境。
历史时期弥苴河下游捕鱼技术并不复杂,只在渔沟中设置“鱼坝”即可轻松捕获大量弓鱼。对于鱼坝结构与捕鱼技术,咸丰《邓川州志》中有简单的记载:“沟中就埂脚织竹,如立栅,曰鱼坝。栅斜开向上,就对岸为口,曰坝口。凡鱼性逆水行,河水由沟入海,海鱼衔尾入沟。触栅,栅水喷沫,鱼愈跳泼,循栅进,既入口,渔者以网作兜盛之,白挺跳泼如梭织,尽昼夜所获,莫可思议。”(21)咸丰《邓川州志》卷四《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第43页。这种在渔沟中设竹栅的捕鱼方式到民国陆恒鼎考察时依旧如此,陆对鱼坝的记载也更为细致,其言:“二十八年(1939)十一月,我在大理一带考察洱海附近的生物状况,就听见大理县建设局长张勉之君对我谈到下江尾的捕工鱼业。他说鱼坝上支板架茅为屋,以供渔人居处,屋旁就是鱼窝,随时以网捕捞取之。所以渔人可以长袍马褂,衣履不湿,一夜千余斤,真算是奇观了。及至一月十八日我离开邓川时,承该县建设局长杨应侯君亲伴送至下江尾来看工鱼坝,方得细视他的构造。”“每一鱼沟只能建鱼坝一个,因为他(它)把整个的河身截断,几乎没有一条鱼可以穿过,所以不能有第二个坝。每个坝全用竹子编成立栅,其密度足以阻止工鱼的通过,然后树栅于沟中,先在下流横截全沟之半,然后在沟的中央纵行而上,分沟为左右二部,此段长约二三丈。最后在向着上流的一端,用竹栅横行封闭,恰好亦当沟宽之半。在纵行栅之近上流端处,另以小栅二栽成八字形口,尖顶正对坝底,即是向着上流的一端。竹栅用粗木横固定于岸上,即藉着横木为下架,在上面建一个茅屋,以为渔人食卧之所;茅屋门向着上游,门前用木板搭一平台,其下正当着坝的上流末端,亦即是鱼窝之所在。”(22)陆鼎恒:《洱海的工鱼》,《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对于这种立竹栅于渔沟中,并在渔沟之上搭建茅屋以方便捕鱼的鱼坝设施,尽管陆恒鼎的描述已经十分清楚,但笔者仍无法完全构想出鱼坝的真实面貌。所幸的是,笔者在当地水利文献中发现了一张20世纪60年代的“鱼坝”照片,与陆鼎恒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鱼坝的立体感才随之形成。
其次,当环境发生改变后,依赖于环境而存在的技术(包括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也将发生变革。因此,在环境演变过程中消失了的技术就需要回到田野中去找回,与亲身经历者进行口述访谈无疑就是最有效而直接的手段。
传统时期的鱼坝技术在当地维持到什么时候?为何消失?据当地人回忆,鱼坝捕鱼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消失,渔沟也在90年代后被农地侵占:“鱼坝一般扎在河道的入海口处。设一道鱼坝,在鱼坝上面可以搭一个窝铺睡觉。以前渔沟入洱海处的宽度大致在6~7米,鱼坝用细的毛竹编成,宽度与河道相同。细毛竹一则好用,二则由于质地坚硬,比较耐腐烂。鱼坝做好后,一次可以用2~3年。鱼坝高度在2米左右,用草绳编成网格状,有一定的缝隙,可以漏水。在鱼坝上游还有一道小的拦水坝,一般是土坝,土坝有放水设施,打开一个缺口,可以人为控制。要捕鱼的时候就将土坝堵住,当土坝与鱼坝之间的水位下降,即可捕鱼。土坝与鱼坝之间长30~40米,渔沟宽6~7米。鱼坝在80年代还有,90年代基本就没有了。70年代末弓鱼逐渐灭绝后,鱼坝里的鱼还有一点鲫鱼、鲤鱼、草鱼。90年代以后渔沟里就基本没有捕鱼的了,一则这种捕鱼方式落后,当时在洱海里发展了网箱养鱼;二则渔沟里的鱼逐渐变少了以后,弥苴河中上游的整体调蓄水能力不断提升,以前依靠渔沟泄洪水的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于是,渔沟在本地农户的不断侵占下越变越窄。”(23)DZW主讲,ZBS补充说明。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鱼坝、渔沟、弓鱼三者形成完整的生态链条,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断裂,整个生态链也将不复存在。随着弓鱼的减少,渔沟与鱼坝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鱼坝从技术层面上看并不复杂,但却在当地维持了数百年。可见,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下来。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发展并不一定要追求技术的革新速度,而是要努力让技术与所依赖的环境形成良性共生。从当地鱼坝捕鱼技术的发展演变看,技术简单正反映了当地弓鱼生境的稳定与和谐。据访谈者陈述,在弓鱼多的时候,渔户坐在船上顺手就可以捞起鱼来。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虽未及查证,但也能大致反映出当时本地鱼类资源之丰富。这种鱼类资源与简单技术之间的关系维持了数百年(或许更长)的平衡,但却在近几十年被彻底打破。
对于弓鱼的消失与灭绝,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南鱼类志》解释为:“近年来由于洱海引入外来种与大理裂腹鱼之间的竞争剧烈,同时由于山溪小河筑堰引水,大部分产卵场遭到破坏,致使大理裂腹鱼数量大减,现已极少见,成为濒危种。大理裂腹鱼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若能控制外来种,改善环境,同时积极进行驯养,则不但可保住珍稀物种,而且可望逐渐恢复它的数量。”(24)褚新洛等编著:《云南鱼类志》(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7页。该书对于下游西洱河电站设置并未提及。而在当地的走访中,多数人提到弓鱼消失与在洱海出水河(西洱河)上建电站有关。虽说如此,这中间的关联度是怎样的,应该需要有科学的数据支持与相关指数分析。历史研究要有探知真理的信念,但不可轻易对科学问题给出结论。对于技术与环境关系的解释分析,要警惕口述访谈中被访谈者的“科学”归纳,而应该更多关注访谈对象对历史事实的细节陈述,并多方考证比对。
四、余 论
环境史需要关注特定区域内人群的生活场域,这种历史场域的“复原”,要对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的生计方式、民俗习惯、行为方式等问题进行关照和挖掘。特定区域的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的人群属性,环境史研究应该将这种具有本地人群属性的环境变迁过程揭示出来,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可以实现此目的,让环境参与的主体人群表达其所感知到的环境演变历史。
基于以上论述,可尝试将走向底层、记录感知底层环境变化,并以口述访谈为主要获取材料之手段的环境史研究称之为“口述环境史”。作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阶段或新方法,口述环境史在转变传统环境史学研究中的主客体以及揭示环境变化后的人群心态转变上优势明显。中国环境史研究特别是古代环境史研究,基本没有涉及环境、生态的专门史料,要研究环境变迁,所用史料多夹杂在其他专题文献之中,进入近代以来依旧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前也没有形成专门的环境保护志书,70年代以后虽有了部分专门的环保志,改变了“环境”在文献资料中缺位的现象,但环保志是以揭示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保护过程为主,强调在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预防环境恶化、控制环境污染,距更深入揭示环境变化过程中的人群生态还有空间,与目前对环境高度重视的社会期望仍有差距,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更细致、深入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作参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口述环境史可以让环境参与的主体人群来表达历史,研究人员不过是历史的记录者。因此,从史学发展角度而言,口述环境史又进一步推进了史学的“向下”发展。
在史料获取与运用上,走向田野的口述方法并非是对传统文献的抛弃与割舍,而是在基于传统史料文献的梳理、解读基础上,运用口述资料将传统史料中重要的关节点串联起来,同时也为开展更精细的环境演变研究提供基础材料。在具体开展区域环境史的研究过程中,合格的口述访谈对象具有敏感的乡土知识与地方经验,这些“乡土”知识(基于特定研究区域中的以本我为中心的环境感知)为立体呈现环境变迁奠定基础。此外,口述访谈能最大程度复原历史时期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关键技术的演变历程,帮助研究者理解影响环境变化的内在驱动因素以及技术消失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
最后,通过口述访谈形式开展环境史研究,笔者更希望揭示区域人群在生境突然变化后对其生计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在当地人心理上留下的印迹,借此关注环境变迁对人群心态的影响。这也是口述环境史区别于传统环境史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对于这项工作,笔者也将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