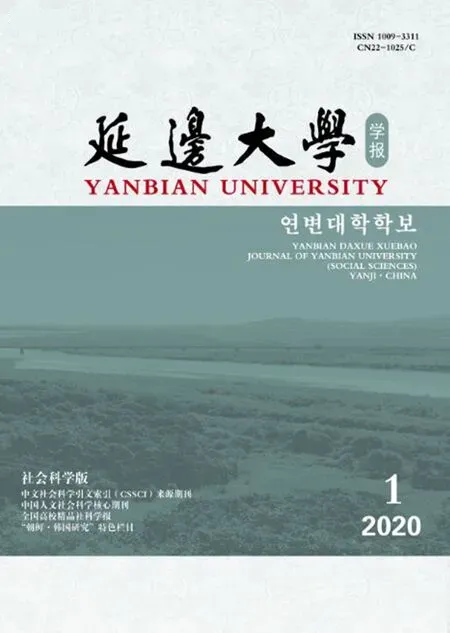论《化鸟》的超时代性
孙 艳 华
《化鸟》(1897)是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体小说,也是第一人称小说的成功之作,虽其篇幅较短,既没有波澜壮阔的布局,也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却是代表泉镜花最高水平的作品之一,在泉镜花300余部作品中占据较为特殊的位置。
目前国内关于《化鸟》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仅有笔者在《“挺拔的孤峰”——备受争议的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中略有提及。
《化鸟》在日本面世之初,对其亦仅限于印象式的评论,未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化鸟》引入研究者视野的是由良君美和肋明子。前者在《镜花的超自然——〈化鸟〉详考》(《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的研究》1974年第3期)中指出少年内心独白及口语体“讲述”的独特性;后者在《幻想的理论:泉镜花的世界》(讲谈社,1974年)中,将《化鸟》定位于“尝试向幻想飞翔”的作品。其后,作为向“幻想小说”蜕变的重要作品《化鸟》引起世人瞩目。
20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围绕着《化鸟》的研究主要从:1.统括全篇的少年的“讲述”及叙事结构;2.少年和母亲的关系;3.对“长着翅膀的美丽姐姐”的解读;4.讲述人的人物形象4个方面展开。将《化鸟》定位于其后诞生的泉镜花“幻想小说”的过渡期作品,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毋庸讳言,《化鸟》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本文将立足于文本分析,探讨意识流手法在构建作品结构及与情节的互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剖析叙事时间结构凸显意识流手法的演绎。同时,将小说置于日本明治20—30年代(1887—1906年)文坛的大框架下,考察作品中第一人称叙事和口语体之于作品的意义,重新审视《化鸟》的艺术价值。
一、意识流手法的演绎
《化鸟》于1897年4月发表在《新著月刊》上。小说中的人物内心独白和叙事时间结构无不体现出意识流小说的特征和作者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
(一)基于内心独白的分析
在《化鸟》中,主人公阿廉以第一人称口吻回忆过去,吐露心声。内心独白与回忆互为层次,交织叠合。开篇即是一大段主人公的内心独白:
好有趣呀,好有趣呀,天气不好不能出去玩儿也挺好啊,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在雨中被淋得跟落汤鸡似的从桥上通过的是猪。
为了不被雨淋湿而迎风低着头,斗笠深深地扣在脑袋上,所以看不到脸。蓑衣长长的下摆盖住脚面,走过时看不到脚。个子大概有五尺左右吧,作为猪来说可是大号的呦,大概是猪中的大王,戴着那个三角形的“桂冠”去城里,回来时会从母亲的桥上通过吧。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就觉得好有趣,好有趣,好有趣。(1)[日]泉镜花:《镜花全集(第三版)》卷三,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第114页。以下文本分析时论及的引文均出自作品《化鸟》,由于数目众多,恕不逐一标注。
这是一段很直接的内心独白,也是回忆中的主人公“我”的内心吐露。其后,旋即以“寒冷日子的清晨,正下着雨,这是我小的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来着?不记得了,是从窗户探出头看到的情景”,点明这是叙述人在讲述自己儿时的故事。接下来,视点回到儿时和母亲居住的小木屋中,再现了雨天与母亲的对话。进而,画面又切换到现在,叙述人以回忆的口吻讲述自己儿时的生活状况: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收取过桥费度日以及小木屋周围的自然环境。形形色色的人去城里,或是出城“都必须经过我们家窗外的小桥”,讲述至此突然话锋一转,“前不久就有几个老师没交过桥钱”,继而问母亲“学校的老师也很狡猾吧”,从而引发与母亲的讨论。其间插入心理活动:自己觉得纳闷,不知为何老师最近对自己很冷淡,由此勾起四五天前的回忆。在与母亲的对话中再现与老师曾就“人类是否比动物和花草更美丽”的讨论。由此情节触发以下内心独白:老师的话不可信,妈妈是不会骗自己的。
作品中共出现8处内心独白的段落。开篇和结尾处及将视点拉回到小屋窗外的“那只猴子现在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吧”“真想看看那张滑稽的脸啊”的内心独白,这3处在构建作品结构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以两个“好有趣呀”开篇,又以3个“好有趣”结束心理活动。如此直白地感情流露,瞬间缩短了与读者的距离,稚嫩的童声敲打着读者的情感神经。主人公关于“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在雨中被淋得跟落汤鸡似的从桥上通过的是猪”“猪中的大王”的内心独白使读者如坠雾中。开篇伊始即触动了读者的神经,抓住了读者的眼球。作者就此展开故事,引导读者渐渐走入主人公的内心深处。“那只猴子现在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吧”“真想看看那张滑稽的脸啊”的内心独白在搭建故事框架时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段心理活动浮现之前讲述的是主人公从妈妈那里听说的八九年前的往事,作者描写这段主人公的心声是为了将叙事时间切换到故事中的现在,同时将视点定格在窗外,并透过主人公的眼睛展现“绅士”的虚伪和吝啬。结尾处的内心独白表达了主人公对母亲及美丽姐姐的憧憬和爱慕,最后一句的“现在有妈妈在我身边,曾经有妈妈在我身边”更是画龙点睛之笔。“现在有妈妈在我身边”表明还沉浸在回忆之中,其后的一句“曾经有妈妈在我身边”瞬间实现时空穿越,读者面前仿佛屹立着一个已长大成人的主人公。
文中其余5处心理独白与故事情节有机结合,心理独白引发情节,情节触发内心独白。关于“不知为何老师最近对自己很冷淡”的心理活动勾起四五天前的回忆;与老师的讨论触发“妈妈是不会骗我的,老师的话不可信”的心声;回忆从妈妈那里听说八九年前的往事时引发的两处心理活动:一是人也是动物的观念虽不被世俗接受,但妈妈的话绝不会错,二是人类无聊、愚蠢,动物和植物有趣、可爱;“绅士”耍赖不交过桥钱的情节触发主人公内心关于“绅士”外观的评论和想象,他大腹便便的像安康鱼,可是那张脸又没有安康鱼可爱,红红的鹰钩鼻子长及上唇,与其说像鱼或是野兽,莫如说更像鸟喙。《化鸟》通篇几乎都是主人公“我”的回忆。在作品中,少年回忆着过去,当回忆一旦与眼前的情景产生联系时,回忆被现实触发,少年便再次沉浸在回想之中,于是少年的深层心理逐渐浮现出来。
(二)基于叙事时间结构的考察
《化鸟》的叙事时间结构也与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法密不可分。《化鸟》的叙事时间共有3个层次:正在回忆的现在,正在被讲述的过去,讲述的过去中又包含的大过去。但是这3种不同层次的时间并不是“形成大、中、小3个同心圆的图形”。(2)[日]三田英彬:《反近代的文学 泉镜花·川端康成》,东京:樱枫出版社,1999年,第55页。正在回忆的现在和正在被讲述的过去虽然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但是对正在被讲述的过去与讲述的过去中又包含着的大过去也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的观点,笔者难以苟同。
故事中的时间呈现如下脉络:故事中的现在时间为“小时候某个寒冷雨天的早晨”——现在1。在现在1中,主人公廉少年回想起数天前几位学校老师从桥上经过而未交过桥费的往事,从而引发了少年“老师都很狡猾”的感慨,进而勾起少年四五天前(小过去)的回忆。与老师之间关于“人和动物、植物哪一方最美丽”的争论,令少年愤愤不平。其后,少年的目光投向河边,随着视线的转移,场面回到正在讲述的故事中的时间——现在2。少年看到一只在堤坝上生活了多年的猴子,于是回想起妈妈讲述的八九年前(大过去)少年尚在母腹中时,家庭遭遇巨变和历经苦难,以及耍猴老人和猴子的故事。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浮现出来的是少年对“人”的认识的演变轨迹。从最初的“猫、狗、人同等视之”的泛神论,到视人为奇怪的蘑菇、古怪的猪,觉得人很可笑、滑稽、没趣、丑陋、傻乎乎的,在少年的心中反倒是红雀更美丽,绣眼鸟更可爱。回忆结束后,少年又注视起窗外。雨过天晴(现在3),妈妈向欲出外玩耍的少年说了一句“别招惹猴子,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长着翅膀的姐姐去救你的。”由此,将少年的思绪带回到半年前(中过去)落入河中被人救起。醒来时问及母亲是谁救了自己,母亲答曰:“一位长着翅膀的美丽姐姐”。于是,少年四处寻找,为再见美丽姐姐一面,差点儿迷失在树林中。回忆结束,少年一句“曾经有妈妈在我身边”将叙事时间定格在正在回忆的现在。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故事中小过去、大过去以及中过去的回忆分别是由现在1、现在2、现在3中眼前看到的景象或听到的话语触发的,从而形成了现在→过去→心理浮现……现在→过去→心理浮现……现在→过去→心理浮现的模式。“杜亚丹给‘内心独白’下定义时认为,这是一种技巧,这种技巧‘直接把读者引入到人物的内心生活中去,没有作者方面的解释和评论加以干扰……’又认为‘内心独白’,‘是内心最深处的、离无意识最近的思想的表现’”。(3)[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在回忆中浮现出来的廉少年“内心最深处的”心理,正是杜亚丹所说的内心独白。因此,《化鸟》中的叙事时间结构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而是交织关系。在过去、现在或与未来的交错中展现人物心理,这也正是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典型表现手法。
此外,作品没有对主人公进行任何外观描写,且年龄不详。连名字也是在故事发展过半才点明叫“阿廉”。这种淡化情节和主人公外貌特征的手法也是心理小说及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特征。
《化鸟》是泉镜花文学创作生涯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日本近代文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少年的讲述自始至终沿着意识流动的方向发展。在绵绵不断的讲述之中,少年的深层心理变化愈发清晰地浮现出来。这种执著于人物内心独白的手法是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主要特征。20世纪初叶兴起于欧洲的心理小说,在日本产生显著影响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化鸟》发表于1897年,早于同时代文学家30余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超越了那个时代。
二、口语体的探索
泉镜花的文学作品常常被刻上“前近代文学”的烙印。然而,《化鸟》中的口语体和第一人称叙事非但不是“前近代”的,反而恰恰具备了同时代作家苦苦探索的“近代小说”的要素。
从日本明治初期到明治四十年(1907)言文一致体确立,日本文学中的文体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蜕变过程。明治初期,占据文体主流的汉文训读体以其独特的韵律感和激昂的格调在翻译小说和政治小说中脱颖而出,但是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欲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必须突破汉文训读体这一文体壁垒。于是,作家们饶有兴致地尝试对文体进行各种“改良”。在汉文体中或加入和文体,或掺杂欧文直译体,抑或揉进口语体,一时间文坛上文体“林立”,百花齐放、蔚为壮观。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1884年)无疑代表了该尝试的顶峰。然而,最适于挖掘人物内心的文体莫过于口语体。
由山田美妙和二叶亭四迷倡导的“言文一致运动”(4)倡导以接近日常语言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运动。因此,史上所称的“言文一致体”与口语体同义。发轫于1887年前后。这种对口语体的尝试以山田美妙的“です、ます”、二叶亭四迷的“だ”、尾崎红叶的“である”等关于文体的探索为先驱。二叶亭四迷率先创作了第一部言文一致体小说《浮云》(1887)。同年,山田美妙在《武藏野》中尝试使用口语进行创作。1907年,言文一致体确立,用口语创作小说成为文坛共识。此20年间,正是日本近代小说界小说语言丧失规范性、文体处于混乱的时期,也是各种文体“群雄鼎立”的时代。小说家们在文体上进行着各种艰辛的尝试和探索。相对于汉文体、汉文训读体与和汉混淆体而言,使用口语体创作并非易事,其中不乏失败之作。
笔者基于《大修馆国语要览》(增补版)中的“近代日本文学史年表”和《新订增补 常用国语便览》中的“近代文学年表”,对山田美妙的《胡蝶》(1889),嵯峨屋御室的《初恋》(1889),幸田露伴的《露珠圆圆》(1889)和《风流佛》(1889)、《一口剑》(1890)、《五重塔》(1891)、《风流微尘藏》(1893),尾崎红叶的《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1889)、《香枕》(1890)、《两个妻子》(1891)、《三人妻》(1892)、《黑暗的心》(1893)、《邻家女》(1893)、《多情多恨》(1896)、《金色夜叉》(1897),森鸥外的《舞姫》(1890)和《泡沫记》(1890)、《信使》(1891),岩谷小波的《黄金丸》(1891),樋口一叶的《暗樱》(1892)、《大年夜》(1894)、《青梅竹马》(1895)、《浊流》(1895)、《十三夜》(1895)、《岔路》(1896),高山樗牛的《泷口入道》(1894),川上眉山的《表与里》(1895)和《书记官》(1895),广津柳浪的《变目传》(1895)和《今户情死》(1896),泉镜花的《巡夜警察》(1895)和《外科手术室》(1895)、《照叶狂言》(1896),国木田独步的《源叔》(1897)、《武藏野》(1898)和《无法忘怀的人们》(1898),内田鲁庵的《腊月二十八》(1898),德富芦花的《不如归》(1898)等,年表中所列1889年至《化鸟》发表后的第二年——1898年出版的38部日本近代重要作家代表作进行了统计。其中,仅有《胡蝶》《初恋》《两个妻子》《邻家女》《多情多恨》《今户情死》《腊月二十八》和《无法忘怀的人们》8部作品是用言文一致体,即口语体撰写的。镜花之师红叶曾热衷于文体尝试,8部中的3部作品系红叶之作。这其中自然有作家的个人喜好和意识差异的原因,但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成功使用口语体创作的作品寥寥无几。
如何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成为那个时代作家的共同课题。在会话体、独白体、第一人称等诸多尝试中,作家们苦苦寻找适合自己作品的表现形式。泉镜花即是其中的探索者之一。其实,泉镜花早期的文体不乏乖戾之作。1892年其发表《冠弥左卫门》时还带有“草双纸”的性质,明显受到了“读本”的影响。《金表》(1893)、《预备兵》(1894)等早期作品都吸收了“戏作文学”的文体。从1894年的《义血侠血》到1896年的《海城发电》使用的是森田思轩的“周密文体”。其后,受到森鸥外的《即兴诗人》(1892—1901年)、《舞姬》(1890)等作品中雅文体的影响,写出了《一之卷》(1896)、《誓之卷》(1896)及《照叶狂言》(1896)等作品。《一之卷》、《誓之卷》及《照叶狂言》虽同为第一人称小说,但使用的却是书面语体。泉镜花虽于1895年10月首次尝试以口语体创作小说《萤火虫》,却因未完成而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口语体小说。《化鸟》遂成为泉镜花首部成功运用言文一致体创作的小说。
关于“口语体”,《百科事典·我的百科》作如下解释:“明治以来,通过言文一致运动,为替代与口语相差甚远的书面语体,口语体得以发展起来。……根据句末的表现形式,分为‘だ’体、‘である’体和‘です·ます’体。”(5)词汇库,https://kotobank.jp/dictionary/mypedia/284/。概言之,作品的句末形式系判断是否为口语体小说的重要标志。不言而喻,此处的句末形式指的是小说的叙述、描写部分,而非对话。在《化鸟》的叙述、描写部分,句末出现如下几种形式:(1)“だ”系列,如:三人だ、猿のおじさんだ、おかしいのだ、着たがるんだろう等;(2)“である”系列,如:であろう、のであろう、のであった等;(3)“ます”系列,如:いいました、聞きました、いいます、おきましょう等;(4)以“ある、出る、見える、する、居る、思う”等为代表的动词简体肯定形式、如“捕えた、思った、しまった、見た、俯向いた”所示的动词简体过去式、“違いない、居られない”等动词简体否定式及“思わなかった、しなかった”等动词简体否定过去式;(5)形容词的简体,以“おもしろい、可愛らしい”为代表;(6)用于口语的终助词或口语中常见的音变形式,如“見えるわ、いいましたっけ、あったんで、わかるものか”中的划线部分。在当时,这些形式都是有别于书面语体的口语表达形式,《化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口语体小说。
《化鸟》以深入内心世界的“道白”展现少年的心理,以万物浑然一体、充满诗意的自然观为基底,描写了少年对母亲和“美丽的姐姐”的憧憬。既然贯穿作品始终的是少年的内心独白,那么文绉绉的书面语显然不符合少年的身份,最终也只能留下败笔。泉镜花选择了以少年的话语道出少年的心声。于《化鸟》面世前一年发表的《一之卷》、《誓之卷》及《照叶狂言》等作品,虽然主人公同为少年,但文体却仍然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雅文体(书面语体)。泉镜花在《化鸟》中使用口语体和第一人称成功地展现了少年阿廉的内心世界。通过《化鸟》,泉镜花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作品的文体,于泉镜花文学而言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从“言文一致运动”发轫至《化鸟》诞生,其间整整过了10个年头。如前文所述,成功运用口语体创作的小说仅有寥寥数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泉镜花成功地实现了文体的转型,《化鸟》是走在那个时代前列的作品。第一部口语体小说《化鸟》付梓后,泉镜花便开始在小说中广泛使用口语体进行创作。但泉镜花的小说并未沿着通常意义上的口语体的轨迹延伸下去,而是进行着各种探索,最终形成叙述、描写部分以口语为基调,夹杂文言的文白相间、雅俗杂糅且独树一帜的文体。《高野圣僧》的问世意味着泉镜花独特文体的确立。在通俗、直白、流畅的口语描写中间插入高雅的文言,既避免了纯口语描写之“俗”,又规避了纯文言描写的晦涩之嫌,作品亦不失文雅的气息。
三、第一人称的妙用
《化鸟》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有别于旧文学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日本文学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是西方文学催生及文学家反思的产物。
在近世后期的“读本”和“滑稽本”“人情本”中,叙述者和作者是一体的,位于故事世界之外。深刻浸润于“读本”影响之中的小说家们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打破“读本”的桎梏才能向近代进发。于是,作家们纷纷踏上探索之旅。近代小说首先实现了叙述者与作者的分离,分化为在文本内记录故事发展的叙述者和在文本外支配故事世界的作者,以《当世书生气质》(1885—1886年)为代表的明治“戏作小说”均显示出了这种变化。进而,叙述者并非作为作者的影子存在于故事世界,而是被赋予了叙述视角的功能,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嵯峨屋御室、尾崎红叶的小说都体现了这种变化的过程。在文本中加入一个有别于作者的叙述者,通过他的报告和解说展开故事是那一时期小说惯用的手法。但是,此时的叙述者无法进入人物的内心。如何在作品中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有血有肉、感情丰润的人物成为那个时代作家共同关注的命题。他们尝试或通过推测叙述的手段加以表现,或通过标注“在心里”的字样以吐露人物心声。这种从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的转变在《浮云》(1887)中有所体现。
1887年出现第一人称小说。先是“自传体”第一人称小说流行,继而第一人称小说的热潮席卷翻译界和创作界。二叶亭四迷的《幽会》(1888)、《邂逅》(1888),山田美妙的《绸缎包儿》(1887)、《这个孩子》(1889),依田学海的《侠美人》(1887),嵯峨屋御室的《初恋》(1889)等,不一而足。译作有森田思轩的《金驴谭》(1887)、《大东号航海日记》(1888)、《幻影》(1888)、《侦探尤拜尔》(1889)。上述作品中的大部分虽为第一人称叙事,但并不是讲述自己的故事,第一人称的表现主体多作为同伴记录、讲述遇到的第三者(他或她)的故事,即同伴式第一人称。成功运用第一人称讲述主人公自己故事的作品当属森鸥外的《舞姬》。
泉镜花的作品中也曾使用过同伴式第一人称,其代表作为《外科手术室》。真正的第一人称小说中,“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与故事之间的心理距离为零。泉镜花真正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始于《一之卷》至《誓之卷》,之后又陆续诞生了《蓑谷》(1896)、《龙潭谭》(1896)、《照叶狂言》、《化鸟》、《清心庵》(1897)、《星光》(1898)、《莺花径》(1898)等一批作品。在《化鸟》中,主人公以第一人称“我”讲述“我”儿时的故事,吐露“我”内心的声音,属告白式第一人称小说。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中的“我”兼有两个主体:一个是讲故事时的“叙述主体”,另一个是经历故事事件时的“经验主体”。讲故事时的视角即通常所说的“回顾性视角”,经历事件时的视角即“经验视角”。一般而言,纯粹运用“经验视角”叙述的第一人称小说并不多见。《化鸟》则是典型的经验视角和回顾性视角相结合的作品。
《化鸟》中,“经验视角”和“回顾性视角”在不经意间巧妙地实现了瞬间转换。在文本开篇的内心独白中,先以“ダ”“ル”“テル”表明时态是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从文体学的角度看,“ル形是从主人公的视点描写自身的心理或周围的状态,这是基于心理时间的主观表达方式。另一方面,タ形则是以叙述者的视点描写出场人物的行动和事件,是受社会时间支配的客观表达方式”。(6)[日]冈崎晃一:《近代文学的时态、色彩与芥川文学:语言文体学的尝试》,姬路:冈崎晃一,2005年,第2页。换言之,此处为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经验视角”。另外,副词“这么”与这一现在进行时搭配使用,增强了“现在正在经历”的临场感,仿佛主人公正在讲述自己现在的内心活动。同时,“好有趣呀,好有趣呀”“也挺好啊”几个表达主人公此时此刻心情、感情色彩强烈的语言形式,更加突出了现在进行时这一时态。接下来,3个“好有趣”将这种情绪推向高潮。然而,此后却突然插入了“这是我小的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来着?不记得了”这样明显表示回忆的句子。紧接着,下一句的时态变为过去进行时,由“经验视角”变为“回顾性视角”。急剧变换的时态和视角,一下子将读者推到了久远的过去。这种强烈对比带来的艺术效果是转换前的画面会非常鲜明地印刻在读者的脑海中。这种美学效果,在小说结尾处的“现在有妈妈在我身边,曾经有妈妈在我身边”也集中地体现出来。现在进行时之后旋即变为过去时,这是十分罕见的时态表达方式。最后一句中的过去时起到了包孕整个回忆的作用,一下子将读者从正在经历的过去(经验性视角)拉回到正在回忆的现在(回顾性视角)。经过一推一拉,结尾与开篇部分衔接得严丝合缝,形成一个封闭、完整的叙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与现在自如变换,来回流动,“经验视角”和“回顾性视角”巧妙交错,引导读者的审美视线不断转移。读者的审美心理也随之远近变换,大大增加了作品的韵味。第一人称叙事可以完美地表现出场人物“我”的内心活动,有效抹去作者的痕迹,增强真实感,易于抒发情感,便于与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四、结语
《化鸟》的诞生早于日本同类小说30余年,堪称日本心理小说的滥觞。它之所以是成功之作,是因为泉镜花找到了最适于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段——第一人称叙事和口语体。《化鸟》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属告白式,有别于旧文学中的同伴式第一人称叙事,通过“经验视角”与“回顾性视角”的巧妙交错引导读者的审美视线不断转移,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韵味。意识流手法于那个时代更属新生事物,其与口语体、第一人称叙事的完美结合使《化鸟》成为超越时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