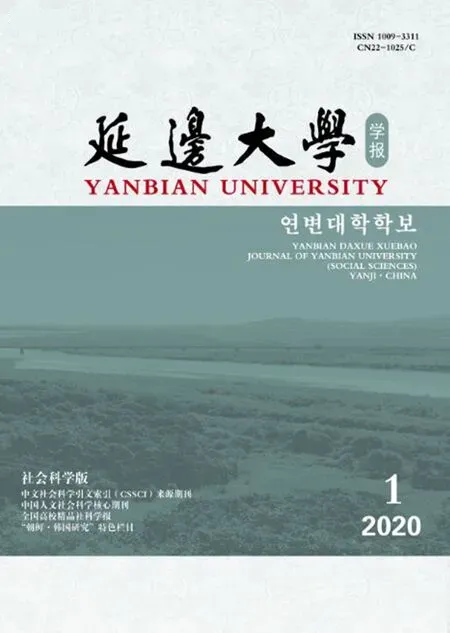汤因比1956年日本之行初探
王 禹 耕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J.Toynbee)的代表作《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自出版之日起便成为世界史学界的焦点。他以扎实的希腊罗马史功底和独特的文明史观点形成了汤因比文明形态史观,成为世界文明史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汤因比曾于1929年、1956年和1967年三次访问日本。以1956年为界,他对日本的评价表现出鲜明的反差。他曾于1929年斥责日本将重蹈迦太基的覆辙,又于1956年称赞日本是“亚洲的先驱”,更于1967年对日本神道教给予高度评价。
无独有偶,在西方学界猛烈批判汤因比学术思想之时,日本却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1956年汤因比访问日本之后,日本出版了大量汤因比日文译著,涌现出一批具有战后时代性的汤因比思想研究学者,还建立了世界唯一以汤因比名字命名的民间组织“汤因比市民会”,成为大力推崇汤因比思想的先锋。本文以汤因比1956年访日经历为重点,通过考证访问期间主要经历和分析汤因比在日期间公开发表的演讲内容,从而探究导致日本与汤因比之间频繁互动的内部动因,勾勒出日本思想界战后重建的“汤因比路线”。
一、汤因比1956年访问日本的背景
汤因比与日本渊源颇深,曾三次访问日本。汤因比192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首次赴日,参加在京都举办的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IPR)。(1)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以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为关注对象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其总部设立于美国,在中国、日本、英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过分会,机关刊物为《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29年10月在日本京都召开。当时,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研究部长兼《国际事务概览》(SurveyofInternationalAffairs)学术编辑,是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访日期间,汤因比曾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踏上了迦太基(Carthage)的旧路并会重蹈同样的覆辙”。(2)汤因比以公元前218年迦太基挑起与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为例,将日本比作迦太基,将中国比作罗马,意在指出日本的侵略道路会像迦太基的命运一样以失败告终。然而,日本将他视为英国代表团的普通一员,将其忠告置若罔闻。
1956年,汤因比再次踏上日本国土之时,其身份与地位与1929年不可同日而语。1946年,其撰写的《历史研究》前六卷(缩编版)在美国出版发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1947年,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Time)封面,被誉为具有独特观点的历史理论家、文明批评家而蜚声全球。1954年,《历史研究》后四卷问世,汤因比已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著名历史学家。
1956年,日本正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在政治领域,日本战败后进入美军占领时期。美国在日本积极推行美式民主政策,修改日本宪法,鼓励民间组建政党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一时间,日本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逐渐成为美国在太平洋西岸的重要战略堡垒和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在思想领域,日本的战败和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摧毁了一直以来支撑日本民族自立的皇国思想。旧史观难以继续指引日本前行,日本思想界处于战后史学理论的“空窗期”。如何重新选择支撑民族复兴和前进的新思想,成为日本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周颂伦在分析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存在的迷惑时指出,“直至战败,日本缺乏国际范围的视野和经验,日本的文明学研究一直都在独善独尊的感觉中孤芳自赏。是战败的重击和重建的历练,使一部分先达开始以清醒的理笥和巨视的目光,考虑日本在世界文明史长河乃至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3)周颂伦:《20世纪日本的比较文明研究轨迹》,《日本研究》2006年第1期,第77页。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正酝酿着引进新思想的变革。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4)威廉·麦克尼尔(1917-2016),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其主要著作有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中译本为孙岳等译:《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Plagues and Peoples(中译本为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Arnold J.Toynbee:A Life以及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中译本为王晋新等译:《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认为,“在战后的日本,唯一可供选择的历史和人类事务的视角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战争爆发前便潜伏在地下……1945年的日本则在冷战中自愿地坚定站在美国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历史观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似乎特别值得一听,况且汤因比在美国的成功保证了他的学识水平和社会地位。”(5)William H.McNeill,Arnold J.Toynbee:A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40.
笔者认为,战后日本引进汤因比思想的背景动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本战后的史学理论匮乏的客观需要。由于身处资本主义阵营,日本必须注意引进思想的意识形态。二是汤因比在美国的成功为日本消除了顾虑。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坚实盟友,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都与美国保持着紧密联系。日本需要美国认可的新思想,美国也需要日本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保持一致。因此,此时汤因比的出现,对美日两国而言都是恰逢其时。
在此大背景下,汤因比的第二次访日拉开了序幕。邀请汤因比访日的任务,由日本国际文化会馆(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IHJ)来承担。日本国际文化会馆是1952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机构出资成立的文化传播组织,主要工作为通过促进日本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增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谢韫直接指出了战后美国基金会对日本资助的本质。谢韫认为,在重塑日本教育和学术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往往避免直接出面,主要依赖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民间机构”推进对日文化交流。这些机构运用资本力量,打着慈善活动、学术交流的幌子,在日本学术界扶植亲美、媚美势力。其目的是培养日本精英阶层的美式思维,主动回避对美国的批评和抨击,迎合美国倡议并为此付出努力,从而引导大众舆论和民众思维。(6)谢韫:《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文化输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12日,第7版。巧合的是,汤因比此次访日活动的旅费,也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全程赞助。
可见,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在美国大红大紫的汤因比思想“介绍”到日本的背后,暴露出美日双边政治上“裙带关系”已经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汤因比的此次访日势必成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
二、汤因比1956年访问日本的经历
1954年12月,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作为汤因比访日活动的邀请方,专程派出曾参加过1929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松本重治(Matsumoto Shigeharu)(7)松本重治(1899-1989),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曾赴美国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曾任国际文化会馆理事、理事长。1969年,松本重治荣获日本政府颁发的一等瑞宝勋章。前往英国与汤因比面商。松本重治时任国际文化会馆专务理事,他在回忆1929年与汤因比见面的场景时,曾如此表述:
“我第一次结识汤因比博士是28年前京都举办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当时他已经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部长,并担任著名的《国际事务概览》的编辑,是世界知名学者。而我本人,当时还是东京大学法学部一名小助教,对头脑如此聪敏的汤因比博士充满敬畏,直至分开一直没有找到接近他的机会。”(8)[英]汤因比著:《历史的教训》,[日]松本重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i页。
当时的松本重治与汤因比并没有语言上的接触,也不可能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与交流。至于松本所说的“敬畏”,究竟是源自地位落差带来的隔阂,还是由于立场不同而带来的“不屑”,笔者无从考证,但二人熟识程度不深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二人见面之时却如老友重逢一般亲切:
“在一个雨夹雪的傍晚,我来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汤因比的研究室拜访了他。在表明邀请他访问日本的来意后,他谈起的尽是对京都往事的回忆,待我仿佛是故友来访一般。”(9)[英]汤因比著:《历史的教训》,[日]松本重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i页。”
显然,汤因比也对再次访日充满兴趣。双方最终商定汤因比于1956年10月访日。对于访问具体细节,汤因比则交由松本安排,不再一一过问。这不仅令松本感受到汤因比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更对其给予的信任产生出强烈的亲切感和责任感。
日本国际文化会馆全权负责汤因比访日期间的日程安排。在其主导下,日本学界以东京和京都两地为中心,汇集历史学、考古学、东洋学、文化人类学、哲学、政治学、思想史等百余名专家学者一同研讨汤因比访日行程。据松本回忆,为确定汤因比访日期间的学术议题,充分展示日本最高的学术水平,相关学者成立了日本史、东洋史·考古学、文明论三个方向的讨论组进行研讨。此外,在日程中还加入了历史遗迹考察、大学演讲以及个人访谈等多项活动。(10)[英]汤因比著:《历史的教训》,[日]松本重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i-ⅴ页。日本学界历经近一年的精心准备,终于确定了汤因比在日期间全部日程安排,可见,日本学界对汤因比访日的高度重视。
1956年10月1日,汤因比抵达日本,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访日之旅。根据其游记《从东方到西方》(EasttoWestAJourneyRoundtheWorld)(11)[英]汤因比(A.J.Toynbee)著:《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赖小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8-249页。的相关记载,访日期间他分别抵达了东京、日光、镰仓、箱根、大阪、京都、神户、别府、小仓、福冈、长崎、奈良、仙台、青森、函馆、秋田、新潟等地,行程遍布日本本州岛、九州岛、四国岛、北海道四大主要国土,足见日方希望为汤因比呈现出一个完整而立体的日本形象。
对具体访问地点,日方同样进行了细致安排。除龙头瀑布、比叡山、高野山、函馆风光等自然景色之外,还增加了镰仓大佛、日光东照宫、伊势神宫、京都城、姬路城、法隆寺等名胜古迹以展示日本历史魅力;安排汤因比体验箱根温泉和大鳄温泉,以凸显日本温泉文化;专程赴广岛和长崎两地考察原子弹爆炸遗址,以宣扬日本所谓“战争受害者”形象。日本从自然、历史、文化和形象四个维度出发而最终选定的访问地点,充分体现出日本“新形象”的主要构架,期待汤因比对日本“新形象”的认可,可谓煞费苦心。
除文化考察活动之外,日本还为汤因比安排举办了多场学术讲座。具体时间与内容详见表1:
从表1中不难看出,汤因比在日本的演讲中既有文明形态学涉及的“挑战—应战”理论,也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邂逅,大多都是围绕汤因比的研究方向。演讲中,汤因比时而利用希腊罗马史中的史实来佐证其学术理论;时而采取由古及今贯穿千年的历史变化来阐述学术观点,充分展现出汤因比在史学领域深厚的功底和世界级历史学大师的学术水准。
由于演讲内容的专业性与学术性,聆听汤因比演讲的受众层次相对固定,均以日本史学界及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主。然而,在全部演讲中,汤因比通过日本广播协会(NHK)转播的“世界史中的日本”(TheRoleofJapaninWorldHistory)极具特殊性。此次演讲在学术层次、传播方式和理论深度上均与其他演讲存在明显差异。笔者认为,此次演讲的性质并非面向专家学者的学术讲座,而是利用大众传媒手段,针对日本普通民众进行的一场思想启蒙,其目的和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三、汤因比1956年访日的“点睛之笔”——“世界史中的日本”
“世界史中的日本”(TheRoleofJapaninWorldHistory)是汤因比访日期间唯一通过媒体转播的演讲。考证其演讲稿件,笔者发现演讲中既没有晦涩深奥的历史学专业名词,也没有推崇“挑战—应战”理论,更没有列举希腊罗马史进行长篇大论。出于对日本民众不同的教育背景及知识结构的考虑,整篇讲稿通俗易懂,准确而清晰地传达出汤因比对日本重新崛起的殷切期望。
汤因比在演讲中提到,“世界史中的日本”是应日方要求而进行的“命题演讲”。这更加突显出日本学界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急于抛弃战败阴影,重新树立日本国家形象的急迫心情。笔者通过对演讲内容的解读认为,日本学界精英着眼日本长远发展,邀请汤因比以“广而告之”的方式进行“命题演讲”,其真实目的在于借助汤因比的学术泰斗地位,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文化,转变战后思想颓势,树立民族自信,为日本重新崛起寻求新的思想基础。
(一)汤因比对日本岛国性的批判
汤因比在演讲中对先抑后扬的把握十分纯熟。在演讲的前半部,他曾多次对日本提出批评。他指出,日本岛国性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孤立,表现为对外国影响的抵抗和排斥。他将英国与日本进行对比,指出英日两国岛国性的本质差别:
“英国也是远离欧洲大陆的岛国。英国人与日本人一样,在附近大陆人民的眼中映射出岛国根性。但,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相比英国更为极端。……这使得英国更容易接受大陆传来的影响,对于英国接受大陆的艺术和文明具有积极作用。……其次,英国在历史上曾被罗马人、诺曼人等被外敌征服。虽然被外敌征服是痛苦的经历,但这种被外敌征服的经验带给英国一个最重要的心理效果,让英国人了解到自身并非强大无比,更并非超人或被上天庇佑的神圣子民,而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此外,在日本接受(外国影响)之时,所接受的东西也被加入某种日本独特的东西进行改编。同时,日本人一旦决定引进外来文明,便会如数家珍般掌握此文明,由此看来,(日本人)比没有岛国性的其他各国国民发挥了更伟大的才能。”(12)[英]汤因比著:《历史的教训》,[日]松本重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48-50页。
在汤因比看来,英日两国的岛国性存在根本不同。英国在大陆频繁影响下其岛国性得到了抑制,而日本则表现得根深蒂固。这一方面意在表明日本在1945年的战败并没有历史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在1945年之前实则目光短浅、骄傲自大。汤因比以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为例,说明日本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之中虽然极力排斥外国影响,但是一旦日本决定引进外国文明,则会变化吸收作为自身的一部分。(13)演讲稿日文版中使用了“作り変えてしまおうとした”,意为“变化吸收”而非“消化吸收”,是通过改变原始形态而迎合自我意愿的自创式吸收。汤因比刻意指出日本意识形态中对外来文化存在“变化吸收”或“曲解吸收”的特征,并用史实力证了日本改变和臆造外来文化迎合自我发展的本质。
(二)汤因比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批判
汤因比一生向往和平主义,他反对战争、反对杀戮、反对暴力。在谈及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将发展重心转为军事领域时,他虽然认可这是迫于时局压力的无奈之举,但更强调日本埋下了民族主义的恶果:
“日本虽然通过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的技术文明,完成了国家的近代化。通过利用实用主义,用事实证明了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可以与西方大国进行对抗的国家。不幸的是,日本都是通过对外军事战争的方式来证明的。……如果日本当时不采取近代西方的战争方式就会被占领,这是不幸的事实。……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都在通过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日本的听众可能会认为明治时代日本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并辩解称,由于近代世界西方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给日本带来了危机,如果日本不学习和实践近代西式的战争技术,不久便会被降服。遗憾的是,这的确是事实。”(14)[英]汤因比著:《历史的教训》,[日]松本重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52-54页。
可见,在探寻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源头之时,汤因比虽然承认当时西方列强正加紧对亚洲的侵略,对日本形成了严重的外部威胁,但他没有严厉斥责西方自19世纪中叶开始武力侵略亚洲的错误行径,而是批判日本单方面的不自量力,规避了日本对外侵略是仿效西方的产物。同样,汤因比在批判日本之时,并未提及日本应该对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反省,而是认为日本战后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崩塌而带来的“精神空洞”,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来填补“精神空洞”是日本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汤因比这种基于“文明”的观点为日本确定引进汤因比思想埋下了伏笔。
(三)汤因比对日本寄予的希望
在完成对日本批判的“先抑”之后,汤因比拉开了“后扬”的序幕:
“我在几天前访问了长崎,并参观了原子弹爆炸地附近的和平神像。和平神像一只手指向死亡来临的天空,另一只手在告诫全世界的人们,在核武器时代背景下不应再有战争。这不仅告诫人们停止物质上的破坏……也是对因傲慢而生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告诫。”(15)[英]汤因比著:《历史的教训》,[日]松本重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55-56页。
此时的汤因比在语言中流露出对日本遭受原子弹打击的无限同情。他认为日本早已将从中国引入的佛教和儒家精神融入生活,成为日本国民精神生活的支柱,战后短短十几年便重获新生,充分肯定了日本自身的“快速修复”能力。在他看来,日本在战胜自身的岛国性之后,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在安抚日本心灵的同时,汤因比也对日本寄予了厚望。他希望日本能够充分总结历史教训,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发挥日本自身优势,“现身说法”,与其他国家一同建设和谐共生的世界国家:
“在世界史开启新篇章的当下,日本传统的岛国国民应当以成为世界市民作为新的理想。在亲身经历了原子弹攻击后,日本应比亚洲的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启新篇章,成为超越民族主义榜样。加之,日本在近代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文明,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进而进行对抗,充分证明了日本是亚洲的先驱者,且得到了亚洲其他国家的认同。日本作为人类社会一员,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技术援助(16)1954年10月,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11月与缅甸签署《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开启了日本“赔偿外交”序幕。是在生活层面奉献人类同胞的途径。”(17)[英]汤因比著:《历史的教训》,[日]松本重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57页。
笔者认为,汤因比在此处刻意回避了部分史实。他鼓励日本从战败的阴影中发现并实践“人类和谐共生”的和平道路,将日本对外的技术援助变为奉献人类的途径,忽略了其包含的战争赔偿因素;将日本视为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受害者,忽略了其侵略者的身份与侵略罪行。但是,他的结论却在日本民众心中产生了共鸣。直至今日,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拥有“战争受害者”的观点。这种论调能够使日本充分卸下侵略包袱,迅速转变为需要保护的“弱者”,从而逃避来自被侵略国家的苛责。
笔者发现,整篇演讲“先抑”有限,重在“后扬”。思想启蒙的本意并不在于批判与反省,而在于安抚与鼓励,讲出了日本民众最想听到的话语。战后的日本,周围常年充斥着国际社会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批评之声。此次演讲宛如一股甘泉清流,沁入日本人的心脾,满足了日本排除战败影响、重获西方肯定、期待民族复兴的内心需求。
此次转播在日本全国上下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仅奠定了汤因比在日本的超凡地位,也开启了日本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汤因比热”,也成为汤因比1956年访日的“点睛之笔”。
四、汤因比1956年访日产生的影响
汤因比1956年的访日活动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在日本学界掀起了一波汤因比思想研究热潮。日本学者对待汤因比的态度由学术研究转变为理论推崇,对汤因比演讲的态度也与1929年的置若罔闻形成了鲜明对比。吉泽五郎在评价汤因比访日影响时曾写道:
“当时的日本,正是在与过去的民族主义诀别、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思潮最流行的时候,汤因比的思想仿佛启明星一样,为新日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18)[日]吉泽五郎:《与汤因比的对话:现代挑战与希望道路》,东京:第三文明社,2011年,第155页。
为进一步扩大汤因比在日本的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汤因比的史学思想,国际文化会馆于1957年将汤因比在此次访日期间发表的9场演讲整理并翻译成日文出版发售,命名为《历史的教训》。
其次,得益于大众传媒的影响,日本民众对汤因比的热情也不断高涨。一方面表现为日本民众对汤因比作品的喜爱。《历史的教训》日文版上市短短几周内便卖出8 500本。不仅如此,《历史的教训》自1957年首次出版起,至1977年的20年间已经翻印出版22次之多。另一方面,表现为日本民众对于汤因比思想的推崇。“汤因比市民会”的首倡者高品增之助(Takashina Masunosuke)正是以研读《历史的教训》为契机,不断深入了解汤因比思想,进而提出成立以汤因比名字命名的民间组织,进一步扩大汤因比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汤因比市民会”自1968年成立至1997年解散,在日本存续近30年。该会设立了专门刊物《现代汤因比》(現代トインビー),并出版了多部论文集,涌现出松本重治、山本新、秀村欣二、吉泽五郎等一批具有战后代表性的汤因比思想研究专家,在日本学界和民间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与日本学者的乐观和推崇相比,西方学者对汤因比此行却有不同的评价。《汤因比传》(ArnoldJ.Toynbee:ALife)的作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评述汤因比1956年访日时认为:
“他(汤因比)后来在日本的名声是由他1956年的访问引发的,其中一个关键可能在于日本准备接受他对民族主义的完全熟悉的谴责——这是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宣扬的主题。无论如何,当他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与随行翻译一起)时,他宣称‘我相信日本人民将为我们克服传统民族主义的共同努力做出重大贡献’。……当被告知欧洲要在某些领域向日本学习时,对于日本来讲是一件荣幸的事。”(19)William H.McNeill,Arnold J.Toynbee:A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40.
麦克尼尔充分指出汤因比对日本的“夸赞”符合了日本国民的需要。笔者认为,作为世界级的史学泰斗,汤因比将日本评价为“亚洲的先驱者”,不仅唤醒了日本人对战败前那段“辉煌”历史的回忆,传达出不论日本战败与否依旧是亚洲的先驱、是举足轻重大国的引申含义,更能激发日本民族自豪感、荣誉感与认同感。
此时的汤因比已经跳出了个人身份,而成了西方史学界的“代言人”。他对日本的肯定变成了西方史学界对日本的肯定;他对日本的期待也上升为西方对日本的期待。
五、结语
1956年成为日本宣扬汤因比思想的转折点,源于汤因比的访日经历。可以说汤因比是在日本政府的认可下,被日本知识界、产业界和传媒界一同推上了日本战后思想引领者的地位。
日本学者引入汤因比思想的出发点与日本战后的现实环境相得益彰。日本学者吉泽五郎曾指出,汤因比有一种“对于弱者的共鸣”。汤因比经常引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曾在《阿伽门农》(Agamemnon)中说的“智慧来自苦难”。在讲述历史的时候,汤因比也并非从胜者的角度,而是从败者的角度,从受压迫的阶层、集团、人民的角度进行讲述。他关注败者的创造性和智慧,并给予高度评价。(20)[日]吉泽五郎:《再读汤因比——解读现代的关键》,《第三文明》2007年第6期,第72-74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日本自1956年起,大力引进和宣扬汤因比思想,不仅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暗中资助的美国因素,更源自汤因比“世界史中的日本”所传达的观点符合了日本民众的心理需求。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摒弃了历史的“是非观”。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非正义性的避而不谈和对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同情,都迎合了日本民众的“受害者”心理,成为日本引进汤因比思想的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