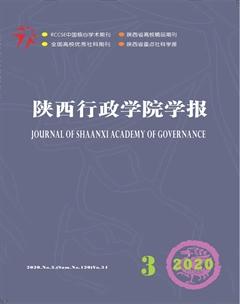十九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熊耀林
摘 要: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界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进一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需深入厘清其科学内涵,阐释其逻辑体系,拓展研究视角,突出多学科交叉性研究。
关键词: 总体国家安全观; 生成逻辑; 基本内涵; 时代价值;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20.03.009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XIONG Yao-lin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oncept of “upholding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was included in the basic strateg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hich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multi-dimensional studies on the notion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including its generative logic, basic connotation, time value and practice path,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explain its logical system, exp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highlight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generative Logic; basic connotation; the value of the times; practice path
“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總体国家安全观这个战略命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论述过该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2] 至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列思想不断升华,其代表性成果是2018年4月出版的《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相关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阐述精辟,把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是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五年来,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库来源,以2014年4月15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为时间节点,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共查阅文献1447篇,其中CSSCI期刊243篇。从文献发表的时间节点来看,十九大以来发表文献878篇,占比60.6%,其中CSSCI刊162篇,占比66.6%。可见,十九大以来,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探索思考更加深入,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综观研究成果,学界主要围绕其生成逻辑、基本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纳,有利于把握研究现状,明确研究方向,对于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
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内在必然性。学界普遍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不仅受马克思主义安全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安全思想的影响,而且受所处时空社会存在的制约。李营辉、毕颖就指出,思想承继与飞跃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依据,现实机遇与挑战的外在动力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依据。[3]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成的理论渊源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国家安全思想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成的理论基础。其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的哲学基础。韩承鹏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唯物主义原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观点。[4]柏坤等也论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其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安全理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的理论前提。刘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生命个体的存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等方面解读了新的安全理念,对当代的安全生存与发展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战略思想。[5]还有学者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阐述了坚持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安全的人民立场。[6]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安全思想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成的文化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7];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工作导向,诠释了古代思想史中的民本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指出了爱民、利民、为民除患是实现人民和国家安全的途径[6];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中的忧患意识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 这正对应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传统文化思想。[8]
3.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理念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历史积淀。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念,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安全观先后经历了传统国家安全观(改革开放前)、转型国家安全观(改革开放后至中共十八大)、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共十八大之后)三个不同阶段。[9]凌胜利、杨帆等学者也持三阶段划分的观点。学界大多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产生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理念,徐光顺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毛泽东新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等方面是一致的。[10]李营辉、毕颖等学者指出,江泽民同志提出互信协作发展型国家安全观,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发展型国家安全观等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有重大指导之义。[3]
4. 西方国家安全理念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理论借鉴。冯维江等指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体和中心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秉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积极吸收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中的有益养分充实和完善自身。[6]马振超系统阐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权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均势理论以及现实主义学派、理想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中保障国家安全的实力理论、文化软实力理论、均势理论等,对中国妥善处置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11]周梦倩等学者也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批判性地吸收了国际建构主义安全理论。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成的现实依据
1. 外部威胁持续增长,安全环境日益复杂。从世界发展图景审视,当前国际社会乱象重生,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2]在国土安全方面,国土边境安全面临挑战,“台独”分裂活动存在威胁隐患、反分裂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在军事安全方面,世界和周边地区依然面临潜在战争风险,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带来新挑战[13];在文化安全方面,一些腐朽落后文化沉渣泛起,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冲击[14];在经济安全方面,中美近期在贸易领域的摩擦增强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15];同时,极端主义不断蔓延,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海盗活动等问题不断显现。[16]
2. 内部矛盾进入多发期,安全形势日益紧迫。从国内安全的整体现状看,国家安全风险扩散具有问题扩散、行为者扩散、空间扩散、时间擴散四个维度,各种安全风险相互联动、耦合,形成系统性风险。[17]从国内具体安全领域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10];在政治安全领域,官僚腐败、消极懒政、颜色革命、“一国两制”实践等方面形势严峻复杂[13];在思想文化领域,不同社会思潮的交流交锋加剧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对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不利影响。[15]从人民的现实需求来看,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生活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和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在民主、公正、法治、环境等方面的需要。[18]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面系统、注重统筹的新型国家安全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学界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 “四重内涵”说。石俊杰从比较视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四大内涵:从安全主体来看,倡导“共同”安全;就安全范围而言,注重“综合”安全;在实现安全的途径方面,采取“合作”对话而非博弈对抗;在安全保障方面,强调“可持续”安全。[19]王宏伟也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其科学内涵: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整体性的安全观,是开放性的安全观,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有认识论的意义,也有方法论的意义。[20] 陈向阳则从“六个坚持”的基本要领,“六个属性”的鲜明特征等层面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钟开斌从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面向主权实体的传统国家安全等方面分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结构。
二是“五位一体”说。李大光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体现了五位一体的安全内涵。[21]张家年、马费成、蒋华福等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丁磊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五对关系: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22]廖生智、孙敬龙比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美国安全观在历史文化、发展道路、世界文明观、制度基础与利益指向和思想理论基石五个维度上的差异,凸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独特内涵。[23]
三是“多种要素”说。鞠丽华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11个方面的安全[15];罗建波综合了前面的观点,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了十一个领域、五大要素与五对关系[24];刘跃进认为其涵盖了“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25]还有学者认为,要以开放性眼光讨论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体系除上述11种国家安全外,还涉及深海、太空、极地等安全问题,共有19种之多。[20]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价值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安全保障。
一是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实践纲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路线图、方法论,为推进国家安全实践指明了方向[26],为我国国家安全观注入了新的内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增添助力。[27]其着力解决人民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支撑。[28] 其涵盖了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既注重国内安全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安全保障,又能解决对外安全工作突出的地区安全问题,维护国家对外发展的利益。[29]
二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摒弃了传统国家安全观中零和、单赢的安全思维模式,提倡以非零和、互利共赢的新安全思维模式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30]。其以发展为实现安全的总钥匙,透视了威胁安全的深层次根源——冷战思维、新霸权主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31],进而提出建立健全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共同面对发展和安全挑战[32],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搭建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走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21]
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指南。总体国家安全观站在人类命运的道义制高点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理念,倡导通过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以互谅互让精神处理分歧,以合作共赢的态度促进共同发展,以面向未来的眼光解决现实问题,展示出对全人类命运的深深关切。[11]其坚持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统一,走共同安全道路,打破了弱肉强食的传统逻辑,超越了结盟的传统模式,为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6]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理论体系、国家战略和工作方针的有机统一,其着力点在于采取现实的、系统的、立体的实践建构。当前,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路径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树立系统科学的国家安全理念。“总体安全观的关键在‘总体,强调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33]一是树立国家安全维护的科学思维。鞠丽华指出,要树立战略思维,从全局性高度统筹国家安全问题;树立辩证思维,坚持顶层设计和具体举措的辩证统一;树立法治思维,健全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树立底线思维,强化危机意识,明确安全底线。[15]二是树立合作共赢的安全理念。坚持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统一,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深化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34]三是树立可持续安全理念。即以发展为路径、以共享为核心、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共同安全体系,为解决当今世界跨境跨领域的普遍安全难题提供新思路。[35]
第二,构筑多维立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一是要设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使之成为相关机构和部门之间的“粘合剂”,加强国家安全战略或政策的整体性和计划性[36];二是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形成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与工作机制,创建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制度[37];三是强化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进国家安全立法工作,出台国家安全系列法律[38];四是形成总体国家安全工作责任机制,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基础上,确立各级党委对国家安全工作的主体责任;五是建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体系,通过学科建设托底、全程教育奠基、全民共识凝练等,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合力和群众基础。[39]
第三,全面增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一是在宏观层面,要持续增强国家安全战略支撑能力、战略实施指导能力、战略运用统筹能力。[38]还有学者指出,能力建设要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协调推进,对内必须提高统筹组织社会公共资源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提高预判、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对外必须加强经济合作、人文合作、军事合作与司法合作能力。[40] 二是在微观层面,要重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特定领域能力体系的建设,如国防军事能力、核能力、网络信息能力、科技自主可控创新能力、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文化影响力等。[41]
第四,实施协同高效的国家安全治理举措。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坚持立足于防范,又要有效處置风险,还要坚持科学统筹,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合力。[38]一是要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重力量,多维度、多视角分析国家安全风险,形成涵盖社会治理、区域治理、全球治理复合的多层次治理模式,使用多样化手段解决安全风险问题。[17]二是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在政治制度领域,建立一系列区域和跨区域的多边机制,实现对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积极贡献;在经济领域,要与世界各国积极交流与合作。[36]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探索了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细分领域的安全治理举措,如胡象明、张丽颖提出了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应创新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多方合作的方式,对敏感性信息要采用渐进披露的方式。[42]
五、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初步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术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由于此论题提出时间较短,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以期刊论文与报纸文章为主,相关学术专著较少,高水平论文数量不多,理论研究尚缺乏系统性与深刻性,对有些理论问题尚处于探讨、争鸣或碰撞期,因此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空间。
1. 内涵界定模糊,需进一步厘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与外延。当前,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尚未形成共识,很多学者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和11个安全领域统一归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包括国家安全价值观念、工作思路与机制路径等内容。然而,内涵最本质的核心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定,而外延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不断拓展。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述总体国家安全体系时,特别强调一个“等”字,就意味着其对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11个领域的阐述应是一个不完全列举,意在强调国家安全领域的广泛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国家安全体系涵盖了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外延与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密不可分,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革与转型之中,影响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不断出现,各种新问题与新挑战随时有可能被“置顶”,并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因此,学者们要根据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外延进行持续动态解读,从而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这一战略思想体系。
2. 研究内容深度不够,需进一步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研究阐释清楚这个逻辑体系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点。虽然学者们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十九大以来有深度且得到各方普遍认可和引用的观点依然不多见,部分研究成果在观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现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要有时间域与空间域,既要从时间维度梳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逻辑,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与新时代不同阶段国家安全观之间的接续转承与逻辑关系,也应从空间维度研究其实践逻辑,对当前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研究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研究全球化场域、市场化时域、多元化论域的大背景,不同社会因素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还要深入研究其理论逻辑,挖掘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国家安全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国家安全思想以及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厘清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和内在特质规定性,进而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创新力。
3. 研究视角存在“三重三轻”,需进一步拓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维度。十九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重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重横向比较,轻纵向梳理,这不利于丰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需进一步拓展研究维度,将理论探讨与规范建构相结合,将整体布局与具体领域相结合,将现实关照与历史透视相结合。如就安全主体而言,国家已不再是单一主体,出现了大量非国家行為主体,因此要进一步阐述公民个体与非政府组织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就安全因素而言,十九大以来研究主要聚焦于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与经济安全研究,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科技安全、核安全等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就安全维护手段而言,当前相关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对举措的可操作性研究不够,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警惕防范“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破解国家安全中的困境。如针对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下就要研究如何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4. 多学科交叉性研究偏少,需进一步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系统性与开放性。国家安全问题不是原生的而是衍生的。当前国家安全和风险源头复杂,国家安全要素呈现立体多元的特点,以致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空前增强。但现有研究大部分是从军事学、情报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公共安全学等单一学科出发,对各安全要素之间如何协同配合,各领域风险防控怎样统筹协调等问题的探索还明显不足,这容易导致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成为“拼盘”式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总体性”,就意味着要凸显各领域安全问题间的相互关联、耦合与互动,形成一个“体系”。因此亟须吸收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科技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通过推进多种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实现各学科协同联动,相互激发灵感,形成化合反应,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更完备,更系统、研究内容更丰富,从而实现研究的整体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李营辉,毕颖.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17):84-87.
[4]韩承鹏.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基础[J].求索,2018(6): 35-42.
[5]刘箴.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品质和方法论特征[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6):31-35.
[6]冯维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4):4-27,154-155.
[7]杨艳.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D].兰州:兰州理工大学,2018.
[8]谢晓光,王陈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与实践[J].唯实,2018(2):90-93.
[9]钟开斌.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战略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8(10):23-30.
[10]徐光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探析[J].邓小平研究,2018(2):54-61.
[11]马振超.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指导思想[J].行政论坛,2018(4):5-10,2.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李大光,韩刚.全球化背景下的总体国家安全(上)[J].中国经贸导刊,2018(9):73-76.
[14]本书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5]鞠丽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8(9):17-22.
[16]凌胜利.2019年的国际安全:变革重塑 亦险亦难[N].光明日报,2019-12-29.
[17]王宏伟.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及其治理[J].现代国际关系,2017(11):50-57.
[18]骞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J].学理论,2018(12):18-19.
[19]石俊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 ——对主要西方国际安全观的超越[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27.
[20]王宏伟.正确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7-17.
[21]李大光.全球化背景下的总体国家安全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8):6-19.
[22]丁磊.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探究[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8(3):8-10.
[23]廖生智,孙敬龙.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冷战后美国安全观差异的五维探源[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8(4):30-35.
[24]罗建波.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J].领导科学论坛,2018(16):79-96.
[25]刘跃进.总体安全为人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J].紫光阁,2018(7):16-17.
[26]孫东方.深刻把握新时代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N].人民日报,2018-04-16.
[27]生忠军.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背景、基本原则和重要任务[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1):17-23.
[28]张青磊.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人民安全”:生成逻辑、内涵与保障路径[J].理论界,2019(9):1-8.
[29]张志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J].才智,2017(36):206.
[30]叶浩豪.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价值[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5):15-17.
[31]孙叶青.习近平安全观及其时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1):48-54,159-160.
[32]高志垒.“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家安全战略关系研究[D].石家庄:河北大学,2018.
[3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
[34]吴玉军.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N].光明日报,2019-04-12.
[35]郭锐,廖仁郎.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嬗变与可持续安全[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6):9-17.
[36]张雪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践路径[J].求知,2018(1):33-35.
[37]王勇.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筑牢国家安全屏障[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1):38-43.
[38]刘跃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总体布局[J].人民论坛,2017(34):38-40.
[39]涂成林.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旨归[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8-07.
[40]韩爱勇.内外统筹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N].光明日报,2019-04-12.
[41]张家年,马费成.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及应对策略[J].情报杂志,2019(10):12-20,152.
[42]胡象明,张丽颖.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J].行政论坛,2019(4):13-21.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