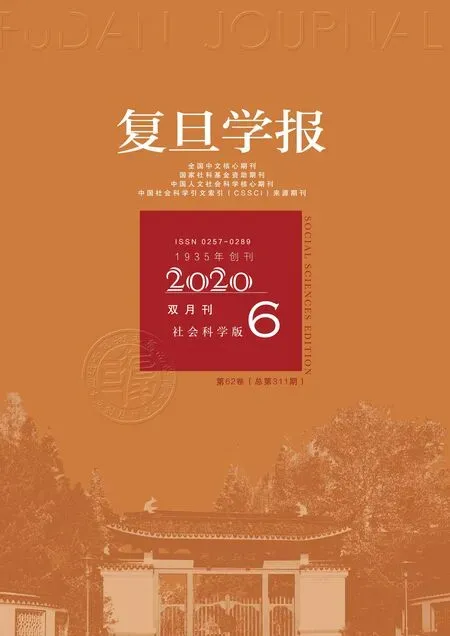从实践的观点重审康德的先验自由
——兼论实践与理论的区分
孙小玲
(南昌大学 哲学系,南昌 330031)
自由问题无疑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不仅因为康德在不同的语境中甚至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自由概念,而且也因为康德几乎从未对这些不同意义的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任何清晰融贯的解释。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对康德那儿可以区分出几种不同的自由概念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一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康德学者都同意先验自由是康德自由观的核心,不仅是康德道德理论的构成性要素,而且,如同康德自己表明的那样,是“纯粹理性,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KpV 3-4)。(1)《纯粹理性批判》按惯例标出A、B版页码,其他康德著作的引文均标注普鲁士科学院版的页码。 KrV 即《纯粹理性批判》,KpV 即《实践理性批判》,GMS即《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S即《道德形而上学》, Rel即《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KU即《判断力批判》。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因此就对康德的先验自由的含义及其在康德哲学中的功能有一致的看法,相反,先验自由概念恰恰是围绕着康德自由理论的争论之聚焦点,是康德自由问题困难的真正所在。在此,不仅有对于康德的先验自由的诸种不同甚或互相冲突的解释,而且也一直不乏对这一自由概念的理论乃至实践必要性的质疑。这至少部分地归因于这一概念所带有的思辨形而上意蕴:虽然康德一再强调自由的实践性,但康德首先是在思辨形而上的背景中界说了其先验自由概念,这事实上导致了一系列几乎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我们将在本文中尝试一种相反的方式,即将先验自由首先界说为道德必要的预设,然后在此基础上审视其可能的思辨与形而上意义。具体而言,我们在第一部分将讨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第一批判”)中对先验自由的界说,并结合《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第三章的演绎以显明从思辨到实践路径的困难。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参照《实践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第二批判”)的思路从道德出发界说作为其必要预设的先验自由,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尝试进一步理清先验自由与其他自由概念的关系,并部分地回应对康德自由理论的主要质疑和批评。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们将深入分析康德的两条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一)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自由首见于康德的先验辩证论,其所关涉的是世界始因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有这一问题,是因为在康德看来理性必然地会追求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因此必须设定一个世界之外的无条件的条件。这就要求理性超出经验去使用原本只能被经验性使用的知性范畴,比如因果性范畴。其结果是理性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冲突,这一理性的冲突在关于世界或者说宇宙论问题上就体现在四组二律背反之中,其中第三组二律背反的正题引入了先验自由的观念。所以,先验自由一开始就被界说为世界的始(第一)因。作为始因,先验自由是不受任何先在原因限制的绝对的自发性(spontaneity),由其自身产生出作为其结果的世界,后者受到自然因果必然性的严格统摄。但先验自由本身并不在世界之中,既不受制于自然法则,也无时间性。这当然不是说先验自由是无法则的任意性,因果性在康德看来总已经是一种合法则性,故而作为始因的先验自由被称为“自由的因果性”(A444/B472)。
与正题相反,反题则否认了这一自由的因果性,以确立自然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康德在此的目的是捍卫作为理性理念的先验自由,但他也没有完全否认反题的合理性,因为反题所基于的恰恰是康德自己在分析论中,具体地说在第二类比确立起的先天因果性法则。这一法则表明:一切事物的发生必然有其原因,并因此排除了不受先在原因限制的因果性,即始因。事实上也正是通过证明这些自然法则的先天与普遍的有效性,康德才得以拒斥了休谟式的怀疑主义对科学(尤其物理学)的侵蚀。所以,为了保存其分析论获得的成果,康德只能借助其先验观念论来为先验自由做出辩护,即区分为自然法则统摄的现象界与自由法则在其中有效的本体界,借此区分,康德就可以辩护两种不同的因果法则之间的相容性。事实上,这一先验观念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理性的超感性使用的结果,因为只有设定一个世界之外的原因或视点,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才是可能的。显而易见的是,康德之设定先验自由具有明显的形而上与认识论旨趣。
但是,另一方面,康德也表达了其实践旨趣。在关于正题的说明中,康德就表明并非经验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先验自由构成了“行为可归责的根据”(KrVA448/B475),并在关于宇宙论理念的解析中进一步断言“自由的实践概念基于自由的先验理念之上”,以至于“对先验自由的取消就会同时根除一切实践的自由”(KrV A534/B562)。换而言之,实践自由以及道德责任在某种意义上预设了先验自由,并因此也预设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思辨形而上学跨越到实践和道德哲学的路径。
但是,这一跨越并不容易,因为宇宙论意义上的始因,正如海德格尔所见,与意志和行动无关,但作为行动者的人却是有意志的存在者。(2)Martin Heidegger, 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Vitorio Klostermann, 1982) 25.并且,海德格尔进一步追问:因果性的含义究竟为何,以至于它有时属于自然,有时属于自由?
在海德格尔看来,将原本属于自然哲学的因果性概念应用于意志自由(实践)事实上表明康德仍然在自然哲学(海德格尔所说的现存性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思辨的认识论框架中谈论自由和道德。但是,康德由思辨向实践的转变是有问题的,至少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想象世界有一个始因,甚至人类可以在认知意义上将世界把握为一个整体,但却不具有道德归责需要的实践自由。
阿利森(H. Allison)也承认“第三组二律背反本身侧重讨论宇宙论诸理念(总体性诸理念),似乎与人们一般所谓的’自由意志问题’ 没有什么直接联系”。(3)Henry E.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但是,他建议我们将第三悖论中正反题体现的宇宙论争执(cosmological conflict)解作“两类行为能力模型或两种行为能力概念之间的冲突,这些模型或概念能够并且在哲学史上已被应用于世界中的理性存在者和一个世界的超验创造者之上”。(4)ibid. p.11.这一解释显然可以在康德那儿找到根据。在证明了一种世界之外的先验自由的可能性之后,康德随即指出,“我们现在也被容许在世界的进程中间让种种不同的序列在因果性上自行开始,并赋予这些序列的实体以从自由出发的能力”(A450/B479)。接下来就是那个著名的例子,即我可能完全自由而不受自然原因的必然规定性影响就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这“就绝对地开启了一个新的序列”(KrV A451/B479)。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先验自由如此侵入自然进程,那么,正如贝克指出,就没有康德同时要肯定的自然的合法则性和一致性(uniformity);反之,先验自由就只是“空洞的宣称”,也没有任何道德相关性。(5)Lewis White Beck, 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1960) 192.对于这一贝克式的质疑,康德的策略是——正如上面的例子显示的那样——将先验自由直接归属于具有决定能力的理性行动者。因为人不仅是感性的现象界的存在者,而且同时是本体界的具有知性性格的存在者。就其作为本体界的存在者而言,人被认为具有绝对的自发性或者说先验自由。显而易见的是,借助于人这样的理性行动者的概念,康德不仅中介了现象与本体世界,而且将宇宙论意义上的自由直接转化为理性与道德行为者的意志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先验自由可以直接被视为道德归责的根据。
然而困难在于,给予现象与本体界的分离是康德证明自由与自然相容的必要设定,也是其先验观念论之核心。我们既不能将行为归责于作为现象界存在者的人,因为这样的存在者并无自由;也不能归责于本体界的存在者,因为这一存在者与现象界发生的行为没有可以被确认的关联。(6)Lewis White Beck, “Five Concepts of Freedom in Kant,”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ed. J. T. J. T. J Srzednick & Stephan Korne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Dordrecht, 1987) 42-43.所以,在伍德(Allen Wood)看来,如果要将先验自由视作行为归责的根据,我们就必须把永恒的属性不仅归于上帝,而且赋予每一个道德行为者。 也就是说,必须假设我们具有上帝一样的自由,因为现象界是一个按照自然因果法则紧密联结的领域,所以,每一单个存在者的本体界的选择只能是对一个可能的世界的选择。(7)Allen Wood, “Kant’s Compatibilism,” Self and Nature in Kant’s Philosophy, ed. Allen W. Wood (Ithaca/London 1984) 89-93.换而言之, 我的永恒选择, 如果要对我的任何一个单一的行为产生影响, 它也必然地同时影响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其结果是我必须不仅对我自己的行动及其直接后果负责,而且必须以某种方式为世界历史上的一切,甚至包括我出生前发生的事情负责。但是,要求每个人为一切实践负责最终会导致责任概念的废除, 从而导致我们普通道德评价体系的崩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沃克(Ralph Walker)指出:“我应当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让伏尔泰感到震惊的里斯本地震受到谴责,并且甘地应当为乌干达独裁者阿明的暴行同等地负罪。”(8)Ralph Walker, Kant: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London 1978) 149.
与伍德不同,对于阿利森而言, 即使我们认可人具有知性性格,并且将宇宙论意义的自由视为一种行为者的模式,我们事实上仍然有必要区分两类自由模型,即人的自由与神的自由。前者就其自身而言就独立于自然原因性,但后者却是世界中的存在者,虽然与动物性存在者不同,不受到自然因果性的决定,却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性欲求从而也是自然因果性的影响。在阿利森看来,伍德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类实践理性的特殊性,从而将宇宙论意义上的自由与道德预设的实践自由混为一谈。(9)Kant’s Theory of Freedom, pp.47-51.但是,阿利森也承认, 伍德的解释确实能够在康德那儿找到足够的文本根据。事实上,伍德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将康德从思辨形而上学出发建构实践和道德哲学的思路推向极致,以至于得出了某种荒谬的结果。(10)这一思路的一个特质即是等同作为思辨概念的宇宙论意义的始因与人具有的自由意志,或者说等同神与人(就其作为本体的存在者)所具有的自由。
当然,虽然提出了先验自由的观念,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却只着眼于一个有限的目标,即证明其可能性。作为思辨理性的理念,先验自由只是一个悬拟的(problematic)概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甚至表明causa noumenon (作为本体的原因性)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设想,“但却是一个空洞的概念”(KpV 56)。只有将其与道德法则相结合,方可赋予其实践意义上的实在性。所以,只有当道德法则在《奠基》中得以建构之后,对先验自由及其道德意义的界说才有可能。尽管如此,在《奠基》第三章,康德仍然延续了从思辨到实践的路径,并试图从“第一批判”给定的自由的因果性,即作为绝对自发性的先验自由及其先验观念论预设对道德法则做出演绎。具体而言,这一演绎所要证明的是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即人作为有理性的感性存在者因其理性已经被置于道德法则之下,并因此能够将法则(定言命令)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理由和动机。整个演绎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确立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故而被阿美立克斯(Karl Ameriks) 称为“朝向自由的论证”(Argument to freedom)。(11)Karl Ameriks, Kant’s Theory of Mind,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4.在此基础上康德在第二部分从积极自由推导出道德法则对人的有效性。因为积极的自由被等同为自律,而道德法则在《奠基》前两章已经被界说为自律的法则,即理性自我普遍立法的结果,所以,一旦将自由解释为自律,从自由到法则的演绎就水到渠成了。所以,真正的困难在第一部分,即从消极的自由转到积极的自由,或者说从绝对的自发性转到道德自律。 在这一部分,康德首先试图证明我们能够把自由的理念赋予每一个有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在康德看来,这样的理性存在者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设想一种理性,它就其判断而言意识到自己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接受指导,因为那样的话,主体就不会把对判断的规定归于它的理性,而是归于一种冲动。”(GMS 448)
但是,从这一理论判断活动的自由,我们并不能直接推出这一理性在实践上是自由的,也不能证明康德的理性意志的观念“不只是一个幻影”。(12)在分析上述《奠基》引文时,Ameriks指出这一论证比康德早先的“讲座”更紧密地结合了思想(thinking)与意志(willing)。如果一个存在者,由其具有思的能力而拥有一个自己的意志,那么这可以被认为意味着他的判断行为(像所有其他行为)必须在他身上有其绝对的来源。但是,这仍然不能表明这样一个理性意志的理念不只是一个“幻影”。Kant’s Theory of Mind, p.203。当然,康德随后也承认“我们无法证明自由在我们自己里面和在人性里面是某种现实的东西;我们只是看到:如果要把一个存在者设想为理性的、而且就其行动而言赋有因果性的意识的、亦即赋有一个意志的,我们就必须预设自由”,因此 “好像我们在自由的理念中真正说来只是预设道德法则,亦即意志本身的自律原则” (GMS 449)。但是,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循环,因为“只有当自由被看作自律而非仅仅在否定意义上的先验自由,我们才可能从理性自由的前提导出道德法则”。(13)Kant’s Theory of Mind, p. 204.换而言之,作为道德法则推导前提的自由本身必须依赖道德法则获得规定。为了克服这个循环,康德重新引入了两个世界,在此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区分。在康德看来,我们虽然就“纯然的知觉和感觉的感受性而言把自己归入感官世界,但就在它里面可能是纯粹活动的东西(根本不是通过刺激感官,而是直接达到意识的东西)而言把自己归入理智世界”(GMS 451),并因此是自由的。但是,此处的自由,即纯粹活动的东西只是理性的绝对自发性,而不是自律,所以,从自发性到道德自由(自律)的转变仍然需要预设道德法则。换而言之,如许多评论者所见,即使引入两个世界或立场的区分,康德仍然没有如其所欲的那样逃脱上述循环。就此而言,康德在此的演绎,即他从思的自发性去证明理性行动者具有的自由的努力是失败的。
(二)
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一批判”以及《奠基》中,康德尝试了一条联结思辨与实践的路径,作为联结点的即是自由的因果性(先验自由)的观念。自由一方面被界说为世界的始因,并因此是绝对的自发性,在世界之外,全然不受自然法则的影响。另一方面,自由又被视为人这样的理性行动者具有的自由意志,人的行动虽然不受自然因果性的决定,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欲求的影响。所以,为了将绝对自发性赋予人这样的理性行动者,康德就不得不求助于其先验唯心主义,即两个世界的区分,这一区分最终落实为人的知性性格与感性性格之间的区分。一旦将先验自由或者说自由因果性赋予理性行动者,康德就可以——正如他在《奠基》第三章所做的那样——从自由的因果性推导出道德法则,因为因果性同时被规定为法则性。由于人同时是感性的存在者,给予本体界是现象界基础的设定,源于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就对人而言呈示为绝对命令,这样康德就借助自由概念证明(演绎)了道德法则,并回答了定言命令如何可能的问题。但此处的自由却已经不是“第一批判”中的始因,也不是认知与理论思辨具有的自发性——两者的对象都是自然,即使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而是与道德法则相联的自律。就此而言,自由的因果性并未如康德设想的那样成功地联结理论思辨与实践领域,其结果是康德不仅未能成功地完成从自由(自发性)出发对法则的演绎,而且也没能澄清先验自由的意义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这一自由是道德的根据。
某种意义上,康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给出了一个与《奠基》反向的演绎。这一演绎的起点不是自由,而是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康德将此意识称为唯一的理性事实,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推导出自由的现实性。对于何以要做出这一与《奠基》不同的演绎,康德给出了如下的解释,我们对无条件实践的东西的认识不可能从自由开始:“原因在于我们既不能直接地意识到自由,因为它的最初概念是消极的,也不可能从经验推论到自由”(KpV 29)。
在一些康德评论者看来,这一替代演绎甚至都很难被称为一个演绎。与之相比,《奠基》中的演绎虽然有种种问题,至少还具有一种类演绎的形式。即使将其看作一种新的演绎尝试,多数评论者也认为它并不比《奠基》中的演绎更有信服力。如果说《奠基》中演绎的问题在于作为起点的自由,那么,此处演绎的问题则在于对理性事实的界定。(14)关于理性事实,康德给出了多种界说,贝克就区分了六种不同的界说,并将其分为客观(主要是道德法则或自由)与主观(即对法则等的意识)两个类别,参阅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pp.166-8,以及Allison对于这一区分以及对贝克在fact for reason 与fact of reason之间所作的区分的评论,见Kant’s Theory of Freedom, pp.232-233. 笔者认为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没有与对法则的意识分离的法则,所以,这些区分与其说澄清不如说是模糊了这一概念。问题在于什么是康德宣称理性事实的现象学基底,或者说什么是这一理性事实指示的原初现象和经验。与《奠基》类似,康德又一次试图从我们对纯粹的理论原理的意识来证明我们“能够意识到纯粹的实践法则”(KpV 30)。尽管如此,这并非康德的主要论证,在对理性事实的说明中,康德更多地求助于我们的道德经验,理性行动者不仅有自己的行动的准则或者说理由,而且总已经同时意识到法则,所以一个把睚眦必报视为自己的准则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准则与法则的冲突。(KpV 19)当然,这种冲突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自然欲求之间,但是,康德认为我们事实上可以意识到两种冲突的不同性。某个人可能认为自己的淫欲是无法抗拒的,然而,康德指出,如果在他前面竖起一个绞刑架,在他享受过淫欲之后马上把他吊在上面,“他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不克制自己的偏好吗”?但如果一个君王以一种毫不拖延的死刑相威胁,要求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提供伪证来诋毁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此时无论他对生命的热爱有多大,他是否会认为他有可能克服这种热爱呢”(KpV 30)?自然欲求之间的冲突的解决服从的是审慎原则,这一原则的最终对象是幸福,而生存则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所以,以生命为代价去满足一个当下的欲求显然是不明智和非理性的。与此不同,道德尤其是正义义务却是一种绝对的要求。这当然不是说这个人在此情形下必定会拒绝做伪证,而是说无论他如何选择,他都会意识到他应当这么做,都会感受到法则压倒所有自然欲求的绝对约束力,从而认识到他在自身中具备的一种越出所有自然欲求的能力和自由。这一自由向他表明他不只是自然的存在者,完全受制于自然欲求——其总和是依托于自然生命的幸福。
当然,一些评论者可能认为上述经验的例证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并不足以证明理性事实,即我们对法则意识的普遍性。但这类质疑事实上混淆了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事实上,康德在此诉求的并非单纯的经验例证,而是对普遍的道德经验(现象)的反思,基于这一反思,康德给出的其实是一个现象学-先验论证。(15)Allison 也指出上述例子虽然出现在正式的演绎之前,却对我们理解演绎具有关键意义(Kant’s Theory of Freedom,p. 241), 但由于否认道德经验(moral experience)的相关性,他并没有对这些例子何以重要做出解释。与Allison 不同, Grenberg 认为康德在此与其说是引入一些例证,不如说是在诉求于我们亲身(first-personal)的道德体验, 是对我们共有的道德经验的现象学反思(参阅Jeanine Grenberg, Kant’s Defense of Common Moral Experience: A Phenomenological Accou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art III 尤其,pp. 162-185)。在Grenberg看来,我们对其中包含的现象学要素的忽略是因为我们在过于狭隘的意义上即对自然物知觉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但是“对物体的经验只是一种可能的经验”,我们仍然需要“开放出诉求于亲身的现象学经验的可能性,以启动实践哲学” (ibid. p.116)。 我们在此试图在Grenberg对上述例子的现象学解读的基础上指出其中同时包含了一个先验论证,以纠正Grenberg过于强调日常道德经验的偏颇。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与孟子对舍生取义的著名解释相比照。《孟子·告子上》中如此写道: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所欲莫甚于生,则几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与上面引述的康德的例子相似,孟子诉求的是我们共享的经验。基于对这一经验的反思,孟子与康德一样区分了自然欲求之间的冲突与欲求和道德(义)的冲突,并且以一个类先验论证来表明如果舍生取义不可能,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也就没有道德可言。所以,如果有道德,那么就证明我们具有舍生取义的能力和自由,并且,这种能力人皆有之,尽管只有少数人才可能践行之。当然,与康德不同,孟子既没有(也无需)求助于先验观念论,更没有求助于思的自发性, 这也表明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道德的途径来通达康德所言的先验自由,因为正如康德自己在“第二批判”指出,“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条件(ratioessendi), 但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知条件(ratiocognoscendi),因为如果不是在我们的理性中我们早就清楚地想到了道德法则,我们就绝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自由这样的东西(尽管自由并不自相矛盾)”(KpV 4 脚注)。
换而言之,并非我们的判断和思辨的能力,而是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才使我们确信自己的自由,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一种第一批判式的演绎——这一演绎的目标是通过我思或者说先验统觉将异质的知性范畴与感性所予联结起来,但先验自由就其根本而言是道德要求的自由,而道德则必须预设这一自由。 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可以说“自由与法则是彼此相互回溯的”(KpV 29)。但是,这并非如大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先验自由就等同于自律。如果先验自由在其自身已经是道德自律,那么,康德所言的自由的最初概念就是消极的,所以我们不能从自由开始的说法就很难理解了。事实上,如果与道德分开,那么先验自由是一种独立于自然欲求行动的能力,并且作为行动能力而具有实践意义上的自发性。但这一能力并不自在地是道德的,(16)我们或许可以在与始因(第一因)的类比中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依循阿里森将始因理解成一种行为者模型的话。除非我们已经假设这一神圣的行为者(康德有时直接将其与上帝相联)的善(道德)性,那么,始因并不因其不受先在原因的制约,或者说因其绝对的自发性而是善(道德)的。与此类同,人类也并不因为其具有的绝对的自发性或者对自然欲求的独立就是善的,善的可能性毋宁说是在于人所具有的对道德法则的绝对约束力的意识。唯有道德行为,即将法则视为超越一切自然欲求的行动理由的行为才赋予自由以道德意义,也即是说才能够将否定的自由转为肯定的自由(律)。这当然不是说,先验自由可以与道德相分离。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在概念上有必要区分否定意义上的先验自由与肯定意义上的道德自由(自律)。(17)贝克在他的《康德的五个自由概念》中就区分了道德自由和先验自由,并指出“必须解开自由与道德(积极的道德价值)之间的标准(criteriological)或分析性联系”。Five Concepts of Freedom in Kant, p. 38.因为如果先验自由被直接等同为自律,那么,正如康德同时代的评论者已然发现,我们就不可能自由地犯错,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追责错误。(18)参阅Carl Leonhard Reinhold, “Eroterungen des Begriffs von der Freiheit des Willens,” Materialien zu Kants “Kritik der pratischen Vernunft,” Rudiger Bittner an Konrad Cramer, eds. pp. 252-74.当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对这一质疑做了回应。首先,康德在意志官能(faculty of volition)中区分了意志(wille)和任性(Willkür)。前者等同为纯粹理性(法则),与行动准则而非行动相关,故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后者则类似于选择自由,可能将法则或者欲求纳入自己的准则,所以,“只有任性才能被称作自由的” (MS 226)。大部分评论者都认为这一区分成功地回应了上述质疑,因为行为是任性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可以归责于行为者。但是,将自由仅仅赋予任性事实上排除了先验自由,所以,康德又不得不求助于他的先验观念论,即现象与本体界的区分来把任性的自由,或者说选择的自由界说为现象界的自由。这一仅从从现象观点来看的自由,不能用来“界定他作为理知存在者的自由”(MS 226)。由此,从本体界的观点看,选择的自由事实上又被排除了,其结果是错误追责问题并没有得以解决。(19)康德在《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表明:“任性的自由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属性,任何动机, 无论是自然欲求还是被理性判断为动机的道德法则,除非人能够将其纳入自己的准则(即将之变成对他自己而言的普遍规则,并按此行动),就不可能成为行动的根据”(Rel. 24), 因为任性是一种可能遵循与违背法则的自由,所以,康德认为我们应当为自己的过错负责。但是,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虽然仍然坚持只有任性是自由的,却否认自由地违背法则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可能自由地犯错,所以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但是,如果我们将先验自由看作一种独立于自然欲求的能力而不直接等同于自律,那么,选择的自由可以被视为这一自由的不完美的实现,因为即使选择的自由也至少需要预设对于自然欲求的相对独立性, 而自律是这一能力的道德(完美)实现,因为自律意味着我们自由地以道德法则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并因此完全独立于自然欲求的制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可以说消极的自由能够转化为积极的自由。当然,这一转化不是概念意义上的转化,而是道德的转化,即是通过我们道德行动的转化。
(三)
如同上文所见,在先验自由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康德哲学中包含了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是从思辨到实践的路径,依循这一路径,先验自由被界说为世界始因,即一种开启一个因果系列的绝对自发性,这一始因是思辨理性将世界把握为一个整体必须预设的认知条件(epistemic condition)。所以,先验自由或者说无条件的条件首先在与为其所规定的有条件的(conditioned)世界(自然)的关联中获得界说。如此被界说的自由显然首先是一个思辨形而上学概念。
这一自由同时被用来界说自由意志,即作为理性行动者的自我所具有的自由。这一自由意志在与始因的关联中也首先被界说为绝对的自发性,这就解释了何以《奠基》中的演绎采取了从“我思”甚或认知的自发性推导出道德法则的方式。这一演绎在某种意义上继续了“第一批判”联结作为思辨形而上概念的先验自由与作为道德归责基础的自由的努力,而这一演绎的失败也就凸显了思辨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所以,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转向了一种道德的路径。依循这一路径,自由首先在与道德法则的关联中获得界说,当且仅当我们将道德法则视为自己行动的规定性根据时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先验意义上是自由的,即具有独立于所有自然欲求(从而是自然因果性)的能力;同时,这一否定意义上的自由只有在与道德法则的关联中才被赋予肯定的,即道德意义。由此,自由首先是道德(实践)而非思辨的概念。另一方面,先验自由或者说对自然的独立性又是道德必要的预设。因为唯有当理性行为者具有这一独立性,道德法则才可能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即能够凌驾于我们的一切自然欲求之上。这一自由同时也是道德归责的必要条件,因为正如康德在“第二批判”中指出,倘若我们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欲求的规定,由于自然欲求受制于自然必然性,我们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因此也就不能因为我们的行为而被归责。因为道德法则之区别于审慎的考虑之处就在于其所具有的绝对约束性,所以,道德,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就证明了我们在先验意义上是自由的,可能完全独立于自然因果性,仿佛我们不只是自然世界的存在者,而且同时是超感性世界的存在者。就后一种存在方式而言,我们服从的不再是自然的法则,而是自由的,即纯粹理性颁布的道德法则。因为正是通过对这一法则的服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所以,康德指出,“真正来说正是自由概念,在纯粹思辨理性的一切理念中,唯一在超感性事物的领域里,即便仅仅就实践知识而言,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扩展”(KpV 103)。
换而言之,并非关于世界的始因的思辨,而是道德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超感性的领域,尽管我们并没有对其的理论知识。由此,借助于自由概念,康德指向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但这一形而上学不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应当恰如其分地被称为道德的形而上学。事实上,通过强调自由(与理性理念)的不可知性,康德同时限制了思辨的形而上学。
当然,这两种路径在康德那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即使在先验自由主要被界说为思辨理性理念的“第一批判”中,实践的旨趣仍然构成了对包括先验自由在内的理性理念的首要的辩护。因为在康德看来,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些理念,即否认一个与世界有别的原始的存在者、否认灵魂的不朽性以及我们具有自由意志,那么“道德的理念和原理也就丧失了一切效力,与构成其理论支柱的先验理念一起作废了”(A468/B496)。诚然,康德也诉求于思辨的旨趣,(20)除了实践与思辨的兴趣外,康德还以通俗性优点对正论做了辩护。这一辩护的大致意思是大多数人更加愿意接受这些正论而不是反论。这在康德身处的基督教文化主导的时代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们这个后形而上学时代,这些理念显然不再具有任何通俗性的优点。指出这一点当然不是要以此驳回康德的论证——毕竟这在康德那儿也并非其辩护的要点,而是表明在康德那儿宗教(形而上学)与道德不可分离。所以,道德不仅被置于形而上领域,而且对其的辩护也首先是形而上的。但是,这是一个相对较弱的认证,因为康德也承认否认理性理念的经验主义“也给理性的思辨旨趣提供了好处” (A468/B496)。并且,《奠基》第三章的演绎虽然不甚成功,但至少表达了康德联结自由与自律以及自律(即道德)的法则的主导意向。另一方面,诚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在道德路径占主导的“第二批判”中康德仍然试图以我们对理论原理的认知来类比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所以,虽然康德确乎强调了实践与理论思辨的区分,但贯穿其思想的是思辨与实践理性统一性的命题,这一命题也构成了康德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核心。当然,这一形而上学已经基于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性审查的基础之上,并因此有别于为康德所拒斥的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尽管如此,从先验自由在其中首先得以界说的辩证论观之,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并非是反形而上学的,毋宁说是为了给形而上学,即诸理性理念寻找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所以,并非偶然,先验自由首先在一个宇宙论问题的背景中引入,并通过等同纯粹理性与自由意志来扩展到实践领域,这也解释了康德何以会在《奠基》中尝试从思辩的自由去推导出道德自由,即自律,从而推导(演绎)出道德(自律的)法则。当然,在“第二批判”中,康德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这一路径,而转向以道德来解释先验自由,其结果是自由作为道德的可能性条件首先呈示为道德所预设自由。但是,这一道德意义上的自由仍然被看作是理性的——不仅实践而且也是思辨理性的理念。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在“第二批判”的辩证论部分康德通过纳入被设定为实践理性最完备的对象,即至善再次辩护了作为理性理念的上帝与不朽的灵魂的观念。与先验自由一样,后两者也不只是实践理性,或者说道德的必要预设,而且同时是思辨理性的理念。即使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对其没有任何知识。但“却总的来说(凭借它们与实践的东西的关系)给予思辨理性的理念以客观实在性,并使思辨理性对于它本来甚至不能自诩哪怕是仅仅主张其可能性具有权利”(KpV 132,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换而言之,康德对先验自由的道德阐释至少部分地是为了辩护纯粹(无论思辨还是实践)理性理念,即确立其形而上学。与此相应,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区分也被归结为理性与知性(原则),或者更为清晰地说,形而上与形而下(经验)之间的区分。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序言中指出,我们应当按照其所依循的原则,即自由或与其相对的自然原则来区分道德(实践)与理论(自然)哲学,由此,我们通常归入实践哲学的一些学说因其主导的是自然原则(知性原理)而应当被归入理论哲学。(KU 172-73)
与康德不同,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则更多地以对象区分理论与实践。理论所研究的是不变的存在(者)或者自然规律,而实践哲学研究的是变动不居的人事,所以,两者理应有不同的方式,也要求不同的智慧,即理论智慧(Sophia)与实践的智慧(phronesis)。(21)当然,在明显地受到柏拉图影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亚氏也将最完美的幸福(道德)界说为思辨生活的幸福。尽管如此,亚氏随即表明人的幸福,即道德的最高目的首先在于合乎德性的活动,思辨或者说沉思的生活更多的是属神的幸福。与康德在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过于形而上的区分相比,亚氏的区分显然更切合我们的日常经验,而且也更具有现象学意蕴。因为意义是活动(noesis)与对象(noema)关联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关注对象的特殊性。而康德的区分看似高妙,却将道德更多地置于思辨形而上的框架之中,不仅与其他在康德看来只是经验层面的实践相隔离,而且——至少在自由问题上——与我们的道德经验或体验相割裂。由于自由原则被界说为自然原则的对立面,自由与自然,包括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的自然面被完全割裂开来,自由作为本体原因性因此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其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影响总是在现象界发生的行为都是可质疑的。当然,康德在“第二批判”中将自由与道德结合起来,其所诉求的——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显明——事实上是我们的道德经验,而不是超经验的“理性事实”。换而言之,先验自由是我们的道德经验所指示的自由,这当然并不否认自由也是我们认知活动的一个要素。但是,这一认知活动中的自由或者说自发性必须在与其相关的活动中得到界说,而不是被直接视同于道德必须预设的自由,也不能被视同为实践行动包含的自发性。
事实上,在《奠基》的前两章,康德很明确地将我们的日常道德经验,尤其是我们的义务意识作为其道德学说的建构的起点。当然,康德的道德学说并不是对芜杂的日常经验的描述,而是通过哲学反思将其提升为道德原则,即定言命令,并进一步将原则与自由(律)的理念相关联。对于康德而言,我们之所以可能自由地服从道德原则,是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理性自我立法的结果,由此,康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由与自律的伦理学。换而言之,自由是在与道德法则的关联中被界说,唯有通过法则,自由才获得其肯定和道德的意义。所以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道德(实践)的自由,有别于理论判断中体现的自发性,也不能从后者被推导出来。这当然不是说理论与实践没有关系,作为人类活动,两者当然互相关联,我们在具体情境中履行道德义务自然就要求对这一情境中诸事实要素的理论认知,同时,我们对自然的研究也经常受到道德考虑的指引和限制。尽管如此,道德的对象是人的欲求,而理论思辨的对象是自然,两者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此相应,自由属于道德领域,而因果性则属于自然领域。或者更为清晰地说,自由是实践的(先天)构成性要素,自然因果性则是认知的(先天)构成性要素。在认知与思辨领域,正如康德自己所见,自由最多只有范导性作用,即对我们的自然研究包括理论思辨做出某些指导和规范。事实上,如果我们将道德与自然看作两种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不是将其置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即本体和现象界,那么我们就可以无需“将自由与自然必然性归结到同一个行动”,也无需“被迫将科学归于(在本体论上具有贬义性的)显像域,将伦理分配给(在认识论上具有贬义性)的本体域”。(22)Five Concepts of Freedom in Kant, pp. 46-7.